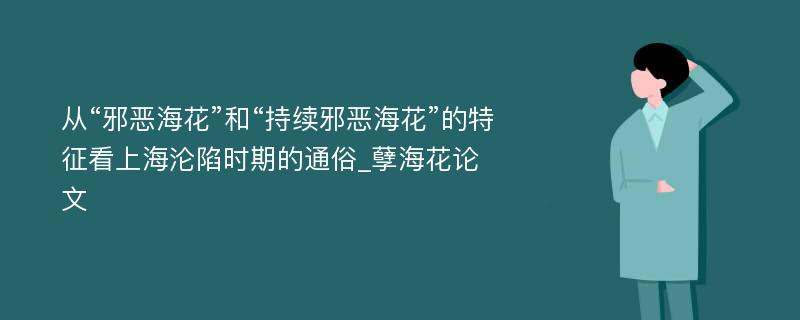
从《孽海花》《续孽海花》人物谈 看上海沦陷时期的掌故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孽海论文,掌故论文,时期论文,人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9)06-0152-06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日军控制了上海华界并扶植傀儡政权实行高压统治。在近八年的沦陷岁月里,上海的杂志陆续刊登一些“清谈”“掌故”文章。这一现象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随即“进驻”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之后,更为明显。或许由于“掌故”文章给沦陷区带来了消极“清谈”气,或许因为主要刊载地——《古今》杂志不名誉的背景①,更或许因为部分研究者与汪伪政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以往研究这一群人及其“掌故”作品时,往往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②。评价时要么将它们简单地看做是“清谈风月”、“无病呻吟”的消极之作,更多的则是干脆将其打入“汉奸”言论的另册。而对于这些文章究竟研究些什么,作者的生活背景怎样,他们是否仅仅是消极清谈,其中体现了怎样的复杂心理等问题却没有具体而准确的答案。上海沦陷时期涉及谈“掌故”的文章数量很多,仅目前搜集到的就有近百余篇,且大多数发表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史料众多,固然能展示历史的全貌,但逐一分析也容易流于空泛。因此,本文希望借助当时热烈讨论的话题——关于《孽海花》与《续孽海花》的人物考察——从微观角度进行分析,同时结合其他掌故文章的内容与写作背景,找出作者们“说什么”、“不说什么”背后的原因,总结其特点,以回答上述问题,并就教于方家。
一、对《孽海花》与《续孽海花》的关注
上海沦陷时期,一些文人学者自称“掌故爱好者”,对历史旧事、人物逸闻尤感兴趣,甚至常常从历史角度出发,对同一个文学作品或历史事件展开讨论,抒发自己的感慨。此时较为集中的研究对象,有如李慈铭和他的《越缦堂日记》、沈三白和《浮生六记》等,而其中影响最大、涉及研究者最多的,莫过于从历史角度对清末小说《孽海花》及《续孽海花》的探讨。
从1943年7月到1944年7月,仅仅一年时间,《古今》就连续刊登了十余篇探讨《孽海花》及《续孽海花》的文章,作者有纪果庵、冒鹤亭、瞿兑之、周黎庵、文载道等,其中除瞿兑之身处北京外,其他人都是当时沪、宁地区的文史掌故名家。
《孽海花》是清末人曾朴(1872-1935)所作的长篇小说。曾朴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充满动荡与变革的时代,他经历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军北伐等历史大事,并与部分亲历其中的晚清官员、文士有所往来,这些都成为他创作《孽海花》的生活基础。该书以金雯青、傅彩云(影射洪钧和赛金花)的故事为线索,描写当时官僚、文士的活动,反映了清代同治中期至光绪后叶近三十年的政治和文化变迁。由于作者的经历复杂,对历史事件的描述既有一定的真实性又富趣味性,引起了读者的共鸣,使该书畅销一时。
抗战时期,曾朴的好友燕谷老人(即张鸿)在此基础上创作了《续孽海花》一书,主要描绘清末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两大历史事件。1943年底,上海真善美书店将原来在《中和月刊》上连载的《续孽海花》,由瞿兑之校订后,集结成书出版,并由古今出版社代售。《续孽海花》的广告称“手此一编,不啻一部清末稗史也”[1]22,其影响虽没有《孽海花》大,但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关于两书的讨论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二、“谈”与“考”
《孽海花》及《续孽海花》两书的人物原型及事迹是研究者们考证、讨论最多的问题。有趣的是,这些文章的标题大都不约而同地带有一个“谈”字,如《〈孽海花〉人物漫谈》[2]、《〈续孽海花〉人物谈》[3]、《〈续孽海花〉人物琐谈》[4]等,其他如《〈孽海花〉人物世家》[5]也可算是“谈”的扩充。这些探讨历史人物的文章无一例外的没有用“考”作标题,这与同时期其他史学文章如《司马相如著述考》[6]、《洪大全考》[7]来说,显然不同。
为什么会有这一差别?我们不妨看看掌故文章里都“谈”了些什么。
纪果庵于1943年7月发表了《〈孽海花〉人物漫谈》一文,是《古今》杂志较早涉及这一问题的文章。
文章首先介绍《孽海花》的主人公金雯青,其人物原型即为清末洪钧。纪果庵对洪钧“因中俄交界图失官”一事,“颇堪同情”。文中引用清人笔记《国闻备乘》中关于洪钧出使俄国的记载:当时洪钧“任兵部侍郎”,“方出使俄国,亦好谈舆地”,俄国“乃诡为一图,悉圈我瓯脱,阑入俄界”。洪钧不了解实际地形情况,“见俄图大喜”,还以为是“海外秘本”,“出重金购之,译以中文,自作跋语,名曰中俄交界图”。俄国遂借机按照地图所标边界出兵侵占中国领土,英国对此有意见,俄国便“旋割帕米尔南疆与英和”。中国的领土被英俄瓜分,却还“不能与争”,“遂丧地七百里”。这一争界事件使洪钧难堪不已,他“闻边事棘,始知受欺,且惧谴,疾益剧,遂卒”。对于野史笔记中记载的这一段往事,纪果庵又引用《清史稿》中的相关记录加以佐证,说明确有其事,并认为《孽海花》中的相关描述“当是事实”。
文章还谈及张謇参加科举的轶事。张謇“文名宿著,翁潘两相国久欲得为门下士”。纪果庵引用张謇的儿子张孝若为父作的传记,叙述张謇“屡于会试时误认试卷”的趣事:张謇于“光绪十五年”参加会试,“总裁是潘公,他满意要中我父,哪晓得无端的误中了无锡的孙叔和,当时懊丧得了不得”。第二次会试,“场中又误以陶世风的卷子当作我父的中了陶的会元”。到了第三次会试,“错的越发曲折离奇”,考官满场找寻张謇的试卷,最后却误中了“常州刘可毅的卷子”。纪果庵指出《孽海花》一书中谈到误判刘可毅试卷一事,却把主考官误作潘伯寅,实际上潘伯寅此时已经去世,小说中的描述并不符合事实。而书中大写误判时潘伯寅的“愤恨之状”,纪果庵推测可能是因为当年会试,曾朴“与张同遭误卷之事,或颇有所感而故将刘可毅丑角化邪?”③除上述人物外,该文还结合晚清社会政局的变化,介绍了《孽海花》中其他人物原型如张荫桓、赛金花、吴愙斋、宝竹坡、文廷式及张佩纶等人的经历及趣闻。
在此基础上,纪果庵又于1943年10月至11月,在《古今》上分三期连续发表了《〈续孽海花〉人物谈》,专门介绍《续孽海花》一书中的人物原型及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周黎庵则将《孽海花》人物原型的讨论进一步扩大。他于1943年12月在《古今》上发表《〈孽海花〉人物世家》一文,考察书中人物原型的“若子若孙”辈,如书中吴愙斋的后人吴湖帆、吴颂皋,以及张佩纶的后人张爱玲等等。1944年3月,他写下《记〈孽海花〉硕果仅存人物》[8]13一文,介绍冒鹤亭的生平轶事。冒鹤亭因本人就是《续孽海花》中的“顿梅庵”的原型,且熟悉晚清的社会变化,遂陆续发表《〈续孽海花〉人物琐谈》[4]1-4、《〈孽海花〉人名索隐表》[9]10-14等,对两部小说中人物原型的真名、籍贯、出身、职业以及事迹等加以详细考证,并列出人名索引。这些文章与前述分析的纪果庵的文章,在写作方式及风格上大体相类。
从上述研究《孽海花》及《续孽海花》人物的文章中不难发现当时掌故文章的几个特点。
其一,研究者往往知识丰富,有很好的旧学功底,且熟悉清末旧事。实际上,这群“掌故爱好者”在同时期还写了大量的关于清末民初人物和逸闻的“掌故”文章,如《记章太炎及其轶事》[10]、《谈纪文达公》[11]等等。他们之所以钟情于清末历史与其生活经历分不开。一方面,文人学者们大多在战前拥有比普通人更好的生活环境、更多接触上层人物的机会,有些人还是世家大族子弟,又有家学渊源。如纪果庵自称与纪晓岚同族,冒鹤亭是明末冒辟疆的后人,周越然既是晚清秀才又兼长西学等,他们在写作时常常文白夹杂,喜用甲子纪年,展现了他们深厚的旧学功底。另一方面,他们对清末民初的社会巨变有所了解甚至亲身经历,因此在作品中总不知不觉地流露出对清代盛况的怀念,对清朝灭亡的态度是痛其不幸,怒其不争。
如周黎庵在文章中就常常流露出对清代社会的留恋和对旧日文士的向往之情,难免给人一种消极复古的印象,他为此解释道:
我为了喜欢谈过去,若干年前很遭一些人的谩骂,以为是骸骨的迷恋,大大要不得。实则并不甚然,我无论怎样落伍,也决不会放弃了现代的文化而去爱慕豚尾补褂。事实上是同光之际,确有使人值得回忆与缅怀的地方。那时候的制度,当然在近日是不值得一文了,唯一可以推崇的,便是那时的人物,诗酒风流,不用说了;即使论傻气与憨劲,也是令人所望尘莫及……现代中国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成就,还不能不归功于那时的一些人们所撒下的种子,因之,我确乎有爱慕他们的热诫。然而,同光风流,已邈若山河了,倘然有机会能和那时硕果仅存的遗老谈谈,那是如何使人高兴的事![8]13
尽管周黎庵一再申明自己不是要“放弃现代文化而去爱慕豚尾补褂”的“落伍者”,但言语中对前代文士的“推崇”与“爱慕”却无法遮掩,且认定:“今日之视同光,犹同光人物之视乾嘉朝士,而流风遗韵,邈不可复得,为之掷笔三叹!”[5]20这也许正是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写的文章给人以“遗老”气的原因之一。纪果庵也认为今日知识分子的专业水准不及清代,“吾见今日之好为名士者,徒以片纸只楮,一诗一词自鸣,记问既丑,根底毫无”,因而发出“以较同光,相去远矣”的感慨[2]20。
其二,在研究方式上,常常对传说、佚闻加以收录甚至作为论据,使文章较之专业的学术研究而言带有更多的传奇性和趣味性。
文人学者们会对“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12]46格外关注,正源于他们对正史的怀疑态度。如纪果庵曾在《〈续孽海花〉人物谈》一文中说道:
余虽嗜史,而深恶正史,翻阅清史,殆个人之履历表,官阶表耳,其余个性,固无所描绘,即事实之肯綮,亦不愿明言。昔人称墓志碑铭,为谀墓之文,披览史书,诚不知相去几许。(《清史稿》尚不如《碑传集》等所刊之文能尽委曲)所幸私家记载,往往详官书所不详,纪正史所不纪。而数十年来,以时事为背景之说部,迭出不穷……掌故之学,未窥门径。徒事挦扯獭祭,草为此篇。[3]24
纪果庵认为“正史”无非是个人的“履历表”、“官阶表”,既不能反映历史人物的性格,也缺少对历史真实性的探讨。而“私家记载”有时反而“详官书所不详”,能更真切、生动地描述历史细节,这也是他喜看“闲书”,爱谈“掌故”的原因之一。
正因为使用野史笔记杂谈,使掌故文章更具趣味性。纪果庵于1943年发表的《谈纪文达公》[11]一文,即体现了这一特点。作者通过后人谈纪晓岚的几则佚事,提出故宫收藏的《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并非纪晓岚笔迹的说法。关于这一问题,史学界其实早有考证。王钟翰先生于1937年4月23日在天津《大公报·史地周刊》上已发表过《辨纪文达手书简明目录》一文,详细考证了《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不是纪晓岚的笔迹。由此看来,纪果庵的观点并非新论,也缺乏严谨的论证,但值得肯定的是,他的文章能以说“故事”的形式为人们提供另一种历史知识的来源,使历史研究成果也能为普通人所接受,而并非仅仅局限于学术界,这也正是其不同于具有严格学术规范的历史研究的地方。
其三,在研究过程中,掌故文章很注意多种资料和证据的结合,但同时也因为研究者喜欢以野史笔记、甚至前辈师友的追述记忆作为考述依据,给研究带来了不准确因素。
一方面,掌故学者们对研究的真实性要求很高,认为文史掌故虽然常常以街谈巷闻为题材,但“绝不是无足轻重的‘街谈巷语’可比”的[12]46。瞿兑之对此曾说过:
通掌故之学者是能透彻历史上各时期之政治内容,与夫政治社会各种制度之原委因果,以及其实际运用情状。要达到这种目的,则必须对于各时期之活动人物熟知其世袭渊源师友亲族的各族关系与其活动之事实经过,而又有最重要之先决条件,就是对于许多重复参错之琐屑资料具有综核之能力,存真去伪,由伪得真……所以既称治掌故,则必须根据实事求是的治史方法才对。然而仅有方法而无实践的经验,也是不行的……所以掌故学者之职务,乃是治史者所不能离手的一部活辞典。[13]9-10
瞿兑之认为掌故学看似只是搜罗前代的遗老轶事,但要求研究者必须对当时的社会状况、人物关系、生活方式等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在考述的过程中,“存真去伪,由伪得真”,运用“实事求是的治史方法”,将书本知识与实践经验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掌故真实而生动地反映出历史的发展过程,成为“治史者所不能离手的一部活辞典”。瞿兑之的看法代表了当时沦陷区相当一部分文人学者的意见:研究掌故的人既要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又要有认真分析的精神;“掌故”文章并不是简单地叙述历史传闻,还要通过考察分析去伪存真,这样才能有裨于历史研究。
通过对《孽海花》人物原型锲而不舍的考证,甚至用多家说法互相印证,确实可以看到掌故研究者为让读者看到历史真实而生动的一面所做的努力。正如周黎庵所说:
一般对《孽海花》说部有兴趣的读者,大都寄重心于主角赛金花,即十年前逝世于故都的刘半农先生也是如此,而我们则不然,完全对于说部中的人物发生兴趣,对于赛金花,不但没有什么兴趣,而且还要从各家的记载中,指出原著人的荒谬,证明书中关于赛金花的种种风流绮事,都不大靠得住,这固然是大煞风景的事,但为了一点胡适之所谓“历史考据癖”的存在,便顾不得许多了。[8]13-14
另一方面,材料的来源及研究方式的特殊性决定了文史掌故的缺陷。如周黎庵在《〈孽海花〉人物世家》中重点考察小说中人物原型的后代,他从朋友处得知:“近顷有一女作家名海上者,有张爱玲女士”,系“南海人,方返自香港,其先人为《孽海花》说部中人物”。周黎庵主观认为,“晚清政局粤人而张姓者,舍张樵野侍郎荫桓无他人,即《孽海花》中庄小燕(焕英)”,由此推测张爱玲是张荫桓的后人。所幸,周黎庵不久即见到张爱玲本人,“乃询其籍贯,则河北也;询其父之外家,则合肥也”,这才“恍然”明白,张爱玲是张佩纶之女而非张荫桓后人[5]22。周黎庵的误差很快得到了纠正,而周越然在《辛亥文献》中的小差错更明显地体现了掌故研究的缺陷。《辛亥文献》辑录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几分文告,文章最后的“附录”部分影印了1912年“同盟会及国民党之收据”,其一为同盟会于1912年4月收到某人捐款的收条,其二是国民公党于1912年5月收到某人捐款的收据。周黎庵专门就第二份收据的落款:“国民公党理财科”,进行了解释:“当时之国民党,自称‘国民公党’,吾人应注意之。”[14]53这一解释实际上是不对的。1912年5月,国民公党还是一个独立的中间党派,同年8月,宋教仁为夺取国会多数议席,组织政党内阁,牵制袁世凯,遂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当时的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等中间党派,共同组成了国民党[15]153-161。因此,第二份收据应是“国民公党”收到的捐款收据,而非“国民党”,更不存在作者所说的国民党曾“自称”国民公党一事。周越然早年曾支持辛亥革命,也与革命党人有所来往[16],对武昌起义的历史深有感触,他认定“国民公党”为“国民党”显然是记忆误差。当然,并非所有的掌故研究都有不准确的地方,我们指出这一点,是想说明尽管研究者力求真实、全面地再现历史,但掌故的这种研究方式给它自身带来了不准确因素。
从上述研究特点中,不难理解为什么文史掌故常用“谈”为题了。其实,“谈”与“考”的区别正是掌故文章与历史学术论文的区别所在,同样是考述历史事件、评论历史人物,同样以反映历史真实面貌为目的,但二者在写作风格、研究方式上有着或多或少的差别。“谈”更为随意,更具趣味性,也更易流露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对生活的态度。
三、“慢声低唱”与“大声疾呼”
瞿兑之曾感慨到:在沦陷区“与其说空话不如说些实在的事,与其大声疾呼,不如慢声低唱,如其浓渲重染,不如轻描淡写”,而这“慢声低唱”正是备受批评的文史掌故的风格。
选择了“慢声低唱”,究竟是要唱靡靡之音还是民间小调,要孤芳自赏还是唱出自己的心声?瞿兑之为之道来:“今日的‘今’便是将来的‘古’”,“回忆也不是迷恋过去,而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能了解过去,便不能了解现在,不能了解现在,便不能发生未来的希望。”[17]27掌故研究者要在“慢声低唱”中表达自己对现实、对未来的看法,这一思想在《孽海花》的研究中可见一斑。
纪果庵曾感慨道:
吾辈中年读此书[按:《孽海花》],所喜者不在其文笔之周密瑰奇,而在所写人物皆有实事可指,兴衰俯仰,味乎碱酸之外,自与专注意赛金花之风流放诞,而为之考索本事,有见仁见智之分也。[2]13
又有:
若《孽海花》,固此中佼佼者,续书恣纵,虽不逮正,唯于戊戌以来三十年之朝局,大致可以得一轮廓矣。[3]24
这两段自述正说明纪果庵探讨历史传闻,是为了考述皆有“实事可指”的人和事,从“兴衰俯仰”中看到历史变迁、吸取历史教训,而不是香艳猎奇、挖人隐私。
瞿兑之“热心”《续孽海花》的原因就更明显了:
我为什么热心于这部书呢?
甲午戊戌庚子辛亥四次重要关头都在我的一生经历了。垂老而逢此地变天荒之世,抚今追昔,履霜坚冰,然后知光绪朝史事之关系重要……试想光绪初元清流的纠弹权贵,抨击阉竖,扶植纲纪,排斥佞谀,是何等义正词严,凛凛有生气。尽管动机不尽纯洁,尽管直言不被采纳。然而这种气概,是叫人有所忌惮的。国本所以不动摇,就靠在此……终觉得士大夫的公论不能轻易抹杀,士大夫的身份不能轻易摧残……大凡人在政治组织中,必须有所畏,畏公论,畏国法,这是最好的……戊戌是使人不畏公论,庚子更是使人不畏国法。不得已倒有一样,就是怕洋人……辛亥以后,一切的改革总不能抓住中心。虽然若干地方有些进步,总抵不过破坏之多而且大。
……我们所要看的不是一朝的史事,而是这三十年中国的国民心理的变迁。[18]5
瞿兑之之所以重视《孽海花》及其续作,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部历史小说,更在于它能反映“三十年中国的国民心理的变迁”,这与前述纪果庵的“于戊戌以来三十年之朝局,大致可以得一轮廓”如出一辙。可见,从历史小说中考察历史事实、总结历史教训是掌故研究者们共同的出发点。瞿兑之认为要使中国进步,即要维护“士大夫的公论”、尊重“士大夫的身份”,让人们“畏公论”、“畏国法”,才能使政治环境好起来,才能稳固“国本”。他的议论固然有书生意气,但维护文人的言论环境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瞿兑之认为辛亥革命的进步“抵不过破坏之多而且大”,近几十年的社会远比不上嘉道、同光时期,这一重古轻今的观点与徐一士、周黎庵等人有相仿之处。
文载道在评价《孽海花》时,则认为它“最进步的特色,就是对辛亥革命的同情与表扬,又因作书时还正处于清廷积威之下,故益感大胆而难能”,并且对于“修正版”中“对这些民族革命的渲染都删去了”表示遗憾,因为原本“保存了作者当时的最激进的思想”[19]24。显然,文载道的观点较之前述研究者来说是积极进步的。
由此可见,“慢声低唱”是要唱出作者心中所想,心中所系,而非简单的为考述而考述。他们在历史研究中常常流露出自己的思想感情。带着这些复杂的感情写作,自然不再是“清谈”了。给这些人扣上一顶“清谈”的帽子,称他们给沦陷时期的上海带来了一股“清谈掌故”风,这样的评价不够准确。
而最后的关键问题是,上海沦陷时期的“掌故”文章,在当时就常常被人批评是对时局无用的“清谈”,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人要选择备受批评的“慢声低唱”、“轻描淡写”?
瞿兑之自己回答道:“这些年来的世事却刺激我们太多了,酸甜苦辣各种味道迸上心来。……无论何处的人,无论在何种环境,都觉得不需要刺激而需要冷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似乎还是清茶淡饭最能养人最有真味。……凡是天然的平凡的一草一木一石在平常不值一顾的,在这时便都是我们所需的安慰”[17]26-27。这段话或多或少道出了掌故研究者的心声:之所以要选择“慢声低唱”,显然受到当时环境的影响。
纪果庵也谈到自己钟情于掌故的原因:“我所乐者不在狐鬼,而是掌故佚闻,也许是生丁乱世,未尝享过一天静福,所以喜欢听听古人的事以当大嚼耳。”[11]12-13与其说“生丁乱世”、“苦于人世尘氛”,而不得不投身于历史,享一享“静福”,是纪果庵、瞿兑之之流主动的选择,不如说他们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环境的险恶让他们自感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们感到只有君子最危险……忠呢,十九是被杀,不忠或逢迎,更不免乎罪,说来说去,路子是很窄的。所以许多人只好做了不说话不做事的隐士……但恨以今日之米价,要想采菊东篱也不可能了。[20]20
文人由于生活所迫,要想在当前做“不说话不做事”的隐士,显然是不可能了。既然必须靠文字谋生,就只能投入到故纸堆里去。从上述对掌故文章内容的分析来看,很多研究者在文中都隐约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倾向,显然他们希望用这种借古喻今的文字婉转表达自己的看法,同时免去许多现实政治的困扰。
而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做,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来自于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死观:
在这儿我又想到史书里面的义烈义民诸传之无理,封疆大吏可以捐款逃走,而老百姓却尽着为国捐躯的义务,……一将功成万骨枯,当兵的固多傻瓜,老百姓中痴人亦不少!近来似乎好一点了,但是大家又跑到屯五洋米面一途上去,等于驱天下人入饿死地狱,此辈不死,则天下人也许要从容而毙了。
友人来信主张平民大可贪生,官吏不当畏死,即是上述一段意义。[21]23
“贫民大可贪生,官吏不当畏死”,是纪果庵针对“封疆大吏可以捐款逃走”,却让老百姓“尽着为国捐躯的义务”而发出的愤慨之声。纪果庵在文中虽高度赞扬秋瑾、杨继盛等前辈先烈“从容就义”的豪情,但也不断表白自己不敢“就死”的心情。
正是环境的逼迫和不敢“就死”的心态,造成了沦陷后期文史掌故的繁荣。租界受日军掌控后,连仅有的舆论保护伞也消失了,此时要想在上海发表反日言论、要想有激进的“大声疾呼”已是不可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文史掌故的研究队伍中。如周黎庵,他在抗战之初本是积极的抗日爱国史学家,曾写下许多反日斗争的文章。1938年,他与文载道等人一起出版过反对日本侵略的合集《边鼓集》;1939年,他在《宇宙风(乙刊)》上先后发表过《明末浙东的对外抗争》、《清初理学与民族革命的关系》等鼓舞民族抗日斗志的爱国文章;1940年,在个人文集《吴钩集》里收录了借讽刺钱谦益投降清朝的贰臣行为,来影射“现代人的脸嘴”的历史小说《迎降》等。但到1942年以后,周黎庵的文章中再也察觉不到反日斗志了,代之而起的是像《谈清代的太监》、《谈明代的妓女》这样无关时政的话题。周黎庵的转变并不是个别现象,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转变,正是因为日军占领上海租界以后,加强了对上海舆论的管制,让知识分子不敢言政治、不敢言现实,只好投身于“故纸堆”里作学问,这也造成了他们不敢反日、又不甘附日的复杂心态,而正是这种复杂心态导致一部分沦陷区文人虽不愿做亲日的附庸,却最终不得不沦为日伪当局繁荣文化的工具。
余论
从上述关于《孽海花》及《续孽海花》的研究中,我们能够大致了解为什么当时关于这两部小说的讨论会如此热烈。首先,《续孽海花》的出版成书是一个契机,它将诸多文史掌故家联系起来。周黎庵等人曾有幸见到该书的原稿及作者,瞿兑之、徐一士直接参与了书籍的校订,而冒鹤亭本人就是书中人物的原型,文史杂志《古今》赞助出版并代售该书,这样的机缘自然使他们对两书的内容发生兴趣。其次,文史掌故本来就重于谈前代的历史轶事,这两部历史小说的内容正符合研究范围,而且曲折变化的情节也可以提供“谈资”。更重要的是,对于部分年纪较长的掌故学家来说,小说的历史背景和人物原型,正是他们熟悉的领域。他们经历过清末民初的社会变化,对清代社会有感情,对小说中提到的历史事件有共鸣。因此,他们的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就事论事或是回忆往事,而是要借此阐述自己的历史观点,表达自己的历史态度,提出对现实社会的看法。
作为生活在夹缝困境中的一群人,研究者们的尴尬就在于既不甘心附日,又不敢于反日。这些研究者的背景复杂,他们在战前往往是抗战的支持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日伪当局的威胁利诱,又与之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周黎庵曾任《古今》主编,纪果庵曾为伪中大教授等等。正因为他们这种政治上的“失节”行为,致使后人对其作品的评价也大打折扣。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应辩证分析而不是简单地施以道德批判。一方面,从他们的研究成果中,我们看到的是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对文字狱的控诉,以及对士大夫命运的同情。他们具有严肃的学术态度,文字中没有媚日亲日的内容,不同于那些甘心为日伪政权服务、为日伪当局政策积极呼号宣传的亲日史学者。另一方面,从个人的政治选择来说,有些人禁不住日伪当局的利诱威吓,或在日伪政权里担任职务,或与伪政权要人多有往来,无形中充当了日伪当局繁荣文化的工具,较之抗日的史学家而言,其行为确有为人所诟之处。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将这一群作家作为整体分析,是因为他们的研究成果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并不代表每个研究者的情况都一样。例如文载道在抗战初期是坚持抗日的爱国史学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也谈掌故、研究史料,其作品里虽不再有反日言论,但总蕴含着积极的意义,他歌颂辛亥革命,批判专制统治,抨击清王朝是异族入侵,也流露出对现实的无奈。在沦陷后期抗日言论无处发表的情况之下,文载道的研究相对于同时代的人来说是有进步意义的。
注释:
①《古今》:上海沦陷时期的一份文史刊物,发行时间从1942年3月起至1944年10月终刊。《古今》的创办与汪伪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主办人朱朴在办刊之前曾先后担任汪伪交通部政务次长、组织部副部长等职;刊物在12期以前由李世群掌管的“国民新闻社”印刷发行;周佛海曾捐资赞助《古今》,为其提供经费来源;而刊物上也时常登载周佛海、汪精卫、陈公博等人的文章。
②以往在研究上海沦陷时期的史学和文学作品时,也有学者对掌故类文章有所涉及,但多从文学史的角度进行零散介绍或简单罗列。《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陈青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是目前所见论及较多的,书中专设一节:“散文的,清谈风’与‘忆旧热’及周黎庵、文载道、周越然等的作品”。作者主要从写作风格的角度对作品及作家进行分类梳理,也简要提及这些作者的写作心态。该书研究重点在文学史及散文风格。
③以上引文均见纪果庵:《〈孽海花〉人物漫谈》,《古今》第27·28合期,1943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