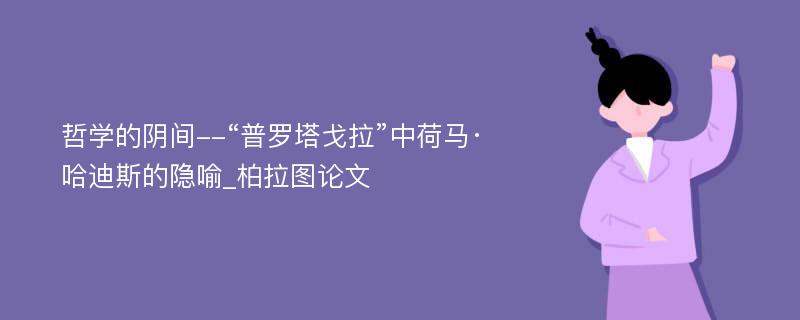
哲学的冥府——《普罗塔戈拉》中的荷马冥府喻发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冥府论文,普罗论文,哲学论文,荷马论文,喻发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普罗塔戈拉》这篇作品的副题是“智术师们”,当时整个希腊最著名的四位智术师,除高尔吉亚之外,其余三位在《普罗塔戈拉》里悉数到场,他们是普罗塔戈拉、希庇阿斯和普洛狄科。苏格拉底与智术师的关系,是所谓“苏格拉底问题”的关键要点之一。因为,苏格拉底被雅典城邦判刑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人们把苏格拉底当成了智术师。在柏拉图记述的这场谈话发生十五年后,历史上的普罗塔戈拉因受到渎神罪指控被雅典人判处死刑。不过,与苏格拉底不同,普罗塔戈拉逃离了雅典,雅典人公开焚烧了他的书。①柏拉图精心设计的这场以普罗塔戈拉为题的戏剧,记叙了由苏格拉底讲述的自己与普罗塔戈拉为首的异邦智术师们在雅典城内的论战,显得意味深长。
《普罗塔戈拉》的戏剧性场景是雅典富人卡利阿斯的家。卡利阿斯崇拜智术师,当三位智术大师到雅典讲学时,卡利阿斯就招待他们住在自己家里。这是普罗塔戈拉第二次来雅典讲学,雅典青年希珀克拉底得知这一消息后,天没亮就急匆匆来找苏格拉底,希望苏格拉底把他引见给普罗塔戈拉。苏格拉底带希珀克拉底来到卡利阿斯家,见到三位智术师正在分别与自己的崇拜者们谈话。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在描述自己眼前所见的这番情景时,化用了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奥德修斯下冥府”的诗句,让自己化身为奥德修斯,用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在冥府中看到的亡灵来逐一指称三位智术师。施特劳斯在讲解这一场景时提到一则典故:由于卡利阿斯与自己的岳母有染,他在雅典得了一个绰号叫“冥府”。由于《普罗塔戈拉》这篇作品以谈论“德性是否可教”闻名,柏拉图让笔下的苏格拉底把卡利阿斯家比作“冥府”的意象可谓反讽意味十足:竟然在一个如此声名狼藉的人家里谈论德性可教的问题。普罗塔戈拉宣称自己是教德性的教师,他接受卡利阿斯做自己的学生表明,自己对受教者的德性毫无感觉。
然而,卡利阿斯的“冥府”绰号与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自比奥德修斯所下到的“冥府”是两回事,因为,苏格拉底化用的是荷马笔下的冥府。为什么苏格拉底要以荷马的冥府作为三位智术师与自己的学生们谈话的叙事场景,何以苏格拉底要用荷马笔下的冥府亡灵来描绘智术师?这是本文要探究的问题。这个问题值得“小题大做”的原因在于,荷马与柏拉图是古典学界公认的两座并峙的古希腊思想巅峰。
一、民主时代的“奥德修斯”
古希腊人熟诵的“奥德修斯下冥府”的故事见于《奥德赛》第11卷,这段著名的冥府之行成了后来西方文学史上无数冥府叙事(阿里斯托芬、维吉尔、但丁等)的母题。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奥德修斯在遥远异乡漂泊十年之久,为重返故乡伊塔卡历经艰辛,几度出生入死。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场历险,莫过于奥德修斯与伙伴下到冥府,向盲人先知忒瑞西阿斯询问返乡路线,预卜未来命向。奥德修斯在冥府中遇到了各色亡灵,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众希腊英雄的亡灵,其中有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英雄阿喀琉斯及他的情伴帕特罗克洛斯,还有英勇的埃阿斯等。在这些英灵身边,还围绕着堪称希腊最优异的子弟的亡魂——特洛伊战争令希腊人折损了许多青年才俊,他们命丧异邦,魂归冥府。奥德修斯在成功返回伊塔卡后,血刃众多求婚人,使伊塔卡乃至希腊其他城邦的贵族子弟几近全灭。所以,我们在《奥德赛》第24卷读到,当阿伽门农的亡魂看到众求婚人的魂灵被引路神赫尔墨斯带到冥府时,大声惊呼,惋惜不已:
你们怎么一起来到这昏暗的地域?尽管你们优秀且年轻?国人中不可能找出比你们更显贵的人。(《奥》24:107—108)②
无疑,长达十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令希腊城邦英才凋零,奥德修斯作为二十年前引领伊塔卡子弟兵出征的统帅,自然受到伊塔卡人的责难和抱怨。求婚人安提诺奥斯之父在儿子被奥德修斯宰杀之后,憎恨地咒骂奥德修斯“恶贯满盈”。因为,奥德修斯“用船只载走了无数的勇士,结果丧失了空心船,也丧失了军旅”,而他“归来又杀死这许多克法勒涅斯显贵”——这大概是英雄的奥德修斯在绝大多数伊塔卡人心中的形象,也是城邦对他最大的指控:毁损了伊塔卡子弟的性命。这让我们联想到雅典城邦对苏格拉底的指控:败坏青年。伊塔卡王奥德修斯身上背负着全体伊塔卡子弟的身家性命,这些年轻而优秀的青年人追随奥德修斯外出征战,毫利未取,反而悄没声息地命丧异乡,无功无名。同样,德尔菲神谕预示的最有智慧的苏格拉底肩负着守护雅典青年人“灵魂命相”的重任,如何向雅典城邦优异的灵魂施教,是苏格拉底命定的任务。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奥德修斯与苏格拉底皆遭到城邦的指控和责难。因杀戮求婚人,奥德修斯引发了全体城邦民的怒气和叛乱,城邦陷入分裂和内乱。幸好宙斯派雅典娜出面阻止奥德修斯的杀戮,避免了更大规模流血冲突,使双方的战斗“不分胜负”而终,并在神的帮助下重缔盟誓(《奥》,卷24,415—527)。即便奥德修斯在这场内乱中获胜,他仍是一个失败的王者。因为,伊塔卡的政制和宗法完全崩溃,贵族子弟几乎全灭,城邦时刻有重新陷入分裂和动乱之虞。
换言之,胜利的奥德修斯将不得不面临一个“荒”城。这让我们想起冥府中盲先知忒瑞西阿斯的预言:返乡后的奥德修斯将被迫再次离开伊塔卡去漂泊。这意味着,奥德修斯用暴力和血腥重建的伊塔卡城邦需要时间去抹平城邦的创伤和裂痕。耄耋之年重返伊塔卡的奥德修斯已然不可能统治伊塔卡,不再是伊塔卡的王者。取而代之的是他的儿子挟带着其父遗留下的血腥威严,重建城邦政制。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奥德修斯是一位被伊塔卡城邦放逐的王。回过头来看苏格拉底,他难道不是一位被雅典人“逐出”城邦的哲人王?不过,被雅典民主法庭判处死刑的苏格拉底并没有听从克力同的劝说逃离雅典,像普罗塔戈拉那样逃亡。哲人苏格拉底选择遵循雅典法律,守护母邦政制和礼法,而非挑起一场精神上的内乱,分裂城邦。在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记述的那一场雅典人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中,支持与反对者各占一半,雅典人如同伊塔卡人一样陷入分裂,苏格拉底也面临着与奥德修斯同样的处境:扩大抑或弥合城邦的裂痕?他们的不同选择和决断,让我们见识了哲人与治邦者的差异,也让我们见识到哲人与诗人关于政制思考的差异。③
从文本的历史时间来看,《普罗塔戈拉》中的苏格拉底还不到四十岁。换言之,彼时的苏格拉底正在成为自己的过程之中。“下冥府”是奥德修斯个人命运的重大转折点,历死重生,见识到生命最大的奥秘之后,奥德修斯才得以认识生命的本质,完成了灵魂的自我转化。同样,苏格拉底得在聆听了《会饮》中第俄提玛的教诲,认识了爱欲的最大奥秘后,他才能深入《普罗塔戈拉》中的“哲学冥府”,战胜智术师的幽灵,把青年人希珀克拉底的灵魂带出“冥府”。我们可以推想,柏拉图笔下的这段苏格拉底的冥府之行与苏格拉底的自我锻造相关。通过与普罗塔戈拉以及其他两位智术师的交锋,苏格拉底澄清了自己与智术师的本质差异,完成了自我认识最为重要的环节。在这场事关城邦教育权的斗争之中,苏格拉底虽然面目模糊,没有泾渭分明的敌友关系,但是,柏拉图让我们看到,苏格拉底终身都在从事对城邦少数青年的教育,如何挑选并引导天素优异的青年灵魂向上攀升,而非堕入“哲学的冥府”被智术师勾走灵魂,是雅典民主时代的“奥德修斯”式问题。作为一个生活在雅典民主时期的“奥德修斯”,苏格拉底除了被迫应对“冥府”中的各色智术师亡灵,还要完成奥德修斯没能完成的任务:安全地从冥府带走年轻的幼稚灵魂。
柏拉图讲述的苏格拉底下至“冥府”的故事从一天中最深的黑夜开始讲起。天还未亮,希珀克拉底急匆匆地用手杖猛敲苏格拉底家的门,“有人刚把门打开,他就冲了进来,高声嚷嚷”(《普》,310b1),毫不顾及苏格拉底还在睡觉。希珀克拉底出身于雅典本地的一个大户人家,家产殷实,“天性似乎与同龄人有得一比”,他欲求在政治上有所建树(《普》④,316b7-c2)。狡猾的苏格拉底没有明言,希珀克拉底的天性与天资高还是天资低的同龄人有得一比。苏格拉底向友人(以及读者)坦言,他对希珀克拉底的真实评价是,“我知道这个人的勇劲儿和急性子”(《普》,310d2)。换言之,希珀克拉底天性单纯而热情,鲁莽而直率,怀有炽热的追求政治事功的爱欲。这类青年的头脑比较简单,喜欢盲目崇拜文化名人,他们的热情极易被煽动和挑拨。希珀克拉底既没有见过普罗塔戈拉,甚至还不清楚智术师究竟是什么品质的人,就轻易冒失地把自己的灵魂托付给这类教师,一腔热情地相信,自己能被智术师打造成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苏格拉底尖锐地批评他:
要是你并不知道把灵魂交付给谁,你就不知道正在把灵魂交付给好的还是坏的事情。(《普》,312c2)
希珀克拉底这类人如果在政治事功上有热情,往小处说是自我毁灭,往大处说则是祸害城邦。柏拉图笔下的这个人物让我们想起荷马在《奥德赛》中刻画埃尔佩诺尔,他与希珀克拉底的天性相似。埃尔佩诺尔是奥德修斯最为年轻的同伴,奥德修斯对他的评价是,“作战不是很勇敢,也不很富有智慧”(《奥》10:552)。这个小人物的故事出现在奥德修斯下冥府之前,当时,埃尔佩诺尔为求凉爽,醉酒后独自跑到屋顶安睡,半夜被同伴们纷乱跑动的声音惊醒,恍惚之中心智迷失,忘记了“重新沿着长长的梯子逐节而降,从屋顶上直接跌下”。(《奥》10:558)由于折断了头,埃尔佩诺尔的魂魄先去了冥府。当奥德修斯与他在冥府相遇时,埃尔佩诺尔将自己身上的灾难归结为神定的不幸命运和饮酒过量,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灾难其实是由于自己天性上的欠缺:心智简单,性情鲁莽,缺乏真正的勇敢。希珀克拉底与埃尔诺佩尔有共同的天性,这间接印证了苏格拉底对希珀克拉底的评价:“天性似乎与同龄人有得一比。”换言之,希珀克拉底有如《奥德赛》中的埃尔诺佩尔:好饮酒意味着他心智不清醒,没有判别最为基本的好坏对错的能力。当这类心智迷迷糊糊地被冒失的哲人引至哲学高处,追求与他们天性不适宜的哲学,冒险去模仿与其天性不匹配的激情,就既无法返回日常的城邦生活,又不能适应哲人的高山生活。这类人追求哲学的结果自然是,从高处摔下来,折断头颈。就此而言,埃尔佩诺尔表征的是所有不适合学哲学的常人灵魂。在《普罗塔戈拉》中的希珀克拉底这个角色上,柏拉图化用了埃尔佩诺尔这个形象,并改写了普通士兵埃尔佩诺尔的命运。柏拉图安排爱好哲学的青年希珀克拉底在苏格拉底下到冥府之前出场,尤其是在黎明之前来找苏格拉底,喻指青年人心智处于将明未明的最黑暗阶段的关键时刻。这时,他遇到什么样的哲学教师,对他的启蒙朝向哪个方向,如何开启他的心智,对他一生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吕西斯》这场关于友谊的对话中,柏拉图也用了类似的譬喻。在懵懂无知、混沌未开的年纪,选择什么样的人为友,以什么样的人为师,关乎一个年轻人今后一生的灵魂安危。《普罗塔戈拉》把希珀克拉底作为苏格拉底冥府之行的戏剧动机,暗示苏格拉底完成了奥德修斯没能完成的任务,安全地从“哲学的冥府”中带出他的同伴。就守护年轻人的灵魂而言,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作为政治哲人胜过诗人荷马笔下的英雄奥德修斯。
二、智术师的幽灵
苏格拉底下到“哲学的冥府”后,他首先看到的是普罗塔戈拉——苏格拉底此行最主要的对手。这位古希腊最著名的智术师一生游历希腊各个城邦,宣讲自己的技术文明观念,并公开向学生收取学费。在当时的雅典,智术师名声不佳,普罗塔戈拉并不忌讳自己的智术师身份,公开自称是“智术师”,专教年轻人学习“如何更好地齐家,然后是城邦事务方面的善谋,即如何在城邦事务方面最有能耐地行事和说话”(《普》,319a1)。对于任何愿意出学费的人,他都承诺传授这门学问。换句话说,普罗塔戈拉公开表明,自己传授的是治邦术(如今叫“政治学”)。普罗塔戈拉与希庇阿斯和普洛狄科显得不同,他关心地上的生活,关心城邦事务,或者说关心政治,而非仅仅关心纯粹的自然学理。由于苏格拉底也自称更关心地上的生活,关心城邦事务,而非关心天上的自然,苏格拉底就显得与普罗塔戈拉非常相似。
普罗塔戈拉善于言辞,苏格拉底一进卡利阿斯家见到普罗塔戈拉时,就把他比作歌声能感动万物的俄耳甫斯,用美妙言辞迷住身边一群出身高贵、容貌美丽的雅典世家子弟以及一些外邦青年。但是,苏格拉底也曾被比做一条言辞曼妙的蛇(《理想国》,卷2,358b),在《会饮》中,我们看到,阿尔喀比亚德甚至当众夸赞苏格拉底的言辞绝妙无比。可以说,苏格拉底与普罗塔戈拉一样,都因为言辞高妙而有一群自己的追随者。在雅典人心目中,苏格拉底与智术师普罗塔戈拉的面目多有重合之处。普通雅典人未必分得清,苏格拉底与普罗塔戈拉究竟有何差异。苏格拉底后来遭受“败坏青年”的指控,在此之前,普罗塔戈拉同样遭遇过这样的指控。因此,柏拉图若想为苏格拉底辩护,就必得区分苏格拉底与普罗塔戈拉,让人们看清苏格拉底与智术师的差异,洗清苏格拉底身上的智术师污名。苏格拉底的这趟“冥府之行”,不仅是为了让希珀克拉底认清普罗塔戈拉是不是懂得德性的好教师,让他免受智术师言辞的蛊惑,也是为了让人们认清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
对于普罗塔戈拉的描述,苏格拉底用了冥府中的两个形象,首先是明确提到的俄耳甫斯形象,另一个形象则没有明言,仅仅暗示。从俄耳甫斯的传说中我们得知,俄耳甫斯虽然是个感天动地的迷人歌手,但他也是一个失败者。他在冥府中靠歌声打动冥王,冥王允许他回到阳间,并可以带上自己妻子的亡灵,但他却因天性软弱未能把亡妻引出冥府。如果普罗塔戈拉的化身是俄耳甫斯,苏格拉底的化身是奥德修斯,柏拉图如此笔法的含义兴许就是,普罗塔戈拉是个天性软弱的歌手,苏格拉底则是大无畏的英雄。
可是,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又暗中把普罗塔戈拉比作阿喀琉斯。⑤既然阿喀琉斯也是荷马笔下的英雄,那么,苏格拉底与普罗塔戈拉的对比,就是荷马笔下的两位著名英雄的对比。阿喀琉斯以勇敢著称,同样,在《普罗塔戈拉》中,普罗塔戈拉在一开始就展现出自己的大无畏姿态。他宣称自己敢于公开自己的智术师身份,绝不畏惧政治权势,绝不掩藏自己要宣讲的政治术。但是,普罗塔戈拉的勇敢缺乏智慧,算不上真正的勇敢。奥德修斯以“足智多谋”著称,这位英雄的勇敢基于智慧。更重要的是,在荷马的冥府中,英雄阿喀琉斯完全丧失了勇者的样子,也就是说,他的勇敢徒有其表。“哲学的冥府”中的普罗塔戈拉既是俄耳甫斯,又是《奥德赛》中的阿喀琉斯,他既有俄耳甫斯的言辞魅力,又有阿喀琉斯的软弱和鲁莽。值得关注的是,在《会饮》中再次出场的人物中,诗人阿里斯托芬取代了智术师普罗塔戈拉,成为苏格拉底主要的对手之一。⑥另一个值得考虑的细节是,据《名哲言行录》中记载,普罗塔戈拉曾经写过《论冥府中的事情》一书,柏拉图在以他为名的这篇对话中化用荷马的冥府很可能暗示:普罗塔戈拉对冥府的理解并不准确。
描述普罗塔戈拉之后,苏格拉底用荷马的“此后我又认出”这句诗引出“百科全书”式的智术师希庇阿斯。这句诗出自《奥德赛》(卷11,601),本来是用在赫拉克勒斯身上的。言下之意,希庇阿斯是荷马笔下冥府中的赫拉克勒斯。荷马原诗意指,奥德修斯在冥府中遇到了力大无穷的赫拉克勒斯的魂影,后者“形象阴森如黑夜”,胸前“环系令人生畏黄金绶带”。荷马特意描述了绶带上的图画:有令人生畏的动物,以及“搏斗、战争、杀戮和暴死的种种情景”。我们可以设想,苏格拉底很可能用绶带图腾来比喻自然哲人希庇阿斯的灵魂:这类哲学教师所传授的知识会把人的灵魂引向最为野蛮和极端的自然状态,不仅不教授关于德性的知识,反而激发人的不受礼法约束的自然本性。假若遇上天性不适宜的青年,希庇阿斯式的智术师教育非但不能使人的灵魂“变得更好”,反倒会“变得更坏”。阿里斯托芬在《云》中就刻画了一个被“自然哲人”苏格拉底教坏的青年。柏拉图把希庇阿斯安排在“哲学的冥府”中,却在这场哲人的聚会中让阿里斯托芬缺席,很可能是提醒读者,阿里斯托芬指控苏格拉底为自然哲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出于无知。施特劳斯提醒我们关注希庇阿斯的一个细节:在《会饮》中,阿尔喀比亚德打断了阿里斯托芬的发言,在《普罗塔戈拉》中,阿尔喀比亚德同样打断了智术师希庇阿斯的话。但是,前者基于醉酒后的无意之举,后者则是有意为之。施特劳斯认为,这意味着“阿里斯托芬与希庇阿斯有共同的东西:均凭靠所谓自然理则,他们都是“自然”的学生。阿尔喀比亚德打断阿里斯托芬,意味着政治人在自然与习俗的对立中站在了苏格拉底一边,反对诗人和智术师——按照信奉自然理则的人的理解,宇宙诸神与城邦不相容”。⑦不过,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希庇阿斯是哲人圈子最为坚定的维护者,他第一个明确提出哲人圈子的同质性和排它性,为“哲学的冥府”做了最为明确的定义:
在座诸位,我认为,你们是同族和同一个家庭的成员,每个都是城邦民——就天性而非礼法而言;毕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相像的与相像的凭天性彼此亲近],可是,礼法作为[支配]世人的王者强制多数人违背天性。……我们懂得事情的本质,而且是希腊人中最智慧的人,眼下聚集在希腊的这样一个地方,[聚集]在这智慧的主席团大厅,[聚集]在这城邦最伟大、最光耀的高宅。(《普罗塔戈拉》,337c6—337d5)
可见,自然哲人希庇阿斯最有哲人意识,甚至还有哲人智性的优越感。柏拉图对追随自然哲人希庇阿斯的美少年斐德若和厄里克希马库斯的一处闲笔,暗示了《会饮》中这两人的爱若斯讲辞的知识根源。
三、冥府里的先知
让我们惊异的是,苏格拉底的老师普洛狄科也在“哲学的冥府”。在苏格拉底描绘的这个冥府中,我们看到,普洛狄科是苏格拉底唯一提到他的身体状况的人物:普洛狄科似乎因年迈而身体衰弱,怕冷,全身裹着羊皮和毯子。在《奥德赛》中我们读到,奥德修斯下到冥府后,曾单独向盲先知忒瑞西阿斯祭献了一只全黑的公羊(《奥》11:525),。普洛狄科身上裹着的羊皮与这只公羊有什么寓意上的关联吗?如果有的话,苏格拉底描述的冥府中的普洛狄科就很可能暗喻的是盲先知忒瑞西阿斯。无论如何,就整部对话而言,普洛狄科是唯一受到苏格拉底礼遇和尊重的老辈智术师,苏格拉底明确表示自己想倾听他的教诲:
虽然我非常想听普洛狄科[说的话]——毕竟,我觉得这人智慧圆融,而且神气——由于他嗓音低沉,屋子里有一种嗡嗡声,使得没法听清在说什么。
苏格拉底用“神气”来描绘普洛狄科,还说他具有“神样的智慧”,并公开宣称“我是普洛狄科的弟子”(341a4),用“最棒的普洛狄科”(358b1)来称呼他。当苏格拉底与普罗塔戈拉讨论西蒙尼德诗句险些落败时,苏格拉底赶紧求助的是普洛狄科:他需要借助普洛狄科具有的某种能力来战胜普罗塔戈拉。那是什么能力呢?施特劳斯提醒我们注意到,普洛狄科与苏格拉底有相同的能力:善于修辞和有强烈的爱欲。普洛狄科以擅长辨析同义语词著称,苏格拉底曾跟随普洛狄科学习修辞术。我们也许可以提出这样的假设:当苏格拉底与普罗塔戈拉在修辞交锋上势均力敌时,需要借助爱欲的力量。普罗塔戈拉不懂得区分灵魂的类型,只看出身门第或表面的爱欲,不懂得按自然天性的差异来辨识少数人与多数人,喜欢受人吹捧,只要别人捧他,他就不管这人的天性如何,一律收做弟子。因此,普罗塔戈拉的如此天性难免把天性不适合的灵魂拖入“哲学的冥府”。按照《会饮》中第俄提玛对苏格拉底的教诲,爱欲有高低之分,正如灵魂有高贵与低贱之别。针对不同的灵魂应施行不同的教育。因此,辨析爱欲的差异,是区分苏格拉底与普罗塔戈拉的关键。换言之,苏格拉底把普洛狄科辨析同义词的技艺用来辨析爱欲的差异。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以“我又认出坦塔洛斯”(《奥德赛》,卷11,583)明确把普洛狄科比作荷马冥府中的坦塔洛斯。坦塔洛斯属于神族,他因偷取神的食物赠予人类被罚在冥府永受饥渴之苦:他总是喝不到近在唇边的水。这种永远追求不可得之物的悲惨形象,似乎是哲人普洛狄科的最好写照:暗示普洛狄科并不知道爱欲奥秘,虽然他也拥有爱欲的部分知识。柏拉图趁机暗示,追随普洛狄科左右的泡赛尼阿斯和诗人阿伽通,同样不懂得爱欲的奥秘。
《奥德赛》中的女神基尔克预言,冥府里只有忒瑞西阿斯能思考,余者皆化为魂影。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赋予普洛狄科以“冥府先知”忒瑞西阿斯的象征性角色,表达了对这位智术师前辈的敬意。但是,苏格拉底在《会饮》中彻底修理了普洛狄科的学生阿伽通这位民主时代肃剧诗人的爱欲颂辞。这暗示了两种可能:要么民主智识人没有听从老派智术师的教诲,把他们在密室里的教诲宣之于众⑧,从而导致了灾难性的启蒙运动。要么,老派智术师的教育完全失败,因为,这类教师并没有传授哲人最重要的德性——审慎与节制。无论哪一种可能,都呈现了柏拉图对智术师和民主文化诗人的尖锐批评,并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师徒关联和精神上的内在关联。我们知道,哲人苏格拉底身处雅典民主的鼎盛时期,他一直面对两类对手:智术师和民主文化人。我们可以看到,在柏拉图笔下呈现出新派智术师与苏格拉底之前的智术师的对立,民主文化的诗人与古风诗人的对立。苏格拉底恰好置身在这种对立之中,在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既不是唯古风的保守派,更不是激进的自由民主派。然而,尽管苏格拉底批评荷马只看到真理的影子(参见《理想国》卷10),他仍然宁可与古风诗人荷马联手迎战民主时代的自由派新诗人。在《普罗塔戈拉》中,柏拉图让我们看到,苏格拉底不仅击败了新派智术师普罗塔戈拉,也击败了新派诗人西蒙尼德斯。
四、结语
柏拉图在《克拉提鲁》中有一段借苏格拉底之口讨论冥王普洛冬(别名哈得斯)名字的话,或可视为他为“哲学的冥府”下的定义。苏格拉底修正了绝大多数常人对于冥神的意见,认为人们没必要恐惧死亡。⑨苏格拉底指出,冥神的本名是普罗冬,原意是来自大地深处的馈赠,其别名哈得斯则“因其懂得一切美好的东西而得名”,而非取其“不可见”之意。苏格拉底称把冥王哈得斯称作“完美的智者,对他近旁的人也大有助益”。哈得斯只与灵魂相处,偶尔也与那些净化了灵魂中的恶及欲望的身体相处。然而,若身体有了冲动和疯狂,就不能留在哈得斯身边。随后,苏格拉底明确指出,哈得斯这一特征就属于“哲学和爱思考的人”。人们之所以宁可留在哈得斯身边而非逃走,是因为被哈得斯的美好言辞诱惑,连海妖塞壬也不能逃离这种诱惑。人们相信自己待在哈得斯身边能成为一个德性上更好的人,这一最大的欲望使得他们甘愿留在冥府而不离去。⑩这段话读来让人倍感困惑,然而,如果与《普罗塔戈拉》中的“哲学的冥府”意象联系起来,多少能让我们领悟柏拉图在这一文字中令人费解的隐喻。
反观《普罗塔戈拉》中的“冥府”,它实际上是一个由智术师及其弟子组成的哲人共同体,一群热爱谈论“天象学和涉及自然和天上的东西”(《普》,315c5)的人。“冥府的视域就是哲学的视域,因为哲学探究的正是无法看清的东西。”(11)欲求智慧的哲人与冥府的亡魂有相同的意象:都生活在黑暗之中,艰难地探索或感知这个世界。差异仅仅在于,哲人对于这种“地下”工作甘之如饴,他们在纯粹的智性思辨中获得愉悦。在“哲学的冥府”中,哲人们可以彼此心照不宣地交谈、论辩,因为他们同属哲人族。因此,哲人苏格拉底能看清灵魂的本质,洞察事物的真相,常人希珀克拉底则要依靠苏格拉底才能看清冥府中的智术师的本相。哲学的探问没有边际,一如冥府黑暗无边。就此而言,哲人的勇敢是真正的勇敢:相对于身体的消亡,古典哲人更恐惧灵魂的堕落。
注释:
①参见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中的《普罗塔戈拉传》,第91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②本文凡引用《奥德赛》原文皆采用Homer,Homer,Opera in five volumes,edited by D.B.Munro & T.W.Alle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0。本文引用的《奥德赛》诗行及译名,均采用王焕生先生译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③施特劳斯在1959年的“《会饮》课程”中曾经提到苏格拉底不写作的原因很可能与他政治上的不活跃相关,两者皆表明苏格拉底的thumos(血气)薄弱,从而间接印证了阿里斯托芬在《云》中对苏格拉底“是非政治人”的批评。(中译见施特劳斯:《论柏拉图的〈会饮〉》,第335页,邱立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就此而言,苏格拉底的非政治性与奥德修斯的政治性可能成为了政治哲人柏拉图思考城邦政制的两端:拥有实践智慧的奥德修斯与拥有纯粹智慧的苏格拉底如何能结合起来?
④本文凡随文注释的地方,《普罗塔戈拉》简称为《普》;《奥德赛》简称为《奥》:《会饮》简称《会》。
⑤见《普罗塔戈拉》340a,苏格拉底引用荷马的诗句来邀请普洛狄科与自己一起迎战阿喀琉斯式的普罗塔戈拉。
⑥施特劳斯在讲疏《普罗塔戈拉》时着重指出,冥府中的普罗塔戈拉的形象更多是阿喀琉斯,而非俄耳甫斯。参见刘小枫《普罗塔戈拉译笺》中施特劳斯的疏解。
⑦转引自刘小枫编译:《普罗塔戈拉译笺》,同上。
⑧按苏格拉底的冥府描绘(315e6-316e7),三位智术师只有普洛狄科显得审慎。苏格拉底明言自己最想听普洛狄科的教诲,但由于他声音太小了,没办法听清楚。在《会饮》中,普洛狄科的弟子阿伽通则在三万希腊观众面前公开表演。
⑨在《普罗塔戈拉》后半部分,苏格拉底让三位智术师一起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自愿去求自己认为坏的东西而不求好的东西”,并不符合人的天性。随后,苏格拉底让普洛狄科来分析“畏惧”与“恐惧”这两个语词。苏格拉底迫使智术师们同意:人所畏惧的东西是坏的。苏格拉底的问题是:会有人去自愿寻求让他恐惧的东西吗?从这个问题起步,苏格拉底再次讨论五种德性中的勇敢德性。如果结合《克拉提鲁》中对“哲学的冥府”的定义,苏格拉底的言下之意也许是:常人最畏惧的莫过于死亡,因而没有谁愿意接受死亡,即便死能让人变得更好。然而,哲人却能在常人停步的地方继续追问下去,直面常人最为恐惧的死这一问题。
⑩参见柏拉图《克拉提鲁》403a5—404b5,苏格拉底向克拉底鲁解释诸神的名和称谓。冥神普洛冬与海神波塞冬都是宙斯的兄弟,普洛冬名称的字面意思是地下的馈赠之物,他的另一称谓是哈得斯,字面直译是“不可见的”。奥德修斯因刺伤波塞冬儿子独目巨人的眼睛而惹怒波塞冬,返乡之路受其阻挡,女神基尔克则指点他去冥府问盲先知,由此呈现了荷马史诗中的神权政治的三分格局:天上、海里和大地之下。倘若联系到柏拉图笔下的“哲学的冥府”意象,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来理解哲学的地域:既在城邦的政制、宗法之中.又隐匿在城邦之外。如同冥府既在宙斯的神权治下,又是自成一体的法外之地。
(11)参见刘小枫:《普罗塔戈拉译笺》,同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