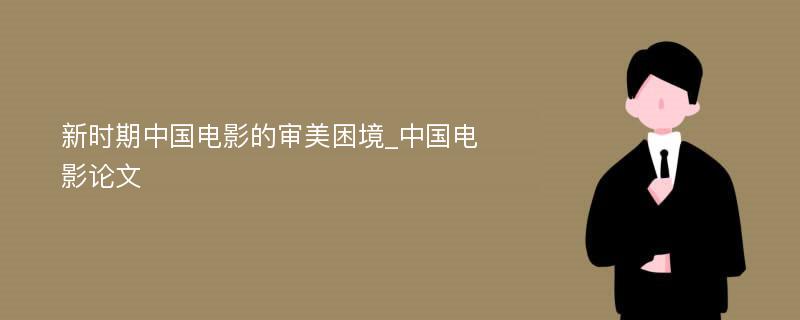
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美学困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顿论文,新时期论文,美学论文,中国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学,意谓人的生命本真之学,是对于人类生存和生命的“求本”之学或“诗学”。在一定意义上,它是对人类的生命和生存状态的指引和标尺,这一标尺就是引导我们生命的超越性、神性。在此意义上,一切艺术,当然包括电影艺术,只有达到美学的层次,只有给人提供这样一种尺度,才可以说是进入其根本。按这样的美学尺度衡量,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新时期以来由第四、五、六代电影及冯小刚为代表的市民剧构成的中国电影①,已经陷入美学困顿。
一、从“寻根”的沉重到“大片”的轻浮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所谓“新时期”文艺的主要特征,在于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进入社会的精神层面,并担当起文化和精神启蒙的责任。文艺开始重新将意义问题提了出来,对人的尊严的尊重被重新强调,理想主义的旗帜重新飘展,崇高和激情、痛苦和寻找、良知和独创……这些久违了的精神价值成了此一时期最为夺目的风采。
这样一种文化背景决定了新时期的中国电影是从文化反思和寻根开始的。
一方面,第四代电影中的很大一部分影片把表现的焦点集中于政治、道德、历史、法律等等,他们延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呼唤人的觉醒,自觉地承担历史赋予的时代使命,满腔热情地进行文化的再启蒙。《生活的颤音》、《苦恼人的笑》、《枫》、《巴山夜雨》、《春雨潇潇》等影片的共同主题,就是呼唤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价值;《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如意》、《小街》、《青春祭》、《小巷名流》则在对社会生活艺术概括的力度和对人性把握的丰富性上,进行了新的开拓,从而从政治反思向文化反思延伸,出现了《良家妇女》、《湘女潇潇》、《乡音》等优秀作品。这类电影,在文化传承上,是对以郑正秋奠立的中国电影传统的变异性承续,即紧跟时代性的社会主题,自觉地认为电影应该肩负教化功能,艺术家则充当社会良知的角色,并以人道主义诉求作为其总体文化价值取向。
另一方面,第五代导演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张军钊等人的电影,通过令人耳目一新的造型和独到内涵,在一个有关民族、历史、人的“宏大叙事”背景之下,表现了对于人生存状态的关注,对历史和民族传统的反思。《黄土地》的历史意识、《一个和八个》的人性光芒、《大阅兵》的个体和类的矛盾、《红高粱》的生命张扬、《猎场扎撒》的蒙古族风情展示和文化思索,均标志着中国电影已经向历史和文化的深度广度进行开掘,开始在人的生存本体论上营构电影;同时,他们也注意从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中汲取丰厚的营养,在电影的民族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一定意义上,此时期的中国电影达到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度,我们也似乎看到了中国电影的希望和曙光。
然而,经过时间的沉淀,今天我们似乎可以较为冷静客观地回顾这些并不久远的电影作品。明显地,第四代的反思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社会意识的层面上展开的,而第五代的《黄土地》、《孩子王》、《红高粱》、《猎场扎撒》、《黑骏马》等代表性的“寻根”作品,更多的意义和价值还是影像造型和文化反思层面上的,它们的这种定位,与当时整个文艺领域不断重复和诉说的主题——“带着乡愁寻找精神的家园”是相呼应的。可是,由于缺乏超验的价值之根和终极关怀所指向的神性的悲悯情怀,第四代的电影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和时代主题的转换而日渐丧失美学的力量,而以“寻根”相标榜的第五代的某些影片也不同程度地滑向了对民族劣根性和原始生命粗野性的宣泄,所寻找到的黄土地、红高粱、西北风、远古高原、大宅院等等,在给我们以视觉的震撼和新奇之后,最后留存记忆的只是民族和地域中激烈、野蛮等非常态的人性阴暗面,说得委婉一些,就是所谓的“伪民俗”——亮出自己的舌苔,满足西人的窥视欲。其结果,第四代的“反思”并没有触及人的生命之根和生存之本,第五代的“寻根”也没有回到真正的“根”——人性本源中的神圣渴望和终极关怀,而是对有限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等方面的视觉包装,是向低俗的原始自我、自然野性的寻找和回归,这样的寻根,即使不是南辕北辙,也是抽空了本质内容的民俗表演和劣根性的大展露。
换句话说,当起初还具有的庄严及其人性内容逐渐丧失的时候,那么其粗野的劣根性和原始生命的一些邪恶内容就堂而皇之地一步步走到了前台,变成了中国电影中的浅薄和放纵,成就了当下的所谓国产“大片”。因此,毫不奇怪,美学层面上,当下的所谓“大片”没有了现实基础,丧失了起码的审美内涵,如《十面埋伏》故事简单得近乎廉价,以两男一女的三角关系结构一个“影像的拼贴”;《无极》本意是关于命运、自由、爱情的寓言,然而,缺乏文化语境和逻辑基础的剧情,远离中国大众欣赏趣味的故弄玄虚,摄影和数字技术的差强人意,布景虚假造作,使其除了3亿元史无前例的投资外,乏善可陈。文化层面上,“大片”的文化责任感和道德意识阙如,不问社会百姓疾苦,集体逃避责任,如《英雄》不惜背离武侠精神,艺术观和历史观的混乱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夜宴》共同把目光瞄向了中国文化中最冷血的宫廷争斗、权谋诡计,这些电影艺术家们似乎忘了:一个国家的文化精英阶层,就是这个民族的良知和眼睛,他们天然地负有传承民族优秀文化、引导民众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应该是历史的盲视者,更不应该靠贩卖历史的血污赚取商业的利润,而缺乏历史的眼光和审美的提升,结果只能是历史和现实一起被放逐!在这些大片身上,我们已经很难发现电影艺术家们的现实精神和历史责任感,更谈不到忧患意识以及植根生活和介入生活的努力,在外表华丽的声光电影中,在影像的“奇观”下,是内容的苍白和生命力的孱弱。在“大片”热闹景象的背后,是忘却了对具有普遍价值的信仰和理想的追寻,对生命幽深之境的探究,对超越于现实人生之上的“天空”的仰望。甚至,已经没有了令我们为之振奋或感动的东西,说得严重一点,中国民族电影的优良传统,在这里已经发生了可怕的断裂。本来可能从第四代的反思和第五代的寻根开始的文化启蒙和美学意识复苏的沉重使命,在这里被轻浮地放逐。
二、从“市民”的调侃到“边缘”的无奈
不幸的是,正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露的中国电影的这些不足和缺陷,成为了张艺谋、陈凯歌们之后的中国电影的直接参照,甚至成为他们的起点和滋养。换句话说,“第五代”们的电影与“后第五代”的电影在精神质素上是属于同一个谱系的,第五代“寻根”的浅尝辄止和后第五代“反叛”的脱离靶心,只不过是同一病源的两种症状,其共同“病灶”就在于他们的价值理念完全依附在现世人生的浅表层面上,始终趋同乃至受制于现世人生的风云变幻,匮乏一以贯之、不受时尚风流左右的精神信仰,从而无法为自己的心灵的存在确立一个终极性的超越维度。
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随后出现的部分国产电影表现出的出奇的短视眼光、对主流价值观念和价值系统轻率的嘲弄或拒绝,或以阴郁怪诞的方式表现一些貌似深刻的东西等特征。如果说作为它们兄长的第五代们还守着一片赤诚,那么这些电影则把真诚与伪善混为一谈了。于是,它们嘲弄真诚就像嘲弄伪善一样,油嘴滑舌、痞化、调侃就成了它们最为醒目的形态表征。这一类影片大致出现在20世纪的90年代以后,以稍早的王朔的四篇小说在同一年被改编为电影作为第一个明显标志,以“冯小刚式贺岁片”为典型代表。客观地说,这些影片对于“解构”或“矫枉”中国电影传统中某些违背艺术规律的倾向是有贡献的,它们的出现和确立无疑经过了一个去蔽去伪的过程,力争从陈旧观念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中解脱出来,追求真实的个人化的表达。它们复归自我或“小我”,用属于自己的感觉去感知,用自己的性灵去领悟,用自己的方式去表现个人化的情绪和思考,也使得国产电影开始关注个体性情感的抚慰,在一定意义上满足了我们个人化的精神和心灵需求。
但问题在于,是否一切称为价值的东西都是伪价值?是否在世俗化了的伪真理、伪价值、伪艺术之外还有真正的绝对超验的生活的真理、永恒的价值和圣洁的艺术?在我看来,冯式电影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正在于此。他们的电影在自觉不自觉地拒斥向着真善敞开的精神质素,因而也堵塞了美的道路,至少直至目前,仍走在一条简单、片面并最终导致没有深度的路上,在反价值的同时,将真正的良善、美好的东西一起毫不留情地抛弃和否定了。因为,当反对伪价值的时候而不确定真正的价值,那么,伪价值之伪又如何区分?这反对活动又有什么意义?在真与善两个维度被现代艺术颠覆之后,艺术之美的品性也必然随之倾覆,美的艺术变成了丑的艺术,以丑为美已成为现代艺术的座右铭。像这样丧失了真诚之真理和价值的“艺术”难道是真正的艺术吗?回答只能是否定的。其结果,艺术或赤裸裸地沦落为商品,或仅作为小圈子内自娱自乐的杂耍。这难道不是我们目前国产电影至少部分的事实吗?
艺术之最大的悲哀在此,出路何在?
也许,以张元、贾樟柯、娄烨、王小帅等为代表的第六代的艺术主张和实践是对这一倾向的纠正,他们的很大一部分影片以一种纪实性的风格呈现出个体生存状态,表现为破碎的片断化的叙事,扬弃戏剧冲突和巧合,随意截取一段日常生活流程,而常使用的一些手法如同期录音,跟镜头、实景拍摄、长镜头,也是为了强化影片的纪实风格。张元就曾半带无奈半带自嘲地说过:“我要的是客观,绝对的客观,客观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这种写实风格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影片的主题狭小和边缘凡俗的创作心态。第六代许多影片的题材,已从“摇滚青年”(《北京杂种》)等带自传性的人物身上,扩展到更边缘和弱势的人群。例如,从张元的《东宫西宫》开始,中国银幕第一次直接触及到一个禁忌的话题——同性恋。影片力图探索人性的丰富多样,并表现出对每一种选择的体谅与尊重。贾樟柯的《小武》(1997年)中,表现了一个名叫小武的小偷在剧烈变化的时代生活中,对友情、爱情、亲情美好幻想的丧失。《站台》则试图“以老老实实的态度来记录这个年代变化的,反映当下氛围”。王超的《安阳婴儿》(2001年)中,则表现了妓女、黑道头目和下岗工人三个不同社会底层人物的命运。这都可以看出,他们的影片是纪实风格的虚构性影片,以最为朴素平实的方式,力图唤起人们对乡土、对变动社会中个体生命的关注与悲悯。
然而,问题在于:这种白描、写实化的“客观”立场在这样一个需要重提信仰以及价值观念大转换,良知、正义、公平、美和善等都遭到冲击的时代,是否是艺术家应该具有的姿态?作为面向大众的文化产品不表明自己的立场,岂不是精神上的犬儒主义!他们拒斥“宏大叙事”而转向对自我感觉和情感的发掘,但又由于缺乏绝对的价值信念,常常陷入没有普遍意义和美学形态的个体性情感的咀嚼和发泄,而没有深入到本体论、生存论意义上的真理层面。如此,中国电影就还没有从美学意识上提出和解决问题,仍然是观念、道德乃至情绪的简单的传声筒,因而也就不具有超越有限的终极关切的意义。在我看来,现时代中国电影的美学困顿就产生于此。
三、重申电影的美学精神
要解决中国电影当下的美学困顿,必须重申美学的精神。
换言之,电影作为艺术,应该具有内在的精神力量,亦即对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根本信赖和承担——对人所归依的精神家园的信赖,对生命的忠诚。“艺术应从‘本真’的意义上给我们迷失的心灵寻找到一条通向‘神性’的路,它必须揭示生活的‘应当’或展示‘可能世界’的生存方式。艺术总是人的‘创造物’,‘创造’的本意就是构想并描绘出一个人们所向往的世界,它遵循的原则是超越而不是自私、是理想而不是现实。”[1] (P66)在艺术的世界中,我们的理想可以自由翱翔,本真的生命能够实现,而这,恰恰是作为审美活动的艺术的价值所在,是一切伟大的艺术理应也必须具有的品格,也是古今中外的艺术实践所证明了的真理,是生活于俗世之中的大众对包括电影在内的艺术的祈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美学精神。
的确,对艺术的要求,实乃植根于人类内心对无限、永恒、绝对的追求,是人为了摆脱尘世的平庸而向真、善、美的自由界升腾,是人不仅要在物质生活领域,更要在精神世界实现自己的全面本质。艺术,就是在感性的世界中寄寓着现世的超验理想,蕴涵着人生的信仰。如德国浪漫主义诗论家、诗人费·施莱格尔说:“诗的应有任务,似乎是再现永恒的、永远重大的普遍美的事物。”[2] (P327)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也说:“运用各种艺术可能供给的方法,来表现亲切感、精神性、色彩、对无限的追求。”[2] (P218)德国音乐家瓦格纳说:“音乐所表现的东西是永恒的、无限的和理想的。”[3] (P132)凡·高更说:“我想用永恒来画男人和女人,这永恒在从前是圣光圈,而我现在在光的放射里寻找,在我们的色彩的灿烂里寻找。”[4] (P34)同样,西方近现代美学中,席勒的“神性”、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尼采的“永恒大生命”、伏尔泰的“生命”、柏格森的“生命冲动”、弗洛伊德的“原欲”、海德格尔的“存在”、马斯洛的“自我”等等,及至当代英美新批评的“作品”,现象学的“形而上的质”,解释学的“意义”等等,莫不是把审美和艺术与超验的彼岸世界,实即“终极实在”相联系。
中国美学中也有类似的思想,老子的美学是以“道”为中心的。“道”的基本特性就在于它是宇宙的本体和生命。由这一思想出发,中国古典美学将对“道”的观照视作审美和艺术的最高目的。他们认为,审美客体并不是孤立的、有限的“象”,真正的大“象”必须体现“道”,体现“气”,才会成为审美对象。审美观照也不是对于孤立的、有限的“象”的观照,审美观照也必须从对于“象”的观照进到对于“道”的观照。这也即老子所说的“玄览”,庄子所谓的“见独”、“朝彻”,宗炳所说的“观道”、“味象”。中国古典美学的独特范畴“意境”,同样是与这一思想相通的。在中国的艺术家们看来,艺术的最高境界乃在于直抵宇宙人生的极致,而这极境,绝不在直观感性形象的摹写,而是要深入对象的内心,以“得其环中”,“在于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尺幅上换去毛骨,混沌里放出光明”[5] (P66)。也正如《易》云:“天地氤氲,万物化醇”,艺术(绘画)的最高境界在于要在作品中把握到天地境界,在于“透过鸿蒙之理,堪留百代之奇”[5] (P61)。这“天地氤氲”,这“鸿蒙之理”不正是超感官、超经验的终极所在吗?所以,绘画要“写长景必有意到笔不到,为神气所吞处”[5] (P64),对这样的绘画的观赏也才是艺术的旨趣所在,也才能“澄然一心而腾踔万象”[5] (P64)。这不正是艺术所应追求的吗?
就电影来说,虽然因其建立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基础上,而使其具有和传统艺术不尽相同的特殊性,但就其本性而言,美学内涵和文化品位仍然是电影不可或缺的基本品性。换句话说,美学精神是电影获得灵魂和人性深度的根本保证。人们观赏电影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一是纯感官愉悦影片。代表是好莱坞的豪华的大制作的惊险科幻电影以及国内的所谓“大片”等等。二是满足观众情感交流需要层次的电影。这其实是所有的电影应该有的品性,是惟一不可替代的,它反映本民族乃至人类情感中观众最容易接受、最容易共通互动的部分,因而是各国电影的主体类型。它的核心是电影里的人以及人性和人情,最基本的就是植根于现实、和观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三是满足审美需要的电影。简单地说,就是从这类电影中不仅看到形式的美、动人的故事,还要从中感悟到某种哲理,激起人们对人生、历史、宇宙等根本性问题的思考,产生人生感、历史感和宇宙感。只有到了这个层面,电影才具备了真正的艺术品格,对它的欣赏也才是真正的审美欣赏。美学精神也蕴含于此。
因此,所谓电影的美学精神,不仅是刀光剑影的“视觉奇观”,也不仅是囿于情感情节的“影戏”,而应与人的生存和生命本性相关。电影自出现于人们的生活中起,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而存在的,并随着人类精神生活的不断丰富而日渐成熟和完善,人与电影的关系必然也应该是一种审美关系,人所要求于电影的,首先是它的美的属性。这既是电影艺术的历史和现实,也是我们在认识电影并对其进行定位时所必须坚持的理论基点。我们对电影艺术的思索,必须深入到人的活动,人的生存状态中去,只有与人生相联系,电影艺术才会放射出它应有的光芒。真正的作为艺术的电影,类似于宗教感的宣言,一种具有宇宙意味的信仰,它作为一种人生的理想及理想境界的揭示,成为人的生命之流。我们才会在电影艺术中领悟着生命的“本真”,或与“终极实在”相遇,因这领悟和相遇,我们在生活中保持着开阔的胸襟和坦荡的心灵,不再因一己之小利而烦恼,不再因抽象的教条而束缚自己的生命。这样,生活不仅不缺少美,而且也不再缺少灵性和发现,“万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因而,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业余艺术家,使生活本身成为一条奔腾不息的艺术之流,这既是艺术的理想,更是理想的人生。电影艺术之所以要与永恒、绝对的“终极实在”相连,要确立自己的超越维度,一句话,强调中国电影要重铸美学灵魂,道理就在这里。
在此意义上,电影作为艺术,理应具有一切真正的艺术都应具有的根本品质:给现实中的人们以精神的泊锚地,给理想以冲破现实藩篱的梦幻空间,让有限的生命获得其永恒和超越性的慰藉。我们需要轻松和发泄,但更需要生存的“诗意”;我们需要让电影发挥它的教育或引导功能,但它首先应以“人性”的方式观照人的存在。所以,让我们漂泊无依的灵魂有所抚慰和归依,使我们的精神有所提升,对人生和世界有所感悟,才是电影艺术所应追求的境界。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有丰厚的美学底蕴作为依托,这,也就是我们重申中国电影美学精神的原因所在。
注释:
①本文所谓“中国电影”,按照国内电影界约定俗成的用法,意指中国大陆电影,而不包括港澳台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