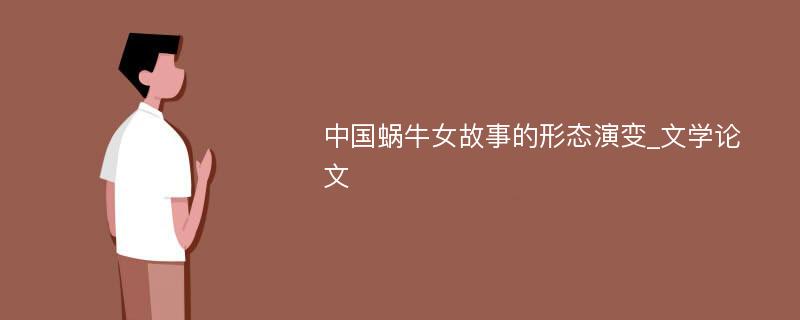
中国螺女故事的形态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形态论文,故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与异类(动植物精灵)的奇特婚恋,是世界各国人民最为喜闻乐见的幻想故事之一。在中国,最流行的是田螺姑娘故事。钟敬文先生30年代撰写《中国民间故事型式》,在45个常见类型中,就有“螺女型”。丁乃通先生于70年代编撰《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将“田螺姑娘”列为400C型,收录古今异文30余例。我研究撰写《中国民间故事史》,它也是重点论析的故事之一。现以搜求到的古代书面文献资料为主,就它的形态演变作如下评述。
《白水素女》及其他
它的早期文本,最著名的当然是署名陶潜(365—427)所撰《搜神后记》中的《白水素女》(或题为《谢端》)。故事以今福州为背景。晋安,郡名,晋初设置,郡治侯官,即今福州市。“晋安”,有的文本作“晋安帝时”,即公元397—418年之间,汪绍楹校注本《搜神后记》指出古代典籍中各书所引均无“帝时”二字,应予以删去,其说有理。故事主人公不仅是一位“躬耕力作”的农民,还是“少丧父母,无有亲戚”的孤儿,孤儿是中国异类婚故事中古今常见的角色。本篇由如下四个情节单元复合而成:男主人公谢端拾得一异螺;螺精幻化成女子为之“守舍炊烹”,操持家务;谢端违犯禁忌窥视其本相,迫使螺女离去;女主人公留下含有魔力的螺壳,贮米谷可取用不尽,谢端因而致富。其引人入胜的情节结构和饱含农家情趣的生活画面,同后世口头传诵的同类型故事众多文本十分接近。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白水素女》就作为螺女故事之生动而完整的文本呈现在我们面前,不能不令人惊叹。它是怎样构成演变的呢?这就要联系相关资料进行探索。
唐人编撰的《初学记》引晋人束皙(?—300 年后)《发蒙记》道:“侯官谢端,曾于海中得一大螺,中有美女,云我天汉中白水素女,天矜卿贫,令我为卿妻。”束皙死后约半个世纪陶潜才出生,《发蒙记》所载似为中国螺女故事的最早书面文本。
南朝梁任昉(460—508)所撰《述异记》中的文本与之大同小异:“晋安郡有一书生谢端,为性介洁,不染声色。尝于海岸观涛,得一大螺,大如一石米斛。割之,中有美女,曰:‘予天汉中白水素女,天帝矜卿纯正,令为君作妇。’端以为妖,呵责遣之。女叹息升云而去。”
略早于任昉的南朝宋刘敬叔(生卒年不详,426 前后仍供职于朝)在《异苑》一书中,有下列记述:“阳羡县小吏吴龛,于溪中见五色浮石,因取纳床头,至夜化为女子。”这里的“五色浮石”为何种异物难以断定,从它夜间可化为女子这一神奇功能来看,却同异螺相同。特别是男主人公小吏“吴龛”,同唐人《原化记》所载螺女故事中的男主人公小吏“吴堪”音同字异,在口语中实为同一角色。因而这段文字也可作为螺女故事的一个特殊异文看待。
还有一则关于白水素女的记述来自明版《万历续道藏》收录的《搜神记》(明人张国祥校梓)中。它似乎尚未受到民间文艺学家的注意,值得引录备考:
素女,天神也。昔闽人谢端有淑行,居室寒素。一日出江边,见一大螺偃仰卧状如斗,异而爱之,因载之以归,畜且珍焉。每外,扃钥严密。返则盘餐罗具如宾筵。端甚疑惧,侦诸长老,或告之曰:“此必若有异畜也。”端乃悟其为螺,为密伺,见一姝丽甚。端前礼问其故,神亦不隐,遂应之曰:“我天汉中白水素女也。天帝遣我为君具食,今限满当去,故为君所窥。我去,留壳与君。”端用以居粮,其米常溢。今福州西北三十里有螺江,其得名由此云。
这里的《搜神记》是作为道教神谱来流传的,它表明在明代以前,以白水素女身份出现的螺女,就作为道教俗神之一受人供奉了。再据《道藏提要》称此书“所涉地域甚广,遍及燕关邹鲁齐梁吴楚,殆采摭传闻而成。”从故事结尾提到的“螺江”得名于此也可以看出,它一直作为具有宗教性的地方传说在福州一带民间流传。这样,它的内容就并非完全来自《搜神后记》的文本,而是有口头传说作依据了。
将上述材料作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比较综合之后,我们对以《白水素女》当代表的中国早期螺女故事的形态构成,可以作如下推断:
它的原初形态是,一贫困男子于海边偶拾得一异螺,螺精幻化成女子与之同居。男人为好奇心所驱使窥视其异类本相,螺女不得不离去,以致美梦归于幻灭。古人心理受“万物有灵”观的支配,螺这类遍地可见的水中小动物,不仅螺肉鲜美可食,螺壳的构造也十分精巧,这就使它成了逗人喜爱,并隐含神异性的小动物。民间流传有螺蛳组字预示天机的传说,以及螺蛳是由观世音菩萨的头髻化成的传说;螺壳还是佛教、道教在宗教活动中使用的重要法器之一,称为法螺。螺女形象即产生在这一民俗文化背景之上。异类婚故事中的蛇女、狐女等,人们在驰骋幻想时,联系其原型的生物特性,常赋予她们以复杂的两重性格,螺女则以更为单纯的温顺而姣好的姿态出现,闪现出独特光彩。
至于早期的螺女以奉天帝之命降临凡间的白水素女的身份出现,同魏晋时期盛极一时的神仙道教的思想浸染有关。“素女”本为道教崇信之女神,《素女方》、《素女经》早有流传。赋予“天”或“天帝”以鉴察人间善恶、赏善罚恶的职能,在魏晋时期的道书中也常有记述,如《抱朴子内篇》就明白道出:“夫天高而听卑,物无不鉴,行善不怠,必有吉报。”在这一信仰背景上,螺精就升格为天上仙女;由男女本性生发而成的爱恋之情,也相应地转变成“天帝矜卿纯正,令为君作妇”。同时冲淡了由窥视引起的冲突,“今限满当去,故为君所窥”。这些改变增强了故事的道德教化意义,却使民间口头文学的自然朴野之趣失去了不少。因素女被列入道教神谱,享受民众香火,无疑促成了螺女故事更广泛的流传。但来自中国近现代民众口头的螺女故事,还是以形态朴野者居多,呈分道扬镳之势,并没有被《白水素女》这一模式所拘限。
《搜神后记》旧题为晋代大文学家陶潜所撰,近现代有一些学人疑为伪托。经有关文学史家考证,《搜神后记》中虽有后人增益之处,定为伪托并无确证(注: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44页。)。就《白水素女》一篇的写定而论, 从《发蒙记》、《述异记》所载及素女祠的存在,可见其本事早已传于民间,陶渊明笔下所述故事主干,并非杜撰。但在谢端怀着好奇心询问邻里及设计潜归窥探秘密这些细节描述中,却饱含世俗生活情趣与文学意味,和见于道书的文字迥然有别,这里显然有着陶氏作为文学家的艺术修饰在内。在故事叙述中融入了某些小说化成分,却又不失口头文学清新自然的本色。《搜神后记》中的许多篇都是如此,它们对推进故事的世俗化与文学化,无疑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唐人笔下的《吴堪》及其影响
三四百年后,螺女故事又出现在唐人皇甫氏的《原化记》中。因男主人公姓名变易,篇名改称为《吴堪》。张友鹤选注的《唐宋传奇选》,选入本篇并作提示道:“这是一篇在晋人所写螺精故事基础上而加以发展的作品。作者写一个小市民,勤恳供职而又鳏独无依,上帝可怜他,叫白螺精做他的配偶。可是县官却生妄想,想出种种方法迫害他;由于螺精的智慧,结果县官自食恶果,被火烧死。这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愿望。”
本篇被列入新版唐宋传奇选本,表明了它在文学史上的重要价值。但把它作为出于文人创作的一般传奇小说来看待,完全忽视了它有口头传说的依据,并不切合实际。故事出在常州义兴,即今之江苏宜兴县,《毗陵志》卷十四《诸庙》宜兴县下载:“西泽庙在县治四百步,旧传吴堪之祠。”“吴堪之祠”的遗存,同当地口头盛传吴堪故事显然是分不开的。再从故事文本来看,也呈现出来自民间口头的鲜明印记。因时空背景的变化,又显示出具有时代与地方色彩的变异。
谢端“少丧父母,无有亲属”,“恭谨自守,不履非法”;吴堪“少孤,无兄弟”,“性恭顺”,他们都是由孤儿长大,秉性勤谨恭顺的单身汉。从故事的发端便可看出它们实属同一类型。谢端偶得一大螺,也有讲他是在海滨钓得大螺。吴堪却因爱护门前的溪水而得白螺。螺女告诉他,自己奉天帝之命下凡,不仅是出于“哀君鳏独”,还因他“敬护泉源”。在一则古代民间故事里,将保护环境的意识表现得这样鲜明,是十分有趣而又发人深思的穿插。本故事的独特之处,集中表现在后半截。男人窥视螺精化身的情节被淡化,螺女没有要求离去,男女爱悦,相敬如宾地建立起了一个美满的小家庭。豪强霸道的县官妄图借故强占螺女,接二连三地给吴堪出难题。由螺女出面破解难题直至用一把大火埋葬恶人,使故事获得了引人入胜、大快人心的艺术魅力。
县官索要的“虾蟆毛”(青蛙毛)、“鬼臂”和“祸斗”三样东西,都是世界上根本没有的,不过是他挖空心思的无理刁难罢了。螺女因有神通,先交了两样东西搪塞了事。本篇情节着重围绕“祸斗”展开。《原化记》的通行刊本中作“蜗斗”,经笔者考证,系“祸斗”刊印之误。“祸斗”是民间传说中的一种食人吐火的怪兽,明人邝露在《赤雅》中就写道:“祸斗,似犬而食犬粪,喷火作殃,不祥甚矣。”有的学者用“祸斗”来注释《山海经·海外南经》中的“食火之兽”。我以为本篇关于“祸斗”这一情节单元,似从三国时期吴地高康僧会所译之《旧杂譬喻经》卷上第22《祸母》一篇化出。试看原文:
昔有一国,五谷熟成,人民安宁,无有疾病,昼夜伎乐无忧也。王问群臣:“我闻天下有祸何类?”答曰:“臣亦不见也。”王便使一臣,至邻国求买之。天神则化作一人,于市中卖之。状类如猪,持铁锁系缚。臣问:“此名何等?”答曰:“祸母。”曰:“卖几钱?”曰:“千万。”臣便顾之问曰:“此何等食?”曰:“日食一升针。”臣便家家发求针。如是人民两两三三,相逢求针,使至诸郡县扰乱,在所患毒无。臣白王:“此祸母致使民乱,男女失业,欲杀弃之。”王言:“大善。”便于城外,剌不入,斫不伤,掊不死。积薪烧之,身体赤如火;便走出,过里烧里,过市烧市,入城烧城。如是过国,遂扰乱人民饥饿。坐厌乐买祸所致。(注:见常任侠选注《佛经文学故事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40页。)
这部印度佛经中讲,某国王乐极无聊,派人去大街上买来一个叫“祸母”的怪物,它以针为食,为了填饱它的肚子,四处求针,弄得举国不得安宁。后来想处置它,用木柴烧得它遍体通红,奔跑起来,“过市烧市,入城烧城”,终于造成一场毁灭性的灾祸。把这篇佛经寓言里的“祸母”和《吴堪》中的“祸斗”相比较:两个怪物如猪如犬,外形相似;作为一个炽热而具有破坏力的火球,实体相同;它们都出自人们的新奇想象,借以表达对自食恶果的统治者和压迫者的尖锐嘲讽。这些契合一致很难用不谋而合的平行雷同来解释。汉译佛经故事对中国民间故事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我以为从“祸母”到“祸斗”,也是其中有趣实例之一。
正是唐人笔下的《吴堪》,围绕“祸斗”所展开有趣叙说,使它别具一格。丈夫在无端受迫害时的一筹莫展,和螺女的有胆有识勇于抗争相映衬;几个难题不但没有难倒女主人公,作恶者反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妙趣横生的叙说中交融着热烈的爱憎。不再对所叙之事均信以为实,而是使用艺术虚构手法,有意识编织新奇动人的故事,从这里可以看出唐代民间故事的显著进步。
《吴堪》这篇螺女故事不断被后人引述。元人编撰的《湖海新闻夷坚续志》中有《井神现身》一篇。男主人公姓名为“吴湛”,与“吴堪”明显相关,或系“吴堪”之误;但螺女以“井神”身份出现,她来到男子身边,不是给她作妻子,而是拉他修仙学道:“君食吾馔,当得道矣。”可以判定是经道教信徒改编,丧失口头文学特质的一个拙劣文本。
明人周清源撰有一部拟话本小说《西湖二集》,据文学史家考证大约刊行于明崇祯年间(1628—1644)。其中《祖统制显灵救驾》一篇,借吴堪故事作“入话”(引子)。结尾处“有诗为证:吴堪忠直不欺,感得天仙下降;知县贪财好色,害得阖门遭丧!”它用小说笔法来演绎这篇唐代故事,保持和发展了原作富于人民性的特色。对螺女故事的传承所起的作用,似乎不应低估。
我在清人笔记小说中搜寻螺女故事,发现了两篇,一是程趾祥《此中人语》中的《田螺妖》,二是陆长春《香饮楼宾谈》中的《螺精》。它们都以农民拾取田螺,和螺女结合,螺女却中途离去为情节主干,变异之处表现为:《田螺女》在螺女离去若干年后,“二子均举进士,为母请封,福乃备空棺,置女前次所衣之衣而葬之,并立其石曰田夫人之墓。”按“母以子贵”的世俗逻辑,硬凑了一个平庸的大团圆结局。《螺精》这一篇则在农民娶亲时,让螺女扮作新娘进入洞房,演成两个新娘同时出现,使人难辨真假的喜剧,在一月情缘已尽之后悄然离去。在上述清代文本中均未看出《吴堪》这一型式的影响,而是按口头叙说原型故事中螺女离去的型式旁枝逸出,生发新的枝节。它们并未给这个著名类型增添多少光彩,但显示出这个著名故事类型在民间口头文学中根深蒂固的生命力。
20世纪以来的螺女故事追踪
20世纪以来采录发表的螺女故事,笔者所见约40篇。故事叙述仍围绕着螺女的离去或去而复归以及男女主人公同邪恶势力抗争这两大主干情节展开,却同其他婚恋故事类型串连混合,演变成一个广泛触及世俗婚姻家庭生活,情节繁复而意趣丰富的故事群。下面是最具代表性的几篇。
1.同“百鸟衣”型混合,以巧智和宝物战胜迫害主人公的皇帝、县官等。如广西毛难族的《螺蛳姑娘》。男主人公是一个孤儿。螺女原形被孤儿窥见之后没有离去,告知他:“我是龙王的小女儿,见你诚实忠厚,孤苦伶仃,特意来和你作伴。”孤儿将螺女画像带在身边上山打柴,引得皇帝、大臣上门将螺女抢进王宫;孤儿按螺女吩咐上山打猎,缝制成一件“百兽袍”穿在身上混进王宫;在螺女的巧妙安排下,孤儿同皇帝换装,穿上“百兽袍”的皇帝被猎犬咬死,孤儿和螺女回到家乡。这个《螺蛳姑娘》也流传在广西壮族地区。此外,高山族的《螺蛳变人》,虽没有出现“百鸟衣”或“百兽袍”,而是安排男人以卖首饰混进王宫并杀死皇帝,其基本形态也属这一型式。
2.同“龙女”型混合。如山东的《葛常和海蚌姑娘》。这位自己作主寻求人间伴侣的海蚌姑娘,没有因男人窥视原形而离去,却来自龙宫受到龙王的迫害。小伙子后得到一块“荡海石”制服了龙王,才使他们的美满结合得以实现。
3.同“两兄弟”型混合。如贵州布依族的《螺蛳姑娘》。兄弟分家,哥嫂欺负老实厚道的小弟,自己占了水沟边的好田,却把半山腰的贫瘠坡田留给弟弟;天旱时节,一群群螺蛳在弟弟田里吐水护秧苗,使他获得丰收;从一枚大螺中化身而出的螺女又做了他的媳妇。恶毒的哥嫂几次加害都事与愿违。故事情节虽不曲折,却洋溢着农家生活情趣,别有一种朴实清新之美。
4.同“张郎休妻”型混合,表达“多情女子负心汉”的主题。如贵州苗族的《孤儿和龙女》。孤儿钓得一只美丽的小蚌壳,养在水缸里变成一个女子给他做家务,原来她是偷偷来到人间的龙王的小女儿;龙女给他带来了富裕生活,生了儿子,他经受不起头人的挑唆,蛮横无理地赶走龙女,演成无法挽回的家庭悲剧。中国民间盛传《张郎休妻》的故事,将无端被休弃反而因祸致福的女人,和休妻后败落乞讨的男人进行鲜明对比。有的地方还说旧时厨房里供奉的灶神,就是张郎的化身(他在原来妻子面前羞愧难当,一头撞死在灶上,妻子便把他影像留在灶前了)。将螺女因被男人窥视本相不得不离去,改变成被负心男人所休弃而能自强自立,这也是贴近民众现实生活而富有积极意义的一个有趣变异。
5.将故事附着于本地特有的自然风物,如“螺女江”、“螺蛳山”等等之上,使其演化为优美的风物传说。如福州市的《螺女江》和桂林市的《螺蛳姑娘》。《螺女江》前半沿用谢端和螺女相爱的情节,后半叙玉帝强令螺女返回天宫,螺女不愿离开,最后葬身于闽江江口。人们便称这条江为“螺女江”了。至今江边还竖立着一块“螺仙胜迹”石碑。《螺蛳姑娘》则讲同小伙子结成夫妻的螺女,同欺凌他们的县官应对抗争,最后化成了漓江边上的螺蛳山。两地传说都着眼于在同邪恶抗争中来突现螺女的高尚品格,口头叙说的故事赋予这些奇丽山川以艺术生命,使它们获得了感人至深的永恒魅力。
关敬吾先生在为《日本民间故事选》的中文版写作引言时指出:日本的《鱼妻》同中国的《田螺精》均属于同类型的“关于奇特的女佣人”的故事(注:见〔日〕关敬吾编《日本民间故事选》中文版,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情节结构单纯接近原型的螺女故事,在今天中国的民间文学中也仍然可以找到,被《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浙江卷》收录的《田螺姑娘》就是一例。小伙子偶然拾回的田螺,养在水缸里化作螺女作了他的妻子,几年之后,只因孩子想外婆,父亲说了声:“你娘是田螺精,哪来的外婆?”螺女不能忍受这种歧视便愤然离去了。故事中以螺女作为出身卑微、勤恳善良,却渴望得到丈夫与世人尊重的农民妻子的象征性形象,我以为是接近故事的原型特征的。但这样的文本因故事情节较为平淡,在中国口头和书面传承中都没有发生大的影响。继“白水素女”作为女神降临凡间之后,螺女在唐人笔下,又被改塑成有胆有识、机巧过人的“女强人”形象,同幻想故事中的龙女角色相融合,故事以战胜邪恶获得团圆给人以大快人心的感受,闪射出浪漫主义的光彩。
一千五百多年来,中国螺女故事的形态是在世俗文化与宗教文化相互渗透,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会通,以及口头传承和书面传承的交错并举中不断演变,渐趋繁复精美的。
以《吴堪》为代表的这类螺女故事在口头文学中得到长足发展,有着深厚的现实生活基础。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对压迫者的抗争十分普遍,而且一浪高过一浪。女性虽处于社会最底层,为自尊自强的进步思潮所激荡,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却不断提高。沿着世俗化这一主导方向发展的口头叙事文学,不能不在角色配置、情节构造上发生种种变异。中国口头文学中的“女强人”形象格外引人注目,虽染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其基础却是社会历史进程的折射。
中国民间故事总体上自然属于世俗文化,它同宗教文化既彼此对立又互相渗透。道教文化对螺女故事的演变有着深刻影响。在道教信仰体系中,草木虫鱼等等均可成为精灵,精灵不仅能化身为人,学道向善者还可成仙;如果逞凶作恶即成为人们鄙视的妖精或妖怪。宇宙间神仙、精灵鬼怪和芸芸众生,都要受天帝(宋以后称为玉皇大帝)的统辖。螺女型故事情节结构的演化,同上述道教构造的这一宇宙模式图息息相关。螺女以“白水素女”女神姿态出现,就是受道教信仰浸染的结果。化身为人的螺女,在人间男子心目中通常被作为仙女看待,这是他们得以实现美满结合的前提条件。螺女一旦被邻人和自己的男人视作精怪,婚姻和家庭就会走向破灭。“窥视”的母题在日本螺女型故事中往往被叙述者所强化,中国故事却是在“螺仙”与“螺妖”之间发生纠葛冲突。有趣的是,直到今天,“女妖精”仍然是人们痛斥那些坏女人的口头禅。在此情况下,“窥视”母题便自然被淡化了。
中国民众将道教信仰中的神仙与精怪形象借用来象征善良与邪恶势力的对立,其意义是积极的。它成为中国幻想故事富于民族文化特色的具体标志之一。可是在《井神现身》中,让螺女以不食人间烟火的女神身份出现来寻求修道伴侣,使其世俗性完全丧失,变得面目全非,就不值得称道了。
佛教思想信仰的影响在中国螺女型故事中尚未看出。本文提到的《旧杂譬喻经》中《祸母》之楔入《吴堪》,应作为中国和印度民间文学相互交流影响的一个实例来看待。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由“祸母”化出的“祸斗”,原本是压迫者无理刁难,强行索要的一种怪物,后来却以其具有食火粪火之特性,出人意外地给了压迫者以严厉惩罚。人们的爱憎情感,借这个新奇有趣的情节得到痛快淋漓的宣泄。它在近现代口头传承的螺女或龙女故事中被广泛借用,这种人造怪物的名称,有的叫“祸害”,有的叫“古怪”,有的叫“窝罗害”,有的叫“稀奇货”,名称是随口叫出的,它的情节构成和艺术功能则和《吴堪》一脉相承。中国民间故事形态之由简趋繁,主干上不断生长出新的枝叶,情趣日趋丰富多样,同吸引外来故事的滋养显然是分不开的。
螺女在广阔时空背景上,不用说是以口头传承为主。但它很早就进入文人视野,化成多种书面文本,这些书面文本在基于口述材料的同时,又有不同程度的缀合加工。《白水素女》和《吴堪》,都曾被作为文人创作的小说看待,其中有着作家个人艺术智慧的鲜明表现。这些书面文本的传播不能不对口头文的变异及艺术性的增强产生有力影响。中国许多故事类型的传承都有口头与书面方式交错并举的特点,单一的口头传播难以使故事得到充分发育,螺女也是其中一个颇有代表性,值得民间文艺学家重视的实例。
收稿日期:1998—07—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