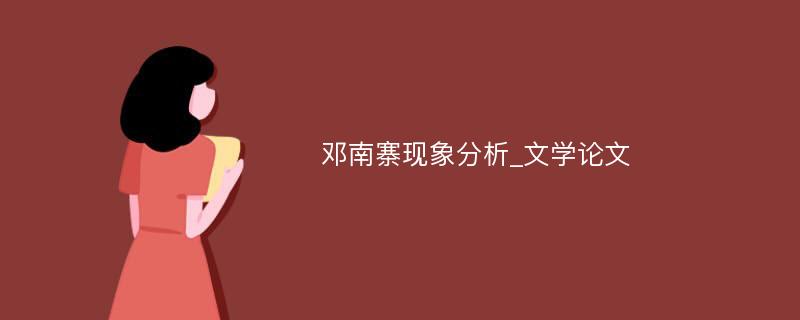
“邓南遮现象”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论文,邓南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南遮(1863—1938)这个名字在19世纪末到本世纪30年代曾经风靡意大利及整个欧洲。他不仅是当时意大利文坛上的一位最有影响的唯美主义代表作家,而且在当时意大利政坛上也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有人用“邓南遮现象”来形容和概括邓南遮这位人物出现的必然性和典型性。每当我们探讨和评价这位意大利杰出的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时,总有一种面对一个“难解之谜”的感觉,因为他的出现和存在不仅涉及到一种文学现象,还涉及到当时一代人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心态。
人们都注意到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事实:邓南遮在生前就立下公证,把他于1923年用13万里拉购置的一幢占地7公顷的别墅命名为“意大利人之胜利”赠给了意大利人民。这幢别墅于1937年被意大利政府指定为国家级博物馆。邓南遮在呈递公证书时写道:“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亲自创建和改造的。别墅的每一个线条轮廓,每一种色彩的搭配,都显示了我留下的风格,以及我想表现的那种风格的痕迹;表达了我对过去的追忆,对英雄业绩的崇拜和向往,对祖国未来的憧憬。”“这里是我思想的一种形式,我灵魂的一个方面,我激情的一种表现。”
参观者从悬挂在别墅音乐厅内的天花板上看到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邓南遮去维也纳上空散发传单时驾驶的那架飞艇。那次他作了历时6小时又40分钟的飞行,航程达1100公里。坐落在别墅一侧山冈上的是当年意大利海军部门为表彰他的卓著战功而赠送给他的一艘战舰,为了纪念1920年7月10日在一次海战中殉难的海军将士,邓南遮称其为“陈列在祭堂里的死难战友的血衣”。展室里那两枚金质奖章、三枚银质奖章、一枚铜质奖章和三枚军功十字勋章以及他于1916年1月16日因飞机失事迫降在海面而失去右眼后的画像,还有他挥舞马刀驰骋在疆场上的照片,都鲜活地勾勒出邓南遮当时崇尚武力和“英雄业绩”的那种英雄主义气概。
邓南遮当初是个最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爆发,他就写信给当时的总理安东尼奥·萨兰德拉,他向总理请战:“您知道,我整个一生就期待着这一时刻,在一个无视荣耀的民族中忧郁而又气愤地生活过来的我,终于可以看到一种我所期盼和奢望的奇迹了。意大利的上空将重新展现民族的雄姿。意大利人民创建丰功伟业的时刻来到了,我为国家洒热血的时刻来到了。”
所以,右眼失明后的邓南遮在战地医院的行军床上熬过一夜后就蒙着动过手术的右眼逃出病房到了威尼斯,在卧床治疗期间写下了悲壮的诗集《夜歌》(1921),它以一个伤员的日记形式讴歌战争,赞美英雄般的献身精神。在不断的军事冒险和创建所谓的“英雄业绩”中去“享受无上的乐趣,领略那狂热的激情”,把生命“只看作是一种冒险的游戏”,“不赢得胜利就无须苟活着”的这种非理性的超人的唯意志论使这位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信徒变成了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一个十足的战争狂。否则就很难想象,一个1881年入罗马大学攻读文学,出入上流社会豪华的沙龙与贵妇人调情打趣的阔少,居然在1919年11月还策动并指挥了一次向意大利东北部与南斯拉夫交界的阜姆城进军,并在那被占领的“自由王国”里当了一年的首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意大利立下赫赫战功的邓南遮,就敢于反对意政府在国际和谈中所采取的妥协立场,坚决主张把阜姆城划归入意大利的版图。
邓南遮的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和非理性的狂热的激情与后来统治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思想体系和理论基础当然是一脉相承,一拍即合。所以,长期以来,人们在谈到邓南遮与法西斯的关系时,往往给他冠以“法西斯御用文人”这顶帽子。所谓“御用”就是“为反动统治者所利用而作其帮凶者”,综观邓南遮在法西斯统治期间的言论和行动,这么提也未尝不妥。1926年,墨索里尼派遣的法西斯军队在北非的黎波里登陆后,邓南遮寄给墨索里尼一组题为《远洋业绩颂》的诗篇,为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涂脂抹粉,诗中还肉麻地吹捧墨索里尼“今天你的每一根血管里都洋溢着活力”。所以,始终没有正式参加法西斯的邓南遮却深为法西斯所赏识,墨索里尼本人对他也推崇备至。1927年成立的国立学院就是为研究和推广邓南遮全部著作而成立的一所学术机构;1929年墨索里尼亲自去探望患阑尾炎开刀的邓南遮;1938年3月1日邓南遮患脑溢血去世后,墨索里尼还去住所向他的遗体告别。这些都是无法抹去的历史事实。
然而,正如意大利当今著名的历史学家、政治家、意大利政府终身议员莱昂·瓦利亚尼(1909—)所评述:“邓南遮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绝不可同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同时,却也不能认为邓南遮的政治思想与法西斯主义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纪念邓南巡逝世40周年会上的讲话》,1978)意大利前众议院议长、杰出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乔瓦尼·斯帕多利尼(1925—)还把邓南遮列入《缔造意大利的精英》(1989)一书《美好的时代》篇目中最后的一位精英,作者在分析意大利当时的具体历史氛围时指出:“1921年初以来,法西斯运动内部酝酿着种种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发展的最终结果,将导致选择邓南遮作为这个运动的新的真正的首领。”看来邓南遮后期被认为是有与法西斯若即若离的倾向,如1921年末和1922年初,当邓南遮撤出阜姆城之后的一段时期里,“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人同邓南遮这位政治诗人也有密切的接触,想采取一项民族和社会协调的政策从而抑制法西斯运动的发展,并阻止法西斯向罗马进军。”“这位心情忧郁的诗人,在那些日子里忙于同无政府主义者、自由意志论者、共和党人和社会党人建立联系。”难怪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对才华横溢的邓南遮一直抱有戒心,还派过一支由警察头子为首的警卫队对他加以特别“监护”。
如今当人们步入“意大人之胜利”国家博物馆那个命名为“假面人”的展室里时,在一面边框用铅浇铸的镜子上方,挂有邓南遮于1925年墨索里尼来访时所赋的一首颇有讽刺意味的打油诗《致来访者》:
莫非你随身戴着的是
那珂索斯[①]的镜子?
啊,假面人哪,
这是一面铅铸的镜子,
你可得把面具戴好,
千万小心哪,
别朝钢玻璃镜面上撞。
应该看到,自幼就以拿破仑为偶像的邓南遮一生中竭力追求的是“禁止的梦幻”和“难以效仿的业绩”,他身上洋溢着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的能动性和极端民主义精神,集中代表了当时的社会思潮:非理性主义、盲目的民族主义和强权主义。这种思潮正是法西斯主义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政治思想的土壤,而以邓南遮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当时也成为法西斯赖以发展壮大的社会基础,所以法西斯党魁们推崇他、仿效他,也利用他,但体现在邓南遮身上的更多的是表现自己“惊人的精力”、“惊心动魄的业绩”和“超人的意志”。对此意大利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萨佩尼奥(1901—)用寥寥数笔对邓南遮作了逼真的描绘:
“哗众取宠的狂热,希望人们象明星似的崇拜他,把他看作是超凡的人,看作是生活在某种神秘而又非凡的环境里的人。”然而,邓南遮几十年所追求的一切却都是“轻率、妄动的,也是肤浅的,缺乏深厚的生活根底,不符合意大利的国情。”(《意大利文学史纲要》第3卷,1947)
邓南遮本人生前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他晚年所写的《百页密书》中不无伤感地评述了自己一生所走过的路:“目睹这惨淡而又痛苦的人生,我真想抹去曾有过的那些经历……如今回想起来真令人毛骨悚然……真想抹去邓南遮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抹去这样一个文艺家和英雄的存在……”
就象在冒险的军事行动中为显示自身的“超凡”而赢得对其个人的盲目崇拜一样,邓南遮的文学创作也同样以“寻求和表现非凡的美的感受”为宗旨而曾在整个欧洲享有盛名,首先深得当时以女性读者为主体的崇拜者的赏识。她们读了邓南遮的作品“感到自身得到了赞美和颂扬,似乎进入了一个香气扑鼻、神秘而又富有魅力的世界”。对他的作品的这种艺术感染力,意大利当代现实主义作家勃朗卡蒂曾作过这样的评论:“它们象是一个奇妙的装置,大大地增加了人的听觉、嗅觉、视觉和触觉:芳香、光线、声音和触感一齐向你涌来,我小小的知觉犹如一根发了疯的指南针胡乱地作着反应。”(《资产者和无限》,1938)
传统的文学评论家都惯于用“唯美”、“性感”、“词藻华丽”、“形式主义”、“超人意识”、“无限的自我表现”、“随心所欲”、“缺乏真实感”等用语来概括邓南遮作品的艺术特点,但是谁也无法否定他是唯美主义的最典型的代表,并达到了唯美主义创作的顶峰。“生活是美和力量两种形式的永恒的交替,是声音和色彩的交响乐(当声音和色彩与大自然交融在一起的时候)。人们就能从中享受到无上的乐趣,领略到那狂热的激情。”邓南遮用他一生实践并完成了这“美”和“力量”的永恒交替:一种把美的价值作为整个人生的实质含义和人生的全部价值的观点、理论和实践。
剧作《琪奥康妲》(此剧于1924年就由张闻天先生译成了中文)最能代表这种把艺术作为人的存在价值的最高体现,作者通过主人公的悲剧性的遭遇,阐明了艺术家只有在艺术创作中才能找到自身价值的观点。邓南遮在该剧本的扉页上引用的是艺术大师达·芬奇的一句名言:
人生一切美的东西总会终结,
唯有艺术的美才是永恒的。
邓南遮的确称得上以文学手段捕捉蕴含在生活中的美的感受的“能工巧匠”,他真的把“生活就是艺术”作为自己的信条,在其文学创作中善于运用多种艺术手段,从怪诞、颓废、丑恶、乖戾的现象中提取美的意境,“传达出他人无法表达的东西”(《密书》,1937),从而大大扩大了艺术创作的范畴和作品的感染力。对于邓南遮的作品,有权威的评论家历来都意见不一。意大利当代著名的美学家、哲学家、历史家和文学评论家克罗切(1866—1952)认为:“邓南遮作品的思想内容绝对地渗透着色情和肉欲。”“当他把明澈、安详、恳切的目光投向事物时,他是个艺术家,而当事物在他看来超越了它们之间的表面联系,就象断了线的珍珠项链似的时候,唯一贯串它们的就是偶然、任意的幻想和色情的诱惑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称不上是个地道的艺术家。”(《批评》,1914)
从哲学范畴来看,超脱一切伦理道德标准的非理性主义正是邓南遮文学创作的思想基础,所以他总是采取逃遁现实的态度,运用寄情于梦幻的手法去追求所谓“超凡脱俗”的梦。有些文学评论家认为他的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生命力也正在此。评论家雷那多·塞拉(1884—1915)曾这样评论道:“邓南遮的作品有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纯真的表现力,他的作品不公式化,也没有条条框框,因而他所写的篇章很洒脱、轻松,就象一片绿叶,本身就很完美,无须加以修饰;又象一滴清水那样晶莹、纯洁,读来令人感到清新,感到生活的温馨,而不是空洞和乏味。”(《批评》,1935)
从艺术风格方面来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片断文学”家和“艺术散文”派对邓南遮的作品这种正面的评价是占主要地位的。然而,当年的《呼声》杂志却认为他的作品是“华而不实,机械生硬,矫揉造作”的典型。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萨佩尼奥也认为邓南遮是企图“用文学语言雕琢出一种‘无法效仿的生活’,从而把文学作品看作是镶嵌画一样的装饰品。”“他的写作技巧虽然娴熟高超,文采虽然高雅,但其作品总给人以一种仓促完成,缺乏逻辑思维,偶然凑合,心血来潮的感觉。”所以在唯美派文人中,比起帕斯科利(1855—1912)和法国的一些代表作家,邓南遮被视作只是具有华丽的形式,“折衷主义地模仿和接受欧洲文学所给予人的启示和诱惑力”,却又没有去“更充实地感受并拥有更深厚、更热切的抒情风格,而只是体现了广泛的和变化多端的表现技术的综合。”(《意大利文学史纲要》,1947)。
可是,意大利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桑圭内蒂(1930—)却认为邓南遮作品中所描绘的是“一个他公开声称为‘无法实现’的美丽的神话,是以阿拉伯式的五彩缤纷的华丽图案,揭示了现实生活的难以辨认的实质。”(《意大利20世纪文选》,1992)
应该说,宣扬“艺术至上”的邓南遮本人连同他的作品都带有严重的消极倾向,因为他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人生观是悲观主义的,其哲学思想是形而上学的,艺术观是形式主义的,他断然摈弃了艺术创作的社会目的和伦理道德准则;然而,唯美主义的文艺观毕竟是邓南遮代表当时文人们选择的一种出路,就象他采用那种逃循世俗的生活方式一样,他采用的这种与现代社会相抗衡的文艺手段,正是他在精神上和艺术上为自己寻觅到的赖以生存的土壤和避风港。
而且,尽管后人对于邓南遮及其作品有着各种不同的评论,争议也很大,但有一点是谁也不能否认的,那就是意大利20世纪的许多作家,不管他主观愿望如何,几乎没有一个不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邓南遮创作思想的影响的。光从意大利诗坛来看,实际上20世纪上叶的新诗人,无论是属于未来派的,还是属于隐逸派的或是呼声派的,以及不少“艺术散文”家们都难以摆脱邓南遮这位语言巨匠的影响。1951年著名的当代诗人蒙塔来(1896—1981)曾大声疾呼说:“如果想要奠定一种新诗歌的基础,就必须要超越邓南遮。”由此可见,邓南遮长期以来对意大利诗坛的影响之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从思想上与极端民族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实行了彻底决裂,注重文学创作的政治思想性和社会意义的新现实主义应运而生;60年代初期以反传统为旗帜的新先锋派文人在欧洲文坛展现了新的风采,反映现代人异化的工业文学也随之出现,邓南遮的影响才大大减弱。到了70年代以后,在文化艺术商品化的浪潮冲击下,邓南遮那种孜孜不倦地追求艺术创作的“精美”和“升华”的精神,以及他用使艺术脱离社会现实的途径来弥补和解决文人与现代社会的关系的做法,似乎有其潜在的说服力。正如当代文学评论家贡第尼(1921—)所指出:“当今评论界的任务是要公正地把邓南遮的作品从多种角度联系起来看,以探索其实质性的东西。”(《统一后的意大利文学》,1968)。
究竟如何深入剖析和客观评价这样一位叱咤风云的历史文化名人,至今仍是文学界一个值得研究和探讨的课题。在我国,自20年代起对这位唯美主义的代表作家的主要作品皆有过译介;对邓南遮的作品有过入木三分的研究和探索的要数杰出的诗人、剧作家和散文家徐志摩(1985—1931)了。36岁就早逝的徐志摩认为,邓南遮是19世纪末年出现在意大利文坛上灿烂群星中的一颗“放射着骇人异彩的彗星,它曳着光明的长尾,扫掠过辽阔的长天”。徐天摩钦佩邓南遮的创作才干,称赞“他的笔力有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深彻与悍健,有弗洛贝的严密与精审,有康赖特擒捉文字的本能,有歌德的神韵,有高梯埃雕字琢句的天才。他永远在幻想的飓风中飞舞,永远在热情的狂涛中旋转”。徐志摩还给了他一个“不雅驯”的名称:“怪杰”,认为“这样的怪人,只有在放纵与奢侈的欧南可以产生,也只有纵容怪僻,崇拜非常的意大利社会才可以供给自由发展与表现的机会,他的著作就是他异常人格的更真切的写照;我们看他的作品,仿佛是面对赤道上的光炎,维苏威火山的烈焰,或是狂吼着的猛兽。他是近代奢侈怪诞文明的一个象征,他是但丁、米凯朗杰罗与薄加丘的民族的天才与怪僻的结晶。”(《徐志摩全集》近年来,邓南遮的诗歌和小说的中译本问世,但数量很少,译介不多,研究的就更少,留有很多空白。原因之一,大概是邓南遮是一个在十分复杂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十分复杂的人物,所以,出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多年来对邓南遮这位“怪杰”和“彗星”的研究似乎形成一种“禁区”。诚然,对这样一位在意大利文学史上有过重大影响,又与当代文坛有着密切和复杂关系的代表人物,既不能采取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态度,也不能采取漠视和回避的态度。本文只是提出个人粗浅的看法,并向读者提供一些有关的资料和信息,以能共同对“邓南遮现象”进行更恰如其分的辨析。
注释:
①那珂索斯(NARCIST),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他只爱自己,不爱别人,屡次拒绝女神瑗科对他的求爱,爱神阿佛洛狄忒为惩罚他,使他变得只爱恋自己在水中的倒影。最后他憔悴而死,死后变成了水仙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