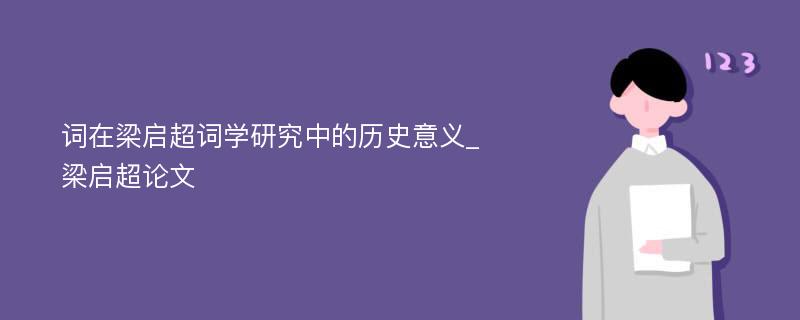
梁启超的稼轩词研究之词学史意义——兼论近世关于豪放词的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世论文,豪放论文,之词论文,意义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32(2006)01—0057—06
南宋词人辛弃疾的作品数量为宋词之冠,艺术风格独特,而且作品的社会内容极为丰富,是词史上杰出的词人。然而宋以来的词学家将稼轩词视为“别调”或“变体”,未能真正认识其价值。中国近代政治家和思想家梁启超于晚年曾对词学产生浓厚兴趣,他的词学论著虽然在其浩瀚的著述中仅是国学研究的一个很小部分,但其研究方法的科学与思想的深邃,对中国现代词学的发展是有显著影响的[1](页77—78)。在其词学研究中稼轩词是主要的对象,用功既多且深,首次揭示了稼轩词的社会意义,着重阐释了它的爱国主义精神。梁启超力图恢复辛弃疾在历史上的真正地位,展现其英雄业绩,使人们不仅以词人来看待这位历史人物。他希望通过关于辛弃疾的研究以探索中国民族文化所蕴蓄的一种积极的精神,它也许能使中华民族振奋起来。梁启超对稼轩词的喜爱与关注是与中国近代以来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精神相关的。自从他以社会学的方法阐扬了稼轩词的社会意义之后,词学界改变了对稼轩词的认识,也改变了词史的“正宗”与“变体”的传统观念,导致了对豪放词的重新评价,而且发展到以辛弃疾为主的豪放派作为宋词发展的主流,而将许多婉约词人作为一股逆流。现在我们回顾近百年词学的进展时,关于豪放派的评价问题仍值得重新审视,而且它作为一种学术现象值得我们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所以很有必要对梁启超关于稼轩词的研究及其影响进行探讨。
一
梁启超在青年时代即与词学结下因缘,其长女令娴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记述:“家大人于十五年前好填词,然不自以为工,随手弃去。令娴从诸父执处搜集,得数十阕。”[2](页275) 据此则梁启超于1894年22岁时已开始作词,在晚年更为酷嗜,今《饮冰室词》存词60余首。他虽然有用周邦彦、吴文英、张炎词韵之作,但长调作品的艺术风格则是近于稼轩词的,风格豪放而沉郁,例如《满江红·赠魏二》的“使不尽,灌夫酒;屠不了,要离狗。有酒边狂哭,花间长笑。剑外惟余肝胆在,镜中应诧头颅好”,《贺新郎》的“不信千年神明胄,一个更无男子。问春水干卿何事:我自伤心人不见,访明夷别有英雄泪。鸡声乱,剑光起”,词中激烈悲壮的情绪与恢弘雄浑的意象皆深受辛弃疾与陈亮唱和诸词的影响。梁启超的名篇《金缕曲·丁未五月归国旋复东渡却寄沪上诸君子》的“瀚海漂流燕,乍归来、依稀难认,旧家庭院。唯有年时芳俦在,一例差池双剪。相对向,斜阳凄怨。欲诉奇愁无可诉,算兴亡已惯司空见”,显然是学辛词《摸鱼儿》的比兴手法而寄托遥深之作。
中国古代儒家重视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而且认为它必须与音乐相结合才能产生广泛的社会效应。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东渡日本,曾提倡“诗界革命”,探索诗歌的政治教化的新途径,主张恢复诗歌与音乐结合的关系。他认为:“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在中国文学史上诗歌总是与音乐结合而并行的,由此产生了不少的时代文学。梁启超认为这种传统自清代以来已经断裂,古代儒家的乐教为士人放弃而为乐工优伎所利用,这必将削弱诗歌的社会功能,亦不利于诗歌自身的发展。他将中国诗歌的现状与近代西方相比较说:“读泰西文明史,无论何代,无论何国,无不食文学家之赐;其国民于诸文豪,亦顶礼而尸祝之。若中国之词章家,则于国民岂有丝毫之影响耶?推原其故,不得不谓诗与乐分之所致也。”[3](页58—59) 以诗歌作为改造国民品质的工具,这与儒家的诗教说是不同的,它强调的是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而不是向民众施行政治教化。然而重新建立诗与乐的关系却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梁启超将希望寄托于词体的改进。他说:
凡诗歌之文学,以能入乐为贵。在吾国古代有然,在泰西诸国亦靡不然。以入乐论,则长短句最便。故吾国韵文,由四言而五七言,由五七言而长短句,实进化之轨辙使然也。诗与乐离盖数百年矣,近今西风沾被,乐之一科,渐复占教育界一重要之位置,而国乐独立之一问题,士大夫间或莫厝意。后有作者,就词曲而改良之,斯其选也[2](《序》)。
梁启超将词体纳入广义的诗学,从诗歌与音乐的关系考察,认为词体是诗歌进化的必然结果,而且是诗与乐结合的典范形式,所以希望改良词体以之为现实的教育服务,从而达到改造国民品质之目的。他深感戊戌变法的失败是由于未得到广大国民的响应与支持,因而改良社会必须改造国民的品质。他曾设想选择具有教化作用的古代和当代诗词谱以乐曲,特别建议将岳飞的《满江红》谱出,使之广泛流行以宣传爱国思想。在《饮冰室诗话》里,他选录一些感慨时事、悲壮激烈的作品,如梁伯隽的《摸鱼儿》、《金缕曲》,何铁笛的《满江红》,蒋万里的《念奴娇》,黄遵宪的《金缕曲》等,认为它们“气象壮阔,神思激扬,洵足起此道之衰”[3](页110)。这些作品都是清季词家有意学习稼轩词豪放风格的。梁启超非常看重它们的社会意义,认为由此可使词学复兴。
梁令娴的《艺蘅馆词选》选两宋词人84家,录辛弃疾词27首,为所选作品最多的一家,表明编者已具新的词学观念,对豪放词特为推重。这显然是家学渊源所致。梁令娴还附录了其父关于稼轩词的评语若干条,乃是其父导读时由她随手记下的。评语甚为简明切要,着重指明作品的主旨,以便循此线索去理解全篇的意义。《念奴娇·书东流村壁》是辛弃疾南归之初在江阴签判任满时作的怀人之词,情调缠绵婉曲,但梁启超却指出“此南渡之感”,以为它超越了儿女之情而别有深刻的寄意。《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作于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辛弃疾与陈亮唱和之后,作者追忆当年的英雄气概,面对被朝廷废弃的现实,梁启超指出此词“无限感慨,哀同甫,亦自哀也”。《青玉案·元夕》自来以为作者是在追求一种自甘冷落的高洁情怀,或者以为是寓写对于真理的发现,但梁启超则认为是“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寄托了政治失意的情绪。以上都是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理解稼轩词之主旨,发掘作品深蕴的意义。《贺新郎·赋琵琶》写唐明皇遗事,以唐喻宋,国家兴亡之感已经明显,梁启超则分析其艺术结构的特点,认为“琵琶故事,网罗胪列,乱杂无章,恰如一团野草,惟其大气足以包举之,故不觉粗率;非其人勿学步也”[2]。从这些评语可见梁启超对稼轩词的思想与艺术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但是此时尚沿袭传统的方法,属于鉴赏的、感悟的批评,尚缺乏具体的分析。从梁启超的创作和欣赏的作品已表现出他的审美倾向是喜爱豪放沉郁的艺术风格,而关于稼轩词的评语,则表明确有真正的学习心得。林志钧谈到梁启超与稼轩词的关系说:“王静庵谓南宋词人其堪与北宋颉颃者唯幼安一人,其推挹也如此。饮冰室好之尤笃,平时谈词,辄及稼轩,盖其性情怀抱均相近。”[4] 梁启超对稼轩词的喜爱除了性情怀抱与辛弃疾的英雄人格相近而外,还因晚清以来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危难命运及革命思潮之涌起的历史条件而使稼轩词的思想意义突显了。然而将稼轩词作为国学的内容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却是在梁启超的晚年。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他曾参照西方社会制度来设计改良中国社会,将西方近代的哲学和政治思想较为系统地介绍入中国,热切希望中国臻于西方的物质文明。1919年他旅欧考察西欧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情况,残酷的现实使他对西方的物质文明和文化精神深感失望。法国哲学家蒲陀罗对他说:“你们中国着实可爱可敬,我们祖宗裹块鹿皮拿把石刀在野林里打猎的时候,你们已不知出了几多哲人了。我近来读些译本的中国哲学书,总觉得它精深博大。可惜老了,不能学中国文。我望中国人总不要失掉这份家当才好。”美国著名新闻记者赛蒙与梁启超闲谈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5] 这使梁启超受到很大的震动,成为价值观念转变的契机。1920年他归国之后即主张尊重和爱护本国文化,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它,吸取西方文化以起化合作用,从而建立新文化系统。因此他转向学术研究,从中国的历史、哲学和文化里发掘积极的民族文化精神。他晚年研究稼轩词即是在此种意识支配下进行的,以辛弃疾为颇能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人物。这使梁启超能够高瞻远瞩,立足于前所未有的思想高度去阐扬稼轩词的爱国主义精神。
二
关于以文学改造国民品质,这在梁启超晚年仍是坚持的,显然因见到重新建立诗词与音乐的关系已经不可能了,于是主张通过文艺以向国民进行情感教育,以为文艺——音乐、美术、文学是实现情感教育的利器。1922年他为清华学校文学社诸生讲中国韵文的情感表现方式,探索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他认为人的情感虽然是本能的和现实的,其力量却可超越本能和现实,使自我生命与自然和社会迸合。然而情感有好的也有坏的,文艺即以感情的、形象的方式使人的情感升华,借以完成情感教育。中国韵文——《诗经》、《楚辞》、汉魏乐府诗、唐诗、宋词,它们作为传统文学亦能起到情感教育作用。梁启超将中国韵文的情感表现分为三类,即“奔迸的”、“回荡的”和“蕴藉的”。在分析这三类韵文时列举了许多词体文学作品,尤其突出了稼轩词的艺术价值。他认为宋词的大多数作品属于蕴藉的,如李清照等人的作品,而属于奔迸的和回荡的却很少,但宋词里最有价值的则是这两类作品。所谓奔迸的情感是突然爆发的激烈的情感,梁启超特别称许了辛弃疾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此词为南宋淳熙初年辛弃疾任江西提点刑狱时经造口而作。造口即皂口,在江西万安县西南。宋人罗大经说:“盖南渡之初,虏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还。幼安因此起兴,‘闻鹧鸪’之句,谓恢复之事行不得也。”[6](甲编卷一) 隆祐太后虽未逃至造口,但南宋初年金兵确曾侵扰赣西。梁启超说:“稼轩是比岳飞稍为晚辈的一位爱国军人,带着兵驻在边界,常常想要恢复中原,但那时的小朝廷却不许他;到了这个地方,忽然受到很大的刺激,由不得他那满腔血泪都喷出来了。”梁启超最欣赏的是宋词表现回荡情感的作品。此种表情方法是将盘绕在心中的情感细细抽绎出来,虽然也强烈,却以曲线的方式表现,而且情感交错复杂,具有网状的特点。他说:
词中用回荡的表情法用得最好的,当然有推辛稼轩。稼轩的性格和履历,前头已经说过,他是个爱国军人,满腔义愤,却拿词来发泄;所以那一种元气淋漓,前前后后的词家都赶不上……凡文学家多半寄物托兴,我们读好的作品原不必逐首逐句比附他的身世和事实,但稼轩这几首有点不同,它与时事有关,是很看得出来;大概都是恢复中原的愿望已经断绝,发出来的感慨[7](页110)。
他具体地分析了《摸鱼儿·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念奴娇·书东流村壁》和《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以为前两首是千回百折,逐层加深的,后一首是堆垒错落的,但它们皆非一般的伤春和离情之词,而是感慨时事的作品。作家创作时用什么方法表达情感,这取决于作家个人的审美兴趣,表现方法并不具有价值的标准。关于以文艺作为情感教育的工具和以情感表现方法确定作品的价值,这是梁启超在文艺理论上的局限,但在具体分析稼轩词时又强调了其内容的社会意义,而且尝试在分析过程中将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起来,这是一种新的探索。
1928年梁启超认真而全面深入地研究稼轩词。《稼轩词》的宋刻本有长沙的一卷本,信州的十二卷本和通行的四卷本。梁启超获得1924年新出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其中的《稼轩词》有甲乙丙三集,它与明末毛晋刊的四卷本和王鹏运翻刻的信州本在文字与编排方面皆有很大的差异。这引起了梁启超的兴趣。于是又借得明代吴讷抄本《唐宋名贤百家词》本之《稼轩集》进行比较,发现二者竟是相同的,但明抄本有丁集,而且甲集存有范开写于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的序言。此本四集大致是按创作时期编的,可以反映词人的创作发展阶段。梁启超遂完成了《跋四卷本稼轩词》和《跋稼轩集外词》。这是从文献的研究而获得的重大发现。
由于词体特殊的文学性质,宋人的词集里留下的历史线索极少。辛弃疾词集里题有纪年的仅19首,作品内容可证实年代的仅20余首,因此对稼轩词600余首作品的编年仍是困难的。然而要深入研究一位古典作家,对其作品的编年则是必需的基础工作。梁启超根据新的学术发现,着手对稼轩词进行编年考证,以明抄四集本提供的时地线索,参考辛弃疾历年的宦迹以及词中所涉及的地名与交游进行考辨,确实了编年的原则,制订了《编年词略例》①。此编年原则是在文献学上最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体现了一种先进的实证方法。《稼轩词疏证》是梁氏兄弟合著的,梁启超辑,梁启勋疏证。其中引用梁启超的编年考证计105条,皆标明为“饮冰室考证”。在编年工作的基础上,梁启超参考大量的历史文献,对辛弃疾的仕历大略已经清楚,遂编订《辛稼轩先生年谱》。1928年9月10日梁启超开始编著年谱,下旬因病入北平协和医院治疗,病中继续寻觅有关资料。9月22日他与友人书云:
日来撰成《辛稼轩年谱》并为稼轩词作编年,竟什得七八,又得一佳抄,用校四印斋重雕之元大德本,是正伪舛将及百条,深用自喜。一月来光阴全消磨于此中,再阅十日可蒇事矣[8](页1193)。
10月5日梁启超回天津,在病榻侧身执笔,继续草写断稿,至12日病体已不能支,写至庆元六年三月辛弃疾61岁家居铅山为文往哭友人朱熹,遂为绝笔。次年1月19日,梁启超于北平逝世。
《辛稼轩先生年谱》是梁启超研究稼轩词的最终成果,内容极为丰富,是词学史上词人研究的一个良好开端,而且具有典范的意义。此著是经得住学术检验的,影响极大。吴世昌于1931年著《辛弃疾论略》,实为评传性质之作,即“大体上是以梁任公先生的《稼轩先生年谱》为经”;邓广铭于1939年著《稼轩词编年笺注》时不仅采用了梁氏成果,而且于词作编年“大体均以梁氏所提出的方法为准则”;徐嘉瑞于1946年著《辛稼轩评传》,也以之为主要参考依据②。
梁启超晚年曾对其弟梁启勋谈到编著《辛稼轩先生年谱》的动机是:“稼轩先生之人格与事业,未免为其雄杰之词所掩,使世人仅以词人目先生,则失之远矣。意欲提出整个之‘辛弃疾’以公诸世。”③ 他力图恢复辛弃疾之真实的历史地位,宣扬其在南宋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爱国的英雄业绩和伟大的人格力量。辛弃疾是中华民族史上一种积极精神的代表者,这正是20世纪初年中华国弱民贫,处于乱世所应提倡的。梁启超对稼轩词从探究创作的历史背景和词人生平遭际入手,进而发掘创作的主旨及其社会现实意义。合观其对若干作品的分析与论述,辛弃疾的爱国精神与崇高人格便愈益显现。这样辛弃疾不仅是一位词人,其事业不再为词名所掩,还原其为南宋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摸鱼儿》一词运用传统的比兴手法,明显地寄寓了政治感慨,而且词意殊怨。梁启超经过细致分析此词后认为:“盖归正北人骤跻通显,已不为南士所喜,而先生以磊落英多之姿好评天下大略,又遇事负责,与南朝士夫泄沓柔靡风习尤不相容。前此两任帅府皆不能久于其任,或即缘诗可以怨。怨固宜矣。”④ “归正”即改正之意,南宋初年称自金国投宋者为“归正人”,他们在朝廷始终受到歧视、怀疑和排斥。辛弃疾因是“归正人”,其政治命运注定是坎坷的。梁启超由此视角切入以分析稼轩词,见到了其思想实质,成为理解其词的关键。梁启超辨析《沁园春·戊申岁奏邸忽腾报谓余以病挂冠因赋此》对待被劾落职的态度;辨析《贺新郎·陈同甫自东阳来过余》的辛弃疾与陈亮的交谊所体现的磊落峻洁;辨析《行香子·三山作》表现的任事负责,不顾时忌,志在雪大耻复大仇,这些皆是足以表现辛弃疾的崇高人格与伟大精神的。
梁启超不仅是全面研究稼轩词的学者,而且是最能认识其社会意义并给予高度评价的。这在中国词学史上是有非常重大意义的。自宋季词学家张炎以为辛弃疾等的“豪气词非雅词”以来,稼轩词是作为词史上的“异军”和“别调”而被否定的,被排斥于词家正宗以外。清代初年由浙西词派掀起的词学复兴运动,崇尚姜夔与张炎之词成为一时词坛风尚。常州词派理论家周济虽然在指示学习作词途径时将辛弃疾与周邦彦、吴文英、王沂孙并列为宋词四大家,但以为学稼轩词仅是求得词法变化的一个阶梯而已,最终是向集宋词大成者周邦彦词回归。王国维是否定南宋词的,但以为可与北宋词人颉颃者仅有辛弃疾,而其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而已。虽然有少数词学家推崇稼轩词,却不能改变其“别调”的地位。这些词学家无论对稼轩词是欣赏或贬抑,都基本上是对艺术风格的直觉的、感悟的批评,未能见到其真正的文学史意义。因此梁启超以较为先进的新的方法,着重阐释稼轩词的社会意义,并给予词史上最高的评价,这是学术思想的突破,体现了一个新时代的价值观念,由此导致了近世对豪放词历史地位的重新评价。
三
梁启超绝笔之后,中国社会正发生着深刻变化,新民主主义革命蓬勃地开展,现代社会科学学科纷纷建立,马克思的社会学说迅猛传播,抗日救亡运动掀起和抗日战争爆发,在此历史条件下,梁启超关于稼轩词的社会意义的论述为学术界所支持与发扬。他是将辛弃疾作为“一位爱国的军人”而定位的,这应是最合理的,但辛弃疾毕竟因事业为词名所掩,所以学术界仍视之为词人,却冠之以“爱国词人”了。1934年10月刘寿松于《国闻周报》11卷43期发表《辛稼轩的爱国词》,1940年7月祝世德于《新知识》1卷5期发表《爱国词人辛弃疾》,这新的历史定位皆是对梁启超意见的发挥。中华民族到了危险的时候,只有辛弃疾等的慷慨激烈的豪放词才能鼓舞民族精神,而那些缠绵悱恻、倚红偎翠的婉约之作背离了时代精神,难以为人们欣赏。辛弃疾是宋代豪放词的杰出代表,其获得“爱国”的殊誉,这标志着词学界对豪放词的传统观念的改变。词史上的“正宗”与“别调”问题是应当重新审视了。王季思于1939年在《词的正变》里开始从社会意义的角度肯定豪放词:
南渡以后,北方沦陷,强邻压境,民族的仇恨,中朝的颟顸,刺激着每一个志士的心。一班民族词人如辛稼轩、张元干、张孝祥、陆放翁、刘后村,大声疾呼,相继而起,豪放一派的词才到了极盛的境界,留下了许多慷慨激昂的作品,替词坛放一异彩[9](页292)。
此种倾向在新中国建立之后获得最适合发展的社会条件。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社会学,也曾是一切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古典文学研究中原有的社会批评方法也必然得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旧的社会批评重视文学的时代、种族、社会环境的因素,我国新的社会批评则增添了经济、阶级、重大社会问题等因素,这必然导致向庸俗社会学方向发展。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庸俗社会学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盘根错节,遂成为数十年来理论批评的基本方法。在只重视文学的社会意义时,古典文学研究又由于两极意识的支配,以为文学艺术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因此,我国文学史贯串着两条道路——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变得空前的密切。宋词豪放与婉约两大风格类型,因庸俗社会学的比附而演为两派的矛盾斗争。豪放词的开创者是北宋的大词人苏轼,他对以柳永为代表的传统的婉约词作了大胆的改革,他们是“站在敌对矛盾的两方面”,因此“后人把它分作豪放、婉约两派,虽然不十分恰当,但从大体上看也是颇有道理的”,豪放派“到了辛弃疾才算充分赋予生命而放射出异样光芒来”[10](页221)。辛弃疾等豪放词人反映了他们那个时代民族矛盾特征,表达了“广大人民的斗争精神”,其“文学风格的社会根源是当时民族斗争中错综复杂的现实矛盾”[11](页23、28)。词学家们的认识,循着这种逻辑直线前进,至胡云翼于1961年作的《宋词选前言》而臻于极臻。他认为:
辛弃疾、陆游两个伟大的爱国主义作家,以及团结在其周围的进步词人陈亮、刘过等进一步发展了南宋词。辛弃疾一生精力都贯注在词的方面,成就更为杰出。他继承着苏轼的革新精神,突出地发扬了豪放的风格。在总结前人的思想艺术方面的创获的基础上,进而扩大词体的内涵,使其丰富多彩,把词推向更高的阶段。他们的词作汇成南宋词坛一支振奋人心的主流——这就是文学史上著称的豪放派[12]。
豪放派是主流,而南宋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等婉约词人“与此相反,代表南宋士大夫的消极思想和个人享乐思想,在词坛里形成另外一支逃避现实,偏重格律的逆流”[12]。宋词的传统观念倒转过来,原来的“正宗”成为“逆流”,而“别调”则升为“主流”。
以稼轩词为线索,我们追溯了现代词学史上关于宋词豪放派认识的发展过程,可见到一种学术思潮发展的必然性,而它代表着一个时代主流文化居于统治地位的特征。因此从梁启超阐扬稼轩词的社会意义并高度评价辛弃疾的词史地位,经过发扬稼轩词的爱国主义精神,重新审视词的正变,将豪放与婉约作为敌对矛盾,到主流与逆流对抗之论,这侧面表现了进入20世纪以来社会价值观念的演进,而在那个特定时代里它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新时期以来,学术界进行了痛苦而深刻的历史反思,回顾现代词学关于豪放与婉约之争时,胡云翼受到严厉而苛刻的指责[13](页501—520),这是极不公允的。胡云翼早在1926年即主张宋词无流派,而且认为:“我们绝不能拿一种有规范的派别来限制他们。”[14](页62) 他在晚年不得不顺应庸俗社会学潮流,不得不改变固有观点,而那时若要争得学术的独立与自由则几乎是不可能的。
宋词分为豪放与婉约两个流派,这是词学史上的一种误会或附会,并无理论与事实的依据。“豪放”与“婉约”这两个概念在唐代司空图的《诗品》里是作为两种文学风格使用的。宋人论词使用它的亦是指某种艺术作风而并无流派的含义。明代词学家张綖在《诗馀图谱·凡例》后所附的按语里始将宋词分为豪放与婉约两体,“气象恢弘”是豪放风格的特征,“词情蕴藉”是婉约风格的特征,而以婉约为正体。张綖的意见很符合宋词的实际情况,对于把握宋词的艺术特点具有指导意义。我们纵观中国的各种韵文体裁,惟有以此两概念区分词体文学的风格是最恰当的,所以自此为词学界所接受。清初王士禛在《花草蒙拾》里论及故乡词人时引述张綖“论词体大略有二”,将“词体”偷换为“词派”。他虽然仍是从风格的含义来使用“豪放”与“婉约”的,但“词派”的概念却从此产生了极为错误的影响,造成长期的词学理论的紊乱,似乎宋词确实存在两大文学流派了。文学流派的概念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存在的,它亦基本上与现代文学理论中的概念是一致的。什么是文学流派呢?我们可作这样的理解: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某个作家群,他们有共同的文学思想和相同的文学风格,表现出基本思想与艺术特征的统一,体现了某种文学思潮,具有一定的组织形式或联盟,提出了新的理论纲领,于是形成文学流派。作家群体、艺术风格、文学思潮、文学流派,这些概念之间有联系,但绝不等同,亦不宜混淆。宋诗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几个流派,而宋词却不存在流派,此自有它们各自特殊的内部与外部的诸多原因。令我们深感遗憾的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使用流派的概念是极为随意的。他于1922年论及南宋的白话词时说:“南宋的‘时代文学’自然是陆游、杨万里的诗与辛弃疾一派的词,张孝祥、张元干、陈亮、刘过、刘克庄都属于这一派。”[15] 辛弃疾一派当然是指豪放派。胡适不仅沿袭王士禛之误,而又另分南宋词为白话派和古典主义。梁启超也在同年论及中国韵文的表情方法时引入流派概念。他关于回荡的表情法说:
回荡的表情法用来填词,当然是最相宜;但向来词学批评家还是推尊蕴藉,对于热烈盘礴这一派,总认为别调。我们对于这两派,也不能偏有抑扬[7]。
梁启超将豪放派另名为回荡表情的一派,视婉约为蕴藉表情的一派,这同样缺乏严谨的态度。这些流派概念的使用,皆不顾宋词的历史真实,亦是有失规范的。此问题现在尚值得我们的检讨与深思。
收稿日期:2005—06—21
注释:
① 梁启超:《辛稼轩先生年谱》附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八。
② 吴世昌《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二卷《词学论丛》第318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例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徐嘉瑞《辛稼轩评传》第18页,上海文通书局,1946年。
③ 梁启勋《稼轩词疏证·序例》。
④ 《辛稼轩先生年谱》第20页。
标签:梁启超论文; 辛弃疾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读书论文; 宋代历史人物论文; 摸鱼儿论文; 唐诗宋词论文; 宋朝论文; 宋词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