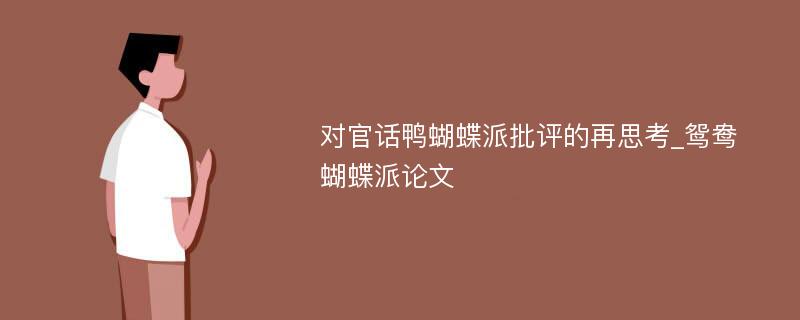
对鸳鸯蝴蝶派批评的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鸳鸯蝴蝶派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鸳鸯蝴蝶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拥有庞大作家队伍、影响广泛,为大众,特别是小市民阶层所接受的流派。它历时40年之久,跨越近、现代两个文学时期,其作品数量之多,远非新文学所能及,它几经沉浮兴衰,而流派特征则始终如一。故长期以来倍受批评,对此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呢?
(一)是否代表封建买办势力
长期以来,对鸳鸯蝴蝶派的批评都立足于他们在政治思想上代表封建买办势力这一认识上。其实,纵观鸳鸯蝴蝶派的创作,可以发现他们的作品大多具有爱国反帝的思想内容。最典型的作家要算该派重要成员周瘦鹃,他在《我的经历和检查》中自叙道:“自从当年军阀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21条卖国条约后,我痛心国难,曾经写过《亡国奴日记》、《卖国奴日记》、《祖国之徽》、《南京之围》、《亡奴家的燕子》等好多篇爱国小说,想唤醒醉生梦死的同胞,同仇敌忾,奋起救国,以致引起了上海日本领事馆的注意,把我列入黑名册,曾派特务到报馆找我,险遭不测。”这种爱国精神,在鸳鸯蝴蝶派中还是有很大代表性的。在民族危难深重之日,该派的《礼拜六》等刊物刊登过许多翻译和创作的爱国作品,用以激励国民的爱国之心。1936年前后,在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在周瘦鹃的《亡国奴日记》的封面上清晰地印着“毋忘五月九日”的字样。后来他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参加了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足以证明他爱国反帝的立场。包天笑列名于《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言论自由宣言》,张恨水更是以自己的创作表达了他坚定的抗日立场。这些,都有力地证明了该派成员不全是买办势力的代表。
那么,在反封建这一点上,鸳鸯蝴蝶派究竟表现如何呢?
说到反封建,很自然会联系到封建制度,封建文化意识,其中包括伦理道德、思想方法等等。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反映出他们对封建专制制度是不留恋的,对封建伦理道德应该说也是有不满情绪的,但因长期受封建文化思想意识的熏陶、禁锢、束缚,和广大民众一样,至少形成了循规蹈矩的个性特征,因而没有冲破封建桎梏的勇气,最终只能囿于封建的伦理道德而不可能冲破封建礼教的罗网,所以,其作品大多是悲剧的结局。故而,从总体上说,他们的作品还是反封建的,但又明显暴露了他们受封建意识支配的浓重阴影。从他们作品的主人公身上,可以看到他们决不是封建地主阶级、封建专制制度自觉的顽固的维护者,也不是旧道德的虔诚信奉者,但也决不是彻底的反叛者。徐枕亚的《玉梨魂》便可说明这些。
周作人在否定《玉梨魂》描写的肉麻时,同时也肯定鸳鸯蝴蝶派提出了男女爱情婚姻问题。这一问题提出的本身,起码说明他们对封建礼教中的“男女授受不亲”,“近女色乃大耻也”等的不满情绪和反叛行为。说明他们并不是封建的卫道士,这正是基于“发乎情”的判断基础上的。虽然包天笑说过,他“所持的宗旨,是提倡新政治,保守旧道德”。但纵览该派多数成员和他们的创作历程,与此言并不十分相符。因此,我们似乎可以把他们对封建伦理道德、礼教的反叛划归初级阶段,或者说仅是一种朦胧的觉醒。因为一到关键时刻,他们的主人公常常“止乎礼”而不敢彻底反叛了。
尽管他们不是买办势力的代表,而反封建又不彻底,但他们的这种犹疑、矛盾的行为,尤其是在“彻底”二字上,仍与五四时代精神相悖,在摧枯拉朽的新文化运动到来之时,在新文学倡导者彻底否定封建道德、封建文学的面前,他们是不合时宜的,更何况新文学还具有启蒙民众、振奋精神、改革社会的功利目的,从一开始就追求着一种正宗的唯一的文学。鸳鸯蝴蝶派所表现的文学功能和审美特征,与新文学倡导者是不同道的,也是违背正宗的唯一文学的建立的,因此双方的论争当属必然。
(二)游戏、消遣、趣味的审美意识之对与错
中国现代文学几乎从一开始就在寻找一种取代封建文学的正宗文学。“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陈独秀提出以白话为文学的正宗,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都提出要描写“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的为人生的文学主张。这些,显然是要发挥文学为人民大众的功能。但五四文学从整体格局看,还是处在一个多元开放的时代。文学研究会的出现更强调了为人生的文学功能,然而其内涵却日见趋于被压迫阶级的血和泪的文学范畴内。到了左联时期,便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时代,从而完成了寻找文学正宗的任务,从此,文坛以革命文学为主宰,文学的功能则突出其政治和教化作用。在当时“左”倾思潮的干扰下,在特定的战争年代的要求下,唯革命文学独尊,对其它文学思潮则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从而开始向文学的一元化格局发展,抗战以后,这种格局日益鲜明。
文学研究会公开宣布反对把“文艺作为高兴时的游戏或是失意时的消遣”工具,郑西谛大声疾呼:“我们需要的是血的文学,泪的文学,不是‘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冷血作品”。(注:《血和泪的文学》,《文学旬刊》第6号。)
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大背景下,鸳鸯蝴蝶派追求游戏、消遣、趣味以及金钱观念的审美意识自然便成了遭枪打的出头鸟。
其实,鸳鸯蝴蝶派的受众也是大众,不过,主要是大都市的市民阶层。这些作家把文艺当作茶余饭后的消遣,追求趣味性、娱乐性和消遣性,嫖学、赌经和黑幕均是他们描写的内容,他们公开宣称“不谈政治,不涉毁誉”。他们时时把握大众的心态,迎合读者的口味,重视和适应市场机制的商品意识,调整创作主体的表现方式,以适应市民阶层的审美要求,但他们在调整过程中是始终不会改变趣味性、娱乐性和消遣性的审美意趣的。这便成为鸳鸯蝴蝶派创作主旨始终不变,且能在受挞伐之后,又几次中兴的决窍。
鸳鸯蝴蝶派反映的是大众文艺中的一个部分,而不能代表整个大众文艺。固然,它赢得了属于大众中市民阶层读者的青睐,其作品畅销不衰,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发挥了文学功能的某些作用,但其审美意识却不完善。
文学的功能是由各种因素构成的,常常是任何一种文学都似乎具有多种功能,且各有主次之分。鸳鸯蝴蝶派同样如此,他不仅具有游戏、消遣、娱乐的功能,而且也具有寓教于乐的感化功能,不过前者是主要的。鸳鸯蝴蝶派的杂志《眉语寅言》明确表示:“锦心绣口,句香意雅,虽曰游戏文章,荒唐演述,然谲谏微讽,潜移默化于消闲之余,亦未始无感化之功也”。《〈游戏杂志〉序》说:“当今之世,忠言逆耳,各论良箴,束诸高阁,惟此谲谏隐词,听者能受尽言。故本杂志搜集众长,独标一格,冀藉淳于微讽,呼醒当世。顾此虽各属游戏,岂得以游戏目之哉”。可见,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不仅具有娱乐消闲的文学功能,同时也还追求具有在“潜移默化”中感化教育的作用,使人们在茶余饭后受到警戒和教诲,这即为通常所说的“劝俗”作用。这种方式是适合市民心理的,由于他们自身文化素养、生活习惯以及职业等方面特点的制约,更多的人便形成了他们工作之外便是娱乐的人生价值观,因此面对具有多种功能的文学艺术的选择,他们往往选择具有以娱乐为主的功能的文学形式,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在娱乐过程中,灵魂受到善恶的拷问,于潜移默化之中,匡正和改变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人生追求。自然,这一论述并不包括鸳鸯蝴蝶派中那些庸俗低级的作品。今天看来,这种文学功能是无可指摘的。
鸳鸯蝴蝶派之一次次的受到批评,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审美意识并不完善;另一方面,当时的审美标准也欠完善。
完善的审美意识应具有时代性、阶级性和民族性,在内容和形式,思想和艺术两方面都能反映审美感受、审美趣味、审美理想和价值,具有准确地认识和反映现实的“自由直观”意识。
鸳鸯蝴蝶派的审美意识是具有民族性的。该派实际上可归属于通俗文学类。朱自清《论严肃》(注:转引自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研究资料》。)将通俗小说具有的民族特性和文学功能作了精致的阐述:“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小说和词曲(包括戏曲)更是小道中的小说,就因为是消遣的,不严肃。不严肃也就是不正经;小说通常称为‘闲书’,不是正经书。词为‘诗余’,曲又是‘词余’;称为‘余’,当然也不是正经的了。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的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中国小说一向以‘志怪’、‘传奇’为主。‘怪’和‘奇’都不是正经的东西。明朝人编的小说总集有所谓‘三言二拍’。‘二拍’是初刻和二刻的《拍案惊奇》,重在‘奇’得显然。‘三言’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虽然重在‘劝俗’,但是还是先得使人们‘惊奇’,才能收到‘劝俗’的效果,所以后来有人从‘三言二拍’里选出若干篇另编一集,就题为《今古奇观》,还是归到‘奇’上。这个‘奇’正是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的。”中国小说正是从口头文学,说故事,讲传奇开始的,是一种茶余饭后的消遣,这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鸳鸯蝴蝶派正是从这一方面体现出了民族性的特色。另外,它注重市民社会的审美要求,即讲究故事情节的曲折惊险、跌宕起伏、新奇怪诞和叙述线索的清晰、简洁。使之既富有刺激性和趣味性,又注意市民性和人情味的交融,在形式上较好地体现出审美感受、审美趣味、审美理想和价值。
鸳鸯蝴蝶派是明末清初,中国门户开放后,随着工业的发达和现代大都市的成型,人们对报章杂志需求的滋生而发展的,它明显具有现代时代的特征,它总是迎合并适应时代新潮流,不断调整主体去满足客体的需求。赵苕狂在《花前小说》中说他们“力求能切合现在潮流”,“以现代现实的社会为背景,务求与眼前的人情风俗相去不甚悬殊”。这说明他们注意到了时代性,但他们所指的现代现实情景,是为创作适合市民阶层需要的审美情趣的文学作品,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视野狭窄的缺陷。新文学倡导者正是看准了他们忽视了中国当时是一个“到处是榛棘,是悲惨,是枪声炮影的世界”,如“武昌的枪声,孝感车站的客车上的枪孔,新华门外的血迹……”,因而认为这时代不适宜专写游戏、消闲、趣味文学。
趣味文学并非不可写。鲁迅曾说:“在实际上,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注:《过年》,《鲁迅全集》第5卷。 ),他还说:“说到‘趣味’那是现在确已算一种罪名了,但无论人类底也罢,阶级底也罢,我还希望总有一日驰禁,讲文艺不必定要‘没趣味’。”鲁迅认为“笑笑既不至于得罪别人,现在的法律上也尚无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规定,并非‘非法’,盖可断言”。但是,“说笑话”还要度时势、合国情。“当大乱压境之际,手无寸铁,杀不得敌人,而心里总是愤怒的”,无法再“笑嘻嘻”。由此可见,鸳鸯蝴蝶派对时代性的考虑并不周全。同样,当他们在认识现实、反映现实时,也只是顾及到了人民大众中的一部分市民阶层,而没有考虑各阶级各阶层的读者群,这自然也是不完备的。当然,如果什么都写,什么阶级和阶层都顾及,似乎有可能会丧失作家的审美个性特征,或许也实在太苛刻。然而,作家的审美意识是否更以时代阶级民族为重要的切入点和认识反映的对象,这才有可能更好更充分地发挥文学的功能性呢?自然,这是指民族处于一种严酷战争或生死存亡的非常时期而言的。
鸳鸯蝴蝶派的作品虽然以写哀情、艳情为主要内容,但也有爱国反帝的作品发表,在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的黑暗、揭露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方面态度也是积极的。在反对清王朝,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军阀统治,拥护武昌起义等问题上,该派的主要代表作家徐枕亚、包天笑、周瘦鹃、陈蝶仙、胡寄尘等表现出的政治立场与改良派还是有区别的。这些都促使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在作品的思想内容上有较大突破,蕴含着较浓的社会批判色彩,如张恨水的《八十一梦》,秦瘦鸥的《秋海棠》,都是具有代表意义的。当我们以审美内容来衡量鸳鸯蝴蝶派时,我们不难发现该派并不象一些批评家们所说的,他们只是专写哀情、艳情的封建买办文人。
当我们去纠正某种偏颇时,仍需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住实事求是这把衡量真理的尺子。我们不得不承认鸳鸯蝴蝶派的重头戏确实在趣味、游戏、消遣那一方。他们的审美感受、趣味、理想和价值虽然具有反封建的积极因素,然而并没有突破他们思想中残留的封建意识,尽管他们也去适应时代和形势的变化并反映在创作中,但其趣味、理想仍然只是迎合市民阶层的娱乐和消闲,甚至有意无意地在消闲中腐蚀和软化了他们的斗志,起到了消极的作用。这是很难令他们跨出既定的创作旨趣的,更不用说站在反封反帝斗争的前沿阵地,寓教于乐,引导市民阶层在娱乐、消闲之中陶冶情操,树立崇高而严肃的生活目的、人生价值和思想境界了。由于他们受金钱观念的驱使,寻找刊物图书迎合读者口味的门径,诚然,该派也的确获得了相当的读者群,人们也毋需抹煞它所能起到的潜移默化的劝善惩恶的教化作用,但其在畅销后面的动机,也不能否定其中的金钱主义的价值观。正如张恨水所说:“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而周瘦鹃更直白地称自己为“文字劳工”,按质论价,期待书畅销,发行量大,所得版税就高。不需讳言,这正是商品社会经济大潮中,某些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价值观、道德观的反映,或许它就是脱去旧知识分子酸味的现代人的品格。鸳鸯蝴蝶派并不认为这会亵渎文学,当然,如果他们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不只是为了钱的话。否则在这种金钱主义价值观的驱使下,鸳鸯蝴蝶派的作品难免出现艺术上的粗制滥造,甚至为了能多抽版税,竟然动用舆论工具,谎称销数之大,“竟虚增五六倍以上的销路以夸示于人”(注:雍文:《无耻》,《鸳鸯蝴蝶派文学研究资料》。)的宣传大有人在。从这一角度观照他们的审美感受、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其审美价值是存在的,然相对而言,并不能说是很高的。由此可见,鸳鸯蝴蝶派的审美意识是不完备的。
新文学批评家们把鸳鸯蝴蝶派批评得一无是处,该肯定的并没有充分肯定,尽管对其主要问题把握得比较准确。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恐怕来自于对审美标准的认识。鸳鸯蝴蝶派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学功能和审美追求,尽管并不完善,但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容许它在文艺的百花园里生根,成长,为完善自己而争妍斗奇,从而为文艺的百花园增添异彩。这应该是不容置疑的。但因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个历程几乎都处在非常时期,新文学从一开始便为自己限定了崇高的社会目标,受国际普罗文艺思潮影响后,更是自觉地努力把自己定型在严肃的、政治的、革命的、阶级的纯文学的审美标准里,对文学的娱乐功能采取一概排斥和否定的态度,片面地认为游戏消遣趣味的文学只属于小资产阶级,封建买办阶级,而不属于革命的无产阶级,由于前者统统是革命的对象,或是被列入改造甚于打倒之列。因此,鸳鸯蝴蝶派为小资产阶级、封建买办资产阶级去献上游戏消遣趣味的文学,理应遭到批判,这是其一。其二,在于新文学自诩为正宗文学,定于一尊的文学,因此,凡与新文学在文学功能、审美意识上有差异的文学均不能成立,这种审美标准显然是片面而带有霸气的,对此,我们也没有理由去批评新文学倡导者,因为这正是历史对他们的要求,他们视这种要求为一种崇高神圣的使命,并且不少人为实现它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遗憾地是这种要求与鸳鸯蝴蝶派的追求存在着较大的冲突,所以,鸳鸯蝴蝶派的悲剧命运在过去时代便是无可改变的了。今天,当我们跨进了新的时代,重新审视它以后,便感到那时的作法多多少少给生机盎然的多元开放的五四文学套上了无形的枷锁,使新文学逐渐走向了一元化的封闭状态,当我们反思对鸳鸯蝴蝶派的批评时,我们应该承认新文学倡导者们一面砸碎了封建文学的枷锁,另一面,又给自己带上了崇高的新的“文以载道”的枷锁。尽管鸳鸯蝴蝶派有许多的缺陷,但有人曾认为应带领他们一道前进,他们自己也反复声明与新文学的“原质”是一致的,只是形式上的差别,他们呼唤创作自由,要求尊重创作者的个性……这些似乎并非是无理的要求。但新文学倡导者自身也只能在历史的规范中调整自我,他们是无力改变历史的。
(三)鸳鸯蝴蝶派是不是“一股逆流”
文学史上众口一辞地认定“鸳鸯蝴蝶派”是“一股逆流”。其理由仍然是从他们的审美意识认定的。
对鸳鸯蝴蝶派的审美意识我们作过较为详细地论述,我们的结论很明确:他们具有爱国反帝的热情,他们对国民党腐败政治有过批判,他们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态度虽然是暧昧的,但是他们总是尽力地赶上新潮流,适应社会现实。白话流行,他们马上改用白话写作,新文学注意妇女问题、劳动问题、新旧思想冲突问题,他们马上模仿;那些专做“红楼一角”、“某翁”、“某生”的健将也改换了笔法。《小说月报》改革后,加强评介外国文学作品,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早就积极从事翻译介绍西方思想和文学作品,周瘦鹃在这方面是早有贡献的,他第一个把高尔基的作品译介到我国来,1917年出版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是经他翻译的,其中有数十位欧美作家的作品,还包括高尔基的《叛徒的母亲》。鲁迅、周作人肯定他:“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娱悦人之耳目,足为近来译事之光。”并说,在当时出版界犹为“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可见,他们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曾受到过异域文化的影响。就在胡适发难文学革命,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的同时,包天笑也改革语文,创办《小说画报》,卷首语是:“盖文学进化之轨道,必由古语之文学变而俗语之文学……自宋而后文学界一大革命,即俗话文学之崛然特起”,在编者《例言》第一条则提出:“小说以白话为正宗,本杂志全用白话体,取其雅俗共赏,凡闺秀、学生、商界、工人,无不咸宜”。该刊于1917年1月便面世了。其实, 包天笑早在戊戌之后便创办有白话刊物,所以,他说“提倡白话文”,“比了胡适之等那时还早数十年呢”。可见,他们并非闭关自守的冬烘先生。
以上事实,足以证明鸳鸯蝴蝶派是能顺应历史潮流的新派人物,他们决不是顽固的抱残守缺的遗老遗少,更不是封建制度的卫道士。正是他们具有对时代变革的敏锐性,而又能摒弃旧的套路,以最快的速度适应瞬息即变的社会现实,他们这一流派才能得以延续40年之久。或许他们的这种适应现实,使用白话作文的动机与他们的金钱主义的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但他们却没有固守文言阵地,似螳臂挡车一般阻挡新文学运动的开展和白话文的推广。据此,我们是没有充足理由称他们为“一股逆流”的。当然,他们也决不是推动社会的革新者。正如署名C.P.的作者在《白话文与恶作者》(注:转引自黄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研究资料》。)一文中指出的那样:使用白话文的作者并不一定都是严肃的改革者,鸳鸯蝴蝶派的某些作者在新文学的浪涛冲击下,只有随波逐流了。
可见,他们迅疾地接受新潮流,除了他们具有商品意识的敏锐性外,应该看到他们并不是从政治上主动而自觉地承担改造社会、革新文学的重任的,也没有具备主动地去思考如何推动社会前进的思想准备。因此,他们对国事采取的仅仅是以个人利益为轴心的态度,他们关心的只是他们个人写作的成败,报刊销售的多少。显而易见,尤其是在他们的兴盛期,他们顺乎潮流只是被动地为了自身的利益,说白了,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精明的出版商群体、优秀的“文字劳工”,而并非逆潮流而动的团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