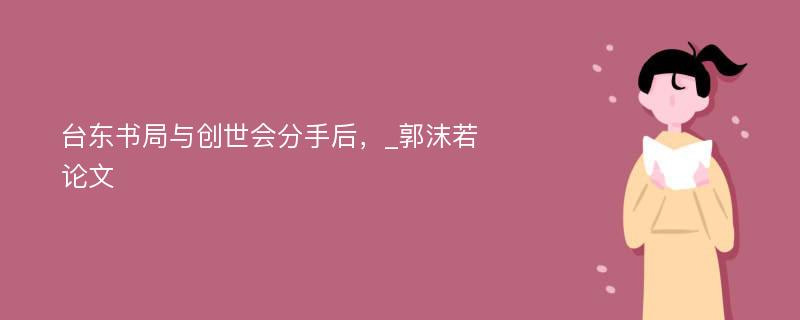
泰东图书局与创造社分手之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有关于泰东图书局与创造社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这方面的论文与专著也相继出现(注:著作是刘纳的《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论文有张勇、魏建《泰东图书局与创造社》,《郭沫若学刊》2000年第四期及《泰东图书局如何成为创造社的“摇篮”》,中华读书报2004年2月25日。)。这些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为创造社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但他们仅仅论述了前期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之间的关系,给我们所造成的印象仿佛是自从1924年9月1 日出版《洪水》后,泰东图书局与创造社之间的关系就此结束,两者之间从此后就再也没有发生任何关系。1933年9月《郭沫若书信集》由泰东图书局出版,郭沫若面对已经与之决裂数年之后的泰东图书局时“言辞之间,仿佛与泰东图书局从未有过芥蒂。其详情究竟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注:刘纳.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M].广西: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P234)
诸如此类的疑问一直在困惑我们。泰东图书局与创造社之间的藕断丝连的分分和和、时而斗争与时而合作的生存境况,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难以揭开的谜团。张静庐曾形象地将两者之间的关系比作为“泰东,是创造社的摇篮。”(注: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M].上海:上海书局,1938。)(P100)两者还算是成功的合作垫实了创造社在新文学征程中的地位,同时也提升了泰东图书局历史的影响力,但他们之间的分手又是那样决绝,可以说是一次两败俱伤地抉择。分手后的创造社在焦急与苦闷的伴随下,用凌乱的步伐艰辛地寻找着重生的道路,根据张静庐的回忆:“泰东编译所的风流云散,使得创造社同人的新作品,也有二年没有见面。”(注: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M].上海:上海书局,1938。)(P100),在此种情形下促使了创造社掀起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由“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转向的潮流。而泰东图书局同样也没有幸免于难,在与创造社合作关系破裂之后,它也逐渐从现代出版界中衰退下去。泰东图书局被后人更多提及的,还是与创造社合作的这段辉煌历史。这些曾经是历史叙述所带给我们的直观印象,那么是否两者在决裂后就再也没有发生任何联系了呢?两者之间的分手除了消极的影响外难道没有任何积极的作用吗?我们对于泰东图书局与创造社分手后关系考辨的努力,不能简单以“详情究竟如何,就不得而知了”的理由一带而过。返回创造社生存的文学现场,通过考察创造社机关刊物《创造》文学季刊的出版情况,便可寻找到解决问题的端倪。
一、泰东图书局与《创造》的出版与发行
《创造》季刊是创造社成立后最早发刊的文艺刊物,由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三人编辑。1922年3月15日创刊,1924年2月下旬停刊,共发行两卷,第一卷共出四期,第二卷共出二期,由上海泰东图书局(上海四马路)发行。
1、《创造》季刊出版时间考证
每一号《创造》季刊究竟被泰东图书局出版发行了几次呢?就目前笔者所能够掌握的资料来看大体如下:
《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一号:第一版发行的时间为中华民国11年3月15日(1922年3月15日);第二版发行的时间为中华民国12年6月20日(1923年6月20日);第三版发行的时间为中华民国15年9月20日(1926年9月20日);第四版为中华民国17年2月20日(1928年2月20日);第五版发行的时间为中华民国18年5月20日(1929年5月20日)。
《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二号:第一版发行的时间为中华民国11年8月25日(1922年8月25日);第三版发行的时间为中华民国12年3月25日(1923年3月25日);第五版发行的时间为中华民国16年8月25日(1927年8月25日);第六版发行的时间为中华民国18年3月25日(1929年3月25日)。
《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三号:第一版发行的时间为中华民国11年11月25日(1922年11月25日);第五版发行的时间为中华民国16年8月25日(1927年8月25日);第六版发行的时间为中华民国18年1月25日版(1929年1月25日);第七版发行的时间为中华民国19年6月(1930年6月)。
《创造》季刊第一卷第四号:第一版发行的时间为中华民国12年2月1日(1923年2月1日);第三版发行的时间为中华民国12年9月10日(1924年9月1日);第六版发行的时间为中华民国16年8月16日版(1927年8月16日);第七版发行的时间为中华民国17年12月25日(1928年12月25日)。
《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一号:第一版发行的时间为中华民国12年5月1日(1923年5月1日);第二版发行的时间为中华民国12年7月1日(1923年7月1日);第六版发行的时间为中华民国17年3月25日版(1928年3月25日)。
《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号:第一版发行的时间为中华民国13年2月28日(1924年2月28日);第三版发行的时间为中华民国13年6月1日(1924年6月1日);第四版为中华民国13年9月1日(1924年9月1日);第五版发行的时间为中华民国17年3月25日(1928年3月25日);第七版发行的时间为中华民国18年8月25日(1929年8月25日)。
通过以上历史资料可以清晰地看出直到1930年泰东图书局还在出版《创造》季刊,重印发行的版次竟然达到7版之多。1924年9月1日出版《洪水》后,泰东图书局与创造社之间编辑与出版发行的合作关系就宣告结束,如果以此为界限的话,在此之后泰东图书局对《创造》两卷六期刊物进行了不止一次的重新印刷和发行,而对此创造社成员并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从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在实际意义上泰东图书局与创造社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真正结束,而是以一种更加潜隐的形式继续着。
2、内容变化的考证
通过以上泰东图书局所出版发行的《创造》季刊的比较阅读,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在我们头脑中油然而生,那就是不同版次出版发行的《创造》竟几乎相同,甚至内部固有的印刷错误泰东图书局重新出版时都是照印不误,没有丝毫的变化。但其中也出现了一些变化,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创造》第一卷第一号在第一版时是采用竖排版,而到了第二号后就采用了横排版。
(2)第一卷第二号到了第五版时,刊物内的三副图画的位置有所颠倒。
(3)第一卷第三号到了第七版时,出现了版权说明及刊印册数。
(4)在第二卷第一号的封面上以前简单白纸黑字被设计精美具有寓意的图片所替代。更为主要的是在中华民国12年5月1日版(1923年5月1日)的《创造》中所出现的创造社同人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的肖像,在泰东图书局与创造社宣告分手之后所出版的《创造》中被泰东图书局删除了。
(5)第一卷第一号到第四号历次出版的《创造》季刊的考察中会明显地发现,版次之间主要的变化在于所刊载的广告宣传,而这种变化又以创造社和泰东图书局关系分裂为时间界限的,分裂之前《创造》季刊的每一期都有大量的有关创造社世界少年文学选集、创造社丛书、辛夷小丛书等与创造社创作有关的宣传广告,但是在分裂之后这些广告全部被泰东图书局所出版的《兴登堡东征实录》、《马克思民族社会及国家概念》、《中国教育小史》等另类书籍的广告宣传所替代。
在这些变化之中,竖排版改为横排版的现象郭沫若在《创造》第一卷的《编辑余谈》中曾作过说明“本志有改版之必要的原因是(一)初版错误太多,(二)自第二期起,改用横排,须求划一。”(注:郭沫若,《编辑余谈》《创造》第一卷第一号,中华民国18年5月25日第5版(1929年5月25日)。)而此方面的变化也是《创造》历次重新出版发行中最明显的改变,从郭沫若的说明可以看出此种变化是作为编辑方的创造社成员有意而为之的,而与出版发行方泰东图书局没有丝毫的关联。除此之外的《创造》季刊所发生的变化仅仅是期刊外部特征的改变,则是创造社成员力所不能及的,而这却是泰东图书局有意而为之。编辑者与出版发行方的着力点的不同便可见一斑了,但在另一方面作为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领域所创办的最早的文学季刊的原生形态,被泰东图书局相当完好地保存下来。
3、泰东图书局出版《创造》所带来的疑惑
一个又一个的疑问伴随着返回泰东与《创造》的出版与发行所建构的文学场的路途。
有关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的预告并不是刊发在泰东图书局所印制的相关刊物上,而是出现在了1921年9月29—30日的《时事新报》上,泰东图书局此时其余的印刷品却没有任何有关《创造》要出版发行的消息。这便与《创造》出版发行之后,泰东图书局在《创造》上大肆宣传起其有关社会、政治、经济类的书籍出版消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创造》第一期出版仅十六天后,就受到了沈雁冰的迎头痛击。而读者对创造社的“闪亮登场”似乎并无太大兴趣,两三个月后,这期刊物还只是卖出了一千五百本。印刷质量不好,错别字又非常多,剩余的五百本也无人问津。(注:材料来源于山东师范大学1998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李卫国的硕士毕业论文《冲撞与嬗变一重评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第21页。)(P21)难道仅仅是印刷与错字的原因导致了滞销的局面吗?泰东图书书局本应承担起《创造》的印刷、出版、发行与销售等方面的事物,但恰恰相反泰东图书局对于《创造》季刊中错误的漠视程度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如第一卷第一号中第49页的“不背”(不肯)、“举社会”(全社会);第135页“埋看头”(埋着头)、“上是(上次)”;第一卷第三号第58页“归末(归来)”;第一卷第四号,目录中存在着明显的错误,第79页“池胖(池畔)”等等俯拾皆是的印刷排版错误,泰东图书局在历次的重印中竟然没有一次将其改正过来。
在《季刊》的每一次的出版发行之中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创造》所发行的范围,“各省新文化及新智识书店皆有出售”,“定价一册四角,全卷四册一元六角”,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泰东图书局对于《创造》发行的读者定位,但一册期刊四角钱无论怎么说在当时社会来讲这也是一个比较高的价格,而同期的《小说月报》的价格仅仅为“一册二角,六册一元一角,十二册两元”,而几乎没有广告出现的《弥洒》月刊的价格也仅为“一册一角五分,半年六册八角,全年十二册一元五角”(注:同期的《小说月报》是指中华民国11年3月10日初版发行的,这时的《小说月报》厚度与《创造》季刊差不多,但是《小说月报》的广告非常多,特别是一些商业性比如有“地球商标,上品油漆”、“奇异安迪生灯泡”、“新华储蓄银行”、“妇科圣药,乌鸡白凤丸”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小说月报》的受众非常广泛,销售情况非常良好,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期刊的成本。)。过高的价位必定会在很大程度影响了读者购买,进而影响《创造》的发行。虽然第一号的销售并不理想但是中华民国11年8月25日发行的《创造》第一卷第二号,泰东图书局竟然将价格提升到了五角(注:本人查阅的所有中华民国11年8月25日发行的《创造》期刊价格一页中发现,在发行日期之下虽用墨迹涂染,但依然十分清晰印着“定价五角”。这期究竟是按照四角出售,还是按照五角出售,我们虽不得而知,但泰东图书局希望提高《创造》季刊销售价格的用心可见一斑。)。
更加令我们所费解的是竟然从最初出版发行到最后再版发行这跨越近十年的时间内,泰东图书局对于《创造》季刊出售的价格、邮费甚至包括广告费用始终没有改变,一直延续着售价四角一册,一元六角全卷四册的标准。跨越如此长的时间,每一期连续出版竟达六七次之多,但价格却始终未见有任何变化。而中华民国16年3月10日(1927年3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的价格由原来的“一册两角一册二角,六册一元一角,十二册两元”变为“一册一角五分,半年九角,全年1元八角”。泰东对于《创造》重新出版发行虽在价格上保持不变,但实际上却是提高了。
从《创造》季刊的发行工作来看,作为总发行所的泰东图书局竟然没有搞过任何的优惠活动,反倒是作为编辑者的创造社在《创造》第二卷第一号中为《创造》周末年纪念发行了一次优惠券,“Mayday是本志的诞生日,他今年算满了一岁了。我们深感读者诸君扶助他的厚爱,我们此次纪念他,发行这种优待券以志薄谢,a、执此券直接向上海泰东图书局总发行所购买本社出版书籍者一律照实价八折;b、此券效力无论购书多寡均以一次为限;c、此券效力以三个月为限。”(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一号,中华民国12年5月1日版(1923年5月1日)。)这种优惠券是创造社的名义赠送的,与泰东图书局没有直接的关系。在此后第二卷第一号的再次出版发行时这一优惠券就被取消了。
虽然泰东图书局在《创造》的印刷质量、价格定位、发行方式等等出版发行的重要环节都出现了问题,但是《创造》季刊却没有因为两者的分手而销声匿迹,究竟如何解答诸如为什么泰东图书局会如此热衷于出版《创造》文艺季刊呢,而且还一版再版,有时甚至同一期在一年之内也要再次出版发行呢;为什么再版《创造》的变化都是期刊外部特征的变化而内容却无丝毫的改变甚至是错误;为什么有关创造社丛书的广告在分手之后的出版发行中就被泰东图书局全部取消了呢?
二、潜隐联系中的同生与共赢
《创造》造成疑问的与现在对此研究的局限促使着我们寻找返回当时文学现场的路径,而泰东图书局便成为揭示历史迷津的重要线索。
1、泰东图书局性质及与创造社合作的背景
泰东图书局创办于1914年,由欧阳振声任总经理,谷钟秀任总编辑。它是一家股份制出版机构,股东大部分是由政学系成员组成。所谓政学系就是在当时中国效法西方国家建立议会政治体系的热潮下,一批热衷于政治的知识分子和旧官僚,在议会内和议会外成立各种团体形成的派系中较有影响的一个,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在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中谋取职位。为了出版自己的著作,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以便更加方便的从事政治活动,他们便决定成立了泰东图书局。创立之初的泰东图书局基本是为政学系服务的,因此他们出版了大量的有关政治方面的书籍。“护国运动”以后,股东们都到北京做官去了,于是泰东图书局便交由股东之一的赵南公主持。泰东图书局创立时确立的出版理念,以及赵南公本人的政治倾向和出版个性使得它得以继续出版具有进步社会思想和论述中国社会问题等政治方面的书籍。值得注意的是,泰东图书局在当时出版这类书籍,在上海乃至全国也是不多见的,使它一下子就在新书业界赢得了良好声誉。于是我们看到《创造》季刊上刊载了那么多有关于社会改革和政治性质的图书广告如:《地方自治通论》、《政治经济学》、《世界联邦共和国宪法集》等就不足为奇了。
这时的泰东图书局已经不是政学系的机关出版机构,于是生存便成为首要问题,而在当时政治社会类的书籍社会需求量毕竟还太少,作为一个出版商,赵南公不能不顾及书局的经济利益,于是他开始调整出版思路。在当时社会需求的驱使下,泰东出了好几种“礼拜六派”的小说,如《芙蓉泪》等。1916年,又推出了一部长篇小说《新华春梦记》,使泰东图书局“赚了一笔钱”。
但是对于一家出版社来说,单靠一种书的赢利是难以长久支撑经营的,更何况时代思潮的变迁带来了社会阅读需求的变化,这一切令赵南公焦虑重重。经过对社会形势和图书市场的分析,他决定放弃原有的出版领域,另行规划新的经营路线。因为他明白所谓“鸳鸯蝴蝶式”的小说书已是回光返照时代,再过下去不再会走民国三、四年的红运了。于是,他就决定放弃过去的一切,“重建理想的新泰东”。(注:根据张静庐的《在出版界二十年》,1938年6月上海书局出版;郭沫若的《创造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秦艳华《泰东图书局如何成为创造社的“摇篮”》中华读书报2004年2月25日中有关泰东图书局的论述整理而成。)
要“重建理想的新泰东”就必须得到五四新文化精英的鼎立襄助。而这时急于掌握话语权利,而又苦于没有出版社的支持濒临流产边缘的创造社同人就进入了赵南公的视野,于是他决定由郭沫若执掌泰东的编审大权。在7月28日的日记中赵南公中写道:“即沫若暂返福冈,一切审定权仍归彼,月薪照旧,此间一人不留,否则宁同归于尽。”(注:《创造社元老与泰东图书局—关于赵南公1921年日记的研究报告》,《中华文学史料》1991年第1辑。)在这种前提下,泰东图书局借助创造社实现自己新的转变和经济利益增长的目的就不言而喻了,而创造社也可以借助泰东图书局避免流产的尴尬厄运的愿望也是十分明显的,因此泰东与创造社之间与其说是合作不如说是相互的拯救与扶持。
2、同生与共赢的潜在合作
明晰了泰东图书局与创造社合作的背景与目的,那么以上由对印刷错误的漠视、违反常理的价格定位等外在表面现象所造成的疑惑也就不解自明了。但《创造》季刊为何能够成为两者分手后联系的纽带呢;泰东图书局为何不厌其烦的对《创造》反复印刷出版呢?
从定价表中的邮费一栏中我们看到标有“国内一册五分,全卷四册二角;日本五分,全卷四册二角;外国一册一角二分,全卷四册六角”的邮资标准。虽然日本邮费与国内一样是当时的通行规则,但是泰东图书局将《创造》发行到日本也可谓是别具用心,1921年6月创造社在日本东京宣告成立,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等等前期创造社同人都是在日本文化的熏陶中成熟起来,而且《创造》季刊每一期中都出现了许多以日本留学或生活经历为背景的作品,如第一卷第一号的《最初之课》、《茫茫夜》;第一卷第二号的《风铃》、《木马》;第一卷第三号的《未央》、《一班冗员的生活》;第一卷第四号的《爱之焦点》、《路上》;第二卷第二号的《茑萝行》;第二卷第二号的《回归线上》,这些作品大多描写了他们在日本生活过程中的所想所思,以及由此而发的性的压抑、生的艰辛的苦闷情绪,这样的内容构成使得日本广大留学生读者群对于《创造》具有了天然的亲和力,这在增加发行量的同时也拓展了《创造》的读者群,从而增加了创造社的国际影响力。
从出版与再版时间情况来看,泰东图书局对《创造》季刊的再版时间没有任何规律性可言,各期再版发行的时间与版次几乎都不重合,但是不置可否的是直到1930年泰东图书局还在出版《创造》第一卷第三号,而且印数竟然达到惊人的“14,000—16,000册”(注:此数字出现在中华民国19年6月(1930年6月)版《创造》第一卷第三号的封二上。), 也就是说这一次就印制了2000册,而且总的印数竟达到了16,000册,由此推算的话《创造》季刊的总印制量与发行量应该在100,000,这在当时应该说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注:泰东图书局在中华民国16年9月1日创办了《泰东月刊》,每一期的封页上都清晰的表明印数1—2,000册,再根据《创造》所出版的次数所以可以这样做出推断。)。试想如果没有泰东图书局对《创造》这样大批量的出版发行,前期创造社的历史影响力恐怕也不会有如此巨大,创造社“转向”后前期的声音也不可能依然回响于20年代后期的文坛,泰东图书局的“摇篮”不仅孕育了创造社的生命也造就了其辉煌历史印记。
因此在历次出版发行的两卷六期的《创造》中“编辑者创造社、发行者赵南公、总发行所泰东图书局,本期所载小说诗剧曲等类皆有著作权不许转载”都非常清晰的出现在刊物的最后一页,即使在分手之后泰东图书局还依然毫无顾忌地一版再版《创造》,而且还毫无芥蒂的告诉读者泰东图书局对于版权的拥有,创造社成员竟然对此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的现象就不难理解了。
基于泰东图书局自身性质的使然,以及《创造》季刊广泛的发行地点、如此频繁的发行版次、读者群体的定位以及对期刊内容的漠视等等方面可以明显地看出,泰东图书局刊发《创造》季刊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扩大书局的社会影响,争取更广泛的读者认同,从而赢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这对于一个出版商来说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前期创造社的光辉历程,扩大了创造社的社会影响,从而进一步奠定了创造社的历史地位。对于双方从这个方面来讲这何尝不是各自生命潜在的衍生和再一次双赢的合作呢?
泰东图书局与创造社表面分手的背后还依然通过《创造》文艺季刊的出版发行发生着潜隐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又是以双方的同生与共赢为前提和指归的,难怪1933年9月《郭沫若书信集》由泰东图书局出版后,对于郭沫若“言辞之间,仿佛与泰东图书局从未有过芥蒂。”(注:刘纳.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M].广西: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P234)
标签:郭沫若论文; 创造社论文; 创造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小说月报论文; 张静庐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