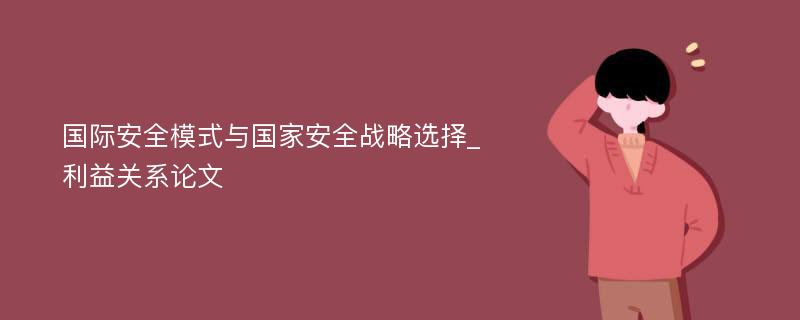
国际安全模式与国家的安全战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论文,模式论文,国家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国际政治中,国家追求安全总是相对他国或一个国际体系而言,会涉及双边关系或多边关系,因此不可避免地会与他国、国际组织乃至与整个国际社会构成一定的安全关系。这种关系的互动性与国际性,决定任何主权国家在谋求安全时都不能离开国际大背景。一方面,国家的行为会受到国际大背景的复杂影响;另一方面,它的安全现状亦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安全的现状。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国家能不能真正实现国家安全,取决于它能不能享有国际安全。因此,每一个国家在确定自己的安全战略的时候,都不得不考虑国际安全模式的问题。
国际安全模式在这里有两层含义:第一,它是指国际安全大环境,也就是相关国家乃至全世界国家所结成的一定的安全关系和安全体系。这种安全关系和安全体系,按照假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每一个相关国家的安全。第二,它亦指国家自身谋求安全的战略追求和政策取向,也就是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处理国际安全关系的方式,或者说是以国际社会为背景,通过国际行为来实现国家安全的方式。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前者是客观因素,后者是主观因素,前者是国际安全的现实,后者是国家针对这种客观现实所做的战略选择。
理论之争
如何实现国际安全,人们历来有不同认识,并因而形成了不同的历史观点。
一种观点通常被称为霍布斯主义,其代表人物是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Hobbes,1588~1679)。霍布斯主义认为,主权国家体系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本质上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它缺乏共同的法规和实施法律的机构。外交和战争是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的主要手段。各个民族国家的主权者,无论是王公还是立宪君主,都负有抵御外来威胁、保卫国内和平的使命。国家实现安全的根本在于增强自己的实力。(注:霍布斯的思想可参阅其著作《立维坦》(Leviathanor theMatter,Form,and Power of a Commonwealth,Ecclesiastical andCivil,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Oakeshot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651/1957.)。也有学者指出,关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洛克(Locke)的论述也许比霍布斯更好。参阅HelgaHaftendorn:"The SecurityPuzzle: Theory- Building andDiscipline-Building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InternationalStudies Quarterly(1991)35,p.6,n2.)霍布斯主义观点构成了有关安全的现实主义传统。
另一种观点是康德主义,其代表人物康德(Kant,1724~1804)是德国哲学家。康德所提出的设计是以“永久的和平”(perpetual peace)作为有理智之人遵循的道德准则。他相信,通过建立开明的政治秩序,即共和主义宪法、联邦主义国家体系和全球公民身份,就能重建民族国家体系,从而构成一种人类共同体。为达到这一点,他认为各个民族国家出于理性的远见都应该把自身利益置于国际法规的支配之下,而这一点,也正是每一个公民对人类共同体应有的道德承诺。(注:康德的原著是Zum Ewigen Frieden,Ein Philosophischer Entwurf.Stuttgart:Reclam.1795/1954.)康德的主张构成了有关国家安全的理性主义传统。
还有一种观点介于这两者之间,即以荷兰哲学家格劳秀斯(De Grotius,1583~1645)为代表的传统。格劳秀斯承认国家体系中有理性的因素,认为共同的法则和制度会把国家间的冲突限制在一定的范围。这一点与康德的主张有相似之处。但另一方面,他的眼光却是国家主义的而非世界主义的。他认为,国际政治所表现的既不是国家间的完全的冲突,也不可能是全球利益的一致认同。在国际政治活动中,国家的互动会受到它们所构成的国际社会的法规和制度的约束。国家必须做的并不是推翻国家体系代之以人类的全球共同体,而是在国际社会中接受共存与合作的要求。(注:本文关于霍布斯、康德和格劳秀斯所代表的三种传统的概括,参阅了Helga Haftendorn:"The Security Puzzle:Theory-Building and Discipline- Building in InternationalSecurity."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1991)35.关于格劳秀斯的思想,可参阅Bull,H.: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World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p.24~40.)这种构想或许可看做是后来建立均衡体制、集体安全体制乃至国际组织的思想的来源。
20世纪以来,特别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政治领域逐渐形成了解决国际安全问题的两大流派,即现实主义(realism )与理想主义(idealism)。
现实主义的世界政治观是从利益出发看问题。这种观点认为,国际政治在本质上是无政府的、自助的王国。在这样的无政府体系中,国家的首要目标是生存。每一个国家都对确保自己的生存负有责任,都有权利自由确定自己的利益并确定追求这种利益的手段。在一个存在威胁的环境里,为了生存,国家必须做的事情就是相对其竞争者最大限度地增加自己的力量,而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国家谋求军事优势。因此,国际政治在本质上是竞争的。在这样的现实主义世界,即使存在共同利益,无政府状态亦会抑制有关国家的合作愿望。即使合作能实现,面对国际政治体系所固有的压力,维持合作也是困难的。现实主义者认为,支配国家行为的是国家的利益与权力。(注:对现实主义的最经典的阐述见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Mass, Addis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6[th]ed.New York:Knopf,1985.)
理想主义则是从国际规范和世界政府出发看问题,认为通过建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能够规范国家的行为,通过国际合作能够制止侵略,达到国际的和平。以集体安全原则来解决国家间的安全问题,就是一种理想主义模式。从威尔逊倡导建立国联到罗斯福策划建立联合国,都是想通过建立世界性组织来实施集体安全原则。这种构想追求的不是权力的平衡,而是某种权力的共同体。在这个新体系中,所有国家将在共同的事业中合作,为所有国家提供安全与正义。理想主义者认为,国际组织即使不能提供世界政府,至少也能提供某种国际行为规范和约束。(注:理想主义固然是一种国际安全实践,但严格说来今天已不再存在与现实主义相对的理想主义学派。有时,“理想主义”甚至成了某种带贬义的说法。)
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作为理论工具到底哪一个更可取呢?
权力均衡与霸权
不管在理论上怎么争论,人们都不得不承认,现实主义作为立论出发点和理论背景的国际权力竞争乃是客观的现实。这种竞争在国际政治中可以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国际组织和国际规范的存在,丝毫没有改变这一事实。在这种竞争中,国家可能面对三种结果:第一,取得优势,确立霸权;第二,不相上下,形成均势;第三,处于劣势,受到支配,或不得不依附别国。就这三种结局而言,国家显然倾向于作前两种选择,即霸权和权力均衡。依附地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是国家适意的安全目标,因为处于那样一种地位,国家就不得不接受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从而损害自身的主权。
在权力竞争中,是追求霸权还是追求均衡,不同的国家显然有不同的选择。这里,国家的实力地位和政策取向是两个基本要素。考察世界上的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只要它的发展是以与其他国家共处为目标,追求的就是均衡;相反,只要它的发展是意在取得对别国的支配,则它的目标就是霸权。当然,这里还有层次的不同。追求霸权者有追求地区霸权与全球霸权之分,追求均衡者也有追求地区性均衡与全球性均衡之别。
以霸权作为国家安全的追求,其目的是要建立这样一种秩序,即霸权治下的和平。在古代,有过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在近代,有过英国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这种和平的主要特征是安全体系中只有一定世界性支配者,它具有超群的实力(以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为基础)和无与伦比的国际影响力,能够制定和维持符合其利益的国际规则,并能在一定历史阶段和一定范围内迫使其他国家服从自己的统治和支配。
尽管对霸权体制的界定和鉴定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有一个事实人们必须承认,即自主权国家体系形成以来,总是不断有国家出来谋求霸权,但也总有国家出来粉碎谋求霸权国家的企图。这样,霸权与权力均衡就构成了这样一种循环:当某个国家取得权力优势并企图确立霸权的时候,其他实力相近的国家就会起来平衡它。一旦平衡实现,霸权国家的霸权企图就失败了。然而,由于国家实力发展是不平衡的,因此平衡只能是相对的,过一段时间又会有国家取得相对优势乃至霸权,但这种相对优势或霸权又会在下一次平衡中消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美国曾以自己的超群的实力确立了世界霸权。然而,随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和华约的建立,美国就不得不承认这个全球性的势均力敌的对手。在冷战中,美苏之间关系的实质是争夺霸权,但所形成的安全模式却是一种均衡。由于双方势均力敌,任何一方都不能战胜对手,因此不得不在一种不战不和的状态下保持紧张的共存: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发展各自的军事联盟——北约和华约,实施核威慑,开展军备竞赛等。
在国际权力竞争中,人们可以看到,尽管对霸权的争夺在世界舞台上最引人注目,但实际上大多数国家的安全战略选择,特别是对中小国家来说,只能是权力均衡。
所谓权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是指竞争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权力大体相当,从而能实现共存。远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和古希腊城邦国家时期,这种现象就已经存在了。例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权力的上升促使那些受到威胁的城邦国家结成了联盟,并在斯巴达的领导下打败了雅典,从而实现了均衡。权力均衡理论认为,对一个国家的权力的最有效的制约者是另一个国家的权力。因此,如果一个国家或国家同盟增大了其权力,并用这种权力进行侵略,那么受到威胁的国家就应该增大其权力作为回应,并以这种平衡行为来实现国际体系的稳定。一般来说,为了保持国际关系的动态平衡,联盟应该具有流动性,也就是说它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总有国家出于权宜之计改变自己的组合。在这种情况下,权力均衡体系的功能最有效。有时,是单一国家起着平衡者的作用。它能够通过变换自己的支持来反对最强大的国家或国家联盟。在18、19世纪的欧洲,英国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特别是在它与法、俄、德的关系中。
在欧洲,均衡与霸权的循环似乎体现得最典型。均衡的每一次失败都会导致战争,而争霸的每一次失败又会使局面恢复均衡。当然,在这种循环中欧洲也经历了无数的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
对于欧洲不断出现的均衡局面,卢梭曾把它称为力学的奇迹:“欧洲的体制的确十分坚固,只要不加以干扰,它就能在永恒的运行状态中维持下去。在形形色色的欧洲社会成员中保持的均势,更多地来自于自然的造化,而不是人为的努力。它不用费力就能维持自身,其方式是:若一边发生倾斜,另一边马上就会重新组合确立新的平衡。”(注:转引自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国家的命运》,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2页。)
以实力地位为主要追求目标的现实主义安全构想,无论是追求霸权还是追求力量的均衡,它所强调的都是作为自助个体的国家。而在这一点上,被称为理想主义模式的集体安全构想则恰恰相反。
集体安全
理想主义者设想集体安全,是因为他们认为单个主权国家在国际范围内不能实现自身的安全。因此,他们寄希望于某种类型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规范,并且寄希望于人类的理性与正义。
作为一种安全模式,集体安全的构想是由一批国家构成一定的安全共同体,诸如同盟、条约组织、国际组织等。在这个共同体中,所有成员国放弃相互使用武力,并承诺共同行动,援助受到侵犯的成员国,对破坏和平的国家实施强制性措施,诸如经济制裁,必要时则实施军事制裁。
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确立主权原则,划定欧洲大陆各国的边界,规定缔约国不得破坏和约条款,否则予以集体制裁,到维也纳会议(1815年)确立“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 以会议外交方式处理欧洲及与欧洲有关事务,其中都体现了某种程度的集体安全原则。在这一阶段,国家进行集体安全实践的特点是有了一定的制度和规范,但还没有实现组织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国际联盟到今天仍在起作用的联合国,国际组织构成了集体安全的主要形式。这种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几乎包括了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不管它的功效如何,至少在普遍性上已达到了最大的限度。
与均衡体系中自助的个体不同,集体安全涉及的是多个国家的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中,基本的特点是大国主宰,小国陪衬。无论是早期的维也纳会议、欧洲协调,还是实现了组织化的国联和联合国,情况都是这样。例如,维也纳会议的参加者有17个欧洲国家和36个日耳曼邦,但实际上一切重要问题都是由俄、英、普、奥四强秘密商议决定的。在国联内部,居统治地位的大国最初是英国和法国,其后有日本、意大利,最后有德国和苏联。在联合国中,对世界安全问题起决定作用的是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在大国支配之下,集体安全能否存在,关键在于大国能否一致。国联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在于大国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利益分歧。由于德、意、日坚持改变领土现状,英、法的政策摇摆于抵抗和绥靖之间,而美国又袖手旁观,从而使得这个体系最终失败。在联合国中,冷战时期所以难有作为,主要原因是美苏两霸的对抗。冷战结束之后,对于如何解决世界上一些热点冲突问题,安理会中也常常出现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使联合国无法采取集体安全行动。事实上,集体安全最大的局限性,就在于它倚为前提的一致特别难得。而集体安全组织越大,这种一致就越难得。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否决权制度,可以确保这个组织不损害大国的利益,而小国要想在这个组织中维护自己的安全利益就困难多了。如果各大国对解决某小国的安全问题意见分歧,那么这个小国尽管身处集体安全体系之中,也根本得不到集体安全的保护。
当然,由若干国家组成的区域性集团,情况可能与联合国这样的普遍性组织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北约作为一个带有集体安全性质的军事组织,其成员国所得到的安全利益就现实得多。但是,人们也必须看到,北约所得到的安全,只是局部的安全,它仍然时时受到国际性的不安全因素的困扰。它干预前南问题,干预伊拉克的问题,并且积极向东扩展,说明它也缺乏安全感。
所以,集体安全,尽管曾被称为理想主义的东西,但实际上并不理想。
国家的安全战略选择
面对人类社会已有的种种安全模式,国家应当做怎样的选择呢?
一般来说,理想的东西往往不现实,而现实的东西则往往不理想。对国家来说,最佳的选择当然应该是既理想又现实的东西。然而,从历史经验来看,显然还找不到这样一种模式。已有的模式,无论哪一种,都不能说是理想的。权力均衡作为安全的客观效果是国家追求的目标,但国家为达到这一目标所作的主观努力却是进行权力竞争。而权力竞争在本质上乃是一种不安全的局面。集体安全在成为全体成员的一致目标时可以实现安全,但因为一致不容易达到,因此集体安全常常没有意义。
从当代国家追求安全的行为来看,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执行某种纯粹的战略。出于安全的需要,国家都不能不发展自身的实力,也不能不理会国际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执政者通常都是“霸王道杂之”,往往在一些问题上带有一种模式的特点,而在另一些问题上带有另一种模式的特点。也许,这样做才是国家最现实的选择。这种选择要求国家首先必须从自身利益出发,实现和保持实力地位的均衡,同时亦要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国际规范和国际组织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国家寻求权力均衡,在某种意义上乃是进行一项系统工程,因为每一个国家所面对的都是复杂的国际关系。其中既包括大国关系,大国与中小国家的关系,亦包括中小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这个体系中,每两个相关国家之间都存在互动关系,而不同的互动关系又构成更复杂的互动关系。所有这些关系,无一不对国家安全发生影响,而最终决定国际安全现状的则是它们构成的合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所追求的权力均衡应当是总体平衡或综合平衡。所谓总体平衡,就是国家面对国际关系中复杂的对象,必须实现一种非常微妙的均衡,它包括世界范围的均衡与地区周边的均衡,包括对外关系中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的总和的均衡,并且包括国家对外关系中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均衡。国家安全不安全,并不取决于其中的一项或几项,而是取决于所有这些关系的总和是否均衡。在通常的情况下,国家可能在某些方面处于有利地位,而在另外的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只要有利的方面能够制约不利的方面,国家在总体上就是安全的。在这里,外交常常会发挥重要作用。国家的外交努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构筑有利于自己的力量组合,这中间又包括非结盟关系和结盟关系;二是确立比较公正的国际规范和国际秩序。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实现均衡的过程中,外交手段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国家的安全地位最终还要靠实力来实现。由于在权力均衡的竞争中,任何国家有机会取得优势都不会放弃,因此总有相当多的国家处于不安全境地。为抵消这种竞争所造成的不安全后果,国家在追求实力地位的同时,还必须求助于国际规范和国际道义,还必须为发挥国际组织和国际规范的作用而努力。当今的联合国以及在联合国名义下制定的各种国际公约、条约等已构成了这样一个国际规范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国家只要行为得当,就可以享有一定的安全保护(尽管非常有限)和争取安全的一定的活动空间。
由于权力均衡与集体安全两种模式都是国家不得不参与其中的游戏,因此,也许我们需要以新的眼光来看待什么是理想主义,什么是现实主义。作为源于理想主义的集体安全模式,经历主权国家几百年的实践,在当代已变成了很现实的东西。就联合国的体系而言,它已存在了半个多世纪,而且还会继续存在下去。当今的主权国家,受到联合国严厉制裁者,诸如伊拉克,没有退出联合国;对联合国极为不满者,诸如美国,也没有退出联合国。从这个意义来讲,集体安全似乎也应看作是一种现实的模式,尽管它的实效不那么现实。
那么,什么是更理想化的东西呢?这就是现存的另外两种安全构想,即民主和平与和平共处。
“民主和平”是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安全理想。按照民主和平论者的假定,民主国家之间是不打仗的,因此,只要全世界的国家都变成民主国家,国家安全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推行这种理想,西方国家所能采取的战略就是实行干涉主义,输出民主,在全世界建立西方式的政治体制。毫无疑问,这样做必然引起具有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冲突。
与之相反,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则主张以和平共处作为国家间关系的最高理想。和平共处原则的核心是尊重主权,强调的是国家间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显然,如果所有国家都有这样的意愿并且都这样做,那么大家就都可以得到安全。然而,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在国际体系中实行和平共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因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所有相关国家都有这样的意愿。在一个体系中,只要有一个国家不愿与别国共处,和平与安全就无法实现。事实上,在世界上的各个地区,几乎都有国家不能与别国和平相处。而推行“民主和平”的国家更是与所有它们认为是“非民主”的国家不相容。
从未来的发展看,“民主和平”与和平共处两种国际关系的理想将会长期斗争下去。它们将作为国家安全战略选择的组成部分,发挥某种规范性作用。显然,国家在谋求安全的国际互动中,既要进行现实的斗争,亦要进行理想的斗争;既要进行个体的斗争,亦要进行集体的斗争;既要进行物质的斗争,亦要进行精神的和规范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国家所实行的安全战略肯定都是某几种模式的组合。而每一个国家在制定自己的安全战略时,都不得不考虑相关国家的安全战略组合,以及所有国家的安全战略选择的总和构成了一种怎样的国际安全的挑战。只有国家的安全战略选择足以适应整个国际体系所提出的挑战,国家的安全才是有保障的。
标签:利益关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