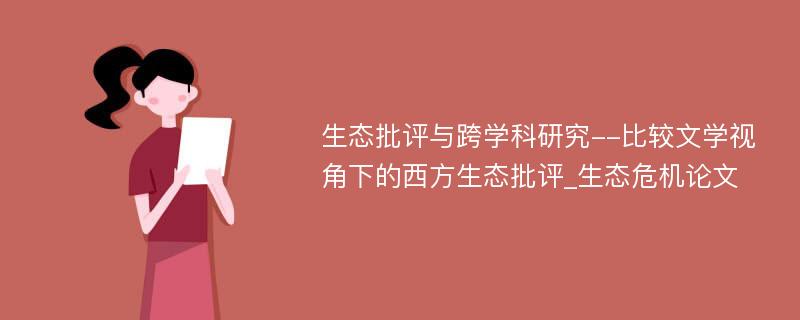
生态批评与跨学科研究——比较文学视域中的西方生态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生态论文,视域论文,比较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态批评是个非常庞杂、开放的批评体系,兼有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特征,它立足生态哲学整体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将文化与自然联系在一起,雄辩地揭示了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人类文明的危机、人性的危机、想象力的危机。因此,要从根源上解决生态危机,仅靠自然科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人文社会科学积极广泛的参与、引导,必须突破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束缚,打破基于机械论、二元论、还原论的传统学科的界限,从跨学科、跨文化、甚至跨文明的视角去探寻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性对策。
生态批评跨越学科界限,一方面深入挖掘文化的生态内涵、凸显人与自然之间不可割裂的亲缘关系,另一方面从多视角透视生态危机产生的复杂原因,进行综合的文化诊断、文化治疗,目的在于建构生态诗学体系,倡导生态学视野,让它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技术领域,以便从根本上变革人类文化。从生态批评的范围来看,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加剧和范围的扩大,西方生态批评也在向国际性多元文化运动的趋势发展,文化的多元性是生态多样性的物理表现,生态文化多元性(ecological multiculturality)必然要求生态批评从跨文化、甚至跨文明的视角去探讨生态问题的复杂多样性及其相关对策。跨学科、跨文化、甚至跨文明是西方生态批评的显著特征,在此,笔者愿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对西方生态批评的跨学科特性作一些探讨。
一 人与自然亲缘关系的跨学科阐发
生态批评的跨学科特征主要表现在对当代生态学的借鉴与超越,也就是说它借鉴生态学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从生态整体主义的立场出发,跨越自然科学、文学、美学、神学、伦理学、哲学,政治学等学科,并且借鉴了多种批评策略,如文化批评、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解构主义等等。其中,环境是联系各个学科的交点,是所有学科关注的中心。
西尔斯(Sears)说生态学是“颠覆性的科学”[1](11—13页),对此,在生态批评学者埃佛德(Evernden)看来,生态学中真正具有颠覆性的因素不是它的复杂的概念,而是它的基本前提:相互联系[2](93页)。生态学家康芒纳(Commoner)说“每一种事物都与别的事物相关”[3](25页),这是生态学的第一条法则。它反映生物圈中精密的内部联系网络的普遍存在。但是,生态学家并未广泛而又充分地认识到这种颠覆性因素中蕴涵的激进的实质,社会活动家、环境主义者更是如此。在西方人的思想中,相互联系被简化成因果联系,一种事物中的变化影响另一个事物,就说他们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当我们说一切事物是相互联系的,这仅仅意味着如果我们要开发“资源”,必须找到相关的技术手段消除这种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然而,生态系统的实际状况是各个部分是相互交错的,没有任何实体是完全孤立的。生态学家Shepard曾用“皮肤”这个比喻来生动形象地说明事物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不可肢解的特性。他这样写道,皮肤的表层“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像池塘的表面或森林的土壤,哪里像是个外壳,简直是个千丝万缕的联系”[2](93页)。
相互联系的观点将人与非人类的自然世界联系在一起,将人类文化与自然世界联系在一起,这样,生态学上升为生态哲学。最初,生态学是作为一门标准的还原论的科学,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它以否定作为现代科学基础的机械论、二元论、还原论的观点而结束。生态学颠覆的不只是增长癖、无限开发,而且还有科学自身,同时,它也预示着生态学时代的来临,正如鲁克尔特(Rueckert)所指出的:“我们必须倡导生态学视野……没有生态学视野,人类将会灭亡……生态学视野必须渗透到我们时代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领域,对它们进行根本性的改造,这不是一国范围内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或星球性的问题。”[2](114页)因为人的脚步不仅遍布整个地球,而且已经闯入了宇宙。
所以,鲁克尔特认为,生态批评指的是“运用生态学和生态学概念研究文学”,甚至“建立生态诗学”[2](107页),其目的是让人文社会科学绿色化,根本上改变我们与自然世界的关系,进而改变我们的世界,正如海德格尔所说,重拯破碎的自然与重建衰败的人文是一致的。从总体上说,生态批评蕴涵自然科学的比重并不大,它主要借鉴了生态学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多元化的观点,其中,相互联系的观点是生态批评赖以存在的重要基础。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人与环境的关系。当我们在涉及到人与环境的关系时候,我们到底指的是什么?斯帕肖特(Sparshott)认为有几种可能的关系:我—你(I-Thou),主体—客体,使用者—被使用者等[2](99页)。但是,对于生态批评而言,惟一真正与讨论人与环境关系有关的是自我(self)与环境的关系。
如果一个人仅把世界看成是供人享用的资源,他是不可能将它看成是环境的。在斯帕肖特看来,这样的人“完全无视构成环境的所有方面”[2](99页)。对于消费者来说,整个世界只是饲料和排泄物,他与身处环境中、属于环境一部分的人形成鲜明的对照。如果说游客只能看看风景的表面,然而当地居民对周围的一切却很敏感,他不会把风景看成只是物理形态的结合,而是那里所发生的一切的外在显现,因为居民早已是该地区的构成部分。在杜威(Dewey)看来,审美经验既不存在于被看的物体中,也不存在于观者的思想中,而存在于个人和环境的关系中,观者和被观者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就是在联系中产生了审美体验,观者并未脱离环境,而在不知不觉中已融入其间,所以,当地居民与地方的关系是一种审美关系[2](97页)。
同样,环境在个体生活中的作用问题也发生了转变。我们必须明白个体是环境的一部分,个体是环境中的个体,而不是独立于环境的实体,这与笛卡尔的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比。因为,自笛卡尔以后,西方人一直相信我们不仅不是环境的构成部分,甚至我们不是身体的构成部分,我们的真正的“自我”集中在某个隐秘之处,与身体、物质世界相分离。也许正是对此予以反驳,弗莱(Frye)宣称,艺术的目标是“充分再现我们已经丧失的与环境的本源上的联系,本来人的思想以外没有任何东西,事物都与人的思想相关联”[2](99页)。
在笛卡尔后的时代,人类社会中多数人并不认真看待万物有灵论,事实上,一旦我们将自我的边界延伸进“环境”之中,那么,我们就给它注入生命,就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它是鲜活的——它是活的,是因为我们是它的一部分。由此,备受诗人青睐的所有的比喻性特征就非常富有意义:所谓的“感情误置”(the pathetic fallacy),只是对固守自我的人来说才叫“误置”。比喻性的语言可表示地方的存在,表示言说者有个地方,并且感到他是该地方的一部分。的确,正如弗莱声称,运用比喻的动机是“渴望将人的心灵与外在的一切联系在一起,最后是与之保持一致,因为一个人只有感到自己已成为所熟悉的事物的构成部分的时候,你才会感到真正的快乐”[2](101页)。
然后,我们来看文学是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文学家、诗人们对人与环境的亲密关系有着更为精彩的描绘。生态文学家梭罗(Thoreau)、谬尔(Muir)、利奥波德(Leopold)、卡逊(Carson)都信奉和赞美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种统一不只是在物质的层面,而更是在精神的层面,他们试图将自然物的秩序与美丽置入人的精神之中。被尊称为西方世界“环境圣人”的梭罗[4](394页),在他的杰作《华尔登湖》中指出,自然是精神的体现,自然万物都可成为他思想的载体。更具有生态学意义的是,他把自然世界与人文社会联系起来,认为自然规律与人的规律是一致的,正如他写道:“我观察到的湖的情况与伦理完全一致。”[5](319页)他还进一步指出,人类对自然的依赖,自然能保持人类社会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要不是我们村子周围没有开发的森林和草原,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毫无生气,我们需要荒野的营养”[5](339页)此外,在他看来,世界上“没有无机的东西”[5](332页),人可以参与自然的有机过程,不仅在生理上,而且更是在精神上,同自然一起周期性地复苏。
被誉为当代环境运动伦理之父的利奥波德[6](63页),对美国的资源保护运动的浅薄、平庸深感绝望,因为它的策略是基于经济的标准而不是伦理的标准。在他看来,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必须拓展我们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向生态中心主义的伦理过渡。为此,在他的《大地伦理》之中,他提出了对生态思想影响深远的大地伦理的概念。在他看来,伦理学的发展已经走了三步。最初的伦理学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后来的伦理学研究扩展到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现在的伦理学研究要“向人类环境中的第三因素(大地)延伸”[7](193页),进一步扩展到人与大地之间的关系。“大地伦理只是扩大了共同体的边界,把土地、水、植物和动物包括在其中,或把这些看作是一个完整的集合:大地。”[7](193页)即是说,把道德权利扩展到动物、植物、土地、水域和其他自然界的实体,确认它们在一种自然状态中持续存在的权利。这样看来,大地伦理学改变人类的地位,把他从共同体中的征服者的角色,转变成为普通平等的成员和普通公民。这意味着人类不仅要尊重共同体中的其他同伴,而且要尊重共同体本身。他主张扩展伦理的理由是“我们滥用大地,因为我们把它看成是属于我们的商品,当我们将大地看成是我们属于它的共同体时,我们开始怀着热爱和尊重去运用它”[6](69页),所以,大地伦理预示着人类以生态为中心的生存状态的可能性。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生态哲学是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深层生态学认为自我与自然环境不仅不可分割,简直就是相互交融的关系。深层生态学两个基本原则之一“自我实现”中的自我,就是强调个体与外在的非人类的自然环境的联系。这种自我与西方传统中的“自我”有着本质的不同。西方传统中的自我是一种分离、孤立的自我:个体与他人分离、人的精神与肉体分离、人与自然分离。然而深层生态学追求的自我是形而上的“自我”,它是用大写的字母" S" 构成的(Self),通常称为“大我”,又称为“生态自我”(Ecological Self)。这种“自我”不仅涵盖整个人类,而且“随着人自身独特精神和生物人性的进一步的成熟,自我逐渐扩展,超越整个人类而达到一种包括非人类世界的整体认同:人不是与自然分离的个体,而是自然整体中的一部分,个人与其他存在的不同,是由与他人、与其他存在的关系所决定的”[8](46页)。从深层生态学的立场来看,环境主义的主张仅限于浅层生态运动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在解决生态危机时候,仍然坚持技术至上,仍然信奉人类中心主义和人与自然分离的二元论,人与自然的关系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所以,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生态危机。
简言之,个体是环境中的个体,自我是地方中的自我,个体与环境之间远远不只是消费者与消费品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审美关系,是情感关系,是伦理关系,二者是相互建构的。所以,生态批评家鲁克尔特呼吁创造性的文学艺术积极地参与生态危机的解决。他在《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践》一文中指出,诗歌(创造性的文学艺术)中蕴藏了取之不尽的能源,阅读是能量的转移,所以,老师、批评家是诗歌与生物圈的中介,他们释放诗歌中蕴涵的能量和信息,让它们在人类共同体中流通,变革人类文化,然后转变成为社会行动,从而有助于消除生态危机[2](108—111页)。
二 人类文化中反生态因素的跨学科清理
一方面,生态批评跨越学科界限,从多视角深入挖掘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的亲缘关系,并且试图巩固和发展这种关系,另一方面还要从跨学科的角度清理人类文化中的反生态的因素,以便从根本上变革我们的文化。正如著名生态思想家沃斯特(Worster)明确指出的:“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渡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关系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革命,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2](xxi页)
生态批评首先向西方主流文化中的基督教发难。怀特(White)将人类破坏地球生态环境的根源归咎于犹太—基督教中的上帝,因为他不仅确立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而且还赋予了人统治自然的神圣权力,所以,怀特认为“西方的基督教是世界上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最严重的宗教”[9](189页)。怀特的批评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怀特对基督教的指责是否公允,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重要的是他迫使西方主流社会对包括基督教在内的文化传统进行痛苦的反思,使他们意识到生态危机本质上是文化危机的反映,要从根本上消除生态危机,必须进行彻底的文化清理,必须变革主流社会的文化范式,促使它从掠夺、征服型向追求和谐共生的生态型转变。怀特的批评开启了生态批评的文化批评纬度之先河。
其次,生态批评对笛卡尔—牛顿的机械自然观、二元论、还原论予以无情的批驳,认为生态危机敲响了培根、笛卡尔、牛顿开创的将人与自然分离的“现代大法”的丧钟。塞尔(Serres)指出,“统治与占有是现代科学技术时代之初笛卡尔发出的两个最为响亮的词汇,从此,西方的理智奔向征服宇宙的征程,我们统治、我们掠夺,这就是工业企业以及所谓的客观科学共同的哲学基础,在此方面,二者并没有区别。笛卡尔的统治使得科学的客观的暴力系统化,成为精心控制的策略。我们与客体的关系根本上说是战争和财产”[10](31—32页),自然成了人类的共同的客观的敌人。贝特(Bate)指责笛卡尔对上帝的放逐,导致生态灾难。笛卡尔—牛顿机械自然观宣布自然是一部无生命的机械世界,而且,人与自然是完全分离、对立的。也许在他们的心中还有上帝,但是,他是冷冰冰的形而上的上帝,不是自然中无所不在的力量,上帝已不在山川湖泊之中,他在人类导演的自然万物生灵的悲剧过程中,只能扮演一个无助的、冷眼的旁观者。启蒙时代的到来,森林既不神秘也不神圣,而是由人来处置的。笛卡尔后的时代,统治、占有自然之梦成为现实[11](168页)。
最后,生态批评对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政治学狭隘的视域予以揭露。稍稍一看近现代西方权利演进的历史,哪个不是只关注人的权利?生态批评家贝特在评价现代权利理论的鼻祖卢梭指出,从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可以看出,他已经认识到文明意味着人与自然的疏离,人对自然的占有,也意味着人的堕落。因此,为了拯救人类,让他们在更高阶段上回复自然,恢复自然人性,人与人之间就应该签订社会契约,这就是卢梭的《社会契约》的主旨。从生态的视角看,卢梭的思想中蕴涵着一定的生态意义,至少,他已经意识到生态剥削与社会剥削如影随形,如他写道:“大片的森林被变成开阔的、洒满阳光的乡村,它需要人的汗水浇灌,从此,奴隶制度和厄运就与作物一起产生、成熟。”[11](48页)但是,卢梭只关注社会契约而无视自然契约,他强调人的天赋权利(natural rights)是基于自然的秩序(natural order),而自然却不能享有权利,这个悖论充分暴露了卢梭思想的局限性。启蒙思想的高潮是普遍的人权宣言的颁布,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都深受卢梭思想的影响,两国革命都主张根据诸如自由、平等、博爱等抽象的原则来组建社会。在强调人权、自由的同时,无视自然的权利,将它放逐,其结果是人欲横流,加速自然的破坏。
总之,随着生态批评的发展,其研究范围不断深入、延伸,它试图将人类一切文化置于生态视野之下重新审视,以期重构崭新的生态型文化范式。
今天,我们正在经受一个物种(人类)单方面宣布他的权利,而忽视其他所有物种权利所带来的恶果。有了普遍的人权,没有了上帝的约束,再加上笛卡尔—牛顿的“方法”,不仅导致了西方社会的整体败落,也引发了全球严重的生态危机。
生态批评坚持生态学的颠覆性的信条——相互联系的观念,将自然、人类、文化联系在一起,跨越学科之间的界限,探寻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策略,其根本目的是建构生态诗学体系,倡导生态学视野,让它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技术领域,以便从根本上变革人类文化,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怪圈,扩展人类的伦理,开拓人类的观念,向以生态中心主义的世界观转变,真正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蓝图。
标签:生态危机论文; 生态环境论文; 生态文化论文; 比较文学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人与自然论文; 生态学论文; 环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