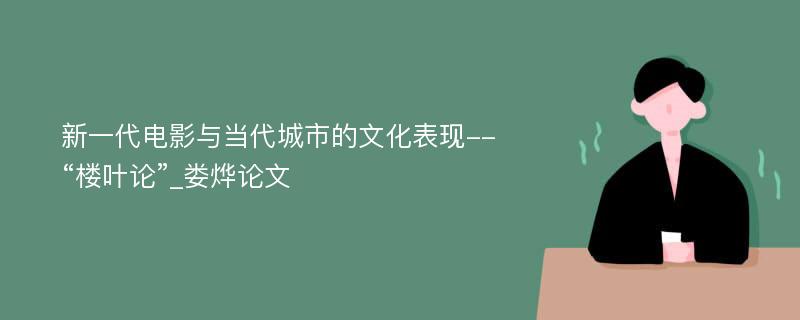
新生代电影与当代都市的文化表达——娄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生代论文,当代论文,文化论文,电影论文,都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选取青年导演娄烨的三部电影为例,对1990年代以来中国都市电影文化的发展态势做出一个简略的梳理,文本细读考察的逻辑出发点在于:其一,作为“超级城市”数字电影系列的主要策划人,娄烨对当代都市生活中衍生出的一切包括文化幻想都具有高度的影像表现冲动,也因此成为新生代导演群体中着力于当代都市电影创作的重要代表;其二,具体到他的作品《周末情人》(1993年)、《苏州河》(1999年)和《紫蝴蝶》(2002年),分别选取1990年代和1930年代的上海为主要故事背景,一新一旧的双重镜像叠加不仅对应了现实生活中上海这座城市文化现代性演变的两个关键时段,而且也因上海在中国现代城市化进程中的独特象征地位,而使影片成为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精神隐喻系统中的重要一维;其三,娄烨本人从属于“第六代”亦即“新生代”群体,而这个群体所具有的文化共同性,决定了“这一代”在从事都市影像创作过程中与主流电影政治/文化一体化导向的某种分野。从“地上”到“地下”,再返回“地上”,导演个人社会文化身份的辗转,恰逢中国社会急遽转型和都市内部多重意识形态制动的复杂变局,这一切都给当代都市文化的影像表达带来了许多的不确定性。
由此说来,娄烨电影创作的独特意义在于,他的三部影片分别以敏锐、多变和多元的镜语表达对应着都市意识形态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这个镜语表述系统本身也充满了不确定性,总是处于不断地自我反思、演变的风格转型之中。换句话说,如果对以娄烨为代表的新生代导演的都市电影创作进行一个总体性的概括,那么唯一可以确定的表述就是他们共同具有的那种个人叙事的“不确定性”。
《周末情人》:都市现实的“不对”与青春文化反抗
在分析《周末情人》之前,我想先对1990年代以来中国都市文化的语境生成做一个简单的描述。1990年代以来中国都市的现代化开始进入高速发力的阶段,上海作为中国当代都市现代性的典范而受到公众的追捧。由此,自19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以来一直作为被批判对象的旧上海魅影再度呈现了者日的荣耀。都市文化怀旧风尚的流行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它牵涉到文化全球化和后现代思潮等问题,在此不作赘述。但是具体到1990年代新上海形象的文化叙事中,它为何迅速接通了对1930年代老上海都市镜像的隔岸返照,这其中还是能够寻找到一些现实性动机的。
可以看到,随着1990年代改革的深入发展,大量“白领阶层”、“成功人士”和“中产阶层”涌现出来,作为被主流意识形态所鼓励的、被寄望于带动社会全面进入小康生活的主要力量,他们被确认为是生产社会财富的经济主体和保障社会稳定的消费力量,进而逐渐占据了社会文化趣味的主导地位。物质财富的丰裕同时也增进了他们的成就感和所谓高尚社群的归属感,他们需要世俗的都市日常生活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文化身份认证、生活品味指南和消费时尚的包装。然而这一时期整体仍欠发达的社会文化现实,常常不能及时地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文化消费指引。这样,对西方社会中产阶层生活时尚的想像,便适逢其时地借助于老上海1930年代的神秘镜像陌生而又熟悉地折射出来。当然这种跨越了时代的文化时尚信息已经无法通过对都市生活图景的全面复制而获得,而是经由怀旧电影、畅销小说和老照片等所展示的老上海遗留的碎片中透露出来。而对当下生活中缺乏现代都市历史经验的中产阶层群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享用这些真假难辨的时尚似乎已经足够满足他们与国际接轨的虚荣心。老上海种种的风物掌故和流闻逸事之于他们,就如同一份生动有趣的中产阶层的社交礼仪手册,优雅别致又略带几分恍若隔世的迷离,吸引着他们匆匆追逐的目光。如果说1980年代曾经风靡一时的电视剧《上海滩》被看作对旧上海魂魄的经典再现,那么1993年陈逸飞的自传性影片《海上旧梦》则借用一种回溯性的视角,将旧上海具象化为一个浪漫的女性魅影加以赞美。整部电影没有故事情节,也没有对白,大量蒙太奇段落的拼贴意在突出画家的梦游和对这个曼妙女体的追寻。影片叙事原型来自于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它突出了此类都市电影的共同主题——对欲望的追寻和想像的再生产。紧接着,《人约黄昏》《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和《风月》也都不约而同地将十里洋场作为都市影像表达的焦点。《人约黄昏》的叙事强化了《海上旧梦》中的“追赶”主题,然而如果从文化症候的角度来分析,这其实更像是新上海对于旧上海一厢情愿的文化招魂。电影中,记者在舞厅中循着“女鬼”的身影追踪而去,当舞曲停下来突然发现眼前翩翩起舞的却不是自己的梦中人。这似乎说明那些曾经作为历史存在的真实,反而失陷到人们因为文化怀旧而不断膨胀起来的幻象迷城之中。这一切都使1990年代以来以上海为题材的影像叙事中大量地充斥了虚假的感性素材和公式化的理解。对那些观看者来说,电影如何叙事并不重要,他们关心的是叙事材料和细节景观的离奇有趣。而在这个过程中,恰恰是他们正置身其中的当下都市现实生活出现了严重的精神空场。
都市怀旧叙事运用了“让历史告诉未来”的修辞,然而由文化怀旧所建构起来的都市镜像离真实的生活太过遥远,在本质上更接近于电影的“白日梦”属性。当幻象消失,逐渐展开的粗鄙生活真相依然显得如此难堪。与此同时,由文化谎言制造出来的结果,恰恰由那些在现实空场中得不到历史精神哺育而显得营养不良的年轻人来承受。现实生活让他们感到处处“不对”,却又无法从前辈和历史那里获得一个理性的解释。“不对”是那些处在都市社会边缘、天生抱有逆反心理的文化青年对于社会现实的应激性反应、一种直接的情绪表达和身体文化反抗。娄烨早期的《周末情人》和主题与之相似的《头发乱了》《北京杂种》中都充满了因现实社会“不对”而产生的莫名愤怒。他们不相信怀旧叙事所描画出的都市前景,然而新的都市叙事和形象塑造权力尚在暗地里的争夺过程之中。
当娄烨试图借助《周末情人》的影像叙事疏离那个被新意识形态所笼罩的老上海形象时,在他和那些老上海故事之间就明显地存在着一种美学的对峙和精神上的紧张。问题在于,越是感到这种精神对立物的强大,就会越不自觉地在自己的影像美学实践中往相反的方向倾斜。然而,作为刺激他们进行反抗的内驱力——那些源自现实生活中的愤怒情绪并不像前辈那样因为文化转型的痛苦而产生出了巨大的思想批判力量,它们不过是都市日常生活笼罩之下个人精神虚空中的一些青春期情绪分泌物,因此不具有太大的现实杀伤力。这样他们剩下了假想式的文化反抗,或者干脆为了反抗而反抗,让反抗变成“这一代”的文化仪式,并且因为能够拥有这种不合时宜的态度而表现出极度的精神自恋和自我放逐的文化偏执。
但是很多情况下他们或许并不明了个人产生怨怒情绪的现实来源,也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反抗的具体所指为何。因此《周末情人》在叙事终端就遭遇到了一个难以避免的后果,他们最终可能会将内心淤积的不满和愤怒情绪转而宣泄到同辈人、群体内部、自身,甚至比自己还弱小的弱势者身上。影片中阿西和李欣偷偷约会,被同学告发后愤而报复,终因过失杀人而锒铛入狱。此后李欣的新情人拉拉因为争风,一时意气失手刺死了出狱不久的阿西,为此也身陷囹圄。在这种普遍纠结于1990年代“愤青”群体内部的互文性叙事中,叙述者借以实践反抗的主体和反抗的对象合而为一,最终新生代导演的都市影像书写陷入了一种自我指涉的怪圈。
《周末情人》中的文化自戕的结局,从某种意义上验证了1990年代都市青年仪式化反抗的叙事局限。大概导演也想挣脱这个奇特的文化宿命,于是在故事的结尾为失败了的文化青年安排了一个光明的前景:若干年后拉拉出狱,迎接他的人群中有一个怀抱中的婴儿,那个婴儿的名字叫拉拉。仪式化反抗的失败者希冀有一个真实可信的文化宁馨儿的诞生,这显然是一个预支的光明。当他们告别了现实坚守,也开始学着“向前看”,所有的焦虑、躁动、抑郁、落寞似乎已被彻底释放的时候,我们似乎嗅到了1990年代初曾经风光一时的都市先锋影像在现实的逼视下迅速衰老的气息。
《苏州河》:反传奇的都市影像“传奇”
1996年,上海市政府启动了苏州河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在此后几年间河流污染治理获得了较大的成效,水体黑臭的现象得以改观。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娄烨开始了影片《苏州河》的构思和拍摄工作。
相信两件事情不存在任何关联,我之所以有意在这里将它们并列叙述,是因为他们相似的文化行动——政府管理机构和个人艺术家几乎同时注意到了这条横穿上海城区的河流,并开始着手对它进行巡视和改造。不同的是,前者的目的是将苏州河从上海城区的排泄通道改造成为景观河,而后者则是漫游在苏州河上,对那些从城市下水道里漂流出的各式传奇故事进行一次美学意义上的打捞。影片伊始,画外音响起:“我经常一个人带着摄影机去拍苏州河,沿着河流而下,从西向东,穿过上海。近一个世纪以来所有的传说、故事、记忆,还有所有的垃圾都堆积在这里,使它成为一条最脏的河。可是还有许多人在这里,他们靠着这条河流生活,许多人在这里度过他们的一生。在河上,你可以看到这些人……看的时间长了,这条河会让你看到一切。”
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代以来有关“都市上海”的集体性叙事尤其怀旧叙事,主要取材于它的“上层”社区也就是城区的西部,而东部或者说苏州河以北,则成了这一叙事的边缘,它通常是被叙述者所忽略的。导演将摄影机对准这条连接着各个社会阶层、各个区域的河流,那么反映在镜头里的也因此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当代都市上海的文化形象,一个繁华与腐烂同体、虚假与真实伴生、赞美与批判共存的、复杂多面的上海。为了避免一些特殊影像可能会造成片面化的情绪暗示,导演在大量运用晃镜技巧的同时也保持了相当的克制。比如影片中的镜头常常徘徊在外白渡桥附近,但是鲜有镜头将视线稍稍抬高,越过桥面,向前延伸到近在咫尺的浦东新区标志性景观。河流的流动性暗示了这个日新日日新的“都市上海”的文化形象表达时刻都处于流动和变化之中,也因此存在了许多不确定性的叙事变量。前一刻发生的事件,因为叙事参照系的变化,就可能会发生叙事指向的变化。也正如此,关于上海的叙事通常都是以传奇的形式播散。所谓都市传奇的本质,简单地说,就是真实和虚假两者相互影射而产生的不确定性。
在我看来,《苏州河》是新生代导演的都市电影创作中最具有不确定性的、因而也最具有阐释厚度的影像文本。从叙事主题上看,《苏州河》成功地借用了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影片《维罗尼卡的双重生活》,追问人类生活和精神世界中“消隐的另一半”。不同的地方在于,“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影片更多的是形而上的生命体验,而我(指娄烨——引者注)的影片还是贯穿在寻找之中”[1](P257)围绕波兰克拉科夫的维罗尼卡和法国巴黎的维罗尼卡两者的叙事是平行地展开的,在她们之间发挥关联功能的是爱本能与死本能的生存意识感应,后者在前者死亡引发的突如其来的“在世的悲伤”中被盗走了性的快感。相较而言,关于牡丹和美美的叙事是以交叉蒙太奇的方式进行,连接她们的是精神病患者马达喋喋不休的回忆和讲述,当美美从最初的拒绝到半信半疑,再到最终相信并彻底沉浸于马达带给她的叙事世界中,她就和牡丹的形象完成了重合,并在牡丹的死尸所引发的巨大震惊中,将世俗的爱情从污浊的黑暗中抽象出来,再次开始对于纯粹的爱的寻找。
具体到叙事结构上,《苏州河》进一步体现出开放性叙事和意义伸展的多种可能,从而与更多的新生代都市电影发生了相关的叙事联想。比如影片中面无表情的民工和桥头上无所事事的闲人,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王小帅的《扁担·姑娘》、王超的《安阳婴儿》和唐大年的《都市天堂》;长焦镜头中阳台上打架拌嘴的小夫妻,似乎也上演着与张扬《爱情麻辣烫》和张元《我爱你》中如出一辙的情感闹剧;甚至马达骑着摩托车在苏州河岸的飞翔,也在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唐大年《北京你早》中有相类似的场景,而影片的运镜又同《摇滚青年》《北京杂种》和《头发乱了》极为类似,甚至直接影响到当下都市青年的DV创作风格。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苏州河》具有近似于中国当代都市影像元叙事的功能,它不仅敏锐地感受到当代都市现实生活和情感世界的变动,而且能够迅速通过独具个性的影像创造与之发生广泛的叙事对应。
在故事的开头,导演借助摄影师的视角完成了对苏州河两岸的巡视。他的镜头在对准婚嫁庆典、高楼大厦的同时,也没有漏掉苏州河上斑驳的渔船、劳动的人们、孤独的背影和突如其来的死亡。在这个持续3分钟之久的段落中,导演运用手持摄影、快扫镜头、迅捷跳切以及富有创意的镜头角度,以不少于100个的镜头,将上海的都市空间进行有效的切割,再按照自己个人的意愿加以蒙太奇的组接和安排。“我的摄影机不撒谎”,叙述者在电影一开始便开宗明义,主动交代自己是在编造故事,用“让我想想”、“可能是”、“也许”之类的字眼来延续故事。这很像是“后设电影”或者说“元(META)电影”的叙事手法,借用电影中的符号反身指涉电影的制作和叙事过程。
影片中围绕马达的叙事有两条线索,一个是过去的马达,一个是现在的马达。关于马达的过去,包括他与牡丹的爱情,与萧红、老K筹划的绑架阴谋,牡丹跳河自杀等,都通过倒叙手法完成。影片默认的全知全能视角与叙事者——“我”的叙事视角基本一致。但随着马达出狱,邂逅“我”的情人美美,叙事开始滑入当下时态,在与马达交谈中,“我”发现叙事的节奏和方向失控,再也无法保持像摄影机一样的超然和客观,反而成为制约马达推动个人叙事的消极介质。最后“我”非但没有成功地阻挡马达对“我”的叙事权力篡夺,反而被马达和“牡丹”并排死亡的场面所说服。这样,“我”的叙事在影片前后部分出现了割裂,观众会发现,在“我”的开场白中部分说法来自于马达的叙事暗示。于是“我”对自己的叙事也产生了怀疑:“别信我,我在撒谎。”
大体说来,对于都市传奇的反叛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彻底摒弃现有的都市叙事手法,重新建构一套书写都市生活的意识形态话语。《周末情人》就是在朝这个方向用力。然而这种革命性叙事的困难在于,它不仅需要社会整体文化思潮的支持、语言观的转型,还需要有天才导演的出现。在目前的情形下,如果以简单排除的方式与都市怀旧传奇的意识形态对垒,结果很可能是它自己首先难以避免意识形态的单一化特征。这似乎应验了贾樟柯的话:你越反对什么,就越容易成为什么。第二种是反其道而行之,即遵从当下流行的都市叙事方式,深入都市传奇的内部,将真实与虚幻之间的各种裂隙显影,进而强化、放大这种裂隙,最终达到让都市传奇自身颠覆自身的目的。
从表面上看,《苏州河》是一个典型的都市爱情传奇故事,每个叙事单元都符合构造都市传奇的要素(巧合的情节、若即若离的爱情、阳光下的罪恶、酒吧间里的光影、时尚的衣着、精神萎靡不振的青年),当这一切元素都化合在一起,呈现给我们的不只是一场经典的当代都市传奇的影像,更因为每一处细节、每一个叙事元素的不确定性而使故事充满了智力化、戏剧化的风格。在公众眼中,都市传奇的神秘魅力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如影片主题歌所言是一种“恍惚的目前”状态。而《苏州河》将这种种不确定性加以无限的丰富和夸大之后,那些建构都市传奇的基本元素因为无法承担自我极端膨胀所带来的叙事重压,在叙事抵达高潮的同时也砰然爆裂,这样恰恰就从传奇世界的内部完成了对都市传奇叙事的重创和消解。当所有的浪漫和谎言消散,叙事者完成了向一个都市现实主义者的转变:“我宁愿一个人闭上眼睛,等待下一次的爱情。”
《紫蝴蝶》: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
在娄烨的城市系列电影创作中,如果说《周末情人》是以现实来对抗传奇,《苏州河》是以传奇来颠覆传奇,那么晚近的《紫蝴蝶》就是以想像来虚构传奇。当然《紫蝴蝶》中的传奇不属于1990年代怀旧风潮中的都市集体叙事,虽然导演将视线投向了1930年代的老上海,但是夜夜笙歌的升平盛事已经尽可能地从镜头中淡出,观众看到的是街头骚动的人群、连绵不断的阴雨、猝然的枪声、凄厉的火光、莫名的忧伤、苍白的脸色和纠缠暧昧的人物关系。一种死亡、延宕和犹疑的气息笼罩在影片中,而他们的生命和情感在一个混乱的年代里又显得是那么的不堪一击。这也是影片以紫蝴蝶作为核心意象的一个缘故。
不妨作一个简单的比较,《苏州河》用惯常的传奇叙事将1990年代流行的都市传奇推到了它的反面,但这种反讽和它希望指示出的现实意义在观众那里也许是无效的,因为影片叙事表层中大量时尚鲜活的镜语符号和快餐式的段落设置为观众提供了各种自由出入的审美通道,所以在盗版DVD市场上,娄烨的《苏州河》反而成为国内独立电影中流传最为广泛的作品。而观众抱着同样的愿望观看获准公映的《紫蝴蝶》后,却得出了相反的反应。影片在大陆电影市场的票房一路惨败,制片方只能通过出售海外版权勉强收回投资。《紫蝴蝶》在艺术和商业上的巨大反差,折射出新生代导演群体“浮出地表”后冰火两重天的普遍困境,具体到这部影片之所以无法获得观众的认同,在我看来主要原因在于它受到“作者电影”的观念影响,脱离了传统的叙事模式和审美习惯。然而影片的超现实影像风格太过于前卫,甚至远远超出了当代人的理解力,这就给《紫蝴蝶》的理解和接受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紫蝴蝶》的故事以1930年代的都市上海为背景,在今天的人看来,似乎那是中国现代都市史上迄今为止最为辉煌的黄金时代,十里洋场中的纸醉金迷和声色犬马占据了这个时代影像画面的中心部位,而娄烨就是在这里尖锐地提出了他的疑问:“我们头脑里的30年代可能只是一个概念,是被曲解的,被歪曲的,一想到30年代就是旗袍,都是那种固定的概念。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一个幻想,不一定是真的。那么,那时候人是怎么生活的,可能你要知道的话会挺吃惊的。他们面临的事情可能比现在要复杂得多,要混乱得多,要厉害得多,因为那时候有很多的战争,有很多民族矛盾,面临的事情要比现在多得多,那时候的生活更是一团糟,30年代可能更没法活,但是好多人都从那个时候活过来了。”[1](P264)娄烨毫不讳言《紫蝴蝶》中的上海是一个假想的都市,故事从人物形象到情节设置都是完全虚构的,因此充满了导演个人的影像风格。相比《周末情人》身体感性的躁动与结尾处言不及义的光明的尾巴,《紫蝴蝶》表现出了更为深沉的感伤与“在世的悲哀”,影片中这种情绪无处不在,并通过导演相当理性克制的叙事而传达出来。
影片进入1930年代都市旧梦的方式是借助今日的情怀来理解、实现的,这其中包括了导演对于当下生活的看法、立场和态度。娄烨敏感到“当时的生活和现在是有关系的”[1](P264),而他受到的质疑也常常会在这里:当下的都市生活本身已经充满了模糊与暧昧,他又如何用当下的不确定性来表现另一段亦未可知的历史,又如何能够“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呢?
如果换个角度看,上述问题或许能够在一个新的层面上获得解释。试图借助影像、文字或者回忆来复原历史这种行为本身是不明智的,然而不管历史还是当下现实,都市生活本身潜藏的不确定性以及它们带给生命个体的精神性压抑则是相同的。以当下的心灵体认历史的情绪,在这个审美创造的过程中,经由当下生活释放出来的压抑情绪,事实上也包含着历史的心理压抑。具体到这部电影,现实与历史的移情和转喻在叙事中是借助紫蝴蝶的意象来完成的。这是一个被文化嫁接过的意象。蝴蝶在中国传统叙事中可以自由出入于梦境/现实、历史/当下、虚假/真实、精神/肉身之间,而在西方文化谱系中,紫色则隐喻了高贵、孤独与受伤。作为一个感性的形象,紫蝴蝶出现在依玲的生活场景中,而随着依玲的猝死,瓶中挣扎的紫蝴蝶也随即失去了生命的光泽,看上去更像是灰色的飞蛾。影片中多次切入依玲在总机操作台前人工接线的场景,这似乎是虚无之神的显影,肆意地作弄故事中的人物关系和命运,同样影片中颇具巴洛克风格的主题曲《我得不到你的爱情》写意化地反复咏唱,这使得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挣扎显得荒谬和非理性,最终陷入存在的虚无之中。与此同时,大量延宕拖沓的默音场面又不断加重着虚无的压抑感,给观众的审美期待制造了巨大的考验。
电影最初的名字叫《无辜分子》,讲述一个普通人卷到一个他不愿意卷入的事件里,此后与事件相关的所有人都陷入了死亡的深渊。影片围绕以谢明、丁慧(辛夏)为首的民间抗日组织与伊丹英彦为代表的日本特务之间的智斗展开叙事,其中又交织着丁慧与谢明、丁慧(辛夏)与伊丹英彦、丁慧与司徒、丁慧与依玲、司徒与依玲、司徒与伊丹英彦等多重人物关系。从叙事结构上看,导演排斥传统的影戏叙事手法(开端-发展-高潮-结尾),同样也摒弃好莱坞电影模式对于影像叙事总体性和完整性的要求,相反,影片总是在最能够博取观众审美共鸣的节点处稍纵即逝,而在功能性叙事十分稀薄的地方反而停顿下来,固执地使用令人视觉倦怠的长镜头,对这些“有意味的形式”进行强化和重复。此外,影片中还大量出现镜头的跳切、快扫、重复、闪回、叠化、交叉和短镜蒙太奇的拼贴,这不仅让原本混乱的事态和人物关系叙述变得更加混乱,甚至连拍摄者本人的叙事逻辑也失去控制,都处在一种“被卷入”的混乱状态。
《紫蝴蝶》的不确定性美学风格源于导演对于影片中虚构的叙事关系的迷恋,(注:事实上娄烨本人在前期剧本创作中也多次遇到人物关系不确定的矛盾,而他解决的方式也很简单,对剧本中无法解决的问题,全都标注“拍摄中处理”。)在他看来,个人在历史中处于一种类似于无物之阵的迷失,表现到影像叙事中则需要在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描述中得以显影。然而“电影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的一个部分”,[1](P265)在因果律的支配下以乱世史诗的手法去概括和把握无边的生活,甚至用1930年代的海上旧梦来推断1990年代的新都市上海,这本身就是一个虚假的电影神话。《紫蝴蝶》的意义在于,它不仅开辟出一条重述1930年代都市上海的新的叙事通道,而且也在精神的层面上完成了历史/现实的互文转换。都市化进程中的物象表征会跟随着时代而发生相应的变异,而在时代的内里,那些精神性的东西会以看似微弱的关联维持着一种真实的传继。这种传继当然也包括一些精神性的痼疾,比如恐惧和犹疑。如果剖开民族主义的叙事外套,就会发现现代都市神话带给个体生命的文化虚无感制造了这个时代最大的精神恐慌。如果说在《苏州河》中局部的细节真实与整体上的反讽叙事营造出了一种相互绞结的悖谬风格,从而戳破了1990年代的都市传奇的话,那么面向1930年代老上海的《紫蝴蝶》则完全来自于导演本人的想象。从细节到整体的真实并不重要,因为他希望超越出具体生活实在的描写,去捕捉社会大变动带给人们关系的变动和情感恐慌,从而提炼出1930年代一个重要的时代精神特征——由乱世所引发的强烈的精神失重。在影片的结尾闪回出丁慧和谢明生前一次毫无征兆的激烈性爱,那是在枪战的前夕,他们突然抑制不住自己的恐惧和脆弱,在逼仄的斗室中像野兽一样疯狂地媾和,似乎要把身体中死亡的虚无感一点点地挤压出来。当丁慧忍不住说“我们为什么要战斗”、“我害怕”之后继续走向让他们为之恐惧的未知世界时,一种西绪福斯般在世的悖谬感和真实的文化悲悯油然而生。也就是在这里,娄烨的上海叙事克服了都市文化失重所带来的虚空,一些新的具有建设性的力量渐渐从内心中生长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