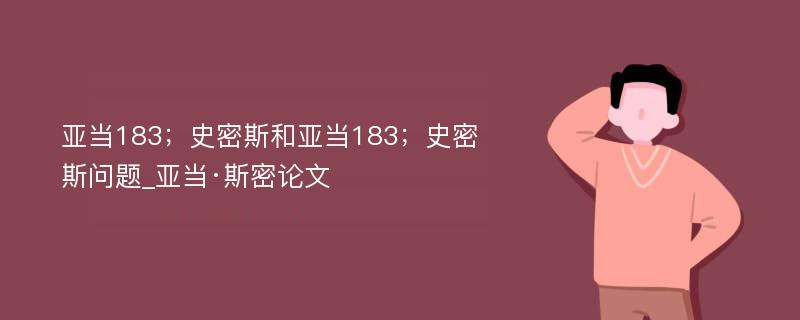
亚当#183;斯密与“亚当#183;斯密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当论文,斯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862(2007)06-0017-07
一 “亚当·斯密问题”的产生与斯密的自相矛盾
1.“亚当·斯密问题”的产生
“亚当·斯密问题”即关于亚当·斯密的人性自利与利他以及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源于19世纪中叶的德国历史学派,他们认为斯密最初在《道德情操论》中主张同情或利他是人的本性,而在后来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中却改变了对人性的看法,转而把行为动机归结为利己或自私,由此造成了《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之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对立。从学术思想产生的宏观历史背景来看,这一问题的产生源于资本主义落后的德国与先进的英国之间的现实矛盾。立足于德国的特定条件的经济学家们追随弗·李斯特,反对亚当·斯密经济理论的普适性,认为斯密强调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的经济学不能适应德国的实际状况,德国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国家的干预、国民的道德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旧历史学派的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1812~1878)“将道德、宗教、习俗和适当的标准指认为影响经济行为的因素,强调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并使人注意德国经济面临的特别的条件”①。这些德国学者认为,“起初认为人类交往是基于人们相互之间所感受到的一种同情的道德哲学家亚当·斯密,在某个时候变成了把自利视为激励人们行动的东西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②;“斯密的两本书完全不一致;斯密可能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但他不是哲学家。”③ 旧历史学派着力批驳斯密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并不断揭示其内在对立。新历史学派的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1844~1931)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把抽象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个人作为理论分析的出发点,批判斯密的“经济人”是“经济的利己主义者”,是唯利是图的“抽象的人”,由此引起边际效用学派的代表庞巴维克的反驳。历史学派与边际效用学派除围绕斯密经济思想存在分歧和论争以外,更主要的是关于斯密《道德情操论》中人的本性与《国富论》中人的本性的论述是否一致的问题。这一从人的本性的角度对斯密两大著作关系问题的论争持续了约一个世纪,在经济学说史上被称为“亚当·斯密问题”。
2.“亚当·斯密问题”研究的历史发展
自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之后,多数学者都把斯密看做伦理学上的利他主义者和经济学上的利己主义者,这一观点几乎成为传统信条;包括原苏联学术界也不例外。20世纪初,苏联著名学者卢森贝认为,斯密“研究道德世界的出发点是同情心,他对于同情心的定义,就是‘对于别人的遭遇的关心’;他研究经济世界的出发点,是利己主义——在经济生活中所追求的完全是个人利益”④。斯密《道德情操论》中的道德世界和《国富论》中的经济世界是两个相互区别、相互对立的世界,而且“斯密没有说明为什么‘经济中的个人主义’在‘伦理学’中变成了相反的东西,即变成了利他主义”⑤。卢森贝认为斯密未能把他的两部著作中的思想统一起来。随着现当代社会与经济的发展,随着伦理学与经济学学术分工的片面发展所造成的缺陷的不断显露,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伦理与经济、伦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相互关系,重新解读“亚当·斯密问题”。D.D.拉斐尔(D.D.Raphael)和A.L.麦克菲(A.L.Macfie)在1990年为纪念斯密逝世200周年而编辑出版的斯密《道德情操论》一书的序言中指出:“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是一个基于无知和误解的伪问题。先读了《道德情操论》的早期某一版本然后读了第六版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对同一个人写下了这样一本书和《国富论》而有感到迷惑的任何轻微的意向,或者认为他关于人类行为的观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斯密的伦理学和对人类行为的论述在1790年的第六版中和在1759年的第一版中是基本相同的。虽有发展但不是基本方面的改变。”⑥
我国对“亚当·斯密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朱绍文教授认为,斯密的“经济人”是当时社会中从事生产性劳动、增加社会财富的“中、下层平民”,在他们那里,“走向致富之路”与“走向道德之路”是统一的;对斯密的“经济人”与“道德人”相对立的误解,“经过几十年的论争之后,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对斯密道德哲学思想体系有了深入的研究,在经济学界才得到澄清”。⑦ 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先生认为,“斯密问题”并不存在,“所谓两书中存在的‘亚当·斯密问题’,不是一个实际而只是一个假象。”⑧ 斯密在《国富论》中对待利己主义的态度是批判的,这一态度“是《道德情操论》中这一思想(以‘自我控制’来裁抑利己主义,引者注)的继续,是以之为前提的。在二书间存在着一个连续性;在两人性论间存在着一个互相补充的作用”⑨。万俊人指出:“只要我们大致了解斯密时代的知识状况,并仔细解读斯密的这两部作品,所谓‘斯密问题’本身并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问题,毋宁说,它的真正意义在于,如何认识市场经济的道德维度问题,其所关涉的经济伦理(道德作为经济的价值要素和评价标准)与伦理经济(经济生活作为人类道德的利益基础)的科学理解及其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解释问题。”⑩
以上有关“亚当·斯密问题”的观点基本上可分为两类:第一,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强调同情与利他,而在《国富论》中则力陈利己与自私,两者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对立与紧张;自德国历史学派开始直到20世纪上半期,大多数学者持此类主张。第二,在斯密的两大著作之间、伦理学与经济学的两大体系之间根本没有对立,它们具有内在的联系和一致性,都是斯密“道德哲学”庞大体系的组成部分;20世纪60年代后的现当代学者多数倾向于这种观点。
3.斯密思想的矛盾性
“亚当·斯密问题”决非空穴来风。其形成除历史的客观原因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斯密本人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看法存在着矛盾。斯密承认经济与伦理的一致性,但他对这两者关系的把握在不同的语境里有很大的差别。他在进行伦理学的叙述时,从人的同情本性出发,把伦理置于首位,使经济因素服从于伦理的规范和考虑,经济只是人们用来满足其道德情感、实现其伦理价值的手段;而在转入经济学的叙述时,他转而从人的自利本性出发,把经济因素放在第一位,从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合理性来阐释相应的伦理规范。就主观而言,斯密认为经济与伦理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它们都是其“道德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他的著述和写作客观上又在体系上、形式上造成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立,让它们各自拥有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在经济学的论述中不让伦理的内容过多地渗入,以保持经济学的连贯性、统一性;在伦理学的著述里侧重于伦理本身,把经济因素弱化到最低限度。斯密的这一做法蕴涵了经济学和伦理学相互分立和背离的发展趋势。在他之后,由于社会经济体系的膨胀与发展以及学科的分化和独立,经济学与伦理学完全分离开来并相互对立;在当代由于理论和现实的逻辑,经济学与伦理学又开始走向相互融合与统一。
二 道德同情与“看不见的手”——斯密对“亚当·斯密问题”的解决
“亚当·斯密问题”究竟应如何解决?斯密对此虽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但我们通过对斯密著述的解读可以梳理出其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思路。
1.“旁观者”的“同情”所形成的道德约束——道德情感论的解决
“在斯密生活的那个时代,‘道德情操’这一短语,是用来说明人(被设想为在本能上是自私的动物)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能力,即能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11) 在斯密时代,人们普遍承认人具有自私自利和同情利他的对立本性,“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最大的恶棍,极其严重地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12)。问题在于如何协调人的这两种不同本性,或者说,这两种本性在人们身上是如何得到统一、协调的?
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基本上是一种关于人们如何形成自己的道德判断、道德情感的心理学的说明(其“论有关美德的品质”是在他去世的那一年——1790年才新写的),“这本书所研究的是对事物的道德上的认可和非难这种观念的根源。人是抱有自私观念的动物,那么他怎么会对事物做出道德上的判断呢?斯密的答案是,我们具有一种能力,能使我们自己处于第三者地位,使自己成为一个公正无私的观察者,从而对一件事情的道德(与自私相对)价值形成同情的观念。”(13) 斯密提出的旁观者的同情理论就是对人们如何约束自利的道德情感过程的说明。他虽肯定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追求自利的经济活动,但他认为经济活动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人们对财富的追求、占有和享受只是实现一个更高目的——取得他人的同情或肯定——的手段。“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辛苦和劳碌是为了什么呢?贪婪和野心,追求财富、权力和优越地位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是为了提供生活上的必需品吗?那么,最低级劳动者的工资就足够了。我们看到工资为他们提供食物、衣服和舒适的住房,并且养活整个家庭。”(14) 他认为人们对物质生活的需求有限,不足以推动人们去无限地从事利己的各种活动。人们物质上、经济上以及政治上的追求都是为了得到一种心理的精神的满足,都是为了“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15)。“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这是因为他感到他的财富自然而然地会引起世人对他的注意,也是因为他感到,在所有这些由于他的有利地位而很容易产生的令人愉快的情绪之中,人们都倾向于赞同他。”(16) 在斯密看来,财富与经济地位只是引起人们关注、羡慕和赞同的一种手段,因此,追求自利的经济活动就不能以损害自己在他人心目中所受到的价值评价为代价;这样,对经济生活的追求就成为人们实现其道德情感需要的手段。
斯密认为人们的各种活动都要经历一个道德情感的心理过程,也就是形成和接受道德评价的过程。他的同情概念具有多种意义,除了把同情作为一种具体的、怜悯他人的道德感情外,他更多的是把同情作为一种心理上设身处地对同类感情的想象能力和体验能力。一种感情只有与他人通过设身处地的想象所产生的感情相一致,才能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情感并得到他人的赞同。人们在社会中究竟应如何对待自己和他人呢?每个人都是别人一切行为的旁观者,别人也是自己一切行为的旁观者,我们通过一个相互的同情过程来协调自己与他人的感情;每个人只有把自己放在旁观者的地位,才能使自己对待自己的情感与他人和全社会看待自己的情感相协调、相一致,才会适度地约束、限制自己的自利自爱之心,使自己得到他人和社会的肯定与赞同。斯密解决个人自利与利他的矛盾,是通过道德的他律和自律来实现的。一方面,其他的社会成员以旁观者的身份对当事人的行为与情感进行道德评价,形成社会的道德舆论压力来对当事人的行为和情感进行修正、调整;另一方面,行为人自己以旁观者的身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我评价,也就是通过把外在的客观的旁观者内化为自己内心的旁观者来对自己进行评价,通过道德自律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以符合社会道德的要求。
社会道德对人的他律,使每一个受利己冲动驱使的人不敢逾越正义的界限。在这里我们看到,斯密把道德情感置于最重要的地位,以人们对道德情感的需要来控制和调整利己与利他的冲突。斯密在论述正义情感的产生、人们在道德情感上被孤立所感到的恐惧时最为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违反十分神圣的正义规则的人,……当他的激情得到满足并开始冷静地考虑自己过去行为的时候,他不能谅解那些影响其过去行为的任何动机。这些动机——就像它们过去呈现在其他人面前总是让人厌恶一样——现在对他显得极为可厌。由于对别人对他必定怀有的厌恶和憎恨产生同感(by sympathizing with……),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自己的厌恶和憎恨的对象。……这种念头长久地萦绕在他的心头并使他充满了恐惧和惊骇。他不敢面对社会,而想象自己已为一切人们的感情所摒斥和抛弃。……人们对他所怀有的情感正是他最感害怕的东西。周围的一切似乎都怀有敌意,因而他乐意逃到某一荒凉的沙漠中去,……但是,孤独比社会更可怕。”(17) 一个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人,当他最初做出不义的行为时,似乎无所顾忌;事情过后,他一方面会受到他人的厌恶、憎恨、谴责甚至复仇和惩罚,另一方面又受到自我反省所产生的道德情感上的折磨,这双重的情感责难使他难以承受,产生悔恨,从而约束自己的一切行为使之不超出他人、社会和自己在道德情感的评价上所能容许的限度。
2.“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的解决
虽然伦理价值在斯密心目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伦理学是其经济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但斯密强调道德生活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时,不得不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人们对自利的追求已经成为全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世俗的物质生活已经取代宗教的精神生活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中心——从而肯定现实经济生活的正当性。如何协调人性中的利己与利他的对立,如何协调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和对道德生活的向往——两者都是每个社会和每个人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这两种不同的趋向,成为历代思想家面临的难题。在斯密所处的封建制度的灭亡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时期,这一难题更是成为斯密时代的思想家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在斯密对新经济的无比优越性给予高度肯定和赞扬的话语中,实际上他已不自觉地为我们提供了其解决“亚当·斯密问题”的另一种答案。
斯密承认,处于文明社会中的各个成员都离不开他人的活动,“随时有取得多数人的协作和援助的必要”(18),而且文明愈进步,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也愈大。但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实现人们之间的相互帮助再也不能完全通过直接利他的道德方式来进行,“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19)。在经济领域内,社会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按照经济本身所固有的运行方式来实现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帮助的目的。就斯密最初的写作计划和思想倾向来看,他把《国富论》作为其《道德情操论》的延伸和具体化,把伦理作为一种目的性价值,而经济只是实现这一价值的手段;因此,“看不见的手”这一市场机制就成为他论证和解决“亚当·斯密问题”的另一种方案。
“看不见的手”这一术语在《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中各自仅出现一次,最初并非一个学术概念。斯密最先把一个用来描述超自然力量的宗教术语转用来表达社会本身中所蕴涵的支配经济运行的一种无形的客观力量。“无论何时,土地生产物供养的人数都接近于它所能供养的居民数。富人们只是从这些收获物中选取了最好的和最宜人的。尽管他们的天性自私和贪婪,他们消费的还是比穷人们多不了多少,虽然他们只为自己的便利打算,虽然他们从其所雇佣的千百万人的劳动中所呈示出来的唯一目的是满足他们自己的自视过高的和极贪心的各种欲望,他们还是同穷人们分享他们所做的一切改良的成果。他们被一只看不见的手(an invisible hand)引导着对生活必需品做出与那种分配——要是土地在全体居民间平等分配时就会对生活必需品做出的分配——几乎一样的分配,他们既没有考虑到要这样做,也不知道这样做,他们被看不见的手所引导而增进了社会的利益,并为不断增加的人口提供了财富。”(20) 在商品经济的社会里,虽有贫富的差别,但总能做到物尽其用。在对食物的基本的需要和消费方面,地主、农场主和贫穷的劳动者并没有多大的数量上的差别,富人们把他们消费不了的大量剩余农产品通过货币交换——购买穷人们为他们所提供的各种劳务——的方式,使这些剩余产品为社会大众所消费和享用。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交换这一经济运行方式非常奇妙地导出了一个极具道德性质的结果:一方面,它肯定和激励人人都去追求自己的利益,以此增进了社会的生产总量,为全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创造了现实条件;另一方面,通过人们之间的商品交换,每一个人都比以往更多地满足了自己的生活需要,比以往直接出于人人为他的道德要求的行为带来了更多的实惠。在动机上人各自利的行为,通过一种特定的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社会经济结构或经济机制——“看不见的手”,造成了普遍的相互利益或相互利他;纯粹出于利己的行为,通过一种经济机制的转换,实现了利他的道德目的。具有这种特定经济机制的社会形态无疑要比以往任何社会具有更大的道德优越性。
在《道德情操论》里,斯密主要是通过“看不见的手”说明了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实现了社会生产物在各个人身上的物尽其用;在《国富论》里,他更明确地用“看不见的手”描述了商品社会所独具的经济运行机制。“确实,他通常既没有打算去促进公共(公众的)利益,他也不知道他将会促进多少公共利益。他更愿意选择支持国内产业的投资而不选择去支持外国产业的投资,他所考虑的仅仅是他自己的资本的安全;他以能使其产出可能具有最大价值的方式去指导、支配他的生产,他所打算的仅仅是他自己(的资本)的增殖,他在这一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lead)去促进一个并非他意图内的目的。”(21) 在一个其内容日益得到充实和发展的商品经济社会里,个人要去充分地了解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而个人要了解他自身的条件和他所面对的影响其利益的周围环境,则相对容易得多,而且他自己具有这一方面的强大的自利动力。在斯密看来,资本家仅仅出于对其资本的安全和赢利的考虑来决定资本投向,在动机上完全没有任何利他的道德上的考量,这样一种出于纯粹利己动机的行为——按照传统的道德标准是不值得称道的行为——所造成的结果,要比出于纯粹利他的道德行为所造成的结果更加有益于社会和他人。斯密在《国富论》里寻求的是一个不依靠政府权威(计划控制)和传统道德的新社会如何能够和谐运转的新机制;在新兴的商品经济社会里,斯密发现了“看不见的手”这一独特的市场机制能够在整体或总体上把个人的利己转换为一种有益社会和他人的结果,从而使全社会在宏观上基本消除了利己与利他的冲突和对立,实现了人的利己与利他的协调与统一。
三 斯密的贡献与不足
实际上,“亚当·斯密问题”作为对现实存在的经济与伦理关系的历史反映——人性的自私自利与同情利他的关系也是对作为主体的人所生存于其中的现实的、物质的社会关系的反映——也就是源远流长的义利关系问题,就是作为伦理学基本问题的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斯密问题所包含的人性的自利与利他的关系,在其现实的表现上即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的关系。斯密自己对“亚当·斯密问题”的独特解决,既有其历史贡献,也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
首先,斯密用旁观者的同情这一道德情感论或道德心理过程来解决利己与利他的矛盾、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矛盾是非常脆弱的。斯密崇尚人的伦理价值,力图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价值导向或动力支撑,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人们追求物质生活的欲望还没有被充分地激发出来,人们的求利活动还遵循着斯密所说的谨慎、正义等美德;一旦人们的物质欲望随着经济的发展极大地膨胀,人们变得狂热起来,这时斯密所说的旁观者的道德评价(即社会的道德评价)能够左右现实社会中每个成员的经济活动使之不超出一定的限度和范围的话语,就成为一种美好的幻想。我们看到,虽然经济与道德相互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互为目的,但经济本身具有自在自为的能动性质,它会不断突破和超越现有的、既存的道德的束缚与限制,并不断地召唤出与自身发展相一致的伦理体系。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呈现为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正表明了社会经济发展所具有的根本性、主导性和包括伦理道德在内的人类精神生活的依附性与从属性。斯密的道德同情论的解决方案随着社会经济和历史的发展就逐步丧失了其合理性。
其次,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成长过程中,虽然“看不见的手”所具有的理论辩护力非常强大,它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所蕴涵的客观必然性,而且有力地论证了其道德的优越性;但斯密过于乐观的、强调普适的经济学论述,有意无意地遮蔽了资本主义发展中所存在的深刻矛盾。就斯密的时代来看,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斯密提出市场将确保经济上的和谐。……(但)斯密没有说明这种雇佣劳动力的和谐是怎样形成的。如果他以史料为基础来进行分析,那么他将不得不面对血腥的原始积累过程。”(22) 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并不是一个自发的、令人向往的浪漫过程,迈克尔·佩罗曼教授充分肯定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始积累过程的说明,他认为“斯密最值得赞扬的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讨论,也是为了回避原始积累给他的体系提出的挑战”(23)。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迫使劳动力进入了一个要么受雇于人、要么忍受饥饿的状态。在那种情况下,雇佣劳动就成了一种自愿劳动”(24)。由此,“经济关系的无声强制已经变得更加有效,资本就可以假装工人们都是一场互惠互利交易中的合作伙伴”(25)。斯密对“亚当·斯密问题”的“看不见的手”的解决,实际上是把自利与利他、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或社会利益的关系交给了一种自发的、客观的经济力量去处理,而且仅仅把握了其中的相对于过去社会的合理的道德性的一面,而没有揭示其当下内含的不道德的一面。由此可见,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对自利与利他、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或社会利益的解决仅仅看到了社会经济总量的增长和整体水平的提高,而没有揭示其中所潜藏的利益对立与冲突。自1825年资本主义的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看不见的手”逐步失灵,“看不见的手”的自由市场的神话被打破。在现当代,必须对“看不见的手”的自发作用予以限制和调控,用法律的、行政的等制度性的“看得见的手”来规范经济,从而以政治的正义、制度的正义来解决“亚当·斯密问题”。
四 “亚当·斯密问题”的意义
“亚当·斯密问题”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它既涉及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又蕴涵着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的自利与利他的关系。斯密的学术著作与思想体系只是对特定时代条件下经济与伦理关系的理论反映。“亚当·斯密问题”这一名词也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特定历史概念——历史的并不只是过去的,历史的同时也是现实的。
“亚当·斯密问题”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斯密个人的著作或思想内容之间的关系。这一术语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关系范畴,其内容在学术思想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得到拓展。最初,“亚当·斯密问题”仅仅指斯密著作中关于人性或人类行为动机的论述存在差异或对立的问题;随后,这一问题包含了对斯密的经济学思想(体系)与其伦理学思想(体系)之间关系的探讨;现在,“亚当·斯密问题”更是演变为以斯密为源头的普遍意义上的经济与伦理、经济学科与伦理学科之间关系的研究。在现代社会里,经济与伦理各自构成为一个有着复杂多元结构的、相对独立的系统和领域——当然,伦理更多地是以渗透方式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的经济现象与伦理现象都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它们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交叉关系与互动关系。经济学与伦理学这一学科上的既分立又相互联结的关系,伴随着现实的运动发展,呈现出相应的改变:经济学是否需要伦理学并以其为价值前提与目的?伦理学能否超越经济学的潜在的或明确的支配而独善自身,即伦理学能否抵制经济学的扩张、经济学的霸权、经济学的渗透或经济学的帝国主义而保有自己的学术领域的完整和独立?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学科分立、学科分化在怎样的度的范围内才是合理的?当代对经济与伦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深入研究,不仅要求我们关注现实,深深扎根于现实的土壤,而且需要我们进行理论的历史回溯,以寻求启迪。
注释:
①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下册,晏智杰、刘宇飞、王长青、蒋怀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365页。
②③James R.Otteson,The Recurring" Adam Smith Problem" ,History of Philosophy Quarterly,Vol.17,No.1,January 2000,p.51,p.51.
④⑤〔苏〕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1卷,李侠公译,三联书店,1959,第243页;第243页。
⑥Adam Smith,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Edited by D.D.Raphael and A.L.Macfie,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1999,p.20,pp.184~185.
⑦朱绍文:《〈国富论〉中“经济人”的属性及其品德问题》,《经济研究》1987年第7期。
⑧⑨陈岱孙:《陈岱孙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第566页;第568页。
⑩万俊人:《道德之维——现代经济伦理导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第5页。
(11)(12)(14)(15)(16)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译者序言”第16页;第5页;第60页;第61页;第61页。
(13)罗伯特·L.海尔布罗纳:《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蔡受百、马建堂、马君潞译,商务印书馆,1994,第39页。
(17)(20)Adam Smith,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Edited by D.D.Raphael and A.L.Macfie,Beijing:China Social Publishing House,1999,pp.84~85,pp.184~185.参见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103~104页;第229~230页。
(18)(19)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第13页;第14页。
(21)Adam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Edited by Edwin Cannan,M.A.,LL.D.,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1999,Volumel,p.421.参见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王亚南、郭大力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27页。
(22)(23)(24)(25)迈克尔·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诠释》,裴达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211页;第11页;第211页;第211页。
标签:亚当·斯密论文; 看不见的手论文; 经济学论文; 伦理学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经济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