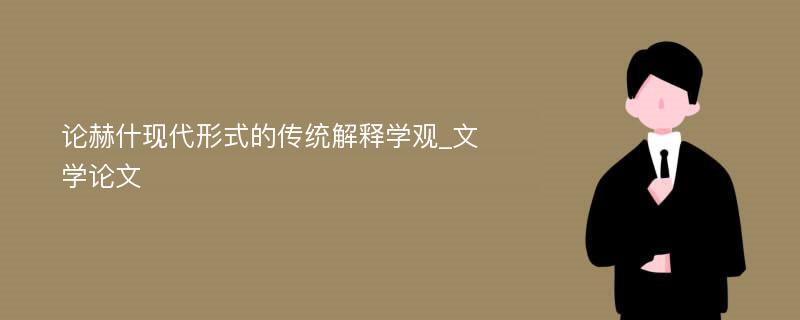
论赫施的现代形式的传统阐释学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式论文,观点论文,传统论文,论赫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08)01—0111—03
美国现代文学批评家J.E.D.赫施认为,文学作品具有客观的本义,它就是作者的意图。这种阐释学观点是对传统阐释学观点的继承。不过,他在其阐释学中融进了某些现代哲学和现代文学批评的观点,以便为传统阐释学做更有力的辩护。赫施的阐释学可以看成传统阐释学的现代形式。赫施在其《阐释的有效性》(1967)一书中表明了他的阐释学宗旨和特点:“我的宗旨在于使文学研究中的一些被人们遗忘了的深刻见解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并把语言学和哲学中的一些独到的见解运用于阐释理论中。”[1]413
赫施宣称作者的意图就是作品的本义,它是永恒不变的。他说:“作品的永恒意义是,而且只能是作者的原义,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1]418 基于此,他指出阐释者的任务是:“我们曾把作品的原义界定为作者的意图的内容(为了方便起见,下面简称为作者的‘表露意图’),阐释者的任务是很明确的,他必须把属于作者的‘表露意图’与那些不属于作者的表露意图的意义区分开。”[1]421 就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看,赫施强调作者意图的观点与日内瓦现象学派的观点接近,后者就强调批评的任务在于找出作者的“我思”,即作者的意识模式①。不过,赫施的观点更突出,更有针对性。因为早先就有美国新批评派力排作者的意图,提出所谓作者“意图的谬误”说,而强调文学作品本身的“本体”地位;与赫施同时代的伽达默尔等现代阐释学者则强调读者的主观条件对建构作品意义的作用,巴尔特等解构主义者对作者的作用更完全加以否定。赫施的《阐释的有效性》一书,首章却以“保卫作者”为标题,与巴尔特的著名论文《作者之死》的标题形成鲜明的对照。
作品的本义既然是作者的意图,而后者又是永远不变的,那么作品的本义也是稳定不变的、客观的。赫施说:“我想尽力表明的就是,尽管作品的意义是由作者的精神活动所决定的,并在读者身上得以实现,但作品意义本身却根本不能与作者或读者的精神活动同日而语。”[1]418 这即是说,尽管作者的创作活动和读者的阅读活动是主观的、心理的,不同读者的这种主观心理活动是各不相同的,但作品的意义本身却是客观的,稳定不变的。赫施认为“胡塞尔的观点为我们讨论阐释这个中心问题提供了极好的参照”[1]421。在胡塞尔现象学的意向性原理中,意向性建构分为“意向对象”和“意向行为”两方面,虽然意向行为对意向对象的作用可以是局部的,因人而异的,但意向对象却能保持自身的统一性和同一性。赫施以知觉一个盒子为例,说他在不同时间和不同侧面所看到的盒子的情况并不相同,“然而我所‘发觉’的还是同一个盒子”[1]419。于是赫施宣称:“作品的本义就是一种特殊的‘有意客体’(按:即意向对象),和其他客体一样,它可以在不同的‘意欲’面前保持自身的统一性。作品本义的一个值得重视的特征就是超个人性。”[1]420 赫施于1976年发表的《诸种错误看法》一文,在批评伽达默尔等人认为作品意义依据解释者的观点不同而不同时,也用类似的例子(两个人从不同角度看一幢建筑物)来说明这一问题。[2]261—262
赫施的上述论说是否可信?就他的论说本身看,他没有对不同类别的意向对象做出区别。首先,由语言所构成的文学作品这种意向对象,是很不同于盒子和建筑物之类的意向对象的。盒子和建筑物之类的意向对象不但是感性的,而且是实在的,它们的确具有自身的同一性。而文学作品这种意向对象,却需要读者在阅读中根据自己所理解的意思并结合自身的经验和趣味在想象中建构出来,它虽然也是感性形象的,但却不是实在的、确定的,不可能具有客观的和确定的自身同一性。例如,现实中的一个人显然具有他确定的自身同一性;而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形象则不可能具有那样的自身同一性,他在不同读者的脑海中会呈现出不同的形象。
其次,赫施在他的论说中还混同了文学作品这种意向对象与其他文字著作意向对象的区别。后一种意向对象的字面意义就是该对象的整个的意义,这种意义相对地是确定的,客观的。而文学作品的字面意义,显然并不等同文学作品的意义。在一般情况下,读者需要通过理解字面意义来再造艺术形象,那艺术形象所体现和蕴含的意义才是文学作品的意义。与此相关并更为重要的是,文学作品的审美特性决定了其形象的意义总要超越作品的文字意义,而在这种超越性意义中,常常包含着与字面意义不同的乃至相反的意义,这在诗歌这种经常运用隐喻和象征等手法的文学样式中最突出。其实,文学艺术的特质在于美,而美这种东西在本性上就是其蕴涵的意义不是确定的、客观的。艺术美如此,自然美也如此。在艺术美中,又以文学审美意义的不确定性、非客观性最为突出。
赫施的论说基于胡塞尔现象学的意向性原理。其实,从意向性原理本身也可以阐发出相反的结论,即文学作品的意义并不就是作者的意图,它不是确定的、客观的。意向性原理的核心,是主体对对象的意向性建构。而所谓意向性建构,其实质就是建构对象的意义。对象的意义因而既不是对象客观自生的,即本来就具有的,也不是主体凭空具有的,而是主体对客体对象建构的结果。胡塞尔说过,在建构对象的意义上,意向性就是主体向客体对象“给与意义”。对象的同一性实际上是由主体保证的;在胡塞尔后期的先验现象学中,则是最终由主体中的先验自我保证的。胡塞尔说:“一切实在的统一体都是‘意义统一体’。意义统一体须先设定一个给与意义的意识,此意识是绝对自存的,而且不再是通过其他意义给与程序得到的。”[3] (按:着重号为原文所有)胡塞尔所说的那个设定的“给与意义的意识”、“绝对自存的意识”,就是主体的先验意识,也就是主体的先验自我。就文学活动看,无论是作者的创作还是读者的阅读(再创作),都是意向性建构,都是向作品“给予意义”。作者所建构的意义,即作者意图,确实是唯一的,对他人来说也是客观的,因为他人不能参与其中。如果仅仅从作者的这种意向性建构看,并且把作者所创作的作品当成已经完成的文学作品,作者的意图确实就是他所创作的作品的意义;那意义确实也是确定的、客观的。胡塞尔本人、其后的日内瓦学派以及现在的赫施,他们就是不同程度地这样去看的,所以认为作者的意图(在日内瓦学派那里是作者的“经验模式”或称“我思”)就是作品的意义,它是客观的,不变的。然而,文学作品的真正完成是在读者的阅读中,因而作品的意义只能是每个读者读出的意义,这种意义总会是有所不同的。这是因为,读者的阅读也是一种意向性建构,而我们知道,正如作者对作品的意向性建构是独特的一样,读者对作品的意向性建构也各不相同,也是独特的,即便他们建构的对象是同一作品,是同样的文字符号。伽达默尔等现代阐释学学者就着眼于读者的意向性建构,所以得出结论说,作品的意义是不确定的,依不同读者和不同时代而变化的。
那么,是什么东西保证着在对一部文学作品的阅读中所显出的共同性呢?从作品的表层看,是文字意义。作品的文字意义大致说来是确定的、客观的。但文字意义还不是作品的意义,它仅仅是产生作品意义的基础。读者在此基础上进行形象构造和审美体验(根据现象学文论的观点,这是读者意向性建构的主要内容),由此才产生作品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必定是不确定的,因人而异的。
从作品的深层看,保证一部作品具有一定的同一性的东西,则是包含在文字意义中可供读者进行意向性审美建构并体现于作品意义中的东西。它就是赫施所说的作品的本义,其中也就包含着作者的意图。但它本身还不是作品的意义,而是构成作品意义的潜在要素:读者在阅读、理解和想象的过程中把它能动地建构成作品的意义,其间必然会融入读者自己的东西。由此可知,这种构成作品意义的潜在要素,这种被赫施称为作品本义和作者意图的东西,在作为读者对象的文学作品中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它的独立存在(我们单独称呼它)只能是一个设定。所以,所谓在阅读中再现作品本义和作者意图,只能是一个永远无法达到的理想——这是一个早就存在于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等人的传统阐释学中的理想。其原因就在于,阅读并不是读者主体对潜在的作者意图和作品本义的客观再现,而是对它们的一种意向性建构,并且常常是一种个人性和主观性很强的意向性审美建构。
所以,阐释文学作品的现实的和客观的基础,只能是作品表层的文字意义,而不是作品中潜在的作者意图和作品本义,后两者不可能客观地、确定地存在着。作者意图只存在于作者心中和作者所写成的作品中。而作品一旦成为读者的阅读对象,就无法原样地再现作者意图了,尽管许多读者常常自认为做到了这一点。这是因为,作者意图已经消融在作为读者建构作品意义的潜在要素——作品本义中去了,而作品本义是不能自身显现的,而只能包含在由不同读者所建构的不同的作品意义之中。
赫施在他的解释学中还做出了“意义”(meaning)和“意味” (significance)的区分,试图在坚持作品本义是稳定不变的观点的基础上,解决现代阐释学中作品意义的不确定性问题。赫施说,“意义”指作者意图,即作品本义,而“意味”则指在意义基础上衍生出的东西。依据他的观点,作品的意义是不变的,意味则因人而异,发生变化。赫施在《阐释的有效性》一书中已做出这种区分,从前面引述他关于作品本义即是作者意图、阐释的任务是把作品本义与不属于此本义的东西分别开来等说法,即可以见出。赫施在后来的《诸种错误看法》一文中也说到这种分别:“意义是一种客体,它仅仅由于是一种单独的、优先的和前批评的观点而存在。无论批评家在批评观上有多大的分歧,如果他们打算完全理解一个文本。他们必须通过对这同一个前批评观点来理解它。”[2]260 那“前批评观点”就是作品的意义,批评家在批评观上的分歧则是在作品意味上的分歧。根据作品的“意义”与“意味”的区分,赫施还做出了相应的“内层次”与“外层次”、“阐释领域”与“批评领域”的区分。大致说,作品的内层次产生意义,外层次则与意味相关;内层次是阐释的领域,外层次是批评的领域。[1]426 赫施的上述区分是对文学研究的深化,是可以为现代阐释学接受的。不同的只是,现代阐释学并不认定作品意义就是作者意图,是确定的、客观存在的。这一点正是包括赫施在内的传统阐释学需要变革之处,也正是现代阐释学的生长点。
赫施还提出了确定作品意义的原则、标准和方法。确定意义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字面意义的“强调结构”原则,即通过对字面意义的相对强调来判定多种可能的阐释中哪一种是正确的。赫施说“可以把这一点称为一条普遍原则”[1]432。确定意义的一个重要标准是连贯性标准,即“面对不同的理解,阐释者就应该选择最符合连贯性的理解”[1]439。赫施说:“甚至当作品没有争议时,连贯性也还是决定性的标准,因为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只有它才合乎逻辑。”[1]439 确定作品意义的重要方法是核实的方法,即用外来材料,尤其是关于“作者典型的世界观、典型的联想和期望”以及他的文化背景等材料,去核实所理解的意义。赫施说:“所以在核实的过程中的一个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对作者的主观态度作细致的考察。”[1]441 并指出:“在阅读时,我们并不把这些外来材料揉进作品中。相反,我们把它们用来核实我们从中理解到的东西,外来材料主要起这样的核实作用。”[1]443 赫施的这些观点,对怎样具体地理解和阐释文学作品是有一定意义的,对现代阐释学来说也有可取之处。
收稿日期:2007—09—13
注释:
① 日内瓦现象学派的主要代表乔治·布莱在他的《批评意识》一书中的“我思”观点。“我思”就是作者创作时的意识模式,它在作品中起统摄其他意识的作用。参见《批评意识》第275—287页(百花洲出版社199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