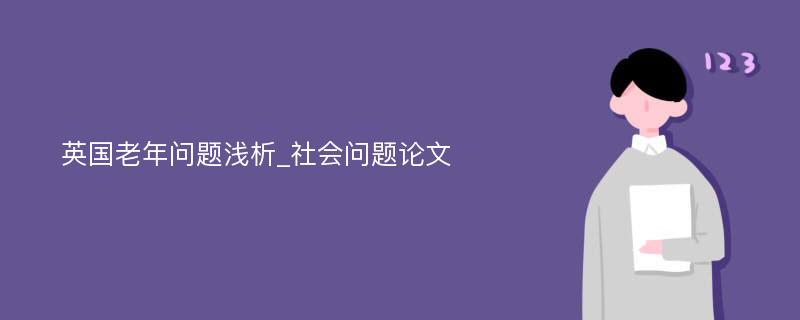
简析英国的老年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老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学者都在热烈地探讨老年人口比例增加的含义,这一比例的增加将不可避免地在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上产生重大的影响。全世界的人口,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人口,正在迅速老化,这一老化的趋势在那些新近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里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例如在日本,1970年超过65岁的老年人口只占7%,而在1996年则可能达到14%;而在法国,同样的人口老化过程经过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而英国也用了45年,即从1930年到1975年[①a]。相比之下,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更加迅速,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也更大,而我们关于这种趋势的学术研究和对策研究,都远未跟上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因此,从具有典型意义的发达国家英国入手,剖析它对老年问题的认识过程及其对策,应该能为我们在处理自身的老年问题时提供某些有益的参考。
一 工业革命前期的老年问题
大多数学者认为,把60岁以上的人称为老年人,应该是可以接受的标准。因为在60岁以后,一个人已不适应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作了。虽然任何社会都有老年人,但老年问题基本上是一个现代社会问题,因为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从人类的生存发展的本能来看,社会一般只能首先满足青壮年人口的生存需要。也就是说,尽管任何社会都有老年人,但他们的生老病死都还不足以构成社会问题。从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来看,在1540—1800年间,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始终在35岁左右[②a]。在此之前的人均寿命当然也不可能超过这一标准。但是,人均寿命并不能完全反映出一般人的正常寿命。因为在现代医疗体系建立之前,婴儿的死亡率极高,从而降低了人均寿命,而一个婴儿只要他度过了1岁,就有希望活到50—60岁。因此,在“现代”之前的英国,老年人口仍然具有相当的比例。据英国学者比较权威的资料统计,超过60岁的老人在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在英国人口的比例中一直保持在9%左右[③a]。换言之,这种比例与20世纪初的比例几乎一样,但老年问题并未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老人中的富人日子相对好过,只要他们在完全丧失料理生活的能力之前仍能控制生产资料或是政治权力,他们就可以利用这种权利来雇佣仆人或其他人来料理自己的生活。至于占老人中比例最大的穷人,他们的日子就过得十分艰难了。在通常情况下,贫穷老人都一直工作,出卖他们唯一的资本——自己的体力,直到完全衰竭时为止。尽管他们的劳动只能提供他们生活的一小部分来源,他们也必须工作;其余的部分则靠子女、亲戚、邻居以及慈善救济和济贫法的资助。从14世纪起英国地方政府就开始征收的济贫税,给老年的穷人以很大的支持[①b]。尽管社会要求年轻人尊敬老人,但同样也必须理解的是,在英国,家庭的成员,尤其是子女,应该给老人提供生活必需品的观点并不是一种社会规范,更何况直到18世纪末,无子女的夫妇占到了10—20%的比例。即便有子女,英国的老人们大多也不和子女住在一起,据估计,在现代初期的英国,有20—30%的老人在去世时没有子女在身旁[②b]。由于英国在近代初期的人口流动性就很大,子女和父母往往不住在一起。即使住在一起,由于面临十分具体的经济问题,他们之间的关系往往也并不和谐。事实上,由于彼此都是穷人,就算他们的关系尚可,作为穷人的子女或邻居也没有多少能力去支援贫穷的老人。由于贫穷老人基本上都是体力劳动者,他们只要能干就继续干,当他们再也干不动时,他们的子女往往也过了体力的巅峰期,要指望子女的照顾也不太现实了。
此外,不同的文化背景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正如林语堂所说,西方的老人被迫感到他们在各方面都已度过了自己最有用的时期,现在正无偿地由孩子们赡养,似乎他们在壮年时并没有尽到抚养儿女的职责[③b]。这种文化使得老人始终不愿自己成为子女眼中的包袱,而尽可能地在临死之前保持独立的生活。虽然济贫法在1601年就规定子女应该对其年老的父母尽责,但却加了一个限定,“假如他们有足够的能力”这样做,而英国的地方当局也从未认真检查子女是否真的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因为这些官员也这样认为,“指望子女来赡养父母不是一种英国人的习惯”[④b]。这并不是说英国的文化中没有尊敬老人的成分,只是没有把赡养老人的责任完全推给子女而已。当子女和亲友帮助加上老人的自助都无法完全满足老人的生活所需时,地方政府则从本地的税收中提取一部分用于资助老人的生活。济贫法能在英国推行,一个原因是英国比当时的北欧国家富裕,政府有能力这样做;另一个原因是对老人的救助是社会保障的一部分,因为就算是一个中等的地主,也有可能破产或无子女而在年老时处于困境,英国政府希望对老年人的救助能减少社会的动荡[⑤b]。
但这种对老人的济贫与20世纪的福利国家并不是同一回事。因为接受济贫的老人必须尽一切努力工作来维持自己的生活,甚至包括向周围的邻居乞讨,济贫只是补足靠这些方式都还不能满足他们生活必需的那一部分开支;其次,老人并没有严格的界定,不是说60或70岁就是老年人了,只要你能动,哪怕上了80岁的高龄,也必须想办法自己寻找一部分生活来源;第三,济贫的原则也并不是由于年老,而是救助那些不能自助的人。所以,没有任何老人在接受救助时是理所当然的,接受的救济数量也不是固定的。尽管如此,老年问题在这一期间并未成为一种真正的社会“问题”,无论政府还是个人,都认为社会可以以某种临时的措施去解决它。
二 关于养老金的社会立法
但是,这种状况随着英国工业化的进程而发生了变化。在1750年前后,英国仍然是一个乡村的英国,2/3的人口居住在农村。由于工业的发展,人口不断从农村涌入城市,致使一些工业城市的人口迅速膨胀,利物浦在1811年有11.5万人,到1851年已达45.3万人;1851年,在英国较大的71个城市中,已经容纳了300万移民,占英国当时全国总人口的一半[①c]。人口大量移入城市的结果,使老年人口的生活状况发生了变化。首先,老年人的自助性劳动几乎无法找到,在年轻人尚不能确保工作的情况下,老年人要找到工作,而且是部分工作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在农村,老人总能干些杂活;其次,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邻居、亲友和子女的照顾也就自然失去;第三,由于医疗技术的改进,一些致命的传染病已经得到控制,也就意味着人均寿命的延长,而人均寿命的延长也就意味着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上述诸种因素终于使得英国人在19世纪末把老年人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并以此作为征税的理由。到了20世纪,大多数老年人才开始享受到固定的养老金[②c]。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由于新济贫法的实施,严格限制了老人在家里接受救济的可能性,而老年人口的群落又在不断增加,因此,英国社会要求政府在某种固定的年龄给老人发放养老金而不是在劳动者丧失劳动能力之时才给他们提供救济的呼声越来越高,至于究竟在什么年龄段上发放养老金,则应根据各个劳动行业的不同情况来确定,但人们普遍认为最低的年龄不应低于55岁。1878年布莱克利(C.W.Blackley)曾提出了一个方案,要求在劳动者年轻时强制性地征收一笔基金,以便在他们生病和年老时提供帮助。但这一建议遭到友好会社的强烈反对而未能产生结果,因为他们担心这会损害他们自己建立起来的互助体系[③c]。然而,在查尔斯·布什(Charls Booth)等人的调查报告公布之后,社会舆论开始强烈要求政府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金问题。1895年,英国皇家委员会关于老年穷人的报告中也指出,老年穷人的数量在迅速扩大,光靠户外的临时性救济已不能解决问题[④c]。劳合·乔治(Lloyd George)也把解决养老金问题视作解除劳工运动威胁的最有效的方式。他在议会的辩论中说,英国应建立一种不纳捐的养老金制度,因为这些老人在他们年轻力壮的时候已经为社会作出了贡献,他们已经交纳了各种各样的税款,他们在纳税后已经所剩无几,他们已不可能再创造出纳养老捐的财富了。在1886年,一个英国工人的每周平均工资是在25先令左右,而十分清楚的是,低于这种工资收入他们就无法维持生活[⑤c]。1908年8月,劳合·乔治提出的养老金预算案得以通过,这是英国关于老年问题立法的一个重要标志。该法令规定,对那些年收入在£21—£31.10并年过70岁的老人,没有犯罪记录,没有亲友的接济,甚至也从未因酗酒而闹事,可以毫无愧色地宣称他没有因为自己的过失而使自己的生活陷入困境者,每周可以领取1—5先令的养老金[⑥c]。尽管有着种种不足,该养老金法还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从1909年1月1日起,共有49万名老人被认为具备领取养老金的资格,其中大部分人是妇女。养老金法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虽然人们认为它确定的年龄太迟数量也太少,但它毕竟给了老人们一种固定的收入,并且接受这种收入是自己的一种权利,不会再受到社会的歧视。这是英国社会对老年人口群体正式照顾的开端(尽管它只涵盖了社会上一部分最贫穷的老人),也表明英国政府已经承担起了社会对老人的应尽的责任。因此,这是一个重要的开端,它强调的是一种新的原则,那就是即使个人努力工作,在年老时也不能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来照顾自己,而社会对老年人的照顾就是完全应该的;其次,它以官方的正式方式确定了老年的概念,即70岁以上为老年。虽然年龄似乎过高,但一个人在某种固定的年龄就应享受一个现代人基本权利的概念,正如英国学者所说,这是福利国家的一种成果[①d]。至1911年英国开始建立社会保险体系时,英国的大多数体力劳动者已经被包含在了社会保险网之内。也就是说,英国的老人现在普遍有了某种固定的收入。然而,社会保险金与养老金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保险金的领取是领取者过去交纳保险捐的结果,而养老金却不是。换言之,英国的老人由此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靠自己的劳动积累可以安度晚年的,另一类则不是。
英国政府在老年立法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虽然很大,但并不能满足英国社会各阶级和两性老人的共同要求,这主要是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定得太高。所以,就在养老金法通过后不久,英国公众又开始要求降低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至65岁。而在1925年,英国政府也比1908年更关心让劳工在更早的年龄退休,这主要是面临着广泛的失业,英国政府想让更多的年轻人取代老年工人的位置,以便减少失业的压力。经过持续的努力,终于在1928年使所有参加国民保险的老人可以在65岁领取退休金,而未纳入保险行业的老人则仍在70岁领取养老金,两类人领取的数额仍是相同的。由于该立法的通过,共有1044.5万名男人和464.5万名妇女受雇于纳入保险体系的行业,而在1928年有36万男人和17.7万妇女首次领取到了退休年金[②d]。
在30年代,除在1931年英国政府废除了令人痛恨的贫困调查法外,在老人问题上比较引人注目的是由全国老处女协会发起了一场争取降低妇女领取退休金年限的运动,她们要求把妇女的退休年限定在55—60岁之间。其理由是,这样作对已婚夫妇也有利,因为妻子的平均年龄比丈夫小5岁,这样他们就可以同时退休;而她们自己之所以没有丈夫,也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过多的男人丧生,才使她们无法找到丈夫,政府因之应对她们的贫穷生活负责。英国政府在调查之后认为,大多数妇女都比男人更早地失去了工作,因而可以考虑降低妇女领取养老金的年限。最终在1940年使所有妇女领取养老金的年限降到了60岁[③d]。
英国的养老金与福利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根据贝弗里奇报告普遍性的原则,英国工党政府在1946年通过了被称为福利国家支柱的社会保障法,该保障法除了对生病、失业、伤残等社会成员付给保险金外,对老人最重要的是将养老金界定为退休金,这一名称的改动意味着一种观念的变化,即老人所领取的是自己应得收入的一部分;而且退休金的标准大幅度地提高,由在此之前的每周10先令上升到每周26先令。如此慷慨的行为,甚至使一些社会学家也担心国家的经济是否能够承担此种重负,他们认为:“较高的年金取得了大选的胜利,但政治姿态并不能平衡社会保障的预算案。”[①e]
此外,在30年代,尽管英国的人口出生率有所反弹,社会对英国将成为一个老年社会还是感到了惊恐,这有助于使人们将老年人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来对待。不过,英国政府还是十分不情愿承担起照顾老人的责任,认为照顾老年人应主要由家庭负责,不管他们是否有能力这样做,直到1946年社会保障法的通过,才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②e]。尽管社会保障法还存在着多少缺陷,但它都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英国穷人的处境。据朗特里(S.Rowntree)的调查,以约克郡为例,贫困已基本被消灭,仅有1.66%的人的生活标准低于人类的基本需求线[③e]。英国的其余地区,情况也大致如此。所以,仅从生活的物质来 源考虑,英国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基本得到了保证。
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老人”开始成为一个界限分明的社会群体,而老人穷人则开始成为社会关注的对象。社会舆论对老人问题的关心,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压力,对英国政府的有关社会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促使英国政府转变态度的根本原因,则是英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结果。这种变化使得“老年问题”成了真正的社会问题,也就迫使英国政府将对老年人的慈善救助转变为老年人理应享受的权利。而英国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也为解决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所有社会问题奠定了一个广泛的基础。
三 老年人的福利问题及其面临的困境
福利国家的建立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一个短期因素促进的结果。其中一个重要的短期因素,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政府很难将战时所提供的那些社会服务再收回去。然而,福利国家是立足于雄厚的经济实力之上的,而战争却极大地削弱了英国的这种实力。因此,除非英国在战后能迅速恢复经济,否则是无法承担社会福利的重负的。十分幸运的是,1951—1973年间,似乎是20世纪英国的又一个黄金时期,只有在1971—1972年间的失业率超过了3%,其余年代都低于此数,而零售物价指数的同期上涨率为4.6%,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0多年中一直保持2.2%的增长率[④e],虽然不及德国和法国,但也足够英国增加公共开支的费用了。
由于有这样一个客观的有利条件,战后英国的历届政府都未改变艾德礼工党政府确定下来的福利国家原则,并不断完善着这一制度。结果,今天的英国已经形成了以国民卫生医疗服务、个人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为支柱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这三项开支都需要国家给予大量的财政补助,其中,社会保障的开支最大,约占总开支的1/4,70年代每年约为70000万镑,80年代则增至每年80000万镑。政府的各项社会开支,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0%以上[⑤e]。
英国的老人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社会集团。工人阶级中的老人在晚年的境遇很坏,他们通常缺乏取暖设施,生活在孤独之中,并由于自己从劳工市场被排除而认为自己已毫无价值。这些因素都十分严重地影响了这部分老人的健康和福利。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他们的处境。在医疗和福利方面的开支的35%用到了这些老人身上,一般医院病床的57%也是被这些老人所占据[①f]。这样一些措施当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英国学者自己也承认,不仅现在,就是将来,缺乏食品和住房的个人和家庭都会存在,但其性质已经起了变化。部分原因是这些人未能申请国民困难补助,不是为了面子就是不大熟悉申请的手续;部分是因为非正常开支所致,即酗酒或赌博或类似的开支不当所造成的困难。而老人由于自己体能的减弱则要求更多的社会服务而不是仅仅增加补助金。为此英国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主要包括建立养老院,给需要保护的老人介绍一般家庭寄宿,由家庭助手对老人实行定期服务,由邻居进行友爱访问等。除此之外,政府还组织志愿人员每周数次将热饭送到行动不便的老人家中,为他们洗澡,为他们改善居住环境等;地方当局甚至为他们建立娱乐中心,给老人提供聚会场所,早上用车将老人们送到这里,提供饮食,晚上再送回去。此外,地方当局和民间团体还以老人为对象组织各种形式的俱乐部及旅行会,电影院、美容院、公共交通等机构也大都为老人设立了专门的特惠收费标准。这些活动的开展,对改善老人的生活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使英国政府不得不大量地增加社会服务的工作人员。
与此同时,老人的自身需求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已不再仅仅满足于吃饱和穿暖,而是要求参与一些社会的文化生活以及满足某些特定的精神需求。换言之,老人同样也要求提高生活质量。精神生活的满足当然不能仅仅靠精神,而是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活动经费。结果,英国政府的国民补助金不断增加,从1948年到1973年,英国政府的此项支出增加了将近1倍[②f]。这种补助的一个结果,就是那些完全靠享受补助生活的家庭,其经济状况几乎和1948年那些有稳定工作的家庭的平均收入相等。而且随着领取养老金的老人日益增多,老人的生活保障也成为国民保险中一个再分配的重要因素,普通税中的2/3被用来支付养老金。由于英国实行的是累进所得税,所以由高收入者支付的养老金部分越来越多。英国政府对此的反应是,立即切断国民保障体系中保障税与补助金的任何联系。政府对保障基金的投入是固定的,其余部分则按物价上涨的幅度而相应增加。对低收入者征收保障金而引起的政治问题由1961年通过的累进保障税计划而得到了解决。在1962年,累进保障税的征收满足了当年所需养老金的19%,而1968年更达到29%[③f]。
提高老人的福利待遇是一个现代社会必须解决的任务之一。当一个人在经过一生的艰苦奋斗之后,能够安度晚年,应该是一种合理的要求。然而,满足这一要求并不容易,它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但最突出的表现仍然还是落实在经费上。于是,英国的社会保障开支越来越大,而这种支出又是与经济状况相联系的,这就使得历届英国政府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根据英国的官方统计资料,由于老人在英国的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上升,目前英国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为1020万人,约占成年人口的1/4,其领取的养老金占社会保险预算的2/3。如此庞大的福利开支,削弱了英国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社会福利开支构成了政府消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70年代中期以来,英国政府消费的增长幅度超过了固定资产形成额的增长幅度,也就是社会福利的开支已经影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围绕着如何处理福利政策与经济政策的矛盾,英国工党与保守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终是以撒切尔夫人的意见占了上风,那就是大幅度地削减福利开支或是将福利开支的负担转移,其中,关于老人福利的一个最重要的提议,是逐步取消国家负担退休金的制度,建立私人企业负责制,工人退休后,领取退休金的数额要同工作时为退休金交纳的金额挂钩,但不得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其次,则是建议医院逐步实行私有化,公民的医疗费用开始由国家补助一部分,逐步过渡到公民以交纳社会保险费的形式自行负担。同时,政府还准备削减老人的福利金[①g]。
然而,撒切尔夫人的政策在经历了英国历史上较为罕见的政治较量后,尽管被人称为撒切尔革命,但在削减公共开支方面的努力却失败了。撒切尔夫人在1979年上台时,中央政府的预算中的防卫、社会保障与国民卫生保健就占了2/3,由于承诺北约每年增加3%的防卫开支,再加上马岛之战,实际的防卫开支上升了5%,而社会保障的开支随着失业人数的增加也有增无减,至于国民卫生保健的开支,由于它已成为在竞选中争取选民的重要筹码,也根本不可能降下来[②g]。
撒切尔夫人在鼓吹市场机制的同时,极大地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然而,经历了十年左右的“革命”,不论人们对她的政绩作何评价,她在削减福利开支方面的努力至少是失败的。目前尚不清楚她的继任者会有什么样的动作,但可以肯定的是,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的行动不可能获得成功。
四 解决老年问题的另一种思路
事实上,多年来在老年问题上英国的两党政府都陷入了一种怪圈,即从当选的角度考虑,必须尽量许诺给选民增加更多的福利和其他的好处,从来没有哪一个宣称要减少社会福利的政党能够当选,而且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老年选民的选票显得越来越重要。因而,试图当选的政党都必须尽量地拉拢这批选民。然而一旦当选,如何平衡财政预算,发展经济,降低通货膨胀率,又不能不成为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而完成这一任务,往往又和选举时的承诺相互冲突。因此,如果从政党政治的角度考察,英国无论哪一个政党上台,都不可能同时解决好这两个问题。所以,这种怪圈也成了所谓“英国病”的根源之一。从英国目前的人口发展趋势来看,老年人口的比例在进一步增加,1951年时英国65岁以上的老人占人口比例的10.9%,而预计至2025年,这一比例将会增至20%左右[③g]。这是一种无法扭转的趋势。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老年人口对生活福利和生活质量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而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也使老人的寿命进一步延长,这就意味着80岁以上的老老人的数量会大大增加。这一切表明,英国社会在老年问题方面的开支只会越来越大。仅从削减开支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解决问题的道路似乎越来越窄,因而老年人口和老年福利几乎成为一切发达国家的无法摆脱的包袱。
对这种人口老龄化所造成的严峻趋势,一些英国学者仍然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虽然老年人口在增加,但由于每个家庭抚养的孩子减少,社会的未成年人口也在减少,换言之,社会总体的需要供养的“依附”人口没有太大的变化。因此,对未来不必过分悲观[④g]。另一些学者在做了更加细致的分析后却认为,即使总的“依附”人口没有增加,但社会为此付出的成本却在增加。因为年龄越大,需要的社会服务和医疗费用就越多,赡养一个老人和抚养一个小孩的花费是决不可能相提并论的[⑤g]。而老人预期寿命的延长,也成倍地增加了社会的开支。例如,当老人的平均寿命由75岁左右增至85岁时,社会负担的老人无异于增加了1倍;而且,年龄越大的老人需要的社会服务越多。所以,随着高龄老人的增多,社会支付的费用将会成倍地增加。
如何筹集这批费用?问题的本质实际上是如何重新分配社会责任。养老究竟应由谁来承担责任,学者和政府官员的意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分摊到个人头上,增加每个人工作时所交的养老捐,因为原定的养老捐是按每人退休后生活10—15年来计算的,而现在人均寿命延长,理应相应地增加费用,也应该是合理的。二是分摊到雇主头上,增加雇主为雇员所交的社会保险捐。此外,政府也应承担责任,但不能指望政府无限制地增加福利开支,而是由政府通过多种方式来筹集资金,如通过招标的方式指定专门机构来经营管理社会保障基金,使其增殖,以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就是一种可行的政策。也有的学者认为应将更多的责任推给私人的保险机构去承担,由个人为自己购买医疗保险等方式来安排自己的晚年生活,也就是说,将这笔开支大部分转嫁到私人头上。这些措施在解决养老问题上不能说没有作用,但其基本思路,都未能摆脱将老年人看作是社会包袱的窠臼。
但是,随着社会进入老龄化的阶段,将老人完全作为社会的包袱肯定是一种偏颇的看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退休的老人已成为经济生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资源——他们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服务和其他类似的劳动。这种状况之所以可能,首先在于老人的健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本世纪初,一般认为60岁已进入老年状态,其体力和脑力已不适合继续工作了。而在半个世纪后,社会的共识是,绝大多数60—70岁老人的身体状况仍是十分适合工作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产技术的改进,老人不用再以纯粹的体力消耗去从事工作。换言之,真正的老龄应从70岁开始。这批老人仍然是可以为社会工作的,如能充分利用他们的潜力,将极大地缓解老年人口对社会的压力。其实,英国学者的调查表明,在1984年,超过65岁的老人就有43%给年纪更大的老人提供定时的帮助,25%给病人和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提供服务,11%为其邻居提供各种服务;在年龄65—74岁的老人中,21%的人参加了各种正式的自愿服务工作,甚至在75岁以上的老人中,也有11%的人说他们经常给别人提供帮助[①h]。
这些统计表明,老人的资源是有挖掘的潜力的。最新的调查表明,在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必须以新的态度重新看待老人。其一,老人虽然退休,但若每天无所事事,他们也会觉得空虚,生活没有乐趣,所以,应该有一个地方让他们发挥余热。其二,老龄化社会产生的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也有必要重新考虑老人作为社会劳动资源的价值。大多数老人也仍然希望发挥自己的作用,让社会觉得他们是有用的人,而不是仅仅由他人照顾的对象。因此,让老人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不仅可以减少社会的负担,也可以使老人的生活更为充实。对老人来说,努力寻找并坚持做对他人有益的事,包括照顾自己的孙子孙女,向年轻的一代传授自己的技术或知识等,也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态度。
由此看来,对老年问题的对策实际上牵涉到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社会应尽可能照顾好老人的生活福利,不将老人视作社会的包袱;二是老人自己应具有积极的生活态度,并认识到社会需要自己发挥一定的作用。在这样一种即将来临的老龄化社会中,家庭的整合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据英国学者的调查,很多老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关注自己的老年生活。收入较高的老人可以依靠自己的积蓄,而贫穷的老人则尽可能寻找有报酬的工作,但毕竟老人需要他人的关心和照顾,而这种关怀不是仅仅靠物质的帮助就可以替代的。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人欲横流,要“垮掉的一代”主动去关心老人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十分困难的。而贫穷老人的子女,往往家境并不优裕,而且由于就业等因素,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可能与老人住在一起。也就是说,他们即便有心,也不可能给自己的老人提供应有的帮助。因此,这部分老人的生活显然更为凄凉。如果从这个角度考虑,无论怎样“开发”老年资源,社会对老年问题毕竟承担着主要的责任。因为社会“利用”老年资源的最终目的不是推卸责任,而是为了更好地解决老年问题。
老年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现代社会的问题。在前工业社会中,老人并不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而存在,他们的生老病死毕竟主要是一个家庭内部的事。然而,随着工业化的进层,社会化的生产已经取代了一家一户的生产,而社会化的生产必然要求社会化的保障,将老年人的养老责任由家庭转移到社会,这是任何一个现代社会所无法回避的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医疗条件的改善,老年人口的寿命将进一步延长,而老年作为人生的一个年龄阶段,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因而,如何界定社会对老年人口所承担的责任,不仅涉及到每个人的利益,也涉及到一个社会是否安定的大事。从英国的经验看,政府在养老问题上经历了一个反复,在初始阶段政府是不愿过多涉及养老问题的,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政府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因而,目前的趋势是政府想尽可能地减少这方面的责任;但这种变化并不可能单纯地退回老路,而只能是尽可能地让各种社会机构和组织来管理养老的问题,政府则在其中起一种协调作用。当然,在这种新体系的摸索过程中,个人肯定也要承担比以往更多的责任。至于各种社会性的福利组织是否能够承担起这种责任,则是需要一段时间来加以验证的。而我国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是否能避免这种反复,“一步到位”,借鉴英国的历史经验应该是有所帮助的。
注释:
①a 帕特·塞恩:《老年人口是一个不断增长的负担?》(Pat Thane,"The Growing Burden of an Ageing Population?"),转引自《公共政策期刊》1989年7月4日,第373页。
②a 皮特·拉斯勒特:《关于生命的新的图示》(Peter Laslett,A Fresh Map of Life.The Emergence of the Third Age),伦敦1989年版,第18页。
③a 里格利与斯科菲尔德:《英国人口史1541—1871》(E.A.Wrigley and R.Schofield,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 1541-1871),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28—529页。
①b 保罗·斯兰克:《英国济贫法》(Paul Slack,The English Poor Law 1531-1782),伦敦1990年版,第10页。
②b 康拉德:《关于老年的文化史》(Christoph Conrad,Toward a Cultural History of Aging),柏林1993年版,第21页。
③b 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191页。
④b 佩林与史密斯:《生命,死亡与年龄》(M.Pelling and R.M.Smith,eds.,Life,Death and the Elderly),伦敦1991年版,第199页。
⑤b 米奇森:《苏格兰旧济贫法的形成》(Rosalind Mitchison,The Making of the Old Scottish Poor Law),转引自《过去与现在》1974年第63期,第58—94页。
①c 马赛厄斯:《第一个工业化民族》(Pater Mathias,The First Industrial Nation),伦敦1983年版,第178页。
②c 康拉德:《关于老年的文化史》,第26页。
③c 弗雷泽:《英国福利国家的演进》(Derek Fraser,The Evolution of the British Welfare State),伦敦1975年版,第140页。
④c From"The 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the Aged Poor",1895,C.1684.
⑤c 转引自:《汉沙德议会辩论录》(Hansard,Parliamentary Debates,House of Commons),第四卷,第140册,第565栏。
⑥c 帕特·塞恩:《福利国家的基础》(Pat Thane,The Foundation of the Welfare State),伦敦1982年版,第82—83页。
①d 康拉德:《现代退休制度的出现》(Christoph Conrad,The Emergence of Modern Retirement),伦敦1991年版,第15页。
②d 威尔森与麦凯:《用历史的学术眼光来看待养老金》,(A.Wilson and G.S.Mackay,Old Age Pensions:An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tudy),牛津大学出版社1941年版,第134页。
③d 帕特·塞恩:《英国的性别、福利与老年问题》(Pat Thane,Gender,Welfare and Old Age in Britain),伦敦1995年版,第201页。
①e 马什:《英国的国民保险与国民补助》(D.C.Marsh,National Insurance and Assistance in Great Britain),伦敦1950年版,第110—111页。
②e 帕特·塞恩:《英国的性别、福利与老年问题》,第204页。
③e 布朗:《英国福利国家》(John Brown,The British Welfare State),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④e 皮登:《英国经济与社会政策》(G.C.Peden,British Economic andSocial Policy),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页。
⑤e 英国情报出版中心办公室:《英国的社会福利》(The Social Welfare in Britain),伦敦1980年版,第29页。
①f 汤姆·伯登、迈克·坎贝尔:《英国的资本主义与公共政策》(Tom Burden and Nike Campbel,Capitalism and Public Policy in the UK),伦敦1985年版,第169—170页。
②f③f 皮登:《英国经济与社会政策》,第187、190—191页。
①g 英国《卫报》1984年6月23日。
②g L.普莱茨基:《收入与支出:公共支出,就业与通货膨胀》(L.Pliatzky,Getting and Spending:Public Expenditure,Employment and Inflation),伦敦1984年版,第171—188页。
③g④g 简·福基汉姆:《英国的老年人口》(Jane Falkingham,Britain's Aging Population),伦敦1987年版,第17、5—7页。
⑤g 帕特·塞恩:《老年人口是一个不断增长的负担?》,第378页。
①h 简·福基汉姆:《英国的老年人口》,第383页。
标签:社会问题论文; 养老金论文; 增加养老金论文; 英国工作论文; 社会保险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老年人口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