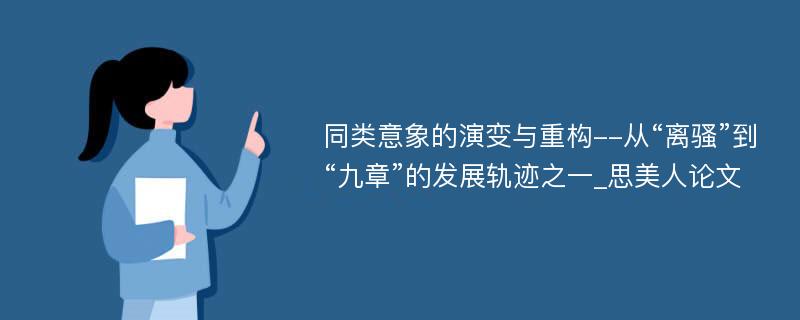
同类意象的演变和重构——《离骚》到《九章》的发展轨迹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离骚论文,意象论文,轨迹论文,重构论文,同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0)05-0249-05
意象是作品的基本元素,《离骚》和《九章》各自都由庞大的意象群落组成。《离骚》和《九章》有许多同类意象,它们在两部作品中都存在。《九章》除《橘颂》和《惜诵》外,其余篇目的创作年代均晚于《离骚》。对于这些篇目,可以把它们和《离骚》中的同类意象加以对比,从而梳理出从《离骚》到《九章》某些意象的演变趋势。
一、香花芳草意象的扩展
香花芳草是《离骚》意象群落的望族,出现的频率极高。《离骚》的抒情主人公以多种方式与香花芳草发生关联,用它们来象征本身高远的理想、峻洁的人格。如:“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茝。”三后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屈原在这里用香花芳草指代夏、商、周明君所招纳任用的贤臣。
《离骚》中不乏以香花芳草指代贤才的诗句,至于抒情主人公本身,他虽然以多种方式与香花芳草发生关联,但没有把自己直接写成是香花芳草,没有把香花芳草说成就是抒情主人公的化身。到了《九章》,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香花芳草和抒情主人公的关联较之《离骚》更加切近。《思美人》有如下一段:
芳与泽其杂糅兮,羌芳华自中出。纷郁郁其远承兮,满内而外扬。情与质信可保兮,羌居蔽而闻章。
对于这句诗,王逸逐句作了解释:
正直温仁,德茂盛也。生含天资,不外受也。法度文辞,行四海也。修善于身,名誉起也。言行相副,无表里也。虽在山泽,名宣布也[1]148-149。
王逸的解释并不是每句都很确切,但他对诗句所作的认定很明确,把它看做是屈原的自况,是在进行自我表现。后来古今注家在对这几句诗进行解释时,都把它看做是诗人的自我刻画。这几句诗是按照香花的属性功能赞美自己,句句是在描写香花,句句又都是在刻画诗人本身。人与花,花与人,在这里已经浑然不分,融为一体。《思美人》作于屈原贬谪汉北途中,因此,诗中有“羌居蔽而闻章”之语,是诗人自身遭遇的现实写照。
抒情主人公直接把自己说成是芳草,这类诗句在《惜往日》中也可以见到。诗中写道:
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没身而绝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君无度而弗察兮,使芳草为薮幽。
《惜往日》是屈原的两首绝命辞之一。这几句诗前面明示自己要自忍沉流,后面又称“使芳草为薮幽”。薮,本指湖泽,这里指水域。屈原把自己所要自沉的水域称为“玄渊”,指的是水很深。后面所说的“薮幽”,也是指很深的水。这几句诗首尾照应,薮与渊相应,都是指水域。幽与玄相应,指水的深度很大。前面是屈原表示要自投玄渊,后面说芳草沉到水的深处,明显是屈原把芳草当做自己的化身来加以显现。《惜往日》还写道:
芳与泽其杂糅兮,孰申旦而别之?何芳草之早殀兮,微霜降而下戒。
这几句诗的大意是:芬芳润泽的香草,谁能从下午到日出就能加以辨别?为什么芳草短命夭折,那是降霜对它的摧残。申,古人以地支记时,指15时至17时。旦,指日出、清晨时节。申旦,指很短的时间。这里是以芳草无人识,最终在严霜降临时夭折,指代屈原本人不被楚王理解,最终饮恨自杀。芳草是诗人的化身,是诗人的自况。
《思美人》、《惜往日》在用香花芳草直接指代屈原本人时,两次出现“芳与泽其杂糅兮”之语,用它来描绘香花芳草的芬芳润泽。这句诗在《离骚》中已经出现过:
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
从上下文的语境判断,“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指的应该是抒情主人公的佩饰。这两句诗前面一句是“长余佩之陆离”,后面的两句诗道出佩饰的美好属性。最后两句“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更明确“芳与泽其杂糅”指的是抒情主人公的佩饰。
对于抒情主人公的佩饰,《离骚》在“芳与泽其杂糅”段落之前反复提及。“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佩饰是用兰草纽结而成。抒情主人公在香木根上缠结白芷,把薜荔的花心串连起来,用菌桂联缀蕙草,编成长长的绳条。上述物品均是以香花芳草为原料,把它作为自己的佩饰。
《离骚》的抒情主人公是以香花芳草为佩饰,在对它进行描写时用的是“芳与泽其杂糅”这句诗。《离骚》是用佩饰的芳香与润泽,象征抒情主人公峻洁的人格和超凡脱俗的品质;到了《九章》的《思美人》和《惜往日》中,“芳与泽其杂糅”之语不再是用来描写抒情主人公的佩饰,而是直接用于描写诗人本身,不是通过香花芳草编结而成的佩饰来象征抒情主人公的人格,而是直接把作者本人描写成香花芳草。和《离骚》相比,《九章》上述写法使得诗人与香花芳草的关系更为切近,以至于达到合二为一,彼此不分的程度。
《思美人》在“芳与泽其杂糅”之前是这样一段文字:
揽大薄之芳茝兮,搴长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谁与玩此芳草。解萹薄与杂菜兮,备以为交佩。佩缤纷以缭转兮,遂萎绝而离异。吾且儃佪以娱忧兮,观南人之变态。窃快在其中心兮,扬厥凭憑而不俟。
诗人撷取林中的芳茝、水中高地上的宿莽。他感慨不与古人同时,无人与他赏玩芳草。他去掉萹薄与杂菜一类普通杂草,用香花芳草编结佩饰。各种佩饰缠绕在周身,但它却枯萎而离开自己。萎绝,曾出现在《离骚》:“虽萎绝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萎绝,指自然枯萎、凋零。《思美人》所说的萎绝,指用香花芳草编结的佩饰逐渐干枯而脱落。有感于此,他要排遣心中的抑郁,纵情宣泄愤懑之情。至此,有关佩饰的叙述已经结束,下面出现的“芳与泽其杂糅”一段转入对诗人自身的直接描写。在《思美人》中,“芳与泽其杂糅”之语与佩饰保持着前后相承的关系,有关佩饰的语境依然存在,只是不再与“芳与泽其杂糅”之语发生直接关联。
《惜往日》在“芳与泽其杂糅”一段文字之后是如下诗句:
谅聪不明而蔽壅兮,使谗谀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贤兮,谓蕙若其不可佩。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虽有西施之美容兮,谗妒入以自代。
这段文字中是以香草所制的佩饰指代贤人,前面的“芳与泽其杂糅”之语虽然与佩饰没有直接关联,但是,前后的语境相承续,“芳与泽其杂糅”与有关佩饰的话语呈现出若即若离的关系。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思美人》、《惜往日》把《离骚》中用于描写佩饰的“芳与泽其杂糅”之语,转用到对诗人自身的直接刻画,由状物转到描写人。在此过程中,有关佩饰的话语或置于“芳与泽其杂糅”的段落之前,或者缀于后面,从中可以看出《思美人》、《惜往日》香花芳草意象脱胎于《离骚》的痕迹。
在《离骚》中,屈原通过用香花芳草编织的佩饰象征抒情主人公峻洁的人格,作品主人公和香花芳草虽有联系,却是分立的。到了《九章》中,诗人直接以香花芳草的形态出现,香花芳草是诗人的化身,人与香花芳草合二为一,难分彼此。这是《离骚》香花芳草意象的进一步扩展和延伸。在《思美人》中,诗人作为香花芳草出现,在表达方式上还不是十分显豁;而到了《惜往日》中,诗人作为香花芳草出现,已经表现得极其明显,并且反复出现两次。从《离骚》到《思美人》、再到《惜往日》,诗人与香花芳草的关联越来越切近。香花芳草作为诗人的化身出现,这个进程从屈原贬谪期创作的《思美人》发轫,到他的绝命辞《惜往日》最终完成,经历了一个演进的过程。
二、时间意象的演变
无论是《离骚》还是《九章》,那些作于《离骚》之后的篇目,时间意象出现的频率都较高,在作品中的分布比较密集。从《离骚》到《九章》,作品的时间意象发生明显的演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时间的感受有短暂与漫长的差异
在《离骚》中,抒情主人公常常感受到时光荏苒,光阴似箭。以至出现这样的想象:“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幻想太阳车的御手停顿下来,使时间停止流逝,延续时间的长度。
在《九章》那些后于《离骚》的作品中,偶尔也可以见到慨叹时光流逝过快、时光有限,如《悲回风》:“岁曶曶其若颓兮,时亦冉冉而将至。”这是说岁月流逝如同物体坠落,一年的季节就要到尽头。这类感慨在《九章》中极其罕见,大量出现的是嫌时间的流逝太慢,使人感到漫长。
《思美人》:“开春发岁兮,白日出之悠悠。”白日出之悠悠,意谓春天白昼漫长,好像太阳的运行很缓慢。《怀沙》写道:“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这是说阴历四月的初夏季节,白昼的时间特别长。中国处于北半球,春夏两季昼长夜短。《思美人》、《抽思》所反映的是客观事实,是物理时间的属性,同时也是诗人的心理感受。
《九章》中后于《离骚》的作品,还可以见到这样的时间意象,即物理时间和心理时间的悖反。《抽思》写道:“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孟夏夜短,这是物理时间。可是,诗人却感到孟夏之夜特别漫长,好像足有一年,心理时间与物理时间构成极大的反差。
《九章》中晚于《离骚》的作品,诗人总的感觉是时间漫长,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诗人都慨叹时间流逝太缓慢。这种感觉是由作者心态造成的。《悲回风》写道:“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以至曙。终长夜之漫漫兮,掩此哀而不去。”诗人之所以感到黑夜漫长,是因为他处于愁苦悲哀之中。愁苦知夜长,这是人的普遍感受。《九章》那些晚于《离骚》的作品,都写于屈原的贬谪和流放期,抑郁的心态使他度日若年,因此,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觉得非常漫长。
2.生命活动节拍有急与缓的不同
《离骚》的抒情主人公有感于时间短暂、人生有限,所以,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汲汲惶惶,唯恐不及,行动的节拍很快,有着强烈的时间紧迫感。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怀土恋乡情结使他在踏上流放之路时行动迟缓,不忍离去。《哀郢》写道:“楫齐扬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涉江》写道:“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这两首诗都作于流放期间,其中都出现“容与”一词,传达的是诗人本身迟回不前的心态。
其次,慢节奏的行动步调,是因为诗人处于徘徊彷徨之中。《思美人》写道:“吾且儃佪以娱忧兮,观南人之变态。”这首诗写于贬谪汉北途中。诗人徘徊不前,为的是排遣内心的忧愁。《悲回风》写道:“终长夜之漫漫兮,掩此哀而不去。寤从容以周流兮,聊逍遥以自恃。”诗人是以缓慢徘徊的方式自持,用以排闷遣怀。《抽思》写道:“低回夷犹,宿北姑兮。烦冤瞀容,实沛徂兮。”诗人徘徊不前,是因为烦躁郁闷,期待尽快离开贬谪地。《九章》中出现的儃佪、周流、低回、夷犹,都是彷徨迟疑之象,是苦闷心理的产物。
3.追昔思往意识有强弱之别
《离骚》以及《九章》那些晚于《离骚》的作品,其主人公都是立足当下而回顾历史,带有明显的以古代圣王为法的倾向。《离骚》多次提到以往历代明君,赞扬他们的美政嘉行,对他们心向往之。尽管如此,《离骚》还没有明显流露出未逢盛世、未能与古代圣人共处的遗憾。《九章》晚于《离骚》的作品,则表现出更加强烈的追昔思往意识。《思美人》写道:
揽大薄之芳茝兮,搴长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谁与玩此芳草。
诗人因不能与古代圣贤共同欣赏芳草而遗憾,为自己未能生活在古代盛世而惋惜,流露出明显的今不如古的感慨。《怀沙》写道:
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重华不可逢兮,孰知余之从容!古固有不并兮,岂知其何故!汤禹久远兮,邈而不可慕。
诗人以贤臣自命,但没有遇到虞舜那样的圣君,以至于没有人理解他。对于这种圣君贤臣无法遇合的现象,诗人感到困惑。更令他悲哀的是,由于相隔时代遥远,像商汤、夏禹那样的圣君,根本无法依恋。《思美人》、《怀沙》中,诗人因为无法和古代圣君相遇而惋惜,表达的是对现实的彻底绝望,是用历史来否定现实。这种对现实彻底否定和绝望所采用的方式,对后来的辞赋作品有深远影响。庄忌的《哀时命》称:“哀时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遭时。”董仲舒《士不遇赋》也写道:“生不丁三代之隆盛兮,而丁三季之末俗。”[2]生不逢时的感慨,寄托在对古人的追思中,继承的是《九章》的传统。
4.未来意识有迷惘与恐惧之分
《离骚》的抒情主人公远游求女、叩天庭、游神境,上下求索,对未来流露出迷惘困惑。《九章》晚于《离骚》作品所流露的未来意识已经不限于迷惘困惑,而是充满恐惧,这从《悲回风》的两句诗看得很清楚:“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来者之惕惕。”诗人怨恨自己以往的希冀,因为它期望值过高,同时又对未来充满恐惧和伤悼。
未来可以期待还是不可期待,是先秦文学的重要话题。《论语·微子》有如下记载: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3]
接舆是一位楚地狂士,他在劝说孔子改弦易辙时,一方面承认“往者不可谏”,即已经过去的无法挽回,另一方面又强调“来者犹可追”,未来还可以补救。到了《庄子·人间世》,这两句歌词被改造成“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4],以往无法挽回,来世不可期待,对过去未来都已经绝望,充满人生的幻灭感。《悲回风》所说的“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来者之惕惕”,和《庄子·人间世》所载的狂接舆歌相近,对未来充满恐惧,不抱希望,流露出屈原对现实的彻底绝望,对未来的心灰意冷,显示的是末世情调,是由人生末日引发出来的悲叹。庄忌《哀时命》云:“往者不可扳援兮,徕者不可与期。”[1]259这两句诗可以说是《悲回风》时间意识的历史回响。
三、媒介意象的重铸
《离骚》在叙述抒情主人公远游求女时出现多种媒介,它们作为沟通抒情主人公与所求之女的使者出现。《九章·思美人》也有媒介意象出现,《抽思》又提到媒介。把这两篇作品出现的媒介意象与《离骚》相比,可以看出二者之间明显的差异。
1.所出现的媒介角色不同
《离骚》作为求婚使者出现的有雷神兼云神丰隆,有鸩鸟、雄鸠,归纳起来有三类角色:一类是自然神,一类是飞鸟,一类是传说中的历史人物蹇脩。前两类媒介在《思美人》当中也都出现,诗人提到丰隆、归鸟。就此而论,《思美人》的媒介角色和《离骚》有相通之处。
《思美人》中还有一类媒介,它们是由植物承担:
令薜荔以为理兮,惮举趾而缘木。因芙蓉而为媒兮,惮褰裳而濡足。
薜荔、芙蓉属于芳草香花,由它们充当媒介,这在《离骚》中是见不到的,抒情主人公没有赋予它们这方面的使命,而是另有承担。《离骚》在叙述抒情主人公制作佩饰时提到“贯薜荔之落蕊”,把薜荔的花心串联起来,作为佩饰的一部分。薜荔是抒情主人公身上佩带之物的组成部分,而佩饰又和抒情主人公的求女有关。抒情主人公为求女作准备时,“折琼枝以继佩”,折下玉树枝对原来的佩饰加以增益,以便赠给所求之女。“解佩纕以结言”,是说解下佩饰交给对方以订亲。对于抒情主人公佩饰的最初制作,《离骚》有具体叙述,其构成因素就包括薜荔,而且是薜荔的精华部分,是它的花蕊。当抒情主人公把经过美化的佩饰作为求女礼品时,其中也有薜荔的成分。在《离骚》中,薜荔是抒情主人公求女礼物的构成要素,到了《思美人》中却被诗人视为传达信息的媒介。《思美人》的薜荔被定为媒介,是对媒介意象的重铸,是通过薜荔功能的延伸实现的。
《思美人》中作为媒介出现的还有芙蓉,即荷花。《离骚》也提到荷花:“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抒情主人公用菱叶荷叶为上衣,集结荷花作为下装,即裙子。《离骚》中的荷花作为抒情主人公的服装出现,和求女没有直接关联。到了《思美人》中被视为媒介,对荷花赋予它前所未有的功能,同样是媒介意象的重铸。
《离骚》中作为媒介出现的有神灵、有飞鸟、有历史传说人物,作者的想象很新奇,把神灵、飞鸟都加以拟人化处理,是从生命一体的层面加以沟通。《思美人》的媒介除了神灵和飞鸟,又增加了薜荔、荷花。把香花芳草作为可以传达信息的媒介看待,这种想象更加大胆和新奇,不但用生命一体的理念贯通人和神、人和动物,而且还贯通人和植物,赋予植物以人的属性。
2.人与媒介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状态
《离骚》的求女段落明确地展示出抒情主人公与求婚媒介之间的关系:在向宓妃求婚过程中,作为婚姻媒介出现的丰隆、蹇脩都听从抒情主人公的调遣,只是由于宓妃傲慢无礼,这次求女以失败告终。在决定求取有娀氏之女的时候,出现两位飞鸟使者——鸩鸟和鸠鸟。抒情主人公对鸩鸟传达的指令遭到拒绝,同时又嫌雄鸠过于轻佻而不肯任用。在这两次求女过程中,求婚使者多数听从抒情主人公的调遣,它们是抒情主人公驾驭的对象。尽管有的媒介并不称职,但毕竟在为抒情主人公服务。从抒情主人公方面来看,为求女相继派出一批又一批使者,他对求女是有热情的,尽量利用求婚媒介,发挥它们的作用。在打算求取有虞氏之二姚时,他感到遗憾的是“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即求女使者的能力不够,难以担此重任。
《思美人》中人与媒介呈现出另一种关系:
媒绝路阻兮,言不可结而诒。……愿寄言于浮云兮,遇丰隆而不将。因归鸟而致辞兮,羌宿高而难当。
诗人希望浮云为他传达信息,但云神兼雷神丰隆不肯承担。想要通过飞鸟致辞,却因为它栖息在高处而难以担当。同是丰隆,同是飞鸟,在《离骚》中多数听从抒情主人公调遣,在《悲回风》中却全都不肯为诗人服务,采取不肯合作的态度。《离骚》的抒情主人公有多种媒介可供利用,《思美人》中却是没有听从诗人指挥的媒介,所慨叹的“媒绝路阻”状态无法改变。《思美人》在重铸媒介意象时,在具体描写中暗示出它们的不肯为用。寄言于浮云,浮云本身漂泊无根,没有固定的去向,媒介本身的可信性就值得怀疑,因此出现丰隆拒绝承担传递信息的情节。“因归鸟而致辞”,在现实生活中,“鸟飞倦而知还”,归鸟是飞行疲倦、需要休息的鸟,它怎能充当传达信息的使者呢?所以,下面出现“羌宿高而难当”的情节,它在高树上栖息,难以承担此任。诗人似乎是在漫不经心之间,把浮云、归鸟的不可依赖巧妙地暗示出来,浮、归二字是画龙点睛之笔。
《思美人》还展示出诗人与媒介的另一种关系:
令薜荔以为理兮,惮举趾而缘木。因芙蓉而为媒兮,惮褰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说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与而狐疑。
在这段文字中,诗人明确昭示,并不是没有媒介可供利用,而是诗人不敢利用,也不想利用。薜荔攀附在树上,荷花生在水中,诗人既不愿意缘木登高,又不想入水濡足,只好听任媒介派不上用场,把它们闲置起来。而在《离骚》中,抒情主人公却是相继派出几批使者,和《思美人》主角的心灰意冷形成鲜明的对照。
从《离骚》到《思美人》,媒介意象经历了一个重铸的过程。在《离骚》中,抒情主人公和他所要利用的多数媒介都有能动性,能够进行合作,抒情主人公有能力驾驭媒介。而到了《思美人》中,或是媒介拒绝诗人的调遣,不肯为他服务;或是诗人面对媒介没有任何能动性。无论哪种情况,人和媒介都是疏离的,无法进行合作。《抽思》也写道:“既茕独而不群兮,又无良媒在其侧。”还是慨叹没有媒介可供利用,相比于《离骚》所说的“理弱而媒拙”显得更加可悲。
《思美人》对媒介意象的重铸,是经历两个途径实现的:一是增加《离骚》所没有出现的媒介角色,二是改变人与媒介之间的关系。前一种做法使媒介意象出现类的变化,后一种做法则是对原有媒介意象的颠覆和解构,使媒介意象的内涵发生根本性质的改变。
四、悖反型意象群的新构
所谓悖反型意象群,是指把两种或多种相反的事象排列在一起,两类事象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照,构成相互悖反的关系。相次排列的两类事象在性质上格格不入,彼此对立,呈现的是冰炭同炉而又水火不相容的形态。
这种悖反型的意象群在《离骚》中已经出现,主要取象于花草和历史典故。先看取象于花草的悖反型意象:
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苏粪壤以充帏兮,谓申椒其不芳。
抒情主人公假托巫咸之口,列举两组黑白颠倒的意象以批判现实:人们把艾草缠满腰间,反而说幽兰不可佩带;用粪土塞充荷包,反而说申椒不香。在所列举的四个意象中,有三个取象于植物。再看下面几句:
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
这几句诗全是以花草为喻:芳草化为茅草和萧艾,不再有芳香。诗人用香花芳草向反面的变化,比喻本来有美好品质的人变得丑恶污秽。
再看取象于历史典故的悖反型意象群:
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
这个意象系列每两句为一组,表达一种意义。前两组是说君主拒谏违理亡国,后两句是说恭敬守道兴邦,是以夏、商、周三代兴亡的历史故实作为依据加以昭示。
《九章》中晚于《离骚》的作品,同样可以见到悖反型意象,但较之《离骚》又有新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九章》的悖反型意象在取材时范围更加广泛,不限于花草和历史典故。《涉江》乱辞写道:
鸾鸟凤皇,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
这段乱辞按其取材可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以飞鸟为喻,后一部分以草木为喻。鸾鸟凤凰是俊鸟,与之相对的燕雀乌鹊是凡鸟。俊鸟远离而凡鸟进入庙堂,暗示贤臣被疏远而奸馋小人受重用。在后一部分,露申辛夷是芳草,腥臊代指各种恶草,同样分别指贤臣和奸佞。和《离骚》相比,这组悖反型意象不但取材于草木,而且取材于动物,把更多的物类纳入意象群之中。《悲回风》写道:
鱼葺鳞以自别兮,蛟龙隐其文章。故荼荠不同亩兮,兰茝幽而独芳。
这里也是同时取象于动物和植物。前两句取象于水族动物,把鱼和蛟龙相对比。后两句取材于植物,先是指出荼苦荠甜,因异类而不同亩,后面又突出芳草的独特香气。
第二,《九章》的悖反型意象群篇幅明显加大,从而增强了抒情力度,对比效果更加鲜明。《怀沙》是屈原的绝命辞,其中出现的悖反型意象,在规模上超出屈原以往任何作品,《怀沙》写道:
玄文处幽兮,矇瞍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
这里出现的悖反型意象有的取材于人世,有的取材于禽鸟,还有的取材于玉石,范围很广泛。同时,所表达的意义也更为丰富。开头四句是批判世俗的无视客观存在,以有为无,视而不见。中间四句是批判现实的黑白颠倒,以凤凰和鸡鸭的生存状态为喻。最后两句是批判现实的是非混淆,不辨玉石。这三层意义交织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对现实的批判极其深刻,诗人的愤懑和悲哀也抒发得淋漓尽致。
第三,《九章》的悖反型意象群,在结构及形态上变得更加灵活多样。《离骚》中悖反型意象群,基本上是每两个或四个意象为一组,形成整齐的前后对应关系,每个意象群所采用的句式也大体一致。《九章》的悖反型意象群则出现一些变化,主要体现在变整一有序为参差不齐。如前面所举《悲回风》的句子:“故荼荠不同亩兮,兰茝幽而独芳。”荼荠不同类,而兰茝和荠属于一类,但是,诗人却把不属于同类的荼和荠放置在一个句子中,而把和荠同类的兰茝单独组织在另一个句子中,上下句所构成的不是整齐对应的关系。再如上面所引《怀沙》的悖反型意象群,并不是用某种句式一以贯之,而是使用多种句式,时有变化。再看《惜往日》如下一段:
自前世之嫉贤兮,谓蕙若其不可佩。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虽有西施之美容兮,谗妒入以自代。
从总体上看,这是一个悖反型意象群。可是如果仔细加以审视,会发现并不是每一组都是相反意象整齐相对,而是参差错落,形成不太严格的对应关系。同时,所用的句式也多有变化,没有采用固定的结构模式。
从《离骚》到《九章》中晚于《离骚》的作品,悖反型意象群的变化是明显的,《九章》相关作品的悖反型意象群相对于《离骚》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新构,从形态到结构都有许多新的特点。悖反型意象群的新构,主要体现在屈原流放期的作品中,尤其是他的两首绝命辞《怀沙》和《惜往日》,在结构及形态上的灵活多变更为明显,它是屈原在生命终结期抒情的需要,也是这种悖反型意象群新构的完成。
屈原之后,悖反型意象群继续在楚辞作品中出现。《卜居》是后人为悼念屈原而作,其主体部分是屈原向郑詹尹的长篇发问和倾诉,全是由悖反型意象组成,其中询问句式的悖反型意象八组,每组两句。揭露世道不公的三组,每组两句。全篇是一个庞大的悖反型意象群,采用的是铺陈扬厉的笔法,更近于赋体。到了贾谊的《吊屈原赋》,这种悖反型意象群又重新以浓缩的形态出现而放在作品的结尾,恢复了它的骚体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