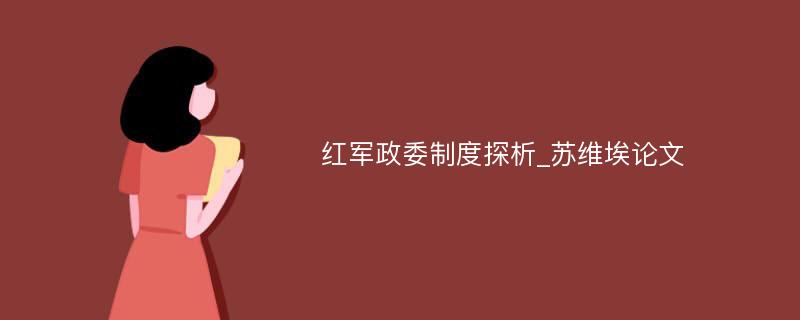
红军政委制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政委论文,红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7.3;K2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0)-08-0029-09
红军的政委制,是红军时期为加强党对军队领导而实行的一项重要制度,在红军的发展史上曾产生过重要影响。研究红军史,红军的政委制是不可忽略的研究课题。在红军的研究中,关于红军政委制的史料比较丰富,但学术界对这一制度很少关注,到目前为止,尚未见有关于这一问题的论文发表。研究这一问题,对于进一步推动红军史的研究,深刻认识党对军队领导制度很有意义。本文拟对这一制度的提出、争论、确立、推行的过程作考证性研究,以求教于方家。
一、政委制的提出
红军政委制,是在红军党代表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而红军的党代表制,则是继承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党代表制。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连以上各级都设立了党代表。
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的党代表制,一般史书都称是效法苏俄红军而建。但查阅史料,当时苏俄红军设立的是政治委员,而非党代表。前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编的《苏联武装力量》一书,对苏俄红军的政治委员有较详尽的记述:“红军中的第一批党政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是1918年3、4月间建立起来的,其目的是为了在军队中贯彻党的政策,对军事专家进行政治监督,领导党组织和全部党政工作”。① 这一制度的存续直到苏联成立后的1925年。1923年,孙中山为争取苏联的支持,派蒋介石率军事代表团赴苏访问。孙中山一直致力于创建一支党领导的军队,苏联红军中党的建设,自然是代表团考察的重要内容。蒋介石当时与苏联军方接触中听到和看到的应该是政治委员,而非党代表。日本人古屋奎二撰写的《蒋介石秘录》记录了蒋介石对苏联红军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政治委员制:“苏联的军队组织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每一团部由共产党派一政治委员常驻部队中。政治委员当然要参与军中主要任务,而且还具有非经其署名则命令不能生效的体制”。② 这段文字透露,苏俄红军政治委员制给蒋介石留下的印象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委员是由共产党党部派遣;二是政治委员有签署命令之权。
但苏俄红军政治委员名称怎么到了中国就变成党代表了呢?查诸史料,无答案可寻。有一种可能,是苏俄政治委员既然是共产党派驻红军中的代表,蒋介石及国民党人顾名思义即称作党代表。9月17日,蒋介石一行视察苏联红军步兵第144团,进一步了解到该团团长和政治委员分工情况。蒋介石日记写道:“大约军事指挥上事务皆归团长,而政治及智识上事皆归政党代表,尤其是精神讲话及平时除军事外之事务,皆归代表也。”③ 蒋介石在这里将政治委员写成政党代表,接着又干脆简洁地称着“代表”,说明政治委员的党代表性质对他印象很深。从史料上看,后来在广州的苏俄顾问和国民党人士没有人对党代表这一名称提出异议。
关于国民革命军党代表职责,1926年10月国民党中央制定和颁布的《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对其作了明文规定。条例指出:“党代表在军队中为中国国民党之代表”,“为军队中党部之指导人”。条例最引人注目的是赋予党代表监督军事指挥员和副署行政命令的权利,如规定:“发现指挥官分明变乱或叛党时”,党代表要“自动的设法使其命令不得执行”。④ 在党代表的职责中,监督军事指挥员的责任,为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人所特别看重。
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党代表中有许多是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在军队中积累了丰富的党代表工作的经验,所以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共产党所创建和领导的红军中,为建立党对军队的领导,一开始就建立了党代表制。1927年8月21日,南昌起义后的20天,中共中央常委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提出:“创造新的革命军队,……建立工农的革命军。这种军队之中要有极广泛的政治工作及党代表制度”。⑤
中共中央在工农革命军中所要建立的党代表制,是对国民革命军党代表制的继承。1927年12月,中央给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在广东一带活动的朱德写信,要求他们“必须依照从前的组织系统”建党⑥。所谓从前的组织系统,就是指国民革命军中党的组织系统。1928年5月,中央在给湘东特委的信中,更为明确地说:“军队中的党部,可照旧日国民革命军中党的组织法组织之。”⑦
中共中央在文件中第一次以政治委员代替党代表名称,是在1928年5月发出的《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规定:“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红军应由苏维埃派政治委员监督军官,并负责进行政治工作。政治委员应即为党的代表。”⑧ 这份通告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将工农革命军改为红军;二是由割据区域苏维埃政府派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即是党代表。6月4日,中央给朱德、毛泽东正式去信告知:“你们的军队,你们可以正式改成红军”,“在政治上设政治部,取消党代表”。⑨ 信中没有提到设政治委员,但要求取消党代表。至于取消党代表出于何种考虑,该信没有交代。
中央6月4日来信直到11月初才转到井冈山。11月6日在茨坪召开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接受了中央来信所提出的“全部原则及政策”,但会议不同意取消党代表制。⑩ 同月红4军召开的第六次党代表大会对此作出解释:“连支委为红军党的工作的核心,党代表则为此工作核心之负责者,并同时负有计划督促政治工作之公开任务。在事实上目前党代表制度不应取消”。(11) 决议案没有提到政治委员取代党代表事,从史料上看,红4军没有收到中央发出的《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
毛泽东在11月25日给中央写报告,汇报了贯彻中央6月4日来信精神的情况,其中一段话强调了党代表制的重要性,他说,“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从表面看,似乎既称红军,就可以不要党代表了,实在大谬不然。第二十八团在湘南曾经取消了党代表,后来又恢复了。”(12) 这是对中央要求取消党代表制的答复。
1928年6月中旬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在红军中以政治委员取代党代表的问题。会议召开前,周恩来会见了苏联军委代表,讨论了中国共产党比照创建时期的苏俄红军建立自己红军武装的问题,也进一步了解到苏俄红军政治委员的设置情况。周恩来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作的军事报告中提出,“红军绝对取消党代表,党代表是从国民党产生的,在苏联只有政治委员,由苏维埃政府派,但多半是党员”。(13) 周恩来在这里阐述了取消党代表两条理由:一是党代表是国民党的产物,在苏联没有党代表,只有政治委员;二是苏俄政治委员并不是当年蒋介石在苏俄以及国民党所了解的“由党部派”,而是由苏维埃政府派遣。当然,政治委员也是共产党的代表者,因此政治委员大多由共产党员担任。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正式决定,“采用苏联红军组织的经验,实行政治委员与政治部制度”(14),从而宣布中国红军与国民革命军的党代表制划清界限,开始完全按照苏俄红军模式建立政治委员制。
二、红四军有关政委制的争论
中共六大关于中国红军政委制只提出原则意见,具体实施的细则还没来得及制定,接着就在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4军中发生了关于政委制的争论。争论首先发生在红4军与中央之间,焦点是关于以政治委员名称取代党代表名称的问题。这是党的六大精神传达学习前争论的继续。
六大以后的九十月间,中共中央致信红4军,介绍了国际形势和党的六大决议,再次提出,“采用苏联经验,实行政治委员与政治部制度——将现有的政治部加以改造,多参加工人同志”。(15) 1928年底,党的六大文件到了井冈山,红4军的领导层在学习中,对党的六大及中央关于红军以政治委员名称取代党代表名称问题仍持异议。关于这一点,我们从两则史料中可以窥知大概。
一是1929年2月湖南省委代表杨克敏给中央的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报告谈到红4军党代表问题时说,“红军中仍采用党代表制。因为红军中多俘虏兵,士兵的质量不见得好,取消党代表制,实在不好。……曾经接过中央来信说要取消党代表制,改用政治委员,设政治部。关于军中的政治训练则党代表与政治委员的作用原是一样”。(16) 应该说,中央来信及其文件对政委制没有具体阐述,给人的印象是政治委员与党代表职责没有多大区别。在红4军的领导层看来,取消党代表是不行的;以政治委员名称取代党代表名称没多大实质意义。
二是这年9月,刚刚由红4军党的七大选为前委书记的陈毅在上海给中央的报告。报告说,红4军“军部有军长、党代表两人直接处理全军日常事务,……军成立政治部……政治部职权与军部平衡,不相隶属。军部与政治部以上的权力,在此未建立最高苏维埃政权机关时,集中于党的最高委员会。在团、营、连设党代表,团又设政治部主任,由党代表兼。因此各级党代表担任政治工作受政治部指挥”。(17) 陈毅的报告不仅反映红4军各级组织仍设党代表。而且还说明这一现象的原因,即最高苏维埃政权机关尚未建立,红4军权力只有集中于党的最高委员会——前委,所谓苏维埃派遣政治委员也无从谈起。
与此同时,在红4军内部又发生一场争论,争论涉及的问题之一是党代表兼党部书记问题。红4军实行三湾改编确立的党的组织制度,各级党代表兼任同级党组织书记,部队的重大问题由党组织讨论决定,“然后通知政权机关负责同志去执行”,党的书记会后即是党代表,按照会议的决定从事分工给自己的工作。这一制度在运行中,一些官兵特别是旧军队出身的军官不习惯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或认识水平的限制,分不清党代表和党的书记的工作,将日常党代表的工作也看成是党的书记在工作,而产生“党管一切”的误解,出现了军事干部与政治干部争权的现象。1929年6月,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说:“四军中有一种党部书记兼充红军党代表制度,一些同志分不清楚党代表与书记在职务上是两样东西,因为党代表与军官的权限历来没有弄清楚,时常发生争权问题,由是引起了头脑不清楚的人把党代表在那里工作看做是党的书记在那里工作了。三纵队几个连上的同志叫那个连的支书做‘老板’,就是这样牵挂来的。”(18)
由毛泽东的这封信看出,当时红4军党内围绕党组织及书记权限的争论比较激烈。1929年9月,陈毅在上海给中央的报告也说,红4军的军官与政治工作人员常常“争权”,“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常常发生纠纷,恍惚是国民革命军旧习一样。”(19) 这场争论的实质,是一些人不习惯党的领导。如毛泽东的信所说,“因为党的意志伸张,个人意志减缩,一切问题都要在各级党的会议席上议决之后,才许党员个人依照决议去执行工作,使得个人没有英雄式的自由”(20)。
为了平息争论,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建议党代表不兼党组织书记,党代表和党组织书记分别由两人担任。他说:“要除去此弊,只有使党代表与书记分开,这是应该一面从内部找人,一面从外面多找人来才可以解决的(从前的兼任是因人材太少的事实,是大家都知道的)。”(21) 毛泽东的这封信还说明,以前红4军的党代表兼党组织书记,还因为是红4军人才太少,要做到党代表不兼党组织书记,必须寻找人才。
陈毅在上海向中央汇报红4军情况时,也谈到红4军前委为解决争论,曾考查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工作关系四种形式,其中之一是“军官与政治人员平等,由党内书记总其成,一切工作归支部,这样可以解决许多纠纷,划分职权,但这要许多人才了”。他又说,红4军“在以前各级书记均由党代表兼,现在业已渐渐改变,书记可由军官士兵兼”。(22) 陈毅的汇报说明,1929年9月前,红4军已经在改变党代表兼党组织书记制度。
中央对红4军争论的态度,反映在1929年中央给红4军的“九月来信”中。对于是否以政治委员名称取代党代表名称的争论,中央坚持以政治委员名称取代党代表名称,来信说:“党代表名称应立即废除,改为政治委员,其职务为监督军队行政事务,巩固军队政治领导,副署命令等”。对于红4军设立的各级党组织及党代表兼同级党组织书记问题,“九月来信”指出:在“召集各地苏维埃代表会成立几省边境苏维埃政权”之前,红军由前委指挥,“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党的组织系统可保存现在状态”。鉴于当时红4军党代表兼党组织书记状况“已渐渐改变”,还特别提出“军政治委员可由前委书记兼”。(23)
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1929年12月,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明确规定在红4军各级设立政治委员,“军事机关的一切命令,……政治委员须副署”。关于政治委员兼同级党组织书记问题,决议案肯定已经开始的改变,在“政治委员与党内工作之关系”条款中,明确规定:“大队(即连一级——笔者注)支队(即营一级——笔者注)两级党部的书记,以不兼政治委员为原则,但在工作人缺乏的部队,仍可暂时兼充。”(24) 这就是说,连和营的政治委员不兼党组织书记。
红4军有关政委制争论的结果,即部队各级设政治委员取代了党代表,营、连政治委员不兼党组织书记。后者尽管是鉴于当时红4军部分官兵认识不到位,为了平息争论而采取的不得已的措施,但它却部分改变了三湾改编确立的党组织制度,降低了党组织在营、连部队中的地位和作用,削弱了党组织的建设和领导。
三、政委制的确立
应该看到,中共中央虽然同意红4军的政治委员和党组织现行运作方式,但中央强调只是在当时“几省边境苏维埃政权”未成立的前提下,而对这一制度的未来安排中央则有新的考虑。
“九月来信”前,中央对党和苏维埃的关系曾作过一些解释:“在苏维埃区域,党应当是苏维(埃)的思想领导者,应经过党团指导苏维埃的工作,纠正过去党代替苏维埃的错误”(25),“党不能命令苏维埃”(26)。“九月来信”则指出:“党对军队的指挥尽可能实现党团路线,不要直接指挥事[军]队,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有政治委员监督”。(27)
1930年3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成立红一军及军事工作的指示中指出:“政治委员是代表政权与党两方面来领导军队的,政治委员在政治上在党的立场上比军官权限大,即在军事上一切问题亦应得政治委员的副署。政治委员由军到大队(连)都要设置”(28),对政治委员的权限进行明确定位。
这些论述勾勒了中央关于党—苏维埃—政治委员—部队军事、政治机关领导关系的大致思想轮廓。党经过苏维埃中的党团指导苏维埃,由苏维埃政权指挥红军,由政治委员监督,党组织不直接指挥部队,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中央的意图通过政治委员个人的作用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
1930年9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简称《条例草案》)(29),贯彻了中央上述的思想主张,正式用法规的形式确立了红军政委制。
关于政治委员设置的目的,《条例草案》明确指出,“为加强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在红军中的领导起见,在红军中设立政治委员”。这说明政治委员的设置是为加强中国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
关于政治委员的定位及设置范围。《条例草案》指出,“政治委员……是苏维埃政权的一部分”,“政治委员不仅是苏维埃政权在红军中的政治代表,而同时是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全权代表。他是代表政权及党的双重意义,执行党在红军政治路线及纪律的完全负责者。”明确规定政治委员属苏维埃政权,是党和苏维埃政权在军队中的代表,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及纪律。《条例草案》规定,在营以上各级设政治委员,连设政治指导员。
关于政治委员的权限。《条例草案》给予政治委员在本部队中的最高权力。“政治委员有监督一切军事行动、军事行政的权力。”如果政治委员与同级军事指挥员发生争执,“政治委员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但必须立刻将争持的详细情形报告上级机关。在未得上级指示以前,须依照政治委员的意见执行”;政治委员在政治方面可单独发布命令,必须在委任、作战等命令上签字;政治委员执行革命法律,“在发现该部一切人员(由同级军事指挥员以至战斗员)有反革命或以破坏军队组织为目的的行动时,政治委员有执行革命法律之权”。此外,政治委员负责指导本部队的政治教育工作。
关于政治委员与本部队党组织的关系。《条例草案》指出:“政治委员是党的全权代表,关于本部队党的工作情形,他是对党负完全责任。”《条例草案》规定,红军只在连队设党支部,团设党总支部,师以上各级政治部设立党务委员会。政治委员不兼党组织书记。党组织书记“直接接受政治委员对本部队党的工作指示”。《条例草案》没有给予总支部和连党支部决定本部队重大问题的权利,总支部“讨论政治生活及一般党的问题,并提出决议”。连支部“在党员大会上应讨论一般的党的政治的及生活的问题”,“参加部队中一般党的工作”。而师以上党务委员会只讨论并决定接受与处罚党员的事项。《条例草案》还规定,“团总支部和连支部不能干涉政治委员的指挥命令。”这是对三湾改编确立的党组织制度的重大改变。
《条例草案》规定的政委制基本套用了苏俄红军的做法。在苏俄红军时期,政治委员是苏俄布尔什维克党在军队中的代表,也是苏维埃政权在军队中的代表。1919年3月,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指出:“政治委员在军队中不仅是苏维埃政权的直接代表,而且首先是我们党的精神”。政治委员对旧军队中来的军事指挥员实行监督,因此,要“使政治委员有实行纪律处分的权利(包括逮捕权)和交付审判的权利”。(30) 1919年,苏俄红军制定了团政委守则,明确提出:“团政委是本团政治上和精神上的领导者,是本团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第一个保卫者,是……团的灵魂”,另外还责成政治委员在各部队建立同志审判法庭。(31) 可见,在苏俄红军时期,政治委员是凌驾于军事指挥员之上的最高首长。
《条例草案》对政治委员与党组织的关系及党组织的设置与作用的规定,与苏俄红军的规定相差无几。苏俄红军党组织的设置,也是在师以上各级政治部中设立党务委员会。与《条例草案》规定的在中国红军团一级设党总支部有所不同,苏俄红军起初在团一级设党支部,1920年后,规定只在连一级设党支部。关于党支部的职责,苏俄红军史料对此反映不多,目前我们所能查到的是1919年1月俄共(布)颁布的《对红军党支部的训令》。这份训令对红军党组织的职责有这样的规定:“党支部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在部队中组成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主义者的坚强核心,它是士兵的组织者,是政治委员和指挥员在巩固高度军纪,提高部队战斗能力方面的忠实助手。”(32) 从阅读苏俄红军历史资料和这份训令的规定中我们知道,苏俄红军党组织没有决定本单位重大问题的职权,主要作用就是通过自身的影响组织士兵,充当本部队首长的助手。苏俄红军的政治委员不兼党组织书记,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还批评了那种让政治委员在支部任职并从属支部的想法,指出:“有些集团和个别同志宣传要改变目前红军的组织制度,实行选举政治委员和使政治委员从属于有关的支部等等的制度,这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它会引起和加剧红军的瓦解,因而是完全不能容许的。”(33)
总之,政委制的目的是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但中央又力图避免党组织直接指挥红军。政委制的结果,是强化了政治委员的个人权利,弱化了党组织集体领导作用。
四、政委制的推行
《条例草案》颁布后,中央要求各地红军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在给红军的训令指出:“必须坚决的执行最近送给你们的军队编制政治工作,政治委员,政治部党和青年团的支部工作诸条例”(34)。并且强调“首先便是政治委员应有的权限要完全实现起来”(35)。
中央明确反对红军政治委员兼党组织书记和党组织讨论决定本部队重大问题。中央认为,“政治委员兼党部书记是不适宜的。党部书记和政治委员的职位是不同的,党的书记是在选出后要得到政治委员的批准,而政治委员则居于政治指挥的地位,政治委员对部队的情状负完全责任,自然对党的组织的情状也要负责。”将党组织的地位明确置于政委之下。中央指出,“要坚决的反对……说在红军中有三头领导(指挥员,政治委员,和党部)的一切错误的倾向,……在有些部队中,党部工作好似部队的行政机关一样或者有的部队中盛行极端民主化,使党员大会来讨论命令等——这些倾向都应坚决的肃清。”(36) 将党组织民主讨论决定部队重大问题视作极端民主化的表现。
在中央苏区红军贯彻政委制过程中,开展了反对党组织“包办一切”的斗争。1931年9月,时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欧阳钦在关于中央苏区的报告中反映:朱德、毛泽东所部红一方面军中“政治委员制度仍未能照新的政治工作条例建立,仍是旧的编制”,红军中“一切问题仍是党来解决,在党的委员会决定之后来执行”。(37) 11月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对苏区红军中的党组织制度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由党的委员会决定部队重大事务“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并决定:“红军中包办一切军队行政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应即取消”。(38) 这种不从党和政权的性质上,而仅从治理方式上认识与国民党的区别,显然是形而上学的。况且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和政委制个人权威,出发点都是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并不存在是否以党治国的界限。
红军初创时期,官兵政治水平相对较低,军事斗争频繁而残酷,各部队普遍存在轻视政治工作的现象,有的则表现出对政治委员制度的不理解,不少政治委员政治水平不高,对自己工作职责不熟悉和不重视。如鄂豫皖地区的红4军反映:“全军无论上下……对政治委员(党代表)制度根本缺乏认识,当(然)政治委员的政治基础不够与成分不好或不军事化的生活,而不能深入群众成为群众的领导者亦是主要原因之一”。(39) 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关于改造红3军的训令指出:“政治委员大部分代替了参谋长的工作,因为许多政治委员不能履行政治工作条例中所规定的工作,反而把共产党在部队中的力量和威信减低了”。(40) 因此,红军贯彻政委制的过程,也是政治工作地位提高的过程,是加强政委队伍建设的过程。到1933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宣布:“红军中政治委员制的建立,都获得了相当的成绩。”(41)
作为红军部队党代表、党组织制度的创始者,毛泽东对政委制的态度值得注意。红军政委制施行后的两三年,我们从当时的史料中看不到毛泽东对此有什么评论。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在各级设立政治委员,但在《条例草案》颁布后迟迟没有取消三湾改编确立的党组织制度,证明毛泽东虽同意设立政治委员,但并不赞成扩大政治委员的权利而取消党组织制度。然而,既然当时中央对党组织制度还没有清楚的认识,既然政委制对提高政治工作地位有帮助,毛泽东还是接受了政委制。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宣布:“现在的红军,已经走上了铁的正规的革命武装队伍的道路”。表现之一是“政治委员制度普遍建立了,红军掌握在可靠的指挥者手中”。毛泽东还号召:“政治委员制度应该建立到一切红军部队、地方部队与游击队里面去”。(42)
在执行政委制的过程中,出现了政治委员专注监督军事、行政的责任,而忽视了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的现象。1934年2月,王稼祥在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批评说:“政委工作中的弱点,就是还没有认清自己的中心工作,军事倾向太浓厚”,“政治委员不能很好地发挥党组织的作用,有的政治工作机关代替了支部”。(43) 政治委员专注监督军事、行政的现象,忘记政治工作这一中心工作,无视党组织的作用,这是政委制造成的。
政委制扩大了政委的权利,使党组织不能对政委的权利实行监督和制约。周恩来在1934年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的政治委员负有保障上级命令执行的绝对责任,如果军事指挥员对命令不了解,或不执行,政治委员要向其解释,监督其执行。可惜得很,我们有些政治委员亦不执行命令,这是更坏的现象”。(44)
在当时中央“左”倾错误的指导下,有的政治委员在肃反中滥用职权,打击同志,甚至后来发展到与党中央分庭抗礼的地步。1937年2月中央批判张国焘错误时,有的人指出,张国焘“是中央派到四方面军去的代表,在红军中他是中央指派的总政治委员”。但他“把肃反工作成为个人的工具,因此滥用权力发展到不能容忍的程度,凡是与国焘个人有意见不同的,他就利用这个权力的机关去加以压制,结果使党内生活成为不可容忍的现象”。长征中张国焘反对红军北上,与中央闹独立。“身为总政治委员可以不服从中央的命令和指令。因为总政治委员的职权,只是中央在红军中的代表,他的权限并不能超过中央政治局,他的责任一定要服从中央政治局的命令,……北上的战略方针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不经过中央政治局,没有任何人有权利改变这种方针的。国焘身为政委应当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命令,可是国焘却能用私人的意志去改变这一战略方针,……以这样一个糊涂的政治委员怎样还能去加强党在红军的绝对领导?”(45) 这是政委制扩大政治委员个人权利,取消党组织制度的惨痛教训。
五、余论
建立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这是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不约而同得出的结论。国民党学习苏俄红军在军队中设立党代表,目的是建立起党对军事指挥员的监督。中共中央建立的红军政委制,也将政治委员的主要责任定位在对军事指挥员的监督上。事实上,这不符合红军的军情。1934年2月,王稼祥在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谈到政委制时,将我国红军和苏俄红军的情况作了比较,认为,“苏联当时的红军指挥员大多是从白军过来的,所以要由政委严格督促。中国红军指挥员大多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出来的,从武装暴动中涌现出来的,大多是党员,所以同苏联红军的情况不同”。(46) 应该说,这是对政委制的深刻反思和批评。
中央的意图是树立政治委员的权威以强化党对军队的领导。但政委制突出政治委员个人的作用,取消了党组织的集体领导,这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政治委员的主要责任应在政治工作,这也是实现党对军队领导的根本途径和保证。正因为如此,红军时期在各部队设立政治委员这一做法,在人民军队中一直延续到今天。红军政委制关于政治委员担负的政治工作的职责和任务的许多内容,为后来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所继承和光大。
政委制的弊端显而易见,所以长征结束后,党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就在酝酿恢复军队党组织制度,以“集体的领导方式来代替政治委员制度”。(47) 1937年5月,苏区党代表会议提出:“健全与加强党在军队中的组织,提高各级党委员会之作用与威信,党的组织应该成为部队生活中的决定的骨干,政治工作的支持与依靠。”会议决定:“在军师及独立行动之单位组织军政委员会,这是党的组织,他指导军队的全部政治和军事工作,并向党中央负责。”(48) 这样,红军政委制的缺陷逐步得到纠正。
今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政治委员与同级军事主官同为所在部队的首长。党的各级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本单位的重大问题,由军政首长分工负责执行。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军政首长对所属部队各项工作共同负责,互相配合,密切协作。这已成为人民军队始终不变的制度和传统。
注释:
① 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编《苏联武装力量》,战士出版社,1981年,第34页。
② [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翻译组译:《蒋介石秘录》第2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64页。
③ 转引自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上)(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1页。
④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291~292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40页。
⑥ 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1册,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第34页。
⑦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湖南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333页。
⑧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33、236页。
⑨ 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1册,第72~73页。
⑩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7页。
(11) 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1册,第170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4页。
(13)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7页。
(1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491页。
(15) 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1册,第145页。
(16) 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1册,第186页。
(17) 《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8页。
(1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78~80页。
(19) 《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24页。
(2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73~74页。
(2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80页。
(22) 《陈毅军事文选》,第24~25页。
(23) 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1册,第284~286页。
(24) 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1册,第348~361页。
(25) 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1册,第146~147页。
(2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第372页。
(27) 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1册,第286页。
(28)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第741页。
(29) 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1册,第599~620页。
(30) 《列宁、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红军建设的若干资料汇集》,兰州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政治教研室翻印,第3~4页。
(31) [苏]波别日莫夫著、张祖德译:《苏联建军简史》,时代出版社,1956年,第28页。
(32) 《列宁、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红军建设的若干资料汇集》,兰州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政治教研室翻印,第3页。
(33) 《列宁、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红军建设的若干资料汇集》,兰州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政治教研室翻印,第6页。
(34) 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1册,第581页。
(3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461页。
(36) 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1册,第581~582页。
(37) 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1册,第766页。
(38) 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1册,第812、807页。
(39)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第361~362页。
(40) 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2册,第111页。
(41) 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2册,第311页。
(4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339~342页。
(43) 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2册,第630、628页。
(44)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第318页。
(45) 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3册,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第728~732页。
(46) 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2册,第630页。
(4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68页。
(4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