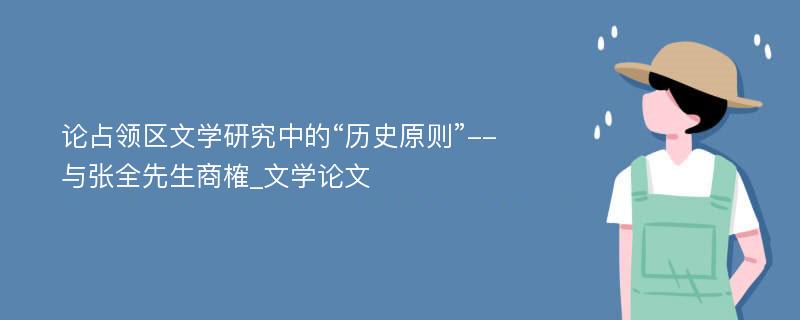
也谈沦陷区文学研究中“历史的原则”——与张泉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沦陷区论文,也谈论文,原则论文,历史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泉先生写了一篇长达2万多字的文章:《沦陷区文学研究应当坚持历史的原则——谈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史实准确与政治正确问题》(注:《抗日战争研究》2002第1期。),就沦陷区文学评价问题,批评我及裴显生、王凤海、冯光廉、蓝海等先生的所谓“全盘否定”的观点。主要是批评我。
关于沦陷区文学评价问题的争论,至今已有3年。我与张泉先生已“争鸣”过一次。这次,张泉先生又写了文章在《抗日战争研究》上发表,在坚持原来观点的同时,又提出:沦陷区文学研究应当坚持历史的原则。作为被批评者,我在张文中努力寻找他所说的沦陷区文学研究中的“历史的原则”指的是什么。可是,我通读3遍,也未看到他所说的“历史的原则”究竟有哪些具体内容,他只是一再重复以前所说的“史实是评说沦陷区文学的唯一前提”。然而,“史实是评说沦陷区文学的唯一前提”,与“历史的原则”并不能划上等号;而沦陷区文学和沦陷区作家中的许多史实,却被张文遮蔽了;在对沦陷区文学做出评价时不能回避的政治问题却被张文回避了。现就以下三大问题对张文进行评议。(按:本文中凡提及“张文”处,指张泉先生的:《史实是评说沦陷区文学的唯一前提》(注:《文艺报》2000年3月28日。)、《二论史实是评说沦陷区文学的前提》(注:《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关于沦陷区作家的评价问题》(注:《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及《沦陷区文学研究应当坚持历史的原则》四篇文章,不一一注明出处。)
一什么是沦陷区文学研究中应当坚持的“历史的原则”
做任何研究工作,都要以事实为基础。研究沦陷区文学也不例外。不掌握沦陷区文学的相当的史实,也就不可能研究好沦陷区文学,这是常识。但是沦陷区文学研究有其特殊性。沦陷区文学是在特定的年代、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和发展的。沦陷区文学研究“历史的原则”,我的理解是:把沦陷区文学放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研究其发生发展的历史情形,研究其不同的历史形态,而后对不同历史形态的沦陷区文学,就其对抗日战争是起了何等作用(促进作用、阻碍作用或消极作用)及其艺术性,分别作出历史的评价。这才是沦陷区文学研究中“历史的原则”。然而,十分遗憾,张泉先生的多篇文章都忽视了这一点。
先说沦陷区文学是怎么产生的。张文认为,由于“日伪文化控制的混乱和软弱无力”,作家和作者就“自发的”创作了沦陷区文学。不对,因为这说的是正常文学的产生情况,沦陷区文学却并非如此。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一部分领土后,第一步是大“讨伐”(在东北)、大屠杀(在南京等许多地方)、大围捕(围捕抗日分子,在上海),那时他们根本不搞文学。第二步在各地维持会或其他形式的汉奸政权产生后,局势稍见稳定,日本占领者和汉奸政权才办报纸(包括文学副刊)、办刊物(包括文学刊物)以点缀太平,进行奴化教育和毒化教育。于是在敌伪报刊上才有文学作品的发表,才有沦陷区文学的出现。也就是说,沦陷区文学不是正常环境下产生的文学,而是由日本占领者以及伪政权出人、出钱、出物有目的地搞起来的文学。1939年创刊于北京的《中国公论》、1942年创刊于上海的《古今》、1943年创刊于南京的《中国青年》、1943年创刊于上海的《文友》、《天地》、1944年创刊于上海的《众论》、1944年创刊于南京的《文艺者》等等百余种报刊(沦陷区的全部报刊没人统计过,总数当在几百种以上)及刊登在这些报刊上的文学作品和文论,就是这么产生的。没有日本占领者和汉奸政权的特许和批准,这些报刊(以及出版社)不会出现,沦陷区文学也不会出现。(注:参见虎闱:《短命的汉奸杂志<众论>》,《开卷》2001年第4期。)(即使像《紫罗兰》那样的写鸳鸯蝴蝶的杂志,也得在敌伪当局批准后方能继续出版)。拿正常文学的产生情形套用在沦陷区文学上面,是忽视了沦陷区文学的特殊性。
然而,当着日本占领者批准和特许出版报刊,企图以舆论和文学在思想上、精神上控制、麻痹沦陷区民众的时候,共产党地下组织及其领导下的进步青年、进步文化人士却采取了孙悟空钻进对方心脏里的战术,打入了其中的某些报刊,某些文学阵地,使之成为自己的阵地,于是在沦陷区文学中也就有了一小部分倾向进步、倾向光明的文学。为了具体说明这一点,我这里以抗日战争时期南通市中共地下组织打入敌伪控制的《江北日报》的副刊,变敌伪舆论阵地为我方舆论阵地的典型事例,说明沦陷区文学中也有倾向进步、倾向光明的文学。
日寇占领南通后,也是先围捕抗日分子,而后成立伪政权,而后再办报纸。在报刊上登些风花雪月的作品。1943年4月,日伪在南通地区开始清乡,以苏中苏北后来人尽皆知的大汉奸张北生(此人已于1954年被人民政府镇压)为首的汉奸集团,从苏南来到南通,取代了原来的汉奸集团。南通市的《江北新报》被改组,改名为《江北日报》。伪政工团长孙永刚掌管宣传、文化机构,要通过搞文化活动来装点门面,苦于没有人手。这时已打进伪清乡公署的地下党员曹从坡同志奉中共党组织之命,也打入了《江北日报》,担任副刊主编;中共党员顾迅逸则出面担任《江北日报》诗副刊《诗歌线》的主编。但《诗歌线》的实际主编则为张师凯(章品镇)。《诗歌线》不发可能引起敌伪注意的抗日、反汉奸的文字,但是促人健康、向上、鼓舞青年人向往光明、追求理想的且有相当艺术水平的诗作、文章,则每期都发。章品镇看到秘密传递到他手里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认为在沦陷区的环境下,虽然不可能做到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但歌颂工农兵、支持被压迫、被蹂躏的小人物,却是可以做到、能够做到的,于是与同人商议后,决定组织为各行劳动者写照的创作。作品一发表,引发了踊跃来稿。《诗歌线》在必要时,利用敌伪内部的矛盾,有时也点一下附逆文人的名,以示警告。其时,附逆文人路易士(后去台湾,改名纪弦),反动气焰极为嚣张,写了《反第三国际诗抄》。章品镇便在发表一个小朋友写的《大街上》的诗后,写了这么一段话:“笔者个人是不希望他写诗的。一个散文基础都没有的人,写诗是暴殄精力,是迷乱习作路线的正确发展,即使终生致力于诗作,结果是再造成一个路易士而已,于人于己两无益的——编者”。路易士看到后对此也无可奈何,一则控制《江北日报》的孙永刚与路易士不是一路人;二则他也知道自己在苏中、苏北不得人心。正因为《诗歌线》采取了这样一些在特殊环境下进行特殊战斗的方式与敌伪作斗争,所以《诗歌线》(共出了四十多期)成了苏中、苏北诗坛上的一面倾向进步、倾向光明的旗帜,为广大青年所欢迎,而且培养造就了一些青年诗人和诗歌作者。《诗歌线》上的作品,有8人8首被选入《中国四十年代诗选》。类似《江北日报》副刊和诗副刊《诗歌线》的沦陷区文学,在其他沦陷区也都有,虽然很少。
正因为沦陷区文学有如上的特殊性,所以沦陷区文学的历史形态就呈现为由4类作家、作者创作的4类文学:
第一类是在沦陷区开展地下工作的和坚持爱国立场的作家、作者及由他们创作出来的文学。我以关露、柯灵为代表。
第二类是在文化领域内为敌伪政权服务的作家及作者及由他们创作出来的文学。我以周作人、陈彬和、胡兰成为代表。
第三类是以不同方式附敌附伪的作家、作者及由他们创作出来的文学。我以张爱玲、苏青为代表。
第四类是不明敌伪底细和真相,只是出于爱好文学而写作的文学青年和由他们写出来的一些文学作品。(按:张文却曲解我的原意,说沦陷区文学“就这样抽象为不同作品的7个作家和一批文学青年”。裴显生教授在《谈沦陷区文学研究中心认识误区》(注:《文艺报》2000年4月18日。)中对我以上的分类有所修正,他认为:“业余作者写的作品,或属于第一类,或客观上适应敌伪的需要,数量也不多。”我同意这一修正。)
沦陷区文学中3类作家作者,3种历史形态,又表现了沦陷区文学的复杂性。
从上可见,我对沦陷区文学中的第一类作家、作者所创作的倾向进步、倾向光明的文学,从来是支持和肯定的。而张文却把我说成是沦陷区文学的“全盘否定”者,这符合“史实”吗?实事求是吗?
不错,我对第二类、第三类作家作者所创作的文学,只承认其中的个别作品(如《金锁记》)写得较好外,基本上是持否定和批判态度的。因为在沦陷区文学中面广量大的,民众接触最多的,正是由第二、第三类作家、作者创作的“整体上适应了敌伪需要的风月文学、情爱文学、色情文学、鬼狐文学、秘闻文学、灰色文学、颓废文学等等。它们表面上不谈政治,脱离政治,实则粉饰沦陷区的现实,消磨沦陷区民众的斗志,因此为敌伪扶持和提倡”。(裴显生语)第一类文学对抗日战争起了促进作用;第二、第三类文学则对抗战起了消极、阻碍作用。这是“史实”,谁也否定不了。
张文对沦陷区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不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侈谈什么“沦陷区文学的主体”是“中国抗战文学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于是,被收入《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的周作人、胡兰成、柳雨生、张资平、张爱玲、苏青、路易士等人的57篇(首)作品,全都成了“中国抗战文学”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一部分。当年在解放区和国统区坚持抗日斗争、坚持抗战文学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创作的老作家会同意对沦陷区文学的如此定性吗?乐意与此等人为伍吗?沦陷区文学研究中的如此“历史的原则”,过去的历史不会承认,今后的历史也不会承认!
什么是“主体”?查《辞海》和《现代汉语词典》,“主体”有哲学意义的“主体”,法学意义的“主体”,在通常场合下,“主体”指“事物的主要部分”,是量化的概念。在沦陷区文学中,像《诗歌线》这样的由中共地下组织和进步人士掌握的报纸副刊和刊物,充其量不到总数的5%;在敌伪控制、掌握的报刊上发表的倾向进步和光明的作品充其量也不到5%,沦陷区文学中的90%,是裴显生先生所说的那些“为敌伪扶持和提倡”的文学,它们构成了沦陷区文学的“主体”,这才是“史实”,这才符合沦陷区文学“主体”的实际。
二沦陷区文学不能遮蔽的重要史实
史实是沦陷区文学研究的起点。没有相当的史实作准备作基础,也就一定搞不好沦陷区文学研究工作。但是,把史实即使如张文提高到“史实是评说沦陷区文学的唯一前提”的高度,它也不能和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历史的原则”直接划上等号。上面,我已讲了我对沦陷区文学研究中“历史的原则”的理解,现在我再说运用这一“历史的原则”时,绝不能像张文那样遮蔽重要史实。
第一,张文遮蔽了沦陷区文学的最大“史实”:八年抗战是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生死搏斗的历史时期,也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与法西斯国家进行决战的历史时期。战争的结局关系到中华民族和世界人民的历史命运。如果没有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早就做了亡国奴。而在沦陷区文学中,汉奸周作人、胡兰成、张资平、柳雨生等人,附逆文人张爱玲、路易士、苏青等人所创作的文学,就其全体而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利于敌伪的,并为敌伪所需要的。张文对此却始终只字不提遮蔽了史实。
第二,张文遮蔽了沦陷区内由日本侵略者所搞的日语文学也是沦陷区文学一部分的史实。还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东北的殖民者就搞起了“满洲文学”(按:这是日本在东北的殖民者对他们策动起来的文学的提法。)。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者更大搞“满洲文学”。1932年9月,《高梁》在新京(长春)创刊;10月,《作文》在大连创刊;被称为“北有《高粱》,南有《作文》”。其后,1938年,《满洲浪漫》在新京创刊,于是又有了“北有《满洲浪漫》,南有《作文》”的说法。它们搞的都是“满洲文学”。“满洲文学”以所谓“建国精神”为中心,在“建国精神”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建国文学”的主张,思考在满洲建立新国家。“满洲文学”虽有日系“满洲文学”和满系“满洲文学”之分,但它们都是东北沦陷区文学的一部分。正如,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一部分作家流亡到了新加坡(那时它还属于马来亚)、马来亚、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地,他们在那里以华文写了作品。这部分华文文学,既是中国文学、中国抗战文学的一部分,又是该国文学、该国抗战文学的一部分,这些国家的文学史家,早已把抗战时期华人作家在该国创作的文学写进了该国的新华、马华、菲华、泰华、印(尼)华文学史,即成了该国文学史的一部分。1998年10月,鹭江出版社出版的《澳门文学概观》(刘登翰主编)即把葡裔人用葡萄牙文创作的文学作品及其代表作家飞历奇、江莲达、爱蒂斯·乔治·玛尔丁妮、若瑟·多斯、圣托斯·费雷拉、马若龙、李安乐等作为澳门文学一部分《澳门的土生文学》加以论述。同理,日本人在中国搞的侵华文学,虽然低劣,它们仍然是沦陷区文学的一部分。至于日本在七七事变后全面侵华,日本政府组织的“笔部队”即随军作家创作的侵华文学,虽然以日文写的,但写的全是侵华战争,美化日本侵略者,宣扬“皇军”胜利,丑化中国军队和中国民众,题材全取之于日本占领区(我国的沦陷区)的“皇军”和中国军民中的人物和事件,赤裸裸地为日本侵华战争服务。因此,它们同样有两重身份:一方面,作为日本人创作的文学作品,它们是日本文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们是日本作家在中国写的,写的是日军占领区(我国沦陷区)的战争和活动,全和沦陷区有关,因此,它们又是沦陷区文学的一部分。这和它们的思想艺术水准的高低并无关系。不仅如此,在侵华战争期间,还有日本“军队作家”搞的侵华文学;日军在中国沦陷区搞的“宣抚文学”,同样具有两重身份:一方面它们是日本文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们是沦陷区文学的一部分。对于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队搞的侵华文学,王向远先生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和批判》(北京师范大学1999年出版)一书中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本节中的史料,即取自该书。)谁也不能仅仅因为它们是用日文创作的就把它们一概排除在沦陷区文学之外。所以,张文对裴显生教授的指责:“草率地将日本的日语言文学谱系中最拙劣的那一部分,堂而皇之地请进中国的汉语言文学谱系”,是毫无道理的。谁也无权规定,沦陷区文学只能是汉语文学。至于张文所说的这样做“会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唯恐日本人会因为我们将上述侵华文学划进沦陷区文学范畴而对我抗议。这一顾虑是多余的。我们的海外华文文学史,把许多国家华裔人写的华文文学作品,早已列入华文文学史的范畴,但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并不因为这些作家是该国的国民而对我国抗议。因此,张文遮蔽沦陷区里的日语文学也是沦陷区文学一部分的史实,既“无学理可言”,更违背“历史的原则”。按照这一说法,东南亚国家的抗战文学就得把华人创作的华文文学排除在外了。因为它们并非用该国的主要民族语言文字创作出来的。
第三,张文遮蔽沦陷区文学中的宣扬“独立精神”与“建国精神”的文学(在东北)、“治(安)运(动)小说”、“护路小说”(在华北)、“剿共剧本”与“和平文学”(在华中)是沦陷区里的实际上的“皇民文学”的“史实”。“皇民文学”确是在台湾被日本占领时期由日本占领者在台湾提出的,旨在使台湾的中国人成为日本天皇的顺民。但是,日本侵略者也企图使东北、华北、华中的占领区的民众成为天皇的顺民。不过,因为在东北还有伪满洲国,在华北、南京还有王揖唐、梁鸿志、汪精卫的伪政权,所以日本侵略者不在占领区(中国的沦陷区)里提“皇民文学”,而在伪满搞有“独立精神”与“建国精神”的文学。在华北、华中搞“治运小说”、“护路小说”、“剿共剧本”、“和平文学”,其目的同样是把中国民众“皇民化”。裴显生教授称这为沦陷区里的“实际上的‘皇民文学’”,符合这些文学的实情。但张文却又断言,台湾的“皇民文学”与这些文学之间,两者有“本质区别”。请问: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在哪里?难道两者不都是要中国人做日本的“皇民”吗?台湾的反独派文论的领军人物陈映真先生政治上很敏感,他在给张泉先生的信中写得很清楚:“大陆文论如何正确对待沦陷期、敌伪期(东北)文学,对我们是很重要参考,尤其是东北。理解伪满‘建国’理论,从而理解伪满地区、伪满时代汉奸文学与‘建国论’的连系,是我们在台湾与台独文论斗争的十分重要的参照。”这是说,伪满时代的汉奸文学及其“建国论”和今天的台独文学及其“建立台湾国家论”在分裂祖国这一点上有一脉相通之处。不料,张泉先生对此毫无察旷,反而把上述“实际上的‘皇民文学’”一概排除在沦陷区文学之外,以维护他的所谓沦陷区文学主体是抗战文学和反法西斯文学论。这里,我也把陈映真先生于2001年7月31日给我来信中的有关内容公布:
在台湾,为皇民文学脱罪开脱、美化粉饰,是台湾反民族的文化阴谋重要的一环。他们说:(1)在那个时代,人无不写皇民文学;(2)说“皇民文学”、“汉奸文学”是扣帽子,是“中国人”意识,应该摆脱中国人观点,重新评价;(3)皇民文学使台湾人既摆脱了日本人又摆脱了中国人的意识认同,是后来“台湾民族主义”的滥觞;(4)皇民文学表现了殖民地台湾面对“现代性”时的矛盾与挣扎。对此,我们是壁垒分明,坚决斗争的。
近年来,大陆上似乎有少数一些人,受到过去极左路线的伤害,反映为抵触、反调。有关皇民文学研究的诸论中,恐怕也有这一层原因。这是可理解的。然而在真理之前,可以理解的,不都是正确的。这是历史留下来的共同之伤痕,要细致对待,也要坚持原则。不知先生以为然否?
我以为,陈先生的意见非常正确。不能因为“受到过去极左路线的伤害”,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因为要维护沦陷区文学主体是“抗战文学”和“反法西斯文学”论,就把那些“实际上的‘皇民文学’”也统统把它们排除在沦陷区文学范畴之外。如此遮蔽沦陷区里的“实际上的‘皇民文学’”,更与“历史的原则”背道而驰。
第四,张文遮蔽张爱玲的反蒋(那时蒋介石还在抗日)、亲日、反苏作品的“史实”。张爱玲在敌伪的庇护下,自由言说,在小说《等》里,她竟借作品中人物之口胡说蒋介石“因为战争的缘故,中国的人口损失太多,要奖励生育”,便下令政府工作人员讨“二夫人”。说了一遍不算,又说第二遍:“……里边蒋先生(即蒋介石)因为打仗,中国人民死得太多的缘故咾,下了一条命令,讨了小也不叫姨太太叫二夫人——叫他们讨呀!”国民党政府在大后方诚然腐败,但它毕竟还在抗战,而且蒋介石从来也不曾下令政府工作人员讨“二夫人”。造谣造到蒋介石头上,可见张爱玲为了紧贴敌伪,已经到了无中生有的地步!张爱玲还公开媚日。在《忘不了的画》中,张爱玲在这么一篇谈绘画艺术的文章里也忘不了对日本人称赞一番:“日本对于训练的重视,而艺妓,因为训练得格外彻底,所以格外接近女性的美善的标准。”而在当时,“对于训练的重视”的日本军人正灭绝人性地大肆杀戮中国人。在《双声》一文中,她说:“同西洋同中国现代的文明比起来,我还是情愿日本的文明的。”这样公开的媚日言论,即使在敌伪的报纸上也不多见。当时饱受日寇蹂躏的中国人知道“日本的文明”究竟是什么。张爱玲还反苏。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哪怕是开电梯的丢了一只旧的牛奶瓶换了一只小一号的牛奶瓶这么一件小事,张爱玲都没有忘记讽刺一下社会主义苏联:“这一类的举动是颇有点社会主义之风的。”而当时苏联是反法西斯的主力,在卫国战争中,伤亡2000万人以上。张爱玲故意扭曲香港大学生。在《烬余录》里,张爱玲对日寇侵占香港没有说半句不是,反而把香港的大学生写成对抗日战争漠不关心:“至于我们大多数的学生,我们对于战争所抱的态度,可以打个譬喻,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盹,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这段话,用之于张爱玲自己则可,但用之于香港大多数大学生,则是对他们的严重扭曲。在日本发动占领香港的战争中和战争以后,香港的大学生有的主动投入香港英军的抗战,有的转移到东江抗日根据地,有的转入内地或海外读书,以求日后报效祖国,像张爱玲那样“到底还是睡着了”醒来后又跑到日寇统治下的上海的香港大学生是极少的。
张文为什么对张爱玲这些明白如画的“史实”都要遮蔽呢?因为在他心目中把张爱玲视为沦陷区文学的代表作家,张爱玲倒了,沦陷区文学就撑不起来了。其实,傅雷(迅雨)早就说过:“在一个低气压的年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在什么幻想,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沦陷区文学中的第二、第三类作家不可能创作出真正优秀的作品,而第一类作家由于他们在敌伪统治下不能自由言说,所以正如《诗歌线》的实际主编章品镇所说的,只能守住“决不发有利敌伪的稿件”的“底线”,“作品力求健康,艺术上决不马虎”。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在此情况下,在沦陷区文学中产生不了大作品,也出不了大作家,是必然的。硬要把张爱玲拉出来充当沦陷区文学的代表作家,也就只好对会使张爱玲出丑的“史实”予以遮蔽了。
三对沦陷区文学、沦陷区作家进行评价,不能不讲政治,不能不讲民族大义
日本占领者和伪政权在沦陷区搞文学,旨在把民众“皇民化”;中共地下组织及倾向进步、具有民族气节的人在沦陷区搞文化,旨在使民众向往光明,追求进步,争取抗日战争早日胜利。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为政治服务。这是在抗日战争的特定环境下沦陷区文学的必然属性。因此,对沦陷区文学、对沦陷区作家进行评价时,不能回避政治,也不能不讲民族大节。这是一。
中国历来就有既评文又评人的文论传统。阮大铖的剧作再好,钱谦益的诗作再好,当时人和后人也因为他俩投靠了清王朝而予以鄙视、蔑视。(按:清王朝毕竟还是中华民族中的一个少数民族的王朝,仍是中国人的王朝。)而在抗日战争中的汉奸和附逆文人投靠的却是要使中国亡国灭种的日本侵略者。在评论这些人的作品时,怎么能够只评文不评人?这是二。
但是,张文却否定沦陷区文学与敌伪的政治联系;反对既评文也评人的文化传统,认为,只有按照他回避政治的、人与文绝对分开的“微观”、“细节”、“具体”的沦陷区文学研究模式,才是“政治正确”。对此,我不能苟同。
仍以沦陷区文学中的几位典型的作家为例。
先说沦陷区头号文化汉奸周作人。据《文史精华》2002年第7期程堂发的文章,1941年1月伪华北教育部总督办一职出现空缺,周作人即继任其位,同时还兼“剿共”委员会委员,并以“教育督办”身份出访日本。1942年5月为庆祝“满洲国”成立10周年,周作人与汪精卫等一同赴“满洲国”访问,在长春拜会了溥仪。在北平,他身装日本式军服,头戴日本战斗帽,陪伪华北新民青少年团正统监王揖唐(华北第一号汉奸)检阅了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分列式。一代文人如此堕落,令人可悲可恨。周作人在《中国文艺复兴之途径》一文中鼓吹:“用最通行的话来说,即是复兴中国,保卫东亚”(载《中国文学》1944年第1期)。张文为之辩解说:“与同期的其他文章相比,周作人的不同之处是,既肯定中国文学传统又生硬地嵌入当局的宣传口号。文章中相互抵捂的表达,以及欲言又止、闪烁其辞的表达方式,多少透露出周作人思想中的矛盾,既不同于官方的说教,又与其他作家有很大差别,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再说胡兰成。胡是汪精卫的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次长,伪法制局长。他“是日本大使馆书记官吉田东祐最赏识的一个文化汉奸,他写的社论在沦陷区是颇具几分煽动性的”。(注:华东七省市政协文史工作协作会议编:《汪伪群奸祸国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他“因受日本人指使,在武汉接编《大楚报》,并创办了一个政治军事学校,其目的是想在武汉炮制出一个日伪政权——‘大楚国’”。日本投降后,胡兰成“不甘束手待缚,积极策划,与二十九军军长邹平凡一起匆匆宣布独立,并拥兵数万,妄想成立武汉军政府”。“‘独立’了13天,便分崩离析了”。(注:邓光东、陈公仲编:《世界著名女作家传·张爱玲》(欧美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115—116页。)胡是个死心塌地的文化汉奸,他吹捧周作人“真是大有根底的人”,“是是非分明,神清气爽的一个人”。但在张文里却说,“胡兰成的著作驳杂繁复”,“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人物,他的学术生涯还是值得研究的”。这是在沦陷区文学研究中把人、文分开,不讲政治的又一事例。
再说张爱玲。她和文化大汉奸胡兰成结识后,竟对他倾心爱恋。她赠给胡兰成一张照片,背面写着两行文字:“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那时,中国军民抗战已有六七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从防御转为进攻,日寇败局已定,张爱玲竟爱上了文化大汉奸胡兰成并和他先姘居后结婚。她这一行为,不仅使当时正义的人们愤慨,她的舅舅也对她不齿。她的弟弟张子静在《我的姊姊张爱玲》(注:学林出版社1997年出版。)中说:“胡兰成说她‘不会跌倒’,她却为胡兰成跌倒了。”但在张文看来,“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感情瓜葛,从头到尾只是一种私人关系”,与评价张爱玲无关。关于这一问题,老作家何满子先生在《“不以人废言”和“知人论世”》(注:载《文学自由谈》2001年第2期。)一文中批判张爱玲:“一个女人的爱情追求,不要讲识见、志趣、人生选择么?一个甘作卖国贼老婆而且恋恋不舍的货色,其灵魂又是如何?这些都不是生活细节,而是顺逆、是非、美丑的大问题,在知人论世上是通不过的。即使在国外,人家也讲究知人论世,大节上的顺逆是非哪个民族都重视,绝不会像中国某些人这样,向丧失大节的棍徒献玫瑰花而行若无事的。”
再说路易士。此人任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苏北行营上校连络科科长”,代表敌伪对苏北作“文化宣抚”,曾有两次对青年人做长篇讲演,一次是在泰兴县,讲“和平文学与和平运动”,一次是在泰县,讲“大东亚共荣圈下和平文学”。他是应该以汉奸论处的,但却未受到国民党政府的任何惩处,因此我们仍以附逆作家看待之。此人尚有羞耻之心,他到台湾后改名换姓,继续写诗,但绝口不谈路易士的事,假如有人说他是路易士,便要躲避、恼怒,惟恐别人揭穿他的旧时真面目。(注:参见刘心皇的《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诗歌卷把他排在第一位,选收的他的诗作占第一位,共18首。我们认为这样做很不妥。而张文则说,《大系》“所收作品,大体上反映出沦陷区主流文学的特点与成就,具有代表性”。“《大系》在尺度的把握上,是恰当的”。于是,路易士的诗作也成了沦陷区主流文学(即所谓“中国抗战文学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一部分,路易士也成了抗战诗人和世界反法西斯诗人了。
再说苏青。苏青任汪伪上海市政府专员,作为附逆作家,在大江南北,当时是人所共知的。1943年10月她得到陈公博的支持和出钱5万元(在当时相当于50令白报纸)、周佛海老婆杨淑慧出钱2万元的资助后办起了《天地》月刊。她以“胆大”著称,把《论语》中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改了一个标点,变成“饮食男,女之大欲存焉”。她的作品迎合小市民心理,大多畅销,但文学价值不高。学者王一心在《苏青传》(注:学林出版社1999年出版。)中就苏青担任伪市府专员一事写道:“苏青由此衣食无虞了,代价是从此沾上了汉奸的嫌疑。”并明确指出,她“在汉奸支持下创办《天地》”。王一心先生在政治问题上毫不含糊。而张文却又只字不谈苏青的政治上的失节,反而把她抬到与周作人、张爱玲同样的高度,夸大地说:“周作人、张爱玲、苏青已成为90年代以来大多数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内容。”但是,1999年8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却没有写苏青一个字。
评价沦陷区文学而回避政治,不讲民族大义,能做到“政治正确”吗?
要在沦陷区文学研究中产生真正的科学成果,那就得遵循“历史的原则”;绝不能遮蔽“史实”;讲政治,讲民族大义。否则,再怎么“微观”、“细节”、“具体”,也出不了沦陷区文学研究的真正的科学成果的。
标签:文学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周作人论文; 胡兰成论文; 张文论文; 日本侵华战争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日本作家论文; 张爱玲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