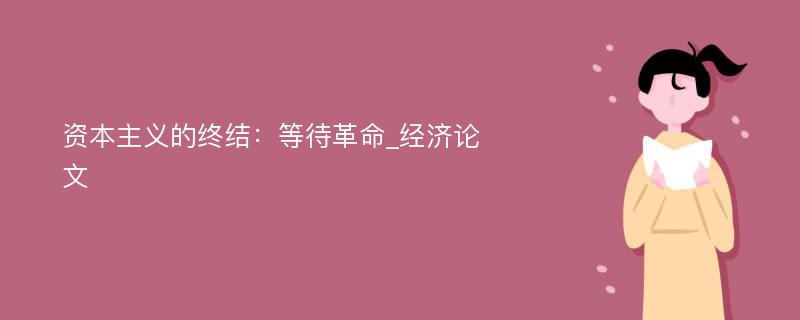
资本主义的终结:等待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61(2001)01-0044 -06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常常为我自己和我周围涌动着的女性主义的东西而感到自豪。这种女性主义重塑了我的社会日常生存环境。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就不能有我每天都在忙于重建的目标?我经历过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哪儿去了?当然,我对社会主义的失落感并不表明女性主义充满活力,而马克思主义就日薄西山。相反,在我所处的学术圈里,马克思主义显然是生机盎然。我相信,这种现象一定同其他某种事实有关。这个事实即:要求马克思主义改革的东西正是那些改不了的东西——这就是我所说的资本主义。
让我从一个稍微不同的角度再来阐述一下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种资本主义话语,这个话语明确勾画了一个变革的阶级政治目标,但是它却更加有力地阻碍和忽略了阶级改造的方案。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马克思主义描述资本主义降临的理论方法,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失落。
此刻,先别急着给资本主义下定义。我只想弄清一些迫使社会主义的(以及其他进步的)变革改变方向的特征。有许多与当今激进主义政治相关的概念,最突出的或许是种族概念、性别概念和性欲概念。资本主义与这些概念不同,资本主义概念(以及阶级概念的延伸,因为在一些不能使用“阶级”这个词的地方,阶级只是一个符号),此刻既不必泛泛之争,也不必重新定义。的确,这里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至少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是这样)——与资本主义这个词相联系的只有一个单一的含义。因此,当我们称美国为资本主义国家时,我们只管叫好了,不用担心什么歧义冲突。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对资本主义的含义有着同样的理解(因为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有多少马克思主义者就有多少资本主义),而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含义并不是广泛再思考和系统再阐述的关键之所在。相反,资本主义这个词常常起一种试金石的作用,发挥暂时过渡性的功能,在这个过渡时期,我们开发马克思主义的共同遗产,形成一种共同的世界观,表明至少我们还没有忘记阶级的存在。
在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语境中,无论是政治主体,还是社会整体,都由各种对立的因素所构成,一直在不停地建造中分化和理论更新,变得开放而没有中心、零散、多元、多声音,其建构既杂乱无章,又是社会性的。但是,资本主义对激进的观念更新具有相对的免疫力。资本主义的近期发展基本上沿袭了传统现代主义思路(如调节论),总的说来,它并未受到后现代主义激进思想的冲击。的确,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动摇和解体,相反更有可能得到赞誉,这些赞誉反过来又加固其稳定的地位。我们不妨把资本主义称作某种“社会宏观结构”、“庞大的统治机构”、“全球经济”或“弹性积累”、“后福特主义”或“消费社会”。资本主义这个词连同形容词使用时,便显得变化自如,如“垄断资本主义”、“全球资本主义”、“后工业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像其他的溢美之辞一样,这些术语很少是由其直接使用者界定的。更确切地说,这些措辞作用在于表达和构成屈服和赞扬兼而有之的复杂心态。因为不管我们是如何的与众不同,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是本质论者还是非本质者,也无论是现代主义者还是后现代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大多数人或多或少得承认,之所以我们显得渺少,是因为我们的生活笼罩于某个庞然大物之下——这个庞然大物就是资本主义,不管是全球资本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面对着这个庞然大物,我们的一切改革举措终归是无足轻重的。
根据一些经济学家,如迈克·阿格里塔、戴维·哈维、欧内斯特·曼德尔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以及众多的社会文化分析家们对资本主义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有许多重要的话语表现形式。我把这些资本主义的话语特征称作“统一性”、“单一性”和“整体性”。这些特征既相互区别(尽管没有哪一个特征真正能够单独存在),又相互联系(因为它们几乎很少出现在一些专业文本中),它们构成的资本主义是一个“不能改革的改革对象”。下面我将依次就资本主义的这三个方面作一番论述。
统一性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概念是随着“自由经济”的产生而产生的。那么就毫不奇怪,资本主义与更为抽象的自由经济一道,具有共同的制度整合特征和自我再生能力(或被再生能力)。资本主义,就像这种自由经济一样,常常被人们描述成一个相互关联的统一体,而不是一套点缀应景的惯例。资本主义代表一种组织或“制度”,通过这一组织或“制度”,社会劳动循环以各种不同形式而流动畅通起来。资本主义由资本积累的活力所推动,沿着某种预定的发展轨迹(尽管并非一帆风顺),按照逻辑或规律来自我调节。
资本主义统一性与有机主义观念相伴随,有时就作为有机主义观念的替代词,常常用建筑学术语来描述。把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社会)当作一栋建筑大厦,在这个建筑大厦里,各个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且“按照建筑学原理,这个建筑大厦的内部结构与外部结构一样重要、看不见的隐蔽工程不亚于看得见的主体工程”(福科:1973 :231)。这种用建筑学或结构学做的比喻明白地体现了资本主义的耐用性、稳定性和持续性特征,也说明了资本主义绝不是昙花一现,而是有着很大的社会现实市场的。
尽管马克思主义常常强调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性和危机性,但是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身就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统一的过程。人们常常这样描述,经济危机起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部位——如劳资关系或者资本积累过程,核心部位一旦爆发危机,常常会辐射四方,引起整个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动荡。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重新巩固或曰复苏,也是整个过程的一个环节。因此,凡是经历过战后时期的人们都可以看到,“长期的繁荣”以“福特主义”危机而终结。这时所有的福特主义“发展模式”都被抛弃了。经过一段时期的动荡和混乱之后,这种泛社会结构就被后福特主义衍生物所替代,使庞大的经济、文化和政治联盟再完善起来。
我的意思是,重要的不在于这些异彩纷呈的社会经济比喻和表象,而在于所有这些比喻和表象都赋予了资本主义完整性。把资本主义描述为建筑大厦和有机整体,说明资本主义并不是零散而没有中心的各种惯例的凑合,而是整体上同全国经济或全球经济有潜在的共同覆盖范围的有结构有系统的统一体。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庞大、耐用的社会形态,一般的政治干预和经济干预是很难动摇的。如果不经过协调一致的艰苦斗争,那么,你只能排斥资本主义,改革资本主义,而不可能取代资本主义。
既然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个统一的制度结构,那么局部的、片面的改革就终归是脆弱无力的。这种局部改革或片面改革的任何努力都将被资本主义以另一种规模或者另一种程度的努力所抵销。可见,如果不控制金融系统,任何企图改变生产方式的举措都是徒劳无益的。由此还可以发现,在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搞社会主义,可能遭到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的颠覆。资本主义不可能被零敲碎打地分化瓦解或逐步取代。对资本主义必须从整体上实行变革,否则,干脆什么也别动它。
因此,资本主义的统一性带来的一个影响就是,给左派提出了一个制度改革的任务。
单一性
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统一性使我们面临着制度改革的艰巨任务,那么资本主义的单一性和整体性就使完成这个任务毫无指望。资本主义基于自身的范畴而存在,没有同类物或对应物:一旦它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形态完全确立之后,就要占据统治地位或者独霸地位。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资本主义表现了自身的单一性。
作为一种经济形态类别,资本主义的确不可类比。无论是奴隶制度、独立的商品生产、封建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原始共产主义以及其他的经济形式都缺乏资本主义的系统性,都无力按照内在规律进行再生产并自我扩张。譬如,社会主义总是要经过努力斗争才能产生,产生之后既脆弱难支又容易变形走样,需要政府的保护和培育。而资本主义却不一样,它的完备是一个内在的自然发展过程。
资本主义的有机统一性是资本主义发展壮大的特有动力,甚至连阶段性爆发的经济危机也成了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而社会主义则没有那么幸运,它从未凭自身的危机孕育出发展的神秘力量;社会主义的再生产从来就不是受内在活力的驱动,而总是来自外在的压力;它从来就不可能主动自我再生产,而总是被动再生产,即便是有这种可能,也常常要经历一个艰苦磨难的过程。
不具备资本主义有机统一性的其他生产方式更有可能被创制、被取代,也更容易和别的经济形式相容共处。相反,资本主义则往往以独立的形式出现。因此,在美国,如果存在封建的或古代的阶级,那也只不过是一些残余形式而已;如果说存在奴隶制度的话,那也是以边缘形式而存在;如果说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话,那它还只是处在萌芽状态。没有哪一种形式真正完全地与资本主义共存。假如真的有资本主义同其他形式共存的地方,也只能是那些没有充分发展的地方(例如,所谓的第三世界,或者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落后地区,而这些地区都被看作是没有充分发展的地方)。与其说它表现了资本主义同非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真正共存,倒不如说这种共存只是标志着第三世界发展的不充分和不完备。根据霸权主义的发展理论,各种各样的非资本主义国家被看作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陪衬“异类”。
资本主义单一排他性观念的影响之一,就是“独石柱”(整体划一)似的阶级观念,至少在论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时是如此。既然资本主义只能容忍一些残余的或者萌芽状态的非资本主义关系,而不能同任何其他生产关系共存,那么,“阶级”这个词通常就是指以资本与劳动为轴线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分裂。这种资本主义独石柱的出现和完备,不但否认现存经济多元化或阶级多层化的可能性,而且也预示着一个人人称同志、阶级无差别的现代化的整体社会主义就要来临。
既然受资本主义排他性的影响,其他那些经济体制和阶级关系势必边缘化,那么资本主义单一性就会起妨碍其他经济体制创立和其他阶级关系形成的作用。既然资本主义不可能共存,那么导致的结果就是,不但排除了其他社会形态存在的现实可能性,而且也排除了其他社会形态存在的将来可能性——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了遥不可及的将来。
整体性
资本主义的第三个特征,也许是大家最熟悉的特征,就是它倾向于把自己表现为社会整体。这点在种种表示兼容并包的比喻中是最明显不过了。有些人本身虽然没有参与资本主义剥削,但很显然,他们或者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的“毛孔里”,或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或者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统治之下。资本主义被当作一个包罗万象的大容器,那么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个体经营的商品生产,或家庭商品生产和服务,在某种程度上就可看作是发生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生产。家庭商品生产作为资本主义“再生产”而隶属于资本主义。甚至社会对立的各个全然不同的行业所遭受的压迫都是在“资本主义整体布局”之内设置的。
相比较而言,资本主义不仅撒的网更广,也更充分地把我们网络到一块。其方法不像是一个强制的过程,倒更像是一个渗透的过程。它浸染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不可能置身于资本主义之外;资本主义没有彼岸(没有逃避资本主义关系的个人或集体生活领地——译者注)。之所以没有彼岸,是因为资本主义吞食了它的存在条件。金融体系、国家政府、国内生产、建造的环境、当作产品的自然、大众传媒——一切的一切都成了资本主义整体性的存在条件,它们似乎丧失了独立自主,丧失了矛盾性——被解读为资本主义非存在条件的矛盾性。我们费劲地把它们一点点条分缕析,例如,从理论上使这个合法“制度”成为一个零散而多样的惯例规则集合体,这个集合体由许多附加于资本主义的事物所构成。但即便如此,资本主义仍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甚至社会主义不主动充当资本主义的矛盾因素,而是充当资本主义的对偶或替换符号,社会主义也还是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就像一块背面大空白的薄膜,一块否定资本主义整体性的社会空间。当社会主义幻想在东欧破灭,资本主义就像瘴气一样到处弥漫。至今我们都成了资本主义者。
我们似乎已经放弃了作为社会改革主轴线的经济决定论和经济主义的阶级观念,结果只不过是再一次把经济奉为神明。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经济名词,被用于每一个社会领域,富有的工业社会以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为其鲜明的特征。一方面,我们从经济回复到社会生活的起点,另一方面,又允许经济打着资本主义旗号去拓殖于整个社会空间。
这就意味着左派不仅面临改革整个经济的革命任务,而且还要取代整个社会。不足为怪的是,尽管认为令人振奋的是非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可以存在,但似乎资本主义却根本就没有余地让非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欣欣向荣、发展壮大。
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法
前面我把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归结为它创立了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学说:相对于经济和社会整体而言,资本主义是统一的而不是零星分散的,是单一的而不是复合多元的,是整体的而不是局部片面的。我不想习惯地把马克思主义本身说成是没有矛盾的——显然,马克思主义种种学说也具有差异,甚至事实上还有矛盾。但是我发现本人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学说有个现存作用问题。在诸如美国这样的一些地方用这种学说谈当代社会主义,简直令人不可想像。我的印象是,马克思主义者没能把我们自身的活动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某种马克思主义学说造成的,按这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说法,资本主义必然导致霸权主义,这是由资本主义的自身特征所决定的(换句话说,即不是由历史过程或偶然事件造成的)。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往往竭力把资本主义的各种暂时过渡特征诠释为假象和谬误。我们撕破资本主义组织系统的整体性外衣。我们抨击那些让资本主义向非经济社会领域渗透扩张的种种伎俩。即使如此,资本主义霸权还是一再地显山露水。譬如,每一次新的分析显然都把经济说成是垄断或独占资本主义。你或许可以去掉资本主义的各种自发性和结构整体性,你或许可以剥夺资本主义那种虚构的难以置信地凌驾于我们社会之上的整体性权力;但是,资本主义本质上仍然是独尔不群。资本主义作为我们生存其中的最大“容器”,却缺乏共处相容性。
尽管资本主义学说五花八门,广泛渗透,但是“如果你想找到事物的不同外貌,却只能是尴尬地空手而归。”也许在这种背景下,摆脱资本主义局限的办法就是倒立起来透过普遍表象看本质。倘若我们理论上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方面,作为众多社会构成因素之一,而不是作为包罗万象的大容器,那会怎么样呢?倘若我们排除那些被纳入到资本主义观念之中的存在条件(如财产法),并赋予它们以矛盾斗争的自由,使之变成一种既是资本主义的也是非资本主义的存在条件,进而变成资本主义消亡的条件,那会怎么样呢?倘若资本主义不是一种根本经济制度,不是一种宏观结构,不是一种生产方式,而仅仅是众多剥削方式之一,那会怎么样呢?倘若经济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不是同质性的而是异质性的,不是铁板一块的而是条块分割的,那会怎么样呢?倘若资本主义是不同惯例的一套组合,这些惯例自由点缀在这种看上去常常是同样(为了方便而违反差异性)的风景画上,那会怎么样呢?要是对个人主观和客观社会之类的范畴进行一番严肃的再思考,以前既有的那种把个人与社会推定为相一致的观念就会出现危机,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对资本主义也提出个一致性危机问题呢?如果我们能,那么,“社会主义目标”自身改革的可能性又如何呢?
问题是我们如何着眼?别把这种独石柱似的和同质性的资本主义看作是我们的“现实”,而要把它看作一个虚拟的整体,一个抹煞经济和社会多样性与非统一性的整体。为了从这点着眼,我们自己恐怕迫切需要对资本主义重新定义。当然,这并非易事!
如果我们撇开统一性、单一性和整体性特点来谈资本主义,我们就只剩下“资本主义”这个普通名词了。要是这样的话,情况会怎样呢?让我们从时下大多数人的话头说起吧。人们感觉资本主义无处不在——造成这个感觉的因素之一就是资本主义对市场的认同。这是一种普遍的认同,不管是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还是在马克思主义范围之外,真是太普遍了。然而,如此多的经济交易都是非市场交易,如此多的货物和服务都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以致于一旦我们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把资本主义与市场界定为同样的覆盖范围,显然就等于把大量的经济活动界定为非资本主义经济活动。
在这一方面,南希·福尔勃(1993)、哈丽雅特·弗拉德(1994)以及其他人所提出的“家庭经济”研究方案,已经绝妙地阐述了我所说的这些资本主义话语(并阐明了曾使我局限其中却又发现不了局限的研究方法)。这些理论家把所谓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庭表示为主要的生产场所,还根据产品价值和参加生产的人数两方面,说明人们不太可能把家庭部门说成是次要的。事实上,有理由说明家庭部门和资本主义部门意义相当,甚至更为重要(当然,参与家庭生产的人数比参与资本主义生产的人数更多)。因此,我们应当设法搞清楚暂时的家庭部门边缘化这么一种复杂的现象,但不能据此就简单地认为家庭经济本身就处在边缘的和残余的地位。
既然我们承认非市场经济交易(无论是来自家庭内部还是家庭外部)在交易中占有相当的份量,并进而认为我们津津乐道的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并不一定整个地或者说绝大部分都是市场经济,那么,也许我们还能在市场上或者在市场背后全面了解市场,从而揭示出其中掩藏的种种情形变化。
市场由来已久,遍布各地,只有具备最最一般的经济性能才能得到开发。如果我们揭开蒙在市场上的面纱,就不难看到在这块面纱底下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在蠢蠢欲动。关键问题不在于“市场”是否抹煞了差别,而在于我们如何区分各种变化情形的潜在特性。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可能并不是商品和劳务的种种交易方式,而是马克思依据剥削方式的不同而描述的经济差异,即剩余劳动的生产、占有和分配的特殊方式,这一点正是马克思所关注的、所要改造的。
在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里,我们都可以发现与商品生产相联系的多种多样的剥削方式,包括个体生产者占有自己剩余劳动的独立的生产方式、占有工人劳动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方式、生产者共同占有剩余劳动的集体或公社方式、以及占有没有人身自由的劳动力剩余劳动的奴隶制剥削方式。如果还没有揭示表面现象底下的本质特征,以上各种阶级剥削方式就都不能被认定是边缘化的。
把所有的经济都称之为“资本主义”,这种说法否认存在着不同经济和不同阶级的变化过程,限制现有经济的多样性,因而也排斥在不远的将来出现经济多元化的可能性。但是倘若我们能够迫使资本主义自愿放弃包罗万象的经济定义的话,那么怎么样呢?我们就会发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经济方式——封建主义的、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独立的商品生产的、奴隶制的,当然还有资本主义的,以及迄今为止还未指明的剥削方式。根据剩余劳动的生产和分配特征来划分出多样性的剥削方式,进而又会导致阶层的多样性,同时也使社会主义阶级改造设想成为可能(这显然是合理的和现实的)。
以上绝不是要否认资本主义的力量或资本主义的普遍性,而只是想质疑对这种力量和普遍性的主观臆断。要在理论上阐述资本主义霸权是否合法合理,就必须在理论上允许非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有充分共存的可能性。只有在这样的理论范围内,才能合理地描述这样的霸权。否则,资本主义霸权就是一种主观臆断,一种政治上的狂妄自大。
结论
创立资本主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目标之一。然而因为众所周知的缘故,资本主义成了我们直接的敌人。这个敌人是一个蒙着意识形态面纱的、朦胧模糊的妖魔。我们已经揭露了它的本来面目。但是,我们又摆上了一个赤裸裸的棱角分明的妖魔。作为对我们创造性劳动的报应,这个妖魔剥夺了我们全部的力量。我们听说,也不难相信,左派陷入了一派混乱之中。
造成左派混乱的部分原因是左派所一致攻击的目标的虚幻。当资本主义被描述成与国家、乃至与世界覆盖范围相同的统一制度时,当它被描述为把所有其他的经济形式排除在外的一种制度时,当允许它规范整个社会时,资本主义就变成了某种只能是被群众性的集体运动(或者被这样一种运动所支持的系统解决过程)所打败和所取代的东西。取代资本主义的革命任务现在似乎是过时了和不现实。然而,我们似乎还没有一个阶级改革的替代概念。以往那种政治经济“制度”和“组织”观念激发系统替代的革命幻想,现在似乎依然占据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念的主流。
世界新秩序常常被描述成建筑在经济一体化基础上的政治断裂。根据这个观点,在一个多样化和多元化的世界里,经济似乎成了统一性和单一性的最后支柱。但难道经济就只能铁板一块吗?如果我们从理论上解剖一下美国经济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美国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国有部门(蕴涵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分配形式)、一个巨大的以家庭为基础自食其力的小生产者部门(大多数是非资本主义),一个巨大的家庭经济部门(这里有各种剥削形式,有些家庭倾向于公共的或集体的分配,有些则以一个成年人占有另一个成年人的剩余劳动的传统模式进行操作),从理论上把上述任何一种形式推导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逻辑结果,谈何容易!?
如果资本主义占据全部有用的社会空间,那么别的任何形式也就没有了存在的空间;如果资本主义不能够共存,那么别的形式就没有存在的可能性;如果资本主义经济大了,其他经济就显得小了、微不足道了;如果资本主义充当统一体,它就不可能被部分地或局部地取代。我的意思是,要有助于创造各种过渡条件,使社会主义或别的非资本主义建设成为“现实可行的”现实行动,而不是荒谬的或乌托邦式的未来理想。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把资本主义碎尸万段,彻底解剖,必须揭露资本主义统一性(作为否认多样性和变迁性的工具)的虚幻性。
即使不存在资本主义,我们仍可以提出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政治目标。或许我们可以把一些改革精力集中于剥削和剩余分配上面去。因为剥削和剩余分配时时处处以这么多形式出现、而且我们以各种方式参与其中。在家庭中,在称之为工厂的地方,在社区,我们所有的人几乎每天都在进行剩余劳动的生产、占有和分配。马克思清楚地揭示了这些过程,但是在资本主义学说里,它们变得十分模糊,因为这个学说的视野被锁定在数百年来的两大对立阶级的斗争中。无论这个学说是如何地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它还是没料想到有多种多样剥削和分配形式的存在,也没料想到可能对形成阶级地位和阶级意识起作用的这些活动过程也存在多样性。
如果可以把我们的阶级观念同系统的社会观念相分离,同时也把我们的阶级改造观念和系统的改革目标相区别,那么局部的和最近的社会主义就指日可待了。如果把社会主义定义为共同生产、共同占有和共同分配剩余劳动的话,那么,我们无论在家里还是在上班,到处都能遇到社会主义,随意都能建设社会主义。这些“轻描淡写”的社会主义自然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以某种整体剧变的形式重塑我们的社会。但是,它们却可以一天一天地构筑和重建我们的社会。诚然,它们不可能是堆积在资本主义门槛上的我们想要包治百病的万灵药,但它们却是现在就可以看得见的、并能重复再生的社会主义。
超越资本主义学说,誓与资本主义权力决裂,以及摆脱已经妨碍社会主义运动的羁绊,这并不是要超越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说得更形象一点,这是为了把马克思主义从一种婚姻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因为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婚姻有许多,而且问题百出。当然,以整体主义和自我维系的形式与“经济”结合的这种婚姻,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已经产生了一代健康的血统,促成了广泛的政治运动,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现在,我要说这种婚姻不再富有成果,或者更准确地说,它近来的后代是脆弱的怪胎。终结这场婚姻的理由数不胜数——尽管我没有描绘,我想判定它的终结,它的终结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终结,我提醒自己并敦促他人,切不可把两者混为一谈。因为马克思主义指引我们思考剥削,而剥削还没有终结。
(本文编译自吉布森·格雷汉姆《资本主义的终结:等待革命》第11章,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95 年版, 中译本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本文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发表)
标签: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经济学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政治社会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