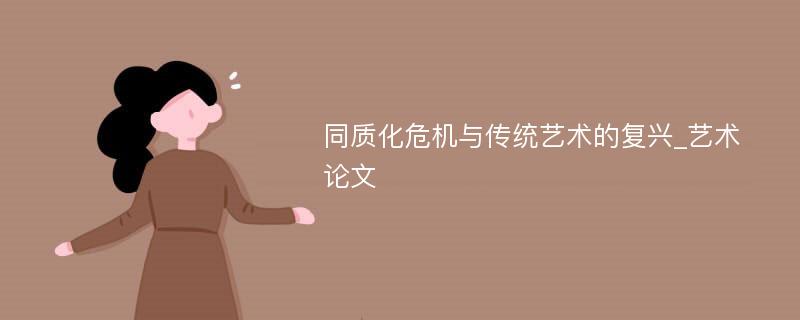
同质化危机与传统艺术的再生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同质论文,危机论文,艺术论文,与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03)03-101-06
一
研究当代任何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传统中的艺术时所不可回避的现实就是被称为“全球化”现象的文化趋同问题。其实全球化是一个充满歧义甚至矛盾的概念。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自十字军东征之后开始的资本主义与近代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就是全球化的开始。对中国而言,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入侵,则是中国被迫卷人文化全球化过程的开端。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全球化观念,不过是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过程在近年来所形成的一种新的形态。
全球化作为一种文化发展趋势而言,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全世界不同文化发展中的趋同,即向具有普适性的方向发展——从普适性价值观念的形成到生活方式、审美趣味等各方面文化特征的可交流性和相似性越来越突出。
黑格尔在自己的历史逻辑观念中设想了历史发展的终结,即随着绝对精神的彻底复归而到达文化发展的终极状态;沿着他设定的三段式逻辑过程发展的人类文明便走到了最高也是最后的阶段。这就是历史终结观念。他的观点在19世纪听起来不过是痴人说梦。到了20世纪末,人们却惊讶地发现了一种历史终结的可能——由于世界文化的交融发展而造成普适性特征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导致了文化同一性趋势的发展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多样性的萎缩,即不同文化形态在发展中走向了“同质化”(homogenization)。过去的世界历史所展示的不同形态文化的独立演变过程因此而告终结。
世界文化的普遍化发展趋势,曾经是18世纪具有世界主义倾向的理性启蒙主义者们所期待的历史发展前景。在理性主义看来,世界文化的趋同是理性的要求。所以莱布尼兹会产生发明“万能算学”来解决人类一切纠纷的想法,歌德会提出“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到来”的乐观预言。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的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把西方文明推向全世界,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同质化真的开始变成了现实。
20世纪初艺术趣味的发展也同整个文化趋势一样存在着走向同质化的趋势。随着现代技术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当代大众艺术突出地表现出这种趋势:好莱坞用巨额资金制作的“大片”、电视中的肥皂剧、脱口秀和综艺节目、不停地涌出的流行歌手和歌曲等等,这些艺术活动尽管一直在想方设法花样翻新,却越来越使人难以找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特色。走遍全世界,到处是好莱坞、麦当劳、摇滚乐和可口可乐的广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和不同的文化社区,相互之间变得越来越相似了。作为精英文化的现代主义艺术虽然是提倡个性而反对大众文化的趋同性的,实际上同样走向了同质化。从艺术活动和审美趣味的发展来看,以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构成主义等激进的艺术流派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思潮崇尚速度、材料、技术和对传统的破坏,这一切曾经给艺术带来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新鲜感,让人觉得现代主义艺术似乎比古典、封闭的传统文化和趣味更富有活力、更有个性也更丰富多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表面上的眼花缭乱就越来越显现出背后深藏着的趋同倾向来:从工艺革命发展起来的“国际风格”建筑虽然是反传统的和不拘一格的,然而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之后,却令人感到这种现代风格对材料和技术的关注抹杀了文化差异,因此而形成的那种所谓的个性差别,都被淹没在对相似的材料、技术和空间感的追求所造成的同质化效果中了。从毕加索的立体派以来走向抽象化的现代主义艺术虽然给人的感觉是新奇怪异,但看多了就会发现,主观化、抽象化的形式由于剥离了传统造成的文化差异和独特性,反而失去了可以辨认的区别性特征——蒙德里安的长方形格子,康定斯基的圆、角和线条,波洛克弯弯曲曲的墨渍,克莱因用板刷涂成的大黑块……虽然我们可以说他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有个性的,但从整体上看过去给人的印象是什么呢?有人说抽象派不过是画了些好看的窗帘布,也就是说那些花样翻新的图形本身已失去了吸引知觉注意和记忆的审美效果,只给人留下了花花绿绿的相似的装饰感。我们站在20世纪初欧洲的达达主义作品和80年代中国的“新”达达主义作品面前,看到的虽然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然而却又是无法区分的同样的乱七八糟——不过是把毕加索用的自行车把手换成了车铃和车锁、把杜尚用的瓷尿斗换成了生锈的水龙头;行为艺术则由光着身子涂墨渍换成了光着身子钻死牛肚子……现代主义的标新立异似乎变成了千篇一律的涂鸦;或者换一种说法,现代主义反传统努力的最后结果是取消了可辨认、可传播的作品,只有转瞬即逝的、不可捉摸的偶然意图。这种同质化对艺术风格的影响至今仍然可见。当我们站在上海外滩向浦东望去,那些五花八门的现代建筑说起来应该算是风格各异了,但从整体看上去仍然不过是相似的材料质感、相似的体量追求和相似的几何形式理念制作成的形状不同的积木而已。
在现代趣味最初带来的新鲜感和狂喜过后,人们正在被各种文化的趋同所困扰。这种越来越趋同、越来越相似的趋势带来的是不同文化变得同质化、单调化的焦虑。这种同质化焦虑与文化全球化的趋势紧密地伴随着,成为当代艺术发展前景中一道灰暗的天际线。
二
对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同质化问题,批评最激烈的是一种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观点,即所谓“文化帝国主义”或“后殖民主义”观点。简单地说,这种文化批判观点把上面所说的文化问题理解为意识形态问题,或者更直接地说,认为文化的同质化是“强势文明”即西方文化的历史阴谋,是企图把其它文明形态都殖民化的结果。对这种历史阴谋的警觉和反抗表现为颠覆西方中心的后现代主义意识以及形形色色的文化相对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国粹主义意识。
这种意识形态批评观念具有一种主观化倾向,就是把客观历史活动从政治动机的角度进行心理化、拟人化的解释。这样的主观解释有助于造成对“强势文明”的敌视心态,却不一定有助于研究和理解当代文化的现实发展逻辑。毕竟,从内在动机的角度研究历史,多多少少带有臆测和诛心的味道,更像政治斗争策略而不大像学术研究。
如果不从揣测政治动机的暧昧角度,而从历史的发展过程和结果来研究和认识当代艺术的同质化问题,可能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就有所不同了。就拿人们最常用来作为文化殖民典型的好莱坞来说,这种电影文化虽然被批判者视为美国文化霸权的代表,而且它作为产业也的确给美国人带来了丰厚的收益。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它所体现的文化特征和价值观念并不一定真正是美国式的。人们熟知的好莱坞电影特征——豪华的场面、逼真的效果、紧张的情节节奏和令人神往的明星风采等等,这些东西尽管是好莱坞电影所长,却很难说就是美国文化的特征。好莱坞所创造的这种电影趣味并不是美国特有的和通过某种策略灌输到其它文化中的东西,或者用我们所熟悉的说法,是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事实上,这是不需要文化中介便可以被当代任何一种文化所接受的普适性趣味。我们甚至可以在与美国文化处于完全敌对状态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电影中找到上述的类似好莱坞风格的东西。至于好莱坞电影中表现的美国文化特有的价值观念,却往往反而会被其他文化所忽略或误读。比如在中国,人们会很容易地把好莱坞政治影片中对小人物英雄主义的表现误读为是在“揭露资本主义的腐朽黑暗”。好莱坞电影的发展趋势与其说是在强化美国特色的文化与价值观念,不如说是在通过越来越高的投资和越来越先进的科技手段制造着对每个文化中的人们具有普遍吸引力的感性效果。好莱坞向全世界的扩张主要不是在传播一种特殊的文化,而是在发展对世界各个民族具有普适性的艺术趣味。
好莱坞电影在世界电影文化的发展中是在制造着一种同质化趣味,但它所制造的这种电影趣味的同质化不是把各国文化都变成了美国文化,而是把包括美国文化在内的各种传统文化都引向作为高技术产物的视听幻觉文化。如果读过美国当代作家的批判性作品,如索尔·贝娄的小说《洪堡的礼物》、《赛姆勒先生的行星》等,就会发现我们作为边缘文化或弱势文化被所谓美国的“后殖民主义”文化同化的焦虑,在美国知识分子中同样存在着。他们当然不是被美国文化霸权所殖民的弱势文化的代表,而恰恰是典型的传统美国文化的代表。他们的焦虑说明当代世界文化的同质化不是简单地被美国文化殖民,而是一种新的普适文化趋势的作用结果。
同质化的问题比文化批评家所焦虑的跨国资本意识形态阴谋更复杂得多。20世纪初的中国文化精英们发起了改造中国文化、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所倡导的新文化,基本精神就是“科学”和“民主”。这是由西方18世纪以来的启蒙主义思想带来的关于文化发展方向的启示。然而也正是以实证和理性为基础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民主”的价值观,无形中影响着20世纪世界文化发展中的同质化倾向。无论是莱布尼兹的“万能算学”、康德的先验判断、歌德的世界文学还是黑格尔的绝对理性,都潜含着对文化同质化前景的期待。换句话说,理性主义者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就是一个建立在共同判断能力和共同价值观念基础上的同质化的理性乌托邦。
从现代艺术的发展趋势来看,20世纪初兴起的现代艺术潮流是以科技的发展和平民化、民主化社会理想为根据的。技术的发展毫无疑问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难道有谁能设想,今后的科技发展会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芯片技术或日耳曼民族习惯的生物工程?普适化的民主社会理想也同样具有同质化含义。康有为提出的世界大同的概念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文化同质化理想。新文化运动的理念中用先进与落后来描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时,“先进性”或“现代性”的观念的基本内涵就是西方启蒙主义时代以来形成的科学和民主精神。这样的文化观念也就意味着一种普适性的、也就是趋向同质化了的文化理想。20世纪初发源于欧洲的工艺革命思潮就是这样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和民主社会理想基础上的现代艺术精神的代表。现代主义艺术精神中最激进的未来主义则这样宣言:
我们走在时代的最前方……当我们必须打破那遏止我们成为万能者的神秘大门的时候,回顾过去有什么用呢?时间和空间都已经在昨天死去了。今天我们生活在绝对之中,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个永恒的普遍的速度。
在这段张狂的叫嚣中,未来主义明确地表达了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信念:由工业和技术开创的现代文化和现代艺术精神意味着对传统的彻底否定,意味着摆脱了历史性和个别性的永恒和绝对,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文化和艺术精神走向终极的同质化。
总之,同质化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侵略和文化殖民的“阴谋”,而是近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普遍历史趋势和理想。我们可以因为这种同质化的趋势是我们向西方、而不是西方向我们的价值标准靠拢而感到不快甚至失落,但却无法因此而否定这种趋势的历史性,除非我们把现代科技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交流统统拒绝。艺术文化也是如此,当艺术的创作、传播、接受和教育融入到逐渐同质化了的当代技术和当代生活方式构造起来的文化环境中时,艺术手段、形式、趣味乃至观念的发展也便在不知不觉中走上了同质化的道路。
由于技术发展的普遍性和社会交流形成的价值观念的普适性发展,同质化似乎是必然的趋势。这是一种进化论式的文化发展观。按照这种观念,文化的发展是新旧更替的过程,最新的便是最好的,旧的意味着落后的和过时的,是趋于灭亡的和应当被淘汰的东西。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一直就怀着这样的信念——火炮淘汰了刀剑、汽车淘汰了马车、西装革履淘汰了长袍马褂……照此类推,所有过去的东西都将被新的东西所取代——话本和戏曲被小说和电影取代、小说和电影再被杂志和电视取代、杂志和电视或许再被互联网或什么更新的东西取代;传统绘画被照片取代、照片再被电脑合成的图像取代……当我们站在百年来建设起来的现代城市中环顾四周黑压压林立的摩天大楼时,当我们从大街上走过看到触目皆是的广告图像、听到大同小异的流行歌曲时,或者漫步在艺术长廊中浏览一个世纪中先锋艺术家们制造的无数千奇百怪而又似曾相识的怪物时,就会发觉曾经作为文化和艺术理想的现代精神真的好像进入了千篇一律的死胡同。把传统文化所形成的差异当作落后性清除掉之后,剩下的所谓进化的、先进的东西变成了单调的同质化的东西。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终结和艺术的终结时代似乎已经来到了。
三
进化论的艺术发展观念似乎正在把当代艺术引进死胡同。国粹主义振兴和张扬传统艺术的努力因此而发展了起来。从中国近二十多年来文化和艺术趣味发展演变的历史来看,向传统的、民族文化的回归似乎也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发展趋势。
就拿餐饮习惯来说,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陆社会思潮曾经有一种很强烈的以“现代化”为标志的趋同性,西方的、晚出的、技术上先进的基本上就是“现代化”概念的主要内容,西餐、咖啡甚至麦当劳之类的美国式快餐都成为象征着先进的时尚,以至于在相声中讽刺的奢侈享受就是吃麦当劳、行贿则是送“雀巢”咖啡。然而到了90年代以后,餐饮的风尚好像又倒退了回去:麦当劳、“雀巢”咖啡变成了普通消费品不说,无论高档餐饮还是流行时尚,西式趣味的东西都失去了大部分地盘,倒是粤菜、川菜、宁波菜、上海菜乃至东北的“酸菜”等形形色色的本民族特色饮食反过来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产生这一显著变化的原因就在于形成饮食趣味的文化根据。尽管麦当劳之类美式快餐的干净、效率、营养等经营理念的先进性对中国饮食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但口味却是长期文化生成过程的产物,因而最终还是压倒了“现代化”饮食的影响力。
看起来这个例子可以成为国粹主义的绝好例证来说明回归传统的重要性。然而这样做可能只是导致了另外一种偏激的理解。我们应当注意到的是,90年代餐饮习惯转向本国传统,并非饮食文化的真正国粹主义式回归。稍微回忆一下就会想起来,在麦当劳进入中国之前,中国人的餐饮习惯是被地域高度限制的单调饮食习惯,而不是如今我们所知道的各种各样口味的鉴赏。如今人们在全中国的随便哪个大城市里,哪怕是在世界屋脊上的拉萨,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挑选广东的生猛海鲜、四川的麻辣火锅、东北的拉皮、西北的拉面、北京的烤鸭、南京的盐水鸭等等。但这已不是麦当劳进人中国之前的中式饮食文化了。过去的中餐是地域性的饮食习惯,而如今的餐饮业所发展的中餐是跨地域的商业性的消费文化;过去既没有如今这么多可供平民任意选择的不同口味样式,也没有当今的餐饮业在卫生、效率、形象乃至仪式等方面的特点。这些显然是受到当代信息传播和消费文化、尤其是美国式饮食文化影响而重新生成的特征。
从餐饮的例子可以看出,一方面,当代文化的同质化发展只是一种暂时、表面的时尚性特征,归根到底不同文化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形成了自身存在的内在根据,这种内在根据仍然制约着当代文化的相互融合和全球化趋势。然而另一方面,文化发展的共同趋势也在影响着文化传统在当今现实中的发展,使之从自我轴心的发展中解脱出来,因受到普遍发展趋势的影响而具有了可交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所说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种说法,只有在当民族传统在世界共同趋势影响下被改造和重新生成时才可能成立。
当今的艺术发展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即怎样从进化论式的所谓“现代性”艺术思维和艺术活动造成的同质化中解脱出来,走向更富于生气的多元化发展。回归传统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早已被国粹主义者提出。然而我们怎么能相信可以通过背诵唐诗、振兴京剧、抢救“二人转”之类的方式来抵消好莱坞、摇滚乐和周星驰的影响,改变当代人们的趣味和时尚呢?
老实说,想通过复兴古典艺术来改变当代人的趣味和时尚,肯定是做不到的。然而通过对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的重新认识、发现和再生成,可以使当代人从“现代性”造成的趣味和心灵的单调枯涸状态中苏醒。上世纪80年代,刘索拉的小说《你别无选择》中描写了一群充满现代反叛情绪的音乐学院学生心灵的焦灼:他们想要从传统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却除了混乱和无所适从外什么也找不到。假如我们把刘索拉的故事当作一种纪实性质的叙述大概和历史实际相差不了多少。80年代中国的音乐学院学生中的确涌现出了一拨激进的先锋音乐家,他们所进行的五花八门的现代主义实验与当时的先锋画家、后朦胧诗人、新潮小说家在追逐彻底的反叛性和“现代性”方面的确是异曲同工。有意思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音乐先锋中的佼佼者如谭盾、叶小钢等人,他们的艺术创作理念中却越来越多地与传统的、古老的音乐素材和乐器结了缘。埙、磬、尺八之类的古乐器和它们那种古朴的音色成了现代音乐家们灵感的触媒,并造就了一些新奇诡异的音乐经验。
谭盾叶小钢们并非绝无仅有的例外。其实从90年代以来,从艺术到日常生活,对传统的古老的文化遗产的重新关注、欣赏或模仿已成了新的时髦。除去被急功近利的商业意图搞得不伦不类的假古董外,这种怀古潮流基本上反映出了人们对单调的、同质化的现代性的不满。怀古实际上并没有把人们的审美趣味拉回到过去,而是把传统通过重新发现和创造而使之再次生成活生生的文化现实,从而使现代艺术趣味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传统的重新发现和再生成,同一般意义上的复古主义或国粹主义不是相同的观念。区别在于前者不是恢复过去的趣味和价值观念,而是重新激活艺术发展的历史过程。谭盾叶小钢音乐作品中的古乐器音色、张艺谋电影中古老粗朴的民俗、陈忠实小说中的旧家族文化、张承志笔下那种仿佛来自远古的牧歌,还有罗中立那幅脸上刻着无数世纪皱纹的油画《父亲》……这些东西不大像我们所熟悉的历史和古典艺术,却又都带着古老的文化遗留下来的韵味。除去这些充满个人创意的奇思异想之作不谈,即使是用一架仿制的编钟演奏《春江花月夜》,那种古雅、深沉而壮阔的效果也是我们所熟知的中国古典乐曲所从未有过的。面对着这样的艺术我们甚至不能确定:这些东西到底该算作创新还是复古?
我们过去所熟悉的传统艺术,准确地说应该被称作“古典艺术”。这个概念的意思是说,它们不仅是过去的文化遗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是经过历史的淘汰选择、经过一代代人的反复加工、修改和阐释后形成的文化凝聚物。所谓“古典”就意味着它们作为历史文化的凝聚,具有了无可争议的恒定价值。然而也正是这个恒定价值使得古典艺术原有的活力衰萎了,逐渐固化而变成了审美历史的标本。现代主义对古典的反叛,从根本上说就是对那种遏制生命活力的恒定性的反叛。当黑格尔认为艺术已终结、未来主义者们宣布“时间和空间都已经在昨天死去了”的时候,他们所意识到的“终结的”或“死去的”艺术就是那种已完成并固化了的古典艺术。
然而古典艺术的固化并不等于艺术发展历史的固化。古典艺术是艺术发展的结果,但结果的产生并不一定意味着发展过程的结束和消亡。实际上一代代艺术发展的活力不仅存在于完成了的古典艺术中,更存在于使古典艺术得以完成的艺术文化活动过程中。那些存在于古典艺术背后的、被称作古风的、古朴的或民间的艺术活动,是古典艺术生成的土壤,也是艺术发展的生命力所在。当我们在树立古典艺术的价值和审美标准时,那些生机勃勃的土壤被剥离了。然而当现代主义推翻了古典艺术的地位之后,被湮没的艺术传统才重新被发现。不同于古典艺术的那些原始的、粗野的、怪异的、稚拙的和神秘的民间趣味的艺术,成为当代艺术家灵感的源泉。这些被重新发现、重新阐释和重新生成的传统艺术精神,给当代艺术的发展赋予了个性差异和多元性,因而成为与同质化趋势相抗衡的力量。
收稿日期:2003-06-24
标签:艺术论文; 同质化论文; 古典艺术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全球化论文; 古典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