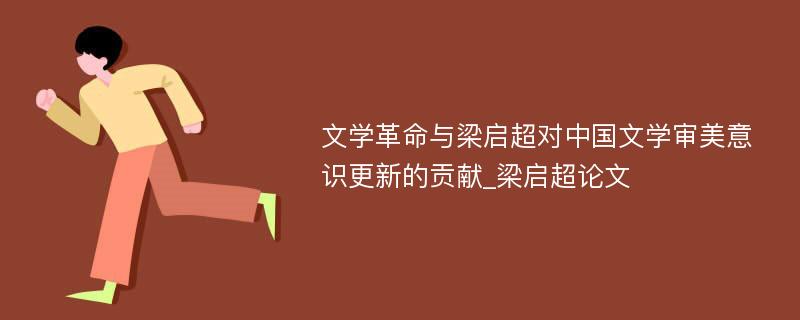
文学革命与梁启超对中国文学审美意识更新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革命论文,中国文学论文,贡献论文,意识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03)03-0061-06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改良派把目光由皇帝转向民众,把主要精力由政治改革转向思想启蒙,从而启动了以文学改革为载体的近代文学革命。文学革命的目标就是通过文学变革来传输西方新思想,促成广泛的思想启蒙。其实,从文化本身的发展演化来看,所谓的革命,更准确地说应为革新。以梁启超等为代表的文学革命的领军人物使用“革命”一词,目的是为了强调文学变革的迫切性必要性,以在最短时间内最大程度上警醒世人。文学革命在配合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体现了文学自身新旧嬗变的历史要求。作为文学革命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梁启超的贡献主要在于理论上的创构与开拓。其理论倡导在客观上体现了新的文体审美理想与文学审美意识的萌生,是中国文学审美理念更新的重要阶梯。本文拟从文学革命的主要冲击对象诗、文与小说三者入手,探讨梁启超对于新的文学审美意识的建树及其理论史意义。
一
诗文一向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正宗,也首当其冲成为近代文学革命运动首先冲击的对象。关于“诗界革命”的构想与酝酿,最早可溯至黄遵宪。1868年,黄遵宪提出了“我手写我口”的诗歌创新主张。他在《杂感》五首之二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烂斑。”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认为黄遵宪的这些文字表明了“诗界革命”的动机,“可以算是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诗界革命”口号的正式提出,则见于梁启超1899年所写《夏威夷游记》。(注:1899年12月25日,梁启超由日本赴美国檀香山,他在轮船上写了一段随笔式的文字,最初题为《汗漫录》,发表于议报》,后作为《夏威夷游记》的一部分收入《饮冰室合集》。“诗界革命”的口号在这段文字中正式提出。)在文中,梁启超首先针对当时正统诗坛的拟古复古逆流,作了尖锐的批判:“诗之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余尝戏名词章家为鹦鹉名士自觉过于尖刻)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1]同时,他也分析总结了“新派诗”、“新学之诗”的经验教训。在批判总结的基础上,梁启超对新诗的前景作了展望,并正式发出了“诗界革命”的号召:“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即麦哲伦)然后可。……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虽然,诗运无绝之时也。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伦布玛赛郎之出世必不远矣。”梁启超还具体地提出了关于新诗的审美理想:“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若三者具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新意境”、“新语句”、“古人之风格”“三长”具备是梁启超“诗界革命”的基本纲领,也是梁启超诗歌审美的基本理想。在稍后的《饮冰室诗话》中,梁启超对“诗界革命”的主张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他指出:“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强调了“诗界革命”的关键在于诗歌精神的变革。按照对于新诗诗美的理解,梁启超对近代诗人的创作与作品进行了具体的鉴赏与批评。他最推崇的近代诗人是黄遵宪与谭嗣同。他认为“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公度之诗,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他最为欣赏黄遵宪的《出军歌》,认为古代斯巴达人在作战时以军歌鼓舞士气,战胜敌人;中国人无尚武精神,原因之一就是没有雄壮的军歌。读黄遵宪的《出军歌四章》,令梁启超“狂喜”:“其精神之雄壮活泼沉浑深远不必论,即文藻亦二千年来所未有也,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矣。吾为一言而蔽之曰:读此诗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梁启超对谭嗣同的人品与诗歌也倍加赞赏:“谭浏阳(谭嗣同为浏阳人)志节学行思想,为我中国二十世纪开幕第一人,不待言矣。其诗亦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
综观梁启超对诗界革命的构想与批评实践,其关于新诗诗美的逻辑建构主要有这样几个层面:(一)、诗歌改革的根本在于精神的变革。(二)、精神变革在作品中的体现是“新意境”的创造。(三)、新意境的表现离不开“新语句”,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四)、新意境在形式风格上应符合国人的审美传统。按照这样的标准,新意境在新诗中占有核心地位。新意就是诗歌作品所表现出的与旧的传统诗歌不同的思想意蕴,实际上就是梁启超所推崇的资产阶级新思想,即“欧洲之真精神”。梁启超要求新的诗歌表现“欧洲之真精神”,走通俗化的道路,为宣传普及新思想服务。这种审美理念不仅是对晚清以来传统诗坛没落诗风的批判,也是对几千年中国传统诗歌观念的冲击。中国是诗的国度。但诗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形态,主要以“雅”作为自己的审美理想,崇尚的是温柔敦厚的诗教与含蓄蕴藉的诗美。它融含的是士的人格精神与自我意识。精美、凝练,重表现,重意境,是士道德自省的载体,是士自我赏玩的对象。这样的诗美理念必然轻视诗歌的认知价值与社会功能。梁启超对新诗之美的构想,首先就在于新诗构造新意境、表现新精神的功能。他把对外部新世界的认知与反映作为诗歌艺术思维的中心,从而将传统诗歌的表现与内省转向再现与观世,体现了对诗歌的阳刚之美和社会功能的呼唤。在《饮冰室诗话》中,梁启超表达了与旧“词章家”的决绝态度:“至于今日,而诗、词、曲三者皆陈设之古玩,而词章家真社会之虱矣。”要求诗歌由“雅”入“俗”、由“陈设之古玩”变为“新民”之工具,鲜明地体现了“诗界革命”的革命性。当然,梁启超的诗美构想也有它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喜新恋旧、新旧参半的过渡心态。在《诗话》中,梁启超对“诗界革命”还作了这样的解读:“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这段话强调了“诗界革命”不在形式,而在内质;但这种新的内质可以也应该通过旧风格来表现。按照这段话,新诗最终只能是新内容与旧形式的统一。这样的诗歌美学理想,既是梁启超自身的局限,也是整个时代文化环境的制约。实际上,在“诗界革命”时期,除了西方新名词的引进外,西方新精神的具体内涵究竟是什么,西方诗歌的形式规律又是怎样,都还是较为朦胧的。1902年,梁启超曾用“曲本”形式翻译拜伦的《哀希腊》。1905年,马君武用歌行体来译《哀希腊》。1914年,胡适用骚体诗来译《哀希腊》。他们对西方诗歌自身的形式均视而不见,或者说难以顾及。真正冲破传统诗歌的形式与风格特征,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
梁启超的“诗界革命”理论与新诗美学构想未能全面完成现代白话新诗的理论建构。但是,它所体现出来的新的诗美意识已经冲击了传统诗歌的根基,预示着20世纪与整个时代紧密相联的新的文学审美意识的破土。
二
在“诗界革命”倡导的同时,梁启超也注意到了“文界革命”的问题。“文界革命”的提法,最早见于《夏威夷游记》。1899年12月28日,梁启超在由日赴美的轮船上读了随身携带的日本政论家德富苏峰的文章,深受启发。他在日记中写道:“读德富苏峰所著《将来之日本》及《国民丛书》数种。德富氏为日本三大新闻主笔之一,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开一别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这是梁启超首次提及“文界革命”的设想,他的目标还是较为笼统的。1902年,梁启超再一次发出了“文界革命”的呼号。他把目标直接对准了以严复为代表的艰深雅涩的文言散文。严复是中国译介西方人文科学著作的第一代翻译家。1902年2月,《新民从报》创刊号上即开辟了“绍介新著”栏,刊登了严复译《原富》。梁启超同期发表了评《原富》译本的书评,一方面称赞译本“精善”,另一方面也指出译本“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梁启超认为:“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他指出:“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比例。况此等学理邃赜之书,非以流畅悦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僮受其益乎?”基于以上认识,梁启超发出了“文界之宜革命久矣”的呼声,再创“文界革命”。但严复对梁启超的批评不服,写了《与梁启超书》(注:载《新民从报》,1902年7号。)与之论辩。严复认为:“若徒为近俗之词,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凌迟,非革命也。且不佞之所以从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使其目未睹中国之古书,而欲稗贩吾译者,此其过在读者,而译者不任受责也。”梁启超与严复的这场论争体现的是对著述的两种不同立场与态度,看起来是对为文问题的争论,实质上隐含的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面对风云变幻的社会现实所把持的人生指向与价值态度的论争。严复体现的是传统士大夫的价值理念,追求文字之雅与个人声誉,希望文章能传之千古。梁启超则认为写作应从大众需求出发,特别是在当时的现实下,应有“思易天下之心”,“求振动已冻之脑官”。梁启超关于“文界革命”的主张得到了黄遵宪等人的热烈呼应。实际上,早在1897年,梁启超就对自己为文的宗旨及风格作过精辟的概括。他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说:“学者以觉天下为任,则文未能舍弃也。传世之文,或务渊懿古茂,或务沉博绝丽,或务瑰奇奥诡,无之不可。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也。”这段话体现了梁启超对为文的两种不同追求与文体风格的清醒认识。“觉世之文”“应于时势”,“救一时,明一义”,随时变迁,转瞬即逝。对这一点,梁启超并非没有意识到。他在《〈饮冰室文集〉自序》中指出:“吾辈之为文,岂其欲藏之名山,俟诸百世之后也。应于时势,发其胸中之所欲言,时势逝而不留者也。”但他又认为:即使“泰西鸿哲之著述”,“过其时,则以覆瓿焉可也”,因为“今日天下大局日接日急,如转巨石于危崖。变异之速,非翼可喻。今日一年之变,率视前此一世纪犹或过之。故今日之为文,只能以被之报章,供一岁数月之遒铎而已。”他豪迈地宣称:“若鄙人者,无藏山传世之志,行吾心之所安,固靡所云悔。”可见梁启超的“文界革命”,最主要的是变革为文的意识,是将著书立说直接推上近代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之中,要求文人志士以自觉的历史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来从事写作活动,把启蒙宣传与社会效果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这样的认识,相对于近代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来说,积极意义远远超过了负面影响。梁启超身体力行,积极创作与古板僵化的传统散文风格迥异的新体散文。他在《新民从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杂文、演说辞、人物传记等。这些新体散文有这样几个特点:(一)、以“俗语文体”写“欧西文思”,文字平易畅达,通俗易懂。(二)、文中杂以俚语、韵语、外来词汇、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三)、条理明晰。(四)、文风生动、活泼、新鲜,笔锋常带感情。这些散文引起了巨大反响,时人纷纷仿效之。梁启超自谓:“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这些散文在当时号称“新文体”。“新文体”的实质是要解放散文,打破旧散文形式主义的种种束缚,以通俗而富有感染力的文字来传播新思想,打动广大读者。(注:梁启超在倡导“三界革命”的同时,也身体力行,进行文学创作实践。小说昙花一现,诗歌成绩平平,散文成就突出。黄宪认为梁启超的“新文体”散文“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矣”。梁启超的学生吴其昌则对梁启超的“新文体”曰评价:“雷鸣怒吼,恣睢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魄,时或哀感曼鸣,长歌代哭,湘兰汉月,血沸神销,以饱带感情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此非阿谀,惟有梁启超之文如此耳!……就文体的改革的功绩论,经梁启超十六年来洗涤与扫荡,新文体(或名报章体)的体制、风格,乃完全确立。”“新文体”不仅开创了一代文风,还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思想。胡适、鲁迅、郭沫若,甚至毛泽东都谈到过“新文体”对于自己的重要影响。)对于新文体来说,它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层次的革命:一是文思的革命,即文章思想与内涵的革命;二是文体的革命,即散文形式与语言风格的革命。对于这两个层次的革命及其相互关系,曾有学者作过精当的分析:梁启超“‘新文体’的‘平易畅达’,与其说为了通俗,不如说为了化俗,不讲究形式美似乎是报章文体平民化了,其实,俗中有雅,骨子里还是近代知识分子的主体性,文章通俗不是为了取悦读者,而是为了教育读者,此乃是新型的文人之文,即梁启超所谓的‘觉世之文’。”[2]“新文体”实践引入了一种全新的文章审美理念,在近代文学与美学观念的变革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综观梁启超两次倡导“文界革命”的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其关于新体散文的基本美学观点是:(一)、散文创作的目的不为传世,而为觉世。(二)、散文效法的目标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新体散文。(三)、散文变革要从内容到形式实行全面的变革。内容上要表现“欧西文思”,形式上要追求“雄放隽快”、“明晰”“畅达”。(四)、散文语言应力求通俗化,可兼容中西词汇语法。“文界革命”的理论主张冲破了传统散文的各种清规戒律,使散文从“文以载道”和“替圣贤立言”的目的规范中解放出来,成为融入社会现实,面向广大民众的具有新鲜血肉和切实内容的崭新文体。“文界革命”的理论主张也使散文挣脱了桐城、八股等僵化凝固的文体规范,成为不拘一格、自由抒写的崭新文体。尤其是在“新文体”的创作实践中,与“欧西文思”相对应的大量西方新名词,如“国民性”、“人权”、“功利主义”、“专制主义”等,得到了介绍传播。这些“新名词”的输入冲击了“古文辞”的格律、习用典故和陈腐语汇,改造和丰富了文言的词汇系统,更新了文学语言的风格,还促进了散文创作主体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的变革。夏晓虹在《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一书中对此作了高度的评价:“‘新文体’对于现代语文最大的贡献,即在输入新名词。借助一大批来自日本的新名词,现代思想才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新文体’的半文半白,也适应了过渡时代的时代要求。”[3]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书中也对此作了肯定:“晚清的白话文不可能直接转变为现代白话文,只有经过梁启超的‘新文体’把大量文言词汇、新名词通俗化,现代白话文才超越了自身缓慢的自然进化过程而加速实现。”[4]当然,“文界革命”也不是没有自身的局限。梁启超的“文界革命”思想虽然突破了向传统散文寻找典范的固有模式,但其关于新体散文的构想还是朦胧浮泛的。其创作实践从整体上看,还是在古文范畴内的革新。他的新体散文半文半白,是由古典散文向现代白话散文演化的一种过渡形态。同时,由于作者急于传达新思想,表达新见解,着意突破传统古文“义法”的束缚,在写作上也有浮夸堆砌的毛病,衍化出一种新的“时务八股”。(注:梁氏“新文体”在当时影响极大,众人争相模仿。梁氏浮夸堆砌的毛病也被推向极端,形成了虚浮不实的“时务文”。)但是,梁启超的理论倡导及其创作实践有力地冲击了传统散文的固有格局与既成面貌,并在实际上形成了巨大的影响。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到了自己所作“新文体”的影响:“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野狐”形象地概括了“新文体”给予传统文坛的强烈震撼。可以设想,没有梁启超的“文界革命”主张与“新文体”创作实践,中国散文审美意识与创作实践的变革肯定还有待时日。
三
“小说界革命”的正式提出,则始自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第一号上发表的著名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格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是一篇具有纲领性意义的小说理论文章,被公认为“小说界革命”的宣言书。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小说向来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界革命的最大功绩是使小说登上了文学正殿,从此成为20世纪文学中最有影响的体裁。在论文中,梁启超明确提出小说是“国民之魂”的响亮口号,并从小说的艺术感染力与读者心理出发,论证了小说何以成为“国民之魂”的美学底蕴,即“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力”的概念梁启超主要借自西方近代科学,他以此范畴来界定小说的艺术功能;并运用西方文论的知性分析方法,将小说之“力”从横向上分解为四种,纵向上分解为二类,从而建搭起“四力说”的基本框架。小说通过“四力”来“移人”,从而“支配人道”。所谓“四力”,即“熏”、“浸”、“刺”、“提”四种艺术感染力。“熏”、“浸”、“刺”三力的共同特点是“自外而灌之使入”,但三者间又有差别。熏之力为“烘染”。人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之间”受到其“烘染”。熏着眼于“空间”范围的扩大。熏之力的大小,决定了所熏之界的“广狭”。“浸”之力为“俱化”。熏与浸都是审美过程中的渐变,强调潜移默化。浸之力如饮酒,“作十日饮,则作百日醉”。浸之力以时间论,其大小表现为对读者的影响时间的长短。熏与浸虽有空间与时间的区别,但都强调逐渐发生作用,接受者在这一过程中自身是浑然“不觉”的,情感变化是一种同质的扩展与延续。“刺”之力是“骤觉”,是由“刺激”而致的情感的异质转化。刺之力的特点是“使感受者骤觉”,“于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与熏、浸之力的作用原理在于“渐”不同,刺之力的作用原理在于“顿”。因此,刺之力的实现对于主客双方的条件与契合有更高的要求,它既要求作品本身具有一定的刺激力,又对接受者的思维特征有相应的要求。刺激力愈大,思维愈敏锐,刺的作用就愈强。同时,梁启超认为,就刺之力而言,“文字”的刺激功能“不如语言”;“在文字中,则文言不如其俗语,庄论不如其寓言”。语言就刺激物而言,它比文字更具有情景性,更具体可感,因为它有说话者的情态融于其中,从而构成对接受者的多感官综合刺激。而俗语与文言、寓言与庄论相较,俗语、寓言对思维的接受压力更少、更轻松、更富有趣味。最后,梁启超得出结论,在文学体裁中,具刺之力最大者,为小说。在四力中,熏、浸、刺三力各有特点,熏强调的是艺术感染力的广度,浸强调的是艺术感染力的深度,刺强调的是艺术感染力的速度。但它们对接受者的影响都是自外向内的,是被动的。“提”之力则是审美中最高境界,是“自内而脱之使出”。在提中,接受主体成为积极能动的审美主体,他完全融入对象之中,化身为对象而达到全新体验。在艺术鉴赏中,鉴赏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于书中,而为书中之主人翁”,这即是提的一种表现。此时,“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彼界”,从而产生“一毛孔中万亿莲花,一弹指顷百千浩劫”的神奇体验。可见,在提之中,主体已进入非常自由的审美想象空间。提是梁启超最为推崇的审美境界,提之力也是梁启超所界定的最神奇的艺术感染力。提是对审美主体的全面改造。在熏、浸、刺三界,主体虽为对象所感染,但两者的界限是明确的;在提中,主体与对象的界限已荡然无存,主体与对象进入物我两忘、情切思纵的审美自由境界。“文字移人,至此而极”。可见,梁启超虽将四力并举,但在认识的层次上是有差异的,熏、浸、刺是艺术发挥作用的前提与过程,提才是最终的目的与结果。四力说描述了艺术作用于人的基本过程与特点。尽管梁启超对四力的作用有渲染夸大之嫌,但他试图对艺术感染力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并始终以审美心理为中介来探讨艺术感染力的作用原理与机制,体现出西方现代心理美学的影响。
在小说理论史上,将小说推到如此高的地位,对小说的艺术作用方式与原理加以条分缕析,试图进行系统阐释,并产生实际的巨大影响的,梁启超应为第一人。中国古典小说理论批评主要集中于虚与实、情与理、人物性格、小说技巧等问题,对小说的艺术感染力与作用方式偶有触及,但主要是鉴赏式的感性体认,未能从理论的高度予以深入分析与系统研讨。“四力”是小说作用于人的具体方式,而小说本身在内涵意蕴上却有“赏心乐事”与“可惊可愕可悲可感”之分,梁启超认为前一类小说“不甚为世所重”,后一类虽“读之而生出无量噩梦,抹出无量眼泪”,但本来欲以读小说求乐的读者却愿“自苦”而“嗜此”。实际上,梁启超在这里已隐含了悲剧美的审美理念,他在价值理念上更偏重于痛而后快的悲剧感和崇高感。当然,这种价值取向也正是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的关键所在,即希望小说能借助自己独特的移人之力来警醒民众,以达到改造国民思想之功效。总而论之,梁启超关于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在美学思想上的意义是:(一)、强调了小说独特的艺术价值与巨大的审美功能。(二)、宏扬了以悲剧和崇高为精神内核的小说型态。(三)、具体研讨了小说的四种艺术感染力,并提出了“写实”与“理想”两种小说创作的基本手法。(四)、突出了读者心理在艺术活动中的重要意义。
四
文学革命是近代政治革命的副产品,但它在客观上催生了文体的变革。文学革新以“革命”相标榜,蕴含了急剧变革现状、破除旧规的强烈欲望。“中国结习,薄今爱古,无论学问文章事业,皆以古人为不可及。”文学革命最重要的功绩就在于确立了文学进化的新的文学理念,它为破除厚古拟古的守旧文学观打下了思想基础。在“革命”的旗帜下,梁启超推出了新的文体审美观:(一)、宏扬觉世之文,欣赏崇高的美感。(二)、主张形式与语言的革命,强调自由与多样的表现方式。(三)、重视艺术感染力与读者心理的关系。但是,在本质上,文学革命只是文体改良,而未举“革命”之实。把作品的社会功效与价值评判直接挂钩,认为社会功效大的作品,艺术价值也高。这在本质上与美善相济的传统文学理想具有难以割舍的联系。文学革命不是一次彻底的文学革命运动,但却是一次自觉的文学革新运动,它预示着新的文艺思想的破土和新的文学观念的涌动。几千年来,中国文学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是没有变革。但是,这些变革都是在自身封闭的系统内寻找典范,修修补补。文学革命第一次将中国文学观念的变革置于东西文化撞击的大背景中,确立了异域文学这一崭新的参照系,从西方文化与域外文学中寻找中国文学新生的现代性质素。它打开了千百年来儒家思想钳制下的一统局面,吹进了西方哲学、美学、文学思想的新鲜空气,中国文学从此有了新的比对物,中国美学也开始酝酿着新的价值走向与理论形态。因此,尽管文学革命留有旧思想的浓重痕迹,在创作上也缺乏骄人的实绩,但它所给予中国文学发展的观念冲击却是富于革命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的文学革命理论构筑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念与艺术审美理念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必要阶梯,在客观上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观念与美学形态的建构产生了无法忽视的重要影响。
收稿日期:2003-03-05
标签:梁启超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革命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哀希腊论文; 散文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