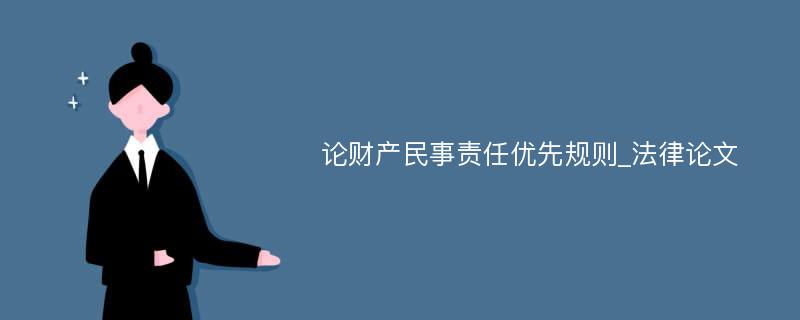
论财产性民事责任优先承担规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事责任论文,财产论文,规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 1)08-0219-08
一、财产性民事责任优先承担的立法渊源、性质及称谓辨析
“法律作为一种抽象的行为规范,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对各种具体社会生活关系进行多元、多维、多层次的综合调整。”①法律规范对于一个违法行为或者一个犯罪行为的评价和调整往往不是单一的或者单方面的,也就是说,对于同一个违法行为或者犯罪行为来说,它往往不仅会受到民法规范、商法规范等私法规范的调整和评价,而且会同时受到行政法规范、经济法规范和刑法规范等公法规范的调整和评价。当同一违法行为或者犯罪行为同时受到不同法律部门的多重调整和评价时,即会产生法律责任重合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律责任重合,有的学者称之为法律责任的聚合,“是指同一法律事实分别违反了不同法律部门的规定,将导致多种性质的法律责任并存的现象”②。本文认为,所谓法律责任的重合,是指行为人的同一违法(犯罪)行为因受到不同法律部门的多重评价,且具备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性质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时,行为人应依法并列、分别承担不同性质法律责任的制度。在我国法律责任体系中,依据法律责任性质的不同,法律责任主要包括刑事法律责任、民事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违宪法律责任。③由于“违宪责任是由国家机关及其负责人在执行职务过程中违反宪法而引起的法律责任”④,且违宪责任的认定具有其特殊性,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发生违宪责任与其他法律责任的重合。同时,尽管商法规范、经济法规范、环境法规范等也会对某一违法行为或者犯罪行为进行评价和调整,并产生相应的商法规范中的法律责任、经济法规范中的法律责任、环境法规范中的法律责任等,但由于不存在独立地位的商法责任(商法责任应属于民事责任或者私法责任的范畴)、经济法责任(经济法责任应属于行政法责任的范畴)、环境法责任(环境法责任是一种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一种综合性、非独立的法律责任形式⑤)。据此,法律责任的重合主要是指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之间的重合。在同一违法行为或者同一犯罪行为分别具备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时,会导致该两种或者三种法律责任的并列存在,且在一般情况下,该两种或者三种法律责任并行不悖,并不发生冲突和矛盾,行为人应分别承担该两种或者三种法律责任。但在行为人即责任承担人的财产不足以同时承担该两种或者三种法律责任时,就需要立法上对如何处理和协调此问题作出规定。对此,我国相关法律作出了民事赔偿责任优先承担或者侵权责任优先承担的相关规定。如我国《刑法》第36条第2款规定:“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其主要内容是:在追究犯罪分子刑事责任而给予其财产刑处罚时,若犯罪分子的财产不足以同时用于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承担财产刑处罚的,应将犯罪分子的财产优先用于承担对被害人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我国《公司法》第215条规定:“公司违反本法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的,其财产不足以支付时,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我国《证券法》第207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同时支付时,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我国《食品安全法》第97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同时支付时,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该三条规定的主要内容是:行为人因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而应同时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缴纳罚款)和刑事责任(缴纳罚金)时,若其财产不足以同时承担该三种法律责任的,应优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我国《侵权责任法》第4条第2款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侵权人的财产不足支付的,先承担侵权责任。”其主要内容是:侵权人因实施侵权行为而应同时承担侵权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若其财产不足以同时承担该三种法律责任的,应优先承担侵权责任。我国上述法律规定充分体现了强化、优先对受害人或者被害人民事赔偿责任的立法价值取向,其积极意义不容置疑。但是,对于上述立法内容的概括和称谓,学者并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而且学者的概括和称谓并不准确。有的学者将上述立法内容概括为“民事责任优先原则”⑥、“民事责任优先承担原则”⑦、“侵权责任优先性规则”⑧等。本文认为,学者对上述立法内容的概括和称谓是欠妥的,并没有准确、完整地概括出立法本意,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和歧义。为了能够正确理解和适用上述法律规定,充分实现对受害人或者被害人民事赔偿责任优先承担的立法本意和立法价值,有必要对上述立法内容的性质和称谓进行辨析和探讨。
1.民事责任优先承担是有特定条件的,而非无条件的
首先,它应以发生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重合为前提条件,即行为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同时受到了民法规范、行政法规范、刑法规范的评价和调整,该违法(犯罪)行为同时具备了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行为人应并列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民事责任的优先承担,是与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承担顺序相比较而言的,特指的是民事责任在承担顺序上的优先。只有在同一违法(犯罪)行为同时构成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情况下,才能在该三种法律责任承担顺序上进行比较,从而确定民事责任的承担顺序先于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承担。若不存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三种法律责任的重合,则不存在承担顺序上的比较对象,也就不存在民事责任承担顺序优先问题。其次,在发生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重合的情况下,该三种法律责任的具体承担形式都具有财产性内容或者都属于财产性责任形式。民事责任优先承担“并非适用于所有的责任聚合,而只是限于以财产责征为内容的责任的聚合”⑨。民事责任主要是财产责任,赔偿损失、返还财产、支付违约金等都是民事责任主要的承担形式。但民事责任不限于财产责任,民事责任也包括恢复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非财产责任形式,但非财产责任形式不占主导地位;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中既有财产责任形式,也有非财产责任形式,而且以非财产责任形式为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各自都有不同的承担形式,在发生法律责任重合的情况下,会产生各种不同法律责任承担形式并列、交错的情形,但并不是说,民事责任一律优先承担。也就是说,民事责任优先承担,不是在任何情况下的优先承担,仅仅限于财产性法律责任承担形式范围内的优先承担。若该两种或者三种法律责任的承担形式不都具有财产性内容,或者该两种或者三种法律责任的承担形式中仅有一种具有财产性内容,而其他的承担形式不具有财产性内容,则不产生民事责任优先承担问题,而是该两种或者三种法律责任的并列承担、分别承担、同时承担。再次,行为人在承担都具有财产性内容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时,其财产不足以同时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即由于行为人的财产数量不足,不足以全部满足承担该两种或者三种法律责任形式的需要,或者说,行为人在承担都具有财产性内容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时,因行为人的财产数量不足,导致其承担该两种或者三种法律责任发生了矛盾和冲突。“如果不存在财产责任的冲突”⑩,就不具备民事责任优先承担的存在前提。
2.民事责任优先承担应是法律责任承担时的一项适用规则,而非一项法律原则
法律规则“是对一个事实状态赋予一种确定的具体后果的各种指示和规定”(11)。通过对上述我国民事责任优先承担相关法律规定的分析,可以发现,民事责任优先承担的立法规定具有具体指导性、可操作性、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具体指导性,即相关的立法规定能够为在法律责任重合的情况下,如何处理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承担形式提供具体指南;可操作性,即相关的立法规定已经对如何适用法律规定规定了明确的适用条件,司法人员可直接适用相关规定;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即相关的立法规定对法律责任重合情形下,对于同一行为人如何处理其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及其后果,都作出了明确的、肯定的规定。因此,我国相关立法的规定具备了法律规则的特征,应将民事责任优先承担认定为一项法律适用规则。本文认为,将民事责任优先承担作为一项法律原则欠妥。“法律原则的特点是:它不预先设定任何确定的、具体的事实状态,没有规定具体的权利和义务,更没有规定确定的法律后果。”(12)法律原则的具体内容和构成要件具有不确定性、较强的抽象性、较大范围的普遍适用性并在适用中需要进行补充价值评价。而我国立法的相关规定,其内容和构成要件已经具有了确定性和可操作性,其内容明确具体,其适用范围特定,仅仅针对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发生重合的情形,而且其内容的适用不需要司法人员进行自由裁量和进行补充价值评价,而只要求司法人员严格适用。因此,本文认为,不应将民事责任优先承担称为原则,而应将其称为规则。
3.民事责任优先承担应是法律责任承担时的一项程序性规则,而非实体性规则
我国上述关于民事责任优先承担的相关立法规定,其内容是针对当财产性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发生重合时,责任人如何承担法律责任的规定,即关于责任人在法律责任重合中如何承担法律责任先后顺序的规定,而不是关于实体权利和义务内容的规定,因此,民事责任优先承担是一项程序性规则,而非实体性规则。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应将我国的上述立法相关概括为“财产性民事责任优先承担规则”,而不应称为“民事责任优先承担原则”。
二、财产性民事责任优先承担规则的正当性分析
由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之间性质各不相同、各自功能独特、彼此地位独立,且该三种责任形式既不能相互转换,也不能相互替代,因此,一般说来,在该三种法律责任发生重合的情况下,三者应独立、并列存在,分别、同时承担,不应出现承担法律责任顺序上的先后问题。但是,我国相关立法确立了我国立法确立的财产性民事责任优先承担规则,并没有违反法律责任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财产性民事责任优先承担规则具有其充分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具体表现在:
1.该规则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体制中,应优先保护私权的立法价值取向
法律规范的核心功能即在于保护权利和利益,不同的法律规范保护不同性质和内容的权利和利益。刑法规范和刑事责任、行政法规范和行政责任都侧重保护公权和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民法规范和民事责任侧重保护私权和私人利益。一般来说,法律保护的公权和私权、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都具有其同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对私人及其私权、私人利益的尊重和保护,而且私权和私人利益的保护日益得到重视和强调。当法律保护公权与保护私权发生矛盾和冲突时,法律应优先保护私权。财产性民事责任优先承担原则,则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体制中,法律优先保护私权的原则。
2.该规则更符合公正原则
行为人承担行政责任的主要功能在于通过对违法人实施惩罚来预防行政违法行为的发生;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主要功能是惩罚性,对构成犯罪的行为人处以人身罚和财产罚主要是为了实现对其的惩罚目的;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主要功能是补偿性,要求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主要是为了实现对受害人或者被害人所受损害的恢复、救济和补偿。在行为人的财产不足以同时承担其行政责任的行政罚款、刑事责任的财产罚如罚金、没收财产和民事责任的赔偿损失等时,实行财产性民事责任优先承担规则,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对受害人或者被害人所受损害的恢复、救济和补偿,最大限度地实现民事责任的功能,实现针对受害人或者被害人的公正。在以行为人的财产优先用于承担民事责任后,尽管使得对行为人处以的行政罚款、财产刑无法实现,但对行为人仍可通过易科(将财产罚易科为人身罚等其他刑种)承担形式得到实行,并以此实现对行为人的惩罚性功能。即对行为人适用人身罚和财产罚,都能实现对其的惩罚性功能。在对行为人处以的财产罚无法实现时,对其处以人身罚,同样能够实现对其的惩罚性功能。而对受害人或者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的实现方式则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若不实行财产性民事责任优先承担原则,将导致对受害人或者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无法实现,却又没有可替代或者可补救的手段,这对受害人或者被害人来说,显然是不公正的,也不利于社会公正的实现。而实行财产性民事责任优先承担规则,则更有利于实现对受害人或者被害人利益的保护。可见,财产性民事责任优先承担规则更符合公正原则。
3.该规则更加符合公平原则
对行为人处以的行政罚款或者财产罚,具有强制性、无偿性、惩罚性的特点,行为人因向国家承担行政罚款或者财产刑而支付的财产无偿归国家所有。而民事赔偿责任是行为人对受害人或者被害人承担的民事责任,该种民事责任具有一定的任意性、明显的补偿性、权利与义务对等性的特点。行为人因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支付的财产,直接归属于受害人或者被害人,以恢复、救济和补偿受害人或者被害人所受的损害。若行为人的财产不足以同时承担行政罚款、财产罚和民事赔偿责任时,即行政罚款、财产罚与民事赔偿责任发生冲突时,实行财产性民事责任优先承担规则,更符合公平原则。
4.该规则更符合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各自的特性
民事责任主要是一种财产责任,追究行为人民事责任的目的,最主要是为了恢复、救济、补偿受害人所受的财产损害。财产性民事责任优先承担规则,更有利于民事责任目的的实现,或者说,更符合民事责任主要是财产责任的性质。而刑事责任的特性的适用必然受制于刑法的谦抑性和补充性规则。“刑法的谦抑性,又称刑法的收缩性,是指应当尽量缩小刑罚制裁的范围。”(13)刑法的补充性规则是指“刑法的调整手段是最具强制性的,是最后手段”(14)。刑法作为以刑罚手段惩治和打击犯罪,保护和促进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专门手段,表现出较其他手段更为严厉的强制力和惩罚性,应将其作为犯罪控制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不应把它作为首选或者优选的手段。“若以任何其他法律效果也能制止不法行为时,则应尽可能避免刑罚的使用,也即只有在其他法律效果不足以生效时,才适用刑罚。换言之,把刑罚保留作为非不得已时的最后法律手段。”(15)“刑罚权应当限制,使之成为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法律手段。”(16)刑法的谦抑性和补充性规则,决定了刑事责任的谦抑性和补充性,也由此决定了财产性民事责任优先承担规则。
三、我国财产性民事责任优先承担规则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1.我国财产性民事责任优先承担规则的立法缺陷
纵观我国现行财产性民事责任优先承担规则的立法规定可以发现,存在着立法规定不统一、不一致、缺乏协调性、科学性、逻辑严密性等方面的缺陷。具体说:
(1)法律责任概念的使用不对称、不对应。如我国《侵权责任法》第4条第2款的规定中将侵权责任与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并列,导致法律责任概念使用上的不对称、不对应。在法律责任体系中,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相互对称、相互对应。侵权责任是民事责任的下位概念,将侵权责任与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并列,逻辑上欠妥。又如,我国《刑法》第36条第2款的规定,将民事赔偿责任与罚金、没收财产一并规定;我国《公司法》第215条、《证券法》第207条、《食品安全法》第97条等都将民事赔偿责任与罚款、罚金一并规定,显然在概念使用上不对称、不对应。
(2)有的立法中没有对法律责任的重合作出全面、完整的规定。如我国《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该条只规定了犯罪分子因其犯罪行为而产生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重合的情形,而没有规定刑事责任、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重合的情形。该条规定明显欠妥。因为该条规定不符合实际情况。如同一经济犯罪可能同时违反刑法规范和行政法规范,如我国《刑法》第404条规定的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或者可能同时违反刑法规范、行政法规范或者经济法规范、民法规范或者商法规范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侵犯知识产权罪等经济犯罪等,对于这些经济犯罪行为来说,犯罪人本应同时承担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或者应该承担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但是,第36条规定却遗漏了经济犯罪同时承担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民事责任三种责任或者同时承担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两种责任的情形,实际上是排除了经济犯罪同时承担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或者同时承担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可能性。又如,我国《刑法》第37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该条规定只在特殊情况下,即只对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而可以免予刑事处罚的犯罪分子,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或者承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或者承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的行政责任。一方面,它没有规定犯罪应同时承担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而是规定犯罪主体或者可以同时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或者可以同时承担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另一方面,它所规定的犯罪同时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或者同时承担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不具有普遍适用的意义,仅仅是对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而可以免予刑事处罚的犯罪主体,可以再承担民事责任或者行政责任。同时,该条规定对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而可以免予刑事处罚的犯罪主体,“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确定是否承担民事责任或者行政责任,而不是“应当”或者“必须”承担民事责任或者行政责任,即该条对民事责任或者行政责任的承担的规定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没有强调应当分别刑事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缺乏必要的严肃性和强制性,存在比较严重的缺憾。再如,我国《行政处罚法》第7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违法受到行政处罚,其违法行为对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该条尽管规定了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的重合,但只规定“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是片面的。因为违法行为引起的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都是独立的法律形式,彼此相互独立,互不排斥,并行不悖,三种法律责任之间都不能相互替代。该条规定并没有表达出三种法律责任之间不能相互替代的内容,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可能会对法律责任的适用产生误导和副作用。
此外,我国《公司法》第215条、《证券法》第207条、《食品安全法》第97条等没有直接规定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重合以及该三种责任的分别承担,而是对三种法律责任的重合作出了间接的、比较模糊的规定。尽管结合该几条中对三种法律责任承担形式的规定内容,可以推导出包含着同一违法行为应同时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含义,但由于在其立法表述并没有直接规定三种法律责任的重合问题,而是以三种法律责任的不同承担形式来间接体现三种法律责任的重合,从而使该几条立法内容显得模糊不清。
(3)没有强调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在法律责任重合中的重要地位。同一违法(犯罪)行为是否构成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重合,行为人是否应分别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其最重要的条件是该同一违法(犯罪)行为是否同时具备了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在法律责任的重合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我国现行相关立法却没有突出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的重要地位。如我国《刑法》第36条规定中的“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的内容,不够准确。因为赔偿经济损失属于民事赔偿责任的承担形式。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不仅“应根据情况”,而且更应该看是否具备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仅仅“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的规定是不准确的。又如,我国《刑法》第37条规定对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而可以免予刑事处罚的犯罪主体,“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确定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或者行政责任,而没有强调以是否具备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构成要件来决定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或者行政责任。再如,我国《行政处罚法》第7条规定的“其违法行为对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内容,也没有强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对民事责任是否承担的决定性作用,该条以“对他人造成损害”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条件,缺乏准确性。因为一般而言,行为人是否应向受害人承担民事责任,取决于是否具备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只有在具备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的情况下,行为人才应承担民事责任。在民事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中,尽管受害人受到损害是其不可缺少的构成要件之一,甚至是最重要的构成要件,但无论如何,受害人受到损害不能成为民事赔偿责任的全部构成要件,换言之,仅有受害人受到损害的事实或者结果,并不必然具备民事赔偿责任的全部构成要件,行为人并不必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所以,该条规定仅规定“其违法行为对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是不充分的,存在立法漏洞。再如,我国《民法通则》第110条规定:“对承担民事责任的公民、法人需要追究行政责任的,应当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对公民、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条规定将“承担追究行政责任”的条件仅规定为“需要追究行政责任的”,而没有以行政责任的构成要件作为决定是否承担行政责任的根据。一方面,使得行政责任的追究具有了主观随意性,是否追究行政责任视是否“需要追究”而定,由于该条规定赋予了行政责任的有权追究主体在是否“需要追究”行政责任方面享有了过于大的权力,使得行政责任的追究的随意性过大,缺乏确定性和强制性;另一方面,该条规定以“是否需要”作为追究行政责任的根据,忽视了行政责任的构成要件的作用,缺乏充分根据和立法内容的科学性。
(4)对财产性法律责任承担形式的规定不科学、不全面、不准确。其一,没有区分不同种类的法律责任及其各自不同的责任承担形式。如我国《刑法》第36条将刑事处罚、赔偿经济损失、民事赔偿责任、罚金、没收财产等内容并列规定,《刑法》第37条将刑罚、刑事处罚、训诫、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行政处罚、行政处分等内容并列规定,《行政处罚法》第7条将行政处罚、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刑事处罚等并列规定,《公司法》第215条、《证券法》第207条、《食品安全法》第97条等都将民事赔偿责任、罚款、罚金等并列规定,导致不同种类的法律责任及其各自不同的责任承担形式的相互混淆,立法表述不够精确,立法术语不对称、不对应,逻辑混乱。其二,对财产性法律责任承担形式规定不全面。根据法律责任的性质和内容的不同,法律责任的承担形式可分为财产性法律责任和非财产性法律责任,而且不同种类法律责任具有各自不同的财产性责任的承担形式。民事责任中的财产性责任主要包括返还财产、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等,民事责任以财产性民事责任为主。行政责任中的财产性责任主要有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等,但其在行政责任中不占主导地位。刑事责任中的财产性责任主要是罚金、没收财产,而且属于刑罚中的附加刑,其在刑事责任中也不是主要的。但是,我国现行立法对财产性法律责任承担形式并没有作出全面规定。如《公司法》第215条、《证券法》第207条、《食品安全法》第97条只规定了罚款、罚金等财产性责任形式,但对返还财产、赔偿损失、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没收财产等其他财产性责任形式没有作出规定,既无法全面体现财产性民事责任优先承担规则,也不利于该规则的贯彻实施。其三,对财产性民事责任优先承担规则规定的立法用语不准确。财产性法律责任承担形式的不同,决定了承担具体财产性法律责任形式的具体行为方式的不同。我国《公司法》第215条、《证券法》第207条、《食品安全法》第97条等由于只规定了罚金、罚款等财产性法律责任的承担形式,因此,该几条规定都使用了“财产不足以支付”、“财产不足以同时支付”的概念。本文认为,立法中使用该两个概念是不准确的。因为财产性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承担形式中,不仅包括金钱支付,如赔偿损失、罚款、罚金等,也包括非金钱支付的财产性承担形式,如返还财产、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没收财产等。财产支付特指的是金钱支付,将其适用于赔偿损失、罚款、罚金该三种财产责任形式是合适的,但对其他财产责任形式,显然不宜适用。因此,对于非金钱支付的财产性责任承担形式,使用“财产支付”的概念显然是不合适的。
2.我国财产性民事责任优先承担规则立法完善的思路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我国财产性民事责任优先承担规则的立法完善,应遵循以下思路:
(1)应对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重合作出明确的、原则上的一致性规定。受我国现行立法体制的制约,我国无法实现对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重合作出专门、集中的规定,而是采取在民商法、行政法、刑法等不同部门法的立法中,分别对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重合问题分别予以规定,即对三种法律责任的重合采用分散立法模式。对此,应对三种法律责任重合的内容作出明确的、原则上一致性的规定。这不仅有利于确保立法内容的一致性、便于法律的实施,而且有利于为财产性民事责任优先承担规则提供统一性的前提条件。同时,由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各自具有各自独立的法律地位、各自不同的性质和各自独特的功能,为了确保三种法律责任的分别承担,发挥三种法律责任各自不同的作用,既要规定三种责任重合情况下,三种责任的分别承担,而且为了强化和确保三种责任的分别承担,应明确规定三种法律责任之间不能相互替代或者相互替换。
(2)应确立和突出“财产性民事责任”的优先承担规则。无论是民事责任,还是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从其责任内容看,都可分为财产性责任和非财产性责任。对此,应在立法上作出不同的处理:对于三种责任中的非财产性责任,行为人应分别承担,不适用责任承担顺序先后的规则;对于三种责任中的财产性责任,当行为人的财产不足以同时承担财产性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时,应优先承担财产性民事责任。
(3)应完善财产性民事责任优先承担规则的立法内容。其一,应统一“财产性……责任”的概念,不同法律责任及其各自具体的承担形式是不同的。对此,应在立法上将法律责任及其各自具体的承担形式区分开来,而不应混为一谈。应在完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重合立法规定的前提下,统一使用“财产性……责任”的规定,分别作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下位概念,实现民事责任—财产性民事责任、行政责任—财产性行政责任、刑事责任—财产性行政责任的概念对应。其二,不必规定财产性责任的具体承担形式。无论是财产性的民事责任,还是财产性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其内容都是通过具体的承担形式加以体现和落实的。民事责任中的财产性责任主要包括返还财产、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等,民事责任以财产性民事责任为主。行政责任中的财产性责任主要有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等,但其在行政责任中不占主导地位。刑事责任中的财产性责任主要是罚金、没收财产,而且属于刑罚中的附加刑,其在刑事责任中也不是主要的。同时,由于三种法律责任各自具有各自不同的财产性责任形式,且三种法律责任的财产性责任形式并不是对应关系。我国《民法通则》、《刑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都就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具体承担形式(包括财产性责任和非财产性责任)已经作出了规定,但为了实现立法内容的简洁,避免立法内容的重复,避免立法中规定的不同财产性责任与其各自的具体承担形式之间产生逻辑混乱,防止对财产性责任具体承担形式立法规定的遗漏,应在相关的立法中统一“财产性责任”概念,以此来概括财产性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具体承担形式,而没有必要再具体规定三种法律责任的具体财产性承担形式。其三,应统一使用“财产不足以同时承担”的概念,而不使用“财产不足以支付”的概念。如上所述,财产性责任的承担形式中,既包括金钱支付的形式,如赔偿损失、罚款、罚金,也包括财产交付或者财产收缴的形式,如返还财产、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没收财产。我国现行关于财产性责任承担形式的立法中,大多使用“财产不足以支付”的概念,这显然不宜适用于财产交付或者财产收缴的承担形式。为此,应选择使用具有更强的概括性、可适用于各种财产性责任承担形式的“财产不足以同时承担”的概念更为合适。
3.我国财产性民事责任优先承担规则立法完善的条文设计
基于上述分析,可对我国财产性民事责任优先承担规则立法完善的条文作出如下设计:
第N条:行为人的同一违法(或者犯罪)行为同时违反民商法规范、行政法规范、刑法规范,且同时具备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的,行为人应分别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或者)刑事责任。行为人承担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不能相互替代或者相互替换。
第N+1条:行为人在分别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时,其财产不足以同时承担财产性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时,应优先承担财产性民事责任。但非财产性责任不在此限。
注释:
①蓝承烈:《民事责任竞合论》,《中国法学》1992年第3期。
②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87页。
③张文显:《法哲学通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7页。
④张文显:《法哲学通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7页。
⑤参见张梓太:《环境法律责任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15页。
⑦奚晓明、王利明主编:《侵权责任法条文释义》,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第13页。
⑧王利明、周友军、高圣平:《中国侵权责任法教程》,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第23页。
⑨王利明、周友军、高圣平:《中国侵权责任法教程》,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第25页。
⑩王利明、周友军、高圣平:《中国侵权责任法教程》,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第25页
(11)张文显:《法哲学通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0页。
(12)张文显:《法哲学通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3页。
(13)张小虎:《刑法的基本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5页。
(14)杨春洗主编:《刑法基础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03页。
(15)王建今:《现代刑法的基本问题》,台北:台湾汉林出版社,1998年,第153页。
(16)陈兴良:《论刑罚权极其限制》,《中外法学》1994年第1期。
标签:法律论文; 刑法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法律规则论文; 民事侵权构成要件论文; 刑法基本原则论文; 犯罪构成要件论文; 行政立法论文; 民事违法行为论文; 公司法论文; 法制论文; 证券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