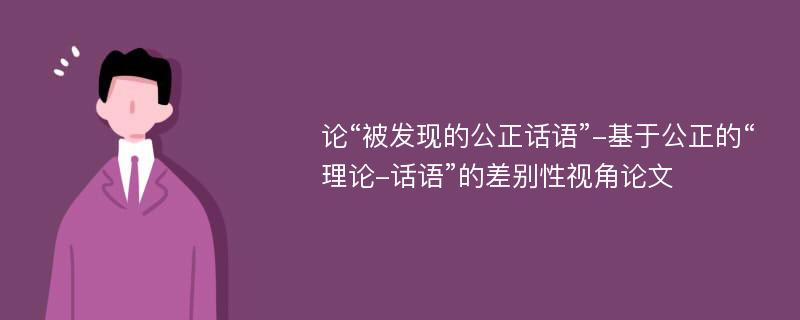
论“被发现的公正话语”
——基于公正的“理论-话语”的差别性视角
亓 光
(中国矿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 公正话语的现代发生始于公正理论的解释困境成为社会普遍问题而进入政治哲学领域,公正话语从“理论-话语”同一思维下的相似性议题转变为“理论-话语”差别性视角下的实践性建构问题。相对于公正理论的创制性,公正话语以被发现性为主要特征,主要体现在实践性建构的内涵层面、总体现象层面与具体的实践理解策略等三个方面的基本规定性之中。为了真正实现“被发现的公正话语”的基本规定性,需要植根于眼前的公正世界确定与选择具体规则与实践策略。在理解“被发现的公正话语”的过程中,公正话语的分析对象必须是“摆在眼前”的公正世界,公正话语的分析原点是“政治正确性”的公正理解,而公正话语的分析方向则是“对社会情境的细致分析”,三者共同构成了公正话语的具体规则。
[关键词] 公正话语;被发现的公正话语;实践性建构;“理论-话语”;差别性视角
凯·尼尔森指出,马克思对公正的论证“是语境主义的,因为它不承认存在单独一条或一组可以适用于所有环境的正义原则,但是,这种论述又是客观主义的和解释式的,因为它坚持认为,身处某个拥有其明确的正义原则及其相关实践的情境,有时候要比身处另一个拥有其明确的正义原则及其相关实践的情境更好”[1](P.349)。事实上,这就是公正的“理论—话语”的差别性视角。这一新观念并不仅仅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研究,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高度对公正话语进行了新思考,为人们深化对公正话语的认识提供了新视角。不过,尼尔森在这里停止了思考,并未继续从实践性建构的高度理解公正话语。众所周知,公正话语不但与特定的社会条件和行为经验的规定性有关,而且与其传播的广泛性和被接受的全民性有关。公正话语既是世界的又是特殊的,是在批判地考察公正话语历史变迁的基础上在具体的语境中不断被发现的。在这个意义上,公正话语的实践性建构应围绕公正话语是被发现的基本判断(即“被发现的公正话语”)而展开,其论证方式与实现方式是有机统一的。
翻译还是一种跨文化心理活动。翻译心理学认为,翻译的本质是译者在两种文化中,从冲突到磨合再到取舍的心理历程。所谓“磨合”就是译者对客体文化的理解、融化;而“取舍”就是译者的整个心理活动外化。译者,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在与另一种文化的载体——作者及其作品的交际中,在心理上必然受到来自作者及作品的所体现的文化冲突的影响。[2]16
一、“被发现的公正话语”的主要理论渊源:承认论与诠释性沟通论
在当代公正理论的学术谱系中,“被发现的公正话语”至少具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承认论中的公正话语,二是诠释性沟通视域中的公正话语。前者侧重于公正概念的实质性陈述,后者则立足于公正理解的程序性陈述,包括内容规定性与形式规定性。在很大程度上,这两个主要来源就是实践公正话语理论范式所应捍卫的核心内容,即在公正话语分析的具体应用中应当维系的核心内容。
(一)承认论域是公正话语分析在内容规定性方面的中心论域
在内容规定性方面,承认论域的作用不可忽视。该论域“之所以在当今颇受瞩目,主要是由于他们敏锐地抓住了当代社会现实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并将其融入全新的承认语境之中,从而引领了当前社会批判理论思潮的发展”[2](P.29),其传播速度之快和传播程度之深在以“左”“右”为基本划分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两大阵营中均有重要体现。
自由主义中的激进派认为,政治生活存在于斗争之中,化解斗争的根本不是寻找一种政治的真理(如公正的社会制度),而是如何在不同的解决方案中相互承认,以维持动态平衡。在这一论域中,公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论题。由于现代性社会在创制中产生的规则思维、制度体系与行为规范越发使社会中的既得利益群体和统治阶级成为合法代言人,公正的界限与原则并没有带来“创制”之初的理想结构,反而造成了社会矛盾和危机的空前积累与爆发。因此,只有在“发现”中寻找不同的公正主张、公正理论甚至公正态度共同构成公正话语的合理性,进而以此为基本尊重产生兼顾不同性别、族群、种族、利益团体等各主体对公正状态的相互承认,才有可能实现真实的公正社会。自由主义激进派主张抛弃创制思维上的公正建构论,皈依发现基础上的公正话语论。沃尔泽的复合平等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承认论域中对公正话语的内容规定性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公正在术语层面依然是原来的公正,甚至还需要一些具体的要素和标准,但是这些标准和内容已经不是为了建构一个完整的公正社会,不同领域不仅可以具有不同的公正话语,而且这些具体的公正话语也不再因与某个具体特定的公正标准而承担相对主义的指责。在沃尔泽看来,公正话语实质上就是一个较大的公正观念,这是因为“正义扎根于人们对地位、荣誉、工作以及构成一种共享生活方式的所有东西的不同理解”[3](P.419),而其所要求的是“(公民们)轮番为治……在一个领域内统治,而在另一个领域内被统治——在那里,‘统治’的意思不是他们行使权力,而是比别人享有对被分配的任何善的更大份额”[3](P.428)。
不过,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最终并没有实现它的任务,在过分强调多元化话语差异的基础上,它们彻底成为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激进理论。除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持续误解外,它们的内在矛盾也非常严重。“其一,他们在否定经济决定社会的同时却变相地以还原论的方式肯定了话语的‘决定性’地位,只不过这一‘决定性’不是宏观的,实证主义的,而是‘建构论’的‘决定性’。其二,他们在否定经济决定论和本质主义,否定马克思的客观性社会总体观的同时,却肯定了话语的‘关系决定论’,并试图用‘关系论’来取代传统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决定论。那么,如何界定这一‘关系论’,并使他们所倡导的‘话语’避免沦入‘结构主义’的陷阱,是他们的话语理论必须面临的一个问题。”[9](P.549)因此,话语如何能够有规则地被运用起来,就成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而恰恰是英美学者在讨论“马克思与公正”问题时才将这一问题与公正话语相结合,将公正的话语批判从“天上”带到“人间”,其目的在于超越马克思的总体公正论(公正的本质分析),进而提出或阐释马克思的实际公正论(公正的现象分析)。正因为要对作为基本单元的“话语”前提下的公正话语进行真实性写照,“被发现的公正话语”的实践性建构才需要分析规则。
(二)诠释性沟通视域是公正话语分析在形式规定性方面的核心论证方式
在具体的实践理解策略中,在重塑与扬弃的过程中逐步实现公正话语的分析必须重视英美学者分析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两个基本观点。其一,分析马克思主义是将不同的研究路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通过马克思主义的“肌体”,或者是将上述内容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场域中进行检验而另辟蹊径、方法组合与焦点重塑的过程。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所发现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也只是一个现象而非一个学派,或者最多只能说是一种风格独特的研究路径。现在,关注严密性及细节的做法在实践中五花八门,而实际上任何形式的理论化和立场都可以依据这一理论化标准予以考虑和评估”[16](P.5)。由此可见,分析马克思主义认为,公正话语的规则策略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公正观在公正话语分析中的呈现,实际上这种分析的目标就是找到(创制)一种完备的马克思公正话语(实质上就是前文提到的公正理论)。而在这一目标的限定下,具体的规则只能是自由主义公正理论的另一张面孔。佩弗就明确地主张马克思与罗尔斯对公正的理解在本质上具有极高的相似性,而仅存在具体规则设定的差异。其二,分析马克思主义力图通过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扬弃”将改造后的两种解释策略作为公正话语的规则策略的基础,进而以“执行公正”作为具体规则设计的对象。这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一种方法论,一种对于自由主义公正理论进行批判的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这种工具的主要任务是将自由主义公正理论的“语境性”和“条件性”揭示出来,以此发现其“燃素”。在20世纪中叶以后,作为“为理性辩护”的代名词方法论个人主义将其研究的主要内容转向理性选择领域,就将公正作为一种个人理性选择的必然性(诺齐克)、目标性(罗尔斯)、功能性(阿马蒂亚·森)的给定选项而确定下来。自由主义公正理论借此再一次在否定对于公正的思考是一个社会过程中取得了“胜利”。这一胜利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冷战秩序下的意识形态决裂与冲突等的“发酵”下不断膨胀而成为一种思维定势。分析马克思主义通过语言规则发现了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严重反例。更有甚者认为,“语言当然仅仅是这种反例中的一个:存在其他的社会规则系统,例如规范着哲学讨论的规则,或者更普遍的,规范着被接受的学术行为的规则,这些规则显然是在不断变化的,因为可以确认的个人在制造变化”[16](P.193)。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公正问题在成为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热点议题伊始就成为了分析马克思主义力图将理性辩护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分离开来的着力点。而批判自由主义公正理论只是完成分离的第一步,第二步则是要对公正本身进行理性辩护。分析马克思主义在根本上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存在公正观的,而仅将其作为一种对自由主义公正理论的完善路径加以“改造”后才使用。所以,当自由主义公正理论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终极价值目标确立为基于个人自由的社会公正时,分析马克思主义是赞同的,分歧只是在于如何更加厚重地、更加可靠地塑造一个称之为“执行公正”的概念工具以避免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性侵害到“公正”概念的自我完备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米勒(R.W.Miller)指出:“唯一保留下来的对‘正义’的用法,可能在当时预设了裁判功能。一个保留用法是社会工程学中的‘正义’,在这里,稳定的零散的改革在基本的社会结构中被推行。另一个保留用法可能是把社会抽象地分成正义的社会或不正义的社会,这种划分受到了一种自由的、神启的观点的指导。”[17](PP.82~83)
事实上,揭示公正话语的规则策略正是批判自由主义公正理论的必然结果。在自由主义内部与“左翼”激进理论中,公正话语只是诸多话语批判中的内容之一。近年来,随着对公正问题的思考越发深入,对公正的自我理解以及自我理解时的理论冲突的同一性就逐渐彰显出来了,这也被看作是公正话语的的直接论域。“理论之间的冲突和竞争作为一个社会事实,不仅反映着现代性条件下的社会的多元现实而且会反过来助长和强化后者并成为后者的一部分。政治哲学理论如果不能够理解和解释理论多元与现实多元之间的相互支撑和生长,就会趋向于用一元论的线性思维方式来看待自己的理想与社会现实的关系。”[14](P.238)对此,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理论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在解构马克思的总体话语性方面,他们将“话语”这个范畴进行了碎片化处理。经过处理,马克思的唯物史论的总体感就被“合理地”重构成了具象的分析,成为了话语(甚至语言)的存在。权且不论拉克劳和墨菲的尝试是否符合马克思的本意,仅从效果上看,通过话语理论的建构特别是将话语作为一个分析社会关系的问题旨在增强马克思主义在诸多现实问题上的争辩能力的意图确实值得关注。
二、实践性建构视角中“被发现的公正话语”的基本规定性
在实践性建构的内涵层面,“被发现的公正话语”具有上文所论述的两种规定性需要实现或捍卫。这样的实现或捍卫却不能仅仅停留在规定性论证的层面,而应进一步指向实践或建构“被发现的公正话语”的具体规则之中。福柯认为:“语言的经验,恰如自然物的认识,都属于同一个考古学网络……语言为自己设定了恢复一个绝对初始的话语的任务,但是,只有设法接近它,设法说些关于它的类似于它的话,从而使大量临近的和相似的阐释精确度得以产生,语言才能陈述这个话语。”[13](PP.56~57)人们发现这些“考古学网络”的话语体验在素材上是分散的,因此才需要确认一种可以将这些素材加以联系、形式化和界限化的规则,也就是如何进行排列。公正话语在话语规定性上对公正理论的扬弃归根结底是一种理解公正思维的超越,但如果这种超越停留在思维层面也就失去了现实意义。因此,公正话语需要通过分析过程来展现其与社会中其所指涉的具体实践及其正当化观念的逻辑关系。这被看作是公正话语的规则策略。
(一)公正话语需要分析的规则策略
“语言建构视域的创造性与一种内在世界的实践结果脱离了开来,而这种内在世界的实践在语言系统中已经预先被规定了下来。”[11](P.371)在这个意义上,创制的公正理论本身并不是问题的根源,而捍卫它的实践才是危险之所在。因此,在实践性建构中捍卫“被发现的公正话语”并不是一种“最终幻想”,而应当在诠释性沟通的辩证法中将公正所表现出的诸善、历史传统、政治说服与话语动机进行一种“本质-表象”的判断和排序,将具体安排的结构和方式与具体安排的论证结构和方式区别开来,以此避免那些排他性的理论创制,这就意味着维系“被发现的公正话语”的内涵“不能追求一种‘最终结果’,而是要将解释分歧看作是诠释性沟通自身的有机组成部分”[12]。
首先,如果想要对焊接质量进行提升就必须对于焊接的机械化与自动化进行持续的推进。结合当前的情况可以发现船舶制造业的焊接人员无论在理论知识方面、职业素养方面以及焊接技能水平上都存有明显的不足,基于这种情况只要对焊接的机械化与自动化进行不断的推进,并且结合合理有效的焊接工艺才能使一些焊接过程中人为因素的影响被控制在最低的范围之内。
与自由主义公正理论不同,主要是为了避免陷入自由主义政治话语的前见即将个人首先性作为公正原则之根本规定的局限,左翼学者大多在“反”“后”“超越”的叙事中重新发现了公正原则的问题性。其一,将霸权视角与关于公正的反规范或规范话语问题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反自由主义公正理论的目标。有学者指出:“前者(霸权视角)历史性地、战略性地看待了正义话语,其目的在于理解权力转移,但是,后者(反规范/规范话语)却从哲学上、规范化上审视了它,其目的在于揭示具有解放意义的变化的现实的可能性……因此,这里发展的视角提供了批判的理论化的一个关键性成分,而单独采纳的霸权理论却并没有提供这一点:正义话语的难以捉摸但却令人鼓舞的视角,它能够揭示确凿无疑的道德侮辱的当代的不公正性。”[4](P.84)那些侧重于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外部特别是历史的高度并实现不同于自由主义公正理论且将之作为公正话语的历史类型或者“诸多先见”之一的思想在总体上所体现的就是“反”的方法论诉求。其二,在否定自由主义公正理论的话语预设和逻辑的基础上,从产生自由主义公正理论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内部重塑这一理论的基础所建立的多元的公正话语体系。霍耐特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承认”表现在他对于自由主义道德观一元性地接受,并认为这是基于“人的完整性”的合理选择,而“在其存在的深层,乃是归因于我们一直在努力辨别的任何和承认模式,这么一种意义是我们日常语言运用中所固有的”[8](P.140)。但是,主体尺度并不是单一的,故实质上在社会生活中主观偏见掌控了关于公正的见解,这是人被“奴化”的象征。那么,自由主义的一元公正论就是被禁锢的理论体系。霍耐特指出,公正观念的主观意志是在其自身中获得公正原则(制度)的客观性,要以公正与关怀的多元化实现将公正从自由主义政治话语的一元论中“解放”出来。在很大程度上,这也就是“后”自由主义公正理论在话语建构上的方法论逻辑,即“提出一元道德为基础的多元正义构想,并试图建构正义与关怀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学’”[9](P.404)。其三,随着马克思主义对公正理论阐释的深入,公正理论实质是自由主义公正理论在前理解上的限制与偏见的不断显化。人们发现,假如马克思有公正理论,其一定不同于公正理论的历史形态(主要指自由主义形态);而即便马克思存在公正理论空场,则更能够证明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公正理论甚至其所界定的公正概念的不屑一顾。这种批判态度至少说明马克思主义从没有以公正的规定性出发理解一切以公正为名的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超越”论就出现了,即唯物的话语对唯心的理论的“超越”。公正话语超越论的方法论基础来自于马克思的两大经典论断。一是“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印象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0](P.501),二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0](P.502)。依据公正话语的超越论,前者是话语理论的方法论建构基础,后者是话语理论的方法论否思渊源。尼尔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公正概念之所以具有超越性,就是因为其在本质上是一种辩证话语,“而且,这种观点是可错论的,甚或是历史主义的,但不是相对主义的……(总之)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提供了日益更加高级、更加充分的视角,同时又否认那个最高的、最充分的视角是一种‘超越正义的视角’”[1](P.346),可见,超越公正中的超越在方法论上是不断实现的,这也就确认了“被发现的公正话语”是始终存在的。因此,超越公正并不会僵化。超越论的具体路径不但否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合法性,而且还要否定公正原则的合法性,要求从公正话语与社会关系之间“中心意义”的选择中发现公正原则,这就是话语理论内部在面对诸如公正话语这样的具体对象时将会产生的“福柯与拉克劳—墨菲”之争在方法论上的根源所在。
西方左翼学者则将自由主义公正理论看作是创制的公正伦理,而非真正存在于伦理生活中的公正原则,反对以“具体的公正”特别是分配公正取代公正的总体性,而主张公正的基础性和统摄性的依据是“承认的斗争”与“认同的话语”。南茜·弗雷泽就将自由主义公正理论的核心内容称为“规范的公正”,并认为创造出这一可辨别的逻辑是现代性争论的一个重要产物。她指出:“不存在有着充分理由的真实世界的语境,在其中,关于正义的公共辩论整个地停留在一个给定的构成性假设系列所规定的边界中。同时,我们也绝不可能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在其中,每个参与者都分享着每一项的假设。此外,无论一个接近规范性的境遇在什么时候出现,人们都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怀疑,它是建立在对那些不赞同主流共识的人加以压制或边缘化的基础之上的”[4](PP.57~58)。而霍耐特则将政治的公正看作是一种基于承认理论对国家社会整体的不确定性进行不断克服的现实话语。他在对罗尔斯的批判中鲜明地指出,公正理论所创制的公正制度只能满足一种预先设定的平等的自由,而从未充分地考虑过自我实现才是一个公正制度的最终诉求。在他看来,要维系社会交往的关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善,而为了实现这一社会善,就必须克服基于个体自由之上的不完整性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因此,在个体自由之上的不完整性的前提下进行公正理论的创制最终还是无法逃离公正理论在不确定性上的困境,也就治愈不了社会分裂的顽疾。在这里,公正话语的观点是“如果没有这种无拘无束的想象,即由于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世界中采取了一种片面的自由观,因而深受‘不确定性’之痛,那么他们就根本不可能获得互主体理论意义上的正义概念,这种正义概念就存在于现代伦理的观念中”[5](P.75)。那么,要克服创制这种公正概念的“现代伦理”(实则是自由主义的伦理解释框架),并要积极地治愈人与人之间相互疏远而必然产生的分裂,就必须将社会交往作为一种语境条件,实现不同公正主张在开放性的公正话语体系内的自由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发现的公正话语具有治疗性,而持续创制的公正理论则只能是关于何种公正标准具有普遍意义的争斗,其结果不是人在社会中的自由解放,而是对僵化的控制关系的道德遮掩与伦理控制。“换句话说,这种诊疗性的分析对正义观产生了直接的后果,因为深入透视虚假信念,批判地克服社会的病症,会促使人们去把握交往前提,透视自由的必要条件,并满足这些条件。”[5](P.76)在霍耐特等人看来,这就是我们诊断时代的公正理论的意义所在,也正是将公正话语放到政治哲学与意识形态的历史考察中去不断地解释“被发现”之意义,其将克服公正理论现实化的难题,而使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到以公正话语为中心的社会交往中。
(二)“马克思与公正”的话语理论观照是公正话语分析的总体实践理解策略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发现,实现“被发现的公正话语”的实践性建构必须立足于其基本规定性,而实现这种基本规定性的具体规则与实践策略则要植根于呈现在眼前的公正世界。围绕这个公正世界,我们就要通过具体准则对公正话语进行分析。归纳起来,“被发现的公正话语”在分析过程中所需要的具体规则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三)“重塑与扬弃”是公正话语的具体实践理解策略
在形式规定性方面,诠释性沟通视域作为一种新方法论成为公正话语的核心论证方式之一。在自由主义公正理论中,基于话语前提而产生的公正观始终将公正原则优先于公正理论而作为一个公理。公正原则就是个体首要性这一真理的现象之维,故无需证明。那么,公正理论就是要将公正原则的“本真性”论证确立起来,不同的公正理论会因距上述“本真性”的远近而分优劣与真伪,但是公正原则是“形式的”,不会直接地展示给所有人,即便哲人也只能管中窥豹,这就是每个公正理论在方法论上都是创制的原因。但是,问题在于,创制与“臆想”的边界被模糊了。正是因为公正原则与个体首要性之间存在“奴化关系”,所有自由主义公正理论的源头都是在为虚假逻辑辩护。在这里,要么公正理论成为一种典型的抽象理论,要么公正理论成为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两者在现实生活中又往往相互干扰。最终,人们可以发现,任何一个宏大的公正理论大多只能在一些微小的问题上成为具有明显局限的解决方案,而如果回归宏大论证的本质考察,则“最为圆融的理论往往就是最易被攻破的理论”。而我们所面对的公正理论的繁荣以及时常加以运用的一些观点,只是当我们接受了自由主义公正话语的逻辑前提以后在其话语逻辑内产生的一种“假相”,“只看树木不见森林”就是此种创制的公正理论的“臆想之危”。“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致力于创制正义理论的哲学家只关心抽象原则,而忽略了社会现实,因此也就无法区别合法的正义诉求与现实中存在的特定偏见或对权力的渴望。”[6](P.57)这种危害绝不仅仅存在于自由主义公正理论的创制过程之中,因为假如创制此类理论的人坚信或者主张其话语前提的真实性,那么倒不失为一种思想的真诚。而更为重要的是其化身为所有公正理论的普遍做法,即从一种不加考量的公正原则的设定出发(却不考虑这一设定的语境条件),以此投射或者观察某个特定语境中的公正问题,进而创制新的公正理论或作出以公正(或不公正)的评价。正如艾里斯·扬所言,自由主义公正理论需要在方法论上进行彻底的检讨,将公正理论与公正原则的因果关系反转过来,将澄清与批判作为公正理论“创制”与传播的基本方法。澄清指向公正概念本身,“阐明概念的含义、描述和解释社会关系、表达和捍卫理想与原则”[7](P.5);而批判来源于解释公正之立场,“批判立场不是基于某些先前发现的关于善和公正的理性观念,相反,善和公正观念源于行动加之于现状的欲望否定”[7](P.6)。事实上,这样的创制已然不同于自由主义公正话语的一般方法意义上的“臆想的创制”了,而更加贴近于“发现的创制”。
三、“被发现的公正话语”的具体规则与实践策略
在总体现象层面,将话语的语言性与实践的历史性进行综合是公正话语如何运转起来(“被发现的公正话语”所需要的规则策略)在政治哲学层面的根本关怀。在面向公正话语而非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的意义上,这样的尝试表现了公正话语的社会性与政治性阐释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正话语的规则策略离不开“马克思与公正”的话语理论观照,而“马克思与公正”的话语理论观照则必须产生一种实践理解策略。“马克思的实践理解策略包含着两个不可再进行现象学悬置、还原或简约的直观既定性:一是通过语言来理解或显示存在及其现象的基本可能性。二是通过实践这一关于人的此在之外的世界历史性的行动来显示和扬弃非世界历史必然性的某种特定的存在状态——某种非现实性的特殊的现存状态,并显示和建构符合世界历史必然性的社会形态——和谐社会。前者是为了认识世界,后者是为了改造世界。在这两者之间,后者处于始基性的中心地位。两者的有机结合,即存在理解与存在扬弃就构成了马克思关于存在问题的实践理解策略。”[15](P.28)
(一)“摆在眼前”的公正世界是公正话语的分析对象
在真实世界、理想世界与语言表征之间,公正话语的分析在“发现”的层面上只能指向已然存在的事实。不论公正论者如何设想理想世界,他们的分析都应来自于整个现实世界中充满的所有与进行公正评价有关的基本因素。它们以纷繁复杂甚至故意被掩藏的状态存在于公正话语的分析面前。“被用于安排这个‘摆在眼前’的世界以及它的二元对立的那些建构过程,也是朦胧不明的。这个世界以及其中的物体,在其出现时便是已然完成的。人们似乎别无选择而只能接受它现在的样子。话语分析的目的就是要阐明‘摆在眼前’的世界之创造过程所牵涉到的建构活动,因此,在考察问题为何以此种方式被构造出来之前,我们不愿轻易把任何二元对立视为当然。”[18](P.193)因此,在真实世界、理想世界的二元对立时,以真实世界的分析为中心才意味着“被发现的公正话语”是合理可靠的。
(二)“政治正确性”的公正理解是公正话语的分析原点
众所周知,“语言使用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一个国家标准语的建立、语言符号的选择、相同事物不同指称的使用不只是语言使用本身的问题,在许多情况下都可能是个政治问题”[19](P.208)。以此观之,自由主义公正理论创造了丰富多元的公正论,它们具有许多共同特点,其中之一就是设定了公正作为一种“道德的善”并以此作为其立论之基。在这个意义上,个体主义仅是这一预设的合法性依据而已。即便是在最中立的或最消极的公正理论中,情感性的先见都是其创制性的核心特点。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为话语分析提供了一种认识论策略。虽然马克思主义所秉持的唯物史观阐明了道德演进的历史规律,并将任何具体的善恶之感作为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但是唯物史观并不否定道德批判的姿态选择——立场选择。问题的关键是,姿态或立场的选择是“一次性”完成的(虽然在完成之前可能会经过漫长的考察和思考),而在这样的选择完成后,任何道德评价的活动都应该基于一种情感无赦的、真实客观的认识论主张。我们不赞同笼统地承认自由主义的“政治正确性”命题,因为这种承认将上述两个阶段混淆了。这种混淆的后果自然就会催生一些为了证明某些特定的政治正确性而创制的公正观念。例如,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多次提到的“人民”与“公正”,就是以一种新的政治正确性(即强调个体、强调美国人、强调白人利益)取代旧的政治正确性,进而又将这种新的政治正确性掩饰为普遍的公正观念。应当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应辨明意识形态批判存在从消极性定性到客观性运用的差异。“马克思就不应当被解读为是一种带有强烈倾向性的认识论主张,即,我们的所有理念和信念都是由我们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尽管他的表述方式有时会引起这种解读。被如此决定的,并不是人的意识,而是既存于社会中的公共自我意识。具有意识形态性的正是后者,而非他的全部思想和信念。”[1](P.180)简而言之,公正话语的分析是在第二个层面上的运用,即公正话语的反身向内的检视。可见,公正话语分析原点的选择不是任意的,而首要是以“政治正确性”为标准的政治话语中的公正问题的表达。
即孟子认为小孩的“良知”“良能”会促使其敬爱其父母兄长的。孟子的“良知”“良能”就是陆九渊的“本心”。所以陆九渊的“本心”也同样具有发动道德行为的能力。这样我们就可以认为“本心”除了是一种积极的精神,同时也是一种能动的精神。
陶保良也认为,“中国为小农制的国家,现在仍停留在农村经济社会的时代,生产教育,固为当世急务”。生产教育必须顾及农村的经济状况,以改良农业生产技术为主,而“中国的工业,仍为手工业时代,用机器以替代人工的大规模工厂,除外人投资经营外,中国公私方面所经营的是寥若晨星”。因此“在现在生产教育上必具之条件,须以发展农业为主;扩充工商业为辅的一个原则”[6]。
(三)“对社会情境的细致分析”是公正话语的分析方向
公正理论的丰富多元为公正话语的分析提供了诸多大相径庭的分析素材,而后者的目的就在于将这些碎片化的素材整合为一个整体,或者在一定条件下(容易辨识的条件)的若干基本假设或具体结论。与自由主义公正理论内的共识性整合研究不同的是,公正话语的分析所追求的整体不是为了对序列和替代方案形成一定的认同而运用的共识策略,而是在发现“共识性领域”的前提下为所有视角和理论传统提供比以往更多的互动关系。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已经开始主张一种“独立的政治正义观……一个政治正义观具有三个特点:首先,它被设计出来以应用于社会基本结构。其次,它是独立的,‘独立于’由民主社会成员持有的整全的道德学说、哲学学说和宗教学说的概念、价值和原则……第三,某些‘根本直观观念’潜在于民主社会的公共文化之中,它们确立的与其说是某些整全学说,不如说是一个政治的正义观”[20](P.341)。这种观点的基础是将道德真理的公正与政治判断的公正进行一定的区分,他审慎地认为后者的存在就意味着合理的政治判断是独立的政治正义观的中心,这与一般的公正原则建构有所不同。那么,基于真理的共识还是基于政治公正的共识就有所不同了。在这里,哈贝马斯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哈贝马斯坚持(真理与社会共识之间)这种必要条件关系,认为有共识必然有真理,无共识即无真理,共识必然包含真理”[21](P.201),这也就是否定了人们可以在政治的公正观上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不过,哈贝马斯之所以否定了罗尔斯的策略并不是因为无法在政治的公正观上达成共识,而否定的是“独立的政治正义观”是难以存在的,只有“终极揭露”才可能发现“政治的正义观”存在真实的社会情境。哈贝马斯认为,“通过‘终极揭露’,可以一举揭开遮蔽权力与理性混同的面纱——这和本体论的企图是相似的:本体论试图彻底区分存在与表象。但是,如果说,在研究者的交往共同体当中,发现的语境和论证的语境有着紧密的联系,那么同样,权力与理性这两个领域也是紧密联系在一切的,以致我们必须通过程序不断重新把它们区分开来”[11](P.150)。只有被终极揭露后,我们才可能带有对公正的本质性批判的敬畏与警惕,对“摆在眼前的公正世界”中的那些符合“政治正确性”的公正话语找到现实的分析方向。而且,这些方向也不是任意的,必须在前二者的指向下才可能确定。对此,有的学者在分析话语态度和行为时曾经提出三个话语分析的未来方向。“第一个领域是,对复杂的、现成的书面文本进行艰巨的考察……第二个可扩展的领域是对自古就为人所知的修辞学的研究,即如何使用话语以达到说服别人的效果……第三个可扩展的领域是,鼓励话语分析家对意识形态领域予以关注。”[18](PP.198~199)可见,这样的公正话语始终存在于被发现的分析中,而虽然那些不断地指向社会情境多元性的分析方向存在出身于繁杂无边的资料之中,甚至分歧开始所需的资源也难以一一囊括,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分析而将系统分析的重要性和价值性以符合社会情境的判断结果呈现出来,也就达到了“被发现”的本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也是公正话语在分析过程中的一条重要的具体规则。
数据经过分层、分块,以及建立LOD模型,海量3DGIS模型数据已经完成制作要求,即完成了海量城市数据的组织与管理。
[参考文献]
[1]凯·尼尔森.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观念[M].李义天,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2]贾可卿.分配正义论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3]迈克尔·沃尔泽.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M].储松燕,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4]南茜·弗雷泽.正义的尺度[M].欧阳英,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5]阿克塞尔·霍耐特.不确定性之痛[M].王晓升,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6]贺羡.“一元三维”正义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7]IrisYoung.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8]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M].胡继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9]孔明安.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哲学话语[M].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12]杨海蛟.探索公正理解问题的力作[J].探索,2016,(6).
[13]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14]廖申白,仇彦斌.正义与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5]李鹏.马克思哲学的现象学思想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16]罗伯特·韦尔,凯·尼尔森.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M].鲁克俭,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7]R.W.米勒.分析马克思——道德、权力和历史[M].张伟,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18]乔纳森·波特,玛格丽特·韦斯雷尔.话语和社会心理学[M].肖文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9]朱跃,等.语言与社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0]萨缪尔·弗雷曼.罗尔斯[M].张国清,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
[21]杨宝国.公平正义观的历史、传承、发展[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
The Discovered Discourse on Justice—— On Perspective of Distinction of Justice Theory-Discourse
QI Guang
( School of Marxism ,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 , Xuzhou Jiangsu 221116, China )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discourse on justice in modern times starts from the difficulty in explaining the theory of Justice and becomes a universal social problem, so it enters the field of political philosophy.It changes from the analogous issue of theory-discourse in identical thinking to the practicality of theory-dis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tinction.Relative to the innovative Justice Theory, discourse on justice is characterized by being discovered.This is mainly embodied in three basic stipulations: on the practicality of the connotation, the overall phenomenon and the specific practical strategy.In order to truly realize the basic stipulation of the discovered discourse on Justice, it is necessary to determine and select specific rules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present world of justice.In the actual process of understanding the discovered discourse on justice, the analysis object of discourse on Justice must be the world at present.The origin of discourse on justice is the fair understanding of political correctness.Discourse on justice analysis tends to analyze the social situation in detail.The three constitute the concrete rules of discourse on Justice.
[Key words] Discourse on Justice; the Discovered Discourse on Justice; Practical Construction; Theory-discourse; the Perspective of Distinction
[基金项目]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及其实现研究”(编号:2017ZDIXM165)。
[收稿日期] 2018-10-12
[作者简介] 亓光,男,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DOI: 10.14137/j.cnki.issn1003-5281.2019.03.010
[中图分类号] D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281( 2019) 03-0067-08
(责任编辑 屈虹)
标签:公正话语论文; 被发现的公正话语论文; 实践性建构论文; “理论-话语”论文; 差别性视角论文; 中国矿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