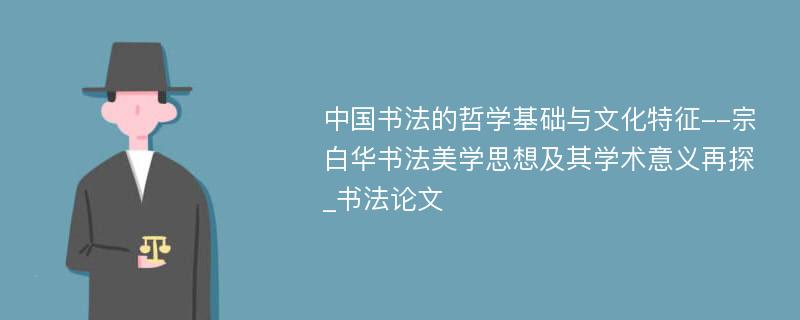
中国书法的哲学基础与文化特质——宗白华书法美学思想及其学术意义重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书法论文,美学论文,中国论文,特质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思想观念不断变革的20世纪初期,书法理论研究却显得相当冷清,整个书坛延续着乾嘉以来的治学风气,偏重于金石学、文字学和考古学的书法史研究是主流,用新观念、新方法进行思辨性研究的理论探讨难得一见,整体上说,这时的书法理论缺乏自觉,而理论的自觉和独立是一个学科得以确立和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从20年代后期开始,一些学贯中西、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者开始关心书法,梁启超、蔡元培、林语堂、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等,不约而同地从美学的角度,给书法理论研究开拓了新的道路,可以说,现代书法理论的觉醒正是从书法美学开始的。
相比其他艺术而言,书法在现代社会中的变革总是最滞后的,而它一旦发生变化却更能折射出中国文化的某些深层问题,因此,书法成为学者们观照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窗口。宗白华的书法美学是中国书法理论从古典向现代转换过程中的一种独特范式,相比之前的古典书论,它具有中西比较视野和现代哲学理据,相比与当代书法理论,它兼具古典美学的诗化色彩,属于传统的“宏大叙事”。
一、20世纪审美主义思潮中的书法美学
用西方美学来研究中国的文艺现象是中国文艺理论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开始,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梁漱溟、胡适、鲁迅等都曾从西方美学的角度来重新阐释中国传统文艺。“上帝死了”之后,人们在感性的、凡俗的“此岸世界”寻找生命的支撑与信仰,艺术取代了宗教,成为现代人的精神家园。而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回归内在性、维护一切生存意趣的此岸性、日常生活的艺术化(诗意化)、艺术代替宗教、对生存持无差异的游戏式态度”,这些本来就被视为“华夏智慧传统”的思想和人生态度,在传统文化价值和精神信仰结构遭到西方现代性摧毁的同时,却意外地、悖论式地成为一条既能沟通西方现代观念又能契合中国古典精神的道路,这就形成了延续整个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一股“审美主义思潮”①。因此,对于现代中国那些最重要的思想家和学者来说,审美主义热潮绝不是为了单纯的感性解放和为世俗生活正名,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反思中国艺术的本体与价值,重新探寻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并阐明其与现代化的关系。20世纪中国美学实际上担负着在民族艺术和审美文化中重建精神信仰的重任,甚至也秉持着反思现代性、为整个人类精神危机寻找救赎的理想。但是,真正完成这一任务的美学家寥寥,宗白华是其中之一。宗白华在中国文化和艺术遭遇大变革的时代,在中国艺术被迫匆匆忙忙地向现代转型时,力图阐明中国艺术精神的哲学本体和文化根基,论证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和现代性意义,并身体力行,用诗意化的“散步美学”和人生姿态,传承着中国艺术的文化品格、民族精神和价值风范,成为民族灵魂的真正守夜人。
与20世纪后期书法美学的主流——侧重技法、构成的形式美学和关注创作、鉴赏的心理美学——不同,宗白华是从哲学本体论高度和整个中国古代思想结构出发去探寻书法的文化特质,他将书法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五四”以来,许多人都质疑书法的艺术地位,而宗白华在30年代就明确指出:“书法为中国特有之高级艺术:以抽象之笔墨表现极具体之人格风度及个性情感,而其美有如音乐。”②后来他又进一步强调:“中国书法本是一种类似音乐或舞蹈的节奏艺术。……中国音乐衰落,而书法却代替了它成为一种表达最高意境与情操的民族艺术。三代以来,每一个朝代有它的‘书体’,表现那时代的生命情调与文化精神。我们几乎可以从中国书法风格的变迁来划分中国艺术史的时期,像西洋艺术史依据建筑风格的变迁来划分一样。”③礼乐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本质,这一本质的最高体现是书法,从这种高度来肯定书法艺术,这在20世纪中国美学家中是独具只眼的。宗白华认为中国艺术将宇宙的和谐、生命的律动和心灵的节奏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中国人的个人人格、社会组织以及日用器皿,都希望能在美的形式中,作为形而上的宇宙秩序,与宇宙生命的表征。这是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也是中国艺术境界的最后根据。”④
对艺术的形而上思索在古典书论和画论中并不少见,宗白华指出,到了现代却被“浅薄的理智色彩”剥夺殆尽,这是生命力衰竭的象征。现代以来,科学主义笼罩一切,艺术研究也逐渐偏重于科学的实证考察,价值判断被事实分析取代,艺术的意义和功能问题被视为是主观的、相对的,难以进入纯学术和科学研究的范围⑤。然而,艺术本体论追问的缺失,恰恰意味着艺术和美学根本无力承担宗教的角色,不可能完成拯救现代人的重任。现代艺术和美学如何把此岸的凡俗性生活和感性世界提升到具有神性的宗教境界?这是现代艺术理论最重要但又往往被不断逃避的问题。同样,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民族艺术的精神特质和形而上根据不能阐明,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延续数千年的文化信仰、审美趣味和艺术理想。因此,宗白华的艺术本体论追问,不仅仅是在为自己的诗意人生寻找根据,也是在为华夏民族的精神信仰和自信心重新夯实地基。
二、“生命之象”与中国艺术的形而上精神
宗白华是从生命哲学的高度来体认中国艺术之美的。宗白华的生命哲学观念主要来自于中国的《易经》、庄子哲学、宋明理学和西方的柏格森等。通过中西哲学和中西艺术的比较,宗白华对生命精神获得了独特的理解:“宇宙生命是以一种最强烈的旋动来显示一种最幽深的玄冥;这种最幽深的玄冥处的最强烈的旋动,既不是西方文化中向外扩张的生命冲动,也不是一般理解的中国文化中的消极退让,而是一种向内或向纵深处的拓展;这种生命力不是表现为对外部世界的征服,而是表现为对内在意蕴的昭示,表现为造就‘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的境界。”⑥这种生命境界是中国艺术的终极追求,中国艺术的价值在于将人最内在的生命情调与外在的无限宇宙打通,有限的生命因具有了与无限的宇宙“同情”的结构和节奏而永恒。因此,根植于艺术家活跃心灵与宇宙律动的“生生的节奏是中国艺术境界的最后源泉”⑦。
宗教、哲学、道德和艺术之间的关系的不同,决定了中西方文化和艺术精神特性的不同。宗白华认为,中国“本之性情,稽之度数”之音乐为哲学象征(后来书法代替了音乐),而西方哲学的象征是数学、几何学。他指出,中国的易学思想中亦重视“数”,不过中国之“数”为“生成的”、“变化的”,充满象征意味和意义性、价值性,故此“数”非空间形体平行之符号,乃生命进退流动意义之象征,“中国之数,遂成生命变化妙理之‘象’矣”⑧。“象”是自足、完形、无待、超关系的。“数”是依一秩序而确定的,在一序列中占一地点而受其决定。“象”与“数”皆为先验的,“象”为情绪中之先验,“数”为纯理中之先验。“象”之构成原理是生生条理,“数”之构成是概念分析与肯定⑨。因此,西方人重推理作用,形成一个概念的世界和“理化的宇宙”观,而中国人重通感作用,形成一个象征的世界和“神化的宇宙”观。西方人爱将感性的形式抽象为确切的数理,而中国人认为感性形式就能直接呈现意义和本质。以感性的“象”而非理性的“数”来表现和理解这个世界,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质。
“‘象’是法象,是‘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是天则,懿德之完满底实现意境。”⑩“象”贯通形下之器与形上之道,“宗教的、道德的、审美的、实用的溶于一象”⑩。音乐、绘画、书法、建筑、工艺、礼器,无不是“法象”,无不是“天则”。尤其书法,“这字已不仅是一个表达概念的符号,而是一个表现生命的单位。书家用字的结构来表达物象的结构和生气勃勃的动作了”(12)。这“象”有中国文字的“象形”的含义,但更多的是指“气象”、“意象”、“象征”,象征生命之“生生条理”,象征宇宙之秩序节奏,也象征了中国人独特的审美意识。如同西方美学从建筑中抽象出美的规律,如均衡、比例、对称、多样统一等,中国美学可以从书法中找到中国人的审美规律,如虚实、向背、避就、穿插、呼应等,这些既是艺术之形式法则,亦是人生之伦理道德规范(法象),更是天道之大化流衍(天则)。
科学和哲学很难直接言说生命本体,而艺术形式可以直接象征、呈现生命本体,因此哲学必须借助艺术之象(如庄子之寓言、柏拉图之神话),或通过阐发艺术来言说生命本体。宗白华正是通过阐发中国艺术的形上境界,完成了哲学和科学所难以直接完成的终极追问和人生安顿,也解释了艺术何以在现代可以代替宗教的原因。因为中国人认为的终极理想和最高关切不必通过抽象的逻辑来论证,而是存留在他们创造的艺术和日常器皿的美中,“我们已见到了中国古代哲人是‘本能地找到了宇宙旋律的秘密’。而把这获得的至宝,渗透进我们的现实生活,使我们生活表现礼与乐里,创造社会的秩序与和谐。我们又把这旋律装饰到我们的日用器皿上,使形下之器启示着形上之道(即生命的旋律)。中国古代艺术特色表现在他所创造的各种图案花纹里,而中国最光荣的绘画艺术也还是从商周铜器图案、汉代砖瓦花纹里脱胎出来的呢”(13)。也正是基于这一原理,后来熊秉明称“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因为书法是中国人“从形而上的抽象思维落实到具体生活的第一境”,中国传统哲学家的终极目的不在建造一个庞大精严的思想系统,而在思维的省悟贯通之后,返回到实践生活之中,“书法写的仍是抽象思维所运用的符号,可又已是活泼生动的具体精灵了”(14)。书虽小技,亦通大道,宗白华把艺术研究视为理解中国人形而上思想和终极关怀的最好途径。宗白华本人的美学即是形而上之哲学,其形而上的哲学亦是美学,“现代中国哲学的各家学说中,宗白华的中国形上学最具美学意味”(15)。“中国哲学正是这样在感性世界、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中去寻求道德的本体、理性的把握和精神的超越”,这就是“中国的智慧”(16)。
三、空间、节奏与中国人的宇宙观
宗白华将“空间意识”作为对比中西哲学、艺术差异的最佳视角,因为空间意识可以折射不同文明的宇宙观,“空间感的不同,表现着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阶级,在不同的经济基础上、社会条件里不同的世界观和对生活最深的体会”(17)。塞尚在空间表现上的实验成为西方现代艺术变革的重要标志,“现代书法”兴起后,空间也逐步成为当代书法理论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宗白华指出,书法最能体现中国人时空合一的宇宙观和生命意识。中国书画都是在二维的空间体现三维(立体)乃至四维(心理体验与联想)空间的艺术。一般认为,书法空间是由字内和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空隙构成的,但书法空间性质的真正特殊之处在于用笔的复杂运动带来的三维空间感(18)。宗白华称之为“力线律动所构的空间境”。这不同于西方几何形线的静的透视空间,而是由生动的点画节奏趋势以引起的秩序感觉(19)。因此,不能仅仅从点画形象本身来解读书法,更重要的是探求点画所引起的各种审美联想(境)。
中国书法中的空间形式是节奏化、音乐化的。宗白华指出,中国字之所以能够成为艺术品,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由于汉字的起始是象形的,二是中国人用的笔(20)。书法的基础是汉字,汉字最初是象形的,但随着汉字不断地发展演化,直接的摹物象形逐渐向抽象的符号化发展,与之相应,字的书写(书法)也逐渐从模拟“物形”转向表现“物本”——生命节奏,从对自然万物和宇宙生命的外在形态的描摹转向对其内在精神的表现,从外在“形质”的刻画转向内在“神采”的捕捉,从外在力量的表达转向内在节奏的暗示,从字形结构的准确、规范(写字)走向情感意志和精神的自由宣泄(艺术)。故艺术形式之最后与最深之作用,“就是它不只是化实相为空灵,引人精神飞越,超入美境。而尤在它能进一步引人‘由美即真’,深入生命节奏的核心。世界上唯有最抽象的艺术形式——如建筑、音乐、舞蹈姿态、中国书法、中国戏面谱、钟鼎彝器的形态与花纹——乃最能象征人类不可言不可状之心灵姿式与生命的律动”(21)。通过变化莫测的毛笔,抽象的点画具有了外在的筋骨血肉和内在的气韵神采,变成了鲜活完整的生命体。一切艺术都以音乐为指归,点画、形式要体现出自然万象之节奏,“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22),这是对物象的暗示与联想。点画、形式与情感意志、社会秩序共节奏,这是通过书法展开的人格化联想。然而这还不是最高的层面,在宗白华那里,中国书法节奏的至高体现是符合宇宙法则——《易经》哲学中的时空节奏。正是这种节奏使书法空间脱离了单纯的形式法则,进入到形而上的境界。书法之难,正在于每笔下去同时要体现形象、空间、节奏、情绪、氛围、意境和形而上之道,看似至简至纯的点画,却要求能激发无限的想象,符合人们对天理世界的冥想。
宗白华认为,中国书画“时空合一”的境界源于古人的生命体验。古人把“时间”的“动”的因素引进了“静”的“空间”之中,秦汉“四时自成岁”之历律哲学,体现了四时(春夏秋冬)之序与四方(东南西北)之位的合奏。古人拿音乐的五声配合四时五行,拿十二律分配于十二月,“时间的节奏(一岁,十二个月二十四节)率领着空间方位(东南西北等)以构成我们的宇宙。所以我们的空间感觉随着我们的时间感觉而节奏化了、音乐化了!画家在画面所欲表现的不只是一个建筑意味的空间‘宇’,而需同时具有音乐意味的时间节奏‘宙’。一个充满音乐情趣的宇宙(时空合一体)是中国画家、诗人的艺术境界”(23)。中国书法形式的变革也与人们居住和观赏的空间转变有关,从案头走向壁上(明代),从书斋走向展厅(20世纪),再从实体走向虚拟(画册、网页、影视再现等),这些空间场景的变化也深刻地影响着书法的表现形式和审美习惯。独特的时空合一观念和“游”动的观照视角,使中国人创造了册页和卷轴等书画形式,它们在摄影、摄像技术发明之前,堪称伟大的视觉创造。徐徐展开的手卷,既是空间的移动、铺展,如变换的镜头在推进、拉远、聚焦、变焦;又是时间的伸展,历史、现在、未来在这里展开,聚散离合在这里上演。时空合一的节奏感,使中国的卷轴书画成为了表现中国人宇宙观和民族心灵的典范。
尤其是通过对《易经》“乾卦”、“鼎卦”和“革卦”的分析,宗白华阐发了中国人时空观念与西方哲学的“几何空间”、“纯粹时间”之根本区别。宗白华指出,“鼎卦”《象传》曰:“君子以正位凝命”,“正位凝命”四字非常关键,“正位”是空间,“凝命”是时间,“人之行为鹄的法则,尽于此矣。此中国空间意识之最具体最真确之表现也。希腊几何学求知空间之正位而已。中国则求正位凝命,是即生命之空间化,法则化,典型化。亦为空间之生命化,意义化,表情化。空间与生命打通,亦即与时间打通矣”(24)。中国人的时空意识背后浓缩了深刻的伦理观念、政治理想和人生态度,与西方哲学和艺术中的时空观存在明显的差异,“我们的空间意识的象征不是埃及的直线甬道,不是希腊的立体雕像,也不是欧洲近代人的无尽空间,而是潆洄委曲,绸缪往复,遥望着一个目标的行程(道)!……中国人于有限中见到无限,又于无限中回归有限。他的意趣不是一往不返,而是回旋往复的”(25)。中国古人理解的时间不是现代人所理解的直线型,而是一个永恒复返的圆环(空间),没有开始,没有终结,生命永远在行进着,转换着,深化着,“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就是中国人特有的生命境界。
当代书法理论喜欢运用完形心理学的“异质同构”理论来阐释书法形式的审美原理,认为书法空间审美意识源于书法结构与物理力学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同构性,而宗白华是用“同情”、“通感”来解释书法与情感、宇宙之间的关系的。人与自然、宇宙之间是“感而遂通”的关系,而不是主客对立的关系,用“同情”、“通感”的思维去对待宇宙万物,人生遂处处充满了诗意。因为体现了人与宇宙这种“同情”和“通感”关系,中国古典艺术便不再是一种平面的形式空间,而是层层深入的灵韵境界。也正是这个原因,宗白华喜欢从“意境”的高度来谈“形式”,称书法形式体现的是一种“空间境”,强调形式所生发出来的层层深入的心灵蕴涵,对于书法形式不能做平面的理解,而应该看到经典的书法作品是一种深层的精神创构,具有一种强烈的召唤力量,它能唤起积淀在观者心灵深处复杂的文化记忆、心理感受和生命体验,使观者迅速地从单纯的形式感中脱离,进入到一个充满历史感的文化对话和情感交流境域。因此,理解书法的前提是理解中国文化,观者必须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生命体验,加上大量的艺术鉴赏和文史知识。
四、汉语的诗性表达与哲学的整全思维
宗白华美学的表述方式与中国艺术的特质极为契合,传承了华夏民族的诗性智慧与独特体悟方式,兼具了哲学追问的彻底性和诗意感受的灵敏力,再现了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感人魅力。但是,这种表述方式显然不符合现代艺术理论的要求,现代理论的“科学性”诉求与传统中国艺术理论那种感悟式、直觉式的“非科学性”之间要划清界限。正如邱振中提出的质问:我们今天能否继续用孙过庭、黄庭坚的方式说出一些他们没说过的东西?这不仅仅是因为以文言文为载体的古代书论不可能在以白话文为基础的现代汉语主导的时代通行,“也不仅因为白话思维取代文言思维的过程,以其逻辑和科学的形式化努力阉割了汉语以神统形的表意传统,致使新一代人难以感悟本土艺术的基质和韵律,从而构成了对书法本体论的潜在威胁;更为重要的是,一种源远流长、习焉不察的生命理性精神,将因寄寓条件的丧失而悄然远去”(26)。话语方式的转变背后是生命感悟方式和整个思维方式的古今转向。因此,问题应该是:今人用现代白话文去言说古典艺术,能比孙过庭、黄庭坚说得更好、更明了、更深入吗?严格意义上说,描述中国古代书法最好的方式还是古典书论式的,今人不能理解和体会古人的原因不在古人的表达方式上,而在古今体物和思维方式的巨大变迁上。我们不可能修改古人的表达,只能是寻找最可能接近古人的方式。通观20世纪中国美学,似乎还没有人比宗白华更好地呈现了中国古典艺术的精神和魅力。其关键在于对古人的情感和思维持“了解之同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27)。
现代艺术理论强调专业化、科学化、学理化、实证化,这是时代的风尚与进步,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宗白华将每一种艺术都纳入到文化的整体结构中去理解,将书法和整个中国哲学、伦理学以及诗、乐、舞、画等文化共生体紧密结合起来,从而避免了就书法论书法。但有学者认为,书法研究的专业化和学科化要求现代书法美学必须从书法本身出发,以书法为“体”,以书法之外的各种理论原则为“用”,找到属于书法自身的基本概念、范畴,进而建立相应的知识结构和理论体系。因此,从这个角度来审视20世纪书法理论和书法美学,存在着明显的“外围化”倾向,不管是用西方的现代理论,还是用中国的传统思想来研究书法,都被视为是“外在”的,都未能将书法作为“主角”,书法始终依附于其他学科,很难走向独立(28)。毫无疑问,要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必须有自己的概念范畴和知识体系,如果始终是借用其他领域的知识工具,那就表明这个学科远远没有走向自觉和成熟。但问题是,现代学术和知识的学科化与分化的原则常常不是基于人类思想和知识的内在逻辑,而是基于社会分工和政治、商业的外在需求,因此,如果从思想的整体性和文化的相关性角度来看,专业化、学科化有时恰恰是“形式的合理而实质的不合理”。书法是放到艺术学下面还是放到文学下面,是在美术系好还是在中文系好?单纯从专业和学科的角度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理论的基础是哲学,但探求整全知识的哲学在现代已经死亡,哲学被分配到了不同的知识领域,如政治学理论、社会学理论、经济学理论、文学理论、史学理论等等。艺术理论实质就是艺术哲学,要真正理解艺术理论,必须回到整全性的思维和知识,就艺术理解艺术,基本是不可能的,把自己禁锢在专业的狭窄空间里,只有死路一条。今人将书法家分成学者型书法家、艺术家型书法家、职业型书法家等,就是一个典型,这种分化与分类体现了书法的艺术自觉和专业化意识,但也暴露了书法在独立化过程中与传统文化母体的背离与冲突,意味着书法的基础已然分裂,是“文化修养”还是“技法”、“形式”更重要?这在古人那里少有争议的问题,却成为当代书坛纠缠不清的噱头。同样,如果认为存在只属于书法的理论知识和阐释框架,那么,书法在与绘画、文学、传统哲学等划清界限的同时,也意味着书法主动将自己赖以存在的文化脐带彻底切割。现代艺术理论和美学思想在强调艺术(相对政治、经济等)自律的过程中,走向了一个误区,过度地强调艺术学科的独立性和自我意识,结果是除了与其赖以生存的文化根基分离外,却依然未能摆脱科学、商业和政治的干预,甚至因为缺乏了文化信仰和价值的呵护,反倒加剧了向金钱和权力投怀送抱的趋势。
宗白华的艺术理论依然保持着一种文化的整体感,今天无法模仿他的原因在于我们缺乏这种“贯通”的能力,即哲学的整全思维。这不是所谓的跨专业、跨学科思维,而是善于从任何一个具体的点抵达知识的整全结构和终极意义的能力。今天的研究者缺乏的不仅仅是全方面的文化修养,更缺乏将每一个具体的现象和局部问题与那些根本性的大问题贯通起来的才能,研究者常常搞不清自己研究的对象到底有什么意义,没有总体性的知识脉络和问题意识,局部做得再好、再精致,也只是钻在故纸堆里的匠人。这是宗白华这样的大家与我们之间的根本性距离——知识运用与价值判断、政治立场,学术探讨与人生情怀、意义追寻是一体的。“学问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29),“学术积累说到底是知识、思想和智慧的积累,不是一群专门家的材料堆积,也不是体制化学术生产的流水作业;也不是小聪明、小做派、小权威的相互模仿”(30)。当代艺术理论越来越细化、精致、多样,但也变得越来越技术化、复制化,越来越缺乏艺术感觉、思想力度和人生智慧,学者的聪明都运用到那些细节化的考证和技术化的理论挪移与嫁接上去了,很少发现和提出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来。诚如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所言:“有关最崇高事物最细微的知识也要胜过有关琐碎事物最确定的知识。”(31)我们常常在小事上斤斤计较,而在关键问题和大事上却如同赌徒。“没有思想,求知作为终极关怀退化为鸡零狗碎的考据,如同一部不断扩大数据的计算机,找不到方向。一个越来越细专业构成的没有思想的知识体系和由一个个孤立的只有欲望(和实现欲望的权利)没有灵魂的人组成的社会是同构的。当大写的人消失时,沟通的理性只是肉体欲望互相投射的幻象。”(32)今日之专业化与社会分工培养出来的技术知识分子,多一曲之士,抱一技之长,“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33)。“道术将为天下裂”亦是今日世界文化、人心和信仰状况之概括。
面对这样的困境,重新认识古典艺术理论不仅仅意味着对历史的重审,同时也意味着对当下艺术理论表达方式的反思。当代艺术创作、艺术批评、艺术理论与艺术教育之间有些分离、脱节,理论家玩着艺术家和大众难以搞懂的概念、主义和词汇,艺术家感叹着自己的意图无人理解,观众得到的是关于艺术的各种奇人异事和八卦新闻,艺术那种打通天地神人、感发志意、凝聚人群、净化灵魂、体悟生命、促进道德的积极功能,难以实现。阅读宗白华的文字,感受是立体的:是学术研究,更是生命对话;有哲理的终极叩问,也有诗意的切身感悟;是理论的层层阐发,也是赏评的步步深入。正如他自己多次提到,艺术与学术,一为理论之探究,一为实践之体验,不同体但相通。他常常一方面是在“概念世界”中分析哲学,另一方面是在“直觉世界”里感受自然的神秘,感觉与思辨在这里得到很好的融合。因此,透过宗白华可以看到,尽管理论如同冰冷的温度计,却应该能敏锐地测量出艺术世界的冷暖。在坚持客观性的同时,如何传达出活泼泼的艺术感受,这是对理论家素养的真正考量。真正的艺术必有穿越、沟通人心之力量,艺术作品可以照亮理论家的智慧和心灵,理论家在阐释艺术的同时,也在阐释着自己,其笔下流动的不是与自己无关的语言泡沫,而是自我与艺术融合而成的共鸣。艺术没有给我们注入什么,而是给我们带出(“自然流出”)了关于宇宙、人生的种种体认和洞见,它让我们发现自己的心灵其实是一个不竭的源泉,因为艺术,我们才变得智慧、清澈而自然。总之,宗白华的理论葆有向内体究的力量,体现出通过艺术而呈现的心灵与宇宙层层深入的交融。
尽管今天的书法理论研究在方法论、学术视野和阐释的系统化层面已有了大大的拓展,但回首书法理论的现代进程,宗白华依然是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其书法美学至少在两个层面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一是从文化哲学的高度,阐明了中国书法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论证了书法在现代社会中的合法性,是今天人们讨论中国文化认同问题的重要资源。二是其理论从书法本体论、价值论出发,涉及书法与中国哲学的关系、书法的内在精神与外在形式、书法审美的文化心理等,全面阐述了中国书法的性质、形态和价值,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方法和概念,在理性认识高度和感性体验深度上,至今难以逾越。
①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09—310页。
②③④⑤⑦(13)(19)(21)(23)(25)林同华主编《宗白华全集》2,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页,第143页,第412页,第246页,第365页,第401页,第433页,第71页,第431页,第437页。
⑥汝信、王德胜主编《美学的历史——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进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54页。
⑧⑨⑩(11)(24)林同华主编《宗白华全集》1,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96—597页,第628—629页,第629页,第611页,第612页。
(12)(17)(20)林同华主编《宗白华全集》3,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02页,第411页,第402页。
(14)熊秉明:《书法与人生的终极关怀》,王冬龄主编《中国“现代书法”论文选》,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15)王锦民:《建立中国形上学的草案——对宗白华〈形上学〉笔记的初步研究》,叶朗主编《美学的双峰——朱光潜、宗白华与中国现代美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37页。
(16)李泽厚:《试谈中国的智慧》,《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08页。
(18)邱振中:《书法:七个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3页。
(22)蔡邕:《笔论》,《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6页。
(26)卢辅圣:《近现代书法论》,《二十一世纪书法》第1卷第1期,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3页。
(27)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9页。
(28)毛万宝:《从外围走向核心——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书法美学研究出发点回顾》,《二十一世纪书法》第1卷第1期,第56—65页。
(29)黄宗羲:《留别海昌同学序》,《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77页。
(30)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3页。
(31)转引自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李世祥等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32)金观涛:《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64—165页。
(33)郭象注、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下,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06页。
标签:书法论文; 宗白华论文; 艺术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美学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宇宙结构论文; 哲学专业论文; 书法特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