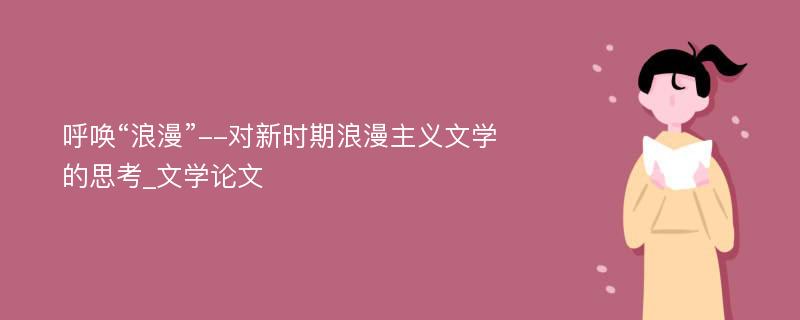
呼唤“浪漫”——关于新时期浪漫文学的忧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浪漫论文,忧思论文,新时期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就当前的文学创作来看,浪漫文学的缺席已是再明显不过的事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浪漫”作为一种艺术风格和批评术语悄悄地从人们的视野中隐退。与此相悖,传统深厚悠久的现实主义文学和新兴的现代主义文学这些年来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并日趋融合相互渗透,持续几年而不衰的“新写实小说”就是范例。它是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心理文学杂交的出色产物,现实的深刻性已直入生存状态、生命本能和潜意识的隐秘领域,它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走向在现实主义的主旋律上固定了一个不太宏亮但很沉稳的总基调,无意中也算是告别“浪漫”的一曲挽歌。
一、命运:“浪漫”在悬空的摇篮中夭折
“新时期”是一个极具历史性、政治性的概念,它代指了自76年以来中国当代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这个概念很快被文化、教育、经济、文艺等意识形态领域所沿用承认。“新时期”绝不仅是一个时间代称,它具有前瞻性、开放性、变革性和创造性的几大时代特征和特定内涵,应该说这样一个解放个性、推崇理想、鼓励想象和创造的社会大环境是浪漫文学滋生成长的肥沃土壤,而蕴藉浪漫情调的文学也是凸现“新时期”积极进取本质特征的最恰当的对应物。
从《班主任》、《伤痕》等作品来看,新时期文学还是从现实主义的路上沉重地起步的,控诉“文革”罪恶,批判极左路线和反思历史教训构成新时期文学早期的创作主潮。但随之而来的哀怨厚重的氛围日趋深沉和无法解脱也无意间形成了社会的惰性情结,其负面影响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作重心转移到四化建设上的现实要求明显脱节。在文学创作徘徊不前的情况下,一种歌唱理想、眼光向前、贴近现实的“浪漫”已是不可避免和呼之欲出,它注定要为在痛楚之中泡得太久而厌倦的心灵送去一些温暖、激情和阳光。《人民文学》1979年7月号刊载的《乔厂长上任记》发出了一个文学可以“浪漫”的重要信号,它的出现标志着一种顺应时代、服从政治、植根于现实,并且极富“浪漫”风格的“改革文学”的诞生。蒋子龙、张洁、柯云路、李国文等人的小说一扫过去文学创作那种痛苦酸涩的表情,在揭示现实发展的未来可能中融入了更具前展眼光的新理性、新思考,将题材的现实化、人物理想化和情绪的浪漫化集结成一种强大的精神推动力,流露出鼓吹积极进取、振奋心智的主体意识。有的研评者把这种创作趋向归结为运用“两结合”方法而不同于单一现实主义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新的风格、新的气质”。
所遗憾的是“改革文学”的激扬文字仅仅是昙花一现的辉煌,尽管乔光朴、李向南、刘钊、郑子云、陈咏明这些形象是社会理想、正义和理性力量的化身,是理想人格、人性和人生的范本,但改革进程的艰难曲折以及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多少使人看到了形象的理想化和创作的浪漫化的幼稚和空泛,这些作品的理想亮色和浪漫与严酷复杂的真实生活情状比照的巨大落差不仅造成反讽,而且连作家自身所坚持的精神理性原则也要为之动摇而更弦易辙。逼近来看,之后的文学创作慢慢进入了一种新的沉重、悒郁甚至灰暗的状态,从“寻根”到“新写实”实际就是浪漫文学被迫退场并被淡化遗忘的悲剧性过程。当然,作为一种历史悠久、影响深广的创作思潮和风格,文学的浪漫也以艺术化而非“改革文学”的政治化浪漫的方式蔓入作家的个体独创之中,这也导致了新时期前期某些作品创作艺术风格上的抒情化和散文化,凸现作者在某一特定心境下的特殊情感,强调人的意识力量对自然存在的超越,象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王蒙的《杂色》、《海的梦》和张承志的《绿义》、《大板》等作品都表现出与现实主义完全不同的艺术品格,无叙述情节的完整交待,个体情感左右作品灵魂,从浓郁的诗意中流露出一种超越现实的浪漫意蕴,创造出了一种自标性灵、不愠不火的审美态势和积极人文精神。
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先锋文学”和“新小说”倒是为浪漫文学的整体性复苏提供了一线生机,因为浪漫文学崇尚个性、非传统理性和超现实的基本内核都是与“先锋文学”和“新小说”的艺术指向相融通的。可惜“先锋文学”和“新小说”拒绝了浪漫的可能,它们的超现实并不是美化和理想现实,相反现实成了它们嘲弄、批判、搓糅和丑化的对象。除了在偏重夸张、虚构和想象等艺术技法与浪漫文学相似之外,它们更多地渲染失常、荒诞、神秘和原始蛮荒,并用极端的个人意识和非理性狂放来抵毁崇高、优美、正义、温暖和浅淡的感伤这些浪漫文学的特长,它们那种现代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是在比现实主义的冷淡还要残酷地碾压碎“浪漫”而铺筑的。
就一个整体性的创作潮流,较之“改革文学”的兴衰突忽,“朦胧诗派”等青年诗人创作中浪漫诗风的演化和丧失则更具悲剧性。就其前期作品来看,北岛的悲壮、舒婷的柔婉、顾城的感伤、江河的激越、杨牧的恢宏从不同的层面映照出浪漫和理想的光辉,他们呼唤真诚、勇敢和执着,追寻真情、理解和信念,歌唱友谊、爱情和大自然。他们这种浪漫完全不同于“改革文学”的政治化浪漫,它是以善美为最高准则的真正艺术化的浪漫,其超然现实、坚信光明理想的底蕴凸现了浪漫文学的精义——美的理想。江河将这种总特点概括为“过去——现在——未来,在诗人身上,同时存在,他把自己融入历史中,同富于创造性的人们一起,真诚地实现着全人类的愿望。”(《上海文学》1981年第3期)但是,“朦胧诗派”的浪漫毕竟也是社会变革初始期的冲动和热情,随着社会震荡反复和自身的解体,浪漫远遁,热情渐冷,其后期创作却表现了咀嚼现实后的苦涩和沉重,慢慢融入了80年代至90年代灰晦沉滞的创作大格局,象北岛的《磨刀》、《无题》,顾城的《吸烟》、《我们写东西》,杨炼的《众目》等有代表性的作品都不难看出理想破灭后的惨淡和灰暗,即便转向写散文的舒婷也在《硬骨凌霄》中冲淡了忧伤和纯情的柔婉,代之的是圆通、成熟的极强现实感。至此,浪漫文学的最后的一线理想之光终于消失在一片灰色、沉厚和冷凝的苍茫之中。
二、反思:由自身脆弱和外力重压导致的没落
浪漫说到底仍然是与现实对峙、抗争及其否定的产物,其要义是突出精神意识的主体作用来激活人们内心世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改造现实的邪恶和失常从而创造合理完善的人类生活。但另一方面,浪漫也需要各个社会现实层面给予配合,既需要人们的精神需求的内在压力大于物欲的扩张,也要社会情绪不溺于计较现实得失的近视,社会的大环境也不能全然无序令人无所皈依,现时政治意识形态须与社会情绪相一致。这些条件的残缺都可能造成浪漫文学的衰微和消失。
浪漫文学在新时期的发展首先遇到的就是政治意识这样一个难题。从十七年和“文革”的“政治文学”来看,浪漫其实就是“革命理想”“革命英雄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的同义词,它作为一种艺术风格必须首先服从题材的选择、创作思想的确立这些内容性的需要,浪漫是一种教化工具和内容标准,从而也在文学脱离现实、从属政治的空泛创作潮流中起过相当虚伪的作用。无论是“主题先行”、“三结合”,还是“高大全”模式都可以看到历史上作为艺术标志的浪漫在政治的高压下异化为政治理想的过程,这种情况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复杂而深入的。即便是“改革文学”也隐约可看出历史的余波,张洁有一段自白对于理解“改革文学”的浪漫的本质内涵是很有帮助的,她说:“我的思想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之中”。(张洁《我为什么写〈沉重的翅膀〉》)从张洁、蒋子龙、柯云路等人的《沉重的翅膀》、《爱,是不能忘记》、《乔厂长上任记》、《新星》一系列“改革文学”作品我们不难看出政治意识的强行进入以及传统“革命理想”的余光,其成功也在于强烈的时代感和政治性。“改革文学”的迅速退潮和这种浪漫的消却,表明浪漫文学与政治形态联姻构成的关系非常脆弱,其致命弱点在于它是主观意识(尤其是政治意识)的浪漫,而非从平凡实在朴素的生活中,从痛苦失意和烦琐中品嚼出的诗意处理和艺术化的浪漫,这种与现实间距太大的危机和与以往“政治文学”不清不白的联系伴随着它的兴亡。
与“浪漫”所展示的理想生活和彼岸世界相比,客观发生着进行着的真实现实无疑是强悍和有颠覆功能的,它能将人从一种幻化的虚空沉醉中拉到琐屑、平淡的真实景象中来,用长时间的磨损力慢慢腐蚀人的精神、意志和感情,将一切有意义的主动追寻导入无意义的受动行为,这对“浪漫”的基础无疑是釜底抽薪。从80年代至今,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处在急剧动荡变化之中,市场经济的确立,商品观念的形成,极大地冲击了人们满足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传统观念。而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各种西方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也潮水般地涌入中国,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精神状态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传统的政治信仰、道德准则和价值观以及人生观都在动摇,社会行为呈现出一种无序紊乱的复杂状态,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官僚主义、虚无主义杂合在一起物化着人的精神追求,一方面是欲望的扩张,一方面是理想的萎缩,它致使人们用一种空前现实的态度去对待金钱、权力、婚恋和文化,一切没有直接经济效益的文化形态从现实生活中淡化退却乃至牺牲,“实用”和“可操作性”成为价值取向的重要标准。在社会由意识向物质、由文化向经济、由“可能”向“所能”的转轨过程中,“浪漫”已被逼到了非常尴尬可怜的角落,它几乎被视为“空想”“浮泛”的同类,作为一种艺术精神和审美观照的“浪漫”不仅无力提升现实的未来可能因素,反而在复杂纷繁多变的真实生活的映衬下显出了幼稚、荒唐甚至苍白。张洁在1986年发表的《他有什么病》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事件,评论界一致认为:张洁变了。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不仅是一个极度崇尚理想的浪漫女神的倾覆,其意义真正的深刻性和普泛性在于现实严酷事实的挤压和侵蚀已使浪漫文学的生存发展面临困境和节节败退。更要命的是,现实的发展变化甚至对浪漫载体的文学本身也构成生存威胁,商品经济大潮无情地将传统的严肃文学抛向了市场,精英文学受冷落,作家无斯文,纯文学书刊难售,这迫使作家必须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去对待创作,以商品文学、通俗文学、影视化和现代传媒的方式去融入大众文化延续生命。这表明现实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作为艺术方法的“浪漫”,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消蚀了作为作家精神创造素质的“浪漫”,这就不可避免造成文学媚俗流泛、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以及精品意识退化丧失的直接后果。
从政治传统和现实反差的角度去探究“浪漫”丧失的原因,毕竟还是外部因素。从内部同源的角度去看,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扩张和吞噬是导致“浪漫”衰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客观地看中国文学历史发展,现实主义文学较之浪漫文学有着更大的生命力和征服力,浪漫文学一直是现实主义文学的附庸和陪衬。新中国建立以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始终是占主导地位,“浪漫”只是提升现实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它理论上和操作上都是相当含混的。虽然新时期文学借鉴吸收了许多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意识、思想和技法,但现实主义总有办法将其化解到属于自己的范畴,独尊现实主义和确保现实主义的主导地位是中国文学至今没变的根深蒂固的思想,诸如“改革文学”、“朦胧诗”、“意识流小说”、“荒诞小说”、“新小说”等非现实主义的创作都被贴上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标签,现实主义文学成了一个无所不包容的普泛体系。在现实主义的消解蚕食下,作为一种独立的、与现实主义并行发展的浪漫文学根本没有生存的余地和空间,说得直率点就是只有文学的浪漫化而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浪漫文学。
三、转机:文学的贫困和“新浪漫”的可能
拒绝浪漫也许是文学力图更深入更真切展示现实的一种无意的决择,但这种内在创造素质的丢弃并未给文学的向前发展带来多少生机和活力,在“浪漫”被抛弃的同时一种原来宝贵的积极人文精神也随之淡薄,文学的社会启蒙功能和超物质功利性质也随之改变,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新时期文学从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整体风貌,使文学的艺术风格、审美时尚和创作心态都沉浸在一片灰色的深刻中。
从1985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开创中国现代派小说算起,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血脉相通的中国式流派和创作思潮此起彼伏,象徐星、莫言、韩少功、阿城、残雪以及“新小说派”的创作风格各异,意趣相去,并与西方现代文学各有宗本,他们的作品的确表现出了一种与传统现实主义截然不同的新内容和新气象,在破除政治神话、文化习规和“反映论”、“阶级论”以及“典型化”方面有着重大的突破,为人们认识现实的复杂现象和终极本质,认识“自我”的丰富层面和发展的艰难性、局限性开启了一些新窗口,实现了文学从对生活现象概括向哲学本体论终极意义探索的飞跃。但是,从各种现代派文学创作的情绪化因素来考察,不难看出其思想的深刻来源于现实思索剖析后的极端冷静,其关注的焦点始终是现实的无常、荒诞和病态以及造成主体的人的异化窘相,“不可知论”、“宿命论”、“神秘论”和悲观主义是弥漫在其中的总的人生基调。
无论怎么说,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始终与真实客观存在的现实之间隔着一层空间和距离,它对现实及其人性的批判停留在哲学本体论的阶段,稍后兴起的“新写实”小说把这一个虚空填满了,它将矫情做作的伪现实主义文学的粉脂气和五彩光晕一扫而尽,并用“生活流”和“纯态事实”的记录反拨了现代主义文学形而上的高蹈玄思。在刘恒、刘震云、方方、池莉等人笔下,生活流程及表象被分解成一幅幅令人沮丧的难堪画面,分解为油盐柴米、吃喝拉撒、七情六欲、生老病死这些最普通真切的人在现实生存的挤压状态下根本崇高、自由和浪漫不起来的那种庸俗、狭隘、丑陋和卑微的心理活动过程。在表现生活无常和人生无奈的这层意义上,“新写实”与以前的现代主义小说比有着更大力量,它更容易激起一种社会情绪对比的强烈反应并认同现实的平庸无奈。“新写实”的成功和创作思潮的风靡,不仅是对“新时期”的社会理想和终极目标的嘲弄,其实也反映出现时文学在现实生活面前的孱弱、无能和贫困。当文学只专注于“审丑”而不能进行美善的升华,当文学只沉浸在“怀旧”和生活流程的真实展示而不能暗示社会发展本质规律,当文学只能喻人顺应自然乐天安命而不能激活理想鼓起信心去征服自然改造现实的时候,那真正应该被揭皮三层、诊治痼疾的不仅仅再是社会、历史、文化和人,反倒应该是文学本身。
正是在这种对文学发展的总体观照的基础上,我感到新时期文学对“浪漫”的遗弃绝不单纯只是一个艺术方法的问题,它反映了出文学的使命感、创造力、亲和力等积极人文精神的全方位塌方的严酷事实。从文学的社会地位、作家的创作心态、作品的精神内涵等方面来看,再也没有什么时期比现时文学更加令人失望沮丧了。在文学滑坡、创作受阻、各方面都不太正常的情况下,随着“重建文学”、“恢复道德意识”的呼声日益兴起,是否预示着一种新的浪漫文学的浪漫精神出现的可能呢?从王蒙的《恋爱的季节》、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史铁生的《第一人称》、刘继明的《海底村庄》和杨争光的《蓝鱼儿》等作品中,我们已感到文学创作出现的一种转机。
要使文学创作实现“新浪漫”首要的一点就是要做到“精神的浪漫”。这里面包含着两个层次:一是作家的创造主体意识的强化,要重新确立和鼓起献身文学、揭发病痛、贡献信念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以健康正常的心态看待转轨时期文学的地位和自身工作的价值,要率先垂范地实现从“有想法(思想)的人”到“有理想的人”的转变,把对现实生活的艺术表现和把握历史发展未来紧密地结合起来。第二是强化作品意蕴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文学作品绝不能从现实的起点再回复现实的终点,它总得留下一些发人深省、耐人寻味、给人振奋、催人泪下、令人情动的某些独特感受,使人从历史和现实的场景中感觉到未来发展的可能。这种意蕴不仅要揭示社会发展因失衡造成的苦闷、隔膜和荒诞,更要将原本存在的温暖、关怀、情谊和人的能动性传达出来,以顺应和平、发展、团结这样一个时代的总趋势。中国的作家应该从大江健三郎的创作中感觉到什么,他的《个人体验》、《燃烧的绿树》不乏生活的沉重失意,但更有生命的美丽和人性的光辉,对人生终极目的和价值的求索是以父子之情为温暖底色的。
现时文学创作的情况表明,文学不是疏离了生活而是过于逼近生活的自然形态消融了自身,作家往往成了历史场景和生活现象的尾随者,这就造成了反映和认识层面的单调和重复。“新浪漫”就作品本身而言还需要提倡“题材的浪漫”,从历史上的浪漫文学来看(如《山海经》、《西游记》、《聊斋志异》等),人的现实完全可能从神话传奇、寓言的角度进行新的艺术再现和创造,文学也完全可能据此反映一种主观性较强的精神生活和理想生活(就象弗洛伊德说的“新型的现实”),未来的生活和理想的实现是在自然趋势和人的动能争取合力作用下完成的,文学有义务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作有益的引导和勘探,狄德罗就曾经说过作家是群众生活的指导“老师”。文学作品“题材的浪漫”不仅能够极大激发创作主体的作家的想象力,也会给受众对象以多方面的精神享受和更多的轻松消遣愉悦,从而使文学创作和欣赏成为一种疏导郁闷、缓冲生活压力的有效途径。
在文学创作的具体过程中,“新浪漫”还应该有别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段,这即是“技法的浪漫”。这要求浪漫文学在文本结构、叙事方式和语言特征上形成自己更为抒情化、更为夸张也更加不墨守陈规的风格;另外对于时空关系的安排、细节具象的处理、情节线索的分布等问题也应当具备更强的主观审美性,以区别于现实主义的“真”和现代主义的“幻”,应该充分调动起一切创造美感的技术手段来形成一种健康的、新鲜的情绪化氛围,让充溢着温暖、爱心、诗意、净朗的“美的文学”重返艺术世界。这一时刻对于人们干涸凝滞的心灵来说已是期盼许久的了。
缺乏理想和激情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社会,拒绝理想和浪漫的文学同样也是没有希望的文学。在目前社会各种机制都不太健全合理的条件下,文学要真正“浪漫”起来显然是个艰难复杂的漫长过程,但在这世纪交替、文学创作何去何从的决择关头,文学的确是该认真地反省自身。针对当前文学创作过度迷执于现实和存在真象探索而无意超脱的局面,我想重复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一段不无启发的话,“小说考察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不是既成的东西,它是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是人可能成为的一切,是人可能做到的一切”。正是出于对艺术之美和一切“可能”的憧憬,我才发出一声对“浪漫”的深情呼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