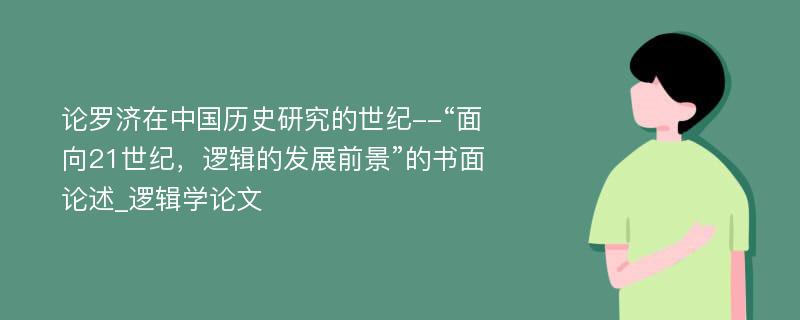
中国罗辑史研究世纪谈——“面向二十一世纪,逻辑学发展前景”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逻辑学论文,发展前景论文,中国论文,二十一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指顾之间20世纪即将过去,21世纪就要到来。在这世纪相交之际,回首近一个世纪的中国逻辑史研究,思考和展望这一研究工作在新的世纪中的深化与发展,是很有必要的。
长期以来,中国逻辑史研究不仅被我国逻辑工作者视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更受到了国家的支持,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与成绩。
然而,当我们以冷静的思考去审视既往,并展望未来的发展时,就会感到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一些问题。其中,更新方法以拓宽思路是尤应注意与讨论的。本文拟就这一问题提出看法。
中国逻辑史研究非自今日始。“中国古代有没有逻辑?”“逻辑在中国历史上的状况应当如何认识与评价?”这些问题是随着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传统逻辑的传入我国而被提出并受到关注的。早在明崇祯九年(1636年),李之藻在所译《名理探》“自序”中就曾盛赞“西儒”所传之逻辑学(《名理探》)“于明悟为用,推论为梯”,是“格物穷理之大原本”;慨叹我国缺此学问,致使世人“侈谭虚无,诧为神奇”,难于获得真知。这实际上是对逻辑在中国历史上状况的评述,已属于中国逻辑史的范围了。
到了19世纪下半期,随着列强的入侵,西方近代文化以更大的规模涌入我国。这种伴随着深重民族危机而来的西方文化冲击,引发了长期自诩处于“天朝上国”、“文化中心”的中国知识界的一种矛盾追求:一些人既强烈要求学习西方文化和技术以救亡图存,又要显示“中学”比照“西学”的绝不逊色。于是,从已经丧失活力的儒家以外的先秦诸子中,发掘与“西学”类似的传统文化,使之作为移植西方文化的合适载体,这就成了当时一种可行的选择(参阅胡适《先秦名学史》)。
基于上述的设想,先秦名学与辨学,尤其是墨家辩学,以其重谈说辩论、讲科学技术、求认知方法的特点,被认为足以与西方哲学和科学,特别是逻辑学相当。“光宣之交,博爱之教,逻辑之学,大张于世。而孔门言语之科,不闻论辩之术。孟轲剧口之谈,亦多不坚不可破之论。加以儒克已慎修为教,更无舍身救世之慨。惟墨子主兼爱则杀身以利天下,出言谈则持论以立三表。事伟理圆,足与相当。”(栾调甫《墨子研究论文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名学与辩学为重点的中国逻辑史研究,被纳入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之中,形成了空前的热潮。这种热潮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梁启超于1904年发表《墨子之论理学》。
推动中国逻辑史研究形成热潮的“西学东渐”不仅影响了这一研究的文化价值取向,也为其提供了方法,即以“东渐之西学”(西方传统逻辑)为依据的解释方法,也可称之为“据西释中”的方法。这种方法影响至今。它的根本特点是,“以欧西新理比附中国旧学”(梁启超《子墨子学说》),“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在中国逻辑史的研究中,“据西释中”的“比附”、“训释”、“衡量”的实质,是以西方传统逻辑的理论、概念和体系为模式去解释和重构名学与辩学,并进而证明西方传统逻辑在两千年前的我国早已存在,只不过未被认知和宣述罢了。
应当肯定,以西方传统逻辑为依据去重构和解释名学与辩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确有一定意义。如,使名学与辩学研究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转换了指导研究的观念,走向全新的发展道路;推动名学与辩学的研究者在校训古代文本的同时,更注重义理的系统整理与阐发;切实又有实效地在中国知识界传播了西方传统逻辑;为后起的中国逻辑史研究开拓了思路、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借鉴。
然而,这种方法也有严重的缺陷。它把以名为对象,以名实关系为基本问题,以“正名”为核心内容的名学,以及以谈说论辩为对象,以谈说论辩的实质及功用为基本问题,以谈说论辩的原则与方法为核心内容的辩学,完全等同于以正确思维形式及其规律为对象,以有效推理规则为核心内容的西方传统逻辑。这种等同模糊了对于对象、内容有别于西方传统逻辑的名学与辩学的认识,也使名学、辩学与西方传统逻辑的具体对应难免牵强比附的成份。
为了克服上述缺陷,深化中国逻辑史研究,应当改变“据西释中”的方法,更加注重历史的分析与文化的诠释。
对于被视为中国逻辑史研究重点的名学与辩学而言,所谓历史分析,就是深入分析名学、辩学产生的社会背景和面对的问题,以及学派代表人物的追求和动机;所谓文化分析,就是视名学、辩学为先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参照先秦时期的政治、伦理、哲学和科学思想,以及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对名学、辩学的理论给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阐释。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当然不排斥比较,只是要求这种比较研究必须以明确认识名学与辩学得以产生并受其制约的根据——社会的和文化的背景为前提。
我们所以提出用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的方法代替以西方传统逻辑为唯一参照模式去解释和重构名学与辩学的方法,是因为任何一种学术思想的倡导者都是生活于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人。因此,要理解一种学术思想,就要探求孕育并生成这种思想的根据——思想家置身其间的社会环境、面对社会提出的问题、一定的文化背景和思想家的动机。有了对这些因素的认识,才有可能进一步理解受这些因素制约所形成的这种学术思想的特有性质,也才有可能更为客观地去解释涉及这些思想的文本。而所有这些,仅靠使一种学术思想与外来文化进行比较(更不要说单纯认同式的比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对于中国逻辑史研究方法更新的必要,我们可以举出对墨家辩学的核心概念“辩”的解释为例,作一些说明。
“辩”的真义和本质是什么?按照“据西释中”的比照对应,“辩”等于“逻辑”。“墨辩”两字,“用现在通行语翻出来,就是‘墨家论理学’”(梁启超《墨子学案》)。但是,当我们认真研究墨家自己关于“辩”的论述以及影响墨家论“辩”的相关因素时,就会发现上述解释的失误。
墨家提出:“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墨子·经说下》)。这说明,墨家的“辩”,属于是非之谓的论争,其意在“取当求胜”。所谓“当”,就是正确、恰当。如“所染当”、“所染不当”(《所染》)。判定言论“当”与“不当”的根据,则是墨家提出的标准。“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尽计;……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天志上》)。
墨家所以把“辩”规定为“取当求胜”和“判明是非”的手段,而不是认识科学真理的方法,这是由特定的背景决定的。
首先是墨家思想特定阶级内容的要求。
墨子出身低微,做过工匠,曾自称“贱人”(《贵义》)。墨家代表“农与工肆之人”,其思想反映了属于社会下层平民劳动者的利益。墨子不仅指斥“当今之主”“暴夺民衣食之财”(《辞过》),更提出“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非命下》),“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非乐上》)。
很显然,墨家的这些主张必定要受到统治者及其思想家的反对。例如,孟子就曾斥责墨家的“兼爱”为“无父”的“禽兽”之见(《孟子·滕文公》);荀子则把墨子归入“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之人(《荀子·非十二子》)。此外,忠于传统的一般士人也会对墨家主张有所非难。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行“义”倡“兼”而又无权无武的墨家,把“谈辩”列为成就义事的首务,并以“取当求胜”为其特征,就是很可理解的了。
其次是百家争鸣以及反辩和非辩学派的推动。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激变,诸子并起,百家争鸣,谈辩成了政治和思想斗争中的重要手段,成了不限于一家一派的普遍社会现象。社会的现实要求对谈辩进行深入研究。
然而,在实践中对谈辩十分认真的思想家,在理论上对谈辩的态度却大不相同。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有的主辩、倡辩,有的反辩或非辩。
孔子以“克己复礼”为理想,以“学礼”、“知礼”、“礼以行之”为头等大事。谈说论辩不仅无助于“学礼”、“知礼”,反会使人“进退无礼”,因而被孔子认为是不必要的,甚至是可憎的。老、庄以消极无为的人生观和不可知论的哲学认识论为据,认为借助谈辩去分辩是非,判定胜负,是不可能的,所以所谓的“辩”是毫无意义的。
面对社会的需求和反辩派对谈辩的指斥以及非辩派对谈辩的否定,重辩、倡辩的墨家从理论上论证并肯定“辩”有“取当求胜”的本质特征和“明是非之分”的功用,以使自家的谈辩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成为责无旁贷的事情了。
再次是中国古代文化重人文特点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化有突出的人文精神。这是指在人、神、自然三者中,以人为本的、十分注意和强调人的生存、发展和人的地位、价值的文化精神。例如,孔子曾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这就使人为先,而鬼神为后了。
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人,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群体中的一分子。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孟子更指出,只要是一个人,就要百士为他提供必需品;如果一切都自己干而脱离他人,就是让天下人疲于奔命了(见《孟子·滕文公上》)。总之,人是相互依存的,是做为群体而生存的。
这样,人生存、发展和实现价值的基本条件就是群体环境——社会的和谐。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就是这个意思。为了实现这种和谐,以伦理规范为内容的人际原则和以社会治乱为中心的政治问题,就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关注的中心。中国古代文化的这种人文精神,必然导向道德方面正误、当否的讨论与辨察,以使人们认识和确立自我在社会关系中的正确位置及相应的行为规范。
墨家自身思想及所处文化氛围均有浓厚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使墨家通过谈变辩以告知人们的,主要是以“兼相爱”与“交相恶”等为主要内容的“取舍是非”与“当否胜负”之理。墨家认定“辩”为“取当求胜”和“明是非之分”的工具,这是与中国古代文化人文精神的影响分不开的。
总之,墨家的“辩”不是认识客观真理的逻辑方法,而是“取当求胜”、“明辩是非”的工具。
这个例子表明,运用“据西释中”方法,把名学与辩学定位于西方传统逻辑中国型的中国逻辑史研究,不利于对名学和辩学的客观阐释,也有碍于对逻辑在中国的真实状况的认识。反之,如果我们转换方法,视名学与辩学为先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结合它们产生的社会与文化的背景来分析和解释其内容,这就会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名学与辩学,以及它们与西方传统逻辑的区别。
这种研究方法的转换,实质上也是思路的转换。“据西释中”的方法使我们更多考虑的是名学、辩学与西方传统逻辑如何“往往相印”(梁启超《子墨子学说》)。因而,二者在具体内容与体系结构上的相符,以及对之作出精细说明,就成了这种方法提出的研究焦点。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的方法则不然。它不仅可以使我们正确比较名学、辩学与西方传统逻辑的同异,更促使我们思考有关逻辑学及其在中国发展状况的一些根本问题。如,逻辑学的发展是否既有共性也有个性?逻辑学在中国发展的特殊性是什么?哪些因素制约着逻辑学在中国的发展?这种制约是如何实现的?逻辑学的发展与滞后对社会与文化发展有什么影响?逻辑学在中国的相对滞后对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发展有哪些影响?我们应当怎样吸收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以推进我国逻辑学的发展,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我国今天的文化建设与社会发展,等等。
我们相信更新方法以开拓思路,将会有助于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深化与发展,并使其以崭新面貌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