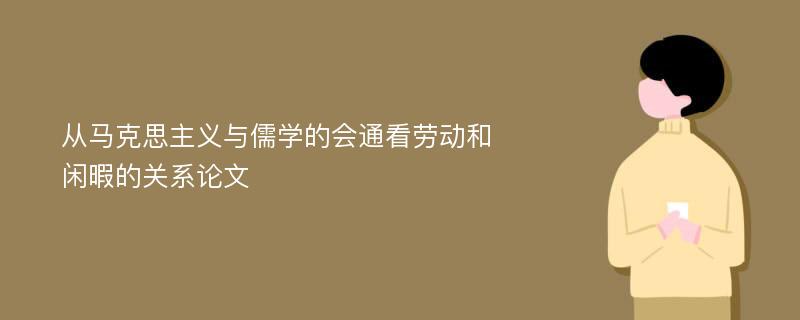
【哲学研究】
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看劳动和闲暇的关系
陈 兵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摘 要: 马克思主义的日常生活理论,主张人的劳动有塑造自我和创造历史的意义,而日常生活则是人民创造历史的现实基础。但马克思只肯认了日常生活的基础性意义,没有注意到家庭人伦具有人之为人的基源性,而儒家重视对人伦日常的超越意义。真正的家庭闲暇应是人保养劳作之余的能量和时间享受亲情生活,使自身的生命条理化、道德化。劳动与闲暇的关系是互为基础又互相发明,同体而异数。基于人伦亲情践履充实的日常闲暇而展开的社会化劳动,乃是实现人性自由解放的必然。综合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可以在对日常生活的不同理解,在劳动与闲暇的辩证关系上实现会通的可能。
关键词: 劳动;闲暇;家庭亲情;同体异数
在中国的现代性探索中,由劳动、实践而人之为人的心灵世界秩序的构建,是当代哲学思考的重中之重。马克思对劳动的考察,有力地解释、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制度的剥削本质,却将工人复杂而主观的生命活动化约为具有空间化的时间计量性特征的劳动力,此一客观化、理性化的做法,割裂工人活生生的生命活动的整体性而无法形成对劳动即人的生命活动的内在理解。他还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日常生活,而把日常生活视作人民劳动创造历史的现实基础。[1]关注日常生活也就是家庭闲暇成为劳动哲学叙事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揭示了人的日常生活之于历史创造的基础性地位,日常生活为人的历史的解放提供可能。然而问题不止于此,日常生活的消费化隐伏的生存危机意味着解放终归是内在的精神觉悟。而从儒学的视角出发审视以“人伦亲情”为内容的日常生活,将为我们理解马克思日常生活批判思想提供新的方向。下面笔者试图沟通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就日常生活的相关论述,从劳作与闲暇的关系的探讨入手,对人之日常性有所思索,以期对人的解放问题有所献益。
一、劳作及闲暇的必要
劳作与闲暇是生命日常的有机单元而互相节制,共同关系到人生存的整体性。《古诗源·击壤歌》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2]1据考证,这是颂扬帝尧之世先民自由劳作的烂漫生活格调。人因为他的自然血肉造就的躯体,不得不在原始氏族时代依照日月的节奏生息着,日常使用自己的劳力作用于生产,虽受部落群体的支配安排却具有最大限度的自主性。然而,工业时代以降,生产疯狂侵蚀劳动力的寿命时,[3]191-192才突然意识到拥有富足闲暇对人本身多么意义重大。也就是说,只是在社会化劳动对普遍人的日常生命时间的侵夺时,人因为闲暇匮乏而逐渐形成真正主宰自己生命的自觉,并期待日常闲暇的降临。
日常的劳作,而不是闲暇,首先进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审视视野。只有在劳动的基础上,谈论日常闲暇才是可能的。反之,只有保证人的日常闲暇,强调劳动才是有价值根基的。马克思强调,人由农民到市民的重要转变,具有文明划时代的性质,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工厂主从而获取经济乃至人格上的独立。但问题是,资本疯狂追求剩余价值,工人被迫沦为工作的奴隶而丧失必要的休养闲暇,因而争取正常工作日和必要生活闲暇逐渐成为关注人健康生存的焦点。《资本论》中对工厂手工业时期面包生产的非人状况,为我们研究日常劳作的限度和人的生存提供了经典材料。[4]288-290
(1)高运营成本。秸秆直燃发电尚且还是一个新兴产业,在价格水平的问题上,国内依然没有可以参照的体系。以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秸秆发电成本约为常规火电成本的1.5倍。一方面因为秸秆发电机组投资成本较煤电机组高;另外,通常秸秆发电机组容量较煤电机组的小,热效率明显低于常规火电机组;三是秸秆燃料的低位热值相比于煤炭少50%,并且秸秆重量轻、密度小,体积大,运输和储存的难度高、成本大,这将导致偏高的燃料成本。
护理后,两组共13例患者对护理工作不满意,其中观察组1例对照组12例,这表示人性化护理确实能提高满意度,与常规护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西方人关于闲暇的定义,依据的是个体主观的情绪感受,而非儒家的理性化的人伦情感。G.A.柯亨提供了发达资本主义中的“闲暇”定义:“这里使用的‘闲暇’是广义的,大致上与‘摆脱令人厌烦的活动’同义,‘劳累’指活动达到令人厌烦的程度。”[8]321柯亨在此处提出的这种划分,区别于经济学上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的区分,强调了人对时间的内在情绪感受如“厌烦”“劳累”,而闲暇指人克服产生负面情绪的劳动的束缚,达到身体和心理情绪上的轻松状态。由于柯亨不仅从主观的方面(人的具体心灵感受)又从客观的方面(摆脱令人厌烦的活动所带来的时间、能量的富裕)来理解闲暇,这使他获得了在对闲暇的广义理解的同时也将此范畴泛化处理了。
然而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所指出的上述敏锐察觉,并没有在后来的历史中被重视,资本的触角肆无忌惮地伸展到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各个角落,资本对人的统治达到了细枝末节的、令人发指的程度。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自动化机器爆发出惊人的生产力,为工人们赢得了更多的闲暇和不错的收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从生产主导的生产社会过渡到消费主导的消费社会。在消费社会中,人的日常闲暇不可避免地全面消费化了。让·鲍德里亚在其《消费社会》中一针见血地指认到:“我们处在‘消费’控制整个生活的境地。”[5]6又“它甚至还支配着——而这才是我们的兴趣所在——休闲与自由时间。”[5]170在消费社会中人仍然是物的奴役,但这种奴役并非不可认识,原因就在人自己。正是人非商品化的家务需要和家庭闲暇生活沦为商品化的耗费性需要,后者的增长催生、加剧了交换价值和交换冲动。人因此丧失了对表现为家务劳动的自由时间的享有,日常生活全面而深入的物化。“休息、放松、散心和消遣也许都是出于‘需要’,但它们自身并没有规定对休闲本身的苛求,即对时间的消费。自由时间,也许意味着人们用以填满它的种种游戏活动,但它首先意味着可以自由地耗费时间。有时是将它‘消磨’掉,纯粹地浪费掉。”[5]172问题不在于人们“闲暇着”,而在于是否以完全自然的方式体味闲暇的真谛。毋庸置疑,儒学所注重的儿孙承欢膝下、阖家欢聚一堂的家庭闲暇,才是日常闲暇的本真面貌。换言之,人伦亲情才是最切己的,人在此切己的生存中才能感受到时间内在于自我,不如此便失去了对自由生命时间的领悟。
老福接过她手中的礼物,客气地请她入坐,她站在那儿不知所措地望着老福的母亲,好像要征得她的同意,老太太拉着她的胳膊让她坐下。没说几句,小宋眼圈就红了,眼泪开始吧嗒吧嗒往下掉,老太太一边安慰她,一边把茶几上的一盒纸巾递给了她。小宋一把一把地抓着纸巾抹眼泪,一句话还没说出来,那盒纸巾都快抓完了。就这样三个人在一起坐了几分钟,小宋终于开口了:“多好的人啊,就这样没了,我到现在还不相信。她除了脾气不好哪都好,是个直性子人。”说完抽泣了半天才平静下来。
二、家庭闲暇批判
作为日常闲暇的家务劳动,是独立于机械性劳动之外的自由的、属人的劳动,亦即人之为人的自由生活。马克思早在机器化大生产将妇女和儿童卷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之际,就已经敏锐地注意到机器带给人便利的同时又变成侵蚀家庭人伦生活的隐蔽手段。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机器生产把妇女和儿童也视为劳动者,主张把妇女、儿童从家庭生活中征用过来强制为资本劳动,所以就把妇女、儿童需要自由劳动的家庭时间消灭了。并且指出由父母自给自足的家务劳动和日常生产,因为妇女被机器生产束缚住,工人的家务闲暇不得不以商品消费来满足日用需要,家庭支出的增加导致无法形成对自身劳动果实(收入)的节省和占有。“因为某些家务事,如照料婴儿和喂奶等,不能完全不管,所以,被资本没收的母亲,必须多多少少雇佣代替者。家庭消费所必需的劳动,如缝缝补补等,必须由购买现成商品来代替。因此,家务劳动消耗的减少,相应地就增加了货币的支出。因而,工人家庭的生产费用增加了,并且抵消了收入的增加。此外,节省地合理地利用和配制生活资料也不可能了。”[3]219也就是说,机器化大生产出人意料地宰制了工人的家庭闲暇,尽管生产上的压榨暂时地缓解。而工人有效管控自己生活资料的消耗(越来越变得不可能),用儒学的观点看,本质上是主宰自己生命闲暇、捍卫家庭人伦的自觉的道德主体的开显。
“闲”字的“门”,正是代表家庭亲情表达的那个生命之门。“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斩恩。”(郭店简《六德》)“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内,不啸不指。”(《礼记·内则》)在郭店简《六德》和传世文献《礼记》中皆强调内外之分,其有两层意味。第一层是社会(门外)和门内(家族、家庭)的区分,另外一层是内庭和外庭的区分。后者是在家庭内部的一种区分。其用意在于,人们的闲暇大部分是在工作后回到家庭中度过的,注意将日常生活中生产性的生存状态和家务闲暇的温情脉脉的状态区分开来,二者不互相干扰侵夺,并且生产乃至闲暇中的消费都应围绕着家庭情感和谐这个核心来展开。因为内外之分,而形成日常生活中不同生存环节上的轻重之分,人不是为了自身的满足和欲求的消费而被迫投入生产,而是为了家庭生活的完满而展示自己亲爱家人的力量自觉承受劳动的重负。正是人的仁爱的能力,造就了日常生命的转折及其节奏,梳理了工作和闲暇的时间秩序。
工业生产中劳动产生的人的生存异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中更是作为专门的主题来进行讨论。撮要言之,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的自由劳动即工人摆脱生产关系的束缚和克服自身的惰性以后,按照美的尺度生产的人类可以走出一条扬弃异化的超越之路。笔者继承马克思的问题意识即超越性的落实,而将着眼点放在与技能性的劳作息息相关的日常闲暇上去。也就是说,生命的形而上追求不全在技艺化生存之中,反而根源于日常闲暇的情感化充实。后者才是人之生存绽放的场域。工人怎样消遣自己的闲暇,就怎样成就他自己。这就形成我们对马克思重视生产的一种颠倒,把生产当成人之生存基础性的物质前提,而真正把日常闲暇中人的生活形式理解为生存的意义根源。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着落,则是人于闲暇中对生产劳作的“哲学的、人文的”再创造和再阐释。下面通过批判日常闲暇的异化,来明了日常闲暇的本真状态和真正享有。
人对自身生命闲暇的自觉,必须表现为坚守家务事等等自由劳动的日常生活空间,并且“节省地合理地利用和配制生活资料”以形成事实上对劳动成果和生命时间的绝对控制。不如此,工人摆脱资本的强大统治就无从谈起。有必要郑重申明,对于人的生存来讲,日常闲暇和必要家务活动是人的自由之呈现,是人之为人的充分且必要的条件。这实际上是在为资本的统治和人的生存进行范围划界,工人通过对日常闲暇立法而完成对资本力量的限制。在其现实性上,意味着妇女在资本生产中争取更短的工作日而自觉从机器生产中抽身出来回归家庭,以自给自足的家务劳动(男人有义务参与其中)达到节省相应地家庭消费。由之,推论出另一个命题:家庭日常闲暇的非消费化。即通过家庭各成员日常闲暇时的自由劳动实现非消耗的家庭生产,这种家庭需要的生产天然跟资本或者货币没有多少关系,而显得生命的纯粹。这是我们所体会出的马克思的“微言大义”,儒家对此则是通过躬耕的田园生活实现的。
然而,工人争取正常工作日以后悬而未决的问题,即日常的生产、生活让人变得麻木、机械,沦为资本积累的手段,使人之为人的意义沉沦。马克思睿智而深刻地指认了人的生存困境,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才是他讨论正常工作日的潜在用意,并非仅仅关注由工作日的分析引申出剩余价值率(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的计算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秘密的揭露。不过,这两个维度的哲学考察在马克思那里同等的重要,这说明他不但要为工人指明一条社会的劳动解放道路,还要在人自身为这种解放寻找到坚实的人性基源。
人要重振日常闲暇,就得自觉回归家庭生活重视自然纯粹的人伦交往,承受养育儿女的更多家务的劳累并化此劳累为充实、快乐和幸福。人的这种转变的可能性在于,对自身生产—消耗冲动的抑制,即明了真正享受自由时间获得更高的意义满足,意味着关注人的生命情意的绵延和密实。闲暇的去消费化,实质上是扎根于闲暇之中对人的劳动的或实践的力量再次地拓展、升华,实现从消耗的否定性的活动向生活的肯定性的涵养的蜕变。这是针对休闲这种纯粹浪费时间的奢侈生存方式,异化了的生存形式发起的一场严肃的斗争。尽管让·鲍德里亚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争取自由时间是不可能的,但在儒学的日常生命践履中却是有迹可循,即克制自己的欲望而保持身心的平和。从而提供对日常生活及闲暇解放的可能性回答。
三、日常生活的儒学向度
人是即凡而圣的灵蠢。充斥着消费的日常闲暇及休闲,都是流俗地生活形式,人的生存本真的境域豁显的契机包孕于其中。而维持着人的生存的根源性事实,是人之道德地体证,生命惠而不费地涵养。生产、消费并非人性的全部。德塞图认为,人的日常生活是以丰富的方式利用外物来不断拓展自身,其根本意义常常是隐而不彰而难以把捉,因此人们不应以某种预设的态度或立场去对待日常生活,而要满怀信心去唤醒自身内部尚未被外界熏染过的那片纯净自然的净土。[6]德塞图所言不虚,儒学早已在日常人伦日用的那片自我确认领域(非物欲充斥、非理性计较的真情生活)体悟到其中所含而不显的天道根源。马克思强调了日常生活的感性的物质需要方面,而孔子则注重人本身的更基源性的血缘亲情所构筑的活络的生存联结。窒欲而重情,从人伦日用中觉悟人生的形上追求,正是儒学的日常生活的智慧。[7]
重提工人正常工作日,不是为了重复马克思早已得出的结论,而是明确劳动、闲暇各自的必要性。“可是工作日有一个最高界限。……正像一匹马天天干活,每天也只能干8小时。……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这些需要的范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3]190对工人自身来讲,他必须对自己劳动力的使用具有充分的自觉,他是面向整个资产阶级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且他每天只能输出8小时的劳动力,除此而外他还要有时间进行精神创造、情感交往的生活。出于此一生命整全的自觉,对劳动力的节制便形成自身对日常生活的一种全新的理解,从而认识到不管是在工厂机器上劳作还是下班家务休闲,都作为自己日常生命的有机部分而为整全生命觉悟所涵摄。换言之,在对日常的劳作和闲暇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之外,还应该对其有一种内在于工人自己的生命体悟,即把劳作与闲暇当作日常安身立命的不同证验场域。显然,此即工人生存的社会性(服从资本逻辑的外部的一切社会关系)和时间性(工人在日常作息中的内在体会)的相互区分中,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强调生命自我修为的儒学传统贯通起来。
而白玛文洲此时却顾不上照顾父母。灾情发生后医用耗材缺乏,他积极协调动员辖区药品经营企业捐助医用耗材,全部免费发放给最需要的群众。4月的玉树昼夜温差较大,白天气温可达30℃以上,晚上则降到零下15℃左右。白玛文洲白天给各救援医院发放药品,晚上则给陆续到来的药品卸货,甚至到凌晨2点多。而第二天早上6点,他必定准时起床到救援中心准备药品发放。
前面探讨了日常闲暇的本来面目及其生存论意蕴。而劳动与闲暇的关系,则成为人的日常性追问的关键。先概要言之,劳动、闲暇二者同体而异数,是因具体实践不断变化的生命的辩证发展。此“体”,指人的生命活动不断修炼塑造的既恒定又变化的一定之体格和规模。不论是劳动还是闲暇,都建基、作用于这个同一的体格规模之上。“数”则是指在一体内的两个不同的意义单元即劳动与闲暇,各有各的营构的法则性的度数,以致彼此相对独立却有机联系。
从汉字闲的字源学入手进行简要探讨。在《字源》中:“闲,会意字。……‘闲’表示栅栏,‘闲’表示空隙,并引申为空间、空暇。如今‘闲’废止不用,‘闲’的空间义由‘间’表示,‘闲’的空暇义由‘闲’表示。”[9]1043本义指古人结束一天劳作,回到家中关上门来的夜间休憩生活。其所展现的生存状态,体现了散逸灵便的生活风格,比劳动的程式化生存更贴近人之日常的生动气质。闲字的空隙义表明人的日常生存状态的非连续性,注重生存节奏的间断和转换。这从其中可知,而且这个闲之生存所涉及的“门”,不是一般的门、栅栏(后文将有详释),而是喻指人结束紧张的日常操劳抽身归藏的节奏转换,意味着人对自己不同生活内容的归置和划界。闲的两种含义所切中的是人对自身生活时空所作出的一种个体化的开辟和重新耕耘、转化。人之为人,他必须实际经验到一定的、附着于某物之上(比如自家的院门)的空间并为他据为己有。而他之享受、沉浸于这个空间并从中完全地舒展自身则是他的自由时光。人通过绝对占有某个空间而体验他个体生命的意义,不管这种意义或者是历史的、磅礴的或者是狭隘的、小气的。由此便可以得出“闲暇”的一种全新的认识:真正的闲暇应是人保养劳作之余的能量和时间来进行生活韵味的体证,使自身的生命条理化、道德化、纯粹化以实现心身的深邃。儒家对闲暇的理解在其整体精神上有一个清晰的把握,即亲爱温和,并以特定的时空为基础,这个时空乃家庭的门内之治。
马克思所指的“某些家务事,如照料婴儿和喂奶等”,这是非对象化的人的自由实践,是人的类本质——圣母般博爱能力的发挥,在人类的记忆中圣母玛利亚就是这样哺育耶稣成人的。一个母亲,一个纯粹的人,只有在“照料婴儿和喂奶”的时刻才真正做回她自己。儒家文化对妇女从事的家务事有更加深沉的审视。像“照料婴儿和喂奶”这样的家务事,尽管在今天男人或者其他人可以代替,首先是母仪之德,是妇女的幸福。除此而外儒学无所着意。儒家视“亲子之情”乃人之为人的基本,而亲子之爱则是儒家范畴性概念“仁”的重要内涵。仁爱流行的天地之道,人的本根气性,皆本于此亲子之情。由此看马克思对于此类家务事的强调,也即是对人的切己闲暇的重视,具有意味深长的人文关怀。
儒家彻透了人之为人的闲暇格局。《大学》讲修齐治平之道。修身作为闲暇的重心,需要做正心诚意的工夫。而正心诚意的实现,就是在日常琐细即人伦日用中处处反求诸己,不伤物不伤人亦不伤己,达到亲、爱、温、和的境地。儒家把人的家庭生活作为全幅人生全幅实践规模的起始点,在家庭生活中的闲暇都为修身这一特殊的自我修炼活动充盈着。日常闲暇的展开,凝练为人的修养工夫,以欲望满足为目的的消费活动在此间得到完全地节制。“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章句下》)人之日常生活及其生产,都不是以欲望为驱动的现实配置,战胜自然欲望的积极性否定才是人之日常性展现的端倪。也正是在此一意义上,人才能把日常中所经历的繁复多变的种种活动,都转化成锻造主体自身内在力量的丰富养分。他既不去盘算工资的挣得与消耗,而考虑奉献他人以挖掘潜能;他的那些看似平常的琐细忙碌,因为亲情融融的家庭生活(人生之仁爱能力的流行)而获得化腐朽为神奇的契机;生命并不因机械化的生产而僵滞、枯燥,相反操作工具的日常技艺生活却充满诗情画意,其境界有如“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等等。
四、劳动、闲暇同体异数
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劳动中的劳累感以及因此产生的厌烦情绪虽真实存在,但精神的方面应由精神的方法来处理而非求诸永无尽头的物质舒适。为了对这一观点进行更加清楚地阐明,不得不引入儒家对闲暇的理解。
历史的进步和发展不仅在于社会的整体的变革,其更具体和细腻的在于人的生活方式的刷新和丰富,这是最为根本的。人性的奥秘在于其不断破除束缚的生生不息的活力,人性日新变化而自由规划整合实现生命同一性。因而,资本及其势力始终只能是人的从属之物。这即意味着人在日常闲暇的亲情修为中节制、纾解自身的消费冲动,而实现生命琐细的自觉,限定资本这个人类自己一手创造的异己力量的合理运用范围,将其格挡在必要的人的本真生活时空之外。
前面的讨论已经明了人的日常生活,关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生存(有组织、大规模的、整体的人类实践)和儒家个体的内圣式的道德定在(当下的、即地的、体悟的个人修为)两种不同生命智慧的综合。这样一种一体两面的理路,要在将人的每日生活(将劳动和闲暇统一起来观察审视)单格化从而多元化,注重劳动向闲暇的不同生命形态节奏的过渡、转换,在一个个体的日常生活的整体内部实现内容的异质和均衡,从而由人的生活内容和体式的丰富复归到日新变化的人性主题上来。也正是在此一层面,我们说劳动和闲暇是同体而异数。
主实体表与联系表的关系与附属实体表与主实体表的关系类似,都是“1对多”的关系,故可以参照步骤3),将每个联系表的频繁项集与其对应的主实体表的频繁项集进行连接。
详细言之,所谓异数,是指劳动、闲暇各自有不同的逻辑理数及其价值信仰体系,可以各行其是而互不通约,彼此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而所谓同体,则是指人的整体的每日生活的不同生活单元之间彼此互相依存,互为条件又互相牵制、补充,繁杂生活内容在这个节段交错的格局中整合起来,因为人的广博深厚的生活实践积累而成一个稳定的整体结构。
也许有人要问,不同的东西把它们生搬硬套到一起可行吗?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在互通有无的条件下能一体流变吗?这正是我们下边要回答的问题。从第一节谈到劳动的限度和闲暇的必要,到第二、三节对闲暇的消费化和日常生活的儒家改造,证明了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人的生活实践阶段上的问题意识及其效力,也表明了人的实践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特征,每日生活的深广意蕴为不同的理论资源备留了各自应有的运用空间。问题的关键在于要为其提供统一性的理论架构,需要对儒学“淮南格物”说的创造性阐释来完成。
“格物”一词,前面已经提及。历史上的儒者对“格物”一词的解释尤以淮南王心斋的“淮南格物”说为正,吴震先生对此专文进行了讨论。这里简要阐述一下吴先生的研究结论:朱熹将“格物”释为即物穷理,王阳明批评其“析心理为二”,主张格物就是正心诚意工夫的贯彻,不假外求而此心万理已具。王心斋(王艮)以“挈矩、格式”释“格”而以“身(本)与家国天下(末)”释物,即安身立本而修齐治平;“格物”就是超越认知观念模式和知识追求的、一种身体力行的践履功夫。[10]可见,格物讲求的是工夫实在我身,实际上以生命践履的通达和深广供给了生命体的统一性的有机框架结构。王艮的淮南格物说给我们的第一层启示是,不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实践,或者儒家的闲暇修养,都是中国人实在我身的工夫锻炼,不同的文化塑造着人的不同生命层次的具体面貌,但人生生不息的身体力行工夫不断打磨着不同文化之间、不同生命层次的深浅区格,决定着异质文化生活最终统一于此身之体。日常劳动操练的是人的身体力量和理智运用,侧重的是技术的传统。但劳作之余的日常生活中,家庭园林的时空玄关的设置激发人生存节奏的转换,进入到自身心灵的安顿和修为,磨砺的是人的心性,讲究道德的存在。也即劳作与休息的同体异数。
基于此,我们认为教育学的教材应有广博坚实的专业知识,能反映科研的最新成果、学科发展前沿和时代精神;应有高深的学问,兼具科学性、价值性、艺术性,对读者和师生有吸引力;能激发教师与学生从事教育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使教师感到有教头,使学生感到有学头。
淮南格物说的第二层意义,吴震先生注意到了并予以揭示,但仍需再引申一下。王艮对于“格”的训释,才是我们思考劳作与闲暇关系问题的根本启发点。“格”在王艮看来,其实是一种动态化的格式、挈矩过程。其犹如木匠将一块原材料,经过打量、绳墨而将材料格式化成不同的配件单元,然后各个打磨修造,最后通过榫卯对接形成一个有机体的物件。各格式单元其实就是同体异用。以中国木构建筑艺术为例,其非生搬硬套,而是各个构件之间活扣拼接而成,力的平衡来自于构件之间的合理嵌套,外力毫无存在之必要,而人变动不居的生命力本身正是这个平衡的奥秘之处所。因而,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劳动的阐释也好,对于儒家看重人的家庭生活重要性也罢,都是从这些具体的生活行动中找到它们融合在一起的节骨眼,在劳动与闲暇之间损益着情感和欲望使二者实现动态的均衡,顺着人的日常生活之体势拨弄盘活整个生命实践。让劳动的归劳动,闲暇的归闲暇,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各有天地,出入其间不亦乐乎!
格物的奥妙还在于,其对工夫的强调指正了人的生存的开阔性和无止境,从完全变化流动的角度去认识人本身的力量。人自觉地将日常生活分成不同的格子,确定不同的价值单元,使万物众有各居其位,因至诚无息的工夫修为傲立天地之间,“磅礴万物而为一”(《庄子·逍遥游》)。其导源于中国古人服习积贯的厚德载物的意识,疏导分流而因地制宜,各自为治。比如修竹节节向上,节律既美且善。“体其宜而节度之,理其情而出入之”(郭店简《性自命出》)对日常生活的各个阶段的发展意义有所了解和把握,对处于不同位格上的人的生存状态深入体贴,分辨节、度不同的生活方式、状态,通晓事物整体发展的情理节奏,而于其间自由变化,实现游刃有余。
式中τ为初始步长因子。若操作后矢量仍不合格,则用对原步长开方的方法进行收缩再计算,通过控制步长合理度保障算法效率和修复结果。该方法采用多参数重组编码理顺变量逻辑关系,再设置染色体修正算子,引入迭代修正公式,可有效保障基因质量,降低非法染色体产生机率,提升种群生成效率;且通过为模型中所有潜在解与染色体位串创建相互映射关系,保证了编码的完备性和健全性。
总起来看,正像《大学》的作者把自己的日常生活格式成身、家、国、天下等深浅交错的不同方所,不断在不同的格局单元中求得自身的规正一样,我们对自身日常生活也可以进行格式化的分层、分段、分流,控制生活的节奏,使日常生活通过人的耕耘而形成人的解放向上之势,如劲竹节节直干青云。如此,便达到劳动与闲暇的异数而同体,互为基础又互相发明,在现实践履上实现人的解放。
五、结语
“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11]4人的自由,根基于儒学人伦日用的亲情生活,发扬于人创造历史的社会化劳动,二者不可割裂或互相侵夺而同体异数。综上所述,不是机械化的生产、物欲化的消费,而是基于享受人伦亲情闲暇的日常生活以积极劳动,实现劳动与闲暇有机结合,从而体悟生命意义成就了人。正是因为实践着的人不断暴露出来的生存危机,才推动我们不断思考“人是什么”这个终极问题。通过把儒学“日用伦常见天道”思想引入到马克思主义对劳作和闲暇的讨论,重新发掘了家庭闲暇的重要意域,即纯粹家庭生活为人的生产劳作奠基,并由人伦亲情的平淡质朴豁显生命的形上境界。总而言之,在日常生活的视野内,调和马克思主义和儒学,深入思考劳作与闲暇的关系,是否能对新时代“人的解放何以可能”这一重要课题提出更多的启示呢?显然问题的答案,将有赖于今后更加全面而系统地现实日常生活的考察了。
参考文献:
[1] 鲁芳,黄秋妹.马克思恩格斯日常生活理论的伦理向度[J].云梦学刊,2018(1):53-56.
[2] 沈德潜.古诗源[M].北京:中华书局,1963.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6] 吴飞.“空间实践”与诗意的抵抗——解读米歇尔·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J].社会学研究,2009(2):177-199.
[7] 丁成际.儒学日常生活伦理的形上之维[J].现代哲学,2018(1): 144-149.
[8] G.A.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M].岳长龄,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9] 李学勤.字源[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
[10] 吴震.王心斋“淮南格物”说新探[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95-102.
[11] 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1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3]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14] 王夫之.礼记章句[M].长沙:岳麓书社,2011.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 and Leis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gration of Marxism and Confucianism
CHEN Bing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 Marxist theory of daily life advocates that labor has the significance of shaping oneself and creating history, while daily life is the realistic basis for people to create history. However, Marx only recognized the basic significance of daily life, and failed to notice that family ethics is the origin of human nature, while Confucianism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transcendence of family ethics. Real family leisure should be the maintenance of life energy and time to enjoy the kinship life after work, so that their emotional activities are organized and morali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 and leisure is based on each other, and they are coexist and constitute the whole of life, but each has its own degrees. Therefore, the socialization of labor based on human relations of kinship life and the fulfillment of daily leisure is the only way to realize the freedom and liberation of human nature. By integrating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Confucianism and Marxism on daily life, we can see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 and leisure.
Key words : labor; leisure; kinship life; one life but every part has its own degrees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5128( 2019) 09-0040-07
收稿日期: 2019-04-17
作者简介: 陈兵(1992— ),男,陕西澄城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先秦儒学、现当代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 贺 晴】
标签:劳动论文; 闲暇论文; 家庭亲情论文; 同体异数论文;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