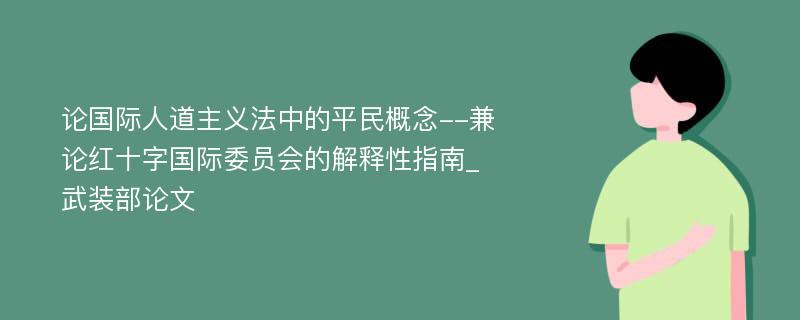
论国际人道法中的平民概念——兼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解释性指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释性论文,国际论文,人道论文,平民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3)06-0103-10
一、平民概念的关键性
国际人道法旨在保护战争和武装冲突受难者,区分原则作为其首要原则和逻辑基础,要求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始终对战斗员和平民、军事目标与民用物体加以区别。区分原则在国际条约①和国际习惯法②中均得到确认,具有不容置疑的法律效力,平民据此享有免受直接攻击之一般保护。不过,这种保护的前提是平民不“直接参加敌对行动”,一旦进行此种活动,平民将丧失保护并成为合法攻击目标,这一点在国际条约中③也得到确认。因此,为了保障国际人道法正常运行,区分原则必须完成两项任务:一是区分战斗员和平民(或军事目标与民用物体),前者一般在任何时间均可被攻击④,后者一般享有免受直接攻击之保护;二是区分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平民和未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平民,前者在直接参加时失去保护,后者享有免受直接攻击之保护。
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首先能够确定谁是平民。然而,国际人道法中并没有平民的直接定义,即没有直接规定平民是什么样的人,而是使用排除的方式,通过规定什么样的人不是平民来定义平民。国际人道法中,与平民概念相对应的是战斗员(combatant),即“有权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人员⑤。战斗员被俘时享有战俘地位并因此受到保护,只要遵守国际人道法,其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行为就不受惩罚;没有战斗员地位但是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人,不享有战俘地位并且可能因其行为而受国内追诉。研究国际人道法中的平民概念,需要首先研究战斗员概念。
二、刻意的模糊:错过的机会
虽然战争的历史几乎与人类社会一样悠久,但从法律上区分战斗员和平民还是近一个历史时期的事情。1863年美国内战时期北方军队的《利伯守则》(Lieber Code)是第一次使用了战斗员一词的法律文件,该守则认为“常规战争中所有敌人分为两大类,即战斗员和非战斗员”⑥,并多次提及非战斗员⑦。但是,《利伯守则》只是在通俗意义上使用战斗员和非战斗员的称呼,还没有法律上的考量。1874年的布鲁塞尔战争法规和惯例草案⑧第一次尝试从国际法角度界定战斗员,名为“谁应被视为交战国(belligerents)战斗员和非战斗员”的第二部分共有三条:根据第9条,“法律、权利和战争义务不仅适用军队,也适用满足下列条件的民兵和志愿部队:(甲)他们被一为其部下负责之人统率;(乙)他们备有可从远处识别之固定的特殊标志;(丙)他们公开携带武器;(丁)他们遵守战争法规及惯例进行战斗。在民兵构成军队或是其一部分的国家,军队一词包括民兵。”第10条规定,“未占领地之居民,当敌人迫近时,未及按第9条进行组织,而立即自动(spontaneously)拿起武器抵抗来侵军队者,如果遵守战争法规及惯例,应被视为交战者”⑨。第11条宣布,“交战国的武装部队可由战斗员和非战斗员组成。如被敌人俘获,均应享有战俘权利。”⑩在该草案的基础上,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和会分别通过了具有法律效力的《陆战法规惯例公约》,两个公约对战斗员的规定几乎照搬了上述三条(11),1907年《陆战法规惯例公约》关于战斗员的规定沿用至今(12)。
虽然有后见之明的嫌疑,但1907年的海牙和会本有机会更清晰地定义战斗员。会议期间,与会国分为“军事派”和“爱国派”两个阵营,“军事派”强调在条约中写入清楚、可操作、现实的规则,而“爱国派”看重的是军事弱国应有能力保卫自己。“军事派”想要清楚地区分享有和不享有战斗员特权的人,而“爱国派”担心这种明确的界限会损害一国保卫自己的能力,因此主张放宽要求,将非正规部队和民众抵抗视为战斗员。两派最后达成了妥协,“爱国派”的胜利表现在公约附件第1条,虽然满足四个条件的民兵和志愿部队能够享有战斗员特权并在被俘时享有战俘地位,但前提之一是遵守战争法规和惯例,而军队成员即使持续违反战争法,在被俘时也不会失去战俘地位(13)。“爱国派”的胜利反映在公约附件第2条,民众抵抗者虽然只需公开携带武器和遵守战争法规和惯例即被给予战斗员特权,但限制巨大,即必须是未占领地之居民(排除了占领地的居民),必须是立即自动拿起武器(时间短暂)而且未能按照公约附件第1条的标准进行组织[1]196-198。1907年《陆战法规惯例公约》采用列举的方式定义战斗员,如军队、满足特定条件的民兵和志愿部队以及尊重战争法规和惯例、公开携带武器的民众抵抗者,并对民兵和志愿部队规定了军队的形式要件要求,但这只是其享有战斗员特权和战俘地位的条件。公约回避了从实质要件上定义战斗员,未能更清楚地界定享有战斗员特权的人和不享有此种特权的人。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虽然详尽规定了战争和武装冲突时对平民的保护,但本身并没有平民或战斗员的概念。由于大部分情况下战俘是落入敌方手中的战斗员,因此1949年《日内瓦第三公约》(《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对战斗员的规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公约第4条(子)款规定了战俘所包括的六类人员(14),其中的战斗员(15)也基本照搬了1907年《陆战法规惯例公约》中的相关条款(16)。总之,战斗员概念基本来自1907年《陆战法规惯例公约》,但其相关规定从一开始就刻意保持了模糊,这使得平民概念也无法精确。
三、问题的加剧:两分法与旋转门
二战后,战争和武装冲突在主体、手段、形式等方面发生明显变化,这给基于传统国家间战争的国际人道法带来巨大挑战和冲击,并促使其做出相应调整。根据现实情况的发展,1974至1977年间,日内瓦外交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第一附加议定书》和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第二附加议定书》,作为对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的补充和更新。《第一附加议定书》是关于战时平民保护最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件,其关于战斗员和平民的规定影响巨大。第43条第1款规定,“冲突一方的武装部队是由一个为其部下的行为向该方负责的司令部统率下的有组织的武装部队、团体和单位组成,即使该方是以敌方所未承认的政府或当局为代表。”相比1907年《陆战法规惯例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从某一特定实质要件定义战斗员,是一种进步,将战斗员特权扩展至民族解放运动成员,也是对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承认其与殖民国家作战合法性的回应[2]6,但议定书中另外两条关于平民的规定却引发了很大争议。
(一)第50条第1款:两分法
《第一附加议定书》仍然采用了排除法间接定义平民。第50条第1款规定,平民是指不属于1949年《日内瓦第三公约》第4条(子)款第1项、第2项、第3项和第6项以及议定书第43条所指各类人中任何一类的人,而且特别强调“遇有对任何人是否平民的问题有怀疑时,这样的人应视为平民。”因此,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一个人如果不是战斗员,就是平民,即所谓人员地位的两分法。如果战争仍然只在,或者主要在国家间进行,这种绝对的、非黑即白的分类方式不会遇到太多问题。但是,从20世纪后期开始,战争和武装冲突越来越多地是在国家和非国家主体之间进行,同时,越来越多的平民实际参加战事,而这样的平民根据两分法,仍然是平民,这就引发了对两分法的批评和讨论。有观点认为,《第一附加议定书》中存在5类人员,即第43条下的“合法战斗员”,第44条第4款下的不同的“合法战斗员”(17),不满足第43条要求的有组织武装团体成员,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平民和未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平民,其中第2、3、4类人员与其说是平民,不如说是“非法战斗员”[3]286。质疑两分法,主要是想将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平民剔除于平民类别,将其归为第三类,即“非法战斗员”。但是,迄今为止,国际条约中还不存在“非法战斗员”一词,也未形成有关国际习惯法,“非法战斗员”只存在于学界的讨论中(18)。“非法战斗员”最初是指没有遵守战争法规与惯例的战斗员(19),现在一般是指“所有无权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却又如此行事,并因此在落入敌方权力时无法被归为战俘的人”[4]46。严格说来,“非法战斗员”并不是法律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客观事实而使用的方便称呼,但其出现可以说是两分法的必然结果,因为两分法并未考虑到或者回避了复杂的现实情况。
(二)第51条第3款:旋转门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51条第3款规定,“平民除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并在直接参加敌对行动时外,应享受本编所给予的保护。”根据该款(20),平民可自由在享有和失去免受直接攻击之一般保护的状态中切换,“白天是农夫,晚上是战士”,产生了所谓旋转门现象(21)。旋转门的关键问题在于,如果平民多次、反复直接参加敌对行动,是否能够在每次行动期间享有免受直接攻击的一般保护,是否仍能被视为平民。对此,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极大争议。规定了两分法的第50条第1款和导致了旋转门的第51条第3款,本意都是最大限度地保护平民,但当今战争和武装冲突的现实恐怕让两分法很难得到切实遵行,旋转门也可能令有关国家无法接受(22)。因此,这两个规定以及国际人道法本身最大限度地保护平民的初衷不仅可能无法实现,平民整体还可能因为“非法战斗员”和旋转门而处于更危险的境地。
四、新世纪的努力:突进的尝试
如今使用的战斗员概念主要来自1907年《陆战法规惯例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虽然试图从某一实质要件定义武装部队,但并不彻底。百余年过去,战斗员的定义没怎么变化,但进行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战斗员和平民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如何区分战斗员和平民,以及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和未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平民,成为困扰学界和军界的一大难题,因为不构成合法攻击目标的平民死伤将直接影响根据比例原则对具体攻击合法性的评估,即平民生命受损失、平民受伤害、平民物体受损害或三种情形均有而且与预期的具体和直接军事利益相比损害过分的攻击,将被视为非法。鉴于此,视自己为国际人道法守卫者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召集了数十名来自学界、军界、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专家,通过5次会议,历经6年的讨论和研究,于2009年5月发布《国际人道法中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定义的解释性指南》(以下简称《解释性指南》),尝试解决平民的概念等问题。《解释性指南》由十部分组成,涉及三个关键问题,即就区分原则而言,谁被视为平民,什么样的行为构成直接参加敌对行动,丧失免受直接攻击之保护具有哪些特征。下文将主要关注第一个问题,即平民的概念,但也或多或少地涉及其他两个问题。
(一)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平民
《解释性指南》依然沿用了排除法定义平民,并分为国际性武装冲突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两种情况。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平民是“既非冲突一方武装部队成员又未参加民众抵抗者”[5]20。关于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平民,《解释性指南》正确地指出“仅仅因为非正规武装部队没有将自己同平民相区分、没有公开携带武器或者没有遵守战争法规及惯例进行战斗,就将其置于适用于平民居民的、保护程度更高的法律制度之下,这同区分原则的逻辑是矛盾的”[5]22,然后对武装部队进行实质界定,以深化《第一附加议定书》第43条第1款的规定。《解释性指南》宣称“所有表现出足够的军事组织程度并且属于冲突一方的武装人员也都必须被视为冲突一方武装部队的一部分”[5]22,认为有组织武装团体要想成为国际人道法上的合格武装部队,必须属于冲突之一方。“属于”这一概念要求在有组织武装团体和冲突一方之间至少存在事实上的关系,这一关系可以通过公开宣布、默示同意或确凿行为表明。实践中,要认定有组织武装团体属于冲突一方,似乎必不可少的要求是它代表该方作战并得到了该方的同意(23),而如果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有组织武装团体并不“属于”冲突一方,那么根据《海牙章程》、日内瓦四公约和《第一附加议定书》则被视为平民[5]23。
在成员身份的判定上,《解释性指南》为正规武装部队和非正规武装部队设定了截然不同的标准。正规武装部队的成员身份“一般由国内法调整,表现为正式加入可以凭借制服、徽章和装备加以辨别的常备战斗单位”,无论其实施了哪些个人行为或在武装部队中担任何职,正规部队的成员都不是平民,除非脱离现役重返平民生活;而非正规武装部队的成员身份“一般不由国内法调整,而只能基于功能性标准来确定,例如那些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有组织武装团体的标准”[5]24-25。这种观点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判断正规武装部队和非正规武装部队成员的标准不一致缺乏合理解释,而且导致后者比前者享有更多保护(后者如无“持续作战职责”将被视为平民,下文将详述)。二是有组织武装团体成员身份在国际性武装冲突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可能完全不同,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可能因不属于冲突一方而被视为平民,而同样的情况下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又可能因“持续作战职责”被视为冲突一方的成员而不是平民,这也不符合逻辑。
实际上,《解释性指南》对待民兵、志愿部队和有组织抵抗运动成员的方式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05年在编纂《习惯国际人道法》时采用的方式有很大不同。《习惯国际人道法》照搬了《第一附加议定书》第43条第1款,规定“武装冲突一方的武装部队由所有为其部下的行为向该方负责的司令部统率下的有组织的武装部队、团体和单位组成”[6]14;而且根据1907年《陆战法规惯例公约》,如果非正规武装部队如民兵和志愿部队构成或是军队的一部分,它们也包含在军队一词中。《习惯国际人道法》认为,《第一附加议定书》没有区分正规武装部队和其他武装团体或单位,而将所有对部下的行为负责的司令部统率下的武装部队、团体和单位视为该方的武装部队,任何以冲突一方名义作战的人员均是战斗员[6]15,并且由于《第一附加议定书》第43条现已广泛适用所有种类的武装团体以决定其是否构成冲突一方的武装部队,因此“没有必要区分正规与非正规武装部队”[6]16。对于武装部队到底由哪些部分组成,仅仅相差四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观点就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具体原因尚不可知。
(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平民
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平民是非“国家武装部队或冲突一方有组织武装团体成员的人”。[5]26相比来说,《解释性指南》关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平民看法更重要,不仅是由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是当今世界主要的战争形态,特别是因为,如上所述,《解释性指南》将国际性武装冲突中非正规武装部队成员身份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适用有组织武装团体的功能性检验标准联系了起来[5]25。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3条(24)和《第二附加议定书》第1条(25)所指的“武装部队”含义并不相同,前者指一般意义上的武装部队成员,而后者将武装部队、持不同政见的武装部队(dissident armed forces)和其他有组织武装团体区别对待。因此,《解释性指南》必须首先选择武装部队的含义。《解释性指南》采用了《第二附加议定书》第1条的分类法,将武装部队分为国家武装部队和有组织武装团体,后者包括持不同政见的武装部队和其他有组织武装团体。
在成员身份的判定上,同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为正规武装部队和非正规武装部队设定不同的标准一样,《解释性指南》为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国家武装部队和有组织武装团体也设定了不同的标准。国家武装部队的成员身份“一般由国内法调整,表现为正式加入可以凭借制服、徽章和装备加以辨别的常备战斗单位”,无论其实施了哪些个人行为或在武装部队中担任何职,正规部队的成员都不是平民,除非脱离现役重返平民生活。有组织武装团体分为持不同政见的武装部队和其他有组织武装团体两种情况。持不同政见的武装部队成员身份与正规国家武装部队成员身份判断标准一样,即“只要他们还有组织地处在其以前所属的国家武装部队的结构内,这些结构就应继续决定个人在持不同政见的武装部队中的成员身份。[5]31”但《解释性指南》没有提及什么时候,或者根据什么,持不同政见的武装部队不再具有和国家武装部队一样的结构,因而不再是其成员。
《解释性指南》认为,其他有组织武装团体的成员身份取决于是否承担“持续作战职责”,即“是否为该团体承担了涉及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持续职责”[5]32,而这正是《解释性指南》关于平民概念的核心标准,因为持续作战职责是正规国家武装部队与无论国家还是非国家的有组织武装团体之间的实质区别。《解释性指南》的理由在于,非正规组建团体的成员身份在国内法中没有规定,也不始终通过制服、固定的特殊标志或身份卡予以表示,因此,在调整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法中,有组织武装团体的概念特指严格的功能意义上的非国家武装部队,因为除为该团体承担某种职责外,很少通过加入行为正式体现成员身份[5]31-32。持续作战职责在国际条约中并无规定,而是《解释性指南》创造的术语,有组织武装团体的“成员身份必须取决于个人所承担的持续职责是否同该团体作为一个整体所共同履行的职责——即代表非国家冲突方作战——相一致”[5]32。在举例说明时,《解释性指南》认为“持续职责涉及准备、实施或指挥行为或者其行动相当于直接参加敌对行动之行为或行动的个人,就是在承担持续作战职责”,而征募人员、训练人员、募资人员和宣传人员以及职责限于在具体军事行动之外购买、走私、制造和保有武器及其他设备,或者收集战术情报以外其他情报的个人,并不承担持续作战职责,只是“承担支援职责的平民”[5]23。这种观点可以说是相当武断的(26),已经并将继续引发巨大争议。
持续作战职责概念中,直接参加敌对行动是关键。要理解持续作战职责的含义,以及其对区分正规与非正规武装部队和有组织武装团体成员身份的影响,必须分析《解释性指南》关于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定义。根据《解释性指南》,一项具体行为要构成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必须同时满足三项条件,即损害下限、直接因果关系和交战联系。损害下限是指“行为必须很可能对武装冲突一方的军事行动或军事能力造成不利影响,或者致使免受直接攻击之保护的人员死亡、受伤或物体毁损”,直接因果关系要求“在行为与可能因该行为(或该行为作为有机组成部分的协同军事行动)所造成的损害之间必须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交战联系意味着“该行为必须是为了直接造成规定的损害下限,其目的是支持冲突一方并损害另一方”。《解释性指南》试图通过非常狭隘地定义直接参加敌对行动,以防止对平民保护造成负面影响:第一,对每一个构成要件做狭义界定,如损害下限要件只关注损害而不关注“增强”、直接因果关系要件中的“一个因果步骤”要求、交战联系要件中必须不仅支持武装冲突一方,而且必须损害另一方。第二,要求三个构成要件必须同时满足。这就使得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只在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才能成立,而以直接参加敌对行动为核心的持续作战职责也因此只在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才能出现,其直接后果是非正规武装部队和有组织武装团体的成员减少,同时享有免受直接攻击之保护的人员增加。
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时间范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平民来说,直接参加敌对行动何时开始,何时结束;二是正规武装部队成员、有组织武装团体成员以及平民失去保护的时间范围。在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开始和结束问题上,《解释性指南》将直接参加的开始和结束限于即刻执行阶段,包括准备、部署和离开实施地点的过程,并仅限于具体行动[5]63。根据《解释性指南》,平民或是由于成为国家武装部队或者属于武装冲突一方的有组织武装团体的成员,因而彻底不再是平民并因此丧失免受直接攻击之一般保护,或是由于直接参加敌对行动而失去保护。《解释性指南》强调旋转门现象不是国际人道法失灵,而是其有机组成部分[5]68,在《解释性指南》看来,直接参加只涉及单个行动,因此每次参加结束后便重新享有免受直接攻击之一般保护。但问题的关键是,《解释性指南》在将持续作战职责作为判断有组织武装团体成员身份的标准时,特意提出与之相应的、不构成持续作战职责的行为,即“自发、零星或无组织地直接参加敌对行动”[5]32。虽然《解释性指南》的确承认“个人超出了自发、零星或无组织地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限度”将成为“属于冲突一方的有组织武装团体的成员”[5]70,但如何判断平民出入旋转门的次数是否超出“自发、零星或无组织地直接参加敌对行动”才最具决定意义。总之,《解释性指南》回避了出入旋转门次数的上限问题,而这正是旋转门问题的核心所在。平民可以“持续、反复”进出旋转门[5]42,而“有组织武装团体成员身份始于平民事实上开始为该团体承担持续作战职责之时,直至其停止承担该职责时终止”[5]70,两者所享有的法律保护上的差别,不仅未得到解决,反而被进一步固化。另一方面,如果从持续作战职责的概念来看旋转门,会得出与《解释性指南》的观点相反的结论。既然“那些持续职责涉及准备、实施或指挥行为或者其行动相当于直接参加敌对行动之行为或行动的个人,就是在承担持续作战职责”[5]33,那么,“持续、反复”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平民,如何能不被视为承担了“持续职责”呢?因此,即使是按照《解释性指南》的框架,关于旋转门也不能自圆其说。
(三)方法上的批判
第一,不谨慎的分类。在论及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平民时,《解释性指南》首先指出平民、武装部队和民众抵抗是相互排除的概念[5]20-21,认为民众抵抗者是“从平民居民中排除出去的武装人员”,只是“缺乏构成武装部队成员所需的足够组织和统率”。但是,1907年《陆战法规惯例公约》只是给予尊重战争法规和惯例以及公开携带武器的民众抵抗者以战斗员特权,从未明确将民众抵抗与武装部队对立起来,而《解释性指南》认为平民、武装部队和民众抵抗是相互排除的概念,使得民众抵抗者成为既非平民又非武装部队成员的一类人,这类人如果尊重战争法规和惯例以及公开携带武器,就同武装部队成员一样,具有战斗员特权。如此看来,《解释性指南》无非是想避开使用“非法战斗员”一词,但实际又以是否具有“合法的”战斗员特权为标准。《解释性指南》也并未说明如何确定民众抵抗的成员身份,仅仅声称“所有其他的自发、零星或无组织地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人,都必须被视为平民。”[5]25
第二,不统一的标准。《解释性指南》规定,所有表现出足够的军事组织程度并且属于冲突一方的武装人员也都必须被视为冲突一方武装部队的一部分。如果《解释性指南》只这么规定,就有可能减轻甚至解决《第一附加议定书》第50条第1款两分法带来的问题,但《解释性指南》接着依然对正规武装部队和非正规武装部队及有组织武装团体采用了差异巨大的成员身份判定标准,这导致正规武装部队和非正规武装部队及有组织武装团体相比,受到的保护明显更少,使后两者在法律上处于远比正规武装部队有利的位置。在实践中,《解释性指南》的成员身份判定标准可能意义不大,比如,当战斗员在瞄准敌人时,他如何能够判断敌人是根据国内法参军入伍(因此是战斗员而成为合法攻击目标)还是是否承担了“持续作战职责”(因此可能是平民而享有免受直接攻击之一般保护)?可能正因如此,《解释性指南》补充说明“持续作战职责可以通过穿着制服、佩戴特殊标志或携带某些武器(27)公开体现”[5]34,但问题在于,现实中,有关人员可能既不穿制服,也不佩戴特殊标志,也不携带某些武器,这种补救是徒劳的。同样,当战斗员在瞄准敌人时,他如何能够判断敌人是承担了“持续作战职责”的非正规武装部队或有组织武装团体成员(因此是战斗员而成为合法攻击目标)还是“持续、反复”出入“旋转门”的平民(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平民,因此可能享有也可能不享有免受直接攻击之一般保护)?
五、结论
平民虽然是国际人道法的基础概念,但却是通过排除战斗员而间接定义的。战斗员是比较模糊的概念,而且形式要件居多,使得平民概念也具有不确定性。在平民越来越多地参与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新形势下,平民概念受到两方面的严重挑战,一是平民和战斗员两分法的地位问题,二是旋转门与平民的保护问题。国际人道法的目的是保护战争和武装冲突受难者,区分原则是其逻辑起点和终点,在这个大背景下,一方面,必须坚持平民和战斗员的两分法,因为如果出现任何其他的人员分类,都将可能最终对平民保护造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必须开始考虑如何解决“非法战斗员”问题,即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平民。在深入讨论的基础上,形成关于“非法战斗员”的国际习惯法或国际条约,是妥善解决平民概念不确定性较为现实和可行的途径。旋转门带来的挑战,更多是理论上而不是实践上的。在理论上,反复、持续地进出旋转门的平民,与从不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平民存在质的不同,如果参考《解释性指南》提出的持续作战职责,此类平民似应被视为承担了持续作战职责,因此成为属于冲突一方的有组织武装团体成员,从而完成了从平民到战斗员的身份转换,彻底失去了一般保护。但是,这只是在《解释性指南》设定的分析框架内的一种推理,而《解释性指南》坚持平民可以自由出入旋转门不受限制。如果是在实践中,问题可能要简单得多。战斗员在判断有关人员是否在直接参加敌对行动时,只能根据当时能够获得的信息做出决定,而假如战斗员已经知道该人曾多次进出旋转门,这很可能使他倾向于做出该人是战斗员或正在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判断。
正是由于这些新问题的出现,国际人道法也开始做出初步的回应。《解释性指南》试图对战斗员实质要件进行完善以更好地区分平民和战斗员,以及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和未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平民,最终更好地保护平民和战斗员。《解释性指南》最大的问题是区别对待正规武装部队和非正规武装部队及有组织武装团体,特别反映在提出非正规武装部队和有组织武装团体成员身份判定的持续作战职责标准,而且将持续作战职责与更复杂的直接参加敌对行动联系起来,使得判断非正规武装部队及有组织武装团体成员身份更加困难,并导致非正规武装部队和有组织武装团体成员比正规武装部队成员明显享有更多的国际人道法保护。《解释性指南》并非如其所宣称的那样“不旨在改变法律”[5]6,也没有简单列举已有的国际人道法,而是在若干关键问题上提出了新概念、新标准,但这些新主张不仅在理论上存在较多瑕疵,在实践中也可能操作性欠佳。最后,《解释性指南》仅仅是反映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自身观点的文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无论如何,它是国际人道法在平民和战斗员问题上的最新努力和进展,并提供了更清晰地界定平民和战斗员的分析框架、工具和方向,因此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收稿日期]2012-10-26
注释:
①如1899年《陆战法规惯例公约》在其序言中阐明“……居民(populations)和交战者仍受国际法原则的保护”,1907年《陆战法规惯例公约》在其序言中阐明“……居民(inhabitants)和交战者仍受万国法(law of nations)原则的保护”,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3条第1款对于“不实际参加战事之人员”的最低限度的保护,1977年《第一附加议定书》第48条“基本规则”规定“为了保证对平民居民和民用物体的尊重和保护,冲突各方无论何时均应在平民居民和战斗员之间和在民用物体和军事目标之间加以区别,因此,冲突一方的军事行动仅应以军事目标为对象”,1977年《第二附加议定书》第13条第2款规定“平民居民本身以及平民个人,不应成为攻击的对象”,1998年《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8条第2款第2项第1目、第2款第5项第1目都规定“故意指令攻击平民人口本身或未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个别平民”构成规约中的战争罪等。
②Jean-Marie Henckaerts & Louise Doswald-Beck(eds.).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Rule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3-76; Jean-Marie Henckaerts & Louise Doswald-Beck(eds.).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Practic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3-450.
③如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3条第1款将最低限度的保护限定于“不实际参加战事之人员”,1977年《第一附加议定书》第51条第3款规定“平民除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并在直接参加敌对行动时外,应享受本编所给予的保护”,1977年《第二附加议定书》第13条第3款规定“平民个人除直接参加敌对行为并在参加期间外,应享受本部所给予的保护”等。
④当然也存在一些限制,如不能攻击失去战斗力的人、不能使用被禁止的武器、不能使用背信弃义的手段等。
⑤《第一附加议定书》第43条第2款。
⑥Art.155,Instructions for the Government of Arm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ield(Lieber Code).24 April 1863[EB/OL].(1863-04-24)[2012-10-20].http://www.icrc.org/ihl.nsf/FULL/110? OpenDocument.
⑦如第18条关于将非战斗员驱逐出被包围的地方以减少食物消耗(以及将其赶回以加快投降)、第19条关于在开始炮击前可通知敌方撤出其非战斗员(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第156条关于如何处理“不忠公民”等。
⑧在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倡议下,编纂战争法的布鲁塞尔会议于1874年8月召开,15个欧洲国家参加。与会国讨论了俄国提交的关于战争法规和惯例的国际协定草案,但由于某些国家不愿意使之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草案最终未能得到批准。
⑨即“民众抵抗”(Levée en masse)。
⑩Arts.9-11,Project of an International Declaration concerning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War.Brussels,27 August 1874[EB/OL].(1874-08-27)[2012-10-20].http://www.icrc.org/ihl.nsf/385ec0826509e76c41256739003e636d/a59f58bbf95aca8bc125641e003232af!OpenDocument.
(11)两个公约的附件第一章均名为“交战者的资格”,均包括三条规定,均只对布鲁塞尔草案第二部分相应三条进行了措辞上的精简和其他些微改动,例如,在叙述民兵和志愿部队成为战斗员的条件时,两个公约省去了“他们”。实际上,两个公约中的许多其他规定也只是对布鲁塞尔草案相应规定进行了些许改动。参见Convention(II) with Respect to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War on Land and its annex:Regulations concerning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War on Land.The Hague,29 July 1899[EB/OL].(1899-07-29)[2012-10-20].http://www.icrc.org/ihl.nsf/FULL/150? OpenDocument; Convention(IV) respecting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War on Land and its annex:Regulations concerning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War on Land.The Hague,18 October 1907[EB/OL].(1907-10-18)[2012-10-20].http://www.icrc.org/ihl.nsf/FULL/195? OpenDocument.
(12)在民众抵抗问题上,1899年《陆战法规惯例公约》的规定与布鲁塞尔草案规定一样,只要求“遵守战争法规及惯例”,但1907年《陆战法规惯例公约》增加了“公开携带武器”,因此战斗员的概念以后者为准。
(13)当时只是通过拘留国军事法规和纪律对战俘有关行为进行处罚。
(14)该款规定:“本公约所称之战俘系指落于敌方权力之下列各类人员之一种:(一)冲突之一方之武装部队人员及构成此种武装部队一部之民兵与志愿部队人员。(二)冲突之一方所属之其它民兵及其它志愿部队人员,包括有组织之抵抗运动人员之在其本国领土内外活动者,即使此项领土已被占领,但须此项民兵或志愿部队,包括有组织之抵抗运动人员,合乎下列条件:(甲)有一为其部下负责之人统率;(乙)备有可从远处识别之固定的特殊标志;(丙)公开携带武器;(丁)遵守战争法规及惯例进行战斗。(三)自称效忠于未经拘留国承认之政府或当局之正规武装部队人员。(四)伴随武装部队而实际并非其成员之人,如军用机上之文职工作人员、战地记者、供货商人、劳动队工人或武装部队福利工作人员,但须彼等已获得其所伴随之武装部队的准许,该武装部队应为此目的发给彼等以与附件格式相似之身份证。(五)冲突各方之商船队之船员,包括船长、驾驶员与见习生以及民航机上之工作人员,而依国际法之任何其它规定不能享受更优惠之待遇者。(六)未占领地之居民,当敌人迫近时,未及组织成为正规部队,而立即自动拿起武器抵抗来侵军队者,但须彼等公开携带武器并尊重战争法规及惯例。”
(15)第1项、第2项、第3项和第6项属于战斗员。
(16)除了照搬,该款还扩展了享有战斗员特权的主体范围,即包括满足条件的有组织抵抗运动人员和“自称效忠于未经拘留国承认之政府或当局之正规武装部队人员”。
(17)这类战斗员因为未“在从事其所参加的发动攻击前的部署时为敌人所看得见的期间公开携带武器”而在落于敌方权力时“失去其成为战俘的权利”,参见《第一附加议定书》第44条第3、4款。
(18)如Yoram Dinstein.The Conduct of Hostilities under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29-32; Lester Nunick & Roger W.Barrett.Legality of Guerrilla Forces under the Laws of War[J].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1946(3):563-583; Daniel Kanstroom.Unlawful Combat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Drawing the Fine Line between Law and War[J].Human Rights,2003(1):18-23; Noman Goheer.The Unilateral Cre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during the War on Terror:Murder by an Unprivileged Belligerent Is Not a War Crime[J].New York City Law Review,2006-2007(2):533-562; Sean D.Murphy.Evolving Geneva Convention Paradigms in the War on Terrorism:Applying the Core Rules to the Release of Persons Deemed Unprivileged Combatants[J].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2007(5/6):1105-1164等。
(19)该词最早出现于二战时期美国最高法院在奎林案的判决中,参见Exparte Quirin,317 U.S.1(1942)。
(20)《第二附加议定书》第13条第3款也同样如此规定。
(21)国际人道法意义上的“旋转门”一词最初出现在1990年的一篇文章中,作者在对《第一附加议定书》关于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规定进行负面评价时,认为“确定战斗员或平民地位的最初问题在于《第一附加议定书》为某些‘平民’提供的新旋转门”。参见Hays Parks.Air War and the Law of War[J].Air Force Law Review,1990(32):118.
(22)例如,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就明确反对旋转门一说,频繁进行军事行动的以色列也同样拒绝接受旋转门。
(23)《解释性指南》中文版对此句话的翻译故意删去了对应英文版中的“it appears essential”,即“似乎必不可少”,这某种程度上误导了中文读者对于问题的理解与判断。
(24)该条规定:“在一缔约国之领土内发生非国际性之武装冲突之场合,冲突之各方最低限度应遵守下列规定:(一)不实际参加战事之人员,包括放下武器之武装部队人员及因病、伤、拘留、或其他原因而失去战斗力之人员在内,在一切情况下应予以人道待遇,不得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或信仰、性别、出身或财力或其他类似标准而有所歧视。因此,对于上述人员,不论何时何地,不得有下列行为:(甲)对生命与人身施以暴力,特别如各种谋杀、残伤肢体、虐待及酷刑;(乙)作为人质;(丙)损害个人尊严,特别如侮辱与降低身份的待遇;(丁)未经具有文明人类所认为必需之司法保障的正规组织之法庭之宣判,而遽行判罪及执行死刑。(二)伤者、病者应予收集与照顾。公正的人道团体,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得向冲突之各方提供服务。冲突之各方应进而努力,以特别协定之方式,使本公约之其他规定得全部或部分发生效力。上述规定之适用不影响冲突各方之法律地位。”
(25)该条规定:“本议定书发展和补充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三条而不改变其现有的适用条件,应适用于为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议定书)所未包括、而在缔约一方领土内发生的该方武装部队和在负责统率下对该方一部分领土行使控制权,从而使其能进行持久而协调的军事行动并执行本议定书的持不同政见的武装部队或其它有组织的武装集团之间的一切武装冲突。”
(26)这里仅从招募或训练人员方面试举一例。有时招募或训练人员可能扭转整个战局或具体战役的成败,从而只能被视为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人员。例如,1995年8月,克罗地亚军队发动了代号为“风暴行动”的进攻,不到4天战斗就宣告结束,并夺取了之前被塞族武装占领的克拉伊那(Krajina)地区。克罗地亚军队在这场战役的表现出乎全世界的意料,其所运用的空中火力、炮兵火力与步兵推进协同进行、破坏敌方命令与控制网络等战术,无一不与之前的苏联模式形成鲜明对比,无一不带有典型的美军风格。虽然外界一致认为这是一家美国的私营军事安保公司即MPRI公司的作用,但MPRI公司竭力否认参与其中,尽管《纽约时报》曾报道在行动进行前5天,克罗地亚军队高层与NPRI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至少有过10次会谈。“风暴行动”是克罗地亚军队获得的第一次大型战役的胜利,而且也是整个前南斯拉夫内战的转折点,塞族武装因此失去优势,进而在1995年12月14日,塞尔维亚总统米格舍维奇、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波黑总统伊泽特贝戈维奇以及美、英、法、德、俄五大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和其它有关国家的代表在法国巴黎爱丽舍宫签署了停止波黑战火的和平协议。尽管MPRI公司对克罗地亚军队的具体训练与指导仍缺乏具体细节,尽管MPRI公司否认跟“风暴行动”有任何关联,但可以肯定的是,在NPRI公司涉及克罗地亚战争后。克罗地亚军队的能力有了明显且重大的提高。
(27)《解释性指南》中文版对此句话的翻译再次故意删去了对应英文版中修饰“weapons”的“certain”一词,即是特定的“某些武器”而不是泛指的、一般意义上的“武器”,这同样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中文读者对于问题的理解与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