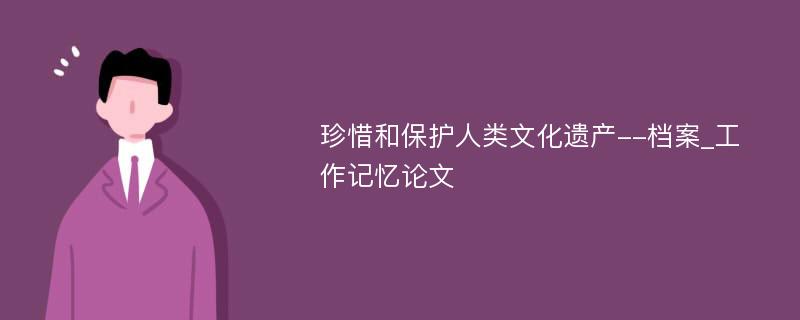
珍惜和保护人类文化遗产——档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遗产论文,珍惜论文,人类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久前,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并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日”。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远见。此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又在国家博物馆开幕。作为一名档案工作者,对此甚觉欣慰,备感振奋。
档案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信息资源、传统意义上的“资政工具”以及现代意义上的“维权利器”,同时也是存储社会记忆、传承人类文明的文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在我国,一般公众不知道档案是文化遗产,这一点不足为奇。让人感到不解和遗憾的是,有相当数量的档案部门和档案工作者也从未将档案看作是文化遗产。他们不清楚档案的本质属性,淡忘了档案工作者最崇高的职责是“守护和构建人类历史记忆”,片面地以档案的利用率高低来衡量档案的价值,贸然决定档案的存留取舍,甚至认为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信息陈旧”,“电子文件”将取代“传统档案”,“数字档案馆”至少要同“传统档案馆”并驾齐驱,“档案工作的中心和根本方向是档案信息化”,“利用是档案工作的根本目的”,因而忽略了档案这一珍贵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忽视了档案的收集、保管工作。笔者担忧,长此以往,“档”将不“档”,历史记忆将在我们这一代档案工作者手中丢失。
如果说中国的档案工作者主要关心的是如何满足现实需要,那么国际组织和我们的外国同行们则更多关注蕴涵于档案之中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这种差异的形成,既源于东西方各自固有的文化传统,也和中外对档案概念迥然不同的诠释相关。
珍惜和保护本民族的文化遗产,在西方社会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漫步于欧洲的城市和乡间,你会处处感受到所谓“老欧洲”那种历久弥香的气息;在美国这个年轻的国度里,一栋建筑即使只有上百年的历史,也不会轻易拆毁。对于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西方国家早就将其视为价值超过一般物质财富的文化财产。历史上,从早期的征服者到后来的殖民者,再到帝国主义侵略者,都曾觊觎、掠夺过被征服者的文化财产。其间或有破坏,但仍是以巧取豪夺为主。众所周知,雨果就曾痛斥英法这两个自称“文明人”的强盗对圆明园的掠夺和破坏。二战中,档案和其他文化财产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破坏和任意掠夺,劫后余生,人们深刻反思,开始意识到了一个国家的文化财产(包括档案),不仅属于这个国家所有,在一定意义上讲也属于全人类所有,因而应当受到他国的尊重和世界各国的共同保护。1954年5月1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海牙召开全体会议,制定了《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公约》。公约规定:文化财产包括档案和存放档案的场所;各国对自己领土的文化财产在平时保障安全,对别国领土内的文化财产给予尊重,不得采取敌对行动和报复行动;在发生武装冲突时,文化财产的收藏处不得用于军事目的,并使其享有豁免权和国际管制。海牙公约将档案和存放档案的场所明确列为受国际公约保护的文化财产的范畴,这标志着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
世界记忆工程的发起正是源于保护档案等文献遗产的初衷。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由于社会进步而造成的大量文明遗存的迅速流失,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文化财产中最可宝贵的、无法用金钱衡量其价值的是文化遗产;毁灭文化遗产的不仅仅是战争,更多的是我们人类自身的麻木不仁。他们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尽快行动起来,敦促各国保护好文化遗产。在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一些与会者相继指出:“不关心自己过去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民族”,“世界各国——即全人类——已经悲剧性地失去,并在继续失去大量的文献遗产——或者毁于粗心,或者毁于无动于衷——最令人痛心的是——毁于故意销毁。”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发起了世界记忆工程。1993年,在波兰普图斯克召开的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IAC)第一次会议认为,世界记忆工程必须有两个基本原则:
——生存:保证收藏品和档案得到妥善保管;
——提供利用:最大限度地向公众提供利用。①
十多年来,IAC与国际档案理事会等国际组织携手合作,在全球致力于保护档案等各类文化遗产,工作卓有成效。在与IAC的合作中,国际档案理事会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1997年9月,国际档案理事会在爱丁堡召开会议,讨论了世界记忆工程,对其中涉及的记录和档案议题发表了立场声明,提出所有的档案文件在其背景中都是独一无二的,要求世界记忆工程能够重视档案的独特性质,修改IAC过去不能以公共档案馆的全部档案为单位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决定,即将所有的国家档案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之中。2004年第15届国际档案大会更将“档案、记忆和知识”作为大会的主题,人们对于档案的社会历史记忆功能和文化遗产属性达成了更加广泛的共识。
我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留下了许多难以用金钱衡量其价值的文化遗产。毋庸讳言,更有难以数计的文化遗产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幸存的文化遗产之得以幸存,就载体因素而言,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必渗透于民族的社会形态、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物质的文化遗产,其载体必是坚固耐久。李学勤先生认为:“要求夏得到和商一样的证明,恐怕实际是不可能的。商王世系的证明,是通过甲骨文的发现和释读。商朝后期的王室和贵族,有用甲骨占卜并在甲骨上契刻卜辞的习俗,是十分特异的事例,而蕴涵大量史料的卜辞文字就得以凭借坚固耐久的甲骨质地保存下来,当时本来大量存在的竹木简册则完全消失了。不能要求夏代也有类似的文字记录传留至今,实际商代前期也是一样”②。幸存的文化遗产之得以幸存,就社会因素而言,客观上是由于旧中国社会发展缓慢、许多地方十分闭塞、人类活动对环境破坏较少,主观上则是由于历代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非常重视存史资政,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为了自家把玩而收藏,以及“厚葬”风俗和宗教传播等等。以档案的收藏为例,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清朝专门存放档案的皇史宬巍然屹立于紫禁城之侧,“石室金匮”名不虚传,清朝宫廷和中央政府的档案保管得非常完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也叫明清档案馆,现在主要保管着清朝的档案,还保管着4000多卷明朝的档案。然而,明王朝17帝277年,其档案留存至今的为何只有区区数千卷?据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同志介绍,大宗的朋朝档案从李自成起义军进京起即遭毁灭,该馆收藏的这4000多卷明朝档案,还是清朝为修明史而征集来的。民国初期的“八千麻袋”事件进一步印证,我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政权更替、战乱往往会造成法治缺失、社会脱序的局面,因而祸及档案。
战乱对档案的毁灭是明显的,也更容易受到人类良知的审判。更令人痛心的是大量的文献遗产毁于粗心,毁于无动于衷,毁于故意销毁,而我们作为当事人甚至守护者对此全然无知。单从历史传统上看,中国社会并不像西方社会那样普遍具有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2003年至2005年,央视和日本NHK合拍《新丝绸之路》,总导演韦大军在其导演手记中深有感触地写道:“西方人对掠夺的文物所采取的研究与保护干得十分出色,这个事实往往会加剧我们内心反反复复的矛盾。”③我们的内心交织着对掠夺者的谴责,对掠夺者所做的出色的研究与保护工作的“佩服”,对我们民族落后挨打历史的悲愤,对国人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淡漠甚至麻木的忧虑。最尖锐的问题是,如果这些文物没有被掠夺到国外,那么它们的命运如何?今天是否安在?最近,我们听到了一位狂热爱好北京历史遗迹和遗存的美国记者爱德华兰·弗兰科的一声叹息:“过去800年间,北京是在进行一个个摧毁与重建的循环。元朝人建起来的东西被明朝人改变,此后周而复始。”由于历史上生存的艰难,公共意识的缺失,实用主义哲学的深入骨髓,因而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全民族自觉妥善的保护。眼下膨胀于时代血脉中的利益驱动,更是我们保护文化遗产的最大“敌人”。
除上述以外,从现实情况看,对档案“生存”构成的主要威胁还有以下几方面:
——信息化浪潮的冲击,使相当一部分档案学者和档案工作者目光迷离,失去“本我”,自动消解档案学和档案工作,使之异化成为信息—情报学和信息—情报工作。
——档案工作的专业门槛过低,有相当一部分从业者人文底蕴不足,从未接受过系统的档案专业知识培训。
——囿于国家→政权→重要历史人物→宏观历史阐述→资政襄政的狭隘历史观和国家档案工作模式,大量有价值的历史记录未进入档案工作者视野。
——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缺失,以一段时期的政治尺度和思想认识水平来确定档案的存留取舍,例如对“文革”档案的人为销毁。
——在档案的鉴定上过于相信人的未卜先知能力,制定和运用档案保管期限表恰如“刻舟求剑”、“削足适履”,过早地、机械地、草率地决定文件的命运。
——档案收集不力。档案部门主动收集档案的意识不强,社会档案意识薄弱,私人收藏之风渐兴,关于收集移交档案的法规制度操作性差,措施偏软,致使大量珍贵历史记录流失在个人手中。
——档案保护意识不强。在档案业务经费的投入中,只有很少一部分直接用于档案预防性抢救和日常保护;在档案扫描是否影响档案寿命之类的重大问题上缺乏论证;档案入库消毒、经手珍贵档案需戴手套等措施不细、不严。
自1996年在北京召开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以来,随着对外交往活动的增加,特别是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档案界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档案的文化遗产属性和文明传承功能。2004年,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对档案馆的功能建设给予了新的系统阐述,即“档案馆作为党和国家的科学文化事业机构,不仅具备收集、保管、利用档案资料这三项基本功能,而且还具备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维护历史真实面貌、资政襄政、繁荣科研、发展经济、宣传教育等社会功能。要充分发挥档案馆的基本功能和社会功能,把档案馆真正建成档案安全保管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已公开现行文件集中向社会提供利用的中心和档案信息服务中心”。这一新的系统阐述首次将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列为档案馆的社会功能,标志着我国档案事业建设理念的一次飞跃。2005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在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调研时强调指出:“档案工作是一项记录历史、传承文明、服务社会、造福人民的重要工作。利用档案为党和国家的现实工作服务,就能更加充分地体现档案工作的价值和功能。”王刚同志的讲话,不仅明确提出了档案工作的基本性质、根本任务和价值实现的主要途径,而且对档案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做了更加完整的表述。
我们应该清楚地知晓,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以物质和非物质的形态留存下来的文化(包括档案)是中华民族自己认定的历史凭证,是中华民族得以延续,并满怀自信地走向未来的根基和力量之源,保护民族的也即全人类的文化遗产是档案事业的永恒之道和至高境界。我们希望并且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档案工作者已经掌握了科学发展观的精髓,是称职的护门神,能够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做出应有的贡献。
注释:
①《永恒的事业——中国与世纪之交的国际档案事业》,毛福民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
②《虞夏商周研究的十个课题》,《文史知识》,2006年第3期
③《南方周末》,2006年3月9日
标签:工作记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