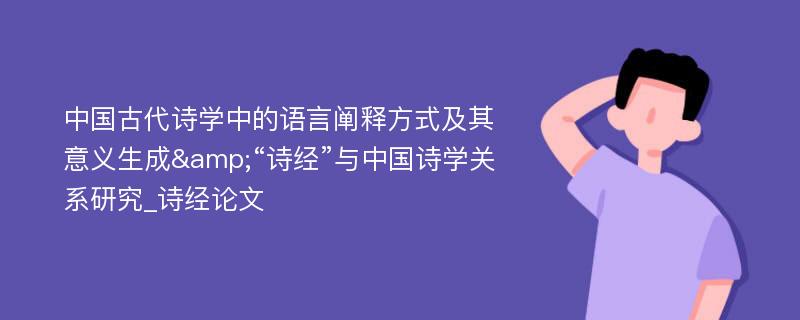
中国古代诗学话语言说方式及其意义生成——《诗经》与中国诗学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诗经论文,中国古代论文,中国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中国古代诗学,不能不研究《诗经》。而迄今为止,人们对《诗经》与中国诗学的关联究竟何在,仍然是众说纷纭。多数人都把《诗经》与中国诗学的关联仅仅定位在《诗经》本身的创作自述及历代对《诗经》的阐释、接受而引申出的具体诗学命题和范畴上。诚然,这确实是《诗经》与中国诗学重要的关联,但也还只是它们关联的一部分。
一、《诗经》与中国诗学的言说方式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诗学的言说方式主要有三种,即:“述而不作”、“一以贯之”、“比”。
一是“述而不作”。中国人都熟悉“子曰《诗》云”这四个字。这四个字看起来很平常,但却包含了中国诗学话语言说的根本特点,那就是“征圣”、“宗经”。“子曰”,就是孔子说。它的含义是,孔子所说的就是标准、依据。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在长达二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成为了统治思想。借助于政权的力量,加上遍布于国内的学校教育,特别是自隋唐以来以科举取士的制度,儒家经典成为了中国人的必读书。儒家的书,已经不再称为“书”,而是叫做“经”。由五经或六经(注:战国时期已有“六经”的说法,见《庄子·天运》。“五经”和“六经”在时间上没有先后关系。)到七经、九经,直到十三经,儒家经典成为中国人最重要书本知识,“读经”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学习文化知识的方式。经典的意识、圣人的意识早已深入人心。还在孔子去世后一百多年,孟子就以孔子为圣人,以孔子的言说为其立论的依据。其后经过荀子的发端、扬雄的发展,到刘勰将其正式归纳为“明道”、“宗经”、“征圣”,使之成为中国人言说的最主要方式,因此也成为中国诗学言说的最主要方式之一,有学者将其名之为“孔语”(注:李思屈:《中国诗学话语》第119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所谓“《诗》云”,是指《诗经》上说的。这句话的意思是“有《诗》为证”。春秋时期,“赋诗言志”成为列国交往的必备手段。在大量频繁的用《诗》活动中,经典的意识不知不觉地渗透到了古人的言说中。引用现成的经典,既可靠,又有权威,何乐而不为呢?由此,“述而不作”(接受前人的成说而不独创新说)就成为中国诗学话语言说的标准方式。“述而不作”对后来的诗学言说方式和意义生成皆有极大的影响。中国古代固然不缺少以立说为主的子书,但是以注经的方式来表达个人的学术见解(包括诗学见解)更成为一种普遍的形式。刘勰在谈到他为什么要写作《文心雕龙》时说:“敷赞圣旨,莫如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注:刘勰:《文心雕龙·序志》。)有刘勰这种看法的人并不在少数。这样做的结果是后来的经典注释学的发达,形成了“传、笺、注、疏”等系统而复杂的解经方式。于是,中国诗学的基本内容就从解释《诗经》中产生出来了,如“六义”说、“美刺”说、“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诗以言志”等等。于是中国“诗学”遂从“《诗经》学”(即《诗经》阐释学)中产生出来了。“述而不作”的言说方式,不但表现在解经上,还表现在一般的立说上。中国两千年来的诗学话语表现出非常强大的因袭性,大家所谈的问题都一样,语言表述也基本一致,以至使初次接触到中国诗学的人感觉中国诗学缺乏新意,这其实是不明白中国诗学话语言说方式的特点所致。
二是“一以贯之”。孔子的“一以贯之”是针对他的整个学说而言,那么,他对《诗经》的言说是否也表现出相同的特点呢?答案是肯定的。孔子诗学也是“一以贯之”的,这表现为两点:
首先是以“用”贯穿其中。“以用贯之”其实也是“以仁贯之”。孔子的学说,以“仁”为核心。“仁”的含义有多端,但其中心是培养出知“礼”识“义”、刚毅仁爱、文质彬彬的君子。因此,孔子论《诗》,强调实用、功利。具体说是,要《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因此他对“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的书橱式的学诗方式很不满意。孔子所说本来是针对用《诗》而言,后人却将其视为整个《诗经》创作的原则,总结出“美刺”的原则,所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美刺”说虽然由汉儒总结出来,而其初创则来自于《诗经》的创作自述。据各位学者的统计,《诗经》中涉及自述创作动机的共有16则(注:参见朱自清、萧华荣、陈良运、王运熙、顾易生等先生的统计。)。笔者数次翻检《诗经》,未见超出上述范围。16则中,《国风》3则,《小雅》7则,《大雅》6则。属于歌颂和赞美的只有3则,而包含哀伤、忧愁、谴责、劝谏、讽刺的有13则,占80%以上。汉儒正是从上述诗歌中看到了《诗经》所蕴涵的创作论的意义,才处处寻求其中的“美刺”。但问题是,《诗经》共305篇,其中谈到“美刺”的只有16篇,为什么汉儒,包括后来的注《诗》家,会把它当作整个《诗经》的创作原则呢?这就不能不引人深思了。其实,汉儒的发挥是有依据的。这依据就是前面谈到的孔子以“用”论《诗》。“美刺”正是汉儒眼中的诗之“用”。以“美刺”论《诗》正是中国诗学“一以贯之”的做法。所以清人程廷祚说:“汉儒论诗,不过美刺二端。”(注:《诗论》,《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第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其次是以“中庸”的方式贯之。所谓“中庸”,就是用其中,无“过与不及”之患,恰到好处。这体现了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就论《诗》而言,是孔子反复强调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尽美矣,又尽善也”,“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由于强调无“过与不及”,《毛诗序》特拈出“主文而谲谏”的方法,《礼记·经解》将其概括为“温柔敦厚”的诗教。中庸的言说方式,表现为诗学立论的不偏不颇,如既强调宗经,又反对抄袭;既强调继承,又提倡革新(所谓“叁伍因革,通变之数也”,“通则其久,变则不乏”(注:刘勰:《文心雕龙·通变》。));既强调文采,又反对雕琢;既提倡发乎情,又强调止乎礼义;既重视诗歌可以怨,同时又强调怨而不怨,如此等等。
三是“比”的方式。“比”本来是《诗经》“六义”之一,其含义非常复杂,可以从多角度、多层次进行分析。有论者将“比”的含义归纳为三个层次,一是用《诗》之“比”,借《诗》为比以达意;二是“比”为《诗经》的创作手法;三是整个诗歌的创作方法(注:黄强:《赋比兴涵义的构成层次及其发展阶段的分析》,载郭晋晞:《诗经蠡测》,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本文只从“比”的一般意义来使用,即“比”就是打比方,就是比喻的方式。翻检中国古代诗学的材料,我们发现,古人在进行诗学言说时,多以描写、形容的方式出之。比如,扬雄说:“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或曰:女有色,书也有色乎?曰:有。女恶华丹之乱窈窕也,书恶淫辞之淈法度也。”再比如陆机《文赋》,完全以“赋”这一文学体裁来论文。至于《文心雕龙》,则可视为一部文学作品。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注:关于《二十四诗品》的作者,目前学界有争论,具体情形,请参见《中国文化与文论》(第一期)独孤棠文。本文采用旧说。)纯粹是二十四首诗。论诗文有风骨,可谓之“有金石声”(注: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第55页。);说诗文好,如“初如食橄榄”;说诗文不好,是“初如食小鱼,所得不偿劳”(注:苏轼:《读孟郊诗(其一)》,《苏轼诗集》卷16,第796页,中华书局,1982。)。在评论诗歌风格的时候,这种表述更成为一种标准的方式,如:“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鲍明远如饥鹰独出,奇矫无前……”(注:敖陶孙:《腥翁诗评》,《诗人玉屑》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形象化或者说用诗语的方式来表达诗学见解是中国古代诗学话语的一种特殊形式,自唐代杜甫开创此体以来,踵武者代不鲜见,至自近代,尚有不少作者,如著名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专家郭绍虞先生。
这一表述方式在近现代招致了许多人的批评,认为中国古代诗学的表述太过笼统,缺乏明晰性、精确性,并进而认为汉语是缺乏思辨的语言,如黑格尔就这样认为。西方的逻各司(logos)中心和语音中心主义当然不懂得汉语这种象形兼表音文字的优点,然而,中国人自己却站到西方中心的立场上否定自己民族的这一特色,就不应该了。
二、《诗经》与中国诗学话语的意义生成
曹顺庆先生认为,中国古代诗学话语意义主要是由孔子奠定、建立起来的。他说:“我认为,孔子是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解读,来建构意义,实现文化导向的。因而,这种经典文本解读模式,是儒家文化的生长点和意义建构的基本方式,对中国数千年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这种解读模式对中国文化而言是真正奠基性的、决定性的。”(注:曹顺庆:《中外比较文论史(上古时期)》,第401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对此,也许有人会感到奇怪,孔子论述文学,不就只是在《论语》和其他儒家经典中有那么一些片言只语吗?孔子又没有一个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建立一个文论体系,他又如何来奠定和建立中国诗学话语的意义呢?其实,这是没想到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以及中国诗学话语意义的生成方式所致。在中国传统的学问中,经学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有“舍经学而外无学问”的说法。因此说孔子奠定和建立了中国古代诗学话语的意义,并不是拔高之论。
具体而言,中国古代诗学话语意义的生成方式就是“依经立义”,就是“宗经”、“征圣”,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子曰诗云”的深层含义。一个孔子,一部《诗经》,就是古人立论的依据。这一点,首先是从《左传》开始的。《左传》引用孔子的评论和《诗经》有很多。继承并发扬光大这一传统的是孟子。据笔者统计,《孟子》一书中引用的《诗经》有35条,引用“子曰”的有21条,由此可见,孟子这样作是自觉的。这里试举一例加以说明。《梁惠王上》说: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於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为灵台,谓其沼为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何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我们不惮词费,引述了上面一大段,旨在说明《诗经》这一部典籍在当时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引用孔子之语以为佐证是孟子立论的主要依据和方式。他在《离娄上》一段文字中三次提到孔子的话,足见其对孔子的倾心。孟子一再说:“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自有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注:《孟子·公孙丑上》,十三经注疏。)。其后,荀子提出“原道、宗经、征圣”。他说:“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注:《荀子·儒效》,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又说:“故凡言议期命,是非以圣王为师”(注:《荀子·正论》。)。西汉之时,儒家学说由在野升入庙堂,正式成为封建统治的官方哲学。东汉时期,涌现出了许多经学大师,扬雄就是这样一位。扬雄的著作鲜明地体现出儒家思想的影响。“原道”、“宗经”、“征圣”经由扬雄,再到刘勰,算是真正建立起来了。刘勰将《原道》、《宗经》、《征圣》放到全书前三篇的位置,足见其对儒家思想的重视。不仅如此,《文心雕龙》的核心思想仍然是儒家思想。自兹而后,“依经立义”成为中国古代诗学话语意义生成和建构的主要方式。
以上只是一个粗略的概述,下面就以具体例子加以说明。众所周知,两汉时期关于屈原的评价,曾引起一场大争论。刘勰在《辨骚》中作了简明的叙述,他说:
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以为露才扬己,忿怼沉江;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昆仑、悬圃,非经义所载;然其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虽非明哲,可谓妙才。王逸以为诗人提耳,屈原婉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驷虬乘翳,则时乘六龙;昆仑、流沙,则《禹贡》敷土;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者也。及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扬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四家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不合传;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
刘勰认为五家都没有真正把握《离骚》。那么,这五家,包括刘勰自己,他们评价《离骚》依据的是什么呢?其实他们的标准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六经。王逸在其评论中,不知不觉地说出了中国古代诗学话语意义建构的根本方式。当然,王逸不是凿空立论,在说到“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注:王逸:《楚辞章句序》,四部丛刊。)的时候,是有先例可援的。这先例就是孔子。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思无邪”三字,出自《诗经·鲁颂·駉》。按照《诗传》,这首诗是“颂僖公也。僖公能尊伯禽之法,俭以足用,宽以爱民,务农重谷,牧于垌野,鲁人尊之。于是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思无邪”,郑笺云“思遵伯禽之法,专心无复邪意也”(注:《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第610页,中华书局,1980。)。按照今人的研究,“思”为助词,无义。孔子将这一具体所指变成了整个《诗经》的主旨,确实有断章取义的嫌疑。不止孔子这样,孟子、荀子、《左传》皆如此。“断章取义”可以说是春秋时期普遍的做法,卢蒲葵就明白地说“断章取义,予取所求焉”(注:《春秋左传正义》襄公二十八年,十三经注疏,第2000页,中华书局,1980。)。长期以来,断章取义被视为武断、主观,缺乏严谨性。其实,任何历史都是阐释的历史。伽达默尔认为,阐释有前见,前见有历史性,而历史性既是接受的障碍,又是接受的前提。也就是说,阐释的前见具有合理性。因此,尽管引用的部分被误读、被发挥,但是,引者将其作为立论的出发点仍然是被允许的。
以上就“依经立义”的来源及其合理性作了说明,下面就“依经立义”的具体方式再作分析。“依经立义”的方式之一是直接引用经典原文。春秋及其后,引用五经以为佐证是立论的普遍方式。这一点,无须再多举例,只需要翻检一下先秦及后代的典籍,就很清楚了。其二是解经学的方式。经典解读的方式主要是注释,具体方法有训、诂、笺、注、疏、正义等。中国古代学术分类,小学(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是附在经学之后的,或者说,就是经学的部分。十三经中,《尔雅》就是一部训诂著作。有学者认为训诂文化与中国古代美学有密切关系(注:祁志祥:《中国美学的文化精神》,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同样,训诂文化也与中国古代诗学有密切联系。中国古代诗学的许多范畴和命题就是从经典注释中产生出来的,比如在对《诗经》的注释中,就提出了美刺说、六义说、谲谏说、志情说等,著名的《毛诗序》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三是关于五经的专题论文。中国古人多有五经论、六经论之类的著作,比如宋代苏洵、苏辙父子,元代郝经等都有。我们试以苏洵为例,看看其中的具体情形。《苏洵文集》今存16卷,《六经论》就占了一卷。《诗论》说: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于生,而愤憾怨怒,有不顾其死,于是礼之权又穷。礼之法曰:好色不可为也。为人臣,为人子,为人弟,不可以有怨于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岂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无思,和易而优柔,以从事于此,则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趋诸其中,是非不平之气攻诸其外,炎炎而生,不顾利害,趋死而后已。噫!礼之权止于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则人不敢触死以违吾法。今也,人之好色与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发于中,以为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处其身,则死生之机固已去矣。死生之机去,则礼为无权。区区举无权之礼以强人之所不能,则乱益甚,而礼益败。……《诗》曰:好色而不至于淫,怨尔君父兄而不到于叛。严以待天下之贤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观《国风》婉娈柔媚而卒受于正,好色而不至于淫者也;《小雅》悲伤诟譸,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于叛者也。
苏洵认为六经各有其用,《礼》与《诗》不同,前者是施之于未然之前,而后者用来解决前者无法达其功之时,或者说《诗》用于《礼》已经无法解决问题之时。在苏洵看来,好色、怨怒之心,人皆有之。当人无法排解之时,必须要有一个宣泄的渠道,如果没有,那么就可能造成不可预料的后果,因此,圣人用《诗经》来使人的情感得到宣泄。这一观点虽然说不上高明,但是,他肯定了人的情感的合理性,肯定了文学创作应该表达情感。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古代文人有关六经的论述,或许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三、《诗经》与中国诗学精神
《诗经》与中国诗学发生关联,还表现在由赋《诗》、引《诗》、教《诗》、注《诗》等系列活动引申出的诗学精神。《诗经》蕴涵的诗学精神非常丰富,可以说,整个儒家诗学的大部分命题和范畴都来自于《诗经》,中国古代文人没有谁不受到《诗经》的影响和沾溉。这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古代诗文的“风骚”(骚雅)传统中的“风雅”。下面就《诗经》引申出的诗学精神作一简要的分析。
一是言志为本的精神。朱自清先生将“诗言志”视为中国诗歌“开山的纲领”(注:朱自清:《诗言志辨》,第4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这一说法大致不错。其实,清代的方玉润就已说过,“诗言志”四字为“千古说诗之祖”(注:方玉润:《诗经原始(上)》,第42页,中华书局,1986。),朱自清先生或许受到其影响。“诗言志”出自《尚书·尧典》,这句话当然不会是帝尧所说,也不是首先从创作论的意义来说的,而是诗歌接受论,陈良运先生对此已作了详细论证(注:陈良运:《“诗言志”新辨》,《江海学刊》,1990(1)。)。虽然“诗言志”是从接受论的角度来谈的,但它并不影响《诗经》与中国诗学的关联。因为《诗经》的创作自述和春秋时期普遍的“赋《诗》言志”,已经把“志”与《诗经》、诗歌紧紧联系起来了。无论是赋诗以言志,还是从《诗》而观志,人们已经明确地把“志”看作《诗经》和一切诗歌的特点。明确从创作论对《诗经》进行总结的是《毛诗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里明确把“志”“情”定为诗歌表达的本源。一般说来,“志”中包含了“情”,但“志”包含的理性是比较明显的,特别是其中包含的儒家思想。魏晋时期,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开启了魏晋主情主义的浪潮。于是,“言志”与“缘情”遂成对垒。唐代孔颖达看出了这一点,提出“情志一也”,力主调和。其实,情志分途自屈原就开始了,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的情感相当浓郁,到了魏晋,更蔚成风气。但是在所谓主情时期的魏晋,儒家诗学的影响仍然存在,比如裴子野就针对陆机的“缘情”说而举起“言志”的大旗,提倡恢复儒家诗学的传统。隋唐时期,随着儒家思想的复兴浪潮,“言志”为本的观点再次被强调,隋末大儒王通、唐代杜甫、韩愈、白居易都力主恢复儒家诗学,直到宋代,张戒还说:“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古诗、苏、李、曹、刘、陶、阮,本不期于咏物,而咏物之工,卓然天成,不可复及,其情真,其味长,其气胜,视三百篇几于无愧,凡以得诗人之本意也。潘、陆以后,专意咏物,雕镌刻镂之工日以增,而诗人之本旨扫地尽矣。”(注: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张戒还只是重申“言志”说,肯定言志为本,没有否定诗歌创作存在的合理性。他与道学家的主张是大有分别的。元明清三朝,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对诗文创作影响更大。元代诗文四大家就十分重视在诗文中表达儒家思想。明代的宋濂、清代的沈德潜、翁方纲,都是恢复儒家诗学的热心倡导者。可以说,言志为本的思想贯穿了中国古代诗文创作的整个历史,尽管其中有高潮也有低谷,但是这一事实是不容抹杀的。至于其影响是正面还是反面,非三言两语可以道断。
二是伦理教化精神。伦理教化就是诗教、比兴美刺。“诗教”首见于《礼记·经解》。《经典释文》引郑玄说:“《经解》者,以其记六艺政教得失。”六教又可谓六艺,见《淮南子·泰族篇》。“诗教”的具体内容是“温柔敦厚”。按照《正义》释文,“温”是外在的神情,“柔”是内在的性情,“敦厚”则是最深层的品德。总而言之,温柔敦厚是人从外到内的和顺、忠诚、朴质。温柔敦厚来自于教《诗》、学《诗》的活动中。至于为何要将《诗》教放到六教之首,《孔子闲居》云:“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注:《孔子闲居》,《毛诗正义》卷1,十三经注疏。)这就是说,人都有“志”,志有所发,则产生了《诗经》。《诗经》也就包含了礼和乐。《诗经》能使人温柔敦厚,因此,礼乐就有了安放之处。白居易说:“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注:白居易:《与元九书》,《白居易集》,卷45,中华书局,1979。)其理论出发点与《诗经》是完全一致的。诗教之所以要用《诗》来进行,是与《诗经》本身包含丰富情感分不开的。欲以理晓人,最好先以情动人。懂得这一点,我们就容易明白,孔子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为什么要以“兴”为开头,因为“兴”是感发志意。诗教由汉儒提出,而其源头来自孔子。孔子“以《诗》《书》《礼》《乐》教”(注: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教的目的是为了“化”,使人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
伦理教化的诗学精神强调文学的现实功能、实用价值,这对中国古代文学及诗学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它使作家意识到自己创作的责任,积极地用笔来干预现实,直面人生,创造出了优秀诗篇,如汉乐府、古诗十九首,三曹七子、陶、阮、杜甫、白居易等作家的作品。另一方面,伦理教化要求太过,又给古代文学带来了忽视审美性的缺陷,其极端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注:高明:《琵琶记》第一出,《六十种曲》,中华书局,1958。)、“如此闲言语,道出作甚”(注:程颐:《二程语录》卷11。),甚至有“作文害道”之说。
三是含蓄精神。中国古代诗学非常重视“言近旨远”、“言内意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等等。含蓄的文化精神是中和,具体方式是“主文而谲谏”。所谓“主文而谲谏”,《毛传》说:“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那么,不直谏,又采用什么方式呢?《正义》说用“譬喻”,就是用比兴。而对比兴的解释,迄今为止,仍是人言言殊。比如最早对比兴作出解释的郑众说:“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也。”郑玄云:“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款,取善事以喻劝之。”则纯粹从政教角度立论。刘勰说:“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注:刘勰:《文心雕龙·比兴》。)刘勰的说法则着眼于比兴如何产生,功能何在。不过,刘勰把情归之于“兴”,把理归之于“比”,就不尽合《诗经》的实际,更与创作的实际相差甚远。其实,比和兴都是比喻、象征,都包含了情、理,只不过有显隐的区别。不管比兴有多少说法,但关涉创作方法这一点是毫无异议的。如果说,两汉论比兴,强调含蓄,更多的人政治教化着眼,那么,魏晋而下,特别是唐宋时期,随着对诗美的探求,比兴就被赋予了更多的审美意义,比如皎然、司空图、严羽等人的诗论就表现出这一特点。当然上述只是大致区别,其中的情形复杂,非一句可以道尽。在唐代,既有皎然、司空图重视从审美角度来分析比兴的,还有杜甫、白居易、皮日休等人强调从美刺的角度来运用比兴。宋代的情形也很类似。苏轼和黄庭坚就很不相同。苏轼提倡“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如万斛泉涌,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黄庭坚则不然,他认为:
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廷,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也。其人忠信笃敬,抱道而居,与时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并世而不闻;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而闻者亦有所劝勉,比律吕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诗之美也。其发为讪谤侵凌,引颈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注:黄庭坚:《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豫章先生文集》卷26,四部丛刊。)
这段话甚类《毛诗序》和班固的《离骚序》,诗教气味十分浓厚。不过,他说这话也是迫于宋代严密的文网,是有鉴于其师苏轼的遭遇而发。
通过上面简单叙述,可以看出,含蓄作为诗文创作的基本要求,有其合理性,也有其片面性。好处是它重视了诗文作为审美对象应该具备的必要条件,看到了诗文的特殊性,对中国古代文学的面貌有极大的影响。而如果作家把含蓄视为逃避现实、谄媚君王的手段,其负面作用可谓大矣哉!
四是诗史精神。中国古代文学创作有一个“风骚”传统,分别构成了诗歌的写实和浪漫两派。我们不赞成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来概括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但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有偏重写实、浪漫两派。“风雅”传统就是写实这一派的概括。先秦时期,荀子就说“天下不治,请陈佹诗”(注:《荀子·赋篇》。)。汉代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汉乐府继承了《诗经》的传统,正如余冠英先生说:“《诗经》是汉以前的乐府,乐府就是汉以后的《诗经》。《诗经》以《变风》、《变雅》为精华,乐府以《相和》、《杂曲》为精华,同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里巷歌谣,同是有现实性的文学珠玉。”又说“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精神虽然早就表现在《诗经》,但是构成一个传统,却是汉以后的事,不能不归功于汉乐府”(注:余冠英:《乐府诗选》,第8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汉乐府之后,三曹七子、杜甫、白居易等人都遵照《诗经》的风雅传统,创作出了大量光辉的诗篇,尤其是杜甫,更成为中国诗史的一座高峰。“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些愤怒的控述,使人感受到杜甫那颗正直的心的剧烈跳动。“公如登台府,临危莫爱身”的殷情叮嘱,“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博大胸怀,确实不负于他的“诗圣”称号。
诗史精神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即中国古代历来有以诗为史的传统。这一传统也是由《诗经》引申出来的。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然后《春秋》作”(注:《孟子·离娄下》,十三经注疏。),又提出应“知人论世”。在其著作中,他往往指明某诗为某人某时作,这当中有的是为了论证的需要而进行曲解,但可见其对诗歌表达的历史的重视。汉儒研究《诗经》,有所谓“正风”、“变风”,“正雅”、“变雅”的区分,其根据就是认为“诗即史”。郑玄就将这一原则贯彻到《诗经》的注释中,并且以此为纲,写了《诗谱》。汉人评价《史记》,也是从“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来进行的。当然,也可以说,《史记》本身就是历史著作,强调真实性,应是题中之义。但是唐代的传奇小说,往往在其结尾,郑重其事地说明所述故事的来源,以取信于人。至于宋元以来的话本小说、明清的历史演义,更是把真实性放在第一位。直到今天,每当一部历史剧引起轰动之时,总是要引发一场关于剧本真实性的争论。这说明诗即史的观点直到当代,仍然有其巨大影响。
以上我们就《诗经》与中国古代诗学的关联进行了分析,从中可以看出,要真正把握中国古代诗学,必须从根本上去进行。所谓根本,即应当从孕育、产生中国诗学的母体——中国传统文化来进行探索。迄今为止的中国古代诗学的研究虽说成果颇丰,也仍需注意从文化与文学的紧密关系来探讨。
标签:诗经论文; 儒家论文; 诗学论文; 先秦文化论文; 离骚论文; 读书论文; 文心雕龙论文; 国学论文; 孔子论文; 毛诗序论文; 古诗词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