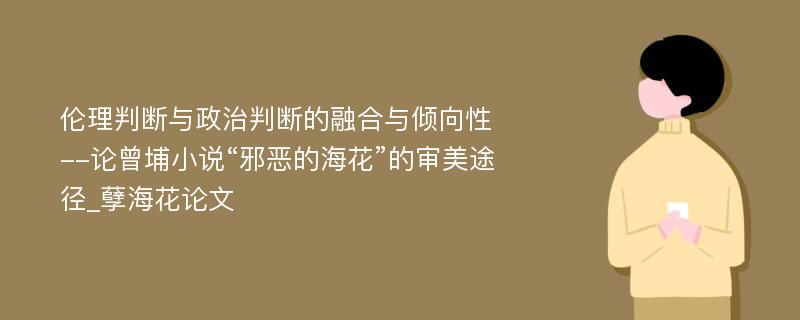
伦理判断与政治判断的融合和倾斜——试论曾朴小说《孽海花》的审美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孽海论文,伦理论文,试论论文,政治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曾朴的《孽海花》,作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表现出与以往中国历代小说甚至同时代的谴责小说明显不同的审美方式,那就是伦理判断与政治判断的融合与倾斜。
关键词 中国小说 曾朴《孽海花》 审美方式 伦理判断 政治判断 表达方式
作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孽海花》,是一部明显有别于其他三部谴责小说的作品,也是曾朴的代表作。它的特别之处表现在它的审美方式上,那就是:伦理判断与政治判断的融合和倾斜。也就是说,在创作过程中,作者曾朴是以伦理判断和政治判断作为他的美学准则来塑造形象,描写故事的。然而,这两种判断不是呈平衡状态的,而是表现出一种较明显的倾斜——伦理判断不再像中国古代长篇小说那样占主导地位,政治判断代替伦理判断的角色主宰了作者的创作倾向,并影响了作品的主题。对于《孽海花》这一审美方式的研究,前人还未作过系统的论述。本文拟从作品(以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35回本《孽海花(修订本)》为研究对象)切入对这种审美方式及其表达方式和形成原因作一番审视。
一、两种判断在作品中的体现
要分析作者的审美方式,就必须先对构成作者审美方式的两个准则来一个界定。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伦”是指次序,表示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理”是指道德和规则,而伦理就是处理人们相互关系所应遵循的道德和规则。因此,所谓伦理判断,是主体依其特定的价值系统,以善或恶,正义或非正义,公正或偏私,诚实或虚伪等道德概念对人们的行为所做的评价。具体到文学作品就是指作者以道德的尺度作为审美标准,通过善恶的内涵来认识、评价和反映社会生活。政治则是经济集中的表现,以阶级斗争和处理阶级关系为其主要内容。它具体表现在国家生活、国际关系方面的政策与活动,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因此,所谓政治判断是主体以其所属阶级的利益作为标准的审美评价。作者以某一阶级利益出发去塑造人物、描述事件并表达他的政治见解和对某些政治现象、政治活动的评价。然而,无论是伦理道德,还是政治主张、政治活动都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和阶级性,这就造成了伦理判断和政治判断在不同的时期、对于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内涵。就曾朴的《孽海花》看来,他的伦理判断是一个混杂着资产阶级维新 改良伦理思想和封建伦理意识的“衡量器”,其政治判断则是以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思想为标准,对晚清三十年血泪史的褒贬。下面我们结合晚清社会状况和作品实际作具体的分析。
(一)、两种判断的融合特点
这种融合主要表现在作品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在作品里,带有伦理色彩和政治印记的人物共游于“孽海”之中,构成了《孽海花》的独特人物群体:有的被染上伦理的色彩;有的被烙上政治的记号;有的则两者兼而有之。
傅彩云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可以说,她是用作者伦理精神铸造出来的,因为在她身上体现了鲜明的伦理风貌。傅彩云,先是一个妓女,后因“体态风流、丰姿绰韵”而被状元金雯青看上,使她由“窑姐儿”一转身成了“状元夫人”、“公使夫人”,开始了她的“浪漫”生活。在柏林交际场中,因“生性聪明、巧得人意,倒弄得艳名大噪起来。”(P90)[①]然而,她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在雯青“杜门谢客”、“补正史传”时,她却和仆人阿福在楼上“翻江倒海、撩云拨雨”。(P118)还在使馆楼上当街演唱“雅词”——“十八摸”。引来青年军官瓦德西的痴恋。在返国的轮船上,又与船主质克掀起了一场“风波”。回国后,与阿福的私通把雯青气得“一时昏绝”,但是,她并不因此而 “悬崖勒马”,又“馋猫儿似的”“刮上了一个戏子”,(指孙三儿,P214)以至把一个“闻名中外”的状元活生生的气死。丈夫死后,她又不安于“妇人之道”——守节,并且暗中偷人,与孙三儿姘居。最后“重张悬牌燕庆里”,又回到了她的起跑点——妓女。以傅彩云的生活历程来看,在她的身上孕含着丰富而复杂的伦理思想。一方面,她体现了作者较为先进的伦理观。傅彩云虽然出身妓女,但她有一种“争自由”的精神。她敢于掀开盖在丈夫金雯青一类腐朽官僚身上的假嘴脸:“你们看着姨娘,本不过是个玩意儿,好的时,抱在怀里,放在膝上,宝呀贝呀的捧;一不好,赶出的,发配的,送人的,道儿多着呢?”(P182)这番话活现了封建士大夫们的丑恶灵魂和污秽行为,同时也道出了封建妇女的可悲地位和反抗心声。能说出这番话,足见傅彩云的勇气。对于封建的伦理纲常,她也是不屑一顾的,她对雯青说:“当初讨我的时候,就没有指望什么三从四德七贞九烈……老实说,只怕你也没有叫我死心塌地守着你的本事嗄。”(P182—P183)这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她对封建伦理纲常的反叛。因为在封建传统的伦理规范里,“三纲五常”是核心内容,作为妻子的要“以夫为纲”,丈夫在世时,要听从丈夫的话;丈夫死后,就要守节,不能再嫁人。但傅彩云却不是这样,她不愿意做丈夫的奴仆,经常独自寻找自己的“快乐”,同时她也不甘守节的寂寞,要求张夫人必放她出去,这是近代比较进步的伦理思想在作家笔下的自然流露。伦理思想发展到近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三纲五常”的封建名教遭到了批判,先进的中国人,一方面继承中国古代伦理思想中的某些有用成分;另一方面向西方学习,吸收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某些伦理思想,提出了同封建伦理思想相对立的新的伦理思想。例如,康有为提出了“去苦示乐”的自然人性论,反对道学家们鼓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禁欲主义。在道德观上,他提出了“以人为主”的人道主义原则,认为“夫为妻纲”是完全无视“女子当与一切男子同之”,“女子最有功于人道”的事实,造成了广大妇女“为囚、为刑、为奴、为私、为玩”的悲惨命运[②]。可以说,在傅彩云身上就体现了这种新的伦理思想,或者说,她就是一个康有为所说的“去苦求乐”式的人物,但可惜的是,作者没有把握好尺度和方向,使傅彩云的追求越出了生活的正常轨道。
另一方面,作者并不是真正要把傅彩云当作是封建伦理的叛逆者来塑造的,相反,把她写成了一个“恶”的典型,一个充满“变态性欲”的“淫妇”。《孽海花》之“花”就是代表着外形美丽而本性放荡的妓女傅彩云,因此,傅彩云就成了一朵“罪恶的花”。但是,历史上的傅彩云并不是这样的人,她虽然是妓女,但更多是由于生活所迫,在她的生活中,有着一段坎坷的遭遇。而作者对于这些都属视无睹,在自己道德判断的驱使下,把一桩桩的“罪状”戴到她的头上去。这是作者用伦理道德代替历史判断所造成的对历史的傅彩云的扭曲。可见在傅彩云的身上,作者的封建伦理观是占主导地位的。
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进入近代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统治阶级的日趋腐朽,帝国主义的入侵,致使妓院林立,妓女、嫖客队伍不断扩大。作者也看到了这一点,除傅彩云外,还写到了诸爱林、梁聘珠、小玉等妓女,但是,作者却没有透过这些风月场中的“欢乐”看到其悲惨的社会根源。更糟糕的是,作者总是把许多重大事件发生的根源归于男女恋情,并大都把责任推在女人身上。例如,金雯青的死是因为烟台旧相识梁新燕化傅彩云来复仇;台湾唐景菘抗日失败是由于两部将争夺美女银荷;两宫失和源于光绪不满慈禧太后为其确定的婚姻……这是作者以“女人是祸水”的观点出发,为封建伦理所作的一番可悲的阐释,足见作者唯心史观的荒谬与可悲。此外,作者还用封建伦理的雕刀,塑造了“孝义”相兼的龚孝琪;“贤惠”的张夫人;“第一忠臣”韩惟荩以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忠孝”全具的威毅伯之女。因此,我们以傅彩云等人身上既看到了闪耀在曾朴身上的先进伦理思想的晨光,但也更加沉重地感到在他的伦理世界里封建的黑夜还主宰着人们的命运。
上述所分析的是伦理判断在某一些人物身上的展现。但是,在作品中这样的人物是为数不多的,更多的人物是带上政治印记而“登场”。这一类人物在作品中真可谓俯拾皆是。维新改良的先驱冯桂芬主张西学,他对金雯青说:“昔孔翻百二十四国之宝书”,我看现在读书,最好能通外国语言文学,晓得他所以富强的缘故,一切声、光、化、电的学问,轮船、枪炮制造,一件件都要学会它。”(P9)而姜剑云则大读公羊学说:“凡做一个人,都有干涉国家政事的权柄,不能逞着一班贵族,任意胡为的……倒是现在欧洲各国,民权大张,国势蒸蒸日上,可见夫子春秋的宗旨,是不差的了,可惜我们中国,没有人把我夫子的公平学说实行出来”。(P87)在这里,姜剑云提出了较为先进的民权思想。在近代,许多觉醒的知识分子都意识到中国的落后,认为“我国只有力图自强,方足自存在这种大战世界。”(P157)于是,他们都在探寻强国的道路,在谈瀛会上,士大夫们各抒己见。薛叔云从外交的角度出发,认为富强之计,有两件必须力争,一是“该把我国列入公法之内,凡事不至十分吃亏”;二是“南洋各埠,都该添设领事,使侨民有所依归。”匡次芳主张“以练兵为第一”;徐忠华提出“农工商三样,实是国家的命脉”;云仁甫认为最要紧的是“办银行”、“筑铁路”;李台霞则认为“用心那些机器事业的形迹是不中用的”,必须着手政体的改革和发展教育……这些人所说的都是他们各自的政治主张,或者说是他们认为中国应该走的路。而他们呢?则成了“政治的单纯的传声筒”,向人们、向社会传出了“自强”之声。像这样充满政治感的人物还有后面写到的革命派,如陈千秋、陆皓冬、杨衢云和孙中山等。总之,作者在塑造这些人物时,是和当时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并且以他的政治标准来进行的。
我们从上述可以看到,充满伦理色彩和印有政治标记的人物在作品中共存,这是一种比较明显的两种判断的融合表面。然而,在某些人物身上,还体现了“两位一体”式的融合,就是说,在一个人物身上,融合了作者的两种判断。金雯青和何珏斋就是这样的人物。先说金雯青,在伦理道德上,他是一个沦丧者,对梁新燕始乱终弃,使其吊死;表面上要“全孝”、“全节”,但他这位“花月总持、风流教主”一见到女色就以“自己不是真道学”而“风流”起来,偷娶妓女傅彩云。在这位“一生见色不乱”的状元身上,体现了封建伦理的绳带已完全断裂。在政治上,他又是一个失败者。不能说他不忧国,但由于昏庸无能,错印中俄交界图而使中国丧失了八百里的土地。最后,作者把他当作“恶”的典型进行了否定。再说何珏斋,他是一个“素来欢喜讲程朱之学”的道学家,因此,不喜欢喝“花酒”,他极讲“仁义”,在和日军的交战中,用告示标明:“惟本大臣率仁义之师,素以不嗜杀人为贵”,对于日军俘虏也“一日两餐,与中国人民,一律看待”。因为他认为“仁者无敌”,要借军威来施行“仁政”,以“救两国人民之命”。这是资产阶级“博爱”人道主义思想的表现。同时,何珏斋又是一个政治性很浓的人物,不说他平时的政治活动,单从甲午中日战争就可以看出来。在日本入侵清兵败退的情况下,他一面“致书北洋,慷慨请行”;一方面招兵买马,准备迎战,成了主战派的先锋人物。在何珏斋身上,政治与伦理已达到了不分你我的融合。
总而言之,无论是在单个人物身上,还是在人物群体之中,都体现了伦理判断与政治判断的融合。
(二)、审美方式构成因素的倾斜表现
虽然作品《孽海花》在人物的塑造上体现了伦理判断与政治判断的融合特色,但是,在作者审美方式的天平里,出现了严重倾斜,政治判断的份量远远大于伦理判断,并影响了作品的主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从作者的创作动机来看,作者是“想借主人公做全书的线索,尽量容纳近三十年来的历史”。[③]而在作者看来,这三十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一时期内飞也似的进行[④]。”于是作者便从这一历史状况出发,把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变迁“收摄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自然地一幕一幕的展现”[⑤]。作者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作品所写的大都是当时重大的政治事件,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中日甲午战争等等。而所描述的其他人物事件都是在这个政治主杆之上的“节外生枝”。而总的来说,作者是坐在政治的“审判席”上,写就了他这部富于政治色彩的小说《孽海花》,展现了晚清三十年的政治文化状况,反映了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和新旧政治势力的斗争与兴衰。
第二、从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和历史事件来看。据刘文昭先生考订的《〈孽海花〉人物索隐表》(P356—368)的统计,《孽海花》一共写了二百七十六个人物。在这些人物群像中,除了名妓(妓女、男妓)、演员、佣仆等之外,没有一个不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没有一个不被打上政治的烙印。特别是那些带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维新改良派和革命派人士,他们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当时的政治斗争,他们的思想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当时斗争的形势和方向。与此相适应,作品所描述的一系列历史事件都是当时的政治斗争。综观整部作品,作者描述了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金雯青出使四国、俄国虚无党运动、谈瀛会(论自强之法)、朝鲜东学党起义、中日甲午战争、《马关条约》的签订、革命党人的政治活动、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和广州革命起义。这一连串的历史大事件组成了《孽海花》的生命内核,形成了作品特殊的政治氛围。在作品中,也描述了一些与政治关系不大的事,如傅彩云、龚定庵、陈骥东等的“风流韵事”,但这些都是作为一种点缀品,在作者看来,是为了增加一点“浪漫”的色彩,对主题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可见,作品在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描述中,是倾向政治判断的。这正如陈则光先生所说:“《孽海花》固然也暴露了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嫖妓纳妾’的罪恶,但这只是次要的,而主要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⑥]。
第三、政治判断占主导地位,影响并决定了作品《孽海花》的主题倾向。对于《孽海花》的主题倾向,只要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阅读和分析,就会发现它蕴孕着一个十分鲜明的进步的政治倾向。用阿英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它能比当时其他谴责名著更深刻、更本质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提出了当时人们最积极的愿望:反清统治、反帝国主义、进行民主革命”,小说“主要的一面,还应该说是革命的、前进的、比较站在人民方面的”[⑦]。即是说,它既有对封建统治、帝国主义的揭露谴责,也有对维新运动、民主革命的肯定与同情。这可以从作品中找到例证。在第一回,作者以强烈的忧患感描绘了一幅封建社会的危机图——奴乐岛。这岛处在“孽海”之中,那儿的国王“暴也暴到吕政、奥古士都、成吉思汗、路易十四的地位;昏也昏到隋炀帝、李后主、查理士、路易十六的地位”。那儿的国民“从古没有呼吸自由的空气”,“没有一个不是奄奄一息,偷生苟活”,“醉生梦死”。这个岛实际上是清末中国社会的缩影,它暗示了封建社会到了土崩瓦解的时候了。所以作者悲痛地呼唤:“四百兆同胞,愿你早登觉岸”。希望人们尽快觉悟起来,通过维新去拯救即将沉沦的祖国。如果说这是救国的呼声,那么作者在这一回以后写的就是对祖国强盛之方的实践探寻。作者首先把他的解剖刀刺向封建的科举制度和官场。他对状元作了这样的讽刺:“这是地球各国,只有独一无二之中国方始有的;而且积三年出一个,要累代阴功积德,一生见色不乱,京中人情熟透,文章颂扬得体,方才合配。这叫群仙领袖,天子门生,一种富贵聪明,那苏东坡、李太白还要退避三舍,何况英国的培根,法国的卢梭呢?”(P4—5)于是提出了维新的主张,“要仿效西法”、“办学堂、开民智”,使国民从混沌中觉醒。然而,作者更多是把封建官场暴晒在太阳光下,用愤懑的笔尖绘出了一幅封建统治者们的丑恶图。小说中写了慈禧太后的野蛮与专权;写了鱼邦礼、徐敏的买官;写了巡抚达兴的道德沦丧……对封建官场的丑恶现象来了一次大曝光,目的在于使人们清晰地认识到封建政府已“不足图治”而起来维新变革。在批判、揭露封建黑暗的同时,作者也歌颂了当时的进步力量,他肯定了维新派的政治主张,又随着时代的步伐赞颂了革命派的先锋人物。对于外国的侵略,作者一直是站在主战的立场上。对中法战争,他指责了只会纸上谈兵的庄仑樵和“只知讲和”的威毅伯,(P42)并且借“花哥曲”赞颂了刘永福的抗法事迹。对日本的侵略,作者的主战态度更是坚决,写了人民的喊声:“战呀!开战呀!给倭子开战呀!”(P219)还写了一批主战派人物的各种活动,如龚尚书、章直蜚、闻韵高写“手折”要求政府“速整舰队游弋日本洋”;何珏斋则“慷慨请行”。战争虽以失败告终,但作者那种主战的精神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心愿。特别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对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的描述,真可谓令人振奋。可见,作品表现出来的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革命的。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曾朴虽然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其他谴责小说家,但他也像其他谴责小说家一样,基本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维新改良的立场上,带着“思改革”的目的来进行小说创作的。这使到他的政治判断露出了不可掩盖的弊端:一方面对封建科举制度进行热烈的抨击,另一方面又表示出苦苦的痴恋;一方面是对封建僵尸的愤怒鞭挞,另一方面是企图挽救这不可救药的病态社会;一方面赞同民主革命,另一方面又害怕革命会流血;一方面痛斥威毅伯的投降卖国,另一方面又对他签订《马关条约》的处境深表同情……还错误地把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说成是由于国力过强,“譬如一杯海水,不能不溢于外。”可见,作者反对封建、反对帝国主义、进行民主革命的思想和行动都是不彻底的。综观曾朴的一生,他出生于封建大家庭,经历了戊戍变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三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他既是封建制度的举人,又是维新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参与者;在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又出任江苏省议员等职,他还从事法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工作。这种复杂的生活经历和政治活动,直接造成了曾朴思想的复杂性和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从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创作动机、人物事件还是主题倾向,都体现出作者的审美方式向政治判断倾斜。所以在《孽海花》中,既体现了伦理判断与政治判断的融合,又体现了融合中的倾斜。
二、扣合和表达两种判断的方式
从小说叙事视角的形态来看,主要有三种模式:叙述者>人物(即全知的叙事观点);叙述者=人物(又称“内焦点叙事”);叙述者<人物。不同的作者会选择不同的叙事形态去创作,以表达他的审美方式。《孽海花》的作者曾朴继承了中国说话小说的传统,采用全知的叙述观点,叙述了印满血痕的“三十年旧事”,扣合和表达了他的伦理判断和政治判断。
所谓全知的叙事观点,它是就叙述者与故事的关系而言的。它的特点是:叙述者(有时是作者,有时不是)常常介入故事情节,远远超离审美对象之外,以凌驾的眼光和对作品中一切人物事件全然知晓的态度去叙述、描写和诠释人物事件,并表明自己的主观态度和价值判断。这种源于中国古代说话小说的叙事模式,在《孽海花》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迹。
中国古代的说话,是一种听觉的艺术,为了吸引听众,使其保持听下去的兴趣,想方设法和听众发生直接心理交流,因而在说话中常常向听众招呼、设问、提示,而且不时和听众站在一道作为旁听者对作品中的人物来一番评论。在《孽海花》中,招呼、设问、提示就常常出现。如小说的第一回,一首词之后就用了设问:“却说自由神,是哪一位列圣?策封何朝?铸相何地?”讲述一段之后又用提示“列位想想”引起读者的注意。又如在第三回写到“海天四友”时,又设问:“你道这个名称因何而起?”(P14)再如第二十四回,在叙述到雯青死后中国外交出现的风波时,又设问:“你道那风波是怎么起的?”(P219)像这样的例子作品中还有很多。
对于中国小说的这个特点,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著名汉学家普实克也看到了,他认为中国近代的政治小说仍然固守着这种全知全能的叙事观点,惯用的开场白是“话说……”。普实克这一说法颇为中肯,在《孽海花》里,几乎每一回的开头都用“却说”、“话说”一类的词语。而在行文中间,从一个故事到另一个故事(或说是情节)的过渡,都用“如今且说”、“闲话休提”、“且说……”、“且说那日”之类的话语作过渡,据不完全的统计,像这样的过渡在作品出现了三十多处。因为这样,作者可以纵横捭阖地处理大范围的社会生活,便于他把三十年的历史,伦理的、政治的事件和人物扣合在一起,形成具有特殊审美方式的《孽海花》。总的来说,作品是以傅彩云的故事为线索,但作者运用“按下慢表,如今且说……”的形式插叙了许许多多的政治斗争。例如,第十八回,在叙述到彩云与质克的“风波”之后,用“按下慢表,如今且说……”把读者引到上海的味莼园,向读者展示了议论维新、富民强国的充满政治氛围的谈瀛会,表达了维新以强国的主张。而在第二十六回,叙述到何珏斋操练军士,准备迎战日军时,用“且暂不表……再说……”把话题转到傅彩云身上,叙述她的所谓浪漫故事。就这样,两种判断的载体相互交叉出现,但叙述政治斗争的篇幅却占作品的大部分。在叙述的过程中,作者这个隐藏在“幕后”的“我”会忽然站出来,对作品中的人物事件发一番议论。如在第五回,作者借庄仑樵之口对贪官污吏来了一番谴责:“我看如今那些京里的常侍,外省的督抚,有多大能耐呢?不过头儿尖些,手儿长些,心儿黑些,便一个个高车大马,鼎享肉食起来!……天也太不平了!”(P34)在第三十一回,作者对金雯青的死作了这样的议论:“从此红颜轩冕,变成黄土松楸,一棺附身,万事都已。这便是富贵风流的金雯青,一场梦幻的结局”。(P292)对台湾的“义民”和革命派人物则作了赞扬:“龚璱人《尊隐》上说的话真不差,凡在朝之人,恹恹无生气;在野自多任侠敢死之士。不但台湾的义民,即如我们在日本遇到和弢天龙伯在一起的陈千秋也是一个奇怪的人”。(P328—329)我们从这些议论中可以明确地把握作品的主题倾向。
虽然在《孽海花》中有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使我们“无忧无虑”地读下去,但是,它使读者读起来非常吃力,感到很难读下去。这是因为这个全知的叙述者“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可以随意安排情节,任意指派人物行动,并且把作者的审美情感和审美评价强加给读者,从而使读者丧失了自己的审美主体性,本来极富于想象的头脑纯然成了盛装作家审美意识的简单器皿[⑧]!”可见,全知的叙述者在小说中经常是令人厌倦的向导。但是,作者为了鲜明地表达他的政治判断与伦理判断,不得不作了这种选择。
三、形成两种审美判断融合和倾斜的原因
传统审美方式的积淀,是《孽海花》这种审美方式形成的原因之一。传统的审美方式使《孽海花》印下了伦理判断的标记。只要我们翻开中国古代美学文献就会发现,在真善美之间,古代的中国人不是像古代的西方人那样强调真与美的联系,而是把审美理想寄托在美与善的统一,强调文学的社会功利。孔子在评论音乐时,提出了“尽善尽美”的美学观点:“子谓《韶》,尽美矣,不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⑨]。”在这段话里包含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审美观念;一是把美和善作为文学艺术创作和欣赏的两个标准;二是把“尽善尽美”、美善统一当作最高的审美标准。而实质上,孔子强调的是善。这种以善为主的审美观一直影响到后来的文学创作。清代的闲斋老人曾说:“稗官为史之支流,若读稗官者可进于史;故其为书亦善善恶恶,俾读者所观感戒惧,而风俗人心庶以维持不坏[⑩]。”可见,在古人看来,创作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善恶分明的艺术形象实现作品的伦理功能。为了表达这种功能,作家在反映社会生活时往往运用道德的尺度,对作品中的人物进行鲜明的囊贬。于是美和伦理道德联系了起来,出现了善与恶、美与丑、忠与奸的“二元对立”式的人物群像。这种审美方式一直主宰着中国古代的长篇小说,例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都呈现出个体人格伦理化或伦理人格个体化的伦理判断特点。这种把审美价值等同于伦理价值,强调文艺的劝惩教化作用的审美意识是儒家功利主义文艺思想对小说审美要求的必然结果。近代作家曾朴也受到了这种审美传统的影响,他的小说《孽海花》的人物大都以美与丑、善与恶、忠与奸的强烈理智形态呈现出来。只要我们细心地考察《孽海花》的人物群体,就会发现这个人物群体的一个很有趣的特点:它是由圣主与昏君、忠相与奸臣、清官与贪官、忠勇报国的民族英雄与出卖民族利益的内奸、豪侠与恶霸、节妇与淫妇等构成的“二元对立”式的人物群体。在作者笔下,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分别是昏君和圣主的代表,因此,作者抑昏君、救圣主。作品中出现了一大批的贪官污吏,如“纳随买缺”的浙闽总督、“侵占饷项”的贵州巡抚、“骄奢罔上”的直隶总督等等。作者对这些败国有余的人物作了强烈的谴责。与此相反,代表作者审美理想的是那些清官、忠臣和豪侠、民族英雄。如“第一忠臣”韩惟荩、豪侠大刀王二、民族英雄刘永福、徐骧、郑姑姑等等。对于这些人物,作者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与赞颂,他称徐骧、郑姑姑等抗日英雄为“为种族牺牲死抗强权的志士”。(P316)如果要说节妇与淫妇,那么张夫人与傅彩云便各是“领袖”。作者就是这样通过赋予人物以单纯的伦理内容来达到惩恶扬善的教育目的。可见,作者曾朴只不过是从前人的手中接过传统的火把在现实中燃烧罢了。
从《孽海花》看来,它既是充满伦理精神的社会生活的反映,又是审美主体的伦理判断对现实世界的观照。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产生于一定的文化传统的历史小说,必定要受到该文化传统的制约,中国传统文化以伦理原则作为绝对价值尺度的价值观决定了中国历史小说之崇理性和对作品道德教育意义的强调。就中国古代的长篇小说来看,伦理判断的确是左右着艺术形象的创造,各种伦理力量的冲突就成了作品的基本矛盾,因此,作家往往把人物关系和社会矛盾纳入伦理的框架,以伦理的观念加以解释。这种审美方式直接制约着古代小说家的创作。但是,到了近代,特别到了《孽海花》,这种现象不再存在了,因为近代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曾朴也不再是古代的作家,他已经懂得在现实中拿起政治判断这准则,以政治判断的眼光去审视生活中、历史中的一切人物和事件。所以,传统的伦理审美失去了对他的主宰地位而仅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依稀可见的痕迹,从而形成了《孽海花》两种判断相融合的审美格局。
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是这种审美方式形成的又一原因。近代政治斗争的发展状况,使富于忧患意识的曾朴把眼光从传统的伦理武库中转向活生生的政治现实,以政治判断作为审美标准的主导。具体来说,形成这种倾向又有如下两个因素。第一是近代的政治斗争。《孽海花》在第一回最后写道:“三十年旧事,写来都是血痕”。这“三十年”是指清朝同治初年至甲午中日战争结束这一历史时期。只要翻开中国近代史就会发现这“三十年”是何等的令人“惊心动魄”。在国内,太平天国运动尚在抗衡,洋务运动风起云涌,维新思潮不断上升,革命派人物活动也渐趋频繁。在这种复杂的政治境况下,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继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对我国东南西北发动了一系列的规模更大的战争:英国把魔爪伸入西藏;沙俄企图吞并新疆;法国侵犯云南广西、攻入台湾、福建和浙江,燃起了中法战争;日本则借口朝鲜“叛乱”出兵入侵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甲午中日战争由此爆发。然而,战争的结果,无不以清政府的惨败而告终,并且留下一大批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条约。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对于这些“惊人”的现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正视现实的作家都会把它写进作品中去,让人们去反思,使他们从“甜梦”中觉醒。曾朴作为一个热衷政治而又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作家,他不可能不把这些关系到祖国前途命运的事件摄入他的“摄影机”。特别是从曾朴的生活年代来看,他正目睹了这些“惊人”的现象。时代的氛围和作家的责任感使深受中国历史小说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影响的曾朴把中国近代发生的这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写进了他的作品《孽海花》,清楚地画出了晚清社会思潮和政治改革的发展轨迹——从洋务运动到维新运动,最后到革命运动,并且表明作者的政治立场。这是其它谴责小说家所不及的。第二是近代小说理论的影响。小说在中国古代一直被认为是“雕虫小技”而遭到冷眼。到了近代,它却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和高扬,并且被普遍认为是“改革社会的工具”。我们知道,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时代。为此,生活和挣扎在这种黑暗、混乱中的有志之士都纷纷起来探寻救国救民、发奋自强的道路。他们在斗争中对人民的力量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夫欲救亡图存,非仅一二才士所能为也;必使爱国思想普及于最大多数之国民而后可(11)。”然而,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国民还处在“甜梦”之中,“民智未开”。正如梁启超所说:“中国之不振,由于公德缺乏,智慧不开”,因此,当务之急是“开启民智”、“警醒国民”。然而用什么来开通民智呢?资产阶级文学理论家从文学阵营里找到了小说这个载体。在他们看来,西欧的政治民主、国力强盛都是得力于小说之功,认为“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12)。因此提出了“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13)的主张。还说:“吾中国若有政治小说,插以高尚之理想,则与之转移风俗、改良社会亦不难矣”(14)。但是,以何种思想来“开启民智”呢?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认为只有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方能使国民从梦中醒来,从而达到改革社会、救国自强的目的。因此,他们要求作家要大胆而真实地揭露社会的黑暗,传播西方的政治思想,宣扬维新变革的主张。换一句话来说,即是要求作家从政治的角度出发,把文学和政治联系起来,反映当代的政治斗争,为政治服务。曾朴作为一个富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并积极参与维新运动的政治家和文学家,深刻地感受到了小说的政治作用,于是在当时那较为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创作了代表他的政治判断的《孽海花》。
注释:
①括号内所注均为《孽海花》页码。
②康有为:《大同书》。
③ ④ ⑤曾朴:《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
⑥陈则光:《正确估计〈孽海花〉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⑦阿英:《孽海花·叙引》。
⑧陈金泉:《和谐:审美视角与叙事方式的美学思考》。
⑨《伦语·八佾》。
⑩《儒林外史序》。
(11)王无生:《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
(12)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
(13)梁启超:《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14)《小说丛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