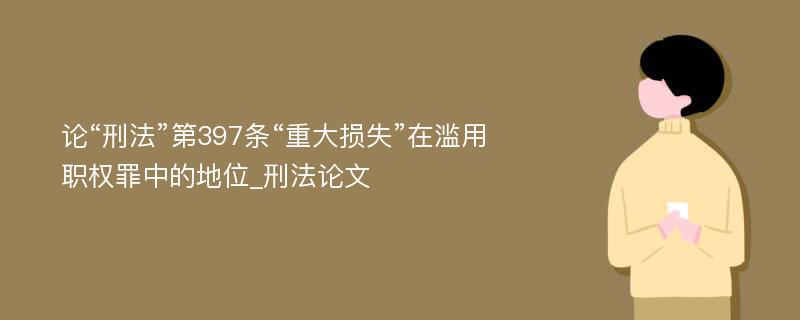
《刑法》第397条中的“重大损失”在滥用职权罪中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刑法论文,损失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512(2006)01-0146-06
由于我国刑法没有明确规定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而是将其与玩忽职守罪并列规定在《刑法》第397条中,配置同一法定刑,这就导致了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见解纷呈。纵观学者们的争论,主要是由于对法条中规定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在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中处于何等地位的理解不当引起的。
一、歧异纷呈的观点
在滥用职权罪的罪过问题上,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判断其罪过的标准是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① 然而何为滥用职权罪的“危害结果”?刑法第397条规定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是否是滥用职权罪的“危害结果”?若不是,那么它在滥用职权罪犯罪构成要件中处于什么地位?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不同,得出的滥用职权罪的罪过结论不同,对其罪过的具体内容的理解亦不同。
有论者将法条规定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作为滥用职权罪的结果,据此认定其罪过,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有的学者认为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其故意的内容就是:行为人明知自己滥用职权的行为会发生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结果,而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② 有的学者则认为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过失,即滥用职权的行为过失地造成了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大损失。③
有的论者则认为国家机关正常管理活动(或者是国家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正当性)是滥用职权罪的结果,其故意内容就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产生破坏国家机关正常管理活动(或国家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正当性)的结果,而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学者认为法条中规定的“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只能是客观处罚条件,即侵害犯罪客体的行为同时造成了“重大损失”时,才具有可罚性。④ 有的学者则认为“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结果,虽然是本罪的构成要件,但宜作为客观的超过要素,不要求行为人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⑤
二、对上述各种观点之质疑
(一)将“重大损失”作为本罪危害结果的质疑
以结果作为罪过鉴定的标准,而不是以滥用职权行为本身作为确定罪过形式的根据,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法条中规定的“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是否就是滥用职权罪的危害结果,或者说是否应以行为人对该“重大损失”的心态作为确定罪过形式的根据,则存在下列问题。
首先,以“重大损失”作为罪过标准,认为滥用职权罪只能是出于故意的观点,要么与实际不符,要么则应考虑认定这种行为为危害公共安全等罪。⑥ 滥用职权罪的主体是掌握国家公共事物管理职权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果其明知自己滥用职权行为会造成重大损失,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那么这种行为就应当构成与其行为方式相适应的危害公共安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或者侵犯财产等方面的相关犯罪,而不能仅仅是一个滥用职权的问题,其滥用职权的行为应当被故意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犯罪行为吸收。⑦ 另外,根据我国从严治吏的立法精神,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犯罪的处罚应重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实施同类犯罪造成同样损失的处罚。因此滥用职权罪最高法定刑相对较低的立法状况则进一步说明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行为并非积极追求或放任“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法条中规定的“重大损失”不是行为人滥用职权故意或放任的危害结果。
其次,认为滥用职权罪出于过失的观点,也不符合事实,并且也不符合刑法将滥用职权罪作为与玩忽职守罪相对的故意犯罪的立法精神。众所周知,滥用职权罪是从玩忽职守罪中分立出来的,只是后来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日趋严重的滥用职权行为惩治于法无据的问题,立法机关才迫不得已在一些附属刑法中将玩忽职守罪作出扩大规定。1997年刑法增设滥用职权罪,显然就是为了与玩忽职守罪相区别。有论者在解释滥用职权罪独立设罪的立法意图时,认为“立法者并不是把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看作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犯罪,而是作为性质相同但表现形态略有区别的犯罪规定的”,其表现形态的略有不同主要表现为“滥用职权是积极作为的渎职,而玩忽职守是消极不作为的渎职”。⑧ 显然,该论者是以作为与不作为的行为表现形式来区分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的。诚然,在实践中,滥用职权罪大多表现为行为人以积极作为的形式擅权妄为、超越职权,玩忽职守罪则表现为消极不作为的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职责,然而不可否认滥用职权亦存在职务上的不作为即行为人故意通过不履行自己职责的不作为方式,来达到与积极滥用职权行为一样的目的。因此,以行为表现形式无法区分两罪,也无法说明滥用职权罪从玩忽职守罪中分离出来、独立成罪的理由。况且在我国刑法中,只是因为行为表现形态为作为或不作为,就要将其区分为不同个罪亦缺乏法律和理论依据。如我国刑法中大量存在的诸如故意杀人罪、非法拘禁罪等不纯正不作为犯都存在着作为和不作为两种行为表现形式,但由于同样侵害刑法保护的法益,具有同样的否定价值,主观恶性亦相同,因而无须将其区分为两罪。由此以行为表现形式的不同来区分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并不妥当。实际上,在我国刑法中行为表现相同,主观罪过不同才往往是界定不同个罪的标准,如放火罪和失火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和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故意杀人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等等。因此,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最主要区别也应该是两罪在主观特征方面的差异,而不是行为表现形式的差异。同时也正因为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区别于玩忽职守罪的过失,使其得以从玩忽职守罪中分离出来,独立成罪。
至于有论者提出将滥用职权罪认定为故意犯罪会导致与过失犯罪的玩忽职守罪在罪刑关系上的失调问题,笔者认为这完全是立法的技术问题,甚至可以说是立法的疏漏,但决不能据此否认两罪在主观方面存在的区别。正如有学者指出,分析法定刑虽然对认识该罪的主观罪过具有某种帮助作用,但并不具有必然性,更无法从法定刑的规定上得出该罪的主观罪过是故意还是过失。⑨ 况且我国刑法在法定刑的规定上各罪间的罪刑不平衡问题大量存在,同危害异罚,异危害同罚的情况并非个别。例如,侮辱罪与侮辱妇女罪、绑架罪与(杀人)抢劫罪、玩忽职守罪与环境监管失职罪等等,均属于在危害程度上相同或相似,但法定刑(包括最高刑和最低刑)都有相当大的差异,造成法定刑失衡。我们不能因为刑法对滥用职权罪的法定刑设置相对较低的立法问题而推定其罪过形式只能是过失,这种立论明显是站不住脚的。
综上,将“重大损失”作为滥用职权罪构成要件中的危害结果,认为行为人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结果持故意或者是过失的态度,均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重大损失”不能作为认定滥用职权罪罪过的标准,不是认定其罪过的危害结果。将“重大损失”理解为危害结果势必导致滥用职权罪罪条虚置,要么导致被更为严重的犯罪所吸收,要么则与玩忽职守罪无区别。
(二)将“重大损失”作为本罪“客观处罚条件”的疑问
“客观处罚条件”(objecktive bedingungender strafbarkeit)是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中的概念,又称客观的可罚条件。关于客观处罚条件在犯罪论体系上的地位,大陆法系刑法学者有不同的观点。⑩ 第一种观点,即刑罚处罚阻却事由说。该说认为,客观处罚条件不是犯罪的成立要件,只具有阻却刑罚处罚的性质。它是立法者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而设立的发动刑罚权的条件,与行为及行为人的规范性评价无关,和犯罪的成立没有关系。不具备客观处罚条件,行为仍然成立犯罪,可以对其进行正当防卫,只是不能适用刑罚而已。德国刑法学者耶塞克、魏根特指出:“应受处罚性的客观条件,是指这样一些情况,它们与行为直接相关,但既不属于不法构成要件也不属于责任构成要件。”(11) 意大利刑法学者杜里奥·帕多瓦尼则更明确地认为,客观处罚条件是犯罪的可罚性问题,而可罚性是指实施犯罪后应该受到处罚的状态或者说是联系犯罪及犯罪的法律后果的桥梁。(12) 有学者甚至认为,客观处罚条件是刑罚论所研究的问题,而不是犯罪论的课题。(13) 第二种观点,即犯罪成立要件还原说。该说认为,客观处罚条件不是与犯罪的成立与否无关的处罚条件,而是决定行为的犯罪性的条件,应该在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责任的内部论述可罚性。如日本的内藤谦指出,不能认为客观处罚条件与犯罪的成立无关,所谓的客观处罚条件实际上是使违法性程度增高的要素,因而是构成要件的要素。曾根威彦则认为,客观处罚条件并非与行为无关,相反是行为的一种结果,客观处罚条件是因果进程中的中间结果,犯罪结果则是因果进程中的最终结果,因为“危险”是一种结果,而客观处罚条件都是使行为的危险性增大的要素,因而其本身也是一种结果,应当还原为构成要件要素。(14) 第三种观点,即犯罪成立独立要件说。该说认为,客观处罚条件在犯罪论中具有独立的体系地位,是继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有责性之后的第四个犯罪成立要件。
总之,上述关于“客观处罚条件”的体系地位的三种学说,尽管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但都是以其现有的犯罪论体系为基础来论证犯罪与刑罚的关系以及客观处罚条件的实质作用。那么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中的“客观的处罚条件”在我国刑法理论中有无存在的可能性呢?我们能否将其照搬进我国刑法,即在犯罪成立之外承认客观处罚条件,或是将客观处罚条件看作为我国传统犯罪构成要件的第5个要件呢?具体到滥用职权罪,我们能否将法条中规定的“重大损失”视为滥用职权罪的客观处罚条件呢?
众所周知,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中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是“递进排除”的立体式的结构体系,各要件可以发挥独立的评价功能。而我国刑法理论中的犯罪构成是由犯罪主体要件、犯罪主观要件、犯罪客观要件和犯罪客体要件四个方面组成,从结构模式上是“齐合填充”平面式的,各要件之间是“一存俱存、一无俱无”,缺少任何一个方面的要件,犯罪便无存在的余地。因而在犯罪成立之外承认客观处罚条件,无疑会破坏我国现行的犯罪论体系。在我国,犯罪构成是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一切主客观要件的总和,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就成立犯罪。应受刑罚处罚性是犯罪的基本特征之一,行为的犯罪性和可罚性是不可分割的。一种行为构成了犯罪,它必定是可罚的;一种行为是不可罚的,它就不构成犯罪。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特征决定,在犯罪构成要件之外,不可能再寻找到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或根据,行为符合犯罪构成是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惟一根据。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不负刑事责任。这里的“不负刑事责任”并不是说构成犯罪后不负刑事责任,也不能说“辨认和控制自己的行为”是犯罪成立之外的客观处罚条件,不具备这一条件就阻却刑罚。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根本就不构成犯罪,因而不负刑事责任。在我国现行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如果承认犯罪成立之外的所谓的“客观处罚条件”,那么将无法解释为什么把不值得刑罚制裁的行为在法律上认定为犯罪,或者说我们有什么必要把根本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仍视为“犯罪”呢?这样做的结果只会给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带来混乱。至于将客观处罚条件作为独立的犯罪成立要件,在我国亦不可取。如前所述,我国犯罪构成体系对行为成立犯罪是进行整体综合评价的,要件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相互说明的,因而没有必要单独设立一个处罚条件来对其他要件进行评述。因此,在我国现行的犯罪构成体系中,无论是将客观处罚条件作为犯罪成立要件之外的事由或是独立的犯罪成立要件的观点,都是不可取的,客观处罚条件在我国现行犯罪构成体系中没有存在的余地。由此,刑法第397条规定的“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也不能认定为滥用职权罪的客观处罚条件。
(三)将“重大损失”作为滥用职权罪的“客观的超过要素”的疑问
“客观的超过要素”概念是张明楷教授针对现行刑法中有些具体犯罪的罪过形式难以准确界定而提出的解决罪过认定问题的方案。根据张教授的观点,“客观的超过要素”是指在犯罪客观要件中,不需要行为人具有认识与希望或放任的态度,但行为人至少对之具有预见可能性的客观要素。它仍然是犯罪构成的要素,而不是犯罪构成要件以外的内容,不是所谓的客观处罚条件。滥用职权罪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结果,虽然是本罪的构成要件,但宜作为客观的超过要素,不要求行为人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15)
客观地说,张明楷教授提出的客观的超过要素对解决某些具体个罪的罪过提供了一定的思路,推动了我国罪过形式理论的发展,促进了法学理论的繁荣,但其观点仍然存在着矛盾,与我国现行的刑法理论存在着不兼容的地方。首先,他主张客观的超过要素不是故意的认识与意志内容,但同时又认为行为人至少对之具有预见可能性,那么也就是说行为人应当有一定的认识,既然行为人有认识,就必然存在意志选择的问题,即行为人要么希望或放任其发生,要么排斥、拒绝、否定其发生,那么又应当如何来说明行为人的这一意志选择呢?难道熟视无睹、忽略不计?显然,用“客观的超过要素”概念无法说明这一问题。
其次,张教授尽管认为滥用职权罪、丢失枪支不报罪等罪的罪过是故意,但同时他又在在书中说到“本书所列举的一些犯罪,似乎都可以直接认定为过失犯罪,而不必认定为故意犯罪。”他之所以将它们认定为故意犯罪,是因为将它们“认定为过失犯罪,总有难以被人接受的感觉。”张教授对这种“难以被人接受的感觉”没有作出具体的解释,故不敢妄自揣测,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说用一句有“难以被人接受的感觉”就要将某种犯罪的罪过形式认定为故意,那么持过失观点的论者也完全可以同样的理由认为,将该罪认定为故意也给他产生了“难以被人接受的感觉”,所以其罪过是过失而不应是故意。显然以“感觉”来判断某种罪的罪过形式是不妥的,因为感觉本是因人而异。
总之,张教授提出的客观超过要素概念存在一定的矛盾,而且其本人对某些个罪的罪过亦不确定,因而不能将“重大损失”视为是滥用职权罪的“客观的超过要素”,并以此来认定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
三、“重大损失”应当是滥用职权罪的定罪情节
笔者认为刑法第397条规定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应当是滥用职权罪的定罪情节。定罪情节是指直接说明犯罪构成事实的情状和深度,从而影响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程度并进而决定危害行为能否构成犯罪的各种具体事实情况。犯罪的本质特征是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任何违法、违规行为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其社会危害性未必达到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为了将犯罪行为与违法、违规行为区别开来,刑法就特别强调某个或某些具体内容,即通过规定定罪情节的方式以提高其社会危害性达到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由于定罪情节涉及到行为的手段、对象以及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结果等多方面,因而其在法条中的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如规定“情节严重(恶劣)”、“情节特别严重(恶劣)”“数额(量)较大”、“数额(量)巨大”、“遭受或造成重大损失”等等。刑法在具体犯罪的基本罪状中通过规定这些定罪情节提高了行为的整体违法性程度,界分了罪与非罪,限制犯罪的成立范围,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发动范围,体现了刑罚的谦抑性原则。诸如此类的“情节严重”、“数额较大”、“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都不过是在总体上评价整个行为过程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它可能涉及到说明我国犯罪构成的每一个要件危害程度问题,因而没有必要应将其归于犯罪构成的那一个具体要件。正如有学者指出,就刑法规定的众多情节来看,有的属于客观方面,有的属于主观方面,还有的属于客体或者对象,有的属于主体。既然犯罪构成的四个方面都有情节,就不能把情节作为一个独立的要件。(16)
就滥用职权行为而言,如该行为虽然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秩序,但如果并没有导致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那么该滥用职权行为就不应按犯罪论处。(17)“构成滥用职权罪必须造成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如果没有该后果,即令行为人系滥用职权主体,其滥用职权行为出于故意,也不能认定其构成滥用职权罪。”(18) 由此可见,法条中对滥用职权行为的描述,尚不能说明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达到了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尚无法将滥用职权犯罪行为与一般的滥用职权行为区别开来,必须以造成了实际的“重大损失”进行限制,提高行为的违法性程度,才能区分罪与非罪。
如上所述,定罪情节是直接说明犯罪构成事实状况和深度的具体事实情况,那么是否要求行为人必须认识这些客观事实情况并作出意志选择呢?笔者认为不必要。比如刑法第246条规定的侮辱罪必须是情节严重才构成,而“情节严重”通常是指“致使被害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对于此种说明行为社会危害性严重程度的具体事实情况就并不要求行为人有认识,更不要求行为人有意志选择。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的侮辱行为可能导致被害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并且予以积极追求的,那么就构成了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而不是侮辱罪。再比如盗窃罪,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构成盗窃罪。其中的“数额较大”是危害结果的程度要求,“多次盗窃”是情节情状的要求。如果行为人以概括的故意秘密窃取他人财物,实际窃得财物数额较大构成盗窃罪;如果实际窃得财物没有达到数额较大的程度,则不构成盗窃罪。在此并不要求行为人认识到具体的盗窃对象是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只要行为人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并且在客观上实施了具体的窃取行为,实际窃取他人的财物达到数额较大,就构成盗窃罪。相反,以概括的故意实施盗窃,如果行为人实际窃取的财物较小,则一般只作为小偷小摸行为,不构成犯罪。同样,“多次盗窃”的,也并不要求行为人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在同一年内第三次盗窃,否则势必出现记忆好的以罪论处,而记忆不好的不以罪处,这种以行为人记忆的好坏来决定罪与非罪显然是不妥的。由此可见,法条中规定的“数额较大”、“多次盗窃”都只不过是从总体上说明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的定罪情节,它不过是发动刑罚权的一个限制条件。由此,刑法第397条规定的“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也是判断滥用职权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具体事实,是区分行政违法与犯罪的程度界限,不能作为认定滥用职权罪的罪过的“结果”。它和盗窃罪等“数额犯”中的“数额较大”等一样实际上都不过是将“情节严重(恶劣)”的部分内容在立法上进一步明确而已。对于这些定罪情节也不要求行为人有具体的认识和预见,因为它们不过是从整体上说明犯罪构成事实状况和深度的具体事实而已。不要求行为人对这些事实状况的认识、预见以及意志选择亦并不违反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因为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要求行为人认识和预见的是客观危害结果事实的有无问题,而不是要求行为人认识和预见说明危害程度的具体事实。
综上,笔者认为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具体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明知自己滥用职权的行为会有损职务行为的正当性要求,破坏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秩序,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法条中所列的“重大损失”不是判断滥用职权罪罪过形式的危害结果,直接以“重大损失”作为判断标准势必造成滥用职权罪罪过判断结论的两难境地。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大损失并非行为人的积极追求或放任的危害结果,它不过是说明了行为人滥用职权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达到了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要素。
注释:
①只有极其少数的学者认为滥用职权罪主观上具有的犯罪故意是指“明知是逾越其职权的行为而为之或者明知是依照职务应当履行的义务而不为之。”(陈兴良:《刑法疏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50页)此种观点把故意的内容理解为对危害行为本身的故意,即故意理论中的“行为说”。对于此种违背刑法基本理论的观点我国学者已做过批判,本文在此不赘述。
②赵秉志主编:《刑法修改研究综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07页。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49页。
③李洁:《论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法学家》1998年第4期。张智辉:《论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评论》第1卷(2002年),法律出版社,第142页。
④李洁:《论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法学家》1998年第4期。
⑤(14)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5页、第212页。
⑥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年通过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刑法中规定的滥用职权罪的“重大损失”是指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1、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以上,或者轻伤5人以上的;2、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万元以上的;3、造成有关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产、严重亏损、破产的;4、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5.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6、徇私舞弊,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
⑦⑧张智辉:《论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评论》第1卷(2002年),法律出版社,第145页、第146页—147页。
⑨李希慧、逢锦温:《滥用职权罪主观罪过评析》,《法学家》2001年第2期。
⑩赵秉志主编:《外国刑法原理(大陆法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177页。
(11)[德]汉斯·海因里希、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667页。
(12)[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陈忠林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页。
(13)[日]大冢仁:《刑法概说(总论)》第3版,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96页。
(15)张明楷:《“客观的超过要素”概念之提倡》,《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4-222页。
(16)高铭暄主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9页。
(17)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49页。
(18)周振想主编:《中国新刑法释论与罪案》,中国方正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3页。
标签:刑法论文; 玩忽职守罪论文; 滥用职权罪论文; 过失致人死亡罪论文; 法律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法制论文; 重大过失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法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