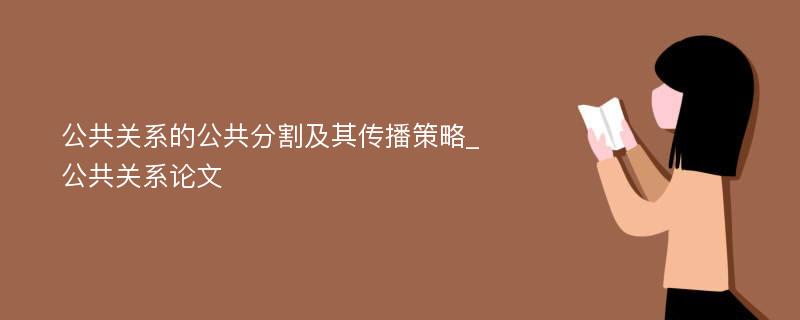
公共关系的公众细分及其传播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共关系论文,公众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虽然学界对于公共关系的定义还没有一致的认识,但是社会组织、传播沟通与公众却是公认的公共关系的三大要素。社会组织是公共关系的主体,其通过各种传播沟通行为来与公共关系的客体——公众建立某种关系,以期达成组织想要实现的目标。
美国学者格鲁尼格认为,公共关系的战略管理就必然包括确认组织的公众,并且对公众进行细分。[1](P.285—P.325)
同时按照传播学的理论,要使得传播效度最大化,就必须对于传播对象——公众进行细分,针对不同的公众采取不同的传播策略。按照什么样的标准进行细分决定了细分是否成功,进而决定了社会组织开展公关传播的战略决策。
一、公共关系中的公众细分
按照现有的公共关系理论,我们主要依照以下三种标准对公共关系的公众进行细分:
(1)根据公众与组织的归属关系分类:内部公众(包括员工、股东、员工家属)与外部公众;
(2)根据公众本身的性质和特点分类:员工、股东、员工家属、顾客、 服务对象、政府、新闻媒介等;
(3)根据公众的发展过程分类:现在公众、将来公众、潜在公众、独立公众。
分类的标准是否可靠有效,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检验:[2](1)分类是否涵盖了该类别的内容。从这个标准来看,第二种分类方法就是不恰当的,因为我们可以无限地列举出不同的公众。(2)不同类别之间是否相互排斥。从这个标准来看,第一种分类方法同样也存在问题,内部与外部如何确定分界点,员工家属的内涵和外延都太大,涵盖了外部公众。(3)直观,不用揣测、解释。第三个分类标准中的将来公众和潜在公众应该如何区别,需要我们进行很大的推敲。因此如果按照以上的标准来对公众进行细分,无疑会使得我们的传播资源被浪费甚至是毫无效果。
要对公众进行细分,首先必须清楚地界定什么是公众。严格意义上来说,公众(publics)仅仅是用来描述那些积极地参与公共议题讨论的人群。杜威(John Dewey)就把公众定义为这样一群人,他们面对同样的问题,都认识到问题的存在,并且组织起来对问题采取某种行为,布鲁默(Blumer)也提出了相类似的定义,他认为公众是指这样一群人,他们面临一个议题,在如何应对这个议题上存在分歧,于是他们参与有关这个议题的讨论。[3](P.45—50)
在当代的公共关系实践中,我们忽略了公众的严格定义,转而用其来指代许多其他的、相关的概念,比如在传播活动中,公众用来指潜在的或现实的信息受众(audiences);在市场营销中,公众用来指经过市场细分后的具有独特的人口统计学、心理学或地理意义上的消费者,他们能对市场信息采取一致或类似的行为;在很多情况下,公众也同时用来指代社群(communities),是指有共同的经验、价值观的群体。
既然公共关系的公众在不同的层面上有不同的指涉,那么我们可以把公共关系的公众界定为:社会组织围绕某个议题所举行的公共关系活动所指向的群体都是属于组织的公众,同时这些公众群体在积极性上有所差异。这个界定虽然比较直接,但是它把公众的界定问题从话语分析的框架中摆脱出来,而话语框架就要求公众的存在必须以个体之间的互动为条件。[4](P.157—183) 因此公众就可以被界定为组织希冀与其建立和维持关系的群体,或者公众也可以被界定为具有不同程度的积极性的、与组织相关的群体。
格鲁尼格从杜威的公众定义出发,提出了公众的情境理论(situational theory of publics)。这个理论的基础是,公众对于组织采取的态度和行为主要是根据公众如何认识其所处的一种情境,而这种情境是由于组织的某些行为或某些问题给公众所带来的影响而形成的,比如污染、产品或服务质量、劳工关系等等。而公众对于情境的认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公众对于情境中存在的问题的认识、公众对于情境对其行为的约束的认识以及公众对其与组织的关联程度的认识。格鲁尼格从这三个方面认识的深浅程度的不同出发,把公众分为积极公众(active publics),知晓公众(aware publics),潜在公众(latent publics)和非公众(nonpublics)。[5](P.145)
格鲁尼格的公众细分模式存在着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格鲁尼格的公众细分是为了预测公众对于某个议题会具有的态度或行为的程度,即组织在采取传播行为之后公众的状态;但是组织在开展传播沟通活动之前必须确认公众是处于什么样的积极程度,以便采取相应的传播策略,而格氏的这个细分却不能做到这一点。第二,格鲁尼格对于“非公众”的界定脱离了杜威对于公众的严格的定义,因为它不是由议题所组织起来的,因此“非公众”不是社会组织的公众,组织的行为对于其没有影响,“非公众”的行为对于组织同样也没有效力。
如何解决格鲁尼格的公众细分中存在的这两个问题?根据社会心理学和消费行为学的研究发现,个体或群体的积极性可以由两个维度来决定:对于某个议题的知识(knowledge)和涉入程度(involvement)。知识是指基于日常生活经历或正规教育而形成的关于特定事物、人物、情境或组织的信仰和态度。涉入程度是指个人与特定事物、人物、情境或组织的相关程度以及这种相关所带来的影响。[6](P.211—P.233) 美国学者Kirk Hallahan据此提出了一个新的公众细分模式。[7](P.499—P.515) 他以公众的涉入程度的高低和对于某个议题的知识多少作为两个维度,将组织的公众划分为四类:消极公众、醒悟公众、知晓公众和积极公众。
消极公众(inactive publics)是指那些对于组织的了解不多,与组织的运作没有什么关系的群体。这里所说的知识和涉入程度不仅仅是指组织本身,还包括组织的产品、服务或代表等。消极公众对于现在其与组织之间的这种关系状态感到满意,因为这种状态符合他的需要,他认为没有必要去改变这种状态。但是并不是说这种状态是无法改变的。醒悟公众(aroused publics)与消极公众一样对于组织的了解不多,但是他们认识到了潜在的议题,因此他们与组织之间的涉入程度就提升了。这种提升可以由以下的因素所引发:个人经历;对于与他们有关的某些群体或个人的情况的媒介报道或广告;与朋友的交谈等等。由消极公众向盲目公众,进而向积极公众的转变,主要是受到公众所处的情境的影响。知晓公众(aware publics)是指那些对于组织比较了解,但是他们不会受到组织行为的直接影响的群体。知晓公众对于公共事务非常了解,在社会中的不同领域充当舆论领袖的角色,但是他们对于组织来说并不是利害攸关的。积极公众(active publics)既对组织非常了解,又与组织有着密切的关联,他们严密关注组织的行为,随时准备组织起来采取行动。他们十分符合杜威对于公众所做出的定义。
同时,Hallahan还将与组织没有关系、对组织又不了解的公众划归为非公众。他们不应该属于社会组织的公众范畴,这也就解决了格鲁尼格对于公众细分中的第二个问题。但是一旦他们对组织有了了解,他们就马上进入到消极公众的范畴。
Kirk Hallahan的这个公众细分模式把消极公众和醒悟公众区分开来,而格鲁尼格则把这两者合并为潜在公众。消极公众和醒悟公众都有可能成为积极公众,但是醒悟公众的这种可能性更大,因为他与组织的关联程度已经得到提升,因此KirkHallahan的模式就意味着涉入程度的提升是获取知识进而步入积极公众的前提条件。并且,Kirk Hallahan 的模式是以公众对于组织既有的知识和现存的涉入程度作为细分维度,这就可以为社会组织预测公众对于组织传播行为的反应提供一个指针。根据Kirk Hallahan的细分模式,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界定公众在组织开展公关传播活动之前的不同状态,这就便于社会组织采取不同的传播策略,也就解决了格鲁尼格细分模式中的第一个问题。
Kirk Hallahan的公众细分模式依然没有完全达到前文中提到的分类标准,但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不管什么分类系统,总要优于混沌,即便是感知属性层面上的一种分类系统,也算是向理性有序化迈进了一步”,[8](P.202) Kirk Hallahan的公众细分模式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在量上确定公众对于组织的了解以及公众与组织涉入关系的程度。我们可以采用统计学中的李卡特量表(Likert Scales)的形式,把公众对于组织的了解与公众与组织的涉入程度分为若干个等级,按照等级程度的不同再对上述四类公众进行细分。
二、公共关系中的传播策略
在确定了公共关系公众的细分标准之后,我们就来分析针对不同公众的传播策略问题。格鲁尼格在其“卓越公共关系”的研究项目中,提出了四种类型的传播模式。
(1)新闻代理人/宣传模式(press agent/publicity):其目的是为了宣传,本质是单向传播,传播的内容是非关键的事实,实践中的代表人物是P.T.巴纳姆,Grunig的研究认为在实践中采用该种模式的组织的比例为15%。
(2)公共信息模式(public information):其目的是为了传播信息,本质是单向传播,传播的内容是重要的事实,实践中的代表人物是艾维·李,Grunig的研究认为在实践中采用该种模式的组织的比例为50%。
(3)双向、非对称模式(mutual asymmetrical):其目的是为了科学的说服,本质是双向传播,最终的目的是不平衡的效果,实践中的代表人物是爱德华·伯纳斯,Grunig的研究认为在实践中采用该种模式的组织的比例为20%。
(4)双向、对称模式(mutual symmetrical):其目的是为了相互理解,本质是双向传播,最终的目的是平衡的效果,实践中的代表人物是伯纳斯、教育者、公关行业的领军人物,Grunig的研究认为在实践中采用该种模式的组织的比例为15%。
格氏的模式虽然可以看作是描述公共关系实践的发展史,但是格氏确是用这个模式来描述传播的本质和目的,并且这个模式表明在相互理解的对称地位取得之前,不同的实践行为必须已经存在。格鲁尼格认为,双向的、对称的沟通模式是公共关系传播策略中的最佳方案。对称模式的一个前提是传播导致理解,另一个关键前提是公众和组织必须关注他们的行为给他人带来的结果,并努力去消除不好的结果。
与此同时,在现今的公共关系实践中,我们把绝大部分的传播资源都投注在积极公众身上,因为积极公众能够对组织产生直接的影响,而对那些对于组织的影响能力、影响机会都较少的消极公众则不太关注。支撑这一实践的理论假设是公众与组织的利益总是处于矛盾之中,公众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十分积极地去思考与组织有关的问题,与他人就此问题进行沟通,并且会采取统一的行动。
可见,无论是学界和业界都把公共关系的公众的积极性建构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但是,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们却证明了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消极本质。李普曼在20世纪20年代就指出,人们是以他们“头脑中的图像”作为行动的依据。[9]后来,他又指出,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成为了“虚幻公众”(phantom public),他们对于公共事务十分公正,并且愿意把对于公共议题的决策权力委托给专家。[10]同时,消极并不等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缺乏能力或者缺乏关注。在过去三、四十年的研究证明,受众并不是消极地,而是积极地处理信息。人们从媒介传播的信息中构建自己的意义,并把信息置于他们自身的生活之中。[11](P.67—P.86) 现代社会公众的消极本质可以解释为现代社会庞大、复杂、互依本质的一种功能。认知心理学家把现代社会的公众称为“认知的守财奴”,他们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会去处理过量的信息。人们在同一时间只会应对数量有限的问题或局势。
个人只会有选择地与少数的个人或组织建立深层次的关系,但是出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他们会与较广范围的组织建立较为浅显的关系。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公众在建立某种关系时会考虑建立这种关系的成本与收益,他们期望收益能大于成本,而当成本超过收益时,他们会从这种关系中退却出来。从这种经济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轻易改变他与社会组织或个人的现有关系的状态,除非公众所面临的问题十分重要或公众受到了外部因素的刺激。公众保持现有关系的这种惰性导致了冷漠,因此现代社会公众的消极本质可以从某种程度上理解为惯例行为。
可见,对于公众来说并不是所有的关系都是重要的,公众也不会轻易改变关系的状态。那么公共关系实践中是否对于所有的公众都必须采取双向的、对称的沟通模式呢?是否对于所有的公众都应该采取象积极公众那样的传播策略呢?这种双向的、对称的沟通模式是否对积极公众、消极公众、醒悟公众、知晓公众都有同样的效果呢?既然消极公众和醒悟公众对于组织的知识程度非常低,也就是说他们对于组织的了解不深,那么组织要与其就组织的某个议题进行互动式的传播与沟通,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同时,对于消极公众和知晓公众来说,由于他们与组织的涉入程度也比较低,无论是作为盈利的还是非盈利的组织都没有必要把太多的资源投注在消极公众和知晓公众的身上。
我们可以从Kirk Hallahan 公众细分模式的两个维度出发,来考虑针对Kirk Hallahan公众细分模式中的四类公众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传播策略。
首先,对于积极公众来说,由于他们对于组织的了解和涉入程度都比较高,因此与他们开展双向的、对称的传播沟通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组织和公众之间存在对话的平台。
对于知晓公众来说,他们对于组织的了解比较透彻,但是他们与组织的涉入程度不深,组织可以采取“公共信息模式”,向他们传播有关组织的信息,组织不必要希望在传播过程中从他们那里获取某种反馈,因为他们对于组织不会产生某种现实中的影响。而这种单向的信息传递反倒有助于知晓公众进一步加深对于组织的了解,在未来的某个议题上他们可能会与组织发生某种关联,知晓公众就转变为积极公众,而且由于以前的公共信息传播,使得刚刚从知晓公众转变过来的积极公众与组织之间不会因为信息的匮乏而没有对话的基础。
对于醒悟公众来说,由于他们对组织的了解不够,但是他们却与组织有着较高的涉入程度,因此社会组织可以采取“双向的、非对称的”沟通模式。非对称的沟通是因为他们对组织的了解不深,他们和组织之间还缺乏对话沟通的平台,或者平台的基础还不扎实。双向的沟通是因为他们与组织的涉入程度较高,组织必须从他们那里获取反馈,以更好地与之沟通或者改进组织的行为。
对于消极公众来说,他们对于组织的了解不多,与组织的涉入程度也不深,组织对他们可以采用“新闻代理人/宣传模式”,向他们传递有关组织的信息,为其将来向积极公众的转变打下基础。
在Kirk Hallahan公众细分模式中,还存在着一类不属于社会组织公众的“非公众”,对于他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传播策略呢?从非公众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于组织既不了解,又毫无关联。组织可以忽略“非公众”,不把他们列入传播的对象;组织同样也可以创造出某种议题,吸引“非公众”来了解社会组织,并且与社会组织发生联系,这就转入到了消极公众的传播策略范畴了。因此,社会组织不必把追求双向的、对称的沟通策略作为其公共关系实践追求的最高目标,而是应该对组织的传播策略实施动态管理,针对不同的受众采取不同的传播策略,这样既可以提高公共关系传播的有效性,又可以为组织节约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