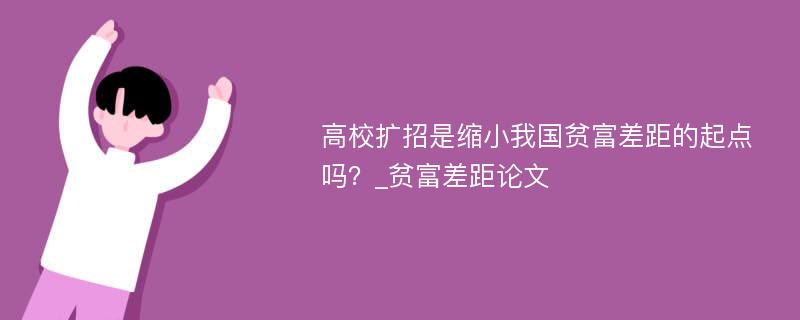
高校扩招是中国缩小贫富差距的起点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贫富差距论文,起点论文,高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8;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870(2002)01-0021-04
根据西方教育扩展与收入不平等变动之间的倒U理论,教育扩展一般会先大尔后逐渐缩小收入的不平等。因此,中国目前的高校扩招现象被有些人认为是中国缩小贫富差距的起点。由于该理论源于西方社会的数据,它与中国社会的现实拟合度有多高?高校扩招是不是中国缩小贫富差距的起点?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些分析。
一、教育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倒U理论
西方教育社会学的研究者们在考察了教育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之后,认为教育的扩展既非一味地扩大收入不平等,也非一味地缩小收入不平等,而是会先扩大尔后缩小收入不平等,即教育扩展与收入不平等变动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关系。我国学者也通过跨国横向分析和对英国的纵向分析,对这一结论进行了实证比较,并得出结论为真。[1]
(一)教育扩展的结构效应与收入不平等的扩大
所谓教育扩展的结构效应是指随着教育的扩展,它会拉大受过教育者与未受过教育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因为受过教育的人有更高的生产能力和更强的配置能力,他能占据收入较高的职业和岗位,从而获得较高的收入。
一般来说,现代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是伴随着现代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的,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经济的发展提出了对教育扩展的需求。我们知道,现代产业的技术和资本越来越密集化,对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级化,这直接导致对简单劳动力即没受过教育或受过教育很少的劳动力的挤压和替代,以及对受过教育的人的需求的直接扩张。与此同时,教育对个人来说是要付出成本的,个人教育成本的筹措,一般有父母和亲戚的赠予或免费贷款,有社会和政府的赞助,但毕竟这些资金来源带有某种配给性,而且,它们也往往难于满足上学的所有开支。由于教育投资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存在诸多风险,因此,教育资本市场必然不完全,这就必然导致教育投入的不足和教育资源的分配更不平等,因为受教育者对教育的投资主要依赖于父母的财富和偏好。
因此,在教育扩展的初期阶段,教育的供给滞后于教育的需求,使受过较多教育的人获得两种益处:一是他们占据着报酬优厚的职位,这既得益于他们有代表着较高生产能力的起始文凭(教育的信号作用),雇主愿优先雇佣他们,又得益于他们有较强的配置能力,即他们能以较低的成本发现并抓住较好的就业机会;二是他们处于卖方市场的地位,能享受某种类似于“寻租理论”中租金的益处。
(二)教育扩展的抑制效应与收入不平等的缩小
所谓教育的抑制效应是指随着教育的扩展,它会缩小受过教育者与未受过教育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这一效应的发挥一是由于教育的迅速发展,二是由于教育分配越来越平等。教育扩展的抑制效应主要是通过两条途径实现:第一条途径是竞争效应。不同教育层次劳动者的相对工资收入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状况决定的。某一教育层级劳动者的市场竞争越激烈,他们的相对工资收入和该层级教育的酬金就越是下降,他们与较低教育层级劳动者的收入差距就越是缩小,从而社会的收入分配就会变得更加平等。
教育扩展抑制收入不平等的另一条途径就是渗漏效应,即有部分受过教育的人被渗漏下来干那些无需接受教育就能胜任的工作。因为,一是由于非竞争集团的存在抑制了劳动力市场的充分竞争[2];二是好的职业毕竟有限,它们根本无法完全接受越来越多的受过教育的人,那些没有被吸纳的受过教育的人只能被渗漏下来。
总之,教育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倒U型变动,是教育扩展之结构效应与抑制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结构效应源于教育的供给小于教育的需求,从而源于受教育者与未受过教育者或受过较多教育者与受过较少教育者之间工资差距的扩大。抑制效应则源于教育供给大增之后所导致的竞争效应和渗漏效应。结构效应和抑制效应都贯穿于教育扩展的始终,但在前期前者大于后者,在后期则后者大于前者,故在整个教育扩展过程中,收入不平等会先扩大尔后缩小。
二、中国教育扩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特殊性
与国际社会相比,我国的教育扩展与收入分配之间有其特殊性:
(一)教育收益率不高,教育扩展的后劲不足
根据上面的理论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的结论:在教育扩展的前期,教育的收益率应该是不断增长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到教育事业中来,教育才能不断扩展从而进入后一阶段。同时,在这一阶段内,受过教育的人才在社会中应该是供不应求的;而在教育扩展的后一阶段,由于教育人才尤其是高级人才的过剩,人才之间互相竞争,从而减缓了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教育的收益率也随之下降。下面,我们据此来分析中国的教育与收入差距问题。首先看1995年与1988年教育收益率的比较结果。
中国1995年与1988年教育收益率的比较[3]
年份
平均教育
女性教育
男性教育
收益率收益率收益率
19955.73%5.99% 2.5%
19883.8% 3.7% 5.14%
从上表的数据可知,我国的教育收益率很低,只相当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相应教育收益率的1/3~1/2,而且该收益率正在不断上涨,从前面对教育扩展不同阶段特点的分析来判断,中国应该处于教育扩展的前一阶段。而当前大学生就业难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受教育人口之间相互的竞争已经相当严重,以致出现了所谓的“人才高消费”与“文凭贬值”现象。因此,从这里似乎又可以判断中国正处在教育扩展的后一阶段。
我们在此无意于争论中国目前到底处在教育扩展的哪一阶段,但只要细作分析就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受教育人口之间的相互竞争已经相当激烈,受教育人口已经“相对过剩”(注:这里之所以讲相对过剩,是因为中国的就业市场很不完善,就业竞争中存在许多不规范的地方,从而出现一定程度的受教育较少者排挤受教育较多者甚至未受过教育者排挤受过教育者的现象,根据笔者的研究,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在低学历层次上,社会资本在就业过程中超过人力资本而起决定作用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出现了西方教育扩展后期所出现的抑制效应,跟随这一抑制效应的是教育收益率的下降,其可能的后果有两方面:一方面由于教育收益率是在本来就不高的水平上的下降,这种低水平的教育收益率的下降不可能对缓和收入差距产生多大的影响。因为教育收益在个人的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即使完全取消教育的附加收益也不会使个人的收入有多大的变化,无助于缓解收入的巨大差距;另一方面是使教育的继续扩展缺乏后劲。我们知道,较高的教育收益率是吸引社会资源投资于教育的动力所在,也是教育扩展的根本动力,而教育收益率的下降,只会挫伤社会资源向教育部门投资的积极性,减少教育投资的预期收益,从而使教育扩展缺乏后劲。
(二)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基础不是教育收益率的提高
从第一部分的分析可知,教育对收入差距缓解作用的发挥,其必要的条件就是收入差距的拉大一定要是教育扩展初期教育收益率增长所造成的,否则,教育的扩展将不会对收入差距的缓解产生多大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世界分工布局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非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具体到产业上多为工农业产品的初加工,因此,对教育人口的重视程度不高,收入的差距中资本收益占很大的部分。同时,由于改革的过程也是体制的转轨过程,在此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政策上的漏洞,因此这些漏洞给一些社会成员带来了机会,使“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加之中国一直在强调“效率优先”,对这一贫富差距也未作适当的调整,在市场的自发作用下,马太效应的发挥使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也随之增大。从这里可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主要不是由于教育收益率的提高造成的,因此,教育的继续扩展不会对中国的收入差距产生多大的影响。
(三)我国的经济收入差距已经很大,而教育扩展所带来的抑制效应还不能作为缓解中国贫富差距过大的及时手段
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很大,据1996-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李强教授的调研结果,中国城乡居民家庭的人均年收入基尼系数已达到0.4577,并在持续扩大[4]。1999年就已经到了“任其扩大是危险的”地步[5]。我们知道,制度还有个惯性的存在,即现行制度的影响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消失,而是在惯性的作用下于一段时间内继续发挥作用。根据上面的分析,教育扩展对收入差距的缓解是一种内在的间接机制,它的效果也不如直接手段快,故其效应的显现也需要一段时间。因此,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如果一味地片面强调教育扩展的作用而不采取其它直接手段来缓解当前的贫富差距,可以预见,我国的收入差距将继续扩大,显然那将是非常危险的。
三、高校扩招不是中国缩小贫富差距的制度起点
鉴于教育扩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如上所述的关系,因此就有人认为,要缩小中国目前比较大的贫富差距,首先就是要改革教育体制,使教育得到大力的发展,当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贫富差距就会自然而然地缩小。同时有学者认为,目前中国实行的高校扩招政策可以看作中国教育扩展的制度起点,并将进而成为缓解中国贫富差距的制度起点。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中国的教育发展至少在目前是不可能成为缓解中国贫富差距的制度起点的。而目前中国高校的大面积扩招也不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初始制度,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决定的:
(一)教育机会的不均等,教育的大面积发展受到限制
我们知道,目前中国的高校扩招是在并轨制实施以后才实行的,以前我们实行的是单轨制,而现在实行的是双轨制和多轨制是向不平等方向的回复,典型的表现就是以贵族学校与希望工程为代表的两个方向,贵族学校所追求的正是高人一等的教育特权,是在没有明确的双轨制的背景下人为地制造对不同阶层提供不同质量教育的新现象,此为表现之一。表现之二就是中国的义务教育,一方面政府宣布义务教育,并以立法的形式予以肯定,另一方面无财力去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取西方强制的一面,弃其免费的优势,致使学生流失严重,义务教育难以实现。
在接受教育的机会都不均等的条件下,实行目前的扩招政策,看起来是增加了全体社会成员受教育的机会,实际上这增加的教育机会大部分特别是在农村,其绝大部分都分配给了富裕阶层成员的后代,这将使富者更富,而穷者则更穷,实际上不是在缓解社会的贫富差距,而是在加剧这一贫富差距,此其一;其二,由于在短期内突然增加许多学生,扩招所造成的学生素质的下降,必须使学生的市场能力下降,这势必使社会降低高校毕业生的工资待遇,这同样使教育的收益率下降,同时也就降低了接受教育的吸引力;其三,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当前的就业机制中,人力资本作为硬件,如大学毕业证、各种专业等级证书等,起着控制进入就业市场的准入关口,而在取得了准入资格的众多就业竞争者中,胜算的决定权则主要取决于就业者社会资本积累量的多少。一般来说,在当前的就业过程中,以本科毕业生为分界线,本科以下的就业过程主要是依靠社会资本实现的,本科以上则主要是依靠人力资本实现的,而本科毕业生则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双双重要的状况,当然,视专业的好坏,也可能会在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有所偏重。所以,高校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就业的压力使学生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在同等条件下,谁的社会资本越多,谁就越有实现理想就业的优势,可见社会资本已经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高校扩招为更多的社会上层成员的子女提供了通行证或者说准入证,其社会资本要比下层成员子女的社会资本丰富得多,如当前垄断行业的用人单位基本上就是在职工子女内部进行的,因此社会资本将使就业部门,特别是公共部门的裙带现象更加严重,这种现象的负面作用就是使教育贬值,这显然也无益于中国教育的发展。
(二)片面发展高等教育只会造成人才结构的畸形,不利于教育的发展
高校扩招使社会上的高中低层次的人才结构不是呈金字塔形,而是呈现圆柱形,目前印度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这种人才结构势必造成高级人才的挤压,为了保持一定的优势,他们就会走入片面追求高学历的误区;而低层次的人才由于高学历人才的参照作用,也会去刻意追求高学历,结果是使教育形式化、应试化,难以达到社会和市场的需求。而市场和社会是根据能力作出回报的,因此,社会和市场所给出的回报也会比人们预期的低得多,这就在无形中提高了教育的机会成本,显然这也是中国教育发展的消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