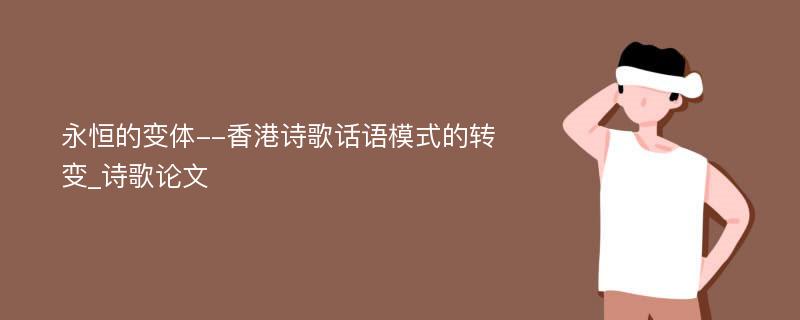
永恒的变奏——香港诗歌话语方式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变奏论文,香港论文,诗歌论文,话语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新诗歌,自“五四”新文学运动实现了古典文言体系向现代白话体系的转变之后,是顺着两条通道向着同一个方面发展的。
一方面,1927年后,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变革的重心由中心城市转向广大农村,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总体革命策略思想指导下,文学的主流话语也发生了由“城市”向“农村”的移动。在诗歌中,这种话语的流动尤为生动,面貌的改变也尤为显著。
同样是歌唱爱情,赞扬青春、自由,在20年代的汪静之笔下,充满了城市知识分子“闷得发慌”的怨愤和伤感:
蕙花深锁在花园
满怀着幽怨
幽香潜出了园外
园外的蝴蝶
在蕙花风里陶醉
它怎寻得到被禁锢的蕙
它迷在熏风里
甜蜜而伤心,翩翩地飞
(《蕙的风》)
到1946年,应和解放区新民歌创作潮流,诗人们已放弃城市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和观察视点,诗歌走出书斋和讲坛,直接面对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发言,于是我们听到李季那朴素、明朗、大胆直率充满泥土气息的“乡村话语”:
捏一个你来捏一个我,
捏得就象活人脱。
捏碎了泥人再重和,
再捏一个你来再捏一个我;
哥哥身上有妹妹
妹妹身上有哥哥。
(《王贵与李香香》)
可以说,从1927年后,差不多半个世纪的诗歌语言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这种以现实主义、古典诗词、民歌民谣为综合特征的“乡村话语”。
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头十年,诗歌的世界,是“个人”的世界。周作人提倡“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郭沫若提倡诗人本职专在抒情和表现自我。无论是否定与更新,乐观与愤懑,无论是师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或象征主义,当时的诗歌都充满尖锐沉酣的个性。但随着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变动广阔而深入的发展,尤其是经过抗日战争这样事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酷烈历史阶段,诗人不可以再躲在象牙塔里自我欣赏或顾影自怜,时代也好,现实也好,都要求诗歌走进人民的苦难与斗争,走进社会洪流、阶级的洪流,在心灵上和美学上都肩负起民族和历史的责任。
在新诗诞生的头十年,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个性的天狗式的飞奔狂叫:
我是月底光,
我是日底光,
我是一切星球的光,
我是X光线的光
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
(郭沫若《天狗》)
但30年代之后,“五四”新诗中扩张的“自我”和滥情的“个性”受到“集体的遏制,诗人们几乎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给自己重新进行了角色定位:
我们是劳动者
是伟大祖国底伟大的
(田间《给战斗者》)
这就是说,从个性解放出发的中国新诗,一当它的神经深延到民族现实生活的土地,它的精神、它的情感就从个体的认同转向对集体的认同。不要说《蕙的风》、《微雨》那样涨满“寂寞、苦恼、厌倦”或饱吸“世纪末的果汁”的诗风不能满足这种认同的需要,即使象《女神》、《红烛》那样充盈阳刚之气的诗风也被诗人们重新检讨。诗歌必须面向“集体”发言,“个人”必须成为“集体”的一部分,哪怕最富有个性的诗作,诗人也成为“集体”的代言者,自觉地将“自我”与“集体”熔化在一起: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艾青《我爱这土地》)
于是,中国的新诗在“城市话语”向“乡村话语”转变的同时,出现了“个人话语”向“集体话语”的移动。在30年代以降直至50年代初期的中国诗坛上,以现实主义为总体特征的“乡村话语”和“集体话语”基本上主宰着诗歌的创作流向,深刻地影响着这个时代中国新诗的美学精神。
当代香港诗歌,是20世纪后半叶都市生活的产物,顺应着香港都市现代化的发展,诗人们始终以都市的情怀、都市的眼光阅读着香港的都市生活。在中国当代诗歌中,香港诗歌最早走出了“乡村话语”和“集体话语”的空间,实现了对“城市话语”和“个人话语”的重建。
50—60年代,先是马朗,用抒情化的缅怀,表现了对都市生活的个体观察和情感。《车中怀远人》将一种无声的哀伤和忧郁,置于“岩石一样寂静的车厢”,让它在平静如水的夜色中,从一个时间铛铛然驶入了又一个时间”。《北角之夜》以“朦胧的视角”写香港繁华区北角的春夜,灯影里慢慢成熟的玄色,满街飘荡的薄荷酒溪流,舞娘们的纤足和卷舌的夜歌,使人们“陷入一种紫水晶里的沉醉”,“疲倦而又往复留连”。诗人用了近乎情诗的醺然徜徉写都市的疲倦和落寞,又用带古典田园风味的意象写都市的纸醉金迷,这都溶解着他个人的特殊经验,因而也成为他特殊的话语方式。
如果说马朗是从大陆进入香港后,用旁观者的姿态诗意地观察着都市,那么在香港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如崑南、叶维廉、戴天、蔡炎培等人,则通过西方现代主义来理解着都市,对都市生活进行艺术的瓦解和改造,力图建构出新的现代“都市话语”。
崑南用荒原式的呐喊和自我剖白,诅咒着都市的“肮脏、恶臭、腥味”,都市从他的眼睛到内心都是“永恒的悲剧”:现实是残酷的,思想是虚无的,生存毫无意义。在理想的破灭和失落中,他对都市的抗拒有着决眦裂帛的否定:“我不了解幸福,不了解真理!”“这个时代,没有悲观,只有毁灭。”〔1〕叶维廉用辛笛的“气氛”、 “卞之琳的“呼应”、“场景转换”、“现在发生性”、冯至的“事件律动的捕捉”、艾青的“戏剧场景的推进”和戴望舒“情绪的节奏”,写出从贫穷的农村流落香港后“深沉的忧时忧国的愁结、郁结”。“在焦急的人们中,在焦急的时代下”,他把“当代中国的感受、命运和生活的激变与忧虑、孤绝、乡愁、希望、放逐感(精神的和肉体的)、梦幻、恐惧和怀疑”表达得有如沉重浓郁的史诗。〔2 〕戴天用“介入中有超脱,困惑中有清醒”的性情,于“唐诗宋词之中,找到超现实,魔幻主义的技法”,写雅朴苍莽的文化关怀;〔3 〕蔡炎培则用了隐晦艰涩的语言和纷乱跳跃的意象写放纵难收的激情。
70年代,在崑南等人用西方现代主义的话语体系构建香港诗歌的艺术时,舒巷城在生活体验和艺术实验的摸索中建立起对都市的道德批判。他用一把“既怜惜又挖苦的刀子,戮裂都市的面具”,将都市中千奇百怪的景象和那可悲、可笑、可叹的人和事,“雕塑成一幅爱憎分明的现代都市的浮世绘”〔4〕
在舒巷城对都市生活进行道德批判的时候,以温健骝、古苍梧为代表的一批现代诗人,重新调整了自己的社会政治和艺术视野,对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同时作了辩证的反思,对台、港现代诗中摹仿西方、脱离社会、脱离生活现实,一味玩弄现代艺术技巧的恶习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温健骝提出要“在一面向‘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学传统学习的时候,创作者不要忘记用笔尖在生活里饱蘸了现实的墨汁、汗水或者血液”。他的诗也从早期“以隽美之句,低诉哀吟又近乎徒然地反抗‘时间的压迫’”,转向“以刚健奋进的生命意识,突破‘自伤幽独’的囿限,而走向‘个我’和‘群我’的调谐与协进”。〔5〕
50—60年代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横向移植,70年代对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双重检视,使80年代以后的香港诗歌创作普遍有了新的艺术自觉。诗人们逐渐认识到,现代与传统,继承与创新,是艺术发展中看似对立实则统一的两个方面。没有现代观念的浇灌,传统就会枯萎;没有对传统的继承,现代就不能成为新的传统。因而创新必须是继承的创新,必须吸取传统的精华。在这种过程中,激进的“全盘否定”式思维被冷静的独立思考所取代,诗人们对诗歌的本质、诗歌的艺术有了新的理解。陈德锦说:“诗本质上是一种情感语言。情感的根源、方向、形态都不是单一的,生活中种种选入诗人心灵的印象,积久而成记忆和情感的价值。情感价值的取向应该鲜活、深远、真实。一切艺术形象和形式的创造,是对这种价值的审美认识和实践”。〔6〕
温明则强调诗歌创作与生活的关系,他说:“诗创作是一种表达个人情感的形式,不论技巧如何,其感情必是源于其生活,欢、悲、喜、愁等并不能在真空状态孕育出人的感情。”〔7〕
当诗人们放弃了现代与传统的对立,偏执于现代或偏执于传统的两极分化情势也随之消退。兼容并蓄的多元化创作局面,使诗歌的艺术出现互相归化的趋势,诗人们在“现代”与“传统”之间有了更清醒的取舍,创作在这个意义是更加个性化了。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首诗:
参差的灌木丛被剪成整齐的高度
强调的是一片翠绿一片四平八稳的
外表 安然渡过游人乐于审美的目光
但底下的果皮纸屑会化为泥土拥护它们吗
抑或是给嫩草的根须忽忽抓紧
一株一株柔柔伸展着变通的刚强
穿插其中的蚂蚁比室内的敏捷得多
除了食物以外谁又是他它更大的敌人呢
驻足的蜻蜓呵总在旁观
是一双复眼更能洞悉世情吗 那么
石头会不会长出灵活的四肢〔8〕
这是青年诗人蔡志峰的《又是夏季的花园》的第2节。在第1节中,诗人描写了“夏季的花园”里如常的生活(“我们如常地生活在这里”),第2节中便对看来是“如常”的生活提出了怀疑, 最后诗人追问道:“我们如常地生活在这里吗?”在这一声追问里,“花园”的空间扩展为“我们”的生存环境,诗人对“如常”生活的怀疑成为“我们”共同的怀疑。诗人所要表达的已不是现代诗初期那种放纵的“自我”,而是对“集体”的焦虑,而这种每个人都可能产生的对生存环境的不满和焦虑,是通过诗人个人的体验、个人的风格在具体可感的情绪中显露出来的。
如果说《又是夏季的花园》是以个人的经验表达了大众的关怀,体现了现代诗对传统诗“集体话语”的改造,那么倾向于传统的诗人们也在努力吸取现代的表现手段,如谭帝森《金钟声声》一诗中的句子:
金钟是斜向湾仔的滑梯
以致中环独有的
王者之气不断向东滑去 滑去
湾仔遂成了
地价和楼房一样
节节高升赛过铁塔〔9〕
诗中的描写已不是写实的白描,而是有主观写意的变形。 谭帝森70年代末定居香港,因“见到郑愁予等台湾诗作, 觉得与内地文革时期的口号诗大不相同。有‘惊艳’之感”〔10〕,从此迈出了诗歌创作的步履。他的诗,于饱满的写实中有灵活的象征,朴素的口语中有新鲜的造句,既得现实之纯,又得现代之巧,可以看作是现实主义诗人向现代主义吸取营养的一个成功的例子。
80年代中后期。后现代主义的诗学观念被引进香港诗坛,也斯(梁秉钧)是这一观念的主要推动者。
也斯的诗歌观念中,有三处特别值得留意。其一,他区别了“象征的诗学”和“发现的诗学”。所谓象征的诗学,即’诗人所感已整理为一独立自存的内心世界,对外在世界的所遇因而觉得不重要,有甚么也只是割截扭拗作为投射内心世界的象征符号”。所谓发现的诗学,即“诗人并不强调把内心意识笼罩在万物上,而是走入万物,观看感受所遇到的一切,发现他们的道理”。〔11〕其二,也斯区别了诗歌中不同的“声音”。艾略特曾将诗分为三种声音,一种是诗人跟自己说话的声音,一种是诗人跟一个人或一群人说话的声音,一种是诗中虚构角色跟另一个角色说话的声音。也斯认为,向一个人说话或向一群人说话是不同的,“向一个人说话,那可以是抒情的声音,对话的声音,问话的声音。向一群人说话,却是演说的声音,公众的声音”。〔12〕他既反对用公众的声音遗漏或压抑了诗里其他的声音,也反对个人的声音“私人得令邮差脸红”,他“宁愿从个人到达公众”,同时又可以保存诗中“由个别情景个别友人个别艺术引发出来那些独特的对生命和艺术的体会”。〔13〕其三,他区别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生活(主要是城市生活)不同的态度,他说:“现代主义兴起于城市,每一个浪潮都跟一个特殊的城市有关,作品也会与城市生活不可分,或者是狂热拥抱物质文明,希望诗作带着马达的节奏,或者是批评这种文明底下的空虚,以城市象征精神虚竭的荒地。到了后现代主义者,明知今日再无法归隐田园,大多数接受了城市生活,面对城市带来的文明与恶果,只有吸纳新知识,调整旧观念,重建一套新的价值标准”。〔14〕
从“象征”到“发现”,从“个人”到“公众”,从对现代文明的批评与批判到对价值标准的重新调整与建构,反映了从现代主义诗学观念向后现代主义诗学观念的过渡。但在香港诗歌中,后现代主义诗歌并没有充分发展起来,除了也斯的呐喊,除了也斯和他的学生罗贵祥的小范围实验,后现代主义诗歌并没有对香港诗歌创作造成巨大的冲击。这一方面是因为香港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工业化、现代化是其社会的基础特征和核心风貌。没有后现代的社会,就不可以有后现代的诗。诗歌毕竟不是某个个体意念的一厢情愿的写照,诗人无法回避也无法逃避他的社会和时代而成为某种理论或教义的解说员。另一方面,作为后现代主义诗歌观念的推动者,也斯并没有想把它发展为一场运动或把自己打扮成某个潮流的领袖,他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热心,只集中在一种学术性的艺术思考,目的在于用后现代主义的某些方法建立一种新的观察方式或表达方式,并从中建立一种新的艺术标准和价值标准。
80年代,香港诗坛和文坛的另一道奇异风景,是“新移民作家”的创作。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尤其是开放改革以后,有一大批作家从国内来到香港定居,他们被称之为“新移民作家”或“南来作者群”,在诗歌活动方面,他们主要集结于“香港作联”、“龙香文学社”和《当代诗坛》杂志周围。
“新移民作家”或“南来作者群”是一个模糊的界定,他们到港定居的目的和途径不尽相同,思想和艺术的追求各有差别,生活的地位和担负的社会角色各有不同,对中国、香港以及世界的认识也并非一致,但正如梅子所说的那样,由于他们所受的文学薰陶和灌输有共同点,这一作者群的审美习惯、价值判断和创作技巧,基本上有相同的地方,与土生土长的香港作家,在创作取向方面,有着比较明显的区别。其诗歌创作的总体特征是,在观念上和方法上大多倾向于现实主义,风格浅易明朗不作艰深晦涩之音。在内容上,大都注重抒写个人的生活经验和体会,关注社会现实的变化和发展。在文化情感上,他们虽然身居香港,却保持着与国内紧密的联系,并将许多优秀的创作观念和经验带入香港。在语言上,他们几乎都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极少顾及语言的“地方色彩”。
这样,我们看到,在香港本土诗人和新老南来作家的共同努力下,工业化时代的香港诗歌形成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多元共存的局面。话语方式也在这种多元共存的格局中不停地变化。随着香港回归祖国,一方面香港诗歌作为中国诗歌的一部分,重新纳入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轨道。另一方面,在“一国两制”的条件下,香港诗歌仍将保持自己的特殊形态。这种双重的背景会使香港诗歌运动发展变得更为错综复杂,也更为深刻。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各种话语都可能将香港诗歌作为实验场,形成各种声音的永恒变奏。在这种变奏中,无论是继承还是创新,无论是因袭还是革命,无论是保守还是激进,都能为我们提供新的经验,并将我们的视角放宽到最佳程度,使我们能用新的形式,将旧的生活、旧的事物进行彻底改造,或者在旧生活、旧事物中发现潜藏的新事物、新生命。
注释:
〔1〕有关崑南的评论, 参见陈少红《香港诗人的城市观照》、叶维廉《自觉之旅:裸灵之死——初论崑南》,收于陈炳良编《香港文学探赏》,三联(香港)有限公司1991年12月第1 版。
〔2〕有关叶维廉的评论,参见叶维廉《我和三、 四十年代的血缘关系》, 收于叶著《饮之太和》, 台湾时代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初版;叶维廉《中国现代诗的语言问题》,收于叶著《秩序的生长》,台湾志文出版社1971年版;萧萧《空间叠层在叶维廉诗中的意义》,收于张汉良、萧萧编选《现代诗导读——批评篇》,台湾故乡出版社,1982年版;王建元《战胜隔绝——马博良与叶维廉的放逐诗》,收于陈炳良编《香港文学探赏》。
〔3〕有关戴天的评论,参见黄维樑《香港诗话》, 收于黄著《香港文学初探》,香港华汉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2 月第1 版;王一桃《向往自由,喜爱人间》,收于王著《香港作家掠影》,香港现代教育研究社;王剑丛《戴天的诗略观》,载《华文文学》1993年第2期(总22期)。
〔4〕引自何华新《香港的诗心——近视舒巷城诗作》, 见《舒巷城卷》之“评论掇华(诸家)”,三联书店(香港)1989年2月第1版。
〔5〕有关温健骝的评论, 参见《温健骝卷》中温健骝之《还是批的写实主义大旗》,古巷梧、黄继持之编后记及“附录”中水晶,聂华苓、古苍梧等人的回忆和悼文。《温健骝卷》, 三联书店(香港)1987年7月第1版。
〔6〕陈德锦《诗观》,见《陈德锦作品选刊》, 《亚洲华文作家》杂志第27期。
〔7〕温明《诗观》,见《温明作品选刊》, 《亚洲华文作家》杂志第27期。
〔8〕蔡志峰《又是夏季的花园》,载《诗双月刊》第4卷第4—5期(总22—23期)。
〔9〕〔10〕见谭帝森《楼梯街的祝福》,香港文学报社,1995 年初版。
〔11〕〔12〕〔13〕见《梁秉钧诗选》之《游诗·后记》、《诗与声音》、《谈艺的明信片》,香港作家出版社,1995年12月初版。
〔14〕也斯(梁秉钧)《书与城市》代序,香江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标签:诗歌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香港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读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