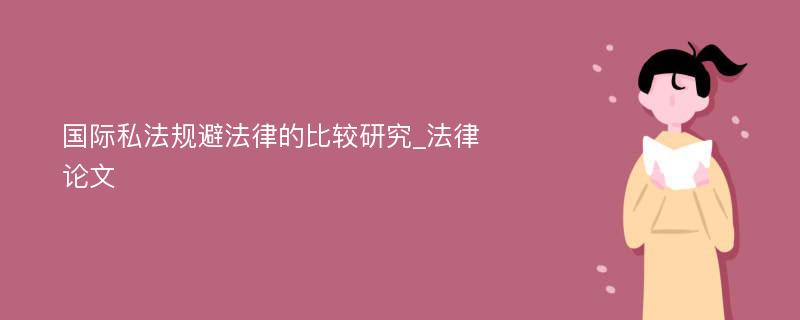
国际私法中法律规避问题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私法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私法中的法律规避(evasion of law ), 又称法律欺诈(fraude àla loi),是指当事人故意制造某种连结点, 以避开本应适用的对其不利的法律,从而使对自己有利的法律得以适用的一种脱法或逃法行为。
自
1878年法国最高法院对鲍富莱蒙王妃离婚案(Bauffremont's divorce Case)(注:参见黄惠康、黄进:《国际公法国际私法成案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94页。) 作出了认定当事人通过规避法国法而取得的离婚与再婚均属无效的判决后,国际私法理论界对法律规避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拟对法律规避问题作一比较研究。
一、法律规避的构成要件
关于法律规避的构成要件,我国学者提出了四种不同的主张。(一)认为构成法律规避应具备三个要件:当事人必须有规避法律的意图,亦即当事人的行为以规避某种法律为目的;被规避的法律必须是依冲突规范本应适用的法律;法律规避是通过故意制造一个连结点的手段来实现的。(注:参见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修订版,第85~87页。)(二)认为构成法律规避,应具备这样三个要件:必须有行为人规避某种法律的故意,或者说,行为人必须具有逃避某种法律的目的;被规避的法律必须是依内国冲突规范本应适用的法律,但系行为人通过构设一个新连结点的手段而达到的;被规避的法律属于强行法的范畴。(注:参见李双元等:《中国国际私法通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166页。)(三)认为法律规避有四个构成要件:从主观上讲,当事人规避某种法律必须是出于故意,也就是说,当事人有逃避适用某种法律的意图;从规避的对象上讲,当事人规避的法律是本应适用的强行性或禁止性的规定;从行为方式上讲,当事人规避法律是通过有意改变或制造某种连结点来实现的,如改变国籍、住所、行为地,物之所在地等;从客观结果上讲,当事人规避法律的目的已经达到。(注:参见黄进:《国际私法上的法律规避》,《百科知识》1995年第10期,第16页。)(四)认为构成法律规避必须具备六项要件:法律规避必须有当事人逃避某种法律的行为;当事人主观上有逃避某种法律规定的动机;被规避的法律必须是依法院地国冲突规范本应适用的实体法,并且必须是这个法律中的强制性规范;法律规避必须是通过改变构成冲突规范连结点的具体事实来实现的;法律规避必须是既遂的;受诉国必须是其法律被规避的国家。(注:参见余先予主编:《国(区)际民商事法律适用法》,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95~96页。)
分析上述主张可以看出,学者们对法律规避必须具备的主观要件是持一致看法的,即法律规避的当事人必须有规避法律的意图。这一构成要件被法国学者视为“法律规避的特有因素”,(注:参见[法]巴蒂福尔、拉加德:《国际私法总论》,陈洪武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510~516页。)因为它是区分某种改变连结点的行为是否属于法律规避的首要标志。换言之,由于法律规避都是通过改变连结点来实现的,但在现实生活中,连结点的改变有时是正常的,只有当事人具有规避法律的意图时方有构成法律规避的可能。根据当事人是否具有规避法律的意图来区分连结点的正常变动和法律规避,就引出了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就是法律规避的认定问题。其复杂性表现在它涉及到“对人的内心意识的侵入”,而法律只涉及外部行为,但关于意图是不能得到可靠的结论的,这样就会使法官做出不可接受的专断结论。(注:参见[法]巴蒂福尔、拉加德:《国际私法总论》,陈洪武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510~516页。)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葡萄牙、澳门学者采用了列举的方法列出以下五种情形不视为法律规避:(1)某当事人改变了国籍, 但他在其新的国籍所属国连续居住,且该国籍正是该当事人长期期望取得的。在这种情况下,该当事人改变其国籍不能视为法律规避。(2 )某当事人错误地规避不存在的某项实体规范的适用,这种行为可以不视为法律规避。(3)某当事人改变连结点时,选择了一个错误的连结点, 即该当事人选择了一个并不指向其所希望适用并对其有利的法律的连结点。(4 )某当事人拟改变或创设一个新的连结点,但事实上他未成功,在这种情况下法律规避没有成立。这也就是说,不存在未遂的法律规避。(5 )如果某法人在特定国家有一个“有效的住所”,不论其选择此住所的用意如何,不能将此项选择视为法律规避。(注:参见黄进、郭华成:《澳门国际私法中的法律欺诈》,《法学研究》1997年第2期,第216~219页。)
尽管上述五种情形可能并不全面,但它提供了解决问题的规则,那就是认定法律规避,最重要的是要把握法律规避的主客观构成要件,结合有关具体情况,加以分析认定,切不可简单地将当事人改变连结点的行为一概视为法律规避。(注:参见黄进、郭华成:《澳门国际私法中的法律欺诈》,《法学研究》1997年第2期,第216~219页。)
当事人为规避法律而改变连结点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改变事实状况(如住所、所在地、行为地);二是改变法律状况(如国籍)。由于当事人对住所的变更较国籍更为容易,大陆法系国家普遍赞成将国籍作为属人法的连结点。(注:参见李双元等:《中国国际私法通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166页。)采用住所作为属人法的连结点的斯堪的那维亚四国为了防止伪设住所的发生,曾经缔结协定,规定缔约国一方公民在缔约另一方设立住所,需经两年以上,才算取得住所。(注:参见[法]巴蒂福尔、拉加德:《国际私法总论》,陈洪武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510~516页。)
但是,学者们对客观要件的表述和概括,彼此有所不同。第三种和第四种主张提到了法律规避必须是既遂,这较符合法律规避的本质以及研究该问题的目的和宗旨,正如前述葡萄牙和澳门学者所列举的第四种情形:“不存在未遂的法律规避。”但是,第四种主张把“当事人必须有逃避某种法律的行为”和“受诉国必须是法律被规避的国家”作为构成要件,似乎并不必要和不太准确。因为法律规避理所当然必须是一种“行为”,且在讨论构成要件时,应着眼于行为的性质和特点,而不是它的效力。所以,第三种主张是较为科学、全面的。
二、法律规避在国际私法中的地位
在国际私法中,法律规避究竟是一个独立的问题,还是公共秩序问题的一部分,在理论界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问题,不应与公共秩序问题混为一谈,因为两者虽然都常常产生不适用本应适用的外国法的结果,但两者的性质却不相同,因公共秩序不适用外国法,是着眼于外国法的内容;因法律规避不适用外国法,却是着眼于当事人的虚假行为。另一种意见却认为法律规避属于公共秩序问题,是后者的一部分,因为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内国法的权威。(注:参见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修订版,第85~87页。)赞成后一主张的学者指出,法律规避只是公共秩序的一种特殊情况,其特殊性在于外国法的适用可能导致的“社会混乱”是由当事人通过欺诈行为引起的。(注:参见[法]巴蒂福尔、拉加德:《国际私法总论》,陈洪武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510~516页。)
我们认为法律规避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并不属于公共秩序问题,因为:(1)法律规避和公共秩序产生的原因不同, 前者是当事人故意通过改变连结点的行为造成的,后者则是由于冲突规范所指定的外国法的内容及其适用与该冲突规范所属国的公共秩序相抵触引起的;(2 )进行法律规避是一种个人行为,而适用公共秩序是一种国家机关的行为;(3)对当事人来讲,法律规避和公共秩序的后果也是不一样的, 因公共秩序而不适用冲突规范所援用的外国法,当事人无需负任何法律上的责任;而由于否定法律规避行为不适用外国法时,当事人企图适用某一种外国法的目的不仅不能达到,还可能要对其法律规避的行为负法律上的责任。
在国际私法领域内,法律规避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冲击着各国法律的尊严。目前,法律规避现象不仅仅存在于亲属法、婚姻法、契约法领域,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法律规避现象几乎渗透到国际私法的各个领域,诸如公司法、运输法、保险法等。比如,在公司法方面,当事人为了在成立公司时少交一些费用或在成立后每年可以少交一些所得税,往往先到某一国去成立公司,再到另一国家去以“外国”公司的名义进行活动,以逃避本国关于成立公司时应交纳的大量费用或每年交纳的高额税款。在美国各州之间就存在这种法律规避现象。特拉华州是美国各州中在成立公司方面规定得最宽松的,因此有许多美国公司都到特拉华州去注册成立公司,可它们根本不在那里从事经营活动,而只是取得一张营业执照就到别的州去从事业务活动,它们在其他州就可以以特拉华公司的名义进行活动,逃避其他各州有关公司纳税的规定。(注:参见黄进:《国际私法上的法律规避》,《百科知识》1995年第10期,第16页。)又如,在国际海上运输中普遍存在着一些船舶挂“方便旗”的现象,即某一国家的船舶所有人,为了逃避在船舶登记时所需交纳的巨额费用及嗣后在航运方面的便利,不到本国的船舶登记机关去登记,而是到对船东条件优惠的有关国家的机关去登记。使船舶取得该国国籍,然后挂着该国的国旗在海上航行,这就是一种法律规避现象。(注:参见姚壮主编:《国际私法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66~67页。)
我们认为,造成上述法律规避现象的主要原因是:(1 )人类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2)各国法律中对同一事项的规定存在歧异;(3)冲突规范赋予当事人选择法律的可能,并且每个国家的法律史都有很多例子说明“破坏法律的方法和技巧是无穷无尽的。”(注:参见[美]马丁·沃尔夫:《国际私法》,李浩培等译,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216~219页。)
但在不同国家的国际私法著作中,法律规避的重要性很不相同。大陆法系国家的教科书常把法律规避作为一项基本制度或一个重要问题专门加以论述;英美法系国家的著作一般不专门讨论这个问题,而是在讲到“时际因素”或“连结点的改变”时附带涉及。这与下面讨论的效力问题密切相关。
三、法律规避的效力问题
对于法律规避行为是否有效的问题,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大陆法系国家普遍认为,法律规避是一种欺骗行为,根据“欺诈使一切归于无效”的原则,在发生法律规避的情况下,就应排除当事人希望适用的法律,而适用本应适用的法律。例如,1891年《瑞士关于民事关系的法律》规定:“禁止通过在国外缔结婚姻来规避瑞士婚姻法。”法国的司法实践更是严格地遵循上述主张,如法国最高法院民事庭1985年3月20日维持了埃克斯法院1982年3月9日的判决, 认为一个定居在维尔京群岛的人规避了法律,这个人为了避免规定保留子女的应继份额的法国法律适用于他的不动产继承,将其在法国拥有的不动产让与一个他拥有三分之二股票的美国公司,这些股票又被交给一个美国的信托公司,他仍然享有对该不动产的使用收益权,并享有自由处置权。这样,他就通过由不动产物权向动产物权的转变导致继承法的变更,从而非常巧妙地实现了法律规避。(注:参见[法]巴蒂福尔、拉加德:《国际私法总论》,陈洪武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 510~516页。)而在英美法系国家, 法院一般不承认法律规避问题。因为英美法院如果不让内国法为当事人所规避,它们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如对冲突规范作某种解释,以排除外国法的适用,从而达到同一目的。(注:参见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修订版,第85~87页。)例如,美国统一各州法律委员会1907年制定的撤销婚姻和离婚的统一法中,把当事人任何一方“是一个州的善意居民”而且在一定时间内“继续是这个州的善意居民”作为该州法院对婚姻无效案件和离婚案件行使管辖权的条件,(注:参见[美]马丁·沃尔夫:《国际私法》,李浩培等译,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216~219页。)便可达到防止当事人规避其婚姻法的目的。值得一提的是,英美普通法国家的有关立法和学说已开始重视法律规避问题。例如,1912年美国统一各州法律委员会全国会议草拟的《防止婚姻规避法》就是有关“规避或者违反住所地州的法律而在另一州或者另一国结婚”的法律。(注:参见[美]马丁·沃尔夫:《国际私法》,李浩培等译,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216~219页。)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出于人类对法律正义价值的追求和对本国法律威严的捍卫,都通过立法或司法实践来对法律规避加以禁止或限制。但对于法律规避行为究竟属“全部”无效还是“部分”无效,各国有不同的主张。法国法倾向于坚持“全部”无效。其理由是:任何用造成涉外连结点的方法来“诈欺地”排除一个法律规则的适用,在法国被认为是无效的,被排除适用的那个规则仍然适用,恰如它未被排除适用一样。(注:参见[美]马丁·沃尔夫:《国际私法》,李浩培等译,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216~219页。)法国学者巴蒂福尔对这一主张的解释是“合法的目的不能使非法的行为合法,目的不能为手段辩解。但是,非法的目的却使本质上合法的行为无效。”(注:参见[法]巴蒂福尔、拉加德:《国际私法总论》,陈洪武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510~516页。)葡萄牙法坚持“部分”无效。例如,葡萄牙法从前规定天主教婚姻不得解除。因此,一位葡萄牙人归化入墨西哥籍,以便在墨西哥离婚。葡萄牙法官仅判决其离婚无效,而对于该葡萄牙人的墨西哥籍则没有涉及。因为,对于葡萄牙人而言,他可以自由改变国籍。(注:参见黄进、郭华成:《澳门国际私法中的法律欺诈》,《法学研究》1997年第2期,第128~129页。)
四、法律规避的对象问题
在禁止或者限制法律规避的国家中,对于法律规避的对象是否包括外国强行法的问题,也有不同主张。
有些国家主张规避法律仅指规避本国(亦即法院地国)强行法。例如,前南斯拉夫法律冲突法第5 条规定:“如适用本法或其他联邦法可以适用的外国法是为了规避南斯拉夫法的适用,则该外国法不得适用。”1972年《塞内加尔家庭法》第851条规定: “当事人利用冲突规则故意使塞内加尔法不适用时,塞内加尔法取代应适用的外国法。”法国法院早期的判例也持这种立场,例如,1922年法国最高法院关于佛莱( Ferrai)一案的判决,(注: 该案详见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修订版,第87页。)就是这样。
有些国家主张规避法律既包括规避本国强行法,也包括外国强行法。因为规避毕竟是规避,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规避外国法的同时,也可能规避了内国的冲突规范,因为依内国冲突规范,该外国法可能就是本应适用的法律。(注: 参见李双元主编:《国际私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页。)例如,《阿根廷民法典》第1207、1208条规定:“在国外缔结的以规避阿根廷的法律为目的的契约是无效的,虽然该契约依缔约地法是有效的。”“在阿根廷缔结的以规避外国法为目的的契约是无效的。”又如,1929年英国法院曾认为目的在于逃避美国禁止输入酒类的法律的契约是无效的。(注:参见李双元等:《中国国际私法通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166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79年 5月订于蒙得维的亚的《美洲国家间关于国际私法通则的公约》第6 条也肯定了法律规避包括规避外国法。
法国后来的司法实践表明,它也越来越重视对规避外国法行为的制裁,并因此废除了在规避某一外国法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1964年1月7日的明策尔判决规定对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应以“不存在任何法律规避”为条件,这一说法是可以包括规避外国法在内的。(注:参见[法]巴蒂福尔、拉加德:《国际私法总论》,陈洪武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510~516页。)尤其典型的是在德国,对外国法的规避似乎与对法院地法的规避没有区别。(注:参见[法]巴蒂福尔、拉加德:《国际私法总论》,陈洪武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510~516页。)此外,在法律规避的对象问题上,各国学者还存在另一种争议,即其对象究竟是仅指实体法还是既包括实体法也包括冲突法。有的学者认为,法律规避行为只是规避实体法,因为只有直接调整当事人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实体法才对当事人具有实际意义,而规避冲突法并不会带来任何利益。有鉴于此,法国学者巴蒂福尔索性把规避实体法看作是“对冲突规则有意利用”的结果,其中的“冲突规则”包括“法律冲突规则和管辖权冲突规则”,(注:参见[法]巴蒂福尔、拉加德:《国际私法总论》,陈洪武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510~516页。)这表明,他赞同法律规避行为仅指规避实体法,甚至根本不承认规避冲突法之存在。
另有不少学者认为,法律规避行为既包括规避实体也包括规避冲突法,因为通过法律规避行为规避本应适用的实体法,实际上就是规避指定本应适用的实体法的冲突规范的适用。(注:参见黄进、郭华成:《澳门国际私法中的法律欺诈》,《法学研究》1997年第2期,第128~129页。)有些国家的立法也持这种主张,如,《匈牙利国际私法》第9条规定:“当事人为了规避本应适用的法律规则,而人为地或虚假地形成一个涉外因素与某一外国法相连接,则不得适用外国法,而应适用依匈牙利法本应适用的法律。”其中的“匈牙利法”就是指的“匈牙利冲突法”。
五、中国的理论与实践
我国立法对法律规避问题也未作明文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通则》的解答第194 条规定:“当事人规避我国强制性或者禁止性法律规范的行为,不发生适用外国法律的效力。”但对于规避外国强行法的行为是否有效,这里也没有规定,依我国多数学者的意见,由于国际私法所调整的法律关系不仅涉及本国和某外国两个国家,甚至常常涉及三个或四个国家的法律,当事人既可适用外国法来规避本国法,也可适用第二国法来规避第三国法,而第二国法和第三国法对法院来说都是外国法。因此,国际私法上的法律规避应包括一切法律规避在内,既包括规避本国法,也包括规避外国法。至于法律规避的行为是否有效,应视不同情况而定,首先,规避本国法一律无效。其次,对规避外国法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如果当事人规避外国法中某些正当的、合理的规定,应该认为规避行为无效;反之,如果规避外国法中反动的规定,则应认定该规避有效。(注:参见肖永平:《中国冲突法立法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3页。)我们认为, 法律规避是一个普遍的法律现象,它在所有的法律领域均存在。在国内法领域,法律规避行为自然是非法的,并应受到制裁。但国际私法上的法律规避行为,既涉及被规避的法律,又涉及到行为人故意改变连接点的行为和因此而成立的法律关系;被规避的法律有时是内国法,有时是外国法。因此,有关法律规避的效力问题,各国在立法、理论和司法实践方面存在着较大分歧。从历史上看,早先的学说普遍认为,国际私法上的法律规避并不是一种无效行为,如德国的韦希特尔(Waechter)、 法国的魏斯(Weiss)认为, 既然双边冲突规则承认可以适用内国法,也可以适用外国法,那么,内国人为使依内国实体法不能成立的法律行为或法律关系得以成立,前往某一允许为此种法律行为或设立此种关系的国家,设立一个连结点,使它得以成立,这并未逾越冲突规范所容许的范围,因而不能将其视为违法行为。一些英美法系的学者也认为,既然冲突规范给予当事人选择法律的可能,则当事人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而选择某一国家的法律时,即不应归咎于当事人;如果要防止冲突规范被人利用,就应该由立法者在冲突规范中有所规定。但这种观点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一个共同的意见是,如果承认法律规避的效力,必然造成法律关系的不稳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由此可见,国际社会的普遍趋势是加强限制法律规避行为。因此,对法律规避行为的认定,只要其符合构成要件即可,不应因内国强行法和外国强行法的不同而不同。
对于规避外国法的效力问题,我国理论界普遍主张的“依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作法,显然不符合现代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原则,因为用法院地法的观念去判断识别外国法是否“正当、合理”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正当、合理”的标准也含糊不清,很难掌握。因此,我们主张,规避外国法也应是无效的,即使外国法的规定确实不合理,当法院地国在适用它的时候,与本国的公共政策相抵触,便可借公共秩序保留排除其适用,这也不会妨害法院地的法制。
总而言之,只要当事人规避的法律是本应适用的强行法或禁止性规定,则不论其是实体法还是冲突法,也不论其是内国法还是外国法,都可构成法律规避。至于对具体法律规避行为的制裁以及制裁的程度和方式问题,则依法院地法的具体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