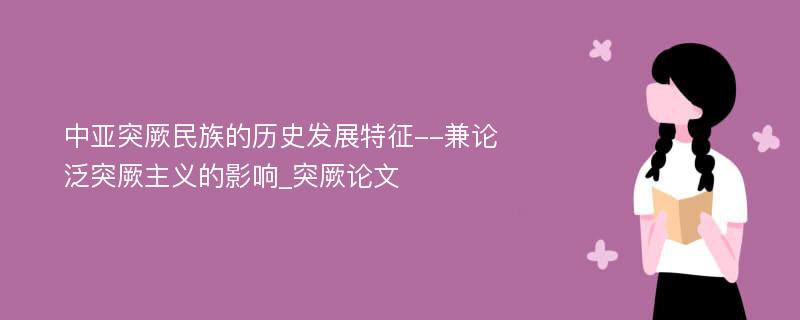
试析中亚突厥诸民族历史发展特点 ——兼论泛突厥主义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突厥论文,中亚论文,主义论文,民族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前苏联解体后,泛突厥主义思潮在土耳其、中亚地区重新抬头,为国际社会所注目。泛突厥主义能否像其希望的那样,使土耳其、中亚和其它地区的突厥民族联合起来,形成某种形式的政治联合体?本文拟结合中亚突厥诸民族历史发展的特点,对此作以探讨。
关键词 中亚突厥诸民族 历史特点 泛突厥主义
一、历史上异族入侵、民族迁徙使中亚突厥民族成份复杂
早在公元前7—5世纪,居住在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就出现了一些部落联盟,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称它们为“巴克特利亚人”、“花剌子模”、“索格底亚人”、“帕提亚人”。波斯历史文献称它们为“萨加人”。再晚一些,我国《汉书》统称它们为“塞种”人,并分称其为“粟特”、“康居”、“大宛”。就人种来说,它们大部分属讲东伊朗语的白种雅利安人,生活在伊朗北部、阿姆河、锡尔河之间及西起乌拉尔山脉,东抵阿尔泰山之间的广大草原。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6世纪的上千年历史中,由于波斯、马其顿、希腊以及匈奴人、大月氏人的入侵和迁徙,塞种人未曾建立起统一的民族国家,反而融合、消失在中亚、南亚的古代诸民族中。
中亚突厥民族发轫于西突厥时代。6世纪,受我国隋、 唐王朝的胁迫,原住我国北部草原的突厥部落开始大批地迁徙到河中及广大中亚地区。6—8世纪,即前伊斯兰时期,是西突厥民族在中亚奠定基础时期。这时期河中及中亚的突厥部落有鄂尔浑碑文中提到的九姓乌古斯部落,有汉文资料中提到的突利失时期的十姓突厥部落。8世纪后, 西突厥可汗王朝开始衰落,代之以分散的异姓突厥突骑施〔1〕、葛罗禄、样磨、处月、回纥、黠戛斯(吉尔吉斯人)等部族。
10—11世纪,阿拉伯人在中亚的统治衰落后,河中及中亚地区先后出现了三个鼎立的突厥王朝。喀拉汗朝(999—1103)就是由漠北的回纥人和其它异姓突厥部族所建,辖有天山主脉两面的广大地区及河中地区〔2〕;塞尔柱克汗王朝(1040—), 由来自黑海以北草原的乌古斯塞尔柱克部落所建,辖有呼罗珊,花剌子模、吐火罗地区;哥疾宁王朝(960—1189),由突厥奴隶出身的军事将领所建, 辖有阿姆河以南到阿富汗等地区。11世纪被认为是中亚突厥化的重要时期,大批突厥游牧部落进入河中地区,并带来了突厥人的军事采邑制,接受、传播了伊斯兰教,促进了以诗歌、文学、编年史和建筑物为主的文化繁荣。在突厥化过程中,原属雅利安人塞种的一些部落,改说突厥语〔3〕, 融合于突厥人中。
值得指出的是,原属西突厥人一支的乌古斯塞尔柱克人,在中亚建立王朝后,又进入伊朗的阿塞拜疆和小亚细亚,在与小亚细亚当地居民融合的基础上,15世纪建立了奥斯曼帝国。另一支乌古斯人的突厥蛮人〔4〕后来在土库曼建立了黑羊王朝(1378—1468)和白羊王朝( 1468—1502),奠定了土库曼人的基础。
13世纪蒙古人的入侵和16世纪乌兹别克昔班尼人进入河中和中亚,带来了大批蒙古族和中亚北部草原的钦察人、鞑靼人,使中亚突厥民族的成份再次发生了很大变化。统治中亚的窝阔台汗国和帖木儿汗国的蒙古部落只是在进入中亚和河中后才接受了伊斯兰教,并与突厥人融合起来,实现了“突厥化”。15世纪上半叶,当金帐汗国分裂时,就有部分“月即别”(乌兹别克人)部落先于大批昔班尼人及蒙古族的诺盖人进入河中地区。而“月即别”一词在俄罗斯,曾与钦察人一直被称为“鞑靼人”〔5〕。后来,哈萨克人也从月即别人中分离出来。 柯尔克孜(吉尔吉斯)16世纪还处在哈萨克汗的统治下,后从哈萨克人中分离出来,改信伊斯兰教,并突厥化。从而奠定了今天中亚乌兹别克、哈萨克、吉尔吉斯三个突厥民族的基础。
二、突厥社会长期分裂,统一王朝时间短,联系松散
从554年突厥木杆可汗与波斯王库思老一世达成盟约, 灭哒国,瓜分其领土,而进入河中地区起,到751年阿拉伯人征服中亚止, 在西突厥统治中亚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突厥可汗的权威只是名义上的,从未建立统一集中政权,而是处于分裂割据状态。
10—12世纪,中亚三个突厥王朝的统治也不长,且处在不断的征讨割据中。塞尔柱克王朝在苏丹马里克时期(1073—1093),进军费尔干纳,打败喀拉汗朝的军队,使其臣服于塞尔柱克汗的节制下,然而1141年,西辽契丹军队在撒马尔罕附近卡特拉旺草原的会战中,打败喀—塞联军,使该地区置于契丹人统治下,同时结束了喀拉汗朝和塞尔柱克人在河中的统治。不久,塞尔柱克人在中亚的呼罗珊王朝桑贾尔苏丹,在1153年同花剌子模人打仗中被俘,结束了塞尔柱克人对中亚的最后统治。
13世纪20年代起,蒙古人在河中及中亚建立的统治,同样始终处在分裂割据中。14世纪察合台汗国分裂后,西部河中地区与突厥人混合的是巴鲁刺思部族。东部费尔干纳盆地与天山以南的是杜格特拉部族。西部突厥人与蒙古人在14世纪后半期又建立了帖木儿帝国,东部则建立了蒙兀儿王朝(也称莫卧尔王朝)。帖木儿在位35年,他死后,其帝国分裂为4个小王国,且战乱不已。
16世纪初,当帖木儿后王陷入混战时,乌兹别克人乘机南下,灭其王国,建立了昔班尼王朝。但是,统一的昔班尼王朝也是短命的,昔班尼死后,汗国分裂为布哈拉、希瓦、浩罕三个小王国,直到19世纪被沙俄征服。
突厥社会长期缺乏统一王朝,处在动荡、分裂、割据状态中,其原因,除了异族入侵、民族成份复杂外,还在于突厥社会的氏族部落制和封建宗法关系,它限制了突厥民族的融合与凝聚力。从10世纪始,尽管封建制度已在河中地区确立,但是,由于游牧生活在突厥人中始终居主导地位,氏族部落制仍有很大影响。如把牧场、甚至国家看作氏族共有财产,各王朝的军队仍按部落组织,土地实行分封制,社会建立在父辈家长制和血缘关系的基础上。氏族部落制的最大特点是氏族部落的利益,自成体系,与别的部族、集团几乎处于隔绝状态,抵制权力集中,继之而来的是为争夺汗位、继承权的内讧及相互间连续不断的战争,结果使社会长期动荡、分裂、割据。同时,由于部落是游牧民的基本社会单位,是传统生产方式的载体,它使各部族长期保持了原有的风俗习惯、传统观念,造成民族内部联系松散。氏族部落制的残余在今天中亚各民族国家中仍有很大影响,如民族的集团性、地方主义、部族主义、家族主义等。苏联解体后,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吉尔吉斯和塔吉克都有“棘手的部族主义问题”,“土库曼斯坦的地区问题也相当复杂”〔5〕。
三、伊斯兰教在中亚扎根不深,到现代更多地表现为民族文化的基础
自8世纪伍麦叶王朝征服河中地区起, 伊斯兰逊尼派就在中亚突厥社会中取得了立足点,但直到19世纪,正统的逊尼派除了在河中定居居民和城市中有影响外,在游牧各部族中影响并不大,相反,影响较大的是苏菲派。12世纪塞尔柱克王朝强大后,苏菲派托钵僧开始在中亚获得发展,起初在呼罗珊、吐火罗,后在河中地区得以广泛传播。13世纪始,蒙古人及后来的帖木儿王朝,为巩固其政权和实现扩张,支持苏菲派托钵僧,使其成为封建世俗贵族的“精神导师”,因而使苏菲派在中亚获得大发展,并成为伊斯兰教统治派别。14世纪布哈拉出现了最有影响的“纳合西班底教团”,布哈拉、撒马尔罕成为推行神秘主义的基地。苏菲派获得发展,还因为它向正统的逊尼派接近,在很多情况下公开承认正统派的教条,并得到正统派的宽容。此外,还与中亚突厥社会环境相适应,苏菲派的泛神论教义,与游牧民居多数和政治上的分散状况相适应,在游牧民逐水草而迁居的环境下,不可能建筑许多固定的清真寺,于是出现了苏菲派托钵僧建立的“霍纳科”(既是招待香客房屋,又是做礼拜、传教场所)。16世纪乌兹别克昔班尼人进入河中后,一方面接受苏菲派教义,另一方面又不完全丢弃传统的部落习俗原则,于是“产生出一种游牧部族统治的合法原则与教义的混合物”〔7〕。
无论如何,到19世纪前,在中亚的绿洲和城镇中,人们能遵守正统的逊尼派,遵守去清真寺作礼拜的教规和伊斯兰“沙利亚法”。而对人口占大多数的游牧民来说,支配人们精神的仍是伊斯兰部落习惯法。同时,另一种现象是,无论是逊尼派、什叶派,还是苏菲派穆斯林,常常能够在一个清真寺做礼拜,可见,中亚穆斯林在遵守教义、教规方面并不严格。
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对沙俄军事征服、民族同化政策的一种反抗,中亚突厥人中的民族意识开始萌发,伊斯兰教的作用倍增,伊斯兰的“乌玛”成了民族共同体的代名词。然而,伊斯兰“乌玛”民族共同体意识并未进一步发展,十月革命后中亚5个自治共和国的建立, 苏联政府后来开展的反宗教和无神论的宣传运动,使伊斯兰教的政治作用日渐降低,苏联政府“取消了构成穆斯林共同体的主要条件、法律制度、合法机构和财政基础,伊斯兰变成了单个人的宗教”〔8〕。
毋庸置疑,苏联时期一些过激的宗教政策和民族同化政策,使一些穆斯林产生了逆反心理,增加了宗教感情和宗教信仰。但是,这种对宗教的感情和信仰,更多地是把伊斯兰教看作民族文化的基础。伊斯兰作为民族文化基础,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体现在传统的生活习俗之中,如婚丧嫁娶、宗教节日、祈祷、礼仪、穿戴服饰等方面,是区别于其它民族、文化的主要标志。
四、在现代民族发展进程中,各民族国家的意识不断增强
十月革命前,中亚各突厥民族仍处于前资本主义形态,游牧的氏族部落制和封建宗法关系支配着人们的生活,各民族、部族的分散、离心倾向严重,人们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们中出现了朦胧的“乌玛”民族共同体意识,反映了各突厥民族来到了现代民族国家的门槛前。
十月革命后,在列宁、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和具体政策指导下,中亚各民族的民族进化与社会进步取得同步发展。1924年和1936年列宁、斯大林在调查中亚各民族语言实际分布的基础上,按地域划分建立了5 个加盟共和国,奠定了其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1917—1918年始,又召集、聘请专家,在各地方言的基础上,发展各国的书面交流语言、鼓励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报刊、文学、出版物、剧院和文化娱乐事业,促进了各突厥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民族意识的增长。20—60年代,苏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民族政策,对中亚各突厥国家的社会面貌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一、实行向中亚的移民政策。斯大林时期,曾因工业化、战争时期迁移少数民族等活动,向中亚迁移了大批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以及犹太人、日耳曼人。据1970年全苏人口普查显示,在哈萨克,俄罗斯人口占该国人口的比重为42.4%,乌克兰人占7.2 %,白俄罗斯人占1.5%;在吉尔吉斯,俄罗斯人占29.2%,乌克兰人占4.1%;在乌兹别克和土库曼,俄罗斯人分别占12.5%和14.5%,乌克兰人占0.9%和1.6%〔9〕,使各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二、 实现工业化,发展本民族经济。十月革命前,中亚没有现代工业,为此,在斯大林时期,在苏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中亚各国大力发展煤炭、钢铁、石油、冶金、机器制造、纺织、食品等工业,奠定了本民族的现代工业,到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工业产值在哈萨克占58.9%,吉尔吉斯占50%,乌兹别克占57%,土库曼占68.9%;三、发展各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通过开展扫盲运动,普及初等教育,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与高等教育,创办科研机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提高了各民族国家的文化水平,促进了社会进步。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亚各突厥国家的本民族意识不断增长,表现为:巩固了以共同的地域、多民族联合体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以丰富的自然资源、现代工业、经济长足进步的民族自豪感;以本民族的现代语言、教育科技为内容的民族文化意识;以本民族利益为出发点、加快民族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国家观念和意识。
几点结论
泛突厥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于奥斯曼帝国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它的实质和目的,是要“联合一切突厥语系各民族建立突厥国家”,将土耳其、俄国、巴尔干、中亚、阿富汗、伊朗、中国境内的“突厥人”统一起来。它强调突厥人的语言、文化、宗教、种族因素和历史认同感。
泛突厥主义能否在中亚新独立的各突厥国家的土壤里“扎根”,引起共鸣,最终建立某种统一的政治联合体?从中亚突厥诸民族的历史发展看,笔者认为这是不大可能的。
首先,从中亚突厥民族的构成看,历史上的“突厥”人,只是语言上的集合名词。11世纪喀拉汗朝的语言学家穆罕默德·喀什噶里在他著的《突厥语大词典》中,是以纯粹的语言学来界定突厥人的,其影响流传至今。而从血统上看,其民族成份是复杂的,并非一脉相承。在前伊斯兰时期的突厥人,仅指鄂尔浑碑文中提到的“九姓乌古斯”和汉文资料中的“十姓突厥部落”为主的东西突厥联盟。11世纪后,它不但包括了异姓突厥联盟,而且还包括了非突厥的回纥、黠戛斯等部族,以及原“塞种”的花剌子模、吐火罗部族和移居中亚的阿拉伯人、契丹人、叙利亚人、部分汉人〔10〕。蒙古人后,又融合了蒙古人、钦察人、鞑靼人及其各部族。因此,今天中亚地区的突厥诸民族,并非拥有共同的血统、共同的政治历史传统的民族共同体。
其次,由于历史上突厥王朝统一时间短,社会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因而,突厥社会缺乏凝聚力。而由氏族部落制繁衍派生下来的部族主义、民族集团性、地方主义等阻碍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政治上的统一。历史上,突厥人远未成为政治上的共同体,今后也很难重新统一起来。
第三,从宗教角度看,一方面,伊斯兰教在中亚扎根不深,它既没有像西亚国家那样的自上而下的伊斯兰机构和土耳其以伊斯兰教大法典官为首的教权阶层,也没有像西亚国家那样伊斯兰教与政权紧密结合的历史,因而伊斯兰教在中亚很难发挥聚集民族内部团结的政治功能;另一方面,作为民族文化基础和生活方式的伊斯兰教,它具有联系民族感情,加强与穆斯林世界联系的作用。然而,要利用伊斯兰教“乌玛”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样面临着内部的挑战。即使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者,它既担心利用宗教因素引起教派之间的争执,难于维持一致,也顾及伊斯兰教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以及伊朗的作用,而不重视强调伊斯兰教在联系民族感情方面的作用,强调种族因素,避开宗教因素〔11〕。
最后,从中亚各突厥民族国家的现代进程看,从建国起,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新的民族国家已经定型。各国经济的进步,民族语言、文化、教育科技的发展,进一步巩固了各国的民族自我意识。今天,在中亚各国,以追寻民族历史、民族英雄、复兴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强化主体民族地位”的寻根意识正在加强,因而泛突厥主义在中亚既会遇到官方的抵制,也会受到爱国主义的挑战。
注释:
〔1〕〔2〕〔10〕参见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4月版,第701、702、701页。
〔3〕〔4〕〔5〕[苏]威廉·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3~144、245、182页。
〔6〕[俄]H·罗塔里:《中亚是否爆炸》,《东欧中亚译丛》,1993年第4期。
〔7〕李玉昌译:《16世纪初中亚文化艺术和政治》, 《中亚研究资料》,1984年第4期。
〔8〕[法]埃莱娜·卡·唐科斯:《分崩离析的帝国》(郗文译),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228页。
〔9〕《苏联民族问题的历史与现状》(附录《苏联居民》), 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88—189页。
〔11〕贾库伯·M·兰都:《泛土耳其主义在土耳其》伦敦, 1981年版,第181页。
标签:突厥论文; 泛突厥主义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伊斯兰教论文; 中亚民族论文; 伊斯兰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伊斯兰建筑论文; 游牧民族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