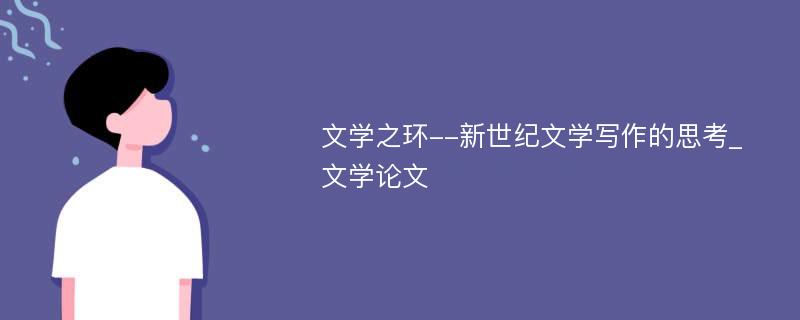
文学的年轮——有关新世纪文学写作的断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断想论文,文学论文,年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代的文学发展,都会遇到自己的问题,其呈现文学经验的方式,也会是多种多样的。新世纪的文学发展就有其非常独特之处。我想说的就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延续至今的文学写作中的年龄问题。以年龄来命名文学写作,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文学写作中非常突出的现象。“新生代”作家、“60年代生”作家、“70年代生”作家等等文学命名,虽然在意义的界定上有其朦胧含糊之处,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命名的目的是希望将一批作家的写作,与另外一些作家的写作区分开来,而这种区分的最终结果,是要确立一些新出现的文学家的文学经验的合法性地位。一批20世纪60年代后期及70年代出身的年轻作家,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当代文学中登场亮相。他们的写作声誉虽不像“知青”作家那样如日中天,但对当代文学的冲击力是人们所可以感受到的。特别是从写作的角度讲,所谓新世纪的文学写作,将是这些“新生代”作家、“60年代生”作家、“70年代生”作家队伍的不断扩大,因此,新作家的文学写作状况更应该值得我们关注。
一
回想起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年龄有关的文学写作大概起始于陈染、虹影的作品。这两位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作家,以非常个性化的写作,突破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写作模式。“新时期”文学写作模式的最基本特征,我以为,可以用寓言写作来概括。所谓寓言写作,是指作家在写作过程中,有意无意要将个人的文学经验置于国家、民族、社会意识形态框架之中,并以占据其中的某一空间,传递意识形态的意义,作为写作者的基本使命。以这种方式进行写作的作家,常常会不知不觉地要求自己扮演某种社会角色,充当社会的代言人。这种写作方式从中国文学史的经验看,确实有着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现实基础。因此,寓言写作不仅构成了当代文学写作中最稳定的写作方式,而且也成为人们判断文学作品艺术水准的基本尺度。但除了这种寓言写作方式之外,文学写作是否还存在别的方式吗?这从理论上讲似乎毫无争议。甚至是那些最恪守教条的人,都会承认文学写作方式的多样性。而事实是,一旦涉及到具体的作家创作,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20世纪90年代初陈染、虹影等作家作品开始出场时,王蒙就写过《陌生的陈染》,这与其说表达了一种文学上的宽容态度,还不如说体现了基于年龄差异而对社会、人生的不同感受方式。无论是陈染的《私人生活》或是她的其他作品,所表现的个人经验应该是明确的。用一个不太确切的概念来表示,可以说都是涉及私人生活的。王蒙们之所以感到陌生,我想主要还不是作品表述上的问题,而是对这种以关注私人生活为主的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感到疑惑。将一个人的内心生活的所有困惑,毫无保留地抖露出来,而这些所谓的内心困惑,既见不到外在直接的社会因由,也看不出苦闷的价值指向,而是平平常常降落在作品人物身上,像风像雨像雾一样,说来就来,说去就去。这样的小说描写,对于习惯于现实主义文本阅读和对现代主义仅仅保持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内心苦闷的理解维度中的人来说,的确会在理解上感到一种陌生与隔阂。为什么要这样沉湎于自己的私人生活呢,广阔的社会现实中不是有许多值得关注和表现的问题吗?的确,所有这些疑虑都有自己的理由,但是,对一个写作者而言,她也有自己的理由。为什么我自己的内心风暴就不值得关注呢?对于那些人们普遍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对一个具体的写作者而言,未必一定显得如此重要,更何况对于新一代成长之中的普通写作者,社会这一概念是再稀松平常不过的了。自我与社会根本不是一种二元对立棱角分明的关系,我的感受、我的内心体验,当然属于这个时代和社会,否则社会又为何物?新一AI写作作者所理解的社会,与以往的“右派”作家、“知青”作家那种偏重意识形态含义的社会的概念是有差距的。这种差距在我看来,主要还不是由观念造成的,而是阅历和个体经验之间的差异造成的。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在“右派”作家、“知青”作家和那些“新生代”作家、“60年代生”作家、“70年代生”作家的人生记忆中,构成人生经验的历史成分有多少是相同的呢?如果一定要从求同原则来要求这些作家的个人经验的话,我想,“右派”作家与“知青”作家之间的人生感受,有着更多的亲缘性。“反右”、“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批林批孔”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构成了“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对自己人生成长经验的最直接也是最深刻的记忆。所以,偏向社会意识形态含义的接受和理解,对这些作家而言,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而且,中国社会的现实矛盾也显示着这样的理解是有着现实意义的。相比之下,一批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及70年代出生的写作者,他们的人生经验中,那种政治性冲突的残酷体验和经历就要弱得多。他们的个人成长是在一个相对平和的学校教育环境中完成的,既没有“上山下乡”的体验,也没有“批林批孔”的冲击,对他们而言,成长中的最直接压抑,是来自升学和择业等方面的,有时自己内心的困惑比外在的压力更大。这是不同年龄的社会群落在成长过程中总体经验之间的差异。所以,像陈染这样一批写作者选择私人生活作为文学的着眼点,未必没有价值,但对于许多习惯于将社会与个人作为二元对立关系来理解的人们而言,多多少少总会觉得这样的文学表现似乎缺少了什么,或是显得不够所谓的大气。这也就是王蒙所感叹的“陌生的陈染”的原由了。
二
其实,陈染也好、虹影也好,在年轻一代的写作者中都还不是写作中的异数。她们对私人生活的表达还是小心翼翼,有所选择的。在她们的作品中,作为新一代人的情感生活标记,想象的成份远远大于行动,无论是陈染的《私人生活》还是虹影的《康乃馨俱乐部》,人物活动都是锁在冥想的囚牢之中,很少体现出现实的活动能力。所谓成长之中的心理苦闷,特别是性苦闷,常常包裹着性别的外衣曲折道出。所以,缺乏这种成长心理体验的年长者,倒是乐意将她们的作品当作类似于“社会问题小说”来接受,从中体会“新生代”们所遭遇到的当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压抑,而很少会注意到这些作家其实是在诉说自己成长的故事。相比之下,后来的所谓“断裂”派作家就让不少年长者感到吃惊和难以理解。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末冠名为“断裂”的文学调查是那些20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写作者在当代文学中刮起的红色旋风。差不多所有那些前代作家奉若神明的教义和准则,在新一AI写作作者眼里统统变成了阻碍他们成长的“老石头”和“遮羞布”。那些在陈染、虹影作品中只能靠想象和心理幻觉软弱地生活的人们,在韩东、朱文等“断裂”派作家笔下充满了活动的张力。朱文的《我爱美元》、《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韩东的《在码头上》、《我的柏拉图》体现了一种新生代的行动方式和生活状态。作品中的人物差不多都是学生出身,在没有确定自己最终的职业之前,他们在社会上飘零。这种无所依傍的飘零生活,让他们感受到自由和解放,但也常常无聊寂寞。不过这种寂寞无聊并不见得毫无疑义,只是意义不明,或意义还不太清楚。相对于现实生活中那些目标明确、苦苦奋进的人来说,“断裂”派作家笔下的人物没有一个愿意进入这种生活状态。他们是现代竞争生活之外的闲者,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弹性,谁都不知道他们将来会做什么,但他们都是靠自己的知识和本领吃饭,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流浪汉,而是浮现在时代新生活上的点点浮萍,尽管数量不多,但有自己的色彩和处世原则。所以,当一些人把他们当作“问题少年”,认真地以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学审美方式来开导他们时,得到的回报常常是一阵奇怪的笑声。这笑声包含着这些青年人对自己生活的自信和对劝导者的劝导:不要总以为别人的精神世界是处在危机之中,很难说谁的精神更危机呢。的确,在这些成长之中的写作者看来,生活并不是按照现有的价值尺度无限伸展开去的轨道,每个人只是将自己的生活纳入到这种既定的轨道中而已。对这些年轻人而言,他们宁愿相信生活是未知的,并且是一个有待充实的崭新空间。就如韩东所说的“在一个体制下生活,有人管着你,这个很可怕,还有什么上级下级,有领导,还要开会,还要守纪律,要为一些非常虚无的事情浪费生命。这些事情我觉得和我的天性不相容。”(引自汪继芳《“断裂”:世纪末的文学故事——自由作家访谈录》第211页,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4月版)开会、上班下班、守纪律,这些在今天已被制度化,成为差不多所有社会成员日常生活内容一部分的东西,在这些年轻的作家眼里,只不过是浪费生命的愚蠢举动而已。他们愿意尝试一种不需要开会、没有上下级关系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尝试,可能对那些老于世故的人而言,想都不用去想,但新一AI写作作者不仅向往这样的生活,而且偏偏用作品人物的故事,展示了这种生活的现实可能性。新作家们有才能,见解和学识并不在那些规劝者之下。作品人物之所以带有那种没有着落的真实感,并不是这些生活是虚假的,而是人们被世俗生活压抑得太久而丧失了对生活具有多种可能性的想象。通常人们所谓的实实在在的生活,其实不过是认同现实的代名词罢了。面对沉闷的现实,能够不按部就班、不循规蹈矩亦步亦趋,这是需要勇气的。只不过我们习惯于一种单一的抗争模式,对其他种种不合常规的行为和处世方式难以认同和接受罢了。
将“新生代”作家、“60年代生”作家、“70年代生”作家写作推向社会前台的,要算上海的卫慧与棉棉了。在这之前,年轻一AI写作作者的写作通常是潜在的,他们的作品只能在一个狭小的同道范围中流传。人们感受着他们的存在,但那种突破性的冲击还没有降临。只有到了卫慧、棉棉手里,笼罩在一批人身上的铁笼才被彻底揭去,他们再也不是无名的写作者,而是可以堂堂皇皇来显示自己的写作才能了。这种文学上的突破,我想是不少年轻写作者所可以感受到的。在这之前,文学期刊和国家出版机构,很少为年轻的写作者留出像今天这样多的版画和机会,而这之后,年轻写作者成为各文学期刊和出版社编辑追逐的对象。因此,现在再纠缠于卫慧、棉棉的作品是不是有价值,她们的写作能力如何等等问题,都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毫无疑问,她们是有写作才能的,她们的作品差不多都刊发在那些严肃的文学刊物上。文学写作应该怎样,那些编辑并不比批评者知道得少。至于她们今后的写作如何,谁也不知道,而且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卫慧、棉棉以及她们同龄人的写作从此都有了自己的生长空间。你可以不喜欢或是不赞同她们(或他们)的作品,但难以取消她们的存在。事实上,年轻的写作者所传递的生活经验,有着前几代作家创作所难以替代的地方。我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已经陈述过,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后的出生者,其成长经验从大的历史背景来说,与1949年前的现代作家、经历20世纪50年代生活的“右派”作家及经历60年代“文革”和“上山下乡”生活的“知青”作家,有着很大的经验差异。我不排除经验之间对话和沟通的可能,但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应该彼此尊重对方经验的存在合理性。特别是对于那些早已获得社会声誉的写作者,当自己的人生经验已经通过各种文本确定下来,并获得成功的情况下,应该有雅量和宽容的态度,对待那些正在成长之中且尚未完全定型的生活经验的文本表现。在我看来,20世纪60、70年代生的作家个人经验,就属于那种尚未被文本化的文学经验。当代文学中,“右派”作家对自己的生活经验有成功的文本加以确认,“知青”作家也有属于自己经验的文本。但20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作家,他们的人生经验至今为止还没有较为成功的文本加以表现,这不是说他们缺乏文学才能,而是需要经验的沉积和各种写作方式的尝试。事实上,前几代作家又何尝不是经过了这样一个成长周期呢?假如当初王蒙因为写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就立马遭到封杀,假如贾平凹写了《废都》后再也不许期刊杂志出现他的名字,或者王安忆因为写了“三恋”而遭受严厉的处罚,甚至不许批评家评论这些人的名字,我想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很有可能就此失去很多光彩的东西。可以说,王蒙最显才华的创作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王安忆等是在20世纪90年代,假如剥夺了一个年轻作家写作实践的各种尝试的可能,不允许年轻作家有一个成长的发展周期,而要他们一开始就创作出某些人确认的所谓“经典”,我想这样的要求未免太荒唐了吧。
三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大批年轻的写作者的文学作品开始出现,其影响愈到后来愈大,要不是一些人为的因素在2000年的作梗,我想发展的势头在今天会更大。为什么新的文学写作的突破,会选择一个新旧世纪的交替之际进行呢?在一些人看来,时间的自然进程与文学的发展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但我以为未必全对。因为历史在自然时间过程中多多少少总会上演一些人生的悲喜剧,尤其对于转型之中的社会而言,历史经验在时间的过程中将增添新异的内容。对那些20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写作者而言,整个20世纪90年代这10年间的写作尝试,是他们由原来的模仿别人的写作,转向对自己成长经验的陈述的过程。我们不妨看看那些20世纪60、70年代生的文学写作者所留下的岁月痕迹。当他们开始自己的文学尝试时,中国文坛上最具有所谓文学价值的作家作品,是一些形式感非常鲜明的作家作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先锋派作家的作品。这些先锋派作家如果按照年龄来划分的话,照理大部分都可以归入20世纪60年代生的作家队伍。但事实上,先锋派是自成一体的过渡性作家,也就是说,从作品所展示的经验方式及这些作家所关注的问题看,基本上延续了“新时期”的文学传统,即这些先锋派作家在写作时不是以自己的经验为先,而是首先将写作的焦距调整到社会关注的“反右”、“文革”等热点问题上,然后搅尽脑汁考虑叙述形式上可以有什么新的变化。所以,读先锋派作家的作品,你会感到非常奇怪,怎么这些年岁并不太大的写作者都对以往的历史这么感兴趣,他们笔下更多的是民国时期的社会风俗以及“反右”、“文革”时期的奇闻轶事,除此之外,对属于他们自己年龄阶段发生的事件和经验都看得很轻。在理论上,先锋派对自己的写作有一种辩护,认为经验可以移置和转移,也就是说,作品的故事可以摆在民国时期或“反右”和“文革”背景下展开,但人物的情感经验可以是现在的。就像苏童写《红粉》那样,背景可以是民国时期,但人物的心理状态是不少今天的普通人所可能具有的。对具体的作家而言,这种写作方式当然是自己的一种选择,但假如同一批写作者几乎都选择了这样的写作方式,我以为这样的选择多多少少值得反省。在我看来,先锋派这样的选择与当时他们所处的写作氛围有关。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正是王蒙等一批“右派”作家写作的巅峰时期,“知青”作家们的写作声誉也在蒸蒸日上。由这样的作家、编辑和读者构成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当代文学世界,影响着那些试图在文学写作上有所作为的先锋派作家的写作。他们只能按照上述这些作家作品的经验和表述对象,来进行写作,唯一的变化是在小说的叙述方式上,不能重复当时这些声誉日隆的作家作品,否则,先锋派就不可能有自己的立锥之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题材问题上,先锋派几乎没有遭遇过前代作家、批评家的过多指责(除了苏童的《妻妾成群》等作品被认为带有男性中心的批评外),因为这些表述对象都是现有的文学长廊巾被无数次复现过了的,人们不会有太大的争议。先锋派在认同这样的题材的前提下,将自己的生活经验嵌入在历史的叙述之中。这样的作品,在一些年岁渐长的过来人看来,虽觉得不怎么像自己的经验,但也不是离谱太远。不像他们后来见到的“新生代”作家写作来得那么触目,那么不守规矩。所以说“新时期”作家们所做的事以及大的文学格局,到先锋派手里基本可以告一完整的段落了。团为文学写作所传递的这两代人的生活经验以及经验的变形,不可能再有更宽裕的发展空间容纳新的文学写作者来发挥。在那些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在中国文坛上的年轻写作者的最初写作中,可以看到,他们一开始确实是模仿着先锋派的笔调和叙述方式,这些模仿的痕迹有些人至今都没有蜕尽,成为他们写作的“行之不远”的历史胎记。这样的模仿并没有给这些新写作者的写作带来发展的机遇,而是变成了他们写作能力平庸的见证。转向成为一种急迫。20世纪60、70年代人自己的生活经验在写作中被渐渐凸现出来。站在新世纪的今天,可以看到,从陈染、虹影,到“断裂”派乃至后来卫慧、棉棉以及浩浩荡荡的年轻写作者的写作,基本上是在自己的经验世界中写作。他们已不需像当年的先锋派那样靠讲述民国故事来晦涩地表现自己的生活感受。那些20世纪90年代成长起来的写作者,将自己的成长经验作为作品表述的主要对象。为了从人生经验上区别于“右派”作家、“知青”作家和先锋派作家,以年龄的方式给自已的写作定位,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的文学写作的生长特点,谁能说这样的命名没有自己的合理性呢,谁能够说文学写作只能按照既定的经验和方式来概括和命名呢?在我看来,一种命名,凸现的是一种写作的特色,“新生代”作家、“60年代生”作家、“70年代生”作家的命名,强调的是这些新作家作品的文本经验,主要是以这一年龄段落的人的成长经验为依据,其表现对象和审美情调也有着年龄的特点,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并不是说,以后的文学发展一定都是按年龄来命名和区分的。随着这些20世纪90年代成长起来的文学写作者的成熟,年龄问题会在创作中慢慢淡化,就像“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知青”作家也曾一度热衷于“代沟”问题一样,随着他们各自创作的成熟,个人的写作会成为他们新的追求目标。事实上,在新世纪的今天,这种趋向正在露出先兆,在2000年至2001年上半年间,推出的如刁斗、张生、毕飞宇、东西、鬼子、西飏、朱文、韩东、鲁羊、吴晨骏、祁智、丁天、李洱、丁丽英等人的作品单集看,他们的写作正从年龄的界面上不断向个人的经验方向扩展。读他们的作品,你可以感受到另一种成长的经验,而这些经验并不像一些人所调侃的显示着“后文革一代”的苍白人生,相反,这是一些丰富多样的人生成长经验,至少在一个多元的文化时代,构成了一种难以替代的经验叙述。所以,不能因为年轻的写作者展示了个人的成长经验,而这种经验又是违背年长者的既定期待,就要被判为“另类”,遭遇贬抑和封杀。当一些人以为只有采取这样严厉的措施,方才显出文学的纯正品味时,我看到的景象恰恰相反。
2001年5月于华东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