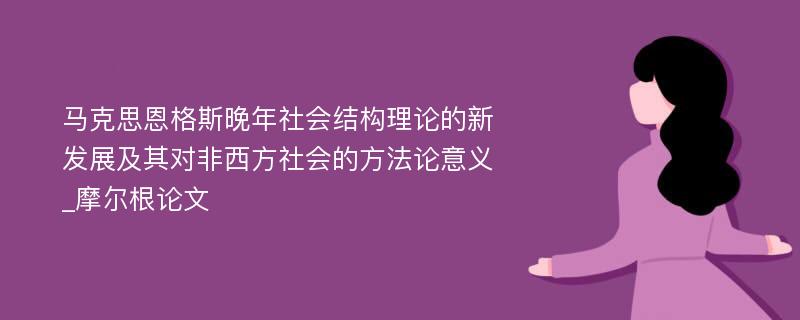
晚年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结构理论的新发展及其对非西方社会的方法论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方法论论文,马克思论文,社会论文,晚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结构理论的探索经历了早期对“人体”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的解剖,到晚年批判吸取摩尔根等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注重对“猴体”史前社会进行人类学解剖的过程,强调指出马恩晚年克服了早期分析史前社会的理论局限,同时运用人类自身生产和社会生产两种生产理论,将史前社会特定的范畴系统与唯物史观社会结构一般理论加以辩证综合,来考察史前社会(特别是其后期“亦此亦彼”阶段)社会结构的演变,体现了马恩晚年对社会结构理论的新发展。文章并揭示了这一新发展对非西方社会结构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社会结构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解开“历史之谜”、创立唯物史观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他们对社会结构理论的探索经历了一个从对“人体”政治经济学的解剖到对“猴体”人类学解剖的过程,而后一个解剖体现了晚年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结构理论的新发展。深入研究这一新发展,揭示其对非西方社会的方法论意义,对于正确把握唯物史观社会结构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社会结构的“人体”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的解剖,形成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其总和构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其相互关系的唯物史观社会结构理论。但是,作为“人体”的资本主义社会(甚至包括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私有制社会)中的社会结构,毕竟只是人类社会漫长历史的特殊表现形式。因此,要科学地把握唯物史观社会结构理论在完全不同于现代文明社会的史前社会中具有怎样的表现形式,只有通过对史前社会的“特殊逻辑”——即特殊的社会结构进行具体的分析,才是可能的。因为在史前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极端低下,既没有商品生产,也没有商品交换,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不是经济因素,而是自然(血缘和地域)因素。如何把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结构的一般理论运用于史前社会,确实是摆在马克思、恩格斯面前的一个难题。
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唯物史观社会结构理论形成时期,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必须对人类早期社会结构作出自己应有的研究。他们从人类社会历史就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历史、以及历史的出发点是从事生产活动的人的观点出发,有力地驳斥了把“宗教的人”当作人类社会全部历史起点的“原人”、和认为“凡是在神学、政治、文学的谬论不能立足的地方,就没有任何历史,那里只有‘史前时期’”[①a]的资产阶级学者的错误观点,指出必须把人类历史推进到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前直到人类诞生之初,把唯物史观社会结构理论的研究与对人类早期生活的研究结合起来。他们当时通过研究认为,人类社会的第一种所有制是与生产不发达阶段相适应的“部落所有制”,在这种所有制中,“社会结构只限于家庭的扩大:父权制的酋长、他们所管辖的部落成员以及奴隶。隐蔽地存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只是随着人口和需求的增长,随着同外界的往来(表现为战争或交易)的扩大而逐渐发展起来的。”[①b]在他们看来,这种所有制产生的基础是以家庭中自然产生的分工和社会分裂为单独的、互相独立的家庭这一点为基础的。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分配(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因而也产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状态和原始形态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孩子是丈夫的奴隶。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虽然已认识到人类最初的所有制是以“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为其第一个前提,在“原始共同体”中劳动主体和客体是“天然统一”的,但总体上这一理论尚未出现重要突破,理论上还存在着局限。这是由史前社会材料极度缺乏和人类学对史前社会的研究还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所造成的。恩格斯后来曾对此感叹道:“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②b]解剖史前社会的“科学手术刀”——两种生产理论,当时尚未形成。
然而,唯物史观社会结构理论的建构不能等到人类学对史前社会研究有了重大突破之后再去进行,因为正在兴起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迫切需要科学世界观的指导。在研究史前社会的社会结构的必要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不得不用分析“人体”资本主义社会时所形成的社会结构理论的范畴及其相互关系,去规定史前社会的结构,用“人体”的解剖去取代“猴体”的解剖。“人体”阶段社会结构一般理论一旦运用于史前社会,出现了以下局限:
第一,把父权制个体家庭而不是氏族组织看作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社会组织,认为其后的社会结构仅限于这种父权制家庭的扩大,也就是说个体家庭在前,氏族在后,后者只是前者的扩大和集合;第二,把家庭中的奴隶制看做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所有制,“但就是这种形式的所有制也完全适合于现代经济学家所下的定义,即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权的支配”[③b]。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马克思为了从逻辑上建构人类社会历史从公有制社会向私有制社会的过渡,从“亚细亚生产方式”中抽取出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一要素,把这一生产方式作为人类社会历史的起点,但亚细亚社会中的国家以及中央专制主义,显然是与史前社会无私有制、无国家、无阶级的情况不相符的;第三,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统一的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结构理论的范畴系统套在史前社会的社会结构上。然而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史前社会中,是人类自身生产而并不主要是物质生产,成为其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血缘亲属关系而并不只是生产关系,成为整个社会的基础;其上层建筑则是亲属制度。所以,只有把亲属制度归结为血缘亲属关系,把血缘亲属关系归结为人类自身的生产,才能对史前社会的社会结构作出科学的分析。当然这并不是说,生产关系在史前社会中不起任何作用,相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缓慢发展,生产关系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最终取代了血缘亲属关系而成为整个社会的基础,同时上层建筑也相应发生变化。所以,分析史前社会的社会结构必须具有上面提到的两套范畴系统,并使之辩证地结合起来,共同构成唯物史观社会结构理论的基本要素;第四,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剖析史前社会的社会结构的基本组织和基本关系,把到目前为止的一切历史都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就使公有制的史前社会与私有制社会在社会结构上质的区别和对立显得不甚清楚。
上面四个局限性,表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理论问题上曾经经历的两个困惑:
第一个困惑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资产阶级学者霍布斯、卢梭等人在反对封建神学历史观的过程中,从永恒不变的抽象人性出发,猜想人类的初始阶段是一个平等、自由的非私有制阶段,提出了著名的“自然状态说”。这一学说虽然是唯心史观和虚幻猜测的,但私有制并非与人类一起产生这一思想,却具有极大的合理性,在逻辑上给马克思、恩格斯以有力的启迪。马克思一方面指出了这一学说在史料上的虚构性:“18世纪流行过的一种臆想,认为自然状态是人类本性的真正状态”[①c];另一方面,吸取了这一学说关于私有制来非私有制的合理思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从“真正人的社会”(没有私有制、劳动异化、阶级、剥削等)、到“异化的社会”、再到扬弃异化向“真正人的社会”复归的依次更替。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又取消了“真正人的社会”的说法,认为当时存在着的是奴隶制的“部落所有制”,这种所有制与奴隶社会的奴隶制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的差别。在19世纪40年代,人类学对史前社会材料的搜集至多只是一些片断的、未加科学分析的事实,描述的只是其中个别方面的局部情况。史前社会材料的缺乏,使马克思、恩格斯不得不放弃了当时无法证实的作为人类历史起点的“真正人的社会”这一提法。
第二个困惑是,在19世纪40年代,由于材料的缺乏,马克思、恩格斯未能区分史前社会和奴隶社会的本质区别,把唯物史观社会结构理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范畴系统套到史前社会的研究,认为作为人类历史第一种所有制形态的“部落所有制”中已隐藏着奴隶制,两者只有量的区别,没有质的区别,进而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史前社会。由此,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出了“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②c]的结论。在总结1848年欧洲大革命经验的过程中,事情似乎出现了转机。马克思在1852年致约·魏德迈的信中谈到自己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新贡献时说:“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③c]这在逻辑上必然推导出在阶级存在以前一定存在一个生产极不发达的无阶级阶段。但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关于“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论断,是针对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关于“阶级存在永恒论”而言,意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激烈化“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产阶级社会的过渡”;而并不是针对以前有一个无产阶级社会阶段而言。也就是说,应当完整、系统、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思想发展的全过程。
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结构理论的局限,决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史前社会结构理论的研究必然由对“人体”政治经济学的解剖转入对“猴体”人类学的解剖,以进一步发展自己的这一理论。
二
晚年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社会结构理论的新发展,是他们通过对史前社会结构的“猴体”人类学的解剖,运用两种生产的理论,揭示人类自身生产在史前社会的决定作用,阐明与史前社会和文明社会交替过程同步发生的物质资料生产对人类自身生产决定性的取代,以及它们之间的辩证过程。体现在社会结构理论的发展上,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科学地揭示了史前社会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部分)及其相互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以两种生产理论为方法论,修正了以前把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统一的社会结构理论套用于史前社会的理论误差,具体地剖析了史前社会结构的三大部分——人类自身的生产、血缘亲属关系、亲属制度以及两对矛盾——人类自身的生产与血缘亲属关系以及基础(血缘亲属关系)与亲属制度的矛盾,从而为研究史前社会的结构设立了一套新的科学的范畴系统。
在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当时的人类学研究已开始取得较大进展。他们批判地吸取了摩尔根关于原始社会发展史上的合理思想,纠正了理论界以往囿于传统的下述误见:(1)把父权制家庭看作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社会组织;(2)认为社会结构是这种父权制家庭的扩大而不是氏族组织;(3)个体家庭在前而氏族在后(后者是前者的扩大和集合)。
摩尔根以美洲易洛魁人对偶家庭与其流行的亲属制度之间的矛盾为突破口,发现了存在于夏威夷群岛上的与这种亲属制度相符合的普那路亚家庭;然后,又从普那路亚家庭与亲属制度之间的矛盾,发现了比之还要原始的最初的群婚制家庭——血缘家庭;最后指出了在血缘家庭之前的是原始的杂乱性交状态;而所谓父权制家庭和一夫一妻制家庭不过是史前社会瓦解时的产物,在它之间还存在着多种家庭形式。不仅如此,他还运用史前社会家庭中发展的史实,对之作了进一步论证,说明了在血缘家庭和普那路亚家庭中不可能存在父权。普那路亚家庭把姊妹及其子女和女系后裔结合于一个氏族之中,氏族由此成为社会制度的单元组织;对偶家庭逐渐由这种状况中发展出来,而父权的萌芽也就与之同时产生。这种权力的发展在开始时是微弱的、不定的,然后开始稳步增长,随着新的家族因社会的进步而愈来愈含有专偶制的特色,这种权力也就不断地得到增强。当财产开始大量产生和想把财产传给子女的愿望使世系由女性改变为男性下传时,父权的真正基础才第一次确立起来。
以此为立论的依据,摩尔根正确地指出:按起源来讲,氏族比一夫一妻制家庭和父权制家庭以及对偶制家庭要早,它产生于普那路亚家庭,母系氏族早于父系氏族。所以,氏族不仅不是个体家庭的扩大和集合体;相反,它的产生出现还远远早于个体家庭。摩尔根还通过对美洲、希腊、罗马等民族的研究,揭示了氏族作为史前社会社会结构基本组织的普遍意义,说明了直到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时为止,甚至再往后一点,是一切野蛮人共有的制度。
马克思在晚年“人类学笔记”中同意并吸取了摩尔根的这一思想并加以深化发展。在关于摩尔根的笔记中,当谈到父权制家庭时,马克思说:“以前的一切大学者,包括亨利·梅恩爵士”都认为希伯来式和罗马式(父权制家庭)是最古老的家庭形式,认为是这些家庭产生了最早的有组织的社会[①d]。这就以否定性的口气吸取了摩尔根的这一观点。马克思以妇女从属于男子并不是自古就有的为论据,反驳把父权制家庭视为最早家庭形式的不正确观点,他说:希腊“对奥林帕斯山的女神们的态度,则反映了对妇女以前更自由和更有势力的回忆。”[②d]在关于梅恩的笔记中,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摩尔根这一思想,他说:“梅恩把他的‘家长制的’罗马家庭作为事情的开端”,“愚蠢的约翰牛的主要的心爱理论,醉心于自古以来的‘专制’”。[③d]他还针对梅恩用爱尔兰家庭的划分作为自己主观臆想的父权制家庭产生过度的论证的做法,讥讽地说:“由此产生梅恩的一个伟大思想:在爱尔兰式的家庭划分的背后,乃是patria potestas(父权),实行划分的基础。”[①e]马克思还针对梅恩在时间上无条件地把个人财产看作是父权制家庭中维护家庭的地位和权威主要条件的不正确观点,把父权制家庭限制在“仅仅是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已远非上古”[②e]。
在科学剖析原始家庭发展史的基础上,马克思正确地揭示了氏族的起源、实质及其作为史前社会社会结构基本单位的重要作用,科学地解决了个体家庭与氏族的关系。在1879—1880年写作的科瓦列夫斯基笔记中,马克思开始注意到氏族作为史前社会基本单位的普遍意义,他摘录了1879年莫斯科版的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的第一册中的有关论述。在摩尔根笔记中,马克思在谈到氏族起源和本质时说:“氏族必然从杂交集团中产生;一旦在这个集团内部开始排除兄弟和姊妹之间的婚姻关系,氏族就会从这种集团里生长出来,而不会更早,氏族的前提条件,是兄弟和姊妹(嫡亲的和旁系的)已经从其它血亲中区分出来。氏族一旦产生,就继续是社会的单位,而家庭则发生巨大变化。”[③e]针对英国历史学家、《希腊史》作者罗特把氏族看作是家庭集团或“联合家庭”的错误观点,马克思更进一步指出:格罗特说希腊人的社会集团的基础是“户宅、炉灶或家庭”,这是荒谬的,因为在史前社会中,每一个家庭,不管是古老或不古老,都是一半在氏族之内,一半在氏族之外,丈夫和妻子分属不同氏族。这就是说,氏族早于对偶制和专偶制家庭之前,产生于普那路亚家庭,血缘家庭也早于氏族,但家庭不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要素或部分,而氏族才是原始社会的基本单位。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是极为深刻的。在史前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以家庭形式的变化为线索,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与其说是生活在家庭中,不如说是生活在社会中;因为那时存在的所谓家庭不过是就传统和习惯所允许的男女婚配的一定范围而言,夫妻双方并不生活在一个集团中。恩格斯后来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对马克思这一思想作了更为详尽的论述,并加以明确的概括[④e]。
马克思进而在更深层次上,说明了氏族作为史前社会的基本单位是由血缘亲属关系决定的,胞族、部落、部落联盟都是血缘亲属集团,它们是在氏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作为氏族制度的不同环节面靠血缘的纽带来维持。在关于梅恩的笔记中,马克思在批评梅恩用存在于印度的由血缘关系组成的家庭取代氏族的错误观点时说:“这表明氏族是一个多么不为梅恩所注意的事实!”[⑤e]“梅恩先生,作为一个呆头呆脑的英国人,不从氏族出发,而从后来成为首领等等的家长出发”[⑥e]。在关于拉伯克的笔记中,当拉伯克为很多处于较低阶段的部落中盛行一个男子的继承者不是他自己的子女而是姐妹感到奇异时,马克思写道:“可是那样他们就不是那个男子的继承者;这些文明的蠢驴摆脱不掉他们自己的旧框框”[⑦e];拉伯克“对基础,即存在于部落之内的氏族一点也不了解”[⑧e]。恩格斯后来谈到马克思这一思想时加以精辟的概括:“后来对人类原始状态的透彻的研究,使作者(指马克思——引者注)得出结论:最初不是家庭发展为氏族,相反地,氏族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自然形成的原始形式。由于氏族纽带的解体,各种各样家庭形式后来才发展起来。”[⑨e]
(二)科学地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人体”政治经济学的解剖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社会结构一般理论对于分析把握史前社会的社会结构及其演进仍然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
就横向静态上看,根据唯物史观两种生产理论,在史前社会中,当人类刚刚从动物界脱离出来的时候,无论就人对自然的关系还是就人们互相间的关系而言,物质生产不可能是起决定性作用的,生产和生产关系不可能是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关系。虽然在一般意义上,只要有物质生产,人们互相间的关系就不能不具有生产关系的性质,但只有当人们赖以生活的物质资料主要由人们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来并加以控制而不是依赖于自然界的“恩赐”时,那种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才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中起决定作用。所以,在史前社会的社会结构中,人类自身的生产是决定性的生产和血缘亲属关系是决定性的社会关系,而建立在作为其社会基础血缘亲属关系之上的只能是亲属制度。
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在史前社会的社会结构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因素是客观存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异常重视摩尔根关于“生存的技术”对史前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的思想,认为这和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思想是一致的,因为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扩充是人类自身生产发展的基础。
就纵向动态演进上看,从人类刚刚由动物界脱离出来开始,到形成人们自己劳动所创造的社会为止,必然要经历一个极其漫长的史前社会。在这个漫长的社会中,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其社会结构也在多大程度上打上自然的烙印。所以,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人们相互之间的狭隘关系,所谓与一定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以及以这种关系为社会基础及其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社会结构,是人们在自己的劳动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人们在通过劳动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资料的同时,也生产着自己的生产关系和创造着树立在其上的上层建筑。随着历史的发展,在史前社会由人类自身生产所决定的以血缘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中,劳动生产力日益发展起来了,与此同时,私有制、交换、财产差别、使用和占有他人劳动的可能性也出现了,所有这些新的社会结构的要素日盛一日地得到发展,不断迫使旧的社会结构组织适应新的变化,直到两者不相容最后导致一场彻底的变革为止。以血缘亲属关系为基础的旧的社会结构,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形成的各社会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由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组织为国家的新社会取而代之。组成国家的基础单位已不是以血缘亲属关系为纽带的氏族,而是地区团体了。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受生产资料所有制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地开展起来。正是这样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天为止的全部文明历史的内容。
这样一来,在这两种社会结构互易其主次地位的过程中,必然存在一个错综复杂的中间阶段。唯物辩证法要求在区别中看到联系,在对立中看到统一,更看到这种矛盾转化过程中“亦此亦彼”阶段的复杂性:“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①f]。这就决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人体”政治经济学的解剖中所形成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相互关系的唯物史观社会结构一般理论对史前社会社会结构的研究仍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在“亦此亦彼”的中间阶段,必须运用人类自身的生产、血缘亲属关系(社会基础)、亲属制度及其相互关系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及其相互关系两套社会结构的范畴系统,着眼于它们之间在矛盾中所处地位的转换,才能对之作出科学的分析,揭示其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
马克思、恩格斯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们着重从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血缘亲属关系和生产关系双方地位转换的视角,以社会分工的发展为基础线索,运用两套社会结构的范畴系统并使之辩证地结合起来,把它们看作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来剖析史前社会特别是其后期“亦此亦彼”的中间阶段社会结构的演变,阐明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这一研究思路是颇为辩证深刻的。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沿着马克思晚年对“猴体”人类学解剖所形成的这一思路,在横向静态和纵向动态的统合上,对马克思的上述思想作了完整、准确、系统的表述,说明了只有同时运用唯物史观社会结构一般理论的范畴系统和史前社会特定的范畴系统来认识史前社会,才能完整地揭示其社会结构各个构成要素的性质、特点及其相互关系。
三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史前社会人类学的解剖过程中对唯物史观社会结构理论的新发展,不仅对研究史前社会社会结构奥秘、而且对于其他各种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特别是非西方社会的研究也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原因是这些社会形态都属于“猴体”,而在对“猴体”的研究中,史前社会是最早的原生的“猴体”。随着财产关系的发展史前社会解体以后,血缘亲属关系在次生的“猴体”的社会结构中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不会随之消退,而是继续残留其中,并和新的社会结构的构成要素长期共存下来。马克思在谈到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时指出:“它们或者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或者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它们存在的条件是: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适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①g]所以,对其他“猴体”社会结构的研究必然要以对史前社会的社会结构的科学把握为前提和出发点。
这一点,对于非西方社会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和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在马克思看来,正如地球的太古结构或原生结构是由一系列不同时期的沉积组成,史前社会也经历了原生的、次生的、再生的社会类型,保持着古老生产方式的农村公社的非西方社会的东方,其农村公社就属于其中的再生阶段,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过程中处于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中间阶段,因而具有“亦此亦彼”的两重性。这就是说,一方面,农村公社“是最早的没有血统关系的自由人的联合体”[②g],农村公社的农民私有财产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开始摆脱血缘亲属关系的全面束缚和割断氏族公社那种“牢固而狭窄的”血缘联系,史前社会根据血缘亲属关系确定的“系谱树”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作为刚刚由氏族公社发展而来的农村公社,不能不带有其母体的“胎记”,经济关系处于萎缩状态,而非经济和血缘亲属关系仍然通过宗法关系、家族关系、种姓关系、人身依附关系等具体形式的泛化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且十分强大。这种两重性在其社会结构中必然会有相应的反映。所以,必须运用两种生产的理论,既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及其相互关系出发,又从人类自身的生产、血缘亲属关系(社会基础)、亲属制度及其相互关系出发;进而把二者辩证地结合起来,即既从社会生产出发考察生产关系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及其变革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同时又从人类自身生产出发考察血缘亲属关系对于社会结构其他要素的制约作用。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科学地把握非西方社会社会结构的根本,对之作出正确分析。
因此,必须反对两种形而上学的研究倾向:(1)过高估计财产关系的发展对非西方社会结构变革的作用,从而导致对其加以西方资本主义化的机械理解(俄国的孟什维克主义就是如此);(2)过高估计建立在泛化的血缘亲属关系基础上的农村公社的集体协作关系,从而导致对非西方社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观空想(俄国民粹派的“农民社会主义”就是如此)。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对社会“猴体”阶段进行人类学的解剖时,总是把史前社会和非西方社会放在一起加以考察。
最后,还有一个不能回避、需要作出阐解的问题,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846年标志唯物史观诞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对两种生产理论有所探索,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也对两种生产的不同性质及其关系有了更深一步的论述,并指出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血缘亲属关系的作用,然而,他们在创立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结构理论时,没有把人类自身生产及其所产生的血缘亲属关系和建立在其之上的亲属制度置于其中,而仅仅着眼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相互关系的考察。长期以来,理论界正是由于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应有的回答,导致了对唯物史观社会结构理论片面的、机械的理解。
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是:(1)如前所述,在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猴体”人类学解剖之前,对人类自身生产及血缘亲属关系以及建立其上的亲属制度在“猴体”社会结构中、特别是在史前社会中的决定作用的研究,尚缺乏人类学方面更充分的材料;(2)马克思、恩格斯是通过“人体”政治经济学的解剖创立唯物史观社会结构理论的,而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彻底地无情地斩断了宗法关系、种姓关系、家族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等等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酋长”的形形色色泛化了的血亲关系的自然纽带,它使人们之间除了类似于隔着柜台的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的关系,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关系了。这样一来,在分析“人体”的社会结构时,人类自身的生产、血缘亲属关系、亲属制度就失去其得以存在的客观根据了;(3)马克思、恩格斯的重点研究对象是“人体”,因而在“猴体”中所表现出来的许多征兆都被抽象掉了。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强调了“人体”的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现出来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被理解之后才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又强调对“人体”的解剖并不能取代对“猴体”的解剖。马克思说:“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人们认识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税等等。但是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①h]
真理是过程。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社会结构理论的研究,事实上经历了一个从对“人体”政治经济学的解剖到对“猴体”人类学的解剖的过程。所以,只有运用过程论的方法,才能把握其根本。而把马克思、恩格斯对“人体”政治经济学解剖中形成的唯物史观社会结构理论加以形而上学绝对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割裂了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思想发展的连续性,从中抽取一段,加以片面化、绝对化,而没有注意到他们晚年在这一理论上的新发展。这一倾向显然应予克服。
注释:
①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3页。
①b《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5页。
②b《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
③b《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6—37页。
①c ②c《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7、250页。
③c《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509页。
①d ②d ③d《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77、634、636页。
①e ②e ③e《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617、587、499页。
④e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16页。
⑤e ⑥e ⑦e ⑧e《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575、581、662、663页。
⑨e《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89—390页。
①f《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4—555页。
①g《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6页。
②g《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9页。
①h《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8页。
标签:摩尔根论文; 恩格斯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家庭结构论文; 人体结构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史前时代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氏族社会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所有制论文; 人类学论文; 科学论文; 亲属关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