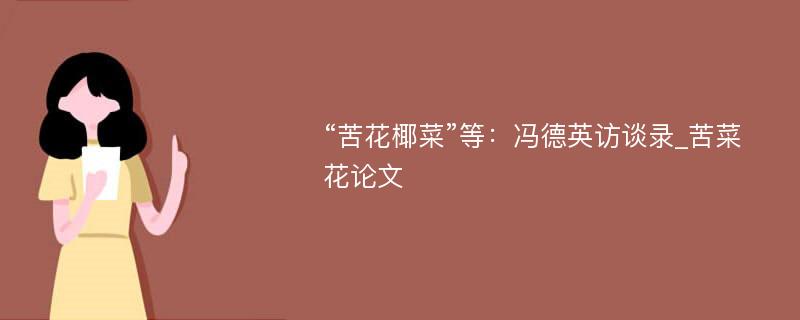
《苦菜花》及其他——冯德英访谈实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及其他论文,访谈实录论文,苦菜花论文,冯德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因为要做“‘红色经典’创作与影响”的专题研究,笔者2006年有幸对冯德英先生进行了一次访谈。当时先生已逾古稀,较少参加社会活动,出于种种渊源,先生还是接待了笔者的远道来访。先生虽已满头华发,可身体硬朗,非常健谈。 俞春玲(以下简称俞):《苦菜花》出版之后,被改编成了电影、吕剧、评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尤其以电影影响最大。您参与了电影的改编。您对改编后的作品有没有比较满意的? 冯德英(以下简称冯):搞创作的人,像写东西的人,都经过长期的积累、形象思维、反复的构思,他的艺术形象,他达到的审美标准,都通过他的原著小说来表达了。换一个另外的艺术形式,就很难按照原著,按照原来的作者他的想象、他的审美要求来表达。苏联那个很有名的瓦西里耶夫,一个很著名的电影编剧,他说过一句话,看自己的作品被拍成电影是最大的痛苦。这个的确是这样。 《苦菜花》这个小说,本身因为我年轻,其中写的大量都是生活的原始的东西加上作者的感情,所以我的结构上来讲是不完整的。但是它为什么影响这么大?因为比较真实,有感情有激情写的东西,这样打动了读者。所以它改编成电影很困难,它的情节、故事,是跟着人物走的。所以后来改编了很长时间,导演也换了好几个。剧本是我自己的,本来我也不想改,因为改编本身意味着舍弃。因为当时那种艺术气氛、艺术环境也不好,比较左倾的东西多一些,限制也多,最后改编成那个样子。电影拍成以后,第一遍我根本看不下去,我看了以后没有跟导演和演员见面,我就走了,感觉跟原来想象的不一样。后来慢慢地看了,特别经过“文革”的反复播放……这个电影拍出来比较晚了,已经1965年了。在当时的环境下观众还是比较接受的,当时轰动一时。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中央拿出来当一个重点剧目全国范围内放。这个作品后来“文革”期间,包括“四人帮”他们批判我的小说,但对这个电影还基本肯定,内部还放,做了一下修改。 写抗日战争的东西很多,为什么《苦菜花》比较有特色?主要是因为它比较典型的把抗日战争的复杂性写出来了,各个阶层……当时中宣部管文艺的周扬,他在第三次文代会的一个报告,他这个报告你能不能找到?他关于《苦菜花》有段评价,大意是,比较全面生动的深刻的表现了抗日战争的残酷性、复杂性和人民群众的复杂斗争。① 当然我受西方意大利文艺复兴思想的影响比较大。我小学现在都没毕业,我13岁当兵。特别是1957年的时候,我到武汉以后,到礼拜天经常夹着本书到安静的地方看,经常跑到武汉珞珈山、东湖边上……但是我对于大学生一点也不羡慕,我没有想着考大学。那个时候出版社已经决定出版《苦菜花》了,但是我还是保密,谁也不知道。我没有那种崇拜学府的思想,我感到通过自学,通过自己到图书馆里借书完全可以获得知识,我感到知识不一定在课堂上获取。高尔基、奥斯特罗夫斯基,我把他们拿出来当楷模当榜样。所以我的《苦菜花》写完了以后,领导又叫我进解放军政治学院或者上北大去进修,这些我都没有去。我都说我没有必要,因为我是搞创作的,我没有必要去到那些地方专门去学习。当时有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很流行的,包括老舍、茅盾这些作家都提,就是大学培养不出作家。它是两个路子。我不愿意去听老师讲课,我愿意自己看书、自己琢磨。 1951年的时候,我在部队上的业余的文化补习班。没有初中毕业的干部都要去参加学习,我也参加那个学习。恰恰我的作文是最差。因为什么呢?我老是不按照老师的题目做,我老是自己发挥,这个时候跟老师也有些争论。所以我的作文一般都是八十来分、七十来分,再没有高的,老师老是不满意,就说我老是自己发挥。所以我少年、青年的时候就有这个遗憾,有这么一种悲剧。话扯得远了。 俞:这些问题也是我关心的。您说您受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比较大…… 冯:文艺复兴的那种批判现实主义的文艺传统,我到现在也是坚持,文艺一定要反映生活,要反映生活的真实性。所以后来我的小说,江青他们为什么批判,就是因为这些东西。说我的小说没有反映现实,是歪曲的丑化的,但其实我恰恰就是反映生活的真实,是对生活的一种反映。但恰恰我不够的地方,是在那种环境下我还没有完全做到反映生活、反映时代。那种文艺传统,我感觉最基本的就是反映生活的复杂性、反映真实,所以才能有文艺复兴,才能有现实主义的传统。 俞:关于江青对您的批判,您能不能具体谈一谈? 冯:江青的批判主要还是从《迎春花》开始。应该是六四年。《迎春花》出来以后,北京的中国评剧院把它改成过评剧,但是那时候它的评剧没有《苦菜花》当时搞的红火。《苦菜花》的评剧中国评剧院有三个团同时演出,一人带一个团去演出。当时有一个统计,《苦菜花》是现代戏中观众数量最多的。后来《迎春花》他们也改了,但是没有怎么轰动。 山东话剧团翟剑萍把《迎春花》改了,山东话剧团王玉梅她们演了这个戏。演了以后他们让我看我也没看,我也没参与。后来到了六三年秋天,他们上北京演出。北京中央青年艺术剧院找剧本,就把山东的剧本弄到北京去了,移植去了。我是到了六三年的秋天或者冬天,吴雪院长——她是后来的文化部副部长,她请我去,说有这么个剧本不错,他们在排练,请我看一看彩排。我看了一下还可以,没提什么意见,也没有说什么。后来呢他们演出,叫我去看演出,茅盾、周扬等中央的负责人也去看演出,反响非常热烈。 看完后,我陪周扬、茅盾他们上台接见演员的时候,周扬就非常肯定这个戏,说这个戏好。我的小说他俩也都看了,(周扬)说戏反映了小说原貌,写得很深刻。他就问茅盾的意见,茅盾说看剧场的现场效果、观众反映这么强烈,说明是成功的。他们说了很多鼓励的话。那时中央要在中南海召开工作会议,周扬说他向周总理报告要周总理看一看,给中央演出,当时就定了这个事。 当时我也比较忙,没有时间弄。但是周扬跟茅盾他们提出一些具体意见,希望在中南海演出前加工一下,叫我能抽点时间帮他们一下,我说好吧。当时我就请吴雪他们找了导演一块处理一下,也没有什么大的改动。当时都请最好的演员演出。 我就以为这个事完了,但过了一阵叫我去,说江青要看这个戏。我当时比较忙,因为我陪过周扬他们了,我就没去。 但是江青看了戏意见就来了。演出当天晚上她没说什么。据说江青当时看了这个戏上了台还挺高兴,跟演员握手,又问作者在不在,有人回答说作者不在,回去以后她就越想越生气。气在哪儿?她的原话我基本上记得一些,她就是说:这个戏是坏戏,我上当了。 上什么当了?《迎春花》小说里不是有个曹冷元烈属吗,我没写他是个党员。结果那个戏烈属为了救公粮牺牲了,戏为了加强他,就设置了从他身上找到了入党申请书的情节。 江青说:这么好的人,为什么不是党员?我上当了。她说:中农落后,贫雇农都死光了,我们的战争怎么能够胜利?这个戏是个坏戏。我当时鼓掌是对演员,不是对戏鼓的。 后来过了几天,江青又看小说《迎春花》,说:戏不好,我又看了小说,小说比戏还坏。坏在哪儿呢?她又发挥了,说,我在延安时期我也做过解放区的后方工作,我的生活不像作者写的,解放区的生活不是这样。她还是那一套,说:我上当了,那么好的贫雇农不是党员,中农那么落后,胜利是怎么来的?她说作者没有生活,书和戏写的跟她在延安时期经历的生活不一样。她让人转告作者,让作者去改,让作者下去生活,重新去修改。 再后来她不断地说类似的话。江青她那时经常看戏看电影,抓文化活动,一提文艺作品就谈到《迎春花》的一些问题,不断地说。后来她也没有正式跟我谈,我都是通过朋友、文艺界的人转达来的。我当时就挺恼火的,感到对文艺作品有意见可以,但我感到她太武断。我就说,我经(历)过的胶东山东解放区当时的生活就是这样,而且对那种残酷性我写的还不够。我说:江青同志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这句话麻烦了。 再一个我说,你这么武断就下结论,我们现在应该是听中央的,我们是共产党,听中宣部的,听人民文化部的。茅盾是文化部长。我光知道江青是毛主席的老婆,你出来发指示,有点不合理,不符合原则。 后来这个事,一直到了六四年的时候,这期间我也没见过江青。听说,江青拿我当是旧社会来的作者,结果去跳舞的空军的文工团员,我们的空军领导就跟江青说,冯德英在创作《女飞行员》,他没有时间下去,另外他是个烈士的后代,他从小参加革命,生活他是有的。江青说,噢,他原来是个红小鬼啊,那这样的人还可以改造嘛,那等过一段时间再说吧。……过段时间就说,不让你下去了,以后有机会再改好了。事情就缓和下来了。 后来总政过些日子就正式跟我谈话,传达江青的所谓指示。……总政的徐立清副主任带了两个文化部副部长,他们在总政排练场,让我去听取江青同志的指示。江青是打电话给罗瑞卿总长,让罗瑞卿总长把她的意见跟我谈。罗瑞卿总长对江青是一直有看法,就交代了总政部的副主任,交代他带着文化部的副部长跟我谈话。……谈话说了几个意思,一是口气缓和了,说我的小说《迎春花》,还有《苦菜花》也有这个问题,就是有和平主义、人性论,有色情描写,写革命战争写得太残酷了,希望我能接受她的意见,对作品进行修改。当时我还是一肚子火,但是领导一再打招呼,我表了个态就是,要认真考虑她的意见。因为总政领导还要汇报,还要反馈给她。我就说等着有适当的机会的话会考虑作品的修改。 结果最后文化大革命一来整个也就完了,我就整个地被打倒了。不光是江青的批判,整个“三花”,包括我那个没有出版的《山菊花》的稿子,都被打倒了。 俞:那么关于“文革”时期的批判资料现在还有没有呢? 冯:“文革”时期对我的批判,也没有公开的正式报刊批判,就是开批斗会啊、小报啊,这类。 俞:当时您和您的家人都受到了牵连,而且书中的人物原型也受到了牵连。 冯:都受到了牵连。我的大姐夫在烟台受到批斗,病情加重去世了……没有办法。因为我的“三花”主要是写咱们胶东的地下党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现在是说这三部书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斗争,“文革”时就全否认了,说都是坏的,说胶东的革命路线也是错的,什么都是坏的,把历史颠倒过来。 我父亲本来在北京我那儿住着,也没法儿住了,造反派一天到晚地斗,去抄我的家。军队内部老实讲,包括吴法宪对我还是可以,一开始说保我,后来也不保了……造反派武斗的情况很少,比社会上武斗少,但是我也是靠边站,一天到晚劳动改造,还没有拉我去游街。 清华造反派去抓我,是因为彭德怀的事,去陪斗彭德怀。空军有个司令员叫刘亚楼,他叫我写了个《女飞行员》,当时看了都说好,我也因为他们奉命写的。结果后来江青他们一看,有人告状说为彭德怀翻案。《女飞行员》我写的是五六年第二批的女飞行员,是彭德怀当国防部长的时候的事,它就牵扯彭德怀的错误路线,被认为是为彭德怀树碑立传。当时有个造反派头头蒯大富就带人去抓我,结果因为空军提前知道消息,叫我躲起来了,就没抓到我。 俞:我看您的《女飞行员》经过了修改,修改的过程跟您的初衷也不太一样。 冯:就是。女飞行员很难反映,这个是都在天上的事,也比较单纯。很难,怎么办?可是空军呢一定要,因为这是周总理他们抓的,全国妇联都非常喜欢反映一下这个事。空军是组织了好多人多年没写出来,最后刘亚楼实在没有办法,问我:你能不能把这个写出来?当时我正在写《山菊花》,六三年。刘亚楼叫我放一放《山菊花》,参加写《女飞行员》这个工作,后来叫我执笔来写的。我就把它生活化,把它人物都写成不同出身。实际咱们山东没有这个什么童养媳这个事,我为了反映它就把它都移植过来。这样空军党委刘亚楼、吴法宪他们看了都非常高兴,都说写得不错。 可是因为刘亚楼,他为了贴紧政治跟形势,他就拼命地给我加学毛著的东西。《女飞行员》故事背景那个时候很少有这些东西,几乎没有。弄得我都没有办法,刘亚楼重病我都和他顶起来了。他非要加上毛主席语录。他这个人呢,你说他不懂文艺吧,他对我是很支持。很多人不同意我再写《山菊花》,叫我去写空军,他在会上公开地说,(不管)写什么好的都是国家的财富,冯德英这样的原来有考虑应该叫他去完成《山菊花》。你看他又很懂。大家都知道刘亚楼对我非常好,给我亲自找房子,安排房子住,给我创造条件写作。可是关于《女飞行员》呢,他这个政治家,他就有矛盾了。他本来很懂艺术,他这个人是在苏联都待过。《江姐》也是他抓的,《江姐》没有他的扶植、他的支持也不行。但是他为了贴近政治,非常违反艺术规律,用行政的命令逼着我。他组织了好几个班子,专门挑选语录一大堆让我往里面插,他是真费功夫。 这也是悲剧,他是用心良苦……空军政治部一个主任说,这是庸俗社会学,我说你不能说啊。所以当时提这个“三结合”,对作家搞创作真是个束缚。 俞:对。我看到一篇文章说,您和其他人是怎么写出这部作品的,是因为经常读《毛主席语录》。 冯:对,你就得这样说啊。《女飞行员》反映的事,那时候还没有《毛主席语录》,哪有《毛主席语录》? 《女飞行员》当时演的时候没有完全按照刘亚楼的要求,是比较成功的。《人民日报》一天一版发了一个礼拜,之前它从来没有完整的发过一个剧本。当时看完了以后,邓大姐邓颖超告诉说,我们(还有罗琼,当时是妇联的第一书记)代表全中国妇女向你表示感谢,不管是你的《女飞行员》还是你的小说啊,都写了很多我们妇女、母亲,我们向你表示感谢。 我的小说写女性比较成功,我写男的不行。这跟我生活经历有关,观察点不一样。我从小跟着我母亲长大,儿时的时候我父亲不在家,我哥哥都当兵,我小,跟着姐姐。大姐参加工作,母亲支前,所以家里老住女干部、女八路,家里都住满了。我小一点,跟她们感情特别深,很依恋这些人,我是这样养成的。从生理上讲儿时的记忆是最深刻的,的确是这样。所以一写到这些人我的感情就很自然的流露出来了。感觉也能抓住她们的特点。还有老头老婆我也愿意写,但是男性青年干部战士接触不多,所以我就很难把握。 当时《女飞行员》写了一个飞行事故,我还是说服了刘亚楼,刘亚楼支持我才能写出来,就是写发生飞行事故对一个女兵的考验。很多人忌讳,不让写。当时刘亚楼跟我说,怎么办?我说非要写,不写这个东西震动不大。他后来就说弄两个方案,写飞行事故牺牲一个,要么就是写不牺牲的,两个方案,你看一看,让他们挑选一个。 我跟你说一个例子。郭老那天看《女飞行员》我没去,看完了以后他谈意见。我就告诉另外一个人,你跟郭老说说这个意思,你说写牺牲好不写牺牲好,飞行事故死个人好不死个人好。死人当然震动大了,而且是现实情况;不死人就是模糊处理,轻描淡写,也可以取得效果,但是震动不够。结果郭老说:“我同意冯德英的第一方案,这是个诗剧。”因为我有些比较押韵的台词。结果《人民日报》登的时候,《人民日报》每天晚上它都搞个清样,《人民日报》副主编就给我提出来说,登在报纸上为了减少麻烦就写飞行事故,别说牺牲人。《人民日报》一发表,郭老第二天马上叫人给我打电话:“还是《人民日报》对,我的意见作废。”他马上就变过来。实际上原来他是作为艺术家跟我说的,你看他马上按照《人民日报》的标准。那个时候的人啊…… 俞:周总理在《苦菜花》写成之后,还接见过您,跟您会谈过,是吗? 冯:那是五八年的冬天,在全国的青年积极分子建设代表会的时候,在招待金日成的宴会之前。会谈请了七八个代表参加。我作为代表,总理提前来跟我谈话。他说你这么年轻啊……还有胡耀邦,还有中央的另一个书记胡克实…… 俞:周总理是怎么评价的呢? 冯:周总理这次没说书,可能当时他没看我的书。但是他一听团中央的同志介绍,说我把稿费大部分捐献了。我当时很瘦,我当时102斤。周总理说,写一本还不够,还要继续写,你这么年轻啊。②另外他也说,稿费捐了好,但是也要保养一下自己的身体。他看我太瘦了当时。 后来是在六四年看《女飞行员》的时候,请了妇联的负责人,在儿童剧场看戏。当时邓大姐邓颖超等妇联的领导来了,空军领导陪着邓大姐看戏,正看着的时候,周总理来了。周总理有一个习惯,他工作忙,有时候看戏走到半路上又把他追回去办事,所以他就叫大家不要等他,你们该怎么看怎么看,我来了能看几场看几场。 来了我就跟吴法宪去休息室接待周总理。吴法宪就要介绍我,周总理说,他我认识啊。周总理记忆力是很好,因为这中间除了五八年那次,我有时候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文化工作会议,他来讲话,也是跟我们打个招呼,没有个别接触。但是吴法宪一要介绍,周总理就说,他我认识,他写《苦菜花》的,他写的生活,我在延安时期就知道一些,胶东那个斗争的情况,我在延安时我就听说,我都知道。 后来我的《苦菜花》小说写的于团长于司令③,六七年被造反派折磨死了以后,周总理当时亲自下指示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指派康生一定要查清。当然“文化大革命”中两派打仗查不清。所以后来“四人帮”一倒台,万里去安徽当书记以后,费了很大的力给平反。 于得水是转业到安徽去的,在那去世的。去年(2005年)五一安徽给我来了几次电话,说安徽人民公园塑了一个铜像请我去,希望我能去参加这个活动。我很感动。我这么讲,他在山东我的家乡工作,战斗的事迹都在这边。他在安徽待了六年多。我说,为人民做了好事的人不管哪儿的人都欢迎。这也与周总理的重视有直接关系。 俞:我发现您的小说中,好多人物的名字都有“海”啊、“水”啊…… 冯:咱那儿离海边比较近,叫这个的也比较多。 俞:那“文革”期间像《苦菜花》就没有再版了。 冯:“文革”期间啊都打成毒草了还怎么再版。就是“四人帮”倒了以后,一开始再版的时候还要叫我修改。所以《苦菜花》还有反复修改,还删了很多。 俞:“文革”后您做了哪些方面的修改?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冯:感情的东西都要删掉,不改出版社就不能出。 俞:我做了一下对比,我看到您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的修改。一是人物外貌的改动。比如英雄人物于得海,身高由“中等个子”变成了“上中等个子”,“身体粗壮”改为“身材魁伟”,修改后眼睛前面还要强调“大”。改动后的形象更符合当时英雄人物高大魁梧、富有智慧、具有威慑力这一普遍的形象特征。二是人物对话、心理活动的改动,把许多流露私人感情的交谈变成了集体式的、革命式的讨论。 冯:我都记不住了。实际《苦菜花》现在说是第一版,还不是第一版。 俞:对,我也想了解这个问题。 冯:最早的那版我这儿也没有。当时那版印了8万多册的第一版,它是用大理石的灰色封面。那一版可能解放军文艺社的老编辑他们还能保存。现在用的这一版实际上是人民文学这版,但是没做什么修改,就是文字上的技术性的修改,基本上是这样。作为初版的话第一版8万多册的,就是我在武汉工作的时候印出来的,五八年一月份那是第一版是最早的。那一版我这是没有了,因为“文革”期间我这原稿也都没有了。 俞:《山菊花》还幸亏是被别人抄走了。④ 冯:那“俩花”的稿子也在解放军文艺社,估计解放军文艺社的也被人抄走了,烧掉了,到现在没发下来。 俞:当时您的第一版也就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时候,我看到您在《我与“三花”》里讲,您是寄到北京解放军总政文化部,然后转给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冯:当时它是叫“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 俞:还有一篇文章说,您是直接寄给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责任编辑杨昉一眼就看中了。 冯:这个不对。我是五五年的秋天,可能十一月份吧,我在汉口工作,那时还是中南空军,在中南空军教导连教授无线电飞行员。实际上小说提笔写,是五五年春节,我在海南岛三亚执行任务的时候,在电报纸上我在那开始写。出差来回反复写。后来五五年我就调到武汉汉口中南空军教导连,我在那儿教无线电,利用晚上时间偷偷地写。非常炎热那时候,我利用业余时间偷偷写。我找一个朋友给我买的稿纸,当时武汉还买不到那样的稿纸,都是竖写的。先在电报纸上写,边改边誊清。可能到了11份。我有一个朋友,他比我年轻,他也在那教学当兵,就他知道。稿子誊完了以后,是28万多字,不到29万。我就叫他看一看,叫他看看行不行。他看了以后说我看行,当时有本五十八天写淮海战役的,他说我看着比那本书都好。他说这个话,我说别瞎说。那好吧,我就寄出去了。稿子很厚很沉。当时我住在赵家桥,可能是现在雷达技术学院那个地方,旁边是个邮局。怕人家知道,我就寄出去了。我就寄给谁呢?我就知道有个文化部长叫陈沂,我就寄给他。我就说我是一个共青团员,怎么怎么的,写了个稿子,希望你们给指导。 稿子刚寄走,肃反来了。肃反一开始是在社会上,后来……我们的学员毕业了以后马上就转入肃反。我那时在教学不知道,我那有个皮箱,我什么东西,家属来的信和朋友来的信,电报纸写的稿子,都弄在那个大皮箱里,还有我的日记,我那时一天不落的写日记。我那个皮箱就被撬开了。专门有一个小组,专门检查你的信件。结果他们就发现了,日记上反映我写作,电报纸上是稿子,搞肃反的知道我是偷偷在搞创作。所以不管怎样,我教学教的班再好,利用业余时间写作也不行 结果学员毕业以后,五六年冬天我们的单位回到广州去,专门搞肃反,我都没想到我是重点。罪状一个是从我日记上,一个是来信上,来信谈一些社会问题,再加上稿子。稿子都没看是写什么,光知道我写稿子,写稿子就和胡风有联系。胡风不是写日记吗?只要写就与胡风有关。他不知道我已经把稿子寄走了,我那个朋友也不错,他没有告诉别人说我的稿子已经寄走了。稿子寄出去,我记得编辑当时还给我回了封信,同时编辑部也给我回了封信,说收到,等审完了以后我们再跟你联系。很简单的一个东西。那封信我藏起来了。 俞:现在没有了? 冯:嗯。当时运动已经发生了。批判斗争我三个月,我就没说稿子自己寄走了,要是说了,他们知道我寄哪儿去了,肯定去给要回来。批斗我三个月,逼着我问,你是否给胡风写过信,你想搞创作,想成名成家,你能不给他写信?我当然不能瞎说。 如果没有运动的话,(《苦菜花》)五五、五六年就出版了。北京也开始运动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也开始运动,也没有办法处理这个稿子。 当时我年轻我非常生气……后来广州空军政治部说这么年轻,这么点儿小孩,13岁参加革命,他怎么能和胡风搞在一起,批错了。就给我解放了,当时不叫解放了,就是不批了。气得我坚决要求复员回老家,不能在这儿干。后来朋友说这么回家也不好,当时连党还没入。这事把入党都耽误了。当时江西有个飞机场需要一个台长,我就要求我去。我就在那个飞机场待了半年。 这个时候北京肃反完了,完了以后他们就来信。第一封信就说稿子感觉基本还是不错,但是还有些缺点,接着没几天他们第二审又看,来了封更长的信,把缺点也否定了,就是肯定稿子非常好。问是在单位修改还是到北京修改。当时单位哪有条件修改……所以五六年冬天,我就到北京修改五个月。 俞:有材料说有专门五个月的创作假期,是指的这个吧? 冯:哎。到北京修改,本来是五七年五月份我《苦菜花》的稿子已经定稿了,结果这又来了“反右”了。如果没有“反右”《苦菜花》五七年上半年就出了,编辑部告诉我马上就出。几个主编看了以后一个比一个肯定“好”,一定要把这部稿子留着作为解放军文艺社自己出版的第一本书,挑一本我们自己打得响的。我当时都不相信,以为他们是说些鼓励的话给我听。结果五八年一月出版。 俞:第一版和您的初稿相比有什么变化吗?修改过程中受到了政治运动或外界的影响吗? 冯:书稿从29万增加到了40万。基本上都是细化,人物关系什么都没有什么变化,情节展开了。过去时间不充裕。别的没有什么变化。他们编辑说怎么改得这么快,他们一提示哪个地方应该细化就改好了。 俞:那个时候出版的作品很多都受到了极“左”思潮的影响,《苦菜花》也有这方面的困扰吗? 冯:好处就在这。因为我写的时候政治因素干扰少,部队干扰少。肃反之前写完了,要肃反以后写可能也受些影响。这不肃反完了之后又有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五六、五七上半年正是好的时候。 我当时还想,我是红小鬼,我家是革命家庭,我不怕。结果呢这不是肃反弄了我一下,但是我的稿子已经出来了。……反右的时候我没参加,我要参加了我也很难说,我几个很好的朋友反右的时候都栽了跟头。根据我那种思想,我至少会对肃反运动提出异议,我要回去肯定是要鸣放的。 俞:您是一九五三年开始酝酿、构思故事框架,先写了四五万字的“母亲的回忆”,这可以说是《苦菜花》的“胚胎”,然后一九五五年正式开始动笔写作? 俞:我看到一些材料上说,您在大会上“受到不点名的点名批评”,是否就是因为肃反运动中发现了您的稿子? 冯:哎,就是肃反运动。 俞:我觉得您的《苦菜花》跟当时其他的作品相比,可读性更强。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在描写革命斗争的复杂与艰险的同时,您还对人物的内心世界尤其是感情有较为细致的描写,人物更人性化,作品也更真实。建国之后很多作家,他们的作品中有些情感描写已经删除了,再版时都做了修改,那您当时为什么还敢进行那么丰富的爱情描写呢? 冯:后来我也自己批判自己,说自己是自然主义,实际上我就想着不能把生活简单化,写东西要描写得深刻,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就完全在于自己的真实和最生动的描写刻画这一方面。到反苏的时候,《迎春花》出来以后就到了六○年、六一年以后,《苦菜花》要改。我那描写说她在那刨地,她那丰满的乳房、脚丫踩的那个……这个都要改,都到了这个地步。我说那还叫什么小说啊?那样一种风气是时代的。我说我宁肯不写了我也不改。 俞:我看到您《苦菜花》中有些爱情描写再版时也改了,民歌中涉及这方面的也改成歌颂解放区的歌词了。 冯:哎,对对对。 俞:那如果有机会再次修改《苦菜花》的话,您觉得是不会再修改了,还是还有自己的遗憾? 冯:不能再修改了,东西是时代的产物。我本来的创作计划是想写完《染血的土地》,后来又出了本《晴朗的天空》,下一步想就是写“文革”这十年。“文革”我写了一部分,到现在,我还准备在有生之年还要写。因为那两本出了一版,就没有再版,《晴朗的天空》还比较粗糙,我等着后边再修改。因为人物都是贯穿的,我等着改完了以后一块出版。但是“文革”的东西不好写。我说不好写,就是写完了以后,材料不断地充实,大的方面还是像过去一样。 过去的东西虽然受一定影响,但是从根本上还是比较真实的,感情啊,人物啊,主要的方面都比较真实。我看一些作品能站得住,这是主要原因。你要是要求完美,不可能的。 俞:而且相对于某些“红色经典”来说,在展现人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方面,您的作品已经做出很大的努力了。 冯:已经很难了。你像《苦菜花》中王柬之这个人物,现在的电视剧的导演他听我说了一些,我没写进小说。他们本身也是很复杂的人物,不是像我写得那么简单。 俞:电视剧中母亲和王柬之发生了感情,那当时生活中确实有这样的事情吗? 冯:不是。实际上王柬之那个人物是非常复杂的。他也做过一些好事,帮着某些人打官司啊。实际上这些人呢,就是大节上有缺失,他实际上是汪精卫派的曲线救国,就干这个…… 俞:您对“红色经典”是怎么理解的? 冯:大家都这么叫吧。老实讲现在有些作品,写得战争某一方面比我们原来都深刻的多,也比较完整。比如莫言的《红高粱》出来以后,我们都交谈过,写得相当不错,当然有些地方还是值得商榷……我们当时写不出他这样。可是人民群众为什么老是看重原来那些“红色经典”,这值得研究。莫言他告诉我,他看了《苦菜花》,他受我的影响。他完全超过了我。因为什么,人们的心理,仗着时代,人们认可当时那个战争就是那样。 俞:我看到,莫言在《我看十七年文学》中,高度评价了您的《苦菜花》⑤。 冯:意大利的一个女士在山大留学,研究莫言的,跑来叫我谈谈对莫言的看法和影响,她也是看了莫言对我的评价。莫言还比较年轻,我看他的作品,可能一个作家就是属于一个时代的。 所谓“红色经典”当时评价也是很宽泛不一。其中有的作品当时大家都认为艺术写得很粗糙的……当时对这些东西评价也不一样。 俞:就是当时的评价也有高有低。 冯:哎,有高有低。艺术上要达到的,光靠情节也不行。 俞:现在有的年轻人不看那个年代的作品,可能也是因为其中有部分不那么优秀的,就认为所有的作品都不值得看。 冯:哎,有些作品除了故事没有别的东西。你看对孙犁的东西我们都评价很高,作品达到的境界,还有杨朔,杨朔也是咱们山东的,这些作家,包括峻青的作品。……当时五六十年代那时候,评价文艺作品包括周扬他们,还是注重艺术性和思想性的结合,单纯的质量不高的东西他们评价也不是太高。但是现在一弄的话一出来都是一揽子评价了。 俞:您跟孙犁的共同点是写女性,写真情实感比较细腻。 冯:嗯,真情实感比较细腻啊。 俞:那当时您的写作有没有受到谁的影响? 冯:很难说了。看书我是什么书都看当时,后来就有选择的看,但是自己一写起东西来有时候就很难再找到。 俞:分那么清楚? 冯:嗯,分那么清楚,谁是谁的。我主要对外国作家作品我看得比较多一些。 俞:您比较喜欢哪些作家? 冯:巴尔扎克的东西啊,再就是《悲惨世界》的作者雨果,法国的莫泊桑啊。俄罗斯的大师的东西,列夫·托尔斯泰的,小托尔斯泰的东西我不太喜欢,再就是肖洛霍夫。肖洛霍夫他这个人真是个奇才,他十四五岁的时候写的短篇,现在看来还非常深刻。高尔基的作品现在年轻人看得少了,但是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夹着高尔基的作品看,我仔细地看。他是散文化东西比较多,但是很深刻。 俞:您的创作有没有受到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我看到您在《迎春花》中介绍一个人物的出场,我当时觉得跟“林冲风雪山神庙”的感觉有点像。 冯:这个很难说。《迎春花》当时在日本翻译后,他们将迎春花与《水浒》、《红楼梦》什么相比,写了些东西……我的作品被翻译最早的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苏联,他们马上就翻译,像《苦菜花》和《迎春花》,他们很快就翻译。 俞:“文革”之前? 冯:都是“文革”之前。翻译《苦菜花》和《迎春花》的是——三好一⑥,很有名的一个人,已经去世了。 俞:关于这些作品在国外的传播情况,您有没有这方面的材料? 冯:没注意。 俞:看来您对这些,对名利都不在乎。 冯:不在乎,联系也比较少。当时《苦菜花》翻译到苏联后反响比较大,读者来信比较多。我到苏联去访问的时候,那个翻译家⑦已经去世了,他那个同事接待的。 俞:那是哪一年的事情? 冯:九零年,那是苏联解体以前了,中国作家代表团官方交流到那儿去。 ①参见周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一九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60年9月4日。 ②冯德英1935年出生,《苦菜花》出版时以及会见周总理时,作者只有23岁。 ③于得水原名于作海,是小说《苦菜花》中于得海、《山菊花》中于震海的人物原型。 ④参见冯德英:《我与“三花”》,《北京日报》,2005年6月24日。 ⑤参见莫言:《我看十七年文学》,杨扬编:《莫言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⑥《苦菜花物语》,三好一译,东京:至诚堂,1962年;《迎春花》,本山舵夫、伊藤三郎译,东京:新日本出版社,1964年。见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馆藏。此处感谢天津外国语大学常晓宏老师在资料查找方面的帮助。 ⑦《苦菜花》俄译名:Цведыосота,译者为B.A.帕纳秀克(1924-1990)。此处感谢天津师范大学李逸津老师在资料查找方面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