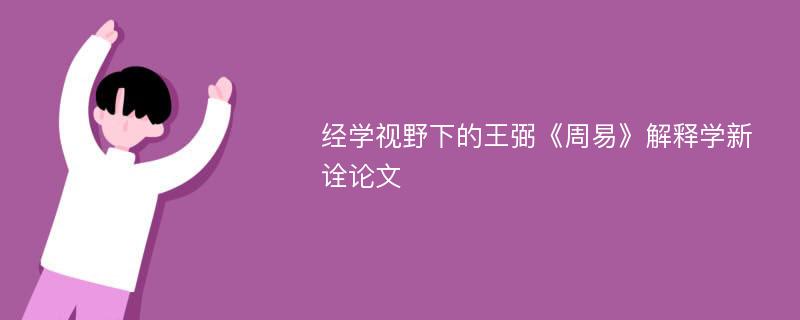
经学视野下的王弼《周易》解释学新诠
王文军1,张立文2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从经学的视野来看王弼的《周易》解释学,其总体呈现出“以传解经”的解释风格:在经传体例上附传于经,突出了《易传》文本的重要性;在卦爻解释上秉承卦本《彖传》、爻本《小象》的思路,并创发出许多新的范式;在义理倾向上,通过人格化的爻位观传达出偏重于政治的旨趣。王弼的《周易》注解是对东汉易学由繁琐走向虚妄,进而陷入神秘主义深渊的一种补救,对《易传》基本义理的遵循保证了其经学的底色,这也是后世儒家将其接受为五经正解的真正原因。
关键词 :王弼;周易;解释学;经学
学界对王弼易学的研究可谓是汗牛充栋,然而以往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扫象”的陈论和玄学的立场之上,缺少从传统经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审视和阐发。《易》之为《易》,首先在于其作为传统经学的一部分所阐发的义理与价值,王弼以“玄谈”的姿态注解的《周易》最终被正统儒家接受并作为后世五经正解,恐怕也与其易学思想中的经学底色是分不开的。因此,对于王弼易学,我们同样只有将之置于“传统经学的学术品格和发展脉络”[1]之中,才能照见其更加完整的思想内涵和学术意义。本文拟从经学的视野出发,以王弼《周易注》和《周易略例》为核心文本,探究王弼在《周易》注解上所呈现出的风格特点和义理倾向,希望可以借此对王弼易学乃至《周易》经传的理解提供一个更为本真的角度。
一、经传体例的调整
《周易》是卜筮之书,《易传》形成后又以“十翼”的体系流传,因此《周易》经传最早应该是各自独立的。东汉熹平石经中,《周易》的顺序先是上下《易经》,然后才是上下《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等“十翼”的内容,这无疑也说明了二者文本的独立。 王弼注《易》本于费氏《易》,费氏《易》虽然没有章句,但“费直以《十翼》解说经旨,传授其学,门徒、后学必据以述作‘章句’,所成‘章句’中的《周易》本文体例或未能一致,故当时流传之经传参合本《周易》亦必有多种”[2]。到了汉末,郑玄将《周易》经传体例重新编订,成为当时范本。据学者张善文考证,郑玄把《易传》中的《彖传》和《象传》取出来,分别附于六十四卦的卦爻辞之后,并加上“《彖》曰”、“《象》曰”以示区别,其他传文则依旧按照《系辞上》、《系辞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的顺序附于经文之后。从郑玄的编订来看,其《易》注已颇具今日通行《周易》之面貌,而王弼的《周易注》体例就是对郑玄方式的进一步发展:首先,王弼将《彖传》和《大象传》依次附于卦辞之后,而将《小象传》附于每一爻的爻辞之后,并分别加上“《彖》曰”、“《象》曰”;其次,王弼将《文言》一分为二,分别附于《乾》《坤》两卦的《大象传》之后,并加上“《文言》曰”。这样,《周易》经传之间的联系就变得更加紧密。另外,由于对余下的《系辞上》、《系辞下》、《说卦》、《序卦》、《杂卦》诸传未作注解,所以王弼当时的《周易注》并不完整,在其后学韩康伯注解了他未注的传文并于南北朝后期二注合为一书后,才逐渐形成了今天的通行本王弼《周易注》体例。
三年级语文教学如果仅凭几十篇课文的精讲深挖、设计无数的练习,由此来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习作水平,往往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学生的学习兴趣难以提高。的确,课文只是个例子,应由一篇文章的阅读触及其余,启发学生把知识融会贯通,灵活、高效地学,有趣有味地学。例如在学习了《燕子》后,相机返顾或推荐多课文,引导学生把课文作横向比较,培养学生读书思考、分析感悟能力,这是从文章的内容方面相串联的;还可以从作家的系列作品拓展,在学习小组里交流安徒生这位“世界童话大王”的名作,花时少、收效高,关键是培养了学生广读博览的兴趣;还可以进行读写知识的迁移,在阅读教学中巧设情境,激发学生的情感。
对于王弼改变传统《周易》经传体例,历来存在许多争议,因为《周易》经传是两种不同的学说,将其混杂在一起确实对经传的各自面貌都有一定影响。王弼为什么要如此调整呢?一方面,王弼对经传体例做出的改动或许正是当时经学发展态势的反映。东汉以后,伴随着朝廷对孔子的不断尊崇,有关孔子的说教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其中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作为“五经”系统之外但属于孔子说教的《论语》地位得到提升,开始进入到“经”的行列。在此背景下,“既然认定《彖》、《象》、《文言》是孔子所作,那么把孔子作的同经文合而为一,也就顺理成章了”[3](P114)。另一方面,从经学义理的角度来看,这种改动实际上也得以让《易传》的地位进一步凸现出来:将《彖传》和《象传》分附于卦爻辞之下是因为二传本来就是解释相应卦爻辞的,而将《文言传》分附于乾坤两卦也是因为它是对此二卦之义的详细阐发。因此,王弼对《周易》经传体例所做的改动体现出的正是他对《易传》的重视,这种改动虽非古本之制,但由于紧紧抓住了《易传》,且便于学者对比参研,所以能够通行至今。“以王弼《周易》传本盛行一千七百余年而不衰的事实言之,王氏其人在《易》学领域对后世的重大影响,除了他‘自标新学’的理论体系外,他对费直、郑玄沿传之《周易》经传参合本体制的重新改定,也是值得估量的一大要素”[2]。王弼这种《易注》体例是对费氏《易》“以传解经”风格的进一步落实,它不但形成了经传合体的《周易》通行文本,而且也为王弼依据传文阐发《周易》义理定下了基调。
教师引导学生发现:在求解等腰三角形的有关题目时,要考虑等腰三角形的三边是两腰和一底边,同时要考虑满足三角形的三边关系。
二、对《彖传》的发明
听力理解是口译过程中的第一步,也是口译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4]。听懂源语是口译输出的基础。受母语发音习惯和自身说话习惯的影响,一些发言人英语发音并不标准,可能对译员的听辨带来消极影响。译员自我熟悉不同口音的英语有利于准确传达源语信息,优化现场的交流效果。
《彖传》在“十翼”中是解释每一卦卦义的篇目,它的特点是首先通过卦爻象言明此卦的特性,然后根据这个特性进一步阐发卦辞所表达的义理,可以将其简单概括为“据卦性而言义”,而王弼对《彖传》的发明首先就体现在他对《彖传》解经体例的阐发上。在《周易略例·明彖》开篇,王弼说到:“夫彖者,何也?统论一卦之体,明其所由之主也。”[4](P591)此处王弼所言的“彖”存在一定争议,有学者认为是指卦辞,也有学者认为是指对卦辞进行解释的《彖传》之文;然而无论为何,其目的都是要总论一卦的卦义,进而说明此卦义由来之“主”。在王弼看来,“主”是一卦的主旨或主导,具体落实在卦爻上就是一卦中具有决定性地位的一爻。通过决定性的一爻解释一卦主旨可以说是王弼对《彖传》解经体例的一个基本立场,朱伯崑将其概括为“一爻为主说”[5](P256)。一般而言,此为主之爻有两种情况:其一为二、五两爻,也就是王弼在《明彖》篇中提到的“中爻”;其二为六爻中的独阴或独阳之爻,也就是王弼在《明彖》中提到的“一卦五阳而一阴,则阴之为主矣;五阴而一阳,则阳之为主矣”[4](P591),总之是一卦中具有主导性的一爻。然而,如果某卦中并无此为主一爻,那么该卦又如何解释呢?对此,王弼认为“或有遗爻而举二体者,卦体不由乎爻也”[4](P592),此处“遗”是遗弃之意,也就是说抛弃一爻为主的方式,改由通过卦的上下二体的具体属性来解释卦义。实际上,就整个六十四卦来看,《彖传》对许多卦义的解释往往都是两种情况兼有,甚至有些卦会出现一些模仿《大象传》的解释方式,如《蒙·彖》曰:“山下有险,险而止,蒙。”又如《恒·彖》曰:“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这或许与《彖传》与《大象传》形成的先后有关,如廖明春就认为这是因为《大象传》成书早于《彖传》[6](P208)。但总体上,王弼对《彖传》体例作出的阐发是非常准确和精炼的。
《小象传》是对爻辞的解释,它的解释体例一般是先引述爻辞语句,然后点明此爻辞的由来或所要表达的主旨。如《需·九二·象》:“虽小有言,以吉终也。”又如《复·六五·象》:“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相比《大象传》立足于卦本身之象,《小象传》则更偏重人事上的象征与比附,并在此基础上点明爻义之由,因此《小象传》虽然以“象”为名,但它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解释系统。整体来看,《小象传》的解释重心更多地落在了爻辞语句的解释上,这些解释或训释字词,如《屯·六二·象》:“十年乃字,反常也。”或说明缘由,如《讼·九五·象》:“讼元吉,以中正也。”或言明结果,如《睽·六五·象》:“厥宗噬肤,往有庆也。”但最终都将爻辞之义归结到实际的人事之上,从而让抽象的爻辞得到了落实。因此,可以说没有《小象传》,我们将很难理解《周易》爻辞的内涵。王弼在注解爻辞时紧紧抓住了这一点,他对每一爻的解释基本上都扣合了《小象传》之旨,如《坤·六五》:“黄裳元吉。《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王弼注曰:‘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坤为臣道,美尽於下。……垂黄裳以获元吉,非用武者也。极阴之盛,不至疑阳,以文在中,美之至也。’”[4](P228)又如《需·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白我致寇,敬慎不败也。’王弼注曰:‘寇之来也,自我所招,敬慎防备,可以不败。’”从王弼对爻辞的解释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小象传》的秉承,而这种秉承也就决定了王弼的《周易注》舍弃象数、注重义理的特点。同时,由于《小象传》文本较为简略,这给王弼解释爻辞留下了较大的空间。实际上,正是在对《小象传》的参考下,王弼对爻辞作出了许多独到的解释,这些解释既阐明了《小象传》的主旨,也充满王弼个人化的风格,其中最显著的就是他对爻位的人格化处理和义理的政治化解读。
三、对《象传》的承袭
《象传》是“十翼”中对每一卦的卦爻都有具体解释的篇章,可分为《大象传》(解释卦辞)和《小象传》(解释爻辞)。对于《大象传》,相比上文提到的《彖传》较为多变的解释方式,它的风格则较为统一,大致可概括为“依卦象而言德”,具体而言就是先以整个卦的上下二体所指代的物象(一般是从上卦至下卦)言明整卦的象征意义,然后将其引申至君子或先王之德。如《蒙·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4](P240)又如《豫·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4](P299)相比于《彖传》对“义”的重视,《大象传》显然更重视“象”。不过,虽然本身并不直接解释卦义,但由于将卦象最终都落实到君子之德,因此《大象传》所要传达的主要还是儒家的旨趣和价值。由于《大象传》体例清晰、主旨明确,所以王弼对其注解除个别卦以外并没有作出太多的引申或发挥,而是紧扣其所要阐发的儒家义理。如《睽卦》:“《象》曰:‘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王弼注曰:‘同於通理,异於职事。’”[4](P405)讲出了君子“同”和“异”之所在。又如《习坎卦》:“《象》曰:‘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王弼注曰:‘重险悬绝,故水洊至也。不以坎为隔绝,相仍而至,习乎坎也。至险未夷,教不可废,故以常德行而习教事也。习于坎,然后乃能不以险难为困,而德行不失常也。故则夫习坎,以常德行而习教事也。’”[4](P363)王弼的解释基本遵循了卦象的寓意以及《大象传》所要传达的儒家旨趣。因此,如果说《大象传》主要是将卦辞与儒家价值相联系,那么王弼在对《大象传》的解释中所做的工作就是将这种联系进一步明确化,而这种明确化保证了其卦象解读的儒家底色。
王弼对《彖传》的发明还体现在他对《彖传》所释卦辞义理的遵循上。《系辞传》云:“智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4](P570)王弼在注解《周易》时很好地抓住了这一点,他对绝大多数卦辞的解释都是依据《彖传》之文,如《姤》卦:“女壮,勿用取女。《彖》曰:‘姤,遇也。柔遇刚也。’王弼注曰:‘施之于人,即女遇男也。一女而遇五男,为壮至甚,故不可取也。’”[4](P439)有些卦他甚至直接通过注解《彖传》来阐明卦义,如《益》卦的卦辞无注,“《彖》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王弼注曰:‘震,阳也。巽,阴也。巽非违震者也。处上而巽,不违于下,损上益下之谓也。’”[4](P427-428)当然,王弼对《彖传》的解释除了阐发其主旨外,还作出了自己的解读和引申,如《乾卦》:“《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王弼注曰:‘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能永保无亏,为物之首,统之者岂非至健哉!……乘变化而御大器,静专动直,不失大和,岂非正性命之情者邪?’”[4](P213)王弼以“健”为“用形者”的说法虽然来自《文言》,但将“形”视为“物之累”的说法则有几分“得意忘象”的味道;而从“静专动直,不失大和”的角度来解读“各正性命”,在参考《彖传》之意的同时作出了较为合理的引申,则又使传文的解释变得更加丰富。再比如《讼·彖》王弼注曰:“凡不和而讼,无施而可,涉难特甚焉。唯有信而见塞惧者,乃可以得吉也。犹复不可终,中乃吉也。不闭其源使讼不至,虽每不枉而讼至终竟,此亦凶矣。……无善听者,虽有其实,何由得明?”[4](P249)相比传统道家推崇的“不尚贤,使民不争”,王弼在这里阐发听讼者以其刚健而听讼且不失“中”这样一个标准,其所要强调的恰恰是“善听者”在争讼中所发挥的作用。王弼的解释发挥合理,也和整卦主旨形成一致。当然,王弼在解释《彖传》时,也吸收了一些卦变的学说,如《贲卦》:“《彖》曰:‘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王弼注曰:‘刚柔不分,文何由生?故坤之上六来居二位,柔来文刚之义也。’”[4](P326)这里似乎使用了“升降”的说法,但这实际上与王弼依《彖》解卦是分不开的,因为“《彖》本有刚柔往来说”[5](P264)。
四、人格化的爻位观
王弼在注解《乾·文言》时提到:“以爻为人,以位为时,人不妄动,则时皆可知也。”这就等于将三百八十四爻的每一爻都落实为具体的人,爻所处的位也就等同于人所处的位,从而就形成了一种人格化的爻位观。具体来说,卦中每一爻的位由下至上应该为初、二、三、四、五、上,但从《易传》文本来看,《象传》中初与上都没有得位或失位的表述,而《系辞》在谈到“同功异位”时也往往将三与五、二与四并列,并没有提到初与上,这是为什么呢?在王弼看来,这是因为“初上者是事之终始,无阴阳定位也”[4](P613),因此初与上是不论位的(“初上无位”说)。既然如此,那么余下的四爻之位具体为何呢?王弼说:“夫位者列贵贱之地,待才用之宅也。爻者守位分之任,应贵贱之序者也。位有尊卑,爻有阴阳,尊者阳之所处,卑者阴之所履也。故以尊为阳位,卑为阴位。去初上而论位分,则三五各在一卦之上,亦何得不谓之阳位?二四各在一卦之下,亦何得不谓之阴位?”[4](P613)这也就是说,三、五在各自的卦中为尊(居于上),所以是“阳位”,二、四是各自的卦中为卑(居于下),所以是“阴位”;而且,由于阳尊阴卑,所以阳爻居阳位或阴爻居阴位就是得其位,否则就是不得其位,而不得其位于《周易》而言就是不得其正。这样,通过对爻位人格化的安排,王弼将现实中不同地位的人都一一对应于相应之爻,并以阴阳之别来比附尊卑之序;由此,高低贵贱、等级分别都通过爻的不同属性、地位被表现出来,而讨论爻位关系也就变成了讨论人与人之间的位序关系。
由于王弼对每一爻以及爻位之间的变化都赋予了人格化的色彩,因此他在解释卦爻辞时也就自然更加偏重人事方面的论述,“王弼将卦爻的变化看成是事物的变化,特别是人事变化的一面镜子,认为人类的行动应以爻变为指南,此即‘爻以示变’”[5](P270)。所以在他这里,卦爻及其位序的变化不光代表着高低位序的转换与其中的利害关系,而且更多地体现出一种人事中的闪转腾挪:“虽远而可以动者,得其应也;虽险而可以处者,得其时也;弱而不惧于敌者,得其据也;忧而不惧于乱者,得其附也。柔而不忧于断者,得其御也。”[4](P604)如《颐·初九》:“舍我灵龟,观我朵颐。王弼注曰:‘朵颐者,嚼也。……居养贤之世,不能贞其所履以全其德,而舍其灵龟之明兆,羡我朵颐而躁求,离其致养之至道,窥我宠禄而竞进,凶莫甚焉。’”[4](P352)这种解释就完全抛弃了象数易学从互体或升降来解释“灵龟”与“朵颐”的方式,而将其落实于具体人事中的进退出处。“刊辅嗣之野文”的李鼎祚尝言:“郑则多参天象,王乃全释人事。”[7](P5)实际上,王弼在偏重人事论述时,更多地是将人事落实于政治层面,如《蛊》卦“先甲三日,后甲三日”之语,王弼注曰:“甲者,创制之令也。创制不可贵之以旧,故先之三日,后之三日,使令治而后乃诛也。”[4](P308)这样的解读完全摒弃了象数易以天干地支来解释“先甲”、“后甲”的方式,而是将其落实于实际的制度创制和遵守。又如《巽·九五》“先庚三日,后庚三日”之语,王弼同样也摒弃掉象数的思维,将“庚”解读为具有实际意义的“申命令”,进而论述其中的政治准则。此外,还有《讼》卦对于听讼的辨明、对于“尚贤”的强调,《师》卦对于将帅品德的强调和军事驻扎战略的阐发,这些注解都是通过具体的政治事例来解释卦爻辞,从而充满政治化的色彩。通过这种政治化的解读,王弼的易学不但确立了“形式服从于内容”[8](P105) 的解释学主旨,而且也使《易传》的义理内涵得到了充分的阐发。
五、政治化的卦爻解读
对于爻位之间的具体关系,王弼在《周易略例》的《明卦适变通爻》和《辨位》二篇中进行了集中阐释。在《明卦适变通爻》中,王弼说:“夫应者,同志之象也;位者,爻所处之象也。承乘者,顺逆之象也,远近者,险易之象也;内外者,出处之象也;初上者,终始之象也。”[4](P604)这可以说是王弼对爻位关系所作的最为精辟的归纳和解读。在此他首先解释了“应”和“位”。“位”即爻在卦中所处的位置;“应”是爻与爻之间的对应关系,具体而言就是初与四对应、二与五对应、三与上对应。王弼所言“同志之象”就是指处于应位的二爻阴阳相应,否则就是无应(或敌应)。明白了王弼对“位”与“应”的界定后,他对爻位之间的关系所做的辨析也就变得容易理解。王弼将爻位之间的关系列举为四种情况:其一,承乘对顺逆,顾名思义,处在下位对上而言是承,处在上位对下而言是乘,由此阴承阳(也即阳乘阴)就是顺,阴乘阳(也即阳承阴)就是逆。其二,远近对险易,按照楼宇烈的说法,就是“远难则易,近难则显”[4](P606)。其三,内外对出处,具体而言就是下卦为内言处,上卦为外言出。其四,初上对终始,即初为始,上为终。这样,通过对爻及爻位的人格化解读,一方面,王弼准确地阐明了《周易》卦象中每一爻的不同角色与相互关系;另一方面,他也因此创发出许多解释《周易》卦爻的新范式、新角度,这些新的范式和角度打上了王弼鲜明的个人风格,也为我们理解《周易》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途径。
将爻位关系视作政治上的君臣关系,由此爻位之间的变化也就成为对现实政治关系的一种模拟或投射,进而通过对卦爻进行政治化的解读,阐发君臣政治中的伦理职责、制度原则、行为准则、策略谋划等内容,这可以说是王弼解读卦爻辞的内在理路。如《比》卦中对于君主与诸侯之间“亲比”的论述就是通众爻与主爻的亲附与叛离来进行某种政治策略的演练,而对于“三驱”的解释也是将其与帝王狩猎的古礼相联系起来。又如《巽》卦中对“田获三品”的解释也是直接将其对应于《礼记·王制》中提到的天子、诸侯“三田”之礼。再比如《同人·上九》,王弼说:“楚人亡弓,不能亡楚。爱国愈甚,益为它灾。是以同人不弘刚健之爻,皆至用师也。”这里通过“楚人亡弓”的例子所要强调的其实还是一种儒家天下观。此外还有《大有·九四》:“匪其彭,无咎。王弼注曰:‘既失其位,而上近至尊之威,下比分权之臣,其为惧也,可谓危矣。唯夫有圣知者,乃能免斯咎也。三虽至盛,五不可舍,能辩斯数,专心承五,常匪其旁,则无咎矣。’”[4](P291)这实际上是讲述了一个君臣之间的政治伦理,通过臣下失位后的利害选择,王弼告诉我们对于君主与权臣的取舍不仅关乎正义,而且也关乎道义。当然,王弼政治化的解读也与《周易》卦爻辞本身相关,作为占卜语句,卦爻辞本身很多就是对君臣关系和政治事例的记录,但王弼的意义在于对卦爻辞进行政治化解读的同时,抛弃掉其中神秘化的联系和穿凿附会的比附,从而就让卦爻辞最终都落实于《易传》所阐发的政治哲理。就此而言,王弼对卦爻辞的解读虽然充满了独特的个人风格,但根本还是对《易传》主旨的遵循。
有关硝盐替代物的研究已涉及不同的添加物类型,以其特异的作用方式单独和复合替代硝盐的不同作用,如红曲红、焦糖色素、亚硝基血红蛋白色素等替代发色作用,乳酸链球菌素(Nisin)、天然植物提取物、乳酸菌和化学防腐剂等替代抑菌防腐作用,茶多酚、生育酚及天然植物提取物替代抗氧化作用,以及I+G、麦芽酚等替代增味作用等,但至今还未能找到更为安全、更为廉价,而又能完全达到硝盐多功能的替代添加剂。
结语
就《周易》的发展来看,汉代的象数易学可以说体系庞杂、蔚为大观,但也存在两个弊端:一曰繁琐。由于过多强调解《易》方式的新颖独特,汉代象数易学特别喜欢采用一些繁复的解《易》之法,如飞伏、纳甲、爻辰、升降、互体之类,尤其对于互体,竟有四爻、五爻连互之法,可谓繁琐至极。王弼言“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弥甚。纵复或值,而义无所取”[4](P609),就是对这种风气的指责。二曰虚妄。由于过于注重经文本身的卜筮作用,加之天人感应的学术思潮和谶纬之学的推波助澜,汉代易学形成了一种神秘主义的倾向,即将节气、历法、音律,乃至人身、官制等统统纳入到象数的框架之内,认为一切都可以在象数中得到解释。这种做法虽然有一定说服力,但更多的是穿凿附会。王弼正是看到了象数易学这种过度诠释所带来的危害,他归本《易传》,“沉淀了牵强附会的象数泥沙”[9](P286),这首先是对《周易》解释由繁琐走向虚妄,进而陷入神秘主义深渊的一种补救。其次,王弼以传解经,让《周易》归于道德义理,这不但开出了义理派的易学,实际上也是对《易传》旨趣的某种回归;王弼以后,诸家解《易》多注重阐发《易传》主旨,这与王弼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黄宗羲认为:“有魏王辅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时岁月,五气相推,悉皆摈落,多所不关,庶几潦水尽寒潭清矣。顾论者谓其以老庄解《易》,试读其注,简当而无浮义,何曾笼络玄旨。故能远历于唐,发为《正义》,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10](P11)皮锡瑞亦言:“孔子之《易》,重在明义理,切人事,汉末易道猥杂,卦气、爻辰、纳甲、飞伏、世应之说,纷然并作。弼乘其弊,扫而空之,颇有催陷廓清之功。”[11](P24-25)就此而言,王弼易学无愧于其里程碑的地位。
而就整个经学来看,李源澄在《经学通论》一书中曾说:“吾以为《易》之成为经学,由其离于象数而进于义理,而后人言经学,反以术数乱之,亦由其本为卜筮之书故耳。”[12](P54)因此,王弼易学对义理的重视和对儒家价值的阐发,实际也是对经学正统的一种回归。东汉后期,随着古文经学的大兴,经学的学风由偏重于章句义理而转向文字训诂,许多经学注解甚至以数万字解二三字,因此不唯《易》,整个汉代经学到东汉末期实际都走入了繁琐的误区。而王弼《周易注》所带来的变化首先就是对繁琐的训诂之风的扭转,他一反汉儒字字训诂的考据之风,采用简洁明晰的方式直接阐发义理。这种新的注经方式不但使经学风气从训诂重新回归到义理,而且也给当时的经学注解带来了一丝清新的气息,后世南北朝义疏之学(尤其南朝经学)“清通简要”的风格实际上就是从王弼这里发端的。值得一提的是,王弼这种注经方式同时也带来了魏晋时期文体的变化,如刘师培就认为:“厥后郭象注《老子》,张湛注《列子》,李轨注《法言》,范宁注《谷梁》,其文体并出于此,而汉人笺注文体不复存矣。”[13](P34)此外,王弼《周易注》多言人事,人事中又多偏重政治,并对许多政治问题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和见解,这其实和经学的现实关怀精神是相契合的。王弼在《周易》注解中虽然注入了一些老庄思想,但这些思想并非全为阐扬道家宗旨,其中不少都兼顾了儒家的思想旨趣,在没有违背《易传》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这未尝不可以看作是对经学增添的一些新鲜血液。
参考文献 :
[1]刘大钧.20世纪的易学研究及其重要特色——《百年易学菁华集成》前言[J].周易研究,2010,(1).
[2]张善文.王弼改定周易体制考[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9,(2).
[3]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4]楼宇烈.王弼集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2.
[5]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一卷)[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
[6]廖名春.周易经传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7]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2.
[8]余敦康.汉宋易学解读[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9]王晓毅.王弼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0]黄宗羲.易学象数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1]皮锡瑞.经学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2]李源澄著作集[M].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8.
[13]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6.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Wang Bi ’s Hermeneutics of Zhou Yi in the View of Confucian Classics
WANG Wen-jun1,ZHANG Li-wen2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
Abstract :From the view of Confucian classics, Wang Bi’s Hermeneutics of Zhou Yi presents the explanatory style of“explaining the I Ching through the appendices”. On the format of Zhou Yi text , he attached the appendices to the I Ching,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appendice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Guaci and Yaoci, he adhering to the idea of Guaci by Tuan Zhuan and Yaoci by Xiang Zhuan, and created a lot of new paradigms; On the tendency of interpretation, it conveys the political purport through the personified view of position of Yao. Wang Bi’s annotation of Zhou Yi is a remedy to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Yi-ology which developed from tedious to false and fell into the abyss of mysticism, following the basic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of the appendices which guarantees the ground colour of Confucian classics, which may be the real reason of his Zhou Yi annotation accepted as the authoritative interpretation of five classics by later Confucian.
Key words :Wang Bi; Zhou Yi; hermeneutics; Confucian Classics
收稿日期 :2018-04-10
作者简介 :1、王文军,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2、张立文,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 :B23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22X(2019)02-0022-06
责任编辑 :李观澜
标签:王弼论文; 周易论文; 解释学论文; 经学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