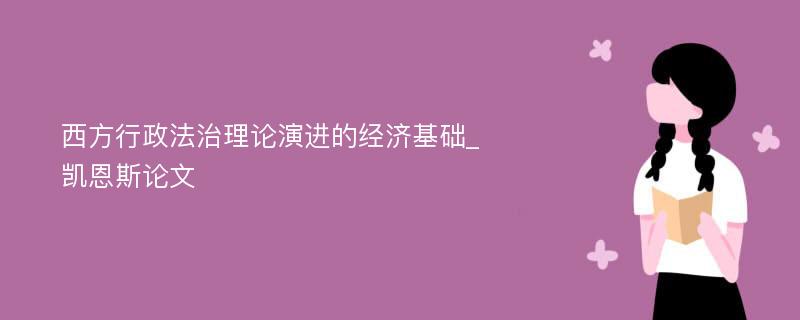
西方行政法治理论演进的经济学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治论文,经济学论文,理论论文,行政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国家的文化是多元的,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思想基础也是多元的。时代的发展、行政法的演变需要我们以更广博的视角来审视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发展历程。我们在关注其哲学基础、法理学基础的同时,亦不能忽视经济学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事实上,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是行政法学和宏观经济学所共同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经验表明,尽管“市场失灵”和对公平的关注提供了政府干预的经济学基础,并由此诞生了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和福利经济学,但市场的不完全和信息的不对称等同样导致“政府失灵”,而试图以政府替代市场的做法将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市场失灵置换了市场万能的观念,政府失效拒斥了国家的神话。可见,没有一个有效的法治政府,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促使我们再次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政府的作用是什么,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及如何更好地去做这些事情。因此,如何在尊重市场逻辑的前提下建设一个有效的法治政府已成为全世界重新关注的焦点。本文拟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阐释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发展历程,洞察其历史脉络及深层次的发展规律,并窥探其发展趋势。这对于政府角色的重塑,政府功能的重新定位以及新世纪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和完善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经济自由主义与警察行政法观
17~19世纪是资产阶级夺取并巩固政权,发展资本主义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尚未摆脱封建统治阴影的笼罩,深感丧失自由和财产的恐惧。因而,他们要求取消一切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措施和政策,论证并且实现经济自由,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深信“最好的政府,最少的管理”。这使得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各国无不围绕“行政权力”构建本国的行政法律制度。在素有“行政法母国”之称的法国,19世纪70年代以前,行政法治理论基本上是以拉菲利埃(E.Laferriere)提出的“公共权力说”为主流。按照“公共权力说”,行政行为被区分“权力行为”和“管理行为”,前者是行政机关在立法机关的授权下执行国家意志的一种行为,受行政法约束,并接受行政审判权的监督;而后者则是行政机关作为社会生活的参与者和组织者而为的一种行为,属于私法范畴,接受司法审判权的监督。通过这种区分,行政法的主要任务被确定为划分公共权力与私人失误之间的界限,并对超过这一界限的“越权行为”予以制裁。这样,行政权的作用便被局限于国防、外交、警察和税收等以“权力行政”为特征的狭小范围。“公共权力说”确立后,影响到整个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法理论。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的行政法治理论称为“警察行政法观”。
这种行政法治理论不仅是当时生产关系状况的反映,而且也与当时的主流经济学——新古典学派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相一致。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将整个经济系统分为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国际贸易、政府预算、居民收支等紧密相联的组成部分。“看不见的手”并不是简单地调节其中某一个市场,使其实现供求平衡,而是通过价格信号同时对整个系统发生作用。任何一个外来冲击,如某种商品的价格或数量的变化,某项政府政策的变化,都会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系统的每一部分。如果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同时达到均衡的话,这就是“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如果外来的冲击破坏了初始的均衡状态,那么,“看不见的手”将通过价格调整,使其转向另一个均衡。
新古典学派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他们认为,政府的干预很可能会阻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给经济系统带来扭曲,从而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有了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不需要政府干预了。但是,新古典学派并不完全排斥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他们主张建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把政府的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即政府应当保证发展生产、公平贸易和积累财富的外部环境,并且向社会提供那些私人所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public goods)。(注:参见[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7页。)于是,政府甘居幕后,扮演“警察”的角色,担当起社会“守夜人”,行政职能集中于“秩序行政”,即保障国家的安定、社会安宁,维护私有财产权和契约自由。
二、国家干预主义与福利行政法观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断发展壮大的资本主义创造出了比以往任何社会都要丰富的物质财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由自由竞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周期性经济危机开始频繁爆发。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社会关系更趋复杂,社会形势的变化更趋迅速,但个人的生存能力却受到社会的严重制约,就业、教育、卫生、交通以及环境等都已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解释经济危机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经济学家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对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研究。在这一时期,新古典学派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受到挑战。在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L.Walras)的均衡理论和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下,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K.G.Myrdal)和林达尔(E.R.Lindahl)提出了动态均衡理论,以德国经济学家施穆勒(G.V.Schmoller)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和以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T.B.Veblen)为代表的制度学派也相继产生。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上述理论与经济自由主义截然不同,它们主张政府应对经济进行干预,强调政府在调节和管理经济中的作用。在政治方面,它们宣扬阶段利益调和,迎和了资产阶级加强统治的需要,因而对当时西方各国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注:参见厉以宁:《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湖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62~66页;陈孟熙主编:《经济学说史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7~405页。)
于是,在西方国家,行政权的作用范围开始拓展。政府在实施有限的间接调控的同时,也开始少量地直接投资,从事教育、卫生、交通以及公共事业等方面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典型的“权力”特征已经很微弱。但这些活动又是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不同于私人行为,因而不受民法规则支配而适用行政法规则。在这种形势下,法国行政法上传统的“公共权力说”开始动摇,以狄骥(L.Duguit)为代表的波尔多学派提出了“公务说”。“公务说”认为,“行政法是公共服务的法”,行政行为也是“以公共服务为目的的个别性行为。”(注:[日]兼子仁、矶部力、村上顺:《法国行政法学史》,岩波书店1990年版,第17页。转引自何勤华:《西方法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0页。)按照这一标准,行政主体直接以满足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活动都是公务行为;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服务与合作的信任关系;政府的服务是一种通过执行法律为公众提供的服务即公务,因而服务与合作关系就是一种公务关系;公务构成了行政法的基础,行政法将随着公务的需要而变化。“公务说”产生后,对大陆法系国家以及一些其他国家的行政法都产生了影响。从此,发生了西方行政法治理论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
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发于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给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带来了致命的冲击。这次经济危机的时间之长、程度之深都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期。按照传统的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无论经济繁荣或衰退,政府都不应当积极干预经济活动,“看不见的手”会自动把经济导向稳定状态。可是,这只“看不见的手”并没有把资本主义国家从经济危机中拯救出来。面对严峻的挑战,政府显得软弱无力。资产阶级理论家们认识到,对这种社会形势,除了政府之外,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或个人能够应付,政府的角色有必要重新塑造。
时代呼唤出来一个全新的经济理论——政府干预主义。凯恩斯(J.Keynes)在1931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凯恩斯认为,完全的市场机制是“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关于完全市场机制的假设往往并不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经济行为的外部效应以及交通运输约束等情况的存在,使得市场机制失灵(marker failure)。凯恩斯认为,周期性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他用“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偏好”三大心理规律来解释这一命题,并指出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中必然会产生有效需求的不足。按照凯恩斯提出的“有效需求原理”,在小于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只要存在着一定量的总需求,就会产生相应数量的总供给。既然“看不见的手”不能有效地对市场进行调节,那么就应当让政府担当起调节供求关系的责任。据此,凯恩斯认为应当放弃主张自由放任、无为而治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国家应当积极地干预经济,扩大政府职能,刺激投资和消费。同时,他认为政府直接投资不仅可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以维持国民收入的应有水平,而且政府每增加一笔净投资,还可以通过乘数效应带动私人投资和消费,使国民收入量比最初的净投资额有成倍的增长。因此,凯恩斯“希望国家多负起直接投资之责”。(注:[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9页。)总之,政府的责任就在于运用各种政策以纠正市场失灵,保证资源优化配置,抚平经济周期波动的创伤,促进经济发展。只有政府为社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才能使公共利益最大化。
后来,这一理论发展为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官方经济学”。于是,行政权力开始大举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资本主义由一般垄断阶段过渡到国家垄断阶段以及各国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发展,行政权也日益膨胀,行政立法大规模出现。在社会生活中,行政权的作用已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以促进公共福利为目的行政服务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面对新形势,“福利国家论”应运而生。尽管随着“福利国家”等现象的出现,“公务说”已不能全面界定行政法的外延,出现了行政法理论基础多元论的局面,但行政法理论中服务与合作的基本精神并未改变,即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给相对人以“生存照顾”是行政主体的职责;享受服务、得到“福利”是相对人的权利。在这一时期,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关系的主体范围不断拓展。同时,因分享公共利益而形成的关系以及因行政事实行为引起的关系也都被纳入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关系的范围。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甚至开始将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关系的触角伸向了传统的民法领域。总之,这一时期行政法理论的中心思想是:只有不断地缩小市场机制作用的领域,扩大行政权力作用的范围,才能为相对人提供更为广泛的服务,公共福利才能实现最大化。因而,我们可以称之为“福利行政法观”。
三、政府干预主义的困惑、修正及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重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风光了几十年。一直到70年代初,普遍奉行政府干预主义的西方各个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稳定增长,并没有遭遇到较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7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的经济却遇到了麻烦——“滞胀”现象,即高失业与高通货膨胀并存。尽管各国政府按照凯恩斯的主张采取了各种药方,但是经济衰退仍越来越严重。对此,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既不能在理论上给以解释,又不能提出有效对策。特别是70年代“雪上加霜”的两次石油危机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更是动摇了政府干预主义的基础。于是,主张经济自由、减少政府干预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学者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展开了尖锐的批评。西方各国也相继放弃政府干预主义,而选择经济自由主义为制定政策的指导原则。到80年代末期,过度的放任自由导致西方国家的经济又一次出现衰退,国家干预主义重新得势。
看起来,似乎新古典学派主张的经济自由主义与凯恩斯学派主张的政府干预主义在经济学舞台上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是,无论是新古典学派还是凯恩斯学派,都在不断地汲取对方的长处,修正自己的观点。例如,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Samnelson)把自己的学说称为“新古典综合学派”或“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1985年以后又改称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又如,克林顿政府强调政府干预,不过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并不是片面地强调增加需求,而是采取既强调需求方面,又强调供给方面的两手政策。克林顿也认为,自己的经济政策既不是新经济自由主义,也不是政府干预主义,而是一条结合两者长处的新道路。(注:参见徐滇庆、李瑞:《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总之,两大学派的融合反映了西方宏观经济学正在加深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探寻政府权力作用的最佳范围,整个资本主义也“几乎在不知不觉中,演变成保持公私两个方面主动性和控制权的混合经济。”(注:[美]萨缪尔森:《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31页。)
面对宏观经济理论各派林立,争论不休,国家政策频繁变动的新情况,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西方行政法治理论也表现出了应有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行政权作用范围的有限缩小。学者们认为,在现代社会,政府并不是唯一的“公共体”;“公共产品”除了可由行政主体提供外,还可以由其他公共体——社会自治组织提供。这是因为,非政府的社会公共体行使公共权力,可以避免或减少行政国家异化的许多弊端,如腐败、低效率、滥用权力等。而且由于它更贴近公众,公众可更直接地参与其运作和更直接对之进行监督。除此之外,学者们也认为,过分强调为公众提供全方位的“生存照顾”会使人的生存能力和创造能力退化;行政权的过度延伸不仅不会使公共利益进一步扩大,而且还会对其产生抵销作用;应该重新重视市场机制激励作用,“只有在个人无力获得幸福时,才由国家提供服务。”(注:陈新民:《宪法基本权利之基本理论》,台湾三民书局1992年版,第145~152页。)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纷纷对行政权重新估价,放松政府管制而加大市场调节的力度。政府也将一些政府垄断项目转到市场竞争领域,或者引入市场机制到公共领域适用。于是,国家行政、社会公共行政的结合和对私人力量的利用便构成了维护、分配和发展公共利益的多元力量结构。(注:参见于安:《新世纪行政法的发展问题》,《法制日报》2000年2月20日第3版;姜明安:《行政国家与行政权的控制和转化》,《法制日报》2000年2月13日第3版;[美]理查德·D·宾厄姆等:《美国地方政府的管理——实践中的公共行政》,九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3页。)
第二,行政强制的弱化。西方学者认为,行政行为既然是一种服务,在相对人能自觉合作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公共利益能够实现的情况下,也可以不运用强制性的行政行为,而运用一些非正式、非强制的行政行为来服务。并且,传统上以“公权”和“强制”为特征的行政行为的性质及形式,都需要重新界定和概括。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在行政法上便反映为:一些新的行政行为形式或者原来在行政法领域中不甚重要的行政行为形式,如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规划、行政给付和行政私法等,已经或者将在行政中发挥新的或者更重要的作用。行政合同和行政规划在法国,行政指导在日本以及行政给付在瑞典等都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行政法制度。这些行政行为形式中既包含了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又体现了相对人的意志,既有行政权力的因素,又有市场自由的精神。它们所具有的应急性、简便性、温和性和实效性等特点,也正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第三,行政程序法治理念的增强。学者们普遍认为,新时期行政法治不仅应重视服务的结果或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而且还应强调行政程序,即服务与合作的过程。通过行政程序,扩大行政民主,调动相对人对服务的合作或参与,增进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相互沟通和信任,使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融合相对人的意志,使行政行为具有公正性、效率性、准确性和可接受性,以避免行政权在其作用领域中的滥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因对抗而致使公共利益遭受损失。而行政强制的弱化,行政程序法治观念的增强,必然会促使行政效率的提高,公共利益的实现。为此,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行政程序法典化浪潮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仍然方兴未艾。
四、结束语
西方行政法理论的发展历程表明,“市场失灵”的另一面是“政府失效”。“福利国家”在给公众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公共产品”的同时,也魔术般地生产出各种各样的“副产品”。当代西方行政法治理论在科学地认识行政权力与市场机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一前提下,坚信服务与合作是其基本精神,同时也更强调服务的实质。因此,当代各国行政法无一例外地都在努力探寻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最佳结合点,即服务与合作范围的最佳边界。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行政法是形式上的服务行政法,那么当代的行政法便是实质上的服务行政法。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上述变化,与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演进是同步的,是西方各国关于国家观念、市场功能、政府角色、行政模式的认识和政策不断演进的共同结果。总之,增进社会福利,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全面提高人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当代行政法的价值追求。
标签:凯恩斯论文; 政府干预论文; 行政主体论文; 市场机制论文; 经济学基础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凯恩斯经济学论文; 行政法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市场失灵论文; 法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