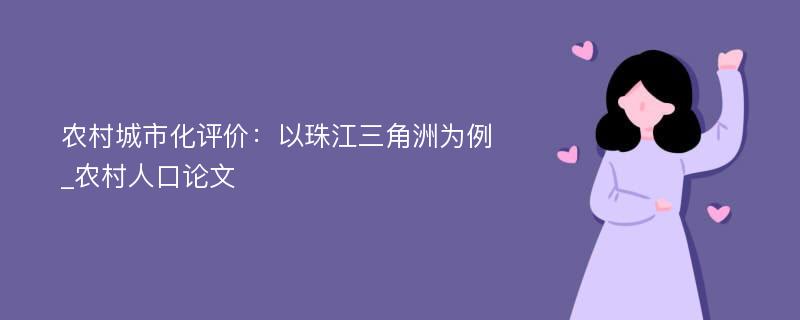
农村城市化的评价——以珠江三角洲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评价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研究农村城市化,必然要对农村城市化的现状和水平进行评价。然而,我国学者大都借助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即所谓城市化率进行总体判断。这一判断虽也简明扼要,但由于过于概括,缺少生动具体的内容,而显得苍白。这里的问题是:农村城市化是一项实证性很强的研究,如果不对农村城市化、尤其是各个不同地区的现状进行准确描述,则很难提出针对性强的实证对策和措施。再仔细琢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是整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城市化率,这就产生了一个比较口径是否对称的问题,农村城市化能等同于整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吗?逻辑告诉我们二者显然是有联系但绝对不能等同的两个概念。那么什么是农村城市化?农村城市化与城市化是一个什么关系?看来要对农村城市化进行评价,还得首先正确把握农村城市化的内涵。
二、农村城市化探源
农村城市化是中国的概念。虽然它不径而走,流传甚广,但却未见对它有过权威性的解释。农村城市化首先是一种城市化,而城市化与工业化是紧密相关的。因此,本文从经典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理论及其实践的分析来寻求农村城市化的诠释。
经典工业化理论是5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W·刘易斯首先提出的(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式,1954年),后经由另两位美国经济学家G·拉尼斯和J·费景汉完善(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式,1961,1964年),并在诘难者们(如D·乔根森“新古典模式”,1961年;M·托达罗“三部门模式”,1969年)的修正和补充中逐渐发展和形成起来的。这个理论虽不形成为一个单一的体系,而是组合补充,但它有一个特点,就是经历了由忽视农业、忽视农村,到重视农业、重视农村发展的转变。刘易斯模式是不重视农业的典型,它认为在落后国家农村传统农业部门中存在着相对于固定制度工资水平而言的无限劳动力供给,可以为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全部所需的劳动力。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现代工业部门,工业化的扩张过程也就是城市化的过程,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一对共生现象。按照已经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城市化水平低于工业化水平,在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化水平变得高于工业化水平,二者差距呈扩大趋势。后来有经济学家进一步论证了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伴而行的原因是城市为工业提供基础设施、社会福利和市场信息服务,使之产生或发挥“聚集经济效益”和“规模经济效益”。
然而,刘易斯模式的实施在发展中国家却带来了始料未及的后果。由于经济发展被片面理解为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化,大量农业劳动力象潮水般涌进城市,却远难为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制度工资杠杆也未能起到制约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作用。一方面,农村由于劳动人口的“出走”而凋敝,另一方面,城市人口膨胀超载,使得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后期才出现的城市膨胀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初期阶段就以极其尖锐的形式出现了。发展中国家既苦于工业化不足,又苦于城市化过度。
严酷的现实迫使理论反思。痛定思痛,在农业严重停滞的6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从为工业化提供剩余的角度开始强调农业。60年代中期开始,人们更意识到农业的发展将不仅具有“工具价值”,而且具有“内在价值”。经过一段时期的“磨合”,重视农业和农村发展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共识。于是,在农村改造传统农业和发展小型工业被提了出来。在这场认识的大转变中,美国发展经济学家G·迈耶、T·舒尔茨和M·托达罗等的论著成为不朽的篇章。他们论证道,改造传统农业,既提高农业的收入和产出率,又保证向工业化提供农业剩余;发展乡村小型工业,开辟了农村就业的新渠道,又把工业化进程引到了农村。由此,农村工业化的概念不径而走。然而,农村工业的发展早期极具自发性和分散性,尤其与农村全面发展脱节,以致在农村经济内部滋生着一个“次二元经济结构”。于是,在70年代后期,农村综合发展、城乡一体化又被提了出来。这种思想注重农村全面发展,注重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的协调,注重农村与城市社会经济的融合。这种思想也许就是农村城市化的萌芽。
农村城市化这个概念是中国的发明。虽然谁是始作俑者已难以考证,但其渊源是明确的。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50-70年代只是限于城市,国家在从农村吸取资源的时候,坚决地采取了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的政策。中国工业化是以城市为中心的。由于控制城市数量的发展,少数大城市成为经济发展的“孤岛”,城乡之间隔绝,由此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化的滞后又反过来阻滞了工业化的进程,我国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呈固化的态势。但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毕竟是阻挡不住的潮流。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进入改革后,工业化的策略转为向农村扩张。由于财力薄人口多的特殊国情,中国不可能大力发展城市来吸收农村劳动力,而是选择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就地发展农村工业,并企图在此基础上形成农村城镇。由于这条道路的立足点是农村,因而被称为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因此在广义上,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工业化看作是农村工业化,把中国的城市化看作是农村城市化,这是二者之间的联系。但是二者毕竟有所不同,工业化和城市化被冠以“农村”后,就具有了强烈的地域色彩。在工业化这个系统中,城市和农村是两个子系统,具有不同的任务;在城市化这个系统中,城市和农村作为两个子系统,也具有不同的发展任务。在特定的研究场合,必须把它们区分开来,否则就搞不清楚研究的对象,混淆不同的发展任务。农村城市化是以农村这个地域为范围界定的。严格地说,中国过去只有少数的特大城市,其余都是农村。目前一些学者不把中等城市看作农村城市化的研究内容,似乎农村城市化只研究县城以下,这是不妥的,因为这无法准确描绘我国农村城市化的真实轨迹,也无法涵盖县改市、市带县体制下我国农村城市化的全部内容。
三、农村城市化的评价思想
从上述理论和实践的回顾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动力,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直接结果。城市化和工业化在量上存在一定的规律性联系,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推动力,因此,城市化水平的评价离不开相应的工业化水平作为支撑。对农村城市化的评价也是如此。
2,城市化绝非工业化的被动结果,城市化对工业化具有极大的反作用,它为工业化提供基础设施、社会公共福利和市场信息服务。城市是基础设施的载体。考察城市化水平应以它能提供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为据,农村城市也应遵循这一规律。
3,人口城市化只是城市化的一个标志,但不是唯一的标志。非农经济发展才是城市化的本质,人口集中只是人口运动在这一过程空间上的投影,人口城市化不能概括城市化的含义。因此,片面考核人口城市化率,实质上是用“唯城市化”的观点来评价城市化。
4,农村城市化是从农村发展、城乡融合的思想繁衍的,因此应当特别注重农村城镇在社会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的实质变化,防止“空壳”城市。同时,还要注意农村城镇在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分工和网络联系,防止把农村城镇搞成放大的村落。
四、农村城市化的评价内容
根据上述思想,我们拟定如下农村城市化的评价内容:1、农村城镇数,包括地级市或带县市、县城、建制镇的集镇。此项指标从绝对数上反映农村城市化的发展状况。2、农村城镇人口数及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此项指标反映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水平。3、农村城镇集聚的乡镇企业数及其在乡镇企业总数、总产值中的比重。此项指标反映农村城市化得自工业化的支持程度。4、农村第三产业产值和劳动力比重。第三产业是农村城市中一个方兴未艾的部门,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考核这一部门具有特殊的意义。5、农村城镇基础设施,包括:(1)农村城镇自来水供应能力;(2)农村城镇供电能力;(3)农村城镇工业区建筑面积;(4)农村城镇公路总长度;(5)农村城镇交通运输能力;(6)农村城镇通讯设施(电话);6、农村城镇生活设施。此项指标反映农村城市化的生活质量,包括:(1)住宅面积,(2)公共文化设施(影剧院,体育场,图书馆,公园,等),(3)学校和医疗机构。
五、案例分析: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下面,我们将按上述评价思想和评价内容,对珠江三角洲农村城市化进行评价。珠江三角洲是改革以来我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也是目前我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珠江三角洲的农村城市化呈现如下特点:
1,农村工业化推动农村城市化快速前进。改革以前,珠江三角洲地区除了广州这一个大城市和佛山、江门这两个省辖市,均是以农业为主的县城,建制镇30多个,平均每850平方公里才有一个建制镇。70年代珠江三角洲地区已有不少乡镇企业,工业产值已超过农业。1978年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76.8%,但70%以上都集中在广州、佛山和江门三市,尤其是55%集中在大城市广州,而这三市的国土面积和人口仅占整个珠江三角洲的6.5%和28.8%,可见中心城市成为经济发展的“孤岛”。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很低,1980年仅27.4%。进入80年代,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开始起飞,到90年代初已步入工业社会。珠江三角洲工业化的进程主要表现为农村工业化。1991年珠江三角洲拥有乡镇企业26万家,总收入591.34亿元,占全省乡镇企业总收入58.7%。在珠江三角洲农村社会总产值中,乡镇企业四分天下有其三。农村工业化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城市化的进程。改革以来珠江三角洲先后有18个县撤县建市,中山、东莞升为地级市,并陆续建立起一批农村城镇,到1993年底,珠江三角洲有建制镇近400座,每70平方公里就有一座城市(包括建制镇)。目前珠江三角洲已形成一个以广州为中心的现代城市群刍形。
2,基础设施建设方兴未艾。城市是基础设施的载体,建城市就一定要建基础设施。改革以来,珠江三角洲花大力气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据有关资料,1991年三角洲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18亿元,比1980年增长17.8倍,年均递增达30%。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区通车里程5.4万公里,公路密度为每100平方公里39.9公里,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多,其中东莞市每100平方公里有公路88公里,密度居全国之冠,甚至超过韩国和台湾。改革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还修建了近1000座公路桥梁,主干公路已无轮渡。但由于以公路运输为主,车辆增多,运输依然紧张。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通讯建设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电话普及率大大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可直拨全国、港澳和世界各大城市。佛山市南海县实现县内自动拨号,是全国第一个农村电话自动化的县。能源方面,珠江三角洲各市投资办电,如广州兴建60万千瓦的珠江发电厂,珠海修建40万千瓦电厂,佛山自筹办电7亿度,这些大大缓解了珠江三角洲的电力紧张。但电力短缺依然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瓶颈”。供水方面,珠江三角洲水资源丰富,广州人均日用水300公升,居全国200多个城市之首。但水资源分布不均,个别地方(如深圳)供水仍比较紧张。
3,小城镇星罗棋布。珠江三角洲目前是全国小城镇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小城镇不仅在量上扩张,内涵也在增强。首先是小城镇的面积大大扩展,如中山市的城区面积从原来的6平方公里扩展到20多平方公里,扩大了3倍多,花都市的城区面积从原来一条街0.33平方公里扩展到6.7平方公里,扩大了20倍,一些新城镇城区从无到有,如南海市的桂城、中山市的东升等等。其次是大办工业开发小区。珠江三角洲各市普遍建有市(县)、镇、村三级工业开发小区,如号称“广东四小虎”的中山、东莞、南海、顺德4市,约有40%的管理区(行政村)办了开发小区,约12平方公里就有一个。三是市场建设。三角洲各市都建了一批功能齐备的地方市场、专业市场,如南海的西樵布匹批发市场,顺德乐从镇的塘鱼批发市场,东莞长安镇的纺织城等,活跃了商品流通。四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珠江三角洲各大小城镇的商饮服务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提高到平均10%左右。五是建成了一批中高档次的文化娱乐设施。影剧院歌舞厅已经普及,人民的精神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一些市、镇还建起了高质量的体育设施,如顺德、恩平、东莞修建的体育馆具有承办国际性比赛的能力。
4,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人民生活富裕。1978年珠江三角洲农业劳动力的比重高达85.5%,1992年已下降到35.5%。在中山、东莞、佛山、顺德等地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已不足20%。按现行户籍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统计口径,1994年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平均人口城市化水平已达41.7%,高于广东全省平均39%和全国28%的水平。如果加上外来打工人员,尤其考虑虽无城市户口但早已离农进城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人口城市化水平应当更高。80年代末90年代初,珠江三角洲人均国内总产值已超过800美元,提前进入小康。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基本结论:改革以来珠江三角洲的农村城市化已有长足的发展,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珠江三角洲的农村城市化还处于以量的扩张为特征的粗放阶段,集中表现为小城镇的发展过多过快过于分散,缺少一批起承上启下作用的中等城市和高质量的小城镇。珠江三角洲农村发展的很多问题都直接或间接与之有关。小城镇过多过于分散使基础设施达不到合理的规模,重复建设,使用成本很高;城市过小,集聚功能不强,也难以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就业机会;小城镇过多过于分散,浪费土地资源,也使环境污染的治理难度增大。限于篇幅和本文的重心,这里不可能就此作深入分析。我们认为,今后,珠江三角洲应当集中发展一批40—50万人的中等城市和高质量的小城镇,这既是弥补目前珠江三角洲城市体系结构的缺陷,也是珠江三角洲农村工业化升级发展的内在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