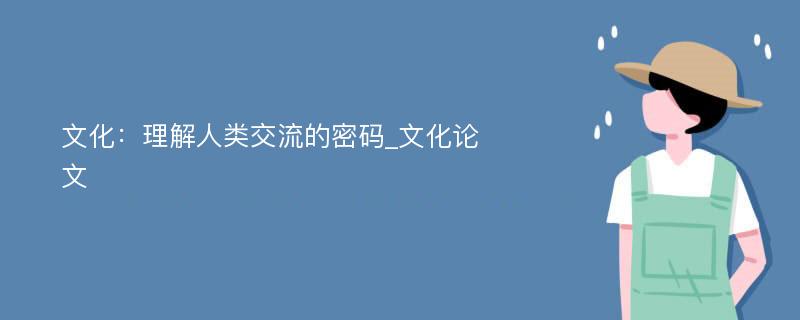
文化:理解人类传播行为的密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论文,密码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7)03—0094—06
尽管亚里士多德说人是“会说话的动物”,但古人最活泼有力的言语莫过于未启口时所呈现的能表达一切的符号。意大利以及普罗旺斯人,话未出口便已手舞足蹈,借此引起关注以取悦听众。塔尔昆、特拉叙布卢斯斫去罂粟花的花头,亚历山大将戒环靠在密友的嘴唇边,第欧根尼当着芝诺面跨步,这些象征性的行动显然比言辞更生动有力。大流士进军斯奇提亚时,斯奇提亚国王派人送来一蛙、一鸟、一鼠和五支箭。传令官呈上礼物时未置一词,大流士心知这是令人畏惧的檄文而旋即罢兵。印度商人在公共场所洽谈生意时,为了保密,他们只在握手时通过旁人无法觉察的手劲之微妙变化来传达意思。① 当然,这些传播行为都必须在同一文化语境中才能有效进行,因为语境决定了人们的解释并设定传播行为的意义。正如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在《文化与交流》(Culture & communication)中指出的:“当与朋友和邻居在一起时,我们会毫无例外地认为交流是包括许多言语和非言语的复杂的持续过程。只是当遇见非本民族的陌生人时,我们才会突然意识到,由于传达信息有各种习惯行为(不仅仅是语言行为)我们只有懂得其中的奥秘,才可能知道发生的是什么事情。”② 所以,人类传播行为的产生,不仅仅是来自于交流所用的器官的功能,还来自于对人们特有的习俗行为中那些奥秘的掌握。
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前卫派的文化人类学家,利奇着重探讨文化问题。他有许多关于分类学、时空观、生育观的论著。他认为文化(观念)形态反映了社会的现实结构,因而也决定了现实社会生活的方式。③ 他在《文化与交流》一书中所论述的中心思想就是:文化乃至文化习俗中的各种非言语方面,如服装风格、村落设计、建筑物、家具、食物、烹饪、音乐、身体姿势等等,被组织在模式化的系统中,其方式就像一种自然语言中的声音、语汇和句子一样。因此,文化应当是人类的交往(传播)系统,④ 它涉及社会成员间的意义生产、给予、交换和获得,它赋予人们源于共享的对于限制传播的文化因子认知的特殊能力。本文试以传播学视角,在利奇俯仰天地贯通古今地审视主导人类交流行为的文化习俗的宏阔视野中,发现提供给传播学超越地域、种族而升至理念的主导认识人类传播与交流行为的研究方法。
一、人类传播行为的多维存在
人类传播行为是意义的“浓缩形式”和盘根错节的文化习俗问题,它把人类种种自我冲突编进了自己的代码之中。在利奇眼里,“这种传播信息的方式包括:写作、音乐演奏、舞蹈、作画、歌唱、建筑、戏剧、医疗、崇拜等等”,因而,“所有的人类行为(不仅说话)均用于传播信息”⑤。而且它们表现于时空、心灵和社会之中。虽然这些维度是可观察到的、有形的和有序的,又是不可感知的、无形的和模糊不定的。总之,人类传播行为始终以某种固定的自我运动方式持续地影响和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之中。探究人类传播行为的多维存在,并非是探究传播行为在社会中的实际功用,而是探究超出“社会结构”的独立的传播体系,探究不同象征之间及象征与其所表示的意义之间的联系本身,藉此揭示人类传播行为如何影响社会行为者的世界观、精神与感知。
1.时空尺度中的人类传播
利奇认为,“习俗的每一细节都被看作是复杂整体的组成部分;人们认识到,被孤立考虑的细节就像字母表中的字母一样毫无意义。因此,民族志已不再是一张习俗的清单,它已经变成一门注重描写的艺术,就像小说大师们的作品那样,各种情节错综复杂地编织在一起。倘若我们认可这点,那么显然,人类学家从田野调查中所获得的细节就不会是枯燥无味的。细节就是精粹。”⑥ 这种细节可以看作遍布人类生活时空的传播行为,因为实际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总是相互交流着人为组合的象征表示形式,即交流语言,交流他们穿的衣服,吃的食物,站立的方式,房间中家具摆式等等。⑦
人类传播行为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利奇在书中列举了人类交流(传播)行为的几个方面:人类身体的自然生物行为——呼吸、心跳、新陈代谢过程及其他方面;用于改变外部世界的物质形态的技术行动——在地里挖洞、煮蛋等;以及评说现实世界,或意欲用抽象手段改变现实世界的表达行动。这种表达行为除了通常的口头表达以外,还包括姿势,如点头、拉长脸、挥手,还包括穿衣、站立讲台、带结婚戒指等。⑧ 用于交易的经济活动——“甚至在具有明显象征意义的交流形式中也是如此。比如,在基督教弥撒仪式中,教士给参加弥撒者面包和酒,并且声称他们是基督的肉和血,这种交流也存在经济交易。处于某种地位的某些人要买这些面包和酒。”⑨
很清楚,这种假设范围很广。利奇的基本观点是,人们通过五官从各方面接受的信息随时转换成其他形式,比如把书面文字变成为言语,把可见的乐谱转换成手臂、嘴和手指的动作,甚至在某些更深的抽象层次上人们所有形式的感知都通过某种交流的方式进行转换,包括把视觉信息转换为声音信息、触觉信息或嗅觉信息,反之亦然。
利奇考察了服装衣着在人类交流传播中的意义。他说:“衣着行为是为了传递意义复杂的信息,那么,服装就必须是高度标准化的和容易识别的。但是,一旦某种特定的服装最后习惯性地与某种特定仪式相联系或与某种和此类仪式相关的特定的社会职务相联系时,该服装的任何特征部分都可能成为这种仪式或职务的转喻代号。⑩ 因此,服装标明衣着者,不仅说明他是什么人,还表示他不是什么人:“王冠代表王位”,“主教冠代表主教”。(11) 衣着在表达结构系统中个体地位的同时还表达一种空间意义上的秩序。在英国社会的某些阶层中,用三种礼节规格的请柬来标识晚宴的性质:要求佩戴“白色领带”参加晚宴表示“非常正式”,“黑色领带”表示“半正式”,“非正式服装”则如其字面意思一样。
拉采尔说,“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是在空间中发生的,所以我们应该可以通过度量历史事件发生的空间范围来度量历史事件的时间流变,或者说可以用地球的钟来度量时间。”(12) 在某种意义上,人类传播行为的秩序是受时间与空间限制的事物能动的系列,其中每一传播行为都与人们生活时空尺度中的某一特殊点相联系:睡觉、走路、烹调、饮食、工作……不仅是可以预测的、次序发生在不同时间的、由社会决定的传播交流活动,也是发生在不同地点、在可预测的系统中相互联结的行为活动。甚至每一地点都有其由禁忌保护的特殊功用,比如在厨房里大便就如在浴室里煮食一样有亵渎之嫌。(13) 而且同一载体在不同时空中的意义又是可以转换的。“根据记载于佛教经典中的传说,僧侣的袈裟是黄色的(而不是红色或绿色)。它提醒穿着者,佛教引导其追随者追求一种完全清贫的生活,只穿从死者身上取来的破衣烂衫。在此,这种联系是‘黄色=死亡’”。“但是,在‘卡西纳’(Kathina)这样重要的周年典礼上,信徒们给僧侣赠送新袈裟,袈裟的黄色和成熟稻谷的黄色明显存在一种传统的联系。这种情况表达的是‘黄色=生命’”。(14)
人类的传播行为离不开特定的时空环境。利奇举例说,“如果你把非复述性的说话记录在磁带上,你将发现,录音重放时,你能立即理解的只是很少的部分。然而,在谈话现场,所有在场的人完全理解所说的那些话。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场合下,言语表达只是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在当时当地,谈话与其他事情的转喻相联系,并且这种非言语的‘其他事情’也是信息传递的一部分”。(15) 甚至,“当你不出声或不动嘴而用词思考时,你本人就切身感受到‘声音意象词汇’。就你的母语而言,每一词语(声音意象)都与内在的思维表现或概念紧密相连。”(16) 因为人类任何类型的行为都是一种潜在的信息,“真正重要的事物性必将沉默不语,而人们只能以闭口不谈的方式表达它们的重要性”。(17)
2.心灵符号中的人类传播
库利认为人类传播的意义是人的关系存在和发展的机制——包括全部的心灵符号,再加上在空间传递并在时间上保存这些符号的手段。(18) 利奇则认为,这种物质的符号表示的最重要的领域是在宗教仪式中。因为所有的抽象理论体系起初都是大脑中的原始概念,当人们推究用词语表现概念(如上帝、精神)时,就必须使它们具体化、形象化。人们往往从两方面着手(1)讲述故事(神话),故事中的抽象观念表现为神灵、超人和神化的动物的各种行为活动;(2)创造特殊的物体、建筑和空间,以表现抽象观念及其精神气氛。显然,这两点是互为依靠的,它们彼此相互隐喻。(19) 例如,“与上帝交流”这一极其困难的观念在基督教神话中表现为《新约全书》里的“最后的晚餐”。在每次举行任何形式的与上帝交流的仪式(弥撒)里,在教堂的祭坛围栏里特别设计的氛围中,这个简单的故事寄蕴着人类心灵的深刻和幽远。
但宗教仪式本身是能动的,它是引发世界(抽象)形态变化的信号。当某个听众听一个神话故事或听一支乐曲时,他所理解的东西,在许多情况下是他个人心灵深处的,人脑的无意识(自然的)部分被那些特定的文化(非自然的)方式激起的反应:“因此,在神话和音乐中,听众表现为管弦乐队指挥的沉默扮演者”。
在合适的环境中,人们的交流行为几乎都可能用于传导得到文化承认的信息。例如:在英国的习俗中,哭“表示”悲伤,笑“表示”高兴,亲吻“表示”爱,这些意识联系并不是人类普遍的文化特征,有时候,某一行为的传播学意义和与之呼应的行为反应完全两样。例如,参加葬礼的人一般要哭泣,在形式上这是恰当的行为,但官方派来的哀悼者就不一定要哭。(20) 在这种仪式中,参与者的身体动作以及动作的次序连贯本身都是信息的组成部分,是把自身呈现为一种内在认知表现的心灵行为,是“抽象形态变化”的直接表现。
而且,人们的许多概念既是对外界客体与事件的反应,又是感觉意象的精神体现,所以甚至“运用感觉意象我们就可以在想象中做游戏”,“我们也可以不亲眼看或亲手摸而用可见与可触的意象思考。”(21)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在头脑中产生抽象观念,然后通过某种方式把这种抽象观念表现为外界事物。(22) 如钢琴家把乐谱信息转换成琴键上的手指动作,由此产生音乐。音乐不是单纯的信息引发反应的结果。音乐中包含引发反应,但这种反应由音乐思维和演奏者的能力加以调节。这一情况同样适用于包括言语和非言语的整个人类的交流领域。无论何时我们讨论传播行为的“意义”,都涉及外部世界可观察的模式与“大脑中”不可观察的模式之间的关系。这里我们又回到人们心灵深处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对立方面来了。(23) 所以,文化人类学家的工作作为一种解释的工作,是基于文化的可翻译性前提之下的。利奇曾经作过这样一种对人的心灵的普遍性的预设:所有人类的行为,不管他们的文化也不管他们心理的成熟程度,在某种更深的抽象层次上,人们形式的感知都以同样的方式转换,即倾向于建构象征并以同样的一般方式来做心灵的联想。
3.社会规范中的人类传播
默顿认为交流是国家共同体建设的工具。阿伦特说交流是发现真理的手段,后来又认为它是产生新的政治秩序的手段(24)。这些观点基于这样的理论前提:人的传播行为是社会结构和认识—象征体系与个人之间的中介,通过不断地对自然适应和认识的实践,人形成一系列对他们的生活有益的“惯习”,久而久之这些惯习导致制度的起源,变成一个传统或象征体系,并反过来在社会生活中被积累和利用。(25)
个人的传播行为要受文化习俗的制约,因为每一种文化模式都有其自身“最喜爱的”或“最珍视宝贵的”习俗。“日神型”、“酒神型”和“妄想狂型”文化的喜好各不相同。只要个人在这些各不相同的文化背景中将其注意力附丽其上,这些颇具差异的文化就会发展出各自的轮廓形貌。但在个人与文化之间的这种互动中,有些个人在气质上比其他的社会成员更能与文化自身的流向意气相投,更能刻意地去发展文化本身的那种特质,也更能推动在这种文化模式下的传播行为的极端整合。正是这些个体的传播行为,影响和带动着其他社会成员的传播方式,使整个社会舍弃别的毫无特色的模式,逐步采用和模仿他们的传播行为,遂成为一种颇具感召意义的个体规范和整合的力量。所以,文化人类学的许多研究成果揭示了人类交流和传播行为表面下所潜在的“无意识模式”,因为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都深藏一种内在的、支配着表面现象的结构,研究者的任务就在于寻找这种内在的结构。(26)
《文化与交流》一书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探讨。利奇说:“人们建造房屋,选择居住点是按照几何图形来安排的。就像人的语言能力一样,这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我们需要井然有序的环境。这种人类文化与自然的对照是惊人的。可见的、原始的自然界的一堆杂乱的、随意的曲线,它不具直线,很少有正规的几何图形;但是让人驯服了的、经人改造的文化世界却处处是直线、四方形、三角形、圆形等等。”(27) 因而人们的感情表露也不可能是随意的,必须受最严格的禁忌规范,人们在某一场合所做的可能与所感觉的完全不同,尽管也不排除这样的感觉本身就可能模糊不清。
虽然人类通过传播行为创造了社会规范,同时人类又受到他们所创造的规范的制约,但利奇认为理想模式与现实模式之间也还是存在差别的,人们的传播行为有其现实利益的考虑,而且社会内部往往存在不同的政治模式之间的转换和摇摆,变迁是由特定文化制约下的政治模式的不定性引起的。(28) 因为任何根据划分类别的分类都暗示可能的等级概念。每一个人所具有的等级、地位和性别都根据文化习俗这一严格的形式决定他或她所能利用的空间。如果我们问:为什么人竟会这样做呢?答案可能是:一切人都有这样一种深藏的心理需求,则“认知自身位置”是一种确认社会和地理位置的问题。
二、文化:理解人类传播行为的终极视界
利奇说过:“人们通过感觉器官接受信息的结构而来——通过耳朵听到了模型化的声音,通过眼睛看到了模型化的光线,通过鼻子嗅到模型化的气味等等。但是,由于我们认识的是一个完整的经验——而不是我们感觉破译的信号系统,即机械地声音世界加光线世界——因此,这就使我们的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似乎在同时发出一种信息。于是,问题就在于设计一种破译代码的手段。”(29) 基于这样的理念,文化人类学认为人类丰富的社会—文化现象,人类的所有行为,都可以从隐藏在行为背后的层次去寻找根源。换言之,人类行为由文化的深层结构所决定。
人是文化的产物,瑞士生物学家A·波尔特曼说:“人的遗传所特有的方式不是生物的,而是社会的。”(30) 因此,从个人的角度说,一个人的成年人格的形成,深受其所处的文化的影响,尤其是不同文化或社会的儿童养育方式,对人的个性形成有着关键性的影响。从族群或民族角度来说,文化因素就像一套供人选择的项目,有些民族选择了这些因素,并形成自己的形貌,另一些选择了其他因素,并形成别的形貌。不同的文化形貌决定了民族个性的形成。(31) 从社会角度则印证了帕森斯的说法,文化价值“对于维持社会系统的稳定和持续动作,发生决定性的影响。”(32)
虽然人是一种编织文化意义的网而又囿限于其中的动物,而文化的内涵,于国学源自《易传》“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语,乃为“人文化成”之意。西学在英法文中均为culture,原从拉丁文cultura而来,意指人对自然界有目的的影响。克里福德·格尔兹则定义为“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中。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绵延传续,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及对生命的态度。(33) 上述定义揭示了文化的本质即人类的本体论。而文化既做为文化人类学研究核心的终极关怀,也是我们传播学的伊甸园之梦——寻找人类传播行为的根本密码。因为,无论从什么意义上看,文化总是和传播密不可分,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当它作为开启人类传播行为奥秘的密码时,总是体现为各种各样的符号,举凡人类的器具用品、行为方式,甚至思想观念。文化的创造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符号的创造,而符号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向人们传达某种意义。
文化以其多种形式预定了我们要关注什么和忽略什么,从而在人与外部世界之间树起一面选择性很强的网筛。它作为一个群体的风俗、传统、价值观念和制度化的原则抽象地存在,通过集体意识、下意识、记忆和社会实践来回流动。但它也成型于这些抽象的怎样在社会互动中现实化的过程。总之,文化的意义精确地出现于抽象理念与现实实践的动态联系中,存在于深层文化的浸润及永久的心理结构和日常生活不甚稳固的表面之间的联系中。因此,从根本上说,文化一方面涉及到符号自身与意图和被表征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又和特定语境中的交流、理解和解释密切相关。这么来看,所谓文化,究其本质乃是借助符号来传达意义的人类行为,文化的核心就是意义的创造、交往、理解和解释。利奇认为“甚至呼吸也是‘表达’——‘表示’我还活着。甚至最简单的行动也包含着生物学和表达学两方面的含义。我为自己冲一杯咖啡,不仅改变了外部世界的形态,而且增进了我身体内部的新陈代谢过程。它还‘说明’了某些事情:我在煮咖啡的过程中,准备咖啡及器具的方式表明了我的文化背景。”(34)
在利奇看来,文化不应当被看做是特殊存在的社会事实的集合物,而应当被看做是人类交往(传播)的系统。文化能够比较,正如语言能够比较一样。文化的相似性是一切人脑都以同样方式活动这一事实造成的。我们所发现的并不是不依赖人类活动的自然真理,而是人类活动这种可能性。利奇的论点的核心是:“非言语表达的交流一般是以乐队指挥把音乐信息传达给听众的方式进行,而不是以书的作者把非言语信息传达给读者的方式进行的。由此,在我们开始破译信息之前,我们必须懂得许多有关的文化场合和背景知识。”(35)
三、文化人类学方法的传播研究视点
自从文化人类学创建以来,它就肩负着对人类文化的各种形态进行比较研究的历史使命。文化人类学家大都是文化旅行家和交际家,他们在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穿梭往返、摸爬滚打,他们往往直接生活到一个群体的成员中并与之“打成一片”,持续观察那里人们的日常生活及相互影响,努力去理解他们习惯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从而获得将一种文化同另一种文化比较和参照的材料与资格。
利奇先后在我国台湾(1937年)、伊朗库尔德斯坦(1938年)、缅甸(1939—1945年)、加里曼丹(1947年)和斯里兰卡(1954—1956年)等地从事人类学研究工作。长期的田野考察造就了利奇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有关统计资料表明,利奇的著作被引用次数之多,在战后的主要人类学家中是首屈一指的,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思想学说影响的广泛。在他的晚年代表作《社会人类学》中,他认为人类学是“一门微观社会学”,它通过参与观察,细致地研究与自身社会不同的小型社会。尽管其研究重点在人类活动的细节方面,但比之长篇大论的概括性教科书,它所告诉我们的有关人类的普遍社会行为要多得多。(36)
利奇在阐释他的研究方法时说,研究与人类学者本身没有距离的本土文化,容易导致人类学描述的不真实性,因为研究者必然是带着一定的价值观去谈论其所熟习的文化,而且对自己的文化司空见惯而无法进行客观分析。这个看法不是利奇的独特创造,而是一个世纪以来人类学界长期存在的理想。人类学即在这样的历程中努力寻求自身的价值体现和学科定位,并以其独特的理论方法和多维的文化视野为人类提供了诸多关于人类行为与思想的认识。无论是曾作为“活社会考古,翻掘现代化表土中原始存在”的民族志,还是强调“人观、情节、风格与心理互动”的后现代艺术文本,以及人类学历史中因人类思维发展和学科互动而上演的种种理论学派之争,无不体现出人类学在理性思维光辉照耀之下对于人类认知体系的建构与人类存在本质的关怀,同时表明人类作为生物及文化意义上的“类”在宇宙中的存在价值。因此,20世纪初人类学大师克罗伯声称:我们已进入人类学的时代。这话显得有些自负。但从整个西方人类学科体系的建构上看,它确实已走上全面的操作阶段。(37)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罗杰·基辛说:“文化人类学是把不同的生活方式当作一面镜子来研究我们自己本身的科学。”(38) 也就是说,在学科内涵中,渗透着人类深刻的自我反思精神,这种“批判与自省”的方式,其深层意义即是哲学对于人类存在与境遇的关怀,基于这样一种情结,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便与哲学思维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闪烁出理性的光辉。
利奇借用维特根斯坦关于美学与伦理是同一的,如果要理解一个社会的伦理法则,我们便必须要研究美学的观点,认为习俗也许是出于历史的偶然,但对于生活在这一习俗当中的个人来说,这些习俗实际上成为他在这个社会中的人际交往的整体体系的一部分,成为一种象征性活动,一种表征。而文化人类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出所象征的和所表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把它们转译成他自己的学术性的术语。从这个意义类推,人类的交流行为与传播行为也是同一的,正如文化习俗是人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际传播交往整体体系的一部分一样,都是传播学意义上的象征性活动。虽然“文化”在文化人类学者眼中指的是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观念形态,而在传播学者眼中则是有意识地建构的符号体系。但是两种文化观之间确实存在着契合点,因为两个学科的表述都具有文化建构的主观性色彩。
施拉姆说:“研究传播行为就像研究大海一样,研究工作可以在任何水平上进行。但超过一定深度之后,研究就只能在黑暗中进行了”。(39) 传播的含义在于对话、并存和记忆,这对于不同的文化来说如此,对于文化研究的不同学术传统来说也是如此。传播学与文化人类学虽然是两个性质完全独立的学科,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一个研究人的传播行为规律,一个研究人的文化现象,而人的传播行为与文化现象又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所以,传播学从诞生之日起就谋求与文化人类学的结合,而文化人类学在发展过程中则不断地从传播学中寻求帮助。传播学与文化人类学之间的互动使两个学科都得到长足的进步。
传播学的历史不长,它从历史较长的学科研究中得到了重要的启迪。而且人们希望,跨学科的理论交流将促使传播学渐渐成为研究人类传播行为的一种更为全面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以传播学的视角来解读《文化与交流》,重新认识该书丰富的理论内涵及传播学价值,借鉴文化人类学家充满理性和哲思的探索,了解该学科于风云变幻的文化历史中得以进步发展之缘由所在,从而使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发展有理由寄希望于未来。
注释:
① 许正林:《欧洲传播思想史》,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第184—185页。
② 埃德蒙·利奇:《文化与交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页。
③ 王铭铭:《西方人类学十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8页。
④⑤⑥⑦⑧⑨⑩(11) 埃德蒙·利奇:《文化与交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6、14、导言、50、导言、5、54、55页。
(12) 王铭铭:《西方人类学十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页。
(13)(14)(15)(16)(19)(20)(21)(22)(23) 埃德蒙·利奇:《文化与交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0、59、71、17、37、46、17、37、16页。
(17) 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18) 彼德斯:《交流的无奈》,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24) 彼德斯:《交流的无奈》,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25)(26)(28) 王铭铭:《西方人类学十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0、31、25页。
(27) 埃德蒙·利奇:《文化与交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0页。
(29) 埃德蒙·利奇:《列维·斯特劳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111页。
(30)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第389页。
(31) 王铭铭:《西方人类学十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32) 高宣扬:《鲁曼社会系统理论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4页。
(33) 王铭铭:《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上海。
(34)(35) 埃德蒙·利奇:《文化与交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导言、第98页。
(36) 埃德蒙·利奇:《文化与交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序。
(37) 田青:《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人类学的相遇》,《呼伦贝尔学院学报》,1999年,第3页。
(38) 陈山:《痛苦的智慧——文化学说发展的轨迹》,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71页。
(39) 许正林:《欧洲传播思想史》,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第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