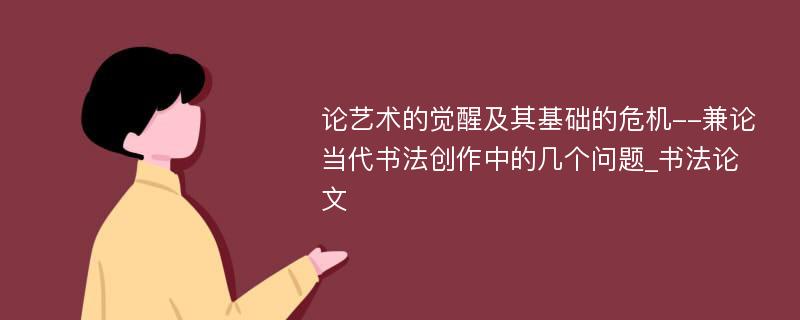
再论艺术的觉醒和基础的危机——关于当前书法创作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问题论文,书法论文,危机论文,基础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八十年代初突然兴起并迅速席卷全国的“书法热”,产生了一项具有历史性价值的重要成果,即书法创作观念的形成。但是,“书法热”掀起和书法创作观念的提出,是在我们刚刚告别那个长达十年之久的动乱年代,刚刚实行改革开放的时期,一方面人们经历了长期的文化饥渴以后,对知识的渴求达到了几乎狂热的程度,另一方面人们经历了与民族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长期隔绝以后,又相当缺乏分辨和认定的能力,年轻的当代知识界处在饥不择食的亢奋之中。在这样的思想状态下,不少人把唯物辩证法这个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原理搁置一边,热衷于理论上的各执一词和实践上的各行其是,使当代书法创作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自由化色彩,引起诸多创作思想上的混乱,妨碍着书法创作的健康发展和成熟进程。
一 对书法和书法创作的基本认识
本世纪八十年代展开的“书法是一门什么艺术”的讨论中,人们往往是拿了“抽象”、“具象”、“意象”这一顶顶帽子硬往书法的头上扣,扣上去看看仍然似是而非,都不怎么合适,于是不了了之,成了悬案,结果使得原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反而成了问题,本来明确的概念反而变得模糊起来。这是因为某些学者从唯心论的立场出发,不是以书法的客观存在为依据,而是以概念、甚至更多地采用西方艺术的概念来强行解剖这门中国独有的书法艺术,就难免要犯这个基本的认识论方面的错误。
这个错误犯得不小。由于对书法概念上的界定不清,直接导致了当代书坛普遍性地对书法的认识混乱:一方面,书法界一致承认书法不等于一般的书写文字,另一方面却又几乎同样一致地把对书法艺术的追索和认定,不仅扩大到历代一切书写文字,而且囊括了所有的铭刻文字。诸如非书法时代的金甲文字,大量主要产生于民间的非书法性质的权量、诏版、砖瓦、简牍、残纸字迹和失去书法特征的碑刻墓志等等,大张旗鼓地打进了书法圈,非书法造了书法的反。于是书法界秩序大乱,“假作真时真亦假”,王羲之不再被重视,端严的唐楷遭人嘲弄,六朝碑志上的错误字成了时鲜货,古代书法史上被淘汰的那一部分粗劣和残缺不堪的文字遗迹被视若稀珍,有的甚至与王羲之、颜真卿的代表作一起被奉为经典,被临摹、被效仿,形成了一起起“现象”,掀起一阵阵“时风”,导致了当代书坛非书法现象的孳生和长时期的广泛蔓延。
书法创作是一个新概念,它是由“书法”和“创作”这两个分概念构成的,对这两个分概念的任何一个认识不清,都不可能求得对书法创作的正确认识。
中国古代书法家理想中的书法作品,主要侧重在技法精熟基础上的自然形成,在古代中国,一般民间百姓和小知识分子们就算有点文化,能拿起笔来写几个字,但迫于生计,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闲兴雅致去“详究点画”的。因此,书法历来只是相当阶层上文人们的专利,而文人们又只当书法为一种业余的文化修养,并不习惯(事实上也不可能)把它作为终生第一位的事业,甚至当代书坛最有权威性的几位老书法家,也绝不仅以书法家的地位引为光荣。书法在书法家自己心目中的地位,决定了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进入到艺术创作阶段,就像文人画只能作为墨戏而不能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绘画创作一样。这就难怪一部分以传统的书写形式为座标的实力派书家,至今仍对书法创作这一课题持保留态度。
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书法创作这一新概念的出现,是有其现实基础的,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凭空臆造。对日趋专业化乃至职业化的当代中青年书家来说,创作已是一个义不容辞的历史课题。历代书法大师们首先以文人的身份为书法艺术设定了一个几乎令后人无法到达的文化积淀的高度,如果我们同样寄望于技法基础上的自然形成,不但无法回避地决定了当代书家面对历史而自惭形秽的劣势地位,而且会使一个矢志以书法艺术为终生事业的职业书家最终失去追求的目标和乐趣。因此,当代书坛创作的概念形成和创作的行为实践,尽管还处在幼稚时期,尽管还存在许多的流弊,甚至常常被导入一个个误区,但它做为中国书法史上一个新的发展起点的标志,无疑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大意义。
要说服“书法无创作论”者接受书法创作这个新概念,并不会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而且也并非特别重要,重要的倒是书法创作本身是否具有说服力,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更注重事实存在,而不愿信奉概念。
当前书法创作的实际状况是不足以让人乐观的。在书法和非书法相混淆,书法本身概念不清的状态下,很难保证创作手段的实现是书法的而不是非书法的;倘使以非书法为前提而进行的创作实践,就不可能是书法创作,而只能是非书法创作。因此,我们在提出书法创作的新任务时,首先应该明确指出:“书法”是前提,“创作”则是依照这一前提而采取的手段。“书法”作为前提,带有专指性和规定性;“创作”作为手段,就不应该有太多的规定性,特别是对书法家个体而言,创作只是作者在特定环境下运用特定的艺术语言实践其对某种情绪、感受和审美理想的追求,在这种追求中,作者应享有手段选择和运用的充分自由,不应有什么思维上或行为上的规定。否则,无论作品被要求具备多么独一无二人的惊人特征,也仍然是缺乏生命力和感染力的,因为在对思维的行为的规定中,运用手段的作者被安排在被动的地位,他的主动权,他的个性、情感、审美理想和创作精神,从根本上被某种原则要求下委曲求全地彻底剥夺了。
一方面向书法勒索自由,另一方面又给创作手段横加桎梏,这种头足倒置的书法创作主张之能够产生并为相当一部分人所接受,说明了我们不但对书法创作这个新概念,而且对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书法本体概念的认识,还存在多么大的距离。而这种距离的存在,正是造成当前书法创作思想上种种模糊观念的总根源。
二 书法创作的实践和理论
书法艺术是在对汉文字的书写实践中产生的,但汉文字的书写实践首先产生的并不是书法艺术,而是文字学的理论。这些理论由于涉及到文字的书写和契刻,常常被后世附会为书法理论,给人造成书法理论先于书法实践的错觉。又由于历代书法作者和论者的非专业性,又把不少非书法的学术理论掺杂进来(最明显的如清代的“碑学”、“帖字”),既不是书法实践的产物,却给书法实践造成许多负面影响。认真鉴别和清理古代书法理论中那些非书法的成分,将有助于我们对书法本体和书法实践的正确认识。只要把那些理论放在历代优秀的书法实践成果面前加以检验,其中的非书法本质是容易辨别清楚的。
当然,理论并不是对实践作直录式的叙述,不是重复实践过程的每个细节,而是对实践经验的概括总结,是通过对实践过程中诸多现象的审慎分析,揭示出其中最本质、最具规律性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谈得上真正的理论。因此,理论并不是以一种被动的姿态面对实践的,而是以哲学的、历史学的和社会学的尺度主动负责地评判着实践成果,它既不能超然于实践之外,又必须保持在实践面前的独立品格和主动精神。对历史的、某一群体的或个人的实践成果作无原则的不负责任的肯定或否定,是理论的堕落,因为当理论处于某种形式的缺乏思想的附庸地位时,势必失却其应具的探求真理的品质和勇气。
书法创作作为书法艺术实践的新课题,确是在近二十年间出现的,但是,如果我们认真检索一下古代书法实践中那一部分最出色的成果,例如王羲之的《兰亭序》和颜真卿的《祭侄稿》,其技法驾权的精熟、文字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协调和谐、点画之间所透露的作者思想情绪的轨迹,虽然当时作者是无意出之,不能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书法创作,但客观上已经达到了我们今天所谓的书法创作所要求达到的标准,给我们今天从事书法创作的探索实践,提供了某种成功的范例。
可惜的是当代书法创作的实践者们并没有对这些似乎耳熟能详的古典名迹以足够的关注。人们开始并不以为“创作”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好像仅仅是为了求得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同等地位而随意地添加在“书法”后边的新名词,因此在实践上还是与以往一样地训练点画、临习碑帖、书写卷轴。一个新的概念而没有新的内容,首先使一部分思想敏捷的青年人感到不能满足,于是出现了一系列以“打破传统格局”为目标的种种创作探索,十多年间彼伏此起,从未间歇。这种殉道式的勇气,是可歌可泣的。但对于书法艺术的新的追求,光靠勇气是不够的,盲目的、缺乏书法艺术客观规律支持的创作探险,可能会使当代书坛损失相当一部分才华横溢而且具有献身精神的优秀青年。
这一时期的书法创作理论,并没有(或者说绝少有)认真去总结分析创作实践中的种种失误,从历史的和现实的角度指出创作实践的前进方向,反而一个劲地鼓动人们向后转,对巨大的历史传统发起一次次冲锋。人们对当代书坛的形成过程和内部结构缺乏符合实际的分析,对其薄弱的基础认识不足,对书法历史传统深厚的积淀又缺乏足够的估价和掂量;不承认中国书法史的客观规律,不承认历代书法家的实践成果和实践经验,不承认我们自身的营养不良和实力不足;过多地注重创作的形式构架而摒弃了书法的本质语言,提出过激的口号、过高的目标。在这种浮躁情绪支配下的书法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不能不犯盲动主义的错误。如果说艺术的创作实践可以甚至应该要求艺术家有更多的感情冲动,允许艺术家在审美取向上有较大的偏激的话,那末对于理论,则要求理智、冷静和公允。一味追求新鲜时髦的轰动效应,给盲目过激的创作冲动火上添油,是有辱理论工作的历史使命的。
当代书法理论界某些宣扬先知先觉的所谓“理论先行”的主张,是完全没有历史根据的,他们受了西方某些唯心主义艺术理论的深刻影响,竭力离间现代书法创作与古典书法传统的关系,把现代书法的特殊性(个性)要求夸大到脱离中国书法共通性的不恰当程度;他们从刚进口的西方艺术理论中寻章摘句,制造出一些完全脱离中国书法实践基础的理论口号,以迎合人们标新立异的创作动向和“与国际接轨”的心理需求;他们效仿西方流行艺术,设计出一套套既省力又见效的书法创作模式,以迎合一部分年轻人急切的成就欲;他们把严肃的学术理论转化为自我宣传的舆论工具,在一个口号刚刚提出,认真的创作实践还没有开始进行时,就已经通过了多方面“比较”,肯定了自己理论的正确和实践的成就,匆忙在四周筑起一道似乎坚不可摧的高墙。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理论家并不考虑对历史负责,也不考虑对现实的和未来的实践活动负责,而只对自己的“理论”感兴趣。他们把自己圈定范围内人们的书法创作实践,当作自己“理论”的试验场,完全违背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当代书坛这种“占地为王”现象的存在,说明了目前书法创作的实践和理论正在陷入一个严重的误区。
三 历史意识与现代意识
当代书坛存在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历史隔阂。因为它的形成,更多的不是由于中国书法史发展的客观需要,而是当代文化艺术事业的现实需要,所以当它开始面对尘封已久的中国书法传统时,便有一种“相见不相识”的感觉,很难达到感情上的沟通,就像要对一位刚从隔离室出来而且架子硕大的陌生人叫一声“爹”,许多人都不大情愿,心理压力颇大。“距离产生美”并不算一个普遍性的法则,因为距离也常常产生误解,从当代书坛一部分激进的人们讥评书法史上那些杰出人物和杰出作品时所采取的那种轻松潇洒的姿态里,我们可以测量出这种误解的深刻。由隔阂而造成的距离和误解,决定了现代书法在总趋向上与中国书法的历史传统相对抗的立场。于是有人提出要与传统“彻底决裂”,要甩掉传统这个“沉重的包袱”,要倡兴“现代意识”等等,这些缺乏历史意识的“现代意识”,因为建立在对传统并不理解的基础上,所以不能不时时显露出它的浅薄和轻率。
在书法的历史与现代之间,确实横亘着一片空旷的荒漠,这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客观事实,是不应该存在又确然存在着的。如果我们今天所谓的“现代意识”真正是属于书法的,那就特别要求我们首先必须具备强烈的历史意识,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去穿越这片荒漠,取得与已往历史的衔接,因为在历史与现代之间是不允许造成隔裂的,任何真正有价值的现代意识终将被融入历史意识之中,成为延绵不绝的历史长河中一簇簇灿烂的浪花。
承认历史的客观存在,承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不可违背和历史发展进程中某些阶段的不可超越,承认经过历史检验的优秀文化艺术遗产不仅对于历史而且对于现实和未来的价值,这就是历史意识。历史意识对现代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指导性和支配力。
当代书坛相当一部分宣扬“现代意识”的人们,其实并不具备真正的现代意识,因为他们总是千方百计把自己不仅从历史的而且从现实的环境中孤立起来,就像阳光下一小泓来无源去无流的死水,一方面闪烁着快活的浮光,一方面却在不知不觉中趋向枯竭。
也只有当有限的分水挥发殆尽的时候,人们才不约而同地开始寻根探源,于是“与传统决裂”的呐喊偃息下去,代之而起的是“回归传统”的呼号。在这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折中,“现代意识”们同样犯了非历史意识的错误,他们一听到“回归”的信号,刚跑就冲出了书法史划定的跑道,跌进了非书法“传统”的怀抱。
传统究竟是什么?传统不等于王羲之,不等于《兰亭序》,也不等于颜、柳、欧、赵,更不等于楼兰残纸和汉魏断简。传统不是一种凝固的形式存在。传统首先是一种长存常新的文化精神,是普遍存在于历代优秀书家和优秀书法作品中的共通的思想和行为准则。而对某一具体书家和具体作品来说,传统不是在“知其然”,而是在“知其所以然”的过程中得到体现的。
无论对于书法的古典传统还是新的创造,要正确认定其在现实和未来环境中的价值,首先需要的不是现代意识而是历史意识,即不仅要习惯于把它放在当时当地的具体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更重要的是必须把它放在整个书法史的发展规律中加以考察。
四 个性、风格与流派
目前书法界对于书法作品的个性问题,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见解:一种认为当代书法作品(特别是那些古典传统基础较深的书家作品)几乎都是千人一面,缺乏个性;另一种认为书法作品的个性是客观存在的,即使同一个人临摹同一件作品,也不可能完全相同,有不同就是有个性。每一幅个别性的作品必然具有个别性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凡作品皆有个性的见解是可以成立的,但我们对一件艺术作品特别是创作作品的要求,显然不能以其自然状态的个性特征为满足,而且某些自然状态的个性特征(例如粗俗、残破等等),并不是创造艺术美的个性所需要的。因此,提高并强化作品的个性,是提高当代书法创作水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个性是对共性而言的,没有个性就不可能组成共性,离开共性,个性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所以我们常说: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如果片面地强调共性,会把书法创作引向概念化;而片面强调个性,又容易使书法创作误入非书法的歧途。所以个性的发挥和强化,并不是无限制的,而是必须接受其所属事物共性的制约,在该事物的共性范围内进行。譬如我们把某些人称为魔鬼、妖精、禽兽等等,是因为他们某些方面的个性表现超出了人的共性范围;书法创作中的个性表现,应该而且必须符合书法的共性要求,否则就不叫书法的个性,而可能是绘画的、一般写字的或者什么其他门类的个性了,于是这个作品便没有理由称为书法作品。
以个性即个别性而论,书法创作中的个性表现,可以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作者素质方面的个性。这是最基本的个性,包括作者的性格、修养、气质和审美取向等等。这些客观存在的个性,当然是真实的,但却不一定是善和美的,或者说不全是善和美的,而作者在书法创作过程中,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自身个性的影响,并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中。
二是技法选择方面的个性。中国书法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异常丰富的技法内容,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选择机会。书法创作中对技法运用的选择,与作者的素质、作品所反映的思想内容和所产生的环境、创作材料的使用等,都有直接关系,因此也就具备明显的个性化倾向。对技法的选择包括了对现有技法的借鉴和对现有技法的充实突破这样两个方面,前者因与作者个性的契合而表现为相对稳定的选择,后者因受作者情绪的驱动或作品构成的需要而表现为非稳定的选择。但稳定的选择只能传达作者的个性,很难体现技法的个性;非稳定的选择则是一种带创造性的选择,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作者的技法个性。根据质量互变定律,量变(渐变)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质变(突变),因此对现有技法充实突破的非稳定选择是有限量的,是现有技法的某些方面确实不足以表达作者此时此地特殊感受的情况下采取的不得已的选择,而不是矜才使气地故弄新奇。如果现有技法被全面突破,如果人人都“创造”一套与众不同的技法,必将导致书法的解体乃至消亡。在中国书法史上,每当技法选择的个性化突破达到一定限度时,往往会有一部分有识之士站出来,恢复技法基础,推动书法中兴,来一个否定之否定。对正在提倡书法创作的当代书坛来说,认真总结这一历史经验,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三是艺术风格方面的个性。这是由某一书家作品的总体特征而显示出来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个人风格,是书法家根据自己的个性或擅长采用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的形式体现,它可以是作者在长期艺术实践中素质积累的自然定位,也可以是作者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对形式语言定向选择的结果。艺术风格方面的个性,只是一个书法家区别于其他书法家的特征,而在其自身的作品中却不可避免地带有规范化或程式化性格,而且这种个性愈突出,其作品的规范化或程式化性格也愈明显。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个性化艺术风格在其作品中的不断重复,不但是允许的,而且是艺术家的艺术实践活动进入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书法创作的风格多样化要求,是对当代书坛的整体要求:而作为书法家个体,个性风格的多样化追求,反而会使自己的创作成果丧失独立的形象和独立的存在价值。
四是创作作品方面的个性。这是中国书法进入创作时代以后所出现的一个新的课题。书法创作是书法家运用自己所擅长的那一部分书法艺术语言,选择尽可能准确的文字内容,表达特定环境条件下的特殊感受。无论创作是发生在即兴的抑或非即兴的状态,它都是书法家有意识的艺术创造活动,既不是兴之所至的日用性文字书写,也不是失去控制的艺术冲动。因此,无论作品中使用的语言形态多么抽象,无论作品在读者眼里引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种种歧解,但在作者的创作行为中,每一种作品都具有一个专指的具体感受。由于每一具体感受的特殊性,我们当然有理由要求作为创作结果的书法作品具备各各不同的个性。但是,在日常书法艺术实践中,不可能经常遇到适合书法创作的特定环境条件下的特殊感受,即使遇到,也不一定适应书法家不同的风格特征和技法范畴,所以,书法家们一生的创作作品总是少量的,大量的还是一般书法作品,一般书法作品因为同样能体现作者个性化的艺术风格,尤其是那些作者无意间有感而发而达到心手双畅的一般书法作品(如古典作品中的《兰亭序》和《祭侄稿》),也同样具有不可复得的高度艺术成就,其价值并不一定亚于创作作品。
风格是书法艺术实践中各种个性特征最集中、最鲜明的体现,也是书法艺术本身能够独立存在并在国内外多种文化艺术的交相冲击下延续数千年终不至于被异化和衰亡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坚定的个性特征。
中国书法的艺术风格是代表中华民族风格的民族文化精神在书法形式上的体现。它与我们民族的哲学、文学、历史学、艺术学等等有着根深蒂固的内在联系。我们伟大民族那种虽经历艰苦磨难而从不放弃追求美好理想的不屈不挠的精神,那种简朴而又端庄的气质,那种刚强而又平和的仪态,那种热情奔放而又谦恭温良的风度,那种不屑于故作姿态的堂堂正正的气派,都反映到中国书法的艺术风格之中。只有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艺术,才可能具备如此博大而崇高的风格内涵。在书法创作中忽视甚至脱离中国书法这个总的相对稳定的艺术风格,就完全可能在个性化风格的求索中迷失方向,丧失自己的民族立场,以至堕落为外民族艺术风格规范下的忠实奴仆。对外民族艺术(即使同属书写艺术)的引进,必须根据需要、根据自身此一时期的消化吸收能力有选择地进行,因此这种引进只能是局部的,而绝对不应该(实在也不可能)是全面的。
中国书法艺术显著的民族风格特征,并不妨碍时代风格、地域风格、群体风格和个人风格的发展。相反时代的、地域的群体的、个人的多样化艺术风格并存和交相辉映的局面,从来就是中国书法史上繁荣时代的标志。一方面要求无限制地拓展书法作品各自独立的个性,一方面又倡言书法风格的融合认同和“国际化”,好像也是当代书坛“现代意识”的话题之一。这自相矛盾的书法创作主张之核心内容,是从两个极端削弱中国书法最本质的风格特征。现代信息和交通的发达,确实为书法的地域性、群体性和书法家个体间的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现代书法的展览、评选和宣传体制,也确实为“时风”的形成和蔓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好像为“融合论”提供了依据。可是“融合论”者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代信息”:那些鼓吹“创作”、标榜“个性”的人们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正是以抄袭和模仿历代那些名不见经传的非书法作品为能事,从而发迹于当代书坛,从而传抄成习以形成“时风”于大江南北。从这整个过程和全部作品中,根本就不存在“创作”,不存在“个性”,也不存在书法艺术所要求的风格,以此作为论定信息时代艺术风格融合的“依据”,显然是非常缺乏说服力的。
群体风格其实也不妨称之为流派风格,但由于中国书法史上并未有过明确的流派划分,姑妄称之为“群体”。
流派的形成应该是书法创作趋向成熟的标志,一般是对创作主张比较一致、个人风格比较接近、基本上生活在同一历史时期的某一个作者群的综称。除此之外,流派至少还应具备这样两个条件:一是有明确的历史渊源,因为有源才能成流,才能有形成的基础,其创作主张才有确立的依据;二是其艺术风格必须在相当范围内造成影响,并在流行中达到稳定。
当代书坛曾经发生过好几起“流行书风”,但都只“流行”了一阵子,慢慢就沉匿下去,其实还是流而不行,当然也无缘形成流派。目前有一些书法群体倒确实是用“流派”的名义在书坛登台亮相的,但当我们深入考察一下他们的背景和结构时,便可以发觉并不真正具备流派的特征。他们的形成往往与他们的作品一样,带有强烈的制作色彩,而且运用的是一整套策划手段:先提出一个口号,再规定一种格式、组织一批成员、制作一些作品、筹措一笔资金、举办几次展览,然后通过报刊、电视、电台等多种新闻舆论媒介造成声势,推向社会。这种状态,十分符合一般书法社团的组织程序,而并不类似书法创作艺术流派的形成过程。而且非常奇怪的是,他们往往宁可与国外的艺术“接轨”攀亲,不愿与中国书法建立传承关系,以自身的“来历不明”而引为骄傲。
五 技法在他作中的地位
神韵、意境、风格、情趣等等,是对一切艺术作品的共同要求,也就是艺术的共性;某一艺术门类区别于其他艺术门类的个性、特殊性、独立性,则主要是以其独有的、高度成熟的、稳定的艺术表现手段——技法为特征的。没有独特的技法,就不可能形成一门独立的艺术;技法的稳定,说明这门艺术的不成熟或独立地位的不稳固。只有真正掌握了某一种特定的艺术技法,才能称得上这一艺术门类的专门家,你所掌握的技法越全面、越纯熟,你在艺术实践中的表现力和自由度也越大。
书法艺术对技法的依赖表现得尤为突出,技法的规范性要求也尤为严格和强烈,因为除了技法的特殊,书法艺术几乎无法与一般的文字书写形态拉开距离。正是由于这种具有生命意味的特有技法的确立、运用、充实、成熟,才使书法终于从一般化文字书写中得到升华,成为一门有生命力的独立艺术,又经过历代的传承,到达丰富和臻于完备。
书法的技法包括笔法、墨法、字法(结字、结体)、章法(布局)四个方面,其中以笔法形成最早,字法次之,章法又次之,墨法则是明清以后才得到特别重视的。笔法又包括执笔、运笔和用笔三个内容,是书法技法的关键部分,其中用笔又是笔法甚至全部书法技法中最具代表性的核心部分,是关键的关键。用笔的讲究,往往是一个时代书法艺术繁荣的标志,用笔的破坏,往往会造成一个时代书法艺术的衰落甚至崩溃。从现存的历代书法作品中可以看出,隋唐以来书法变化众多,风格各殊,技法上也有不同程度的充实或突破,只有用笔仍一脉相承,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可见在书法技法中,用笔具有极大的稳定性,赵孟頫说“用笔千古不易”,确是行家的真知灼见,否定不得,因为在书法的所有技法内容中,其他都可以容许有不同程度的改革,只有用笔是不能改变的,用笔一改变,书法创作为独立艺术的地位就会从根本上被动摇。因此,当代书坛一部分菲薄技法传统而急于“创新”的人,首先拿用笔开刀,倒真是击中了中国书法艺术的要害,是足以置其于死地的。对传统不甚了了的菲薄和对新创作成果急于求成的企盼,使技法基础的修复和建设举步维艰。如果我们不充分认为创作思想上的这种危险倾向,不能促使人们在这种状态中猛醒,当代书坛完全有可能在一片急躁的呼号声中,把中国书法引入非书法的艺术迷途。
技法在书法创作中的重要地位,不仅因为它作为书法艺术独立性标志的不可动摇,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具有生命意味的艺术存在,试看《笔阵图》对用笔点画的解析:“千里阵云”、“高峰坠石”、“陆断犀象”、“百钧弩发”、“万岁枯藤”、“崩浪雷奔”、“劲弩筋节”,以及历代讨论用笔的“锥画沙”、“屋漏痕”等等等等,无不印证着古代书论中所说的“书肇于自然”、“纵横有可象者”的道理,这每一点画的形成,都包含着人对自然、对生活的理解的热爱,寄托着人的情感,从而使我们能通过对点画的组织运用,在更大的范围表达更为丰富的情感,并不像绘画的线条以塑造形象为目标,再通过形象去创造意境和寄托人的思想感情那样单纯和间接。正因为如此,一幅技法完美的一般书法作品,也能在观众中引起某种情绪上的共鸣,甚至产生心灵的震撼。
六 超越与局限
当代书坛在短短十七年间发展到如此声势、如此规模,形成覆盖全国城乡各个角落、各种行业和社会各阶段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恐怕是任何人都始料未及的,别的不说,光是一部接一部出版的厚厚的名人大辞典中,当代书法名家的数量,也已远远超过了两千年中国书法史为我们保存的书法家的总和,大师、巨匠、泰斗等的重大头衔,也出现了严重的“透支”。十年来一直有人预言的“书法热”的降温迟迟没有发生——我们这个年轻的当代书坛以其充沛的活力踌躇满志地要干一番超越以往历史的大事业,人们因自己双手创造的一个个填补历史空白的“成就”而兴奋着。
历史的机遇和历史的创造者们共同把当代书坛推拥到了历史的极限。仓促组建的各类专业机构和各类专业教育推动着书法的专业化职业化进程,从而对书法创作发出一年比一年更为强烈的呼唤。这偏偏又是一个失去权威的时代,人们一边否定权威的价值,一边却急切地要求树立权威的形象。于是从庄严的领奖台上传来了“杀猪的也可以成大师”这样让人瞠目结舌的呼叫,于是柏拉图式的“体系”和“学说”带着沉重的使命感和渴望理解的心情按响了一个又一个门铃。火热的现代书法生活给人们已经浮躁的情绪再插上一副“理想的翅膀”,让人产生一种“只要想得到就一定做得到”的幻觉。
这确实是一个能在书法界办成几件大事的时代,但也确实不是一个产生书法大师的时代。因为当代书坛的客观基础为艺术成果的获得作出了历史的限定。刚刚提出却又迅速铺开的书法创作还处在探索期的初级阶段,我们没有理由为它的现实表现和现有结果作出太乐观的判断。整整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书法技法方面的扰乱、荒废、再扰乱的过程,酿成了当代书法基础内在的深刻危机。大批刚涉足书法便身不由已地被卷入创作活动的人们,不可能认识到技法的重要性,甚至并不真正认识技法,当然更不可能认识基础的危机,在“爱拼才会赢”的鼓动下,还是一个劲地往上“添砖加瓦”;大部分理论家要么远离创作前线,热衷于自己的那一小块“自留地”,要么忙于设计一些时髦的创作模式或参与某些具体成果的评论,仿佛很不情感涉及基础危机的话题。
在充分把握时代为我们提供的大好机遇的同时,也应该充分认识时代的局限性,这才是客观而又清醒的态度。当代书坛基础的危机,是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积累起来的,也是造成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中书法艺术衰落的深层原因,书法艺术事业上的繁荣现状,容易使我们对此造成疏忽。但是,既然基础的危机是历史性的现实存在,就必然会损及当代书法创作成果的实际水平和历史价值,必然会危及我们努力构建的当代书法艺术大厦的最后成功。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欲速则不达。要克服这种时代的局限。静下心来做好基础的修复加固工作,遏制住当前书法创作盲目发展的势头,首先必须克服书法家中普遍存在的浮躁心态,实现思想意识上的自我超越。
对书法艺术提出过高的社会地位和过大的社会作用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由于受汉文字的局限,书法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不可能具有绘画等造型艺术那样快的速度和占有那么大的空间,书法创作几乎没有直接参与社会生产实践的能力,也很难达到与观众进行准确无误的对话。书法创作的主要社会功能是陶冶情操,给人们提供赏心悦目的审美享受,为提高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起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
当前书法创作中有三种倾向性的现象:一是出于“与国际接轨”的构想,对书法创作提出离开文字的抽象化要求,实际上是把书法创作纳入抽象画的艺术轨道,削弱了书法艺术的本体特征;二是试图克服书法艺术固有的局限,对书法创作提出“主题性”、“造型”化的要求,实质上是把书法创作纳入绘画创作的程式,削弱了书法艺术的独立形象;三是强调书法创作的自娱功能,并把这种自娱功能与书法创作应该具备的社会功能对立起来,这又势必削弱书法艺术应有的社会地位。当然,处在探索性初级阶段的当代书法创作实践过程中,探索总比不探索好,有倾向性总比没有倾向性好,因为他们毕竟为后来的探索者提供了一个启发性的路标。但是,我们希望在进行书法创作这一历史性艺术超越的探索中,应该充分顾及书法这一特殊艺术门类所规定的无法超越的局限性,充分顾及到我们脚下基础的薄弱,少一分盲目性,多一分科学性。因为我们肯定不愿意自己勇猛先行的战士遭受无谓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