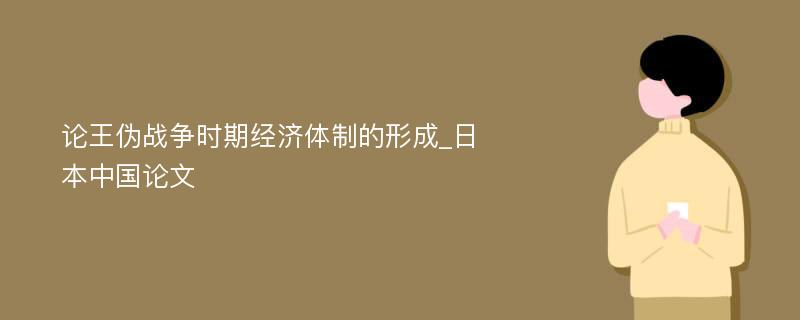
试论汪伪战时经济体制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时论文,经济体制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汪伪战时经济体制是1943年1月,汪伪政府向英美宣战,参加大东亚战争后实行的一种经济体制。对这一体制形成的背景及其过程展开深入探讨,有助于我们认识汪伪政权经济的本质,对研究日本的经济掠夺政策及日伪之间的关系也有重要意义。
汪伪参战前日本对华中的经济控制
1937年7月,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在不长的时间里,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大城市相继沦陷,中国关内的主要工业中心和农业发达地区均被日军占领。华中沦陷区(注:日本占领军将中国关内沦陷区划分为华北、华中、华南等区域。华中地区包括苏浙皖赣之一部分,上海、南京两市,武汉及其附近之狭小区域等。)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上海尤其是中国经济的中心,其特殊的经济地位自然成为日本掠夺的重点。从八一三事变到1942年底日本实行“对华新政策”,日本对华中的经济侵略大体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八一三事变至广州、武汉沦陷,日本对华中的经济要害部门实行直接的经营和控制。
八一三事变后不久,日本内阁会议便通过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明确规定:在华中,经济上的目标是“以上海为据点,确立帝国向华中方面经济发展的基础”(注: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2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1938年7月,日本五相会议又提出,华北、华中等沦陷区的经济开发与交通建设,必须有利于确立日满华三国的国防,“铁路、水运、航空、通讯等,实质上应掌握在帝国势力之下”(注: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271~2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按照这一方针,日本首先建立起由军方领导的以日本企业主、商人为主体的经济机构,取代中方原有的经济机构,对一些要害的经济部门实行直接的经营控制。在产业方面,日军进入华中沦陷区之初,便运用军管理、委任经营等方式把中国资产阶级经营的稍具规模的工厂强制接管。这些企业涉及面粉、树胶、造纸、缫丝、纺织、造船、机器、水泥、染织、金属制造等行业,共计“一百四十家,内纺织厂六十七家,其它工厂七十三家”(注:《申报年鉴》(1944),230页。)。在物资流通方面,日军实行严格管制。上海至北方各港口的海上航路全部被封锁,一切产品运出上海都必须向支那派遣军经理部第七出张所申请核发搬运许可证。在邻近抗战区地带还遍设检查站,建立起以上海为中心的扇形封锁网,封锁网内一切物资均在其控制之下。在金融方面,日军以军事武力控制占领区的金融机构,中、中、交、农四行的部分分支机构相继被其夺占。(注:参阅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史》,37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其中“中、中、交、农四行”分别为: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与此同时,为解决侵华军队的费用,日军还大量发行军用票,从1937年11月柳州兵团在杭州湾登陆开始发行流通,“1937年末发行额为137万日元,一年后猛增到3600万日元”(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日本侵华七十年史》,61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在交通方面,日军则设立华中派遣军铁道局,对京沪、苏嘉、淮南、沪甬杭等铁路实施军管。这一时期,日本扶植的维新政府只是在政治上起傀儡作用,在经济上没有实际的控制力。
第二阶段,从广州、武汉沦陷到1942年底。日本的经济掠夺政策由先前的直接经营转变为以日本为中心的“分工合作”。
随着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日军迫切需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军需工业,以补充消耗殆尽的军需物资,同时希望有新的金融和物资流通体制,以满足其侵略战争的需要。
1938年秋,日本政府将中国沦陷区的工矿业划分为统制事业、自由事业两大类,前者包括与国防资源、军需物资直接相关的矿山、钢铁工业、电力、公用事业、交通通讯事业以及与日本经济有“发生摩擦之虞”的蚕丝、水产等业,后者包括一般的工业和商业。在华中,统制事业由“华中振兴公司”负责经营。该公司成立于1938年11月,由前日本正金银行总经理儿玉谦次任总裁。公司下辖许多子公司(统称国策公司),到1942年止,计有华中矿业、华中水电、华中电气通讯、上海恒产、华中水产、华中蚕丝、华中铁道、淮南煤矿、华中轮船、华中运输、华中火柴等14家。这些子公司由中国原有工矿企业发展而来,虽都采取中日合办形式,但其经营管理权和利润都为日方所掌握。14家国策公司中,华方股份占50%以上的仅5家,其余9家中,竟有3家日方股份高达90%以上,其他6家都在60%至80%之间。统制事业以外的自由事业,如纺织、毛织、面粉、烟草、啤酒、造纸、火柴、硫酸、水泥等,名义上由中国资本“自由经营”,但都逃不脱日方各种势力的压制、操纵。
在金融方面,日本一方面继续发行军用票,至1942年发行额已达5亿元;另一方面开始扶植伪政权建立银行。1939年5月,华兴商业银行在上海成立。1941年1月,汪伪政府在南京设立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中储券。中央储备银行虽明确规定是汪伪政府的“国家银行”,但其业务大权、方针决策都在日本的掌握之下。该行先后聘请的日本顾问、顾问附、顾问辅佐有37人,一切有关银行的营业、理事会议决议事项、与国外汇兑和外国银行关系、对法币和军票以及日元的关系等事项,都必须经顾问的咨询与同意,“必要时,顾问并得要求该行总裁、副总裁以书面报告该行业务”(注:中央调查统计局特种经济调查处编:《四年来之倭寇经济侵略》(非卖品),71页。)。
在物资统制方面,情况也有所变化。汪伪政府成立后,希望从日本手中接管物资统制。1941年6月,汪精卫率团访日时,向日方提出了如下建议:“(一)由国民政府和日本在华各机关成立联合委员会,共同决定有关物资统制的范围及方法;(二)汪日双方共同组织物资流通的管理机关;(三)关于物资的运输及配给,中国商人享受同等待遇;(四)在和平区内应允许生活必需品的自由流动;(五)对外贸易问题,双方应互相协力和协商”(注:转引自蔡德金著《历史的怪胎——汪精卫国民政府》,13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经过谈判,日本接受了汪伪政府提出的某些要求,如对上海海关输出或转口之物资,由中方积极协力实行封锁;中方派警察协助日军宪兵在主要车站及码头实施货物检查;实行食盐按人口配给制度等。同年9月25日,日汪双方联合成立了“中央物资统制委员会”,日方参加的有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登集体(十三军)司令部、在华海军舰队司令部等,汪方参加的有全国经济委员会、财政部、实业部、内政部、社会指导委员会等,但实际权力完全操纵在日本军方手中。
至于交通方面,日本于1939年4月在华中振兴公司属下设立华中铁道公司,将以前的军管铁路移交给该公司经营,并相继成立中华轮船公司、东亚海运株式会社等机构,垄断华中的运输业。
总之,在日本实行“对华新政策”和汪伪政府参战之前,日本的经济掠夺政策虽有所变化,但华中沦陷区的一切重要经济部门,如工矿、金融、物资、贸易、交通等都在其严密的操纵和控制之下。傀儡政府的自主权很小,它的一切经济决策、人事任命、政策实施等都必须唯日军马首是瞻。
日本的“对华新政策”和汪伪政府的“参战”
1942年下半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接连遭到失败,逐步丧失了作战的主动权,在中国战场也陷入泥潭之中。
在大局转向对日愈益不利的情势下,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42年12月18日,日本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讨论,并经21日御前会议通过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对华处理根本方针》,决定在汪伪对美英“宣战”的前提下,放宽对它的某些控制。其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在政治上,强化汪伪政权,“尽量避免干涉,极力促进它的自发活动”;“极力调整占领地区内的地方特殊性,加强国民政府对地方政府的领导”;“交还”在华租界和“撤废”治外法规,“及时考虑对《日华基本条约》及其附属协定加以必要的修改”。(二)在经济上,以增加获取战争必需的物资为主要目标,“设法重点开发和取得占领地区内的重要物资”;在不影响日本对煤、铁、棉纱及粮食等主要战略物资需要的前提下,减少日本在经济上的垄断,要“利用中国方面官民的责任心和创造精神,实现积极的对日合作”(注: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420~4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这就是日本的“对华新政策”。这一政策于1943年初开始全面推行。
在世界形势特别是太平洋战场形势发生重大转折的关头,日本为什么要改变以前的某些侵华策略,而实行所谓强化汪伪政权的“对华新政策”呢?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日本想利用汪伪政权来榨取沦陷区更多的战略物资,以挽回其侵略战争的败局。
为应付英美“业已迫切的决战”,日本对煤炭、钢铁、粮食、棉花等物资的需求与日俱增。为解决这些问题,它开始竭尽全力地动员本国和占领区的力量,决心“举大东亚之民族,以所有之资源,集中于贯彻圣战之一途”(注:黄和材:《日寇“对华新政策”分析》,《新中华》复刊第2卷第1期。)。
日本国内经济自欧战以来便开始恶化。欧洲各国纷纷停止物品出口,国际贸易逐渐停顿,这对以进口为主的日本经济无疑是个沉重打击。1941年7月,英美两国对日本资金实施封存,更使其经济雪上加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虽占领了东南亚资源丰富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国,但这些国家的矿山、动力、工厂、交通设施等已遭到严重破坏,加之运输船只不断被美军击沉,已开发的物资也难以运回。为对付英美反攻,日本便把主要精力放到扩大对中国占领区的掠夺上。
然而,由于日本的巧取豪夺,中国沦陷区的经济已遭受严重破坏。华中地区“因日军之加紧统制愈趋恶劣,生产减少,运输梗塞,物价暴涨,漫无止境”(注:袁愈佺:《自白书》,南京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下),104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物资统制使许多地方货物来源“顿告减少或甚至断绝,遂相继陷于岌岌可危之境地”,“连年各方呼吁政府撤废禁止华中物资移动之声浪,响彻云霄”(注:纪元:《国府对物资统制之新决定》,载《上海》1943(4)。)。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如继续采用过去“杀鸡取卵”的掠夺政策,要获取更多的战略物资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迫使其不得不进行调整。日本大东亚大臣青木一男向日本最高当局建议,经济编制由汪伪出面主持,“交给中国人去办”(注:(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2卷,177页,台湾军事译粹社,1978。)。日本大本营也认为,“过去日本方面尤其是一部分军队在行政、经济等方面采取了无视中国方面的立场,挫伤其自主性的过失态度,应予纠正”(注: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27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日本政府接受了这些建议。由此可见,日本的“对华新政策”只不过是在掠夺的形式上作了改变,由以前的直接操纵沦陷区经济改由汪伪政府出面进行掠夺而已。
其次,日本企图通过强化汪伪政权以调和日伪之间的矛盾,并以“独立”、“主权”、“进步”的名义收揽沦陷区民心。
汪伪参战前日本在中国沦陷区实行的“分而治之”政策,不但加深了伪政权之间的冲突,同时也加深了日伪之间的矛盾。汪伪政府名义上是中央政府,实际上只是一个地区性政权。它对华北政委会自成体系深感不满,“武汉、广州不能实行国府统一管理,因为战争关系,接近前线,尚可理解,而华北俨如独立国,最不能信服”(注:《中华日报》1943年4月15日。)。日本对华中经济的全面控制和对汪伪行政事务的处处干涉也引起它的强烈不满,甚至产生了对立和抵触情绪。1942年12月16日,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落合甚九郎在向日本最高当局的报告中说,“国府思想上虽不抗日,却采取不抵抗、不服从主义态度。领导阶层对日本的信任下降”(注: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65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为平息汪伪的不满并调和日汪之间的矛盾,日本政府决心强化汪伪的地位和作用,使它成为伪政权的“中心势力”,并“尽量避免干涉,极力促进它的自发活动”(注: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42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另外,日本还想通过“交还租界”、“废撤治外法权”等手段把汪伪政权打扮成一个“独立”的、拥有“主权”的政府,拂拭其傀儡面目,达到收揽民心的目的。对此,青木一男说得非常清楚,要活跃地对外,尤其是对华展开新政策的宣传战,“努力收到大的政治效果”(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66·大本营陆军部6》,153页,日本东京,朝云新闻社,1973。)。
第三,日本试图通过汪伪政府的参战,以增强对付英美的力量。
对汪伪政府的参战,日本一开始并不予以支持。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汪精卫即表示愿追随日本对英美开战,但日本并没有同意。1942年7月,周佛海在东京再次表示参战的希望,也遭拒绝。因为这时日本正在作“五号作战”的准备,即1942年6月日本大本营提出的四川作战计划,其目的是“歼灭中央军主力,占领四川省要地,摧毁敌之抗战根据地,促进重庆政权的屈服或崩溃”(注:《战史丛书55·昭和17、18年的中国派遣军》,33页,日本东京,朝云新闻社,1972。)。然后利用“在五号作战后的适当时机,以宽大的条件导致与重庆政府达成全面和平的设想”(注: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27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因而不许汪伪政府参战。但到了1942年下半年,由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接连失利,四川作战计划最终导致流产,“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战局趋势已成为大本营、政府的最大苦恼,五号作战的准备工作也不得不命令停止进行。此种形势的恶化,也促进了对华政策的空前大转变”(注: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27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五号作战”取消后,日本感到对蒋诱和几乎无望,遂改变策略,试图通过汪伪政府参战以增强对付英美的实力,让伪军代替占领区的部分日军,以便自己能“金蝉脱壳”,从中国战场上抽出兵力增援太平洋战场。
从上可知,日本的“对华新政策”并不是其侵略战争进一步扩展的产物,而是为了挽救其败局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强调依赖占领区的政策,“是日本法西斯在国际地位上已陷入完全孤立状态这一种情况的反映”(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1943年7月),见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280页。)。
为了贯彻这个所谓的“对华新政策”,1942年12月20日,汪精卫应东条之召率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等抵达东京。21日下午,东条英机根据是日上午御前会议决定的要旨,向汪精卫作了通报,得到汪精卫的完全赞同。随后日汪双方就实施新政策问题进行了会谈,并达成了初步的协议。12月25日,汪精卫在东京发表《告日本国民》的广播讲话,决心与日本“同心协力,共安危共生死”,使大东亚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注:蔡德金、李惠贤:《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18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1943年1月9日,汪伪中央政治会议召集临时会议,决定设立最高国防会议,并发表宣战布告。1月15日,伪国民六届五中全会发表宣言,声称:“参加大东亚战争,实为当然之步骤,亦即最后之决心。吾党同志,应牺牲一切,以贡献于大东亚战争”(注:蔡德金、李惠贤:《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18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这样,汪伪政府按照日本的旨意及其本身的需要,以参战的名义,开始将其统治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转入所谓“战时体制”的轨道。
汪伪战时经济体制的确立
(一)战时经济机构的调整与改组
汪伪政府参战前,中央经济管理机构由财政部、实业部、交通部、水利委员会、粮食管理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等组成;地方经济机构,在各省、行政特区设有财政厅、建设厅,各特别市设有财政局、社会局,各县则没有财政局、建设局。汪伪参战后,为实行战时统制,首先对统治区的经济机构重新作了调整和设置。
1.经济机构的调整
(1)改组全国经济委员会。1943年1月13日,最高国防会议通过改组全国经济委员会的决议。1月20日,修订了《全国经济委员会组织条例》。其改组要点有二:一是加强该委员会的职能,即由原来的经济政策审议扩大为设计、计划、咨询、审议和调查。二是增加该组织机构的人选。委员长仍由汪精卫兼任;副委员长增为2人;委员从原来的14人增加到37人,其中包括一些金融和实业界的头面人物,如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原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原中国银行经理吴震修、上海民丰纱厂经理江上达等。
(2)改组粮食管理委员会为粮食部。1943年1月,汪伪政府将粮食管理委员会升格为粮食部,凡粮食增产、粮食管理事宜均由粮食部掌理。其内部组织,除参事厅、秘书厅、技术厅外,置总务、增产、调节、储备、管理五司。1943年10月米统会成立后,有关米粮采办及配给业务移交米统会接办,粮食部专办粮食增产事务。1944年4月,最高国防会议复将粮食部裁撤,其主管业务划归实业部接办。
(3)水利委员会与交通部合并,改设建设部。1943年1月,最高国防会议决定将原先的水利委员会与交通部予以合并,设立建设部,掌办“全国”路政、邮电、航政、水利及都市建设事宜。内设路政、水利两署及总务、邮电、航政、都市建设四司。
(4)改组地方经济机构。1943年2月,最高国防会议第四次会议通过《各地方经济局组织原则》,决定在汪伪统治区各省、特别市、行政特区及苏北行营管辖区域(注:苏北行营:全称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苏北行营”,成立于1941年10月,其名义上是个军事机构,实际上兼管政务。臧卓任行营主任。其管辖区域为江都、仪征、高邮、宝应、泰县、泰兴、靖江、东台、兴化、盐城、南通、如皋、启东、海门等14县。1943年5月,“苏北行营”撤销,改设苏北绥靖主任公署,汪精卫、项致庄、孙良诚先后任主任。),分别设立经济局,管理地方经济事务。原各地建设厅主管之工商事项划归经济局掌管,裁撤特别市社会局。
2.物资统制机构的建立
(1)组建全国商业统制总会。日本实行对华新政策后,为充分利用“中国方面官民的责任性和创造精神”(注: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420~4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决定将物资统制权移交给汪伪政府。1943年3月15日,全国商业统制总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唐寿民任理事长,闻兰亭为监事长,主要成员都是上海金融、实业界的大资本家。该会成立后,凡华中“统制物资之收买配给”、“各地域物资交换之营运”、“军需物资之采办”、“输出物资之供给”等事项,均归其掌理。(注:《申报年鉴》(1944),770页。)商统会总部设有油粮、粉麦等专业部门,基层组织为各业同业联合会及各地区同业公会。米粮及棉花两统制委员会为其外围机构。1944年7月,商统会进行改组,总会之下设米粮、棉业、粉麦、油粮、日用品五统制委员会,分别办理一切统制事宜。
(2)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和物资调查委员会的成立。继商统会建立后,1943年3月19日,日伪双方联合成立了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周佛海任委员长,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公使堀内干城任副委员长。委员会“以从事督导商统会完善地运用其机能,强化物资统制”(注:《申报年鉴》(1944),613页。)为任务。它每月开会一次,审议汪日双方提出的有关物资统制的重大问题,如物资的收购和配给计划,有关安定物价、维持币值的措施等(注:《中华日报》1943年3月20日。),实际上它是物资统制的决策机构。1943年5月13日,日汪双方又联合组成了物资调查委员会,以陈公博为委员长,其任务“为彻查上海中外商民非法囤积大量主要物资”(注:《申报年鉴》(1944),778页。)的情况。调查委员会有权派员检查任何厂、栈、公司、行号及个人的物资。“对查出的囤积物资,应将囤积人及囤积之物资,分别惩处”(注:《中华日报》1943年5月24日。)。
商统会、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物资调查委员会是汪伪物资统制的三鼎足,其中商统会的规模与作用最大,成为华中沦陷区物资统制的中心。
经过以上的调整与设置,汪伪战时经济管理机构基本确立。
(二)《战时经济政策纲领》的制定
1943年2月12日,改组后的全国经济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战时经济政策。会议决定取消地域经济,实施物资统制,并通过《战时经济政策纲领》,13日经最高国防会议批准,由伪国民政府公布实施。《纲领》内容计分五项(注:《战时经济政策纲领》,见台湾《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6编,1417~1418页。):
1.关于生产方面。为满足日本的军需供应和解决沦陷区基本的民食需要,《纲领》提出要发展农工生产。“改进农业技术,兴修水利,拓辟耕地,以求食粮及其他战时主要农产品之充分的增产”,开辟矿藏资源“以确保军需工业之发展”,“使军需及主要民需工业之原料及燃料能得便利之供给”。
2.关于物价方面。为平抑物价,打击囤积居奇,《纲领》主张,改善运输机构,“免除一切不必要之耗费”,尽量减少生产者与消费者之中间阶段,“以免除居间者之不当利益”,“以严格的法律制裁取缔投机居奇”。
(三)关于节约消费方面。《纲领》象征性地提出要限制或禁止各种奢侈品的生产,对“一切不必要之消费应予以取缔”,并决定“逐步并分别实施定额配给制度”。
(四)关于金融方面。《纲领》提出,“通货政策应与生产力之增进相配合,以求币值之稳定”,“健全金融机构,使金融力量逐渐集中,以与经济政策其他部门相适应”,企图逐步实现币值的统一和稳定。
(五)关于改造经济机构。《纲领》宣称,各种旧有经济机构,不适合战时经济体制者,一律予以调整或改组;各种产业部门,自生产以至于配给之各个阶段,务使其联合组成一贯的机构,作计划的运营;各种健全的产业机构,得在政府的指导监督之下,为自治的统制。
《纲领》系统地提出了汪伪参战后的经济大政方针,其核心是实行战时经济统制。汪伪政府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其统治区的经济实行干预,最后一些重要的经济活动都是在《纲领》的指导下实施的。
战时机构的调整与改组及《战时经济政策纲领》的制定,标志着汪伪战时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