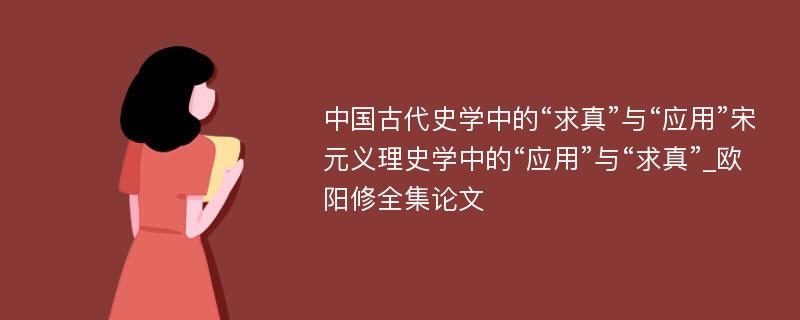
中国古代史学的“求真”与“致用”——5.宋元义理史学的“致用”与“求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致用论文,义理论文,宋元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元时期的史学以其深刻的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白寿彝先生指出:“从史书撰写的情况来看,或从历史文献学的发展情况来看,都不容易看出这个时期的发展阶段。如从史学思想上看,阶段性的发展还大致可以看出来。”(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白先生的这个见解,对于我们认识宋元史学发展趋势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从史学思想的角度考察宋元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史学出现义理化的发展趋势[1]。在这一史学趋势的影响下,宋元史家对史学的“致用”与“求真”概念重新加以思考,形成一些不同于前代的史学观念。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这个问题,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史学思想非常重要。
宋元时期,有一派史家突出强调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是由“天理”所决定的,历史研究只有以儒家的“名教”、“义理”思想为指导,才能显示出史学的功用,否则就无法评判历史的价值与意义。这种以阐明“义理”为致用原则的观念,主要表现为在经史关系问题上,主张以经学作为史学的指导思想,从学理上批评汉唐史学通过客观真实记载历史事实的方式达到借鉴历史上是非善恶的治史观念,突出强调史学的明道穷理以致用的功能。
北宋史家开始探究史学的“道”与“理”,主张史学应当体现出儒家思想作为指导的原则和功用。曾巩认为:“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曾巩集》卷11,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88页)他对史学性质与功能的界定,重在强调史学明道的本质,与前人明显不同。范祖禹指出,治史必须“稽其成败之迹,折以义理”(《范太史集》卷13,四库全书本),主张读史应当明道,撰史必须贯彻义理。程颢、程颐认为“天下只有一个理”(《二程遗书》卷1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52页),“天理”是永恒存在的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原。而人类社会的纲常伦理,就是这个绝对精神的彰显外化。他们把封建礼制与纲常名分看作维持王道政治的核心,这一观念反映到对历史价值观念的解释与评判中,就形成鲜明的以礼法道德为指归的史学功用原则。
南宋时期,治史阐明“义理”的观念已经成为经史学家的普遍共识,反映出宋人对史学的性质和功能有了进一步深入的思考。胡寅撰《读史管见》,阐述了理学与史学的关系,认为二者是“道”和“器”的性质,亦即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他说:“夫经所以明者,理也;史所以记者,事也。以理揆之事,以事考诸理,则若影响之应形声,有不可诬者矣。”(《致堂读史管见》卷16,续修四库全书本)胡寅之侄胡大壮为此书作序,准确地把握了他的思想:“后圣明理以为经,纪事以为史。史为案,经为断。史论者,用经义以断往事者也。”极力阐扬以经为本,而史为末的经史理念。朱熹继承二程的思想,进一步阐明历史演变存在“天理”。他说:“《六经》是三代以上之书,曾经圣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这边自若也。”(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0页)朱熹对经史关系作了全面论证,形成了先经后史和以经统史的观念。他指出:“凡读书,先读《语》、《孟》,然后观史,则如明鉴在此,而妍丑不可逃。若未读彻《语》、《孟》、《中庸》、《大学》便去看史,胸中无一个权衡,多为所惑。”(《朱子语类》,第195页)所谓“权衡”,就是儒家的“义理”。朱熹认为:“今人读书未多,义理未至融会处,若便去看史书,考古今治乱,理会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须是陂塘中水已满,然后决之,则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决之以溉田,则非徒无益于田,而一勺之水亦复无有矣。读书既多,义理已融会,胸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看史书,考治乱,理会制度典章,则是犹陂塘之水已满,而不决以溉田。若是读书未多,义理未有融会处,而汲汲焉以看史为先务,是犹决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朱子语类》,第195页)主张治史必须以儒家“义理”思想作为衡量尺度,才能够对历史事件和典章制度作出价值判断,否则历代治乱兴衰只不过是一幕幕相互争夺的闹剧而已,看不出有什么意义。
元初史家郑思肖指出:“史书犹讼款,经书犹法令。凭史断史,亦流于史;视经断史,庶合于理。”(《郑思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页)这就是说,评价历史的标准不是根据客观历史形势,而只能依照儒家的笔削褒贬原则。许衡说:“阅子史,必须有所折衷。《六经》、《语》、《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诸子百家之言,合于《六经》、《语》、《孟》者为是,不合于《六经》、《语》、《孟》者为非,以此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鲜有失矣。”(《许衡集》卷1,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2页)强调读史必须以《六经》寓含的“义理”为尺度,才能判断历史上的善恶是非。金履祥更明确表示:“不本于经,而信百家之说,是非既谬于圣人,不足传信。”(《仁山先生金文安公文集》卷5,清雍正九年刻本)认为应当把经义和史事相结合,以经统史,以史证经,最终发挥史学为政治服务的功能。杨维祯在《正统辨》中进一步指出:“《春秋》,万代之史宗也。”(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3,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页)主张改变《史记》、《汉书》以来史学注重记事的做法,把史学和《春秋》注重笔削褒贬的传统联系起来,撰写出所谓的“圣人之史”,从而突出予夺褒贬的道德致用原则。这一史学思潮的出现,可以看作是义理史学确立的标志,对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宋元史学义理化发展趋势及其作用的认识,大多指责其空疏不实,批评义理史学的史家仅仅突出“致用”而放弃“求真”,甚至认为其本质是一种致用史学或政治化史学,导致历史科学变得面目全非,具有落后性和腐朽性。事实上,宋元义理史学不但有突出“致用”的一面,也有讲究“求真”的一面。关于后一方面内容,常常被研究者所忽略,而它恰恰又影响着义理史学的发展,直接关系到义理史学的面貌。
首先,义理史学的史家大多具有疑古惑经的意识,体现出治学“求真”的一面。这一派史家为追求儒家“义理”之真,以“求真”的目光审视前人对经典文本的胸臆曲解和穿凿附会所造成的谬误,形成了疑古辨伪思想。
北宋史家欧阳修在强调治史明道的同时,表现出鲜明的疑古辨伪意识。他提出疑古辨伪的原则是:“《经》之所书,予所信也;《经》所不言,予不知也。”(《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131-132页)这种宗经而不惑传注的思想,包含着明确的求真取信精神。他本着这一原则,考辨《周易》之《十翼》“非圣人之作”;《河图》、《洛书》“非圣人之言”;《诗序》导致“圣人之意不明”,力求恢复经典文献的本来面目,最终目的在于探求圣人之道。欧阳修认为:“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欧阳修全集》,第481页)阐明儒家之道可以更好地应用于当代社会,为现实社会服务。欧阳修的“疑古”、“求真”意识和“明道”、“致用”思想具有密切关联,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缺一不可。
南宋义理史学思潮进一步强化,到朱熹而集其大成。在他的整个学术体系中,疑古辨伪是其阐发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体现出治学“求真”的特色。朱熹说:“读书玩理外,考证又是一种工夫,所得无几而费力不少。向来偶自好之,固是一病,然亦不可谓无助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4,四部备要本)朱熹总结了前人的辨伪经验,又结合自己考辨古籍的辨伪实践,总结出一套辨伪学理论。他指出:“熹窃谓生于今世而读古人之书,所以能别其真伪者,一则以其义理之所当否而知之,二则以其左验之异同而质之,未有舍此两途而能直以臆度悬断之者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8)朱熹一生考辨了近60部古籍,成就相当可观。他对儒家经典的存真求实态度,反映出鲜明的历史意识。
其次,义理史学的史家不仅对历史事实笔削褒贬、驰骋议论,同样注重据事直书,主张从历史事实中彰显儒家“义理”之道,能够适当处理议论褒贬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不顾历史真相。
欧阳修治史既突出议论褒贬,也重视记载历史事实。他指出:“《春秋》辞有同异,尤谨严而简约,所以别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于是非善恶难明之际,圣人所尽心也。”(《欧阳修全集》,第132页)欧阳修反对世人所谓《春秋》字字寓含褒贬之说,强调“《春秋》谨一言而信万世者也,予厌众说之乱《春秋》者也”(《欧阳修全集》,第134页),主张恢复《春秋》的本来意义。他着重指出:“凡今治《经》者,莫不患圣人之意不明,而为诸儒以自出之说汩之也。今于《经》外又自为说,则是患沙浑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尽去,则水清而明矣。”(《欧阳修全集》,第500页)要求学者正确理解《春秋》义理,避免因曲解附会而失其大义。在对待书法与事实的关系问题上,欧阳修认为:“史者,国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恶功过与其百司之废置,可以垂劝戒、示后世者,皆得直书而不隐。”(《欧阳修全集》,第849页)可以看出,欧阳修具有求真征实和据事直书的素养和品质,并在其治史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朱熹对待历史的态度,也表现出褒贬与事实并重的特征。他说:“《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朱子语类》,第2144页)倘若处处以义例解释《春秋》,必然造成穿凿附会。朱熹批评这种疏解《春秋》的学风说:“或有解《春秋》者,专以日月为褒贬,书时月则以为贬,书日则以为褒,穿凿得全无义理!”(《朱子语类》,第2146页)他在注重“义理”的同时,仍然主张应当根据历史事实撰写史书,不能以己意改修国史,批评“一代史册被他糊涂,万世何以取信”!(《朱子语类》,第3056页)因此,朱熹治史主张用儒家“义理”思想来规范历史事实,提出一套在理学思想指导下的书法义例之学。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朱熹评论史著的两条标准:一是义理是否得当,即叙述古今之变时,是否根据义理之精微来撰写;二是记录史实是否正确。朱熹认为两者缺一不可,即要根据义理来阐述,又要史实记载准确,如此便可经世致用。”(汤勤福:《朱熹的史学思想》,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219页)这两方面内容的有机结合,构成了朱熹义理史学的全部内涵。
元代史学在义理化发展趋势之下,一方面强调治史必须折中于《六经》、《论》、《孟》,另一方面也突出了重视历史事实的重要性。金履祥治史固然以《六经》为本,但并不完全迷信经书,而是注重事实的考证。他认为古史渺茫难稽,“大抵出于《尚书》诸经者,为可考信。其出于子史杂书者,不失之诞妄,则失之浅陋”(《仁山先生金文安公文集》卷1),形成了求真考信的史学思想。刘因反对空言说经的风气,指出:“古无经史之分,《诗》、《书》、《春秋》皆史也。因圣人删定笔削,立大经大典,即为经也。”(《静修先生文集》卷1,畿辅丛书本)郝经也指出:“《六经》具述王道,而《诗》、《书》、《春秋》皆本乎史。王者之迹备乎《诗》,而废兴之端明;王者之事备乎《书》,而善恶之理著;王者之政备乎《春秋》,而褒贬之义见。圣人皆因其国史之旧而加修之,为之删定笔削,创法立制,而王道尽矣。”(《郝文忠公集》卷14,乾坤正气集本)这就说明,儒家义理思想不能凭空产生,而是要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胡三省更明确地说:“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司马光撰、胡三省音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8页)这种把义理之学建立在史实之上的思想,对于扭转治史空疏学风意义重大。
在评价义理史学给中国传统史学造成的影响时,有一个问题必须搞清楚,那就是宋元时期史学发展的主流究竟是义理史学还是非义理史学。这不仅关系着对义理史学如何估量的问题,而且涉及怎样评价整个宋元史学的问题。从宋元史学的实际情况来看,史学受到理学的影响而产生义理化发展趋势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但如果说这一史学思潮已经占据整个宋元时期史学的主流,恐怕不符合实际情况。就以义理史学形成时期的南宋中叶来说,尽管朱熹撰写《资治通鉴纲目》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同时也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三部著名的记事兼考证性质的史学著作问世,更何况还有撰写《通志》明确主张记载历史而反对议论褒贬的郑樵史学,不能说义理史学完全定于一尊。对于这个问题,吴怀祺先生指出:“从理学在古史、史评及与史评有关著作中的浸透,到朱熹的考亭史学,反映宋代史学理学化运动的趋势。从司马光的涑水史学到以二李为代表的蜀中史学和浙东史学,是另一种情形,在思想上既有理学化的一面,又有重考订,求致用的一面。从主导的方面看,郑樵史学是和理学化的史学相对立的异军。从欧阳修到马端临两宋史学思想的变化,反映出宋代史学在同理学又联系又矛盾的运动中向前发展,史学没有成为理学的附庸。在论述宋代理学对史学影响时,这是应有的基本看法。”(《宋代史学思想史》,黄山书社1992年版,第22-23页)周少川先生也认为:“元代史学虽然受到理学的多方面影响,但从总体而言,并没有失去自己的独立品格,相反,随着元代理学用世精神的逐步增强,需要从史学中汲取营养,在人们心目中,史学的价值和地位得到不断提高。”(《元代史学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7-38页)这样认识宋元史学,不仅内容全面,而且观点正确,给人诸多启示。我认为,尽管宋元义理史学对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影响,但并没有把史学完全沦为理学的附庸和政治的奴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典型的义理史学在整个宋元史学中所占的比重远远小于以记载历史和求实考信为宗旨的实证史学,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则是义理史学本身也存在着一个“致用”与“求真”的相互制衡维度,并未完全失去史学固有的属性。因此,宋元时期的史学不但继承前代史学注重征实的传统,而且增添了注重经世的理论内涵,在汉唐史学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提高,达到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繁荣阶段。
注释:
①关于这个问题,可参阅蔡崇榜《〈唐鉴〉与宋代义理史学》,《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86年总32期;王东《宋代史学与〈春秋〉经学——兼论宋代史学的理学化趋势》,《河北学刊》1988年第6期;刘连开《理学和两宋史学的趋向》,《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1期和《宋代史学义理化的表现及其实质》,《广西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钱茂伟《关于理学化史学的一些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罗炳良《从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的转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2期等文。
标签:欧阳修全集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读书论文; 宋朝论文; 欧阳修论文; 朱熹论文; 文化论文; 朱子语类论文; 理学论文; 儒家思想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