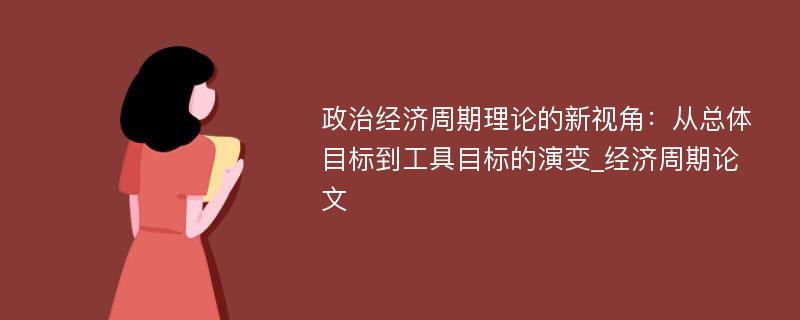
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的新视角——从总量目标到工具目标的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标论文,理论研究论文,总量论文,政治论文,经济周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585(2008)02-0054-04
政治经济周期理论多按照政党动机、参与者是否理性进行分析,研究重点放在政治因素对经济总量结果的影响上,[1][2] 例如经济增长率、失业率等,而没有注意到政治经济周期理论在观察经济政策工具主要是财政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工具上的发展。我们首先考察政治经济周期理论从观察经济总量发展到观察经济工具的原因,并指出在经验证据上支持预算周期和货币周期的存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财政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工具在解释政治经济周期现象中的关系。
一、政治经济周期理论观察目标发生变化的原因分析
我们可以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分析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的观察目标发生变化的原因。[3]
1.从理论上看,无论是执政者还是投票人、经济人都将政策工具作为自己容易观测的目标
从执政者的角度来说,与增加GNP的增长率相比,选举前从财政上讨好关键选民对选举是很有用的,也容易执行。因此,如果短期选举前的机会主义政策能提高他们再次当选的机会,那么他们会执行短期的机会主义政策。从经济人和投票人的角度讲,由于他们都是理性的,会根据对未来的预期决定选票的投向,他们的这种理性预期行为有可能使政府操纵失效,其结果就是在经济总量上观察不到周期现象。在OECD国家中,掌握大量民间财富的往往是各类基金经理人或是金融专业人才、财团法人等,这些财政金融精英人才有理性预期的能力,而他们也正是政府操纵经济时要对付的对象。
2.从经验证据看,相当多的文献所进行的统计检验表明:在经济总量上并不存在政治经济周期现象,而在政策工具上具有周期现象[4]
(1)对OECD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产出和失业上没有产生诺德豪斯式的机会主义周期,而且也基本否定了对产出和失业有永久性影响的党派理论。[5] 即选举前产出水平没有明显增加,失业率也没有明显降低。但从政策工具上观察到了选举的周期现象:选举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明显扩张现象,在经合组织国家的选举年预算赤字和货币供应往往会增加。Alesina等对OECD国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实证研究。
(2)对于政治经济周期的实证研究来说,研究德国的情况意义重大。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关于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的争论中,无论支持还是反对该现象的证据都取自德国,使得具体分析德国的情况很有意义。Berger和Woitek研究了德国在政策结果和政策工具上是否存在周期。[6] 他们使用1950~1989年的德国月度资料以及标准的时间序列分析方法,针对德国的情况进行了经验分析,得出三个重要结论:第一,数据拒绝了党派方法,包括非理性版本和理性预期版本。第二,也不支持机会主义周期的诺德豪斯假设,联邦选举对净产出和价格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第三,在政策工具的验证方面,虽然在财政政策和贴现率上都没有发现选前活动的迹象,但发现在货币总量M[,1]上确实存在机会主义周期:选前6个月M[,1]会扩张,选后12个月会紧缩。
(3)在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的实证研究中,土耳其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与有些国家不同的是,土耳其并不存在党派周期,显著存在的是机会主义周期。Ergun考察了土耳其的政治经济周期现象,他使用1985年1月至1999年5月土耳其的月度数据检验了机会主义政治经济周期理论,发现在财政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工具上都存在明显的选举前扩张行为。[7] 具体而言,在统计上非常显著的情况表明选举前政府支出会增加,同时税收收入会减少,两方面的合力使得选举前的财政赤字在统计上非常显著。在货币政策工具方面,货币供给例如M[,2]在选举前有周期现象,并显著增加;关于利率,选举后出现显著性周期现象。实际上,土币和美元的定期存款利率在选举后有显著增加。
(4)对澳大利亚政治经济周期的实证研究侧重于从支出的角度观察是否存在预算周期。Eccleston 1998年通过1976~1994年的数据考察了选举需求对财政政策制定的影响。[8] 选举需求来自两方面,一是选票上的要求,使得政府倾向于扩张性财政政策,二是来自国际金融市场和新自由主义利益集团的国际环境约束,在这种需求下,政府的财政扩张计划会承担政治成本和国际金融市场信誉的成本,这些都构成了对政府操纵财政政策的约束。通过实证估计得出结论,在操纵财政政策的核心机制上,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周期模型中假设操纵财政政策的核心机制是增加公共支出不同,澳大利亚政府偏好在选举前减少个人税负。
二、预算周期和货币周期的经验证据
对政治经济周期的观察侧重于工具目标,主要关注两方面的问题:侧重于货币政策工具的货币周期和侧重于财政政策工具的预算周期。
1.预算周期
预算周期主要观察财政部门控制下的财政政策是否有选前扩张现象,在实证中主要将政府支出和税收收入作为观察目标,从收入和支出两方面观察政府的财政行为。[9] 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存在预算周期现象。Tufte 1978年提供了大量的在选举前对财政转移支付的操纵,包括对社会保障支付和对退伍军人收入的操纵。Keech,W.和K.Pak 1989年找到了美国在1961~1978年退伍军人收入上的选举周期。[10] Alesina 1988年发现在1961~1985年期间美国在净转移支付上存在选举周期。Alesina,Cohen和Roubini 1992年找到了在转移支付上存在机会主义周期的证据。但是他们认为除了转移支付以外并不存在财政周期。从以上经验考察可以得知,无论使用转移支付还是使用税收收入作为财政政策工具,都发现在很多国家存在选举前的周期现象,支持预算周期的存在,区别仅在于表现为支出面还是表现于收入面。
发展中国家存在更为明显的预算周期。例如,在土耳其,选举前的财政操纵非常普遍;在拉丁美洲,选举前的财政操纵也很普遍,墨西哥准税收的增加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Gonzalea 1999年认为在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中,墨西哥的政府支出存在选举周期。跨国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表明了预算周期的存在。Ames 1987年研究了17个拉美国家的面板数据,表明在1947~1982年间,选举前政府支出增加了6.3%,选举后减少了7.6%,明显的存在周期现象。Schuknecht 1996年首先综合研究了1970~1992年35个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周期,认为在权力制衡比较弱以及执政者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更强的权力时,政策操纵的空间更大,并认为,在有些发展中国家,支出政策可能比削减税收在影响投票者行为上更为有效。
2.政治货币周期也存在系统的经验证据
货币周期主要观察中央银行控制下的货币政策是否有选前扩张现象,其指标有货币供给、利率、汇率等,对货币周期的实证研究主要将货币供给和利率作为观察目标,考察在选举前中央银行是否为了机会主义目的或意识形态目标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按照不同的政党动机将政治货币周期分为选举推动的货币周期和党派货币周期。对于这两种货币周期均有支持其存在的经验证据。
(1)选举推动的政治货币周期。研究选举动机的货币周期的经济学家主要有Grier、Beck、Alesina等。Grier 1987年通过估计美国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得出结论:选举时间在统计意义上显著支持政治货币周期存在的假设。[11] 而Beck 1987年认为政治经济周期模型主要反映对财政政策压力的承受能力;Grier 1989年通过引入一个更加全面的经验描述,发现即使考虑财政政策仍可以找到选举周期成立的证据。另外,Alesina和Roubini 1992年也有一个出人意料的研究结果:德国尽管拥有独立的中央银行和保守的财政政策,但仍然存在政治经济周期。而且,实证研究并没有发现财政政策满足Rogoff-Sibert模型,而是发现M[,1]的变化规律体现了政治经济周期的存在。
(2)货币政策的党派政治经济周期。Hibbs 1977年最早建立了意识形态为政党动机的模型,当我们把该模型推广到货币政策方面时就得到了货币政策的党派政治经济周期。在实证研究中,表明党派货币周期模型存在:民主党领导下的货币政策比共和党领导下的货币政策更宽松;欧洲一些国家及英国左倾和右倾政府有相同情况的证据;由国会任命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党派构成对美国的货币政策有一定影响。
而理性的党派货币模型则加入了理性预期的假设,认为在理性预期条件下只有没有被预期到的货币政策才会推动政治经济周期的产生。如果将货币政策变动与美国的失业率联系起来研究,会发现存在一定的政党影响(Chappell和Keech,1988)。而且大量证据表明18个经合组织国家的货币政策在理性预期条件下存在党派周期(Alesina、Roubini和Cohen,1997)。
三、预算周期与货币周期之间的关系
早期的政治经济周期模型,无论是机会主义的还是党派的,都开始于Nordhaus 1975年的模型,之后的模型虽然在政策制定者的动机和理性形成的模型化方面有所改变,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将货币冲击作为其分析的核心机制,其模型都建立在基本的三等式框架基础上:一个等式代表政策制定者的目标,一个等式代表货币增长率或通货膨胀率与经济活动的关系,用菲利普斯曲线表示,最后一个等式将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具体化。[12]。
这些模型在概念上和经验上存在缺陷。在经验上,以货币冲击作为驱动力来解释政治经济周期并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对货币周期的经验观察不准确。从理论上说,该模型认为货币政策基本上是由政治家根据其愿望来选择的,很大程度上货币当局屈从于政治家,因而并不能做出独立的货币决定。实际上,能观察到政治周期的国家通常具有高度独立的中央银行,例如德国,[13] 所以货币政策被政治家控制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由于仅以货币冲击作为分析机制存在如上缺陷,因此把财政政策也考虑在其中将丰富模型的内涵,新模型可称为积极的财政政策被动的货币政策模型(the active-fiscal,passive-monetary model,简称AFPM模型)。在Rogoff 1990年的预算周期模型基础上,通过假设一个更有能力的政策制定者能够在扩大政府支出或减少税收的情况下仍能不扭曲经济,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放在一个模型中来研究政治周期,这样使机会主义模型和党派模型相融合,将政治经济周期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14][15]。
比较以货币冲击为驱动机制的货币周期模型与AFPM模型,我们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区别:在货币周期模型中,货币效应是政治经济周期的驱动力,货币增长是扩张性的并导致利率下降,反映了货币政策工具在扩张方向上的变化;而在AFPM模型中,货币影响是引致效应,它取决于货币当局抵消财政效应的愿望,货币扩张是与利率稳定或利率上升相适应,仅有货币总量上的扩张,而不是货币政策工具上的扩张。从AFPM模型得到的第二个推断是选举前的货币增长应该反映财政刺激,在财政刺激和货币周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财政刺激引致了货币周期。所以,货币周期与预算周期之间的关系就是货币周期更有可能是一种增强财政推动力的效应;在试图影响选举结果上,财政政策是主动的,货币政策被动适应财政政策,财政刺激和货币周期之间是一种因果关系。
四、结语
至于中国是否存在财政周期和货币周期尚没有定论,但研究西方政治经济周期理论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我们应该在预算过程和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重视政治因素的影响,例如,在财政政策方面,重视预算民主建设、增强预算的透明度等,从而有助于国家实现税收收入最大化和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也使制定的财政政策更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对于货币政策来说,通过加强中国人民银行的组织独立性、职能独立性、人事独立性以及货币政策目标独立性等塑造真正独立的中央银行,更好地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保证价格稳定并减少经济波动。
收稿日期:2007-10-12
标签:经济周期论文; 货币政策论文; 财政政策工具论文; 经济论文; 货币职能论文; 预算控制论文; 预算执行论文; 央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