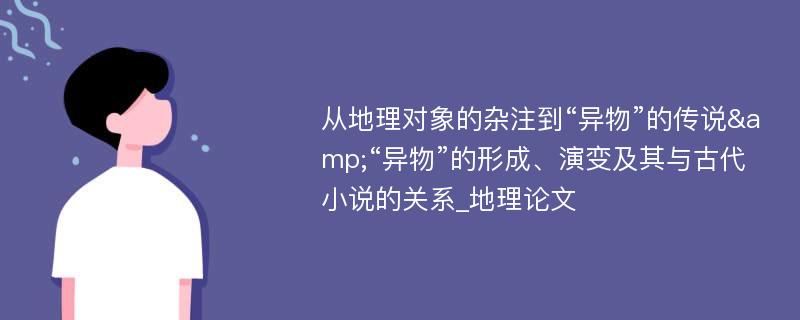
从地理博物杂记到志怪传奇——《异物志》的生成演变过程及其与古小说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博物论文,异物论文,杂记论文,地理论文,过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自汉至唐,其间以《异物志》命名的著作为数众多而又自成系统。《异物志》的生成演变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那一时代的人们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并且与我国古小说——志怪传奇——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唐以前的《异物志》中,知识性与文学性共存是其基本特征,充其量不过是知识性逐渐减少、文学性不断递增而已。进入唐代以后,文学性一举压倒知识性,成为决定《异物志》性质的主要因素,《异物志》由此从传播知识、认识世界的地理博物杂记,一变而成为志怪传奇小说。
【关键词】地理博物杂记 志怪传奇 《异物志》 生成演变过程 知识性文学性
【中图法分类号】I207.409
从东汉末年杨孚写出第一部《异物志》,到唐中叶房千里作《南方异物志》,在长达六七百年的岁月中,以《异物志》命名的各种著作不断涌现,仅今日可考者,就达20余种。这些数目众多而又自成系统的著作,在中国文化历史的发展中,构成了一种独特而又重要的景观。随着岁月的推移,这些著作大多已被历史的尘埃所掩埋,以致于在今天的文化研究中,很少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异物志》的产生、发展和衰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它反映出那一时代人们对周围世界的认识,以及这一认识发展的过程,从侧面体现着汉唐社会文化的发展。同时,《异物志》的生成演变过程,同我国古小说志怪传奇的发展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考察《异物志》产生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理清其发展线索,认识其在不同发展阶段中的特征,对于我们全面认识汉唐社会文化,研究古小说的产生、发展及其与其他文化现象的关系,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
一、地理博物学趣味的高涨与《异物志》的产生
作为一种持久的文化现象,《异物志》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宏观地看,它的产生与发展,是与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体说来,则是在这一文明进程中人们对世界认识不断扩大,地理博物学趣味持续高涨的体现。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兼并战争,除去直接的政治经济意义之外,也是中华文明内部各地域文化之间的碰撞、交融和汇通。伴随着政治、军事、文化活动的展开,中华文明圈逐渐形成并不断扩展,这一过程的演进,必然给社会的知识结构带来新异的内容,地理博物知识就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种。人们对这种知识的最早认识和重视,可以追溯到《诗经》的时代。在“十五国风”甚至一部分“雅”诗中,就有不少反映各地物产风俗的内容,以至孔子在谈及《诗》的作用时,特别提到《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①]。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博物学的滥觞。明代胡应麟称孔子为“万代博识之宗”[②],正好指出了孔子在这一文化发展中的突出地位。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都很注意扩大视野,积累博物知识。这一时期的著作,如《庄子》、《管子》、《晏子春秋》、《尹子》、《鲁连子》、《尔雅》、《吕氏春秋》等都记载了殊方异物异俗,地理博物学知识随之而广泛流传。成书于战国的《山海经》,则是第一部系统记述先秦时期人们对周边世界认识和想象的地理博物学专著,记述中的神话色彩和荒诞怪异成分,对后来的地理博物学著作有着深远影响。
秦汉统一帝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华文明圈内各地域文化融合的基本完成,人们的地理博物学兴趣随着文明圈的向四周拓展而转向更加新奇的地方。秦始皇经略南越,置桂林、南海和象郡;汉武帝通西域,设河西四郡,开发西南夷,都是中华文明圈拓展的体现。随之而来的,就是地理博物学兴趣的高涨和地理博物学的发展,尤其是汉代中西交通开辟以后。张骞通西域,带回了有关月氏、大宛、乌孙等远方各国山川地理、风俗物产的情况,更让人们亲眼见到苜蓿、葡萄、石榴、胡桃、天马等奇异物产,整个社会原有的地理博物学兴趣因此而空前高涨。除西北陆路交通的开辟以外,武帝还派黄门译长率领一批应募者自海道出发,寻求与海外诸国的交通,曾到达波斯湾、红海。在宫廷内部,武帝也聚集了一批博学多识、善言奇异的人士,司马相如、东方朔就是代表。汉赋中大量的奇花异草、珍禽怪兽,在渲染大国气象的同时,也满足着人们认识世界、获取知识的好奇求知心理。在这种心理和对外交往扩大、地理发现不断的共同推动下,汉代地理博物学有了很大发展,《史记·河渠书》、《汉书·地理志》、《水经》、《河图括地象》、《洛书》、《遁甲开山图》、《括地图》等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而专门记载远方奇异物产、风俗地理的《异物志》,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并很快获得了繁荣。向达曾云:“汉时南方渐与中国相通,殊异之物,多为中原所未有,览者异之,遂有《异物志》一类书籍出现,与《山海经》、《博物志》相先后。”[③]说的正是这种情况。汉唐之际,中华文明圈的拓展从未停止,但其发展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人们对周边世界的认识也是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由模糊到清晰,《异物志》的发展演变正体现出这一过程的种种特征。
自汉至唐,以《异物志》命名的著作,今日可考知的,共有21种,即:杨孚《异物志》,万震《南州异物志》,朱应《扶南异物志》,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薛莹《荆扬以南异物志》,谯周《巴蜀异物志》,续咸《异物志》,宋膺《异物志》、《凉州异物志》,陈祈畅《异物志》,曹叔雅《异物志》,孙畅《异物志》、《南中异物志》、《南方异物志》、《南中八郡异物志》、《郁林异物志》,郭氏《异物志》,沈如筠《异物志》,孟琯《岭南异物志》,房千里《南方异物志》、《岭表异物志》[④]。
根据现存佚文来看,早期的《异物志》大多是记载我国南方及海外诸国异物异俗的,涉及区域广阔,从我国南方大片地区直至东南亚、南亚、西亚及欧洲,均有涉及;记载内容博杂繁富,举凡各地山川、地理、气候、动植矿物及历史传说、风俗神话、商业贸易、科技工艺等,无所不包,而重点则在山川地理和物产风俗,故《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等书将其列在史部地理类。这些著作因追求知识性,内容多有事实依据,在所见与传闻的基础上加以记述,虽有怪诞荒唐和炫耀博学之处,但反映的都是人们对世界认识的真实水平及其局限,并非有意虚构和夸张。如:
交趾冬又熟,农者一岁再种。
《初学记》卷27引杨孚《异物志》
外徼人随舟大小,或作四帆,前后沓载之。有卢头木叶如牖形,长丈余,织以为帆。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风,吹风后者,激而相射,亦并得风力。若急,则随宜城减之,邪张相取风气,而无高危之患,故行不避迅风激波,所以能疾。
《太平御览》卷771引万震《南州异物志》
余甘如梅李,核有刺,初食之味苦,后口中更甜。高凉、建安皆有之。《文选·吴都赋·注》引薛莹《荆扬以南异物志》
杉鸡,黄冠青绥,常在杉树下,头上有长黄毛,头及颊正青,如垂緌。
《太平御览》卷918引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
唐以前的十几种《异物志》,内容大多类此,我们可称之为地理博物学杂记。
二、《异物志》知识性与文学性的共生
从《异物志》的发展演变历程来看,知识性与文学性共生一直是它最基本的特征,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这二者各自所占的比重有所不同罢了。如前所述,《异物志》是为了人们认识世界、增长见识而出现的,在满足着求知欲望的同时,也迎合了当时好奇求异的社会风气。这种情形在《异物志》产生之初就存在着。也就是说,在传播知识、认识世界的前提下,《异物志》从它一产生,其内部就已经隐含着非功利的文学性因素。这种文学性因素在早期还处于比较隐蔽的状态,其表现也往往是无意识的,常常见于记述的荒诞之中:
黄雀鱼,常以八月化为黄雀,到十月入海为鱼。
《太平御览》卷940引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
鼠母,头脚似鼠,毛苍口锐,大如水牛而畏狗。水田时有外灾,起于鼠。
《初学记》卷2931《异物志》
乍看起来,这类记载荒诞不经,同古代的神话没有多大差别,但仔细考查后,可看出所谓的荒诞,不在记述的态度,而在于当时人们认识水平的局限。前一则记述,在《风土记》中是这样说的:“六月东南长风,俗名黄雀风,时海鱼化为黄雀,因为名也。”(《太平御览》卷940)可见当时人们确实是这样认为的。但随着科学认识的加深,人们逐渐认识到它的不正确,其原本所具有的认识作用就丧失了,对于今天的读者,它已是纯粹的神话,欣赏的倒是它的神奇荒诞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受社会风气的影响,特别是佛教的流传、方术的盛行,以及《搜神记》、《拾遗记》等志怪小说的影响,《异物志》中的荒诞怪异内容越来越受到重视,原本隐含其中的文学性因素逐渐萌发增长了起来,并且有了道德评判的味道。知识性内容较前期已有所减退,但仍保持着主导地位;志怪的因素逐渐生长,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内容。这在宋膺《异物志》、《凉州异物志》,曹叔雅《异物志》、《南中异物志》、《郁林异物志》的佚文中都有明显的体现:
姜赖之墟,今称龙城。恒溪无道,以感天庭。上帝震怒,溢海荡倾。刚卤千里,蒺藜之形。其下有盐,累棋而生(原注:姜赖,胡国名也。恒溪,其王字也。矜贪无厌。上帝化为沙门,游于国,观其政,遂往溪乞之,以盐于帝。帝乃震怒,使蒲昌海溢以荡覆也。其地化为卤而刚坚,嶷如蒺藜,拨发其底,盐方大如棋,以次相累也。坐以盐乞天帝,故使其地化生盐也)。
《太平御览》卷865引宋膺《凉州异物志》
知识性的记载在这里掺杂进许多传说和附会,善恶果报的说教味道十分明显,正文和注释合在一起,既有知识性的记载,同时又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相似的内容,在《水经注·河水》中这样记载:“龙城,故姜赖之墟,胡之大国也。蒲昌海溢,荡覆其国,城基尚存而至大,晨发西门,暮达东门。浍其崖岸,余溜风吹,稍成龙形。西面向海,因名龙城。地广千里,皆为盐而刚坚也。行人所迳,畜产皆布毡卧之。掘发其下,有大盐方如巨枕,以次相累。类雾起云浮,寡见星日,少禽,多鬼怪。西接鄯善,东连三沙,为海之北隘矣。故蒲昌海亦有盐泽之称也。”与这样纯粹的地理记载相比较,《凉州异物志》的文学意味就显而易见了。
从总体来看,知识性与文学性共存,是唐以前很长一段时期内《异物志》的显著特征。科学中夹杂神话,文学中包含知识,既有明显的地理博物杂记特征,又很容易混淆于同时期的一些志怪小说。这从前人的认识和著述中就可以看出。这时的《异物志》,文学性虽在逐渐增多,但还未能压倒知识性成为主导因素,还不足以改变《异物志》的整体性质,还只是处在量变的过程中,所以,这时的《异物志》仍然还是知识性的地理博物学杂记。
三、《异物志》认识使命的完成及其消亡
从春秋战国以来的中华文明圈向周围的不断拓展与融汇,到唐代已基本完成,中华文明圈大体形成,人们对处在同一文明圈内部及其邻近的世界不再感到新奇和陌生,从此直至鸦片战争,人们对世界的了解认识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对地理博物学的兴趣也不再如前一时期那样普遍持续地高涨,这样,《异物志》的存在也就失去了它的社会文化根基。
在唐以前的《异物志》中,知识性与文学性共存是其基本特征,不过是知识性在逐渐减少,文学性在不断递增而已。进入唐代之后,知识性、文学性二者共存的局面被打破,文学性一举压倒知识性,成为决定唐代《异物志》性质的主要因素,《异物志》从传播知识、认识世界的地理博物杂记,一变而成为志怪传奇小说。这时的《异物志》,其写作已完全是为了满足人们猎奇求怪的心理,在记述中尽量渲染荒诞怪异,甚至抛开事实与传闻的基础,捕风捉影,凭空虚构,文辞也开始追求华艳绮丽,与早期的《异物志》大相径庭,更是与《淮南子·要略》所提出的“地形者,所以穷南北之修,极东西之广,经山陵之形,区川谷之居,明万物之主,知生类之众,列山渊之数,规远近之路,使人通回周备,不可动以物,不可惊以怪”的原则背道而驰,恰恰就是“动以物”、“惊以怪”,从而跻身于志怪传奇之林。请看以下记述:
唐孟琯尝于岭表买芥菜,置壁下忘食。数日,皆生四足,有首尾,能行走,大如螗螂,但腰身细长。
《太平御览》卷980引孟琯《岭南异物志》
后汉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郡人,高才过人,性聪,明天象,善书。累拜侍中,出为河间王相,年六十二。昔建州满城县山有兽,名骇神,豕身人首,状貌丑恶,百鬼恶之。好出水边石上,平子往写之,兽入水中不出。或云,此兽畏写之,故不出。遂去纸笔,兽果出,平子拱手不动,潜以足指画之。今号巴兽潭。
《太平广记》卷210引郭氏《异物志》
前一则记述采用荒诞夸张的手法,表现了人们对南方湿热水土环境中植物生长迅猛的惊异,已完全脱离了知识性记载的范围,充满浓郁的文学情味,是完全的志怪小说了。后一则故事完整,叙述生动,描写细致,在志怪的基础上,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塑造,更近于传奇。志怪小说向传奇小说的演变,是唐代文学发展的重大突破,这一变化,也同样表现在《异物志》的发展中,“巴兽潭”故事所表现的,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艺术特征。中唐以后,随着传奇小说这种艺术形式的成熟,《异物志》也完成了由知识杂记到小说的转变,《太平广记》卷112所引无名氏《异物志》“李元平”故事,就是这种转变完成的代表性作品。
唐李元平,故睦州刺史伯诚之子。大历五年,客于东阳寺中。读书岁余,薄幕,见一女子,红裙绣襦,容色美丽,娥冶自若。领数青衣,来入僧院。元平悦之,而窥见青衣,问其所适及姓氏,青衣怒曰:“谁家儿郎,遽此相逼,俱为士类,不合形迹也。”元平拜求请见,不许。须臾,女自出院四顾,忽见元平,有如旧识。元平非意所望,延入,问其行李,女曰:“亦欲见君,以论宿昔之事,请君无疑嫌也。”既相悦,经七日。女曰:“我非人,顷者大人曾任江州刺史,君前身为门吏长直,君虽贫贱,而容色可悦。我是一小女子,独处幽房,时不自思量,与君戏调。盖因缘之故,有此私情。才过十旬,君随物故,余虽不哭,殆不胜情,便潜以朱笔涂君左股,将以为志。常持千眼千手咒,每焚香发愿,各生富贵之家,相慕愿为夫妇。请君验之。”元平乃自视,实如其言。及晓将别,谓元平曰:“托生时至,不可久留,后身之父,见任刺史。我年十六,君即为县令,此时正当与君为夫妇未间,幸存思恋,慎勿婚也。然天命以定,君虽别娶,故不可得。”悲泣而去。他年果为夫妇。
像这样故事曲折,情节描写细腻,人物形象鲜明而篇幅又长的作品,已丝毫看不出唐前《异物志》的知识杂记的形迹,完全蜕变为传奇小说了。至此,一种沿续了六七百年的文化现象已走到了它的尽头。
唐以后,尽管地理博物学著作仍在不断出现,科学性已有明显增强,虚妄荒诞成分也几近消失,但专门记述殊方异物、突出新异特点并以《异物志》命名的著作则不再见于历史记载;而已有的著作,也大量亡佚,仅有一些片断佚文散见于史籍之中,没有一部完整的著作流传至今。今人对待《异物志》的态度,明显地分作两种:历史地理学家注重其知识性因素,视其为可资参证的史料;小说史家则看重它的文学性成分,视其为小说的早期发展。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现象,《异物志》的意义被割裂开来。在价值判断上,史家讥其怪异,文学家又嫌其平实,《异物志》作为人类认识水平发展过程的阶段性特点的表现,被完全忽略,它自身的发展演化及其与科学和文学的关系,也从未有人论及。本文所述,只是对《异物志》这种现象及其与科技、文学的关系的初步探讨,抛砖引玉,希望引起更多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与研究。
收稿日期:1997-3-28
注释:
①《论语·阳货》。
②见《少室山房笔丛·华阳博议》。
③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出版社1957年版,第566—569页。
④参拙文《〈异物志〉编纂及其种类》,《社科纵横》199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