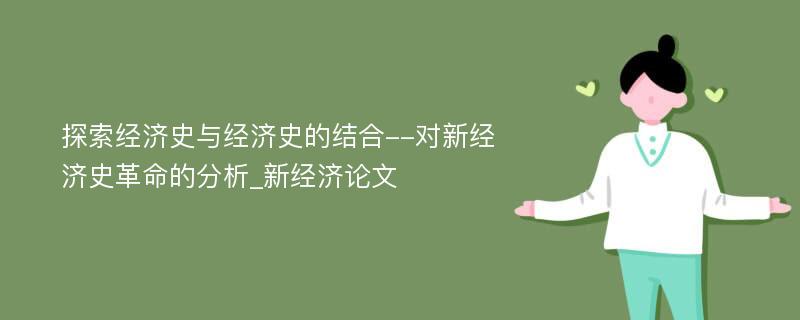
探寻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结合——“新经济史革命”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史论文,理论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1)01-0040-06
学术史上的“革命”,都是指伴随主流学派或学术体系缺陷的发展而滋生的新流派或新学术思想体系产生、发展并逐渐取代原有主流学派或学术体系地位,从而学术发展进程出现重大转折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经济史”的产生、发展及其影响过程正是这样一场理论革命。本文考察和评析“新经济史革命”产生与发展的路径、内容,从中探寻有关对中国经济史学与经济学发展的启示。
一、“新经济史革命”产生与发展的路径
这场革命的主线是探索人类历史上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因素与动力。围绕这一主线,这场革命分为逻辑上互相呼应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计量分析为基本内容的,其方法主要是“反事实度量法”和“间接计量”。第二阶段是以制度分析为基本内容的,主要方法是制度经济理论特别是产权理论。第三个阶段是历史生理学,主要方法是经济发展的热动力学与生理学。三个阶段环环相扣,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新经济史革命”的第一阶段,即产生阶段,也是以历史计量分析为主的阶段。
20世纪50年代,新经济史学家发起“新经济史革命”,直接地是因为他们对当时美国经济史的研究状况不满和对已有结论的怀疑。在他们看来,当时美国经济史研究突出的问题是:1.资料有限;2.主要是定性分析,并对资料进行简单的分类和归纳;3.强调史料考证与罗列,与经济理论脱节。1960年,戴维斯说:“如果这门学科还想完全停留在文字传统方面,那么除了继续把现存的史料拿来改头换面一下,除了延续经济学与经济史学之间长达100年的脱节现象之外,很难看出还有什么指望”。(注:Davis,L.,ct.al.,"The Problem of Quantitativc Rese-arch on Economic History",Journal of Economuc History,Dec.,1960.)对这种资料与加工资料方法的不满进而发展到对原有一些结论的怀疑。他们“怀疑对美国经济史的传统解释,深信新经济史要以可靠的统计资料作为坚实的基础”,他们希望以此为基础改写美国经济史。
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诺思开始运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包括国民经济核算法、经济增长要素分析法和经济计量分析法,研究美国经济增长史。他首先对1790-1860年间美国国际收支状况进行经验性研究。以后,他又进一步提出一个关于同期美国经济增长的模型,这些成果集中体现在1961年出版的《1790-1860年美国经济的增长》一书中。这项研究被认为是“新经济史学家”运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改写美国经济史的开端。
1964年,福格尔发表的《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是“新经济史学家”提出并运用“反事实度量法”这一“新经济史”两大计量分析方法之一的代表作。在福格尔之前,美国经济史学界都认为铁路运输在19世纪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起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如罗斯托认为美国经济起飞与铁路不可分割。福格尔认为这种观点只是假设,没有经过验证,因而是可疑的。他指出,只有能证明采用铁路比采用其他方法所带来的增值额直接地或间接地占19世纪美国经济产出的大部分,才能认为铁路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要计算出铁路所带来的净收益,就要采用一种反事实模式,即假设一演绎模式,以推断出各种未发生的情况。他把实际国民收入水平与假设没有铁路时国民收入水平加以比较,发现,铁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被经济史学家夸大了。在没有铁路的情况下,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最多只减少3%多一点,铁路并没有在美国经济增长中起决定性作用。即使没有铁路,美国经济增长最多推迟两年时间。换言之,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应该从铁路之外的方面去寻找。
如果说福格尔在1964年提出并运用了“反事实度量法”,那么,1968年,诺思在《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中,提出并运用了历史计量分析的另一个主要方法,即“间接计量”分析。1600-1850年间,海洋运输生产率的提高是显著的事实。为什么会提高呢?传统的解释归结为技术进步,但是,海洋运输使用轮船代替帆船的技术进步发生在19世纪后半期,而在1600-1850年间帆船并没有发生重大改进,所以,传统的解释暴露了问题。诺思依据间接计量法,认为,1600-1850年间的海洋运输生产率虽然没有直接可比数字,但可以运用航运成本作为间接衡量航运生产率的指标,然后,找出影响航运成本的各个因素进行分析。计算结果表明,在1600-1850年间平均每吨货物所担负的成本是下降的。诺思对每项成本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由于航运安全性加强和市场经济扩大等因素的作用使成本降低的结论。这样,诺思通过间接计量法,算出了缺乏直接可比数字的海洋运输生产率的变化,解释了航运增长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诺思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单纯的量化分析,因为他实际上考察了数字背后更深层次的制度性因素,即市场扩大,市场规则趋向完善,交易活动安全性提高等。既然“新经济史学家”意识到制度性因素在经济发展史中的作用,他们必然要从历史中验证。因为,在他们看来,“经济史与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即是说明那些创造出能诱致递增生产力的经济环境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变迁过程”。(注:North,D.,
"Institution",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Winter,1991.)因此,“新经济史革命”开始进入第二阶段。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是“新经济史革命”的第二阶段,即以经济制度分析为主的阶段,也是这一“革命”的发展阶段。
运用制度经济学框架分析经济史的尝试首先是从对欧洲经济史的分析开始的。1970年,诺思与罗伯特合作发表“西方世界增长的经济理论”一文,1971年,两人合作发表“庄园制度的兴衰:一个理论模型”。如果说此前,诺思不自觉地意识到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可能有作用,在这两篇文章中,他们自觉地提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观点: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
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经济理论界发生了“产权运动”,“新经济史学家”及时借鉴这一运动的成果,以产权理论作为经济史制度分析的主要视角和方法,考察了美国制度变迁的产权含义。1973年,诺思与罗伯特·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将产权理论运用于欧洲经济史的研究,探索欧洲兴起的原因。该书的核心观点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欧洲的发展正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注: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译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传统的对欧洲兴起原因的经济史解释是,以技术进步、规模经济、教育发展和资本积累为主要表现的工业革命。实际上,这种解释是不够深刻的。因为,这些因素和工业革命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表现和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换句话说,还必须探索这些因素的深层原因,探索什么保障和促进了工业革命产生和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创新、资本积累等,即必须探索工业革命为什么在欧洲首先发生的原因。诺思从制度经济学理论出发,通过对900-1700年间西方世界经济史的考察,认为,这一原因在于制度,即在欧洲首先出现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为什么历史上的经济增长没有在整个西方世界同时出现,而首先在尼德兰和英格兰出现,原因在于,尼德兰和英格兰最早进行了产权结构方面的改革,从制度上激发和保护了经济领域的创新活动,因此,它们首先在西方世界兴起。而法兰西和西班牙则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它们在西方世界的竞争中落伍了。
1981年,诺思出版的《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一书是他运用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系统分析经济史的代表作。按照诺思的定义,“结构”即制度框架,“变迁”指制度创立、变更以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注: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25页。)在本书中,诺思构建了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框架,然后,在本书第二篇“历史”中,运用这一框架解释了人类社会全部经济史。其核心结论是,制度变迁是经济史演变动力的源泉。在传统经济史学观看来,产业革命的爆发无非是蒸汽机和飞梭之类的技术发明带来的技术进步的结果。产业革命似乎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突变。但在诺思看来,正是一系列的制度方面的变化给产业革命这一根本性的变革铺平了道路。因此,产业革命作为人类社会经济史上第二次经济革命(第一次经济革命是农业的产生),是一系列因素长期发展、变化所带来的渐进性结果。而其中,制度变迁是动力的源泉。
由于诺思成功地将产权理论运用于经济史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史进行了重新的解释,他对西方经济史的考察成果成为西方经济学中“产权运动”的四大支柱之一。(注:“产权运动”的其他三大支柱是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经济学和比较经济组织理论。参见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15页。)他本人也成为产权学派的代表人物。
当制度因素被确立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性推动因素以后,新经济史学家开始致力于探索推动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综观人类对经济增长因素的探求,可以发现,这一过程是沿着技术(如技术发明、技术改进)、制度(包括经济、政治、法律制度,社会文化)的路径展开的,进一步的探求必然推进到人本身。正是在这一时期,意大利著名经济史学家卡洛·奇奇波拉出版了《人口经济史》,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人类发展中热量与能源的转换问题;同时,医学、生理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为精确计量人体转换和输出热能的效率提供了分析工具。因此,新经济史有关经济增长因素的探索必然进入新的阶段。
80年代以来,是“新经济史”第三阶段,即将人类生存状况演变史研究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结合起来,将历史计量分析、制度分析加以综合和扩展并与现代生物与医学分析技术等自然科学成果结合起来的阶段,也是这一“革命”拓展的阶段,将经济史分析与现实经济政策探讨结合的阶段。
80年代以后,福格尔的研究着重强调经济发展中“人”在生存与工作中的物质和制度条件。他把人力资源的各种生理指标的历史变化作为对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反应,把经济发展中的投入产出过程类比为物理上能量守恒与转换过程,提出了他所谓的“经济发展的热动力学与生理学”。这是对经济历史统计学、历史计量学和制度分析的重要扩展。福格尔的研究和基本结论是:
首先,就经济发展的热动力学因素而言,他以热力学第一定律,即能量转化与守恒定律为基础,把机械上的能量扩展到人力资本上的能量上,提出了营养改善促进经济发展的结论。他推测,英国在1790-1980年间由于营养改善,劳动强度相应调整,仅此一项就大约使人均收入增长30%多,即过去200多年间英国经济增长的30%可以归因为总体营养状况的改善。(注:罗伯特.福格尔:《经济增长,人口理论和生理学:长期过程对制定经济政策的意义》,载王宏昌编译,《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演讲集》(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7页。)
其次,从经济发展的生理学角度,福格尔运用历史计量分析方法,评估人的体型与重量变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他的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人类生理学结构的变化,例如人的体型与重量的变化,提高了人体将食物能量转化为工作产出的人体效率提高,这项因素可以解释英国
1790-1980年间长期经济增长率的20%。这样,在他看来,热力学与生理学因素可以解释这一时期英国经济增长率的50%。(注:罗伯特.福格尔:《经济增长,人口理论和生理学:长期过程对制定经济政策的意义》,载王宏昌编译,《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演讲集》(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可见,福格尔实际上是把人口作为受制于社会基本制度的一项制度安排来研究的。人口的热动力学与生理学只是为了解释人口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而借用的技术性工具。关键问题在于,一个国家不仅值得对这项制度进行投资,而且应该通过长期性经济政策对这项制度进行持续投资。这样,长期被经济学家设定为外生因素的人口被内生化了,并且成为长期经济发展的重要解释变量。福格尔的分析还试图表明,从长远角度来看,国家的干涉只能对经济发展起次要的作用,相比之下,更为根本的推动力应该是人口、人类潜在能力与质量的提高与发展,以及以前积累的资本储备和有利于发挥个人积极性的社会经济制度。
从上述过程看,“新经济史革命”从产生到80年代,经过了一个展开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基本路径是:从研究的方法来看,从经济历史计量分析发展到制度分析,再发展到历史计量分析、制度分析与经济热力学和生理学分析等自然科学的结合;从研究的地域范围来看,从美国这个国家的单个部门经济史,发展到美国整个国民经济史,然后发展到欧洲整体经济史,再发展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历史的比较分析。
二、“新经济史革命”的内容及其评析
尽管诺思在宣称他们的“革命”正在进行时是针对传统经济史研究,但是,事实上,这场“革命”不仅给经济史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而且给经济学的发展以及经济史与经济学的结合指明了趋势。
对于经济史学来说,“新经济史”的“革命性”表现在:
首先,在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层面,“新经济史”强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意义。“新经济史”首先“新”在运用经济理论作为经济史的分析框架。A.K.凯恩克罗斯曾在一篇“称颂经济史”的演讲中划分了两种经济史,即历史学家的经济史和经济学家的经济史。前者与历史的唯一区别是它研究的对象是经济制度和经济现象。经济学家的经济史则运用一般的理论来说明历史事件,而不单是就事论事。两类经济史学家往往互相排斥。例如克拉彭拒绝使用经济理论,他认为经济理论为经济史毫无关系。(注:A.K.Cairncross:"In Praise of Economic Histo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2cd scr.XLП,2(1989)p174.)与此相反,新经济史学家们指出,传统的经济史研究与经济理论是脱节的,因此,在方法论、分析工具、资料运用、研究结论的可信性以及学术价值等方面都存在缺陷。例如,福格尔认为,传统经济史学家尽管也试图描述和解释经济增长,但是由于缺乏精确的计量方法和统计资料,只能在模糊的推测中打转转,不能给人们提供关于经济增长的准确信息;而经济史与经济理论的分离使得经济史研究局限于单纯对史料的考证,不能对现代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见解。(注:参见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9-260页。)
“新经济史”则强调经济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分析框架意义。在“新经济史革命”的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尽管主要是运用历史计量分析,但是,正如福格尔所指出的,经济理论是历史计量分析的理论指导。要把不能直接比较的数字变成可比数字,必须首先有经济理论作指导,一方面,经济理论被用来决定究竟在哪些方面需要计量;另一方面,经济理论被用来指导间接计量中数字换算问题。(注:参见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实际上,新经济史学家在进行历史计量分析时,主要是以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等理论为分析框架的。在第二阶段,即制度分析阶段,新经济史学家主要运用制度经济学特别是产权理论的最新成果,解释整个人类经济史,特别是欧洲的兴起。
如何看待将经济理论引入经济史的研究?如果作为历史学家的经济史与作为经济学家的经济史的划分成立的话,经济史应该是经济学家的经济史。经济史不应该是研究经济历史的历史学,而应该是研究经济历史的经济学。经济史不是单纯的历史研究,而是采用经济理论作为方法的历史研究。这是因为,经济史是经济学的基础学科,是为经济学服务的。同时,经济史的产生与发展与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能想象,要研究经济的历史或者要对历史进行经济的分析和解释,而不运用经济理论,还能有什么更合理的方法。
其次,在经济史研究的逻辑学与方法论层面,“新经济史”强调“间接计量”和“反事实度量法”。
传统经济史的研究主要只限于把可比的数字拿来直接比较和分析,这约束了经济史学研究的范围和领域。“间接计量”即通过运用经济理论的指导,把不能直接相比的数字通过核算,使他们成为可比数字。这不仅充分利用了现有数据资料,而且扩大了经济史研究的范围。可以对以往因为缺乏数据资料或因资料无法量化而无从着手的课题进行研究。
我们认为,“间接计量”不失为一种可以采用的历史计量分析方法。一方面,任何历史资料,包括数据,都和文物一样,包含着历史的大量信息。按照信息论的观点,任何一个史料都可能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全息”反映。但是,由于认识方法与认识水平的局限,人们不可能充分挖掘出其中的全部信息。“间接计量”则提供了一种利用资料与数据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科学推断和相互印证的方法,可以赋予数据以丰富的、鲜活的生命,唤醒数据中沉睡的历史。另一方面,只要采用科学的经济理论来构建数据与资料之间的联系,确定科学合理的参数,运用“间接计量”方法得出的结论是具有一定的说明力和解释力的。诺思有关1600-1850年间美国海洋运输业效率提高原因的研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也证明了这种方法的科学性所在。
“反事实度量法”是指在经济史研究中,根据推理的需要,提出一种与事实相反的假设,并以此为依据估计经济史上可能出现而没有出现的情况,来与历史事实做比较。例如,19世纪后期,美国西部已经建成了铁路,但为了推理的需要,可以假设当时没有铁路;又例如,18世纪70年代以前,北美殖民地的存在是历史事实,但是,可以假设当时美国是独立的。
这种方法受到了以尊重历史事实为信条的历史学家的反对,他们认为这种研究是“‘好像’历史、准历史、虚构历史——根本不是历史……而且是凭空捏造”。(注:参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译本第一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59页。)应该说,从逻辑学和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方法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从逻辑学角度看,要想证明有关某种因果关系的判断是否正确,而又找不到直接的证据和方法,那么,证明该判断的逆命题是否正确,完全是等价的,是合乎逻辑的。因此,虽然历史本身不能假设,但是历史研究中是可以运用假设方法的。从经济理论角度来看,“反事实度量法”可以看作是机会成本概念与计量分析的结合和扩展。新经济史学家只是将一般的经济学分析方法运用到经济史研究中。他们对长期经济增长感兴趣,但又不愿意将已经发生的经济增长成果看成是理所当然的,更不愿意接受传统经济史学家的解释,于是,他们设想如果经济增长的条件发生变化,经济增长会产生什么绩效,并与实际绩效作比较,以解释经济增长的因素以及各种因素的贡献。这实际上是经济增长因素的一个事后比较分析。当然,这只是一种分析方法,由此形成的研究不是真正的历史,而只是观察真正历史的一种参照。
第三,在经济史研究的分析工具层面,“新经济史”强调历史计量分析。
无论是“间接计量”还是“反事实计量法”,都是运用历史计量分析。应该看到,历史计量分析方法可以使经济史研究尽可能精确化和定量化,可以弥补传统定性分析为主方法的不足。在历史统计资料相对贫乏的情况下尤其如此,正如福格尔和恩格尔曼指出的:“如果资料十分完备,简单的统计方法就够用了。资料越是贫乏,就越需要使用高深的统计方法。但无论如何,可以利用的资料的确总是低于标准统计方法需要的最低限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获得成就,关键就在于研究者要能够设计出在利用资料方面特别有效的方法,也就是说,尤其要发现一种可以靠有限的资料来解决问题的方法”。(注:Fogel.,R.& Engerman.,S.,"Time on the Cross",Little Brown,1974.)这是对历史计量分析方法的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但是,经济史不是简单的数学问题,量化分析必须与质态分析相结合。应该说,诺斯、福格尔等人坚持了质态分析与量化分析结合的方法。他们先从庞杂的历史资料中抽取最有用的部分加以定量分析,然后,再从“质”的角度去解释“量”的结果之所以产生的原因,把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制度因素加以内生化处理,从而对经济史进行有说服力的解释。但是,也有一部分经济史学家出于将经济史“科学化”的意愿,盲目使用过多的数量分析方法,以致于出现了历史计量分析的庸俗化。正如索罗所批评的:“很多著作看起来正是我讽刺过的那种经济分析:千篇一律地用积分、回归、t系数来替代思想”,“经济史已经被经济学腐蚀了”。(注:Solow,R.,"Economics:is Something Missing",in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Modern Economist,cd.,Packer,W.Blackwell,1986.)
对于经济学来说,“新经济史”的“革命性”意义表现在:
首先,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看,“新经济史”强调经济史研究在经济学发展中的地位,促使经济学研究历史视野的回归。正如麦克罗斯基(McCloskey,D.)在1976年就指出的:“在大约15年中,计量历史学已经向历史学的同行们阐明了经济学的重大作用,那么现在,他们也应该向他们的经济学同行阐明历史学的伟大作用了”。(注:MeCloskcy,D.
,"Does the Past Have Useful Economics",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No.2,1976.)在经济学产生与发展的早期阶段,经济学家是具备历史视野的。亚当·斯密首先是从历史中抽象出他的理论体系的一系列范畴和原理,如分工、市场、分工导致市场扩大,市场规模制约分工程度等,然后专门研究了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在历史中抽象了经济发展的不同类型,解释了不同类型形成的历史原因,以历史证明他的分工与市场理论。德国历史学派则从历史出发证明建立德国国民经济学的必要性,试图从历史事实出发反对英国古典学派的自由贸易主义。熊彼特、库茨涅兹、罗斯托、希克斯等,既是经济学家,又是经济史学家。经济学家还从理论的高度论述了经济史在经济理论中的作用。马歇尔曾在给艾奇沃斯的信中论述了将经济史与经济学割裂开来的危害:“我想没有比抽象的、一般的、或纯理论的经济学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更具有灾难性的想法……进行一般推理是必要的,而广泛彻底的事实研究也同样重要。把这两方面的工作结合起来,就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注:参见A.K.Cairncross:"In Praisc of Economic History",Economic History Review,2ed ser.XLП,2(1989)p174.)熊彼特是“20世纪主要经济学家中分析经济制度变迁的唯一的一人”。他一向重视经济史,他曾说过,“经济‘科学’家与一般对经济问题想过、谈过和写过文章的人之间的差别在于‘科学’家掌握了三门基础学问:历史、统计和‘理论’”。这三门学问合在一起,构成我们所说的经济分析……在三门基础学问中,包括直至今天为止的事实在内的经济史是最重要的一门”。(注:Schumpeter,J.,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12-13.)
其次,新经济史学的结论推进了经济的发展。新经济史有关经济增长因素的历史考察推动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它测试了现有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力与解释力。特别是,它的成果促使一系列经济增长因素的内生化。新经济史有关经济制度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考察促进了经济制度的内生化,有关经济增长热力学与生理学的分析促进了经济分析中人口因素的内生化。此外,新经济史的分析还将公共选择、社会知识、意识形态、法律制度等因素纳入了经济理论的视野,扩展经济理论的分析空间。诺思成为“产权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就是新经济史这种作用的突出表现。
三、结论与启示
“新经济史”是具有生命力的。这场革命是否已经终结,我同意诺思弟子们的观点,即它正在继续进行之中。“新经济史革命”是一场尚未完成的革命,它正在拓展其边界和深度。陈振汉先生认为,这场革命以1974年福格尔和恩格尔曼合著的《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人奴隶制经济学》的“失败”为标志而终结。(注:陈振汉:“西方经济史学与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这部书是否失败,是值得讨论的。但是,陈先生实际上把“新经济史革命”仅仅界定为对美国经济史分析的革命,界定为在方法上运用“计量分析”和“反事实度量法”,而将诺思等人在70年代以后转向运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对欧洲经济史的重新研究排除在“新经济史革命”之外。实际上,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新经济史革命”包括若干阶段,70年代以后,诺思等人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上的转向正是“新经济史革命”的深化和拓展。而且,这场革命正在对经济史的发展产生日趋深刻的影响。正如诺思所说:“对一个学者所做的贡献的真正检验,不在于他的名声,而在于他的思想所具有的力量,要看它是否鼓励他人,是否能促进经济学科充满生机以及它本身是否有能力长期存在下去”。(注:转引自厉以平等:“经济增长与制度因素”,《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译本序言,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同样,对于一种新的学术流派,也是如此,判断其生命力,主要看它是否对学术发展方向具有长期而深刻的影响。
“新经济史革命”给经济史学和经济学的发展带来的主要启示,就是经济史与经济学必须结合,实现互动、互补和互相交换知识。新经济史的产生是在经济增长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的启发下开始的,新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将制度、人口逐渐内化为经济增长的因素,因而丰富了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史的发展是在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展开的,其成果反过来推动了制度经济学特别是产权理论的发展。1984年12月,美国经济学会在美国德克萨斯的达拉斯召开了一次小型研讨会,其论题就是“经济史:经济学家的必要条件但非充要条件”(Economic History:A Necessary though not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An
Economist),几乎所有与会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都担忧经济学家对经济史的忽视以及经济学与经济史的隔离状态。他们强调经济史与经济学应该互相补充、互相提供方法,并通过分工协作互相促进。
新经济史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具有借鉴意义。前面所述的“新经济史革命”的几个层面都是值得中国经济史学界借鉴的。在运用经济理论方面尤为迫切。传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也运用理论,但主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这种理论主要是一般历史观和历史理论,不是具体的经济观和经济分析方法。运用这种方法研究的经济史,主要是历史学家的经济史。我们固然需要历史学家的经济史,但需要经济学家的经济史,这就要需要运用经济理论。
借鉴和运用历史计量分析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以计量历史方法为例,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看,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为计量分析方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正如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A.索布尔曾说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历史社会学有许多相似之处,所有的政治史,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社会史,而对社会史的最终分析,只能是计量史。因为应用于社会史研究的资料必须以精确的有关社会结构、社会变化过程和社会经济事态的知识为前提条件,绝不能是“脱离实际的”或“非社会性的”。这类资料本质上就具有数量特征。(注:参见G.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68页。)从资料方面看,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记录未曾中断,而且丰富多样。从经济史和人口史的资料看,正统的25史都有专门记载赋税、田亩、人口以及其他经济情况的《食货志》,成为一种定例,这些《食货志》中包括定量性资料。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文献,特别是众多的地方志中,数量型资料也很丰富。我相信,如果运用合理的理论框架,采用科学的计量分析方法,是可以通过历史计量分析方法的运用提高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水平的。
标签:新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革命论文; 美国革命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美国铁路论文; 计量史学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