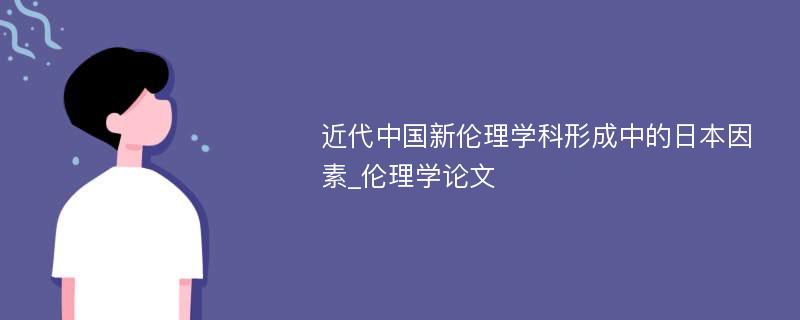
中国近代伦理新学科生成中的日本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伦理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因素论文,新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2 【文章编号】1003-4048(2016)01-0059-6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6/j.cnki.rbyj.2016.01.007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地缘上的接近,使日本受中国文化的恩泽甚多。鸦片战争前,由于汉文化高势能的地位,中国一直保持对日本的文化输出态势;鸦片战争失败后,汉文化地位一落千丈,日本则“脱亚入欧”,直接学习西方。明治维新后,日本学习西学卓有成效,其传统文化逐渐完成近代转型。甲午一役,彰显了日本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已领先于中国。由此,中日文化传播路径扭转为日本向中国逆输入。中国近代伦理新学科是在中西日文化的相互作用下逐渐生成,其中日本影响甚大。探究中国近代伦理新学科的生成状态,不仅可厘清我国近代伦理学萌生中的历史原貌,而且是研究近代中日文化互动与交流的重要切入点。 一、清末新式伦理教育的形成 虽然西方伦理学的大量涌入是甲午战后,但中国新式伦理教育的时间可追溯至19世纪早期。有学者研究,马礼逊在香港开办的英华书院开设的伦理课程是中国新式伦理教育的开端[1]。虽然新式伦理课在一些教会学校开设,但教会学校的传教宗旨决定其以介绍宗教伦理为主,以世俗伦理为辅。晚清时人对此批判道:“教会中人所作,以基督教为主,不合于中国之体。”[2]因此,来华传教士虽传播了一些西学伦理知识,但对中国近代社会影响十分有限。再加上清政府固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天道观,所以教会学校的伦理课对中国传统伦理触动不大。 真正触动中国伦理变革的是在甲午战后。由于甲午惨败,有识之士痛定思痛,认识到了日本文化教育的成功。康有为说:“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3]因此,以日为师,革新教育,成为甲午战后学界的普遍共识。在教育中,尤重德育,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国民素质的高低,而国民素质又决定着国家富强。正如严复指出的:“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4]基于这种认识,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人不遗余力地向国人介绍西方伦理新思想,倡导伦理新教育。 由于日本近代教育的成功,于是清末新式伦理教育也以日本为样板。国人对日本新式教育推崇备至: 今日欲救中国,不可不首从教育。欲从事教育,不可不取所长于最近最易之日本。此义人多能知之[5]。 甲午战后,清政府派出不少官员到日本考察教育,罗振玉、姚锡光和吴汝纶等官员都曾去日本考察。他们折服于日本学制的严密,回国后极力鼓吹日本学制优良,促成了清末学制的改革。清末新学制基本仿照日本拟定。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进呈《钦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略仿日本例定为大纲”,标志着中国近代学制的生成。“壬寅学制”明确规定: 中国圣经垂训,以伦常道德为先,外国学堂于智育体育之外,尤重德育。中外立教本有相同之理。今无论京外大小学堂,于伦理修身一门视他学科更宜注意,为培养人才之始基[6]。 因此,从蒙学到大学堂,一律设置伦理修身课,而且居各科目之首。这门课程在小学叫“修身”,在中学、高等学堂叫“伦理”。为何名称各异?1903年初,张百熙奏道:“惟修身偏重私德,伦理兼及公德。小学即课修身,应如原定,中学改课伦理。”[7]由于“私德”讲求个人修养,“公德”讲求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二者内容重点不同,决定了“修身”和“伦理”名称各异。《钦定学堂章程》亦说明了这种区别。“伦理”是“考求三代汉唐以来诸贤名理、宋元国朝学案及外国名人言行,务以周知实践为归”[8],“修身当本论语孝经之旨趣,搜以人伦道德之要领”[9],二者相较,“伦理”比“修身”范围广而学理深。因此,学校等级不同课程名亦不同理所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修身”的内容本于中国传统人伦道德,而“伦理”的内容除了中国传统伦理外,还要学习“外国名人言行”即西方伦理道德,已具近代新学的性质。另外,张百熙提出“中学改课伦理”,应是受张之洞的影响。1902年底,张之洞在《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中,建议小学设“修身”课,中学设“伦理”课,高等学校改修“道德学”。张百熙1903年的这篇奏折是回应张之洞的。他接受了张之洞的意见,“中学改课伦理”,但大学仍用“伦理”一名。而张之洞之所以有名称变更的要求,可能受了日本的影响。1890年西村茂树的《修身教科书说·附言》提及了日本关于“修身”与“伦理”的区别: 近五、六年间,有修身学、伦理学之名目,余不知其为何义。问某教育家,答曰:“修身学宜用于小学科者,英语(Moral)之译语;伦理学宜用于中学以上者,英语(Ethics)之译语。”[10] 可见,日本对于小学的伦理教育采用了“修身学”,对于中学则采用了“伦理学”,这种分野基本奠定了日本伦理教育不同阶段的学科格局。而张之洞和“壬寅学制”(1902年)对中国伦理教育不同阶段的命名,显然受到日本学科名目的影响。但中国学人对日本学科命名方式并不是全盘照搬,而是有所取舍。比如日本在近代学科命名时经常使用“……学”之类的后缀,国人在引进中仍按中国固有习惯,去掉“学”,而使用中国传统伦理固有名词“修身”、“伦理”来对应西方学科,足见浓郁的中国特色。“壬寅学制”由于制定过于仓促,再加上清廷内部权力倾轧,所以并未实施。1903年,张百熙、张之洞等人在“壬寅学制”基础上拟定了更完备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于1904年1月由清政府正式颁行,由此开始了中国新学制的实施。“癸卯学制”继承了“壬寅学制”有关伦理教育的内容,学科名沿用不变。这样的名称改订,基本奠定了清末伦理修身课名称的格局。 虽然清末十年社会上依然出现了“伦理学”、“伦理”等名称混用的状态,如麦鼎华将日本元良勇次郎的《伦理讲话》翻译为《中等教育伦理学》(1902年),蔡元培将德国哲学家泡尔生著的《Systemder Ethikmiteinem Umrissder Staatsund Gesellschaftslehre》翻译为《伦理学原理》(1909年)等,都采用了日译名“伦理学”。但无论是“伦理”还是“伦理学”,都具有了近代学科名的内涵,标志着近代伦理新学科的兴起。譬如1906年刘师培为新式伦理教育编写的《伦理教科书》就采用清政府拟定的“伦理”学科名来构筑中国近代伦理新学科。《伦理教科书》首次使用西方伦理学概念诠释中国传统伦理。刘师培将西方Ethics的五种类型(己身伦理、家族伦理、社会伦理、国家伦理、万有伦理)与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一对应。“大学言正心诚意修身即对于己身之伦理也。大学言齐家即对于家族之伦理也。大学言治国平天下即对于社会国家及万有之伦理也。”[11]显然,刘师培是按照西方伦理学体系改造中国传统伦理,力图使其成为一门具有科学意义的近代学科。他规划的伦理学框架展示了中国近代伦理学的雏形,因此《伦理教科书》被学者们誉为“中国现代伦理学的开山之作”[12]。 由此可见,在中日文化互动中,清末新式伦理教育的学科名逐步走向近代,这其中虽有日本因素的影响,但也体现了中国伦理教育的自觉选择。 二、日本对清末伦理新教材形成的影响 1905年科举制废除后,清末学堂急速增长。据统计,1903年学堂769所,学生31428人,而1910年学堂达到42696所,学生1284965人,分别增长了56倍和41倍①。学堂数量和学生人数的激增,引起了新式教材(包括伦理教材)的短缺,以致时人不断呼吁: 今日之急,莫急于开教科书局,编纂文武教科书及教程,方可供用[13]。 为了应急,一大批日文伦理教科书不得不火速翻译过来。1901年樊炳清翻译日本人井上哲次郎、高山林次郎合著的《伦理教科书》;1902年王国维翻译了日本人元良勇次郎的《伦理学》,樊炳清翻译了文部省的《伦理书》,麦鼎华翻译了日本人中岛力造的《中等教育伦理学》;1902年麦鼎华翻译了日本人元良勇次郎的《伦理讲话》(改名《中等教育伦理学》),范迪吉翻译了日本人木村鹰太郎的《东西洋伦理学史》,董瑞椿翻译了日本人秋山四郎的《伦理教科范本》;1905年王章述翻译了日本人中古延治郎的《伦理学》,胡庸诰翻译了日本人法贵庆次郎的《伦理学》等等。一些日本学者在中国教授伦理学课程中也编撰了不少伦理教材和讲义,如京师大学堂的教习服部宇之吉编写的《伦理学教科书》,法贵庆次郎编写的讲义《伦理学》等等。另外,一些中国学人出于教材的亟需,也想方设法编撰讲义和教材,如刘师培编撰了《伦理教科书》(二册),蔡元培编撰了《中学修身教科书》和《中国伦理学史》等。 清末伦理教材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直接从日本翻译的教材。据笔者统计,在1898-1912年编写的88种教材中,直接标注从日本翻译的伦理教材就达18种。由于是直接翻译,所以教材中的章节、体例、用词、语气等内容与日文原本几乎一模一样。 二是虽标明中国人编著的教材,但基本是由日本转译而来。如1909年“四川速成师范学生编有《地理总论》、《外国地理》、《行政法大意》、《算术》、《法学通论》、《西洋史》、《教育学》、《教育史》、《伦理学》等多科讲义,多译自日本,曾由四川提学使送学部审查,以取材适于日本化,经学部批斥”。“同年,孙清如著《女子修身》、《家政学》、《管理法》、《教育史》等书,均译自日文,多为日本人说法,学部批准作为参考书。”[14]可见,当时一些标明国人所著的教材,其实是编译作品,来源日本。只是出于各种原因,在教材归属权上标识不清罢了。即使编撰教科书最负盛名的商务印书馆,在清末出版的伦理教科书中,也深受日本影响。《教科书之发刊概况》介绍了商务印书馆在清末编译教科书的一些情况: 同年(1902年,笔者注),商务印书馆聘高凤谦为编辑所长,由蒋维乔计划,请日本人长尾、小谷、加藤三人协助,由刘崇杰任翻译,高凤谦、张元济、蒋维乔、庄俞任编辑,经半年成《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一册。该馆又依照学部新颁章程所定学制,将最新教科书陆续分编为初等小学及高等小学两套。其最新初等小学教科书,除上列国文教科书十册外,有杜亚泉等编之《格致》三册,张元济等编之《修身》十册……其最新高小教科书由张元济等编之国文八册……高凤谦等编之修身四册……[15] 可见商务印书馆在编辑教科书的过程中,请来日本人相助。日本人在编辑中自然按照日本教科书的编排体例和内容结构编写,所以这些教科书必然或隐或显地带有日本痕迹。因此,当我们接触清末国人编著的一些作品时,乍一看以为是国人的专著,其实大都是来自东洋的舶来品,或多或少地夹杂着日本特色。 三是确为国人自己编写的教材,但大都受日本影响,如刘师培的《伦理教科书》,蔡元培的《中学修身教科书》等等,书中关于道德起源的认识、伦理的类型、伦理概念范畴的界定等都来源于日本,甚至连教材的编排体例也仿效日本。 所以,清末伦理新教材虽然琳琅满目,种类繁多,但几乎都受日本影响②。因此清末传播的西方伦理学,基本上是日版的“伦理学”。为什么出现这样奇特的现象?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甲午战败,促使中国不得不以日为师,模仿日本教育及教材。甲午战后,日本学习西学迅速强盛的事实,颠覆了中国人视之为“蕞尔小国”的观念。日本教育改革之成功,人才之兴盛,让中国人艳羡不已。取法日本,已成为甲午战后国人的共识。取法日本,人才培养是重中之重。因为在智力并争之世,朝廷的维新变革,国家的富强之治,都需要大量优秀人才作支撑。而考察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教育之制度,几经考查试验改修,以至今日。其间始事之经营,逐年之进步,成事之可稽,历然在目,实足为我先路之导,欧美诸国未有如此若合符节者也”[16]。因此,仿效日本的学校教育之法乃至教材编写方法,甚至直接采用日式教材,在国人看来都是合宜的。而日本伦理教育与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同源共生性,又使国人乐于借鉴。闽浙总督魏光焘的奏章清晰地描摹出国人效仿日本伦理教科书的心态: 近年日本骤致强盛,实有全国人忠君爱国之心,观于明治二十三年,所颁之教育敕语,及其国人之伦理教科书,皆本中国古圣贤所述之伦常道德,以为根本,用能强国势而固民心。足见其各项科学虽多取法欧美,而德育一科,仍必资我圣教。中国近年学生,往往习于嚣张恣肆,殆于圣贤根本,先未请求,于蒙养之年,无以育成其孝、悌、忠、信之气质。微臣愚见,拟请将中国经书,小学及日本之伦理书,互相参酌,择要编辑,定为《中国伦理教科书》[17]。 在以日为师心态的左右下,清末的伦理教科书大都兼采中西伦理之长(主要仿照日本伦理新学),具有近代伦理的新质。况且“日本言政、言学各书,有自创自纂者,有转译西国书者,有就西国书重加删订酌改者,与中国时令、土宜、国势、民风大率相近。且东文、东语,通晓较易,文理优长者,欲学翻译东书,半年即成,凿凿有据。如此则既精而且速矣”[18]。中日同文同风的便利,致使清政府乐于效仿日本教科书来编辑中国课本。但正如魏光焘指出的,这种效仿不是全盘照搬,简单复制,而是将中国经学、小学与日本伦理相互参酌而成,因此具有中日融合的鲜明特征,是中日文化共同作用的成果。 二是清末伦理教材编撰者大都留学日本,他们所编撰的书籍自然具有鲜明的日本色彩。甲午战后,中国日益羸弱,而日本一跃为可与西方列强较长短的强国。这一变故深深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在后进效法先进的信念下,中国学子纷纷赴东洋留学。虽然甲午战前,清政府也向欧美派遣了少数留学生,但前后不到两百人。甲午战后,这一局面彻底改观。由于日本较欧美路程近,学费又低廉,况且中日同文,种种便利使留日学生激增。据统计,1900年,中国仅有13名学生赴日留学;1902年,留日生猛增到1300多名;1904年又翻了两番,人数达5000多人;1906年又翻了一番,有1万多人。可见青年学子赴日之踊跃。这些留学生,多为清政府派遣,亦有一部分自费留学。如内陆省份山西,在1904年派遣五十余人留学日本。出发前,晋省张中丞训诫曰: 晋省山河四塞,民生不见外事,风俗之朴厚,性情之循谨,均非他行省所及。今诸生复慨然奋发,违故乡,踔大海,以从学于异域。异日成就,尤难限量……望诸生力防乎歧途,潜心乎大业,学成归国,上以分朝廷之忧,下以备晋省之用[19]。 交通信息闭塞的山西,也派学生东渡日本求学,可见晚清留日热潮之高涨。对于官派留洋的学子,清政府也有严格要求,“限三年之内,每人译书若干种,每种若干字,回华缴呈,不得短缺;短缺及过少者,不准保举”[20]。因此,留洋学子纷纷译书或编书。清末伦理学著作的翻译者赵必振、范迪吉、樊炳清、王国维等人都曾留学日本。当时在留日学生中还兴起了大规模译介教科书的活动。留日学生成立了几个重要的翻译团体,如成立于1900年的东京译书汇编社,1902年的教科书译辑社、湖南编译社、上海支那翻译会社等等,都翻译了大量日文教科书。尤其是范迪吉等人选译的日文教科书多达一百册,内容涉及伦理、文学、政治、历史等多个学科,门类齐全,内容丰富,在当时颇负盛名。因此,以留日学生为主力军,清末伦理教材被大量编译或辑成,其日本色彩自然浓厚。 三是日本为了控制中国教育权,热心推介日文教科书和日文教习,使清末伦理教材不可避免受其影响。甲午战败,日本一跃为亚洲强国。它除了通过《马关条约》攫取中国巨额赔款外,还欲通过教育影响控制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报纸日日宣传如何控制中国教育权。他们说: 今日支那,渴望教育。机运殆将发展,我国先事而制其权。是不可失之机也。我国教育家苟趁此时容喙于支那教育问题,握其实权,则我他日之在支那,为教育上之主动者,为知识上之母国。此种子一播,确立地步,则将来万种之权,皆由是起焉[21]。 可见,日本野心勃勃,它帮助中国发展教育,是欲以控制中国教育权为起点,进而控制其他诸种权利。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日本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日式教科书,并邀请清政府官员考察日本学制,还向中国派遣大量日本教习。服部宇之吉等教习即在这种情况下被派往中国。由于清末新式学堂激增,各学堂都缺乏合格师资,再加上日本教习比欧美教习薪资低廉,因而清政府也乐于引进日本师资。据统计,1906年日本教习在中国已达五百多人。以后略有减少,但1909年仍有三百多人。这些教习任教期间感到教材匮乏,纷纷给中国推荐各式日本教材,他们甚至亲自编写讲义,以供教学。如服部宇之吉编写的《伦理学教科书》起初只是一个讲义,后由学部审定,1909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该书民初时仍受教育部器重,给予批语道:“此书出版在数年前,久为世重,自今论之,能举伦理学大要,发挥中国道德特色,仍与学校课程标准相符,准为中学校伦理学教科用书。”可见对于一些日本人的教科书,中国政府还是比较满意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日本人在中国编撰的教科书还是国人引进的日本教科书,书中既有浓厚的日本味道,又散发出浓郁的中国气息,如服部宇之吉的《伦理学教科书》均能“发挥中国道德特色”,否则难以得到官方认可,也不可能在社会上堂而皇之流行。因此,清末社会上流行的伦理新教材几乎都是中日合璧的结果。 三、日本在中国近代伦理学核心术语生成中的作用 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先生指出,“中外历史上产生的术语,是学术发展的核心成果,人类在科学及技术领域的每一项进步,都以术语形式在各种自然语言中记载下来,一个专业的知识框架,有赖结构化的术语系加以构筑。因而,术语,尤其是术语系,成为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的宝库,是精密思维得以运作、学科研究得以展开的必要前提。”[22]中国近代伦理学核心术语是构建中国近代伦理学的重要基石,也是其茁壮成长的重要支撑。 从中国近代伦理学核心术语的生成过程来看,除少数伦理术语属于中西伦理共有,是直接对接形成的外,中国近代伦理学绝大多数核心术语是从日本“贩卖”而来。 中国近代伦理学核心术语为何贩自日本?这是因为日本自明治初年开始接触西方伦理学,经过三十多年消化吸收,19世纪末已形成较为成熟的近代伦理学。日本在学习西方伦理学过程中,也碰到一些西学术语无法在日语中找到直接译词。对于这些概念,他们首先采用音译,后来为了概念精准,又用表意准确的双字汉语词表示。这样,日本学者通过创造新词、旧义翻新等手法,创制了一大批汉字新名词对译西方伦理术语,所以西方伦理学的一些核心概念首先由日本翻译,如伦理学、道德、义务等,这些新名词被称为“和制新术语”。 而甲午战后,有识之士认识到要救亡图存,就必须开启民智、培养具有新道德的新国民。因此引进西方先进伦理迫在眉睫。但中西语言不通,要想掌握西方伦理精粹谈何容易?正当国人进退两难时,一些启蒙思想家发现日本几乎汲取了西方文明(包括伦理文明)的精华,我国可借助日本而登西方文明的堂奥。正如康有为所说:“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本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23]日文西书的完备与精要,使中国人如获至宝,这是国人以日本为中介学习西方伦理的首要原因。况且中日文字相近,为国人阅读日文书籍提供了很大便利。因此,清末学人热衷于以日本为中介学习西方伦理学。 随着国人引进日本伦理学,“伦理学”、“义务”、“博爱”、“理想”、“人生观”等日本新名词也联翩而至。这些名词是日本学者对译西洋概念时创制,经过中国学人的转换,成为汉字“新名词”。晚清瞿铢菴的《木屯庐所闻录·新名词》记载了这些名词的由来: 当时新政皆自日本稗贩,而译者未谙西文原义,又不通古训,一概直袭,若文襄者,固未可厚非也[24]。 由于中国译者中西学问有限,因此对于日文汉字不加辨识,一概直袭,导致日本新学语大举入华。可见,日本充当了西洋术语概念入华的“二传手”。著名文字学家杨树达曾阐释了中西日语言的互动状况。他说: 盖日本文化本受自中华,近数十年来,始又和剂之以西欧文化。吾国语言一时蒙彼之影响,实则间接受欧洲之影响耳[25]。 中国近代伦理学绝大部分核心术语正是在中西日文化的互动中涵化而成。 日本新学语之所以能大量进入中国且广受社会欢迎,一方面由于这些新学语符合汉字构词习惯,又同为汉字,易为中国人接受;另一方面由于它们表意准确,又在日本历经锤炼,学名已比较成熟,非普通译者所能擅改,以致时人感叹:“(吾国人)学有所得,复编译新籍,以惠国人……所惜者,名词艰涩,含旨精深,译者既未敢擅易。”[26]“未敢擅易”虽突显了中国人沿袭日译名的窘态,但也折射出日译名的准确和精深。对此,王国维赞道:“日本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者也。窃谓节取日本人之译语,有数便焉:因袭之易,不如创造之难,一也;两国学术有交通之便,无扞格之虞,二也。……有此二便而无二难,又何嫌何疑而不用哉?”[27]日译名的精准和便利,使其在中国不胫而走。但是日译名能够转化为中国近代伦理学核心术语,也在于它与中国学人的伦理认知高度吻合,是中国学人反复斟酌、主动选择的结果。譬如“善”的学名厘定。在16世纪至18世纪的第一次西学东渐中,耶稣会士利玛窦、庞迪我等人传播宗教伦理时,就用“善”来指称西方的“Good”,如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说:“善纯备无滓,而为众善之宿。”[28]“善”即指“Good”。但随着第一次西学东渐的夭折,以中国之“善”来对接“Good”的进程给戛然而止。 中国“善”近代义的再次生成是在清末。其生成路径有二: 一是直接与西方对接,如严复1903年翻译《穆勒名学》、《群学肆言》和《群己权界论》都直接以“善”对译“Good”,但严氏翻译的“善”数量很少(总共才十来处),涵义单一(基本上只有“善良、好”的意思),而且严氏的翻译有可能受到第一条路径的影响,因为1902年借用日文汉字“善”来翻译“Good”已在中国蔚然成风。所以,就翻译的成果和影响来看,中国“善”的近代义的再次生成主要依靠的是第二条路径。 二是输入日本新名词。中国近代学人如梁启超、王国维、麦鼎华、刘师培和蔡元培等大都有过留日经历,熟稔日本新学,所以在新概念翻译中,受日本影响很大,经常借用日本新名词来对译西方伦理新概念。如麦鼎华翻译日本元良勇次郎的《伦理讲话》(麦氏译为《中等教育伦理学》)时,直接将日文汉字“善”译为“善”。元良勇次郎在《伦理讲话善恶的标准》中写道: 然らほ善とほ如何なる事なるか。……宇宙の理に适ふ所即ち是れ善なりと云ふものあり、神の命ナる所即ち是れ善ななりと云ふものあり、或ら自人情つ向ふ所を善なりとするものあり、社会の安全を维持する事を善なりとするものあり[29]。 麦鼎华译为: 然徒问何为善?……或云适于宇宙之理则为善,或云神之所命即为善,或云人之所向则为善,维持社会之安全则为善[30]。 显然,元良勇次郎阐述的“善”就是西方“Good”的概念,其内涵与古汉语“善”义无涉,而他借用汉字“善”来翻译这一新概念,显然是对“善”义的引申。麦鼎华在日中对接中,把日文汉字“善”移植过来,旧瓶装新酒,使中国古汉字“善”焕然一新,蜕变为对接西方伦理的新术语。 刘师培在《伦理教科书》(1906年)中,也多次使用“善”。他除了使用中国古代伦理中“善”的原义“善良”、“德”等外,还在《释服从》等篇中阐述了“善”的新内涵:“人生有欲,所以利己也。及与事物相接,有利于己,则谓之善;无利于己,则谓之恶。”[31]这里的“善”就是霍布士代表的西方利己主义关于“Good”的内涵。刘师培的“善”与“Good”概念的高度契合,正反映了他以中学阐释、比附西学的治学理路。至此,作为中国近代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善”,其涵义和学名在《伦理教科书》中基本定型。可见,“善”的学名是在中西日文化互动中生成的。其中虽受日译名的巨大影响,但我国学者亦结合古义,主动甄别,才推动中国伦理新术语的诞生。除“善”之外,“道德”、“义务”、“幸福”、“博爱”等核心术语的生成情形也大抵如此。 综上所述,日本对清末伦理教育课程设置、教材编写使用和中国近代伦理学核心术语的生成确实有着直接而重要影响,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学人亦参与其中表达了自身认识和选择,使清末伦理新教育糅合了中国元素,具有中国气息。而新式伦理课程的开设、新式伦理教材的使用和中国近代伦理学核心术语群的形成,标志着中国近代伦理新学科在清末的萌生,这一新学科的生成就是中西日文化交互作用的结果。 注释: ①根据清学部总务司文书科编订的《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第二次教育统计图表》、《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东方杂志》第9卷第7期(1912年)的《中国政治通览·教育篇》、陈青之《中国教育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以及王笛《清末近代学堂和学生数量》等资料统计。 ②笔者依据徐曼《西方伦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中的表3-1、黄兴涛的《清末新式学堂的伦理教育与伦理教科书探论》中57-58页的表、《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中小学教材)》、《教科书之发刊概况(1868-1918年)》以及《高等学校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国际合作计划(民国图书)》等材料统计,在1898-1912年所编的88种教材中,只有4本是国人或传教士翻译的英美德等国的伦理学作品,如王国维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要》(英国西额惟克著),林乐知翻译的《人学》(美国李约各著),蔡元培翻译的《伦理学原理》(德国泡尔生著),林万里翻译的《自助论》(又译《西国立志篇》,英国斯迈尔斯著),但后两本著作都是从日文本转译过来的。